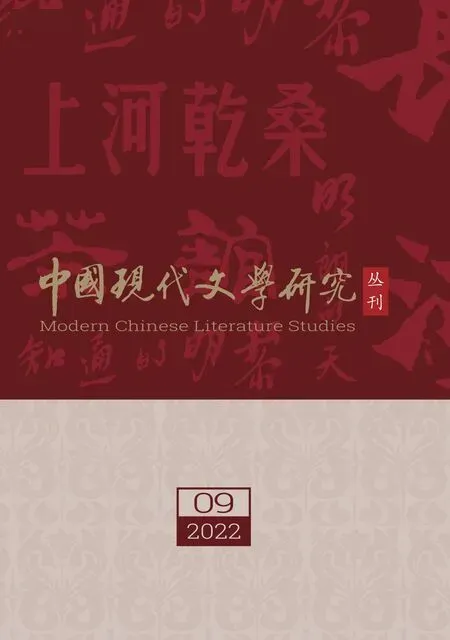从“师母”形象看阿袁的小说创作※
王澄霞 吴嘉瑜
内容提要:《师母》标志着阿袁高校知识女性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突破。沿用“师母”称谓暗含新旧并行的矛盾。小说中高校女性对“师母”称谓的态度,揭示她们似进实退的内心状态以及心理禁锢。庄瑾瑜、鄢红、朱周不同的形象特征,表明以“师母”为代表的女性群体的生存困境与内心动荡。散见于中短篇的“师母”成为长篇的主角,实现类型人物的整合与丰富;深耕高校题材,融合市井题材,使得“师母”形象实现知识女性和小镇/底层女性的身份拓展;超越女性个体意识,在“师母”等形象中寄寓对女性群体命运的思考,呈现主情到主理的创作转变。
本文聚焦阿袁201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师母》中的“师母”形象。首先,研究“师母”称谓,分析现实生活中该称谓的使用情况和相关问题,以及小说中高校女性自身对该称谓的看法态度,从内外双重视角发掘“师母”形象背后女性的生存困境;其次,针对小说最主要的三个“师母”形象,探讨高校内部婚姻情感生活的多种样态,强调她们应对两性问题时异中趋同的精神内质;最后,将《师母》置于阿袁创作史体例、题材、主题等方面的系统性调整中,探究“师母”形象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一 “师母”称谓研究
(一)社会大背景下的矛盾:新旧并行
《师母》中的“师母”,是学生对男教师配偶的敬称。随着社会进步和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一称谓的落后性和局限性日益凸显。古代女性地位低下,没有受教育权,无论学生还是老师,大都是男性。师生关系等同父子关系,老师的配偶自然就对应母亲身份,“师母”称谓由此产生。20世纪以来,女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地位显著提升。“师母”称谓遮蔽了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个体形象。
从应用语言学角度,“师母”对应称谓的缺位问题由来已久。从现实情况角度,“师母”称谓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交际需求,又因巨大历史惯性被继续沿用,折射出社会转型阶段的矛盾观念。
(二)高校小环境中的心态:似进实退
“师母”在小说中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知识女性。庄瑾瑜和朱周既是师大教职员工,又是教授妻子,都不喜欢被称为“师母”。庄瑾瑜反应最强烈,她瞧不起鄢红和朱周,语带轻蔑讽刺地称她们是孟师母、沈师母。朱周对庄的恶意心知肚明,便学小贩声调喊庄瑾瑜是胡师母。庄瑾瑜、朱周对被降格为“师母”的反感和抗拒,能体现其进步。第二类是小镇或底层女性,鄢红仅凭与教授丈夫的婚姻关系住进师大,从打工女变成全职主妇,实现了阶层跃升,她对师母身份无比满足。从表层看,这是由于她受教育程度有限,缺少知识女性的认知能力;从深层而言,鄢红作为男权体系的实际受益者,也是其忠实拥护者。
细究高校知识女性有关“师母”的表现,会发现她们似进实退的心理状态。一方面,知识女性对“师母”称谓的抗拒被她们限制在私人纠葛中,具体表现为庄瑾瑜和朱周日常见面时的言语争锋往往是意气之争,唯一一处观点表述流于片面,庄瑾瑜指出“师母”称谓,使女性丧失了主体价值,可谓一针见血。问题是,庄瑾瑜为代表的这些知识女性的独立观念既不彻底也不统一。朱周为代表的知识女性,虽也反对标签化的“师母”称谓,但论学历、职称这些新标准,她都逊于前者,于是就借重色容、婚嫁等传统标准替自己辩护助势,自认为此举能扳回一城。她们都落入困扰女性千年的历史旧辙当中,强化了当代女性的“他者”属性。在以“师母”称谓为代表的男性主导话语体系变革之前,新标准糅合旧规条,成了压迫女性的又一重枷锁。另一方面,知识女性很难和“师母”称谓彻底决裂。系主任胡丰登总对博导杨老毕恭毕敬,对杨师母更是百般讨好,殷勤备至,就因师母能量不容小觑,往往能干预丈夫录取学生的人选结果。庄瑾瑜之流排斥鄢红,一来是社会地位不能相提并论;二来根本利益的冲突让她们难以相容,鄢红作为年轻的后妻,挑战了发妻师母同盟,让庄瑾瑜们深感婚姻江山连同“师母”称谓随时可能换代易主。
知识女性对“师母”称谓的迎合乃至追捧,既出于自愿也有无奈,大众的刻板印象抬高了师母的社会资本,形成了负担和束缚。鄢红明白家乡传言和现实处境的差距,但她还是以传言形象和同乡前男友见面。人们会把“师母”与母亲的勤劳善良、师者的严谨博学相联系,庄瑾瑜等知识女性不得不隐去个性,压抑自我。
二 “师母”形象分析
(一)庄瑾瑜的败局——镜城之困
在“男权至上”和“女为悦己者容”的封建时代,女性难逃被置镜前的命运,她们是“被看”“被窥”的客体,镜子是实现男性凝视的道具。戴锦华以“镜城”喻指男权传统构建的文化堡垒,表明当代女性确立主体地位的突围之路艰难重重。
阿袁笔下的高校知识女性大多自恋。但自信与自卑总是相伴相生,尚待确立的现代女性形象和历史与传统投下的阴影相交缠,使得高校知识女性身处矛盾中。师母庄瑾瑜就是此类形象的典型。庄瑾瑜喜欢揽镜自照,她一边高傲地进行自我标榜,一边谦恭地随侍男性身侧。高校知识女性虽已经具备自我体认、欣赏的主动意识,但她们要为镜中一颦一笑寻找价值时,仍会下意识地向男人邀宠,再次投入男性视角。庄瑾瑜更擅长和享受的是以人为镜。拉康指出主体先通过镜中影像实现自我初步认同,然后受他人影响,以他人为镜完善个人形象,把自我他者化。基于“自恋式”想象的认同构建起来的自我,实质是伪我。阿袁借创作谈发问:“你生活着谁的生活?”违背真实的形象迟早会受到真实的冲击,原本辅助确立自我的镜像,变成了使人逐步抹杀自我的诱因,这种异化就是自恋者的困境。
镜像和实像第一次爆发冲突,是庄瑾瑜发现丈夫对着他的美貌学生吕小黛的照片自渎。尽管悲愤交加,她考虑的却是不能让丈夫知道自己已经知情,庄瑾瑜畏惧的不单是打破“夫权”这一面镜子,还有此举在“男权”之镜的城池中引发的连锁反应。于是她选择默许丈夫自渎,暗中阻挠吕小黛考博,保持师母风度直至其毕业离校。
第二次冲突是在旁人探问下,庄瑾瑜得知胡丰登力促吕小黛留校工作。但庄瑾瑜照旧为丈夫做饭,俨然岁月依旧静好。主观镜像和客观实像的反差,造成了自我意识的分裂和精神的扭曲:自我退居一隅,冷眼旁观本我恣意主宰的这具躯体在镜前继续表演。庄瑾瑜对内表现为自我摧残,对外则表现为毁灭他人。“女人的幸福,不都是建立在别的女人痛苦之上吗?”①阿袁:《师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7页。可转嫁痛苦所得的快意,根本无法扭转她的婚姻败局。
庄瑾瑜和胡丰登的故事,宣告了才子佳人式爱情的退场,合伙经营式婚姻的高张。庄瑾瑜的败局揭示了女性群体受困于镜城的普遍性,正应了阿袁创作谈里的总结:“对女人而言,或许自己真正的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别人眼里,她过着怎样的生活。”②阿袁:《创作谈:你生活着谁的生活》,《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5年第4期。
(二)鄢红的侥幸——文化宿命
鄢红是地理意义上的高校女性,心理意义上的小镇/底层女性。鄢红原名鄢雉,生于小镇辛夷,出走省城本是想挣脱“家”的束缚,体验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痛苦后,她设计嫁给离异教授孟一桴,复投“家”的怀抱。改名鄢红,意在与过往一刀两断。但她身处高校却无法融入知识分子群体,内心认同辛夷,又因高傲心性成为故乡的过客。鄢红身上折射出两种不同社会力量的交集:高校知识分子秉持的现代精英意识,看似握有社会话语权,辛夷人信奉的传统世俗观念则盘踞民间,象征着一种幽深广大,无可挣脱的文化宿命。
鄢雉信仰理想主义,一心摆脱辛夷,却遭逢人生失意。高考落榜的鄢雉不愿听从父母安排,受男同学陈良生鼓动来到师大旁听,践行文学理想。在陈的灌输下,鄢雉辛夷式的传统道德观破防,从身体到思想都被征服,开始与陈同居,却在情感关系中越发尴尬被动。鄢雉遵循现实主义,借助辛夷传统,迎来人生的峰回路转。打工生活愈是压抑难捱,鄢雉的内心欲望就愈是膨胀。离异的师大教授孟一桴的出现,让她下定决心以婚姻为跳板来个咸鱼翻身,皈依辛夷式的传统女性之路——婚嫁为重,夫贵妻荣,成为孟师母,成为鄢红。
这种文化上的宿命轮回耐人寻味:都市代表的现代文明何以造成人性滑坡?辛夷代表的传统伦理为何在省城高校仍然适用?难道承认宿命安于宿命,才是女性获得幸福的不二法门?
孟一桴的高知前妻小北追求男女平等,全心投入事业,对婚姻有更高的物质要求而非情感需求;马骊深知消费社会男女终有别,索性加入游戏,凭借性别优势博取利益。孟一桴面对这两位知识女性,经济、事业、情感全部处于被动的状态。而鄢红谨遵男性权力规约,这就是鄢红以弱胜强的最大秘诀。
胡丰登“不爱”庄瑾瑜的理由之一,是认为她从性格到长相都过于强势。但他未“休妻再娶”,而是把干练的妻子放在明处,把佳人置于暗处。若非小北主动要求离婚,孟一桴夫妇的婚姻也能像庄瑾瑜夫妇那样维持下去。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与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便是辛夷文化在高校环境中如鱼得水,甚至生命力更强的根源所在。
鄢红对幸福生活由衷的不安是因为在这场强弱悬殊的婚姻中,裁判权、选择权和最终解释权都归属男性。在由父权统治的文化历史中,女性永远是这样的命运。
(三)朱周的清醒——幸福哲学
在师母群体内,尤其在庄、鄢二人旁衬下,朱周的婚姻生活堪称美满顺遂。师母朱周有着自己的幸福哲学:一是享乐主义,遵循快乐原则,追求本我欲望的满足。二是奉行自由主义,洒脱随心,摈斥虚假,宁可得罪领导也不委曲求全。三是个人主义,致力于维护自身权利,带有温和的利己主义色彩。朱周对丈夫沈岱宗的情,其实源于对自己的爱。她与丈夫在精神上志同道合,在物质上互相满足,能同进退。以自我利益为前提,爱自己胜过爱男人,是她认识到女性现实处境后做出的清醒决断。
阿袁曾在处女作《长门赋》结尾修改钱氏的“围城”理论:“那些想出来的其实都是男人,女人却是守城者——守住里面的男人,也守住外面的女人。”①阿袁:《长门赋》,《上海文学》2002年第6期。阿袁在《师母》中塑造的朱周,进化为拥有替代性经验的守城者,即便男人的爱从未远离,女人也能未雨绸缪。朱周的底气来自于谋略,来自于她对丈夫对周围其他夫妻的透彻了解。庄瑾瑜把世间婚姻比作张爱玲口中爬满虱子的华美衣袍,朱周身上的虱子不过藏得更隐秘,或许也是阿袁在小说中的暗示和留白。
说到底朱周只是个守城的女人,本无走出围城的想法。朱周的幸福哲学可实施性又有多少?阿袁安排这场乌托邦式婚姻喜剧的用意值得反思。
三 “师母”形象意义
(一)类型人物的再发掘
阿袁表示自己塑造“师母”形象,是想给文学的人物群像图谱添枝加叶。阿袁的小说早就蕴含“师母”形象因子。《长门赋》里的小米和陈青,《虞美人》里的陈果和虞美人,都兼教师和师母双重身份。彼时阿袁所写多是女教师间抱团取暖或损人安己的日常故事,尚未生出塑造“师母”形象的自觉。
阿袁笔下第一个真正的“师母”形象,是《俞丽的江山》中的俞丽。这则高校故事本质上是两个女人的战争,师母被定义为婚姻江山的守卫者。阿袁之后的小说中师母退居客位,给青年教师兼硕博士生的女主角作配,二者间的攻守之战亦反复上演。除了师母和女学生的对峙关系,还有师母内部的明争暗斗。陈师母对吕师母家的女婿关怀示好,意在让吕家翁婿的冲突升级,这是双方丈夫积怨对抗的延伸(《鱼肠剑》);得到丈夫授意,陈师母设计让苏师母撞见女同事前来找寻苏老师,意在引发苏家夫妻争吵,这也是陈苏两位丈夫由来已久的矛盾所致(《子在川上》)。
小说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评点“师母”形象,把师母框定为高校“第二性”,加剧了女性的异化危机。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阿袁小说为人诟病之处。作者的文学理念和写作策略有其不足。阿袁认同《繁花》作者金宇澄的说法,即“中国传统最漂亮的小说、笔记体都是八卦”②古欣、金宇澄:《写人与人永远的不同》,《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2期。,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小市民,阿袁的高校知识分子,虽然披着文化的神圣外衣,内里无不是热衷八卦的凡夫俗妇。两位作家皆以说书人口吻叙事。阿袁取法话本小说的全知叙事,其洞若观火的叙述风格符合书场情境。文学理念和写作策略成就了阿袁独树一帜的高校题材创作,却也阻碍了人物形象更进一步的立体塑造,导致“师母”在反类型化书写之后陷入又一种类型化。
《师母》一反高校题材的写作常态,同时也打破阿袁对该题材的写作惯性,长期景观化的师母群体直接登台发声,按阿袁的话说:“至少她们在我的小说中,是哈姆雷特了,而不是奥菲莉娅。”①吴佳燕、阿袁:《没有谁比女人更知道爱的存在和虚无》,《长江文艺》2019年第9期。在“师母”形象再发掘的过程中,阿袁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高校女性的婚恋困境,高校知识分子文化品格的失落,传统价值标准在高校的回潮等。有评论说阿袁小说止于现实,缺乏超越,这是对其创作理念的误解。第一,阿袁走的是世情小说的路数,作者只是提出问题,并不提供答案。第二,阿袁本人认为站在女性立场写她们的隐忍、失败,是为了反映女性当下的真实处境与主流状态,起到刺激和警醒作用,捏造成功女性形象反而是麻痹大众,不负责任的做法。
其实阿袁为这部长篇小说所做的改变很有限,除三个主要角色,其他次要形象给人面目雷同之感。即使这些次要形象在细节填充上不惜笔墨,场外叙述上强化翻新,仍给人似曾相识之感。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是阿袁小说初见惊艳的原因之一,也是其不耐多读的症结所在。阿袁小说在叙述内容和形式上夺人眼目,在思想内涵方面开掘不深,余味不足,给人油滑印象。
(二)高校题材的延展
格局有限,是研究者对阿袁小说的普遍评价。阿袁本人却很坚定,阿袁近二十年的写作始终围绕高校,大多数小说有共同的人物和空间设定——知识女性和师大,这已然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阿袁所长是互文性中短篇。“师大”作为特殊的文化符号,极具文学性和表现张力。师大的硬件与自然环境,在情节需要时才有衍生交代。如西门外的生活区,是小米大隐于市,回绝男学生示爱的地方(《长门赋》),也是俞丽约见老孟,旧情复燃的地方(《俞丽的江山》)。师大的人事环境,则会通过教职工群像塑造进行插叙。长篇小说《师母》同属“师大”系列故事,阿袁在这方熟稔而狭窄的空间内腾挪翻覆,借陈良生撺掇鄢雉租房同居一事,阿袁着重介绍了师大西北两区,颇似风月宝鉴的正反面……阿袁从师母鄢红的视角,回忆小镇高考落榜生鄢雉的旁听生活,看似一体,实则两声,在过去和现在的意识交叠间,完成了对师大的“赋魅”与“祛魅”。
中文系主任陈季子代表官僚化学者形象,折射了中国大学的权力和文化生态,即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倾轧,以及儒家重事功和道家尚无为的文化性格冲突。《师母》中阿袁安排陈季子将权力让渡给胡丰登,胡得势后打压同僚的举动,与陈季子如出一辙。但有庄瑾瑜居间谋划,把陈季子式的“阴谋”改换为“阳谋”。从女性情感经验出发观照男性的政治生命,既体现权力运作的周而复始,也表明权力的诱惑力并无性别之分。
阿袁还致力于开拓高校题材以外的市井题材,“辛夷”系列故事日渐丰满。阿袁频繁化用王维《辛夷坞》,以寂寞盛开又黯然凋落的辛夷花,喻指中年知识女性的生存境遇。《俞丽的江山》《汤梨的革命》等早期作品明显有阿袁自身的经历和情感投射,“辛夷花”成为作家兼高校女教师内心世界的直接剖白。2011年的《子在川上》可视为阿袁创作历程的一个转折点,大家开始关注社会大环境和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意识到“多数的女子都是王维《辛夷坞》里自开自落的辛夷花”①阿袁:《细数风流》,《牡丹》2021年第1期。。阿袁小说出现了另类的小镇/底层女性形象,一个名叫“辛夷”的市镇呼之欲出。
《姹紫嫣红》《守身如玉》《打金枝》三部小说见证了阿袁在两类题材间的调试。《姹紫嫣红》写辛夷故事,但对底层女性形象把握不足,导致与女主角命运攸关的一系列情节发展缺乏内在逻辑。意识到没法“贴着写”纯粹的底层女性,阿袁改变策略,在《守身如玉》里塑造了小镇出身的知识女性形象,用第一人称孩童视角写辛夷故事,来弥补前作的不足。《打金枝》由《米红》《米青》《米白》三个中篇系列组成,用师大故事辅衬辛夷故事,阿袁在《米红》《米白》篇生动描绘了辛夷风物,《米青》篇又回归高校故事的经典模式,这种时空转变使得情节衔接稍显凌乱,拼凑的痕迹较为明显。
《师母》用辛夷故事辅衬师大故事,是一次较为成功的调整。鄢红兼具两类女性的特质,起到了关键作用。生在辛夷,她不像顾嫣红、米红、米白这类小镇/底层女性轻易安于现状,但无法像顾姹紫、朱小愚、米青一样靠着读书跳出小镇,只得逐渐屈从现实。阿袁安排鄢红充当师母群体内的异质力量,采用意识流写法,借助其心理活动把“辛夷”嵌入“师大”,在保持叙事空间一以贯之的同时完成了题材整合,也做到了环境与人物的相辅相成。
(三)主情到主理的转变
20世纪女性写作取得长足发展,先后出现两次高潮:一次是“五四”运动时期,一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男性写作者不同,对于每个女性写作者来说,个人的生存经验对其书写内容有着先验的指导性意义。而男性写作者却可以依仗其强大的文学写作传统,以理念为先导来操纵具体的文字创作。女性的写作却多半要由自身经验出发,权衡自己在重重密布的传统宗族宗法秩序中的身份地位,谨慎落笔小心出手。”①徐坤:《文学中的“疯狂”女性: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这是“五四”女作家遭遇的困境,也是现代女性驾驭作家这一全新社会身份所要面临的挑战。阿袁小说带有女性写作的明显特征,实现了从主情到主理的转变。
阿袁坦言《长门赋》有点像日记,当时她30岁,正处于人生低潮期,有种进退失据的悲伤,对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私人化写作”确有承接。阿袁着力描述性别体验,仍是重复书写着女主人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不幸和感伤,并未挑战、颠覆男权话语下的传统女性形象。阿袁前期代表作《俞丽的江山》、《郑袖的梨园》和《汤梨的革命》,同样弥散着幽怨之情,逐渐克服了“私人化写作”的弊病,转而关注女性群体的生存境况,把她对社会、世界、生命的思考加注到女性形象创作中去,显示出新世纪女作家对女性写作的纠偏与匡正。
阿袁笔下女性形象的理念化倾向,在写《打金枝》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她曾谈及自己一直思考女人究竟应该怎样才可能拥有幸福人生,强调自己的女人观是反美反智而崇尚朴素。米红、米青、米白三姐妹形象,分别对应美、智、朴。阿袁认为朴素能战胜美与智,让女性获得幸福。如此设置,理念凌驾于形象之上,导致承载作家女性观的米白形象尤其苍白空洞。米白的幸福人生近于充满女性幻想的童话。此外,阿袁也承认米青的圆满结局未能贯彻她预设的反智倾向:“米青在我原来的构思里,也是没有抵达幸福人生的,但写着写着,我到底不忍了,或许是因为我也在高校,米青和我有地缘之亲,所以我徇私了。”①阿袁:《创作谈:打金枝》,《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2期。
其实,用“消极抵抗,世故妥协”概括阿袁的女性观似乎更为合适。因为美智合一的女性形象多是出于迎合男性心理需求的艺术创造,女性降低对人对己的要求,看似安稳朴素,实则退让求安,她们回归传统家庭妇女的角色,落入男权传统。
阿袁小说女性形象的理念化还加入了对拜金主义和男性生存困境的思考。消费社会在物化女性的同时,也在向各阶层男性施压,小说中男性角色为现实所迫都弃美弃智,选择了朴素的异性。阿袁指出两性关系不该是对立的,重利轻情的婚恋现状非由一方造成。男权社会传统中,男性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和家庭职责,地位逐步提高的当代女性既以“平权”为名争取权利,同时又想继续享有男权社会为女性提供的种种庇护,回避或推卸相应的义务责任,不利于两性关系真正的和谐平等。
《师母》的女性形象比起《打金枝》已趋于调和。庄瑾瑜、鄢红、朱周已不是简单对应智、朴、美三要素。作者只还原世相,一任师母们众声喧哗,带着各自理念在不乏缺憾和无奈的现实中追求幸福,让读者据此权衡利弊,自行选择人生道路。作者不再提供答案,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或许更具合理性。
阿袁发现以师母为代表的中国女性既接受了高等教育,也拥有体面工作,按伍尔夫、波伏娃的设想理应获得身心解放,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作家身份和女性身份让阿袁对师母的感情极为复杂,作家阿袁笔下女性的困境,也是她作为女性遭遇的现实困境。虽然阿袁小说无法为女性解放指明更好的道路,但她通过真实的女性书写,为自囚自困而不自知的女性立此存照。
——写给我们亲爱的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