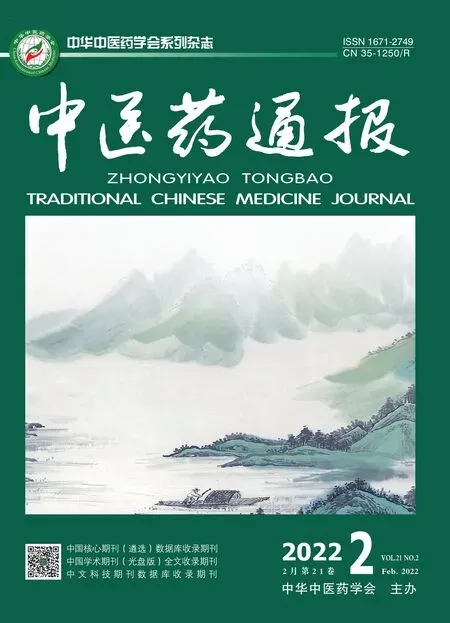基于梁漱溟的观点从中西文化对比看中医药发展前景※
王鹏伟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其学贯中西,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视角看待中西医学,无论是对中医的医疗实践还是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中医学是生命医学
中医强化了梁漱溟对生命的理解:“对于我用思想做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1]14梁漱溟所说的医学当然是中医学,所说的医书当然是指中医医书。梁漱溟认为人的身体健康、疾病康复主要依靠生命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医生和药物。因为“药物如果有灵,是因其恰好用得合适,把生命力开出来。如果用之不当,不唯不能开出生命,反要阻碍生命的”[1]14。梁漱溟没有明确说中医是生命医学,但其理论确实有这个意蕴。
生命医学与生物医学是对立的。生物医学的典型代表是西医(现代医学)。如今,西医与单纯的生物医学已有很大不同,被认为已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因而也是生命医学。然而,西医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生物医学的基本模式,生命医学与生物医学(即中医与西医)的不同,主要在于两者对研究对象的不同定位及由此所导致的诊疗方法不同。
1.1 中西医对研究对象的认知不同从表面上看,中西医的研究对象都是人,即人的生理、病理、疾病诊治以及药物制备等,但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中医把人看作生命,西医把人看作生物。生物是有机的、系统的、复杂的,人更是在生物和生命基础上出现的产物。人不仅仅是一般的生物和生命,更是具有知情意和利益关系的社会人。相对而言,生物远低于生命。西医主要将人当作生物,甚至是无机物、机械物。系统科学表明,一切事物都是以系统复杂方式存在的,控制机制、自组织机制和适应机制是事物发展的三大机制。在它们的作用下,物质世界经历一个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非生命到生命、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人及人类社会则是物质世界演化的最高产物。事物的性质和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依随于其低层次元素和构件的性质和规律、理论上的下索和还原是合理的。这是经典科学坚持机械还原论的系统科学解释。然而,系统科学也表明,事物一旦突现出高层次实体和过程,就具有低层次元素和结构所不具有的整体性和自主性,并且,高层次实体和过程对低层次实体和过程具有约束和限制的下向因果关系,使低层次总体上服从于高层次或系统整体的功能和目标。
西医是经典自然科学的产物。西医通常把人看作没有知情意和利益关系的生物,甚至以物理、化学来解释人,把人当作无机物、机械体。譬如其至少不把老鼠、兔子、狗、猴子等当作生命来对待——它们是实验品。西医对人的研究往往要排除知情意的干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然而,人之所以是人,正是因为人是生命,有知情意和利益关系,比之无机物和机械物,乃至一般的生物和生命更高层、更复杂。人不仅是生物人,更是社会人。因此,我们必须尊重人,原则上不能随意解剖生命,更不能解剖活人。而中医认为药物也是有生命的。它们是本草,远复杂于单一成分的化学合成药,其中许多是“血肉有情之品”。因此,用解释无机物、机械物、一般生物和生命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来解释高层级的人,显然是不充分的。要解释人,还需运用到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
1.2 中西医的诊疗原理不同中医认为人是生命,西医认为人是生物甚至是机械。这决定了中、西医在诊疗原则上大相径庭。生命人怎能随意解剖呢?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中医形成了特有的诊疗方法,即黑箱性质的功能法——望、闻、问、切;而西医主要是基于生理、病理、解剖等的白箱法。与西医学相比,中医是真正关于人的医学。大医精诚就在于大医懂“人”。正因为中医坚持生命观和望、闻、问、切的黑箱法,决定了中医学具有“天人相应”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特色。譬如,人为什么会生病?因为,人体各系统之间、人体和自然系统与(或)社会系统之间出现了不和谐。因此,治病的原则是“调”,即“损有余、补不足”,而不是一味地“攻杀”。具体而言,中医学的优势和特色突出地表现在整体观念等十个方面[2]。然而,中医无法提供现代自然科学范式的说明,从而遭到顽固坚持科学主义的人的攻击。西医主要坚持还原主义的结构功能分析法,即通过解剖、化验、影像等寻找人体以及药物发挥功能作用的最小单位,确定致病实体是哪种细菌或病毒,再通过手术修补或剔除相关组织器官,以靶点性药物攻杀病毒。因此,与中医相比,西医的精准性高,疗效明显。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仍是其主要缺陷,且攻杀性治疗往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2 中西医难以沟通的深层原因
中西医难以沟通的关键在于它们是不同的范式。一种范式就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中医是生命医学范式,西医是生物医学范式,甚至是非生命医学范式,因此中西医难以沟通。“要把中医根本容纳进来……西医便须放弃其自己的根本方法,则又不称其为西医了”[1]15,对中医来说同样如此。梁漱溟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下述发现或证明都不能认为是中西医沟通:(1)中医的某些表述符合自然科学;(2)发现某种中药经化验可作为现代应用;(3)发现中药单方有效可用。因为这些都是根据西医的基本理论来说明中医的某个内容是对的,是西医对中医的零碎拾捡,并没有把中医从根本上容纳进来。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研究实践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西医两种范式的区别实则是中西文化的不同使然。梁漱溟认为,相对于西医所基于的西方文化,中医所基于的中国文化是早熟的,与西方文化长在“人对物”上不同,中国文化长在“人对人”上。因此,与西方学术重视从经验上格物致知不同,中国学术偏于从理论上格物致知。从前者而言,人也被当作是与其他自然存在一样的,是静止的、构成的、无机的、无意志和利益的,因而,机械还原是研究人的主要方法,西医就秉持这种研究模式。从后者来说,人不同于其他生物,更不同于无机物,是有知情意和利益关系的社会人,因而,必须把人当作生命而尊重对待他们,中医学正是秉持这种观点。
从根本上说,中西文化的不同又是由各自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3]由于“路径依赖”及随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综合作用,形成了中西不同的文化类型,由此导致中西学术的差异。具体而言,古希腊的自然生存条件较差,发展出拷问大自然的求力的科学文化;中国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则较为优渥,形成重视血缘人伦的农耕文化。“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中国文化中的“人”不是西方文化中动物性的自然人,而是脱离动物界的社会人。按照梁漱溟的看法,西方文化中的人只是生物人,而中华文化中的人乃是生命人!这是中国文化的长处。
当然,由于没有经过“人对物”的自然科学阶段,这一阶段对研究对象的层层分解虽然割裂了事物各个部分的有机联系,使我们失去了整体,但也使我们掌握了“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4]。这就是中医学昧于细节的根本原因。而正是基于对细节的廓清,自然科学(包括西医)才获得巨大发展。因此,梁漱溟认为西洋科学的路子才是学问的正统。相反,中医已经发展到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因而,中医只是粗疏的生命医学。整体而论,中医学的路子是先进的,但由于昧于细节不能说明自己,所以很难被人了解和信服。
3 中西医沟通的前景
中西医是不同文化的两种不同范式,因而很难沟通。然而,两者彻底无法沟通吗?否!中西医最终是可以沟通的,但需在较远的未来。“要在西医根本转变到可以接近或至沟通中医时……只有待西医根本方法转变,能与其接近,从西医来说明他,认识他。否则中医将是打不倒也立不起来的”[1]15。这是否意味着西医失败了呢?否!“西医转变接近中医,仿佛说西医失败,实则倒是中医归了西医。因中医不能解释自己,认识自己,从人家才得到解释认识,系统自然还是人家的”[1]15。因为,这是用西医(现代医学)资源来解释中医,而不是用中医资源来解释西医。从科学解释看,如果一套理论的解释性更强、解释范围更广,能够将另一套理论纳入自身之中,那么前一套理论就更优越。就此而言,确实是中医归了西医。然而,西医也并未真正从根本上容纳中医。因为,中医所能解释的好多现象是现代自然科学依然无法解释的。梁漱溟也指出,不能因为西医无法解释中医就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医“还能站得住”“现在西医对生命认识不足,实其大短”[1]15。当然,中医也不是不能解释和认识自己,只是不能以西医范式来解释和认识自己。实际上,几乎任何理论都不能以其他范式解释和认识自己,否则,它岂能成为独立的理论呢?但梁氏关于“西医接近中医”以证明中医的论断,还是非常有见地的。
然而,一些人却认为西医无法解释中医就说明中医根本就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甚至是反科学。这是科学主义的典型体现。科学主义认为,唯有源自古希腊的现代数理实验科学,即自然科学是科学,其他一切理性知识系统和实践都不是科学,因而是不科学的,是伪科学、反科学。科学主义是错误的、反动的。若对现代自然科学进行严格的科学哲学分析,譬如经验证实和经验证伪,即便物理学和化学也是很难被称为科学的。实际上,科学是一个宽泛概念,有两种密切相关的基本含义:其一,指科学工作者所从事的分科性的理性研究工作;其二,指某种价值判断,即科学是关于对的、正确的、真的、合理的、有道理的、好的、高级的价值判断[5]3。显然,自然科学并非唯一的分科性理性研究,更不是唯一对的、正确的、真的、合理的、有道理的、高级的理性学科。
科学主义当然是错误的。中医当然是科学!科学哲学发展表明,若胶柱鼓瑟于科学主义,是很难界定哪一门学科是真正的自然科学的。科学是一项理性的、系统的探索性活动。科学坚持无神论,对事物的解释诉诸自然因果关系,而不是诉诸鬼神迷信。从这方面讲,中医无疑是科学。因为,中医学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坚持无神论,很早就实现了巫医分家,要求不与那些拘泥于鬼神迷信的人谈论高深的医学理论,坚持不治“信巫不信医”者等“六不治”原则[6]。
当然,中医确实不是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中医大体上是自然志意义上的科学[5]281。究其原因,中医“在其彻头彻尾为一生命观念”[1]15。但是,中医只是一种早熟的、粗疏的生命医学,这意味着它在中国传统文化框架内无法再获得突破性发展。然而,它在整体上是优越于西医的。正是这决定了梁漱溟认为中医只能坐等西医发展来认识它。坐等到何时?“必须待西医对生命有所悟,能以生命作对象时;亦即现在西医研究的对象为身体而非生命,再前进如对生命能更有了解认识时”[1]15,即作为学科群的生命科学大发展、大成功之时。
4 思考与评价
梁漱溟关于中医的看法不是十全十美的,但确是深有见地的。中西医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产物、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这决定了中西医很难沟通。据之,现在许多打着中医现代化名头的中医研究,实际上乃是现代科学在认识中医、容纳中医、验证中医!为何中医要现代化?这预设了中医不是现代自然科学。中医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这预设了中医现代化的目标对应物是现代医学。但实际上,中医现代化就是个伪命题。它以形而上学的经验证实为圭臬,这种意义的中医现代化一旦实现,中医实际上就消亡了。然而,这种意义的中医现代化又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自然科学的自我发展,是从根本上包容和解释中医的需要。在此过程中,中医对现代自然科学起到“范导”作用——虽然西医无法有效解释中医,但中医确实能治好病,因此,西医必须不断努力以自身的范式来解释中医,而不是简单地说句“中医不是科学”等所能了事的。这表明,与中医的创新发展相比,中医的继承整理更重要。因为,在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如果不发掘、整理和保存好中医,可能等不到现代自然科学能够真正容纳、解释和沟通中医之时,中医早就不复存在了。如果这样,青蒿素的发现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