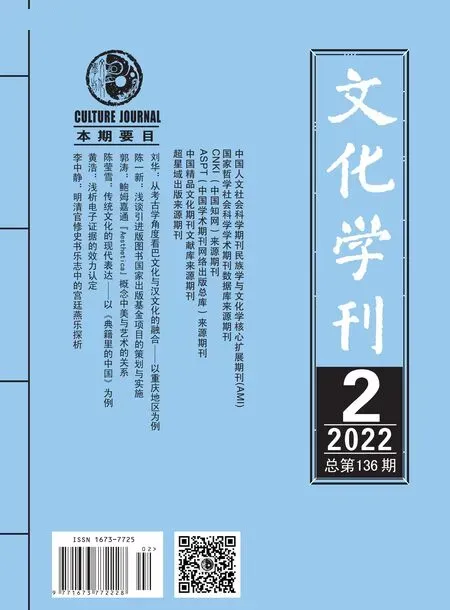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成机制及其实质
冯明宇
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面相之一。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成机制可以概括为数字技术—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数字技术变革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随着新生产力的取得,资本主义变革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使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状况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得到深化。也因此,数字资本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运演逻辑的外部附加了一层“数字化”的外壳,它仍是资本主义。
一、缘起:数字技术对生产力基本要素的改造
数字技术通过渗透并影响生产力各要素而变革生产力,是数字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步骤。
其一,数字技术使劳动者的生产工具发生改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明与普及,传统的机器设备被嵌入了集成电路、传感器、软件和其他各种信息元器件,形成了机器设备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新生产工具——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机器。数字机器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马克思生活年代的机器:一方面,就其构成来看,构成数字机器的构件结构更复杂和精密、科技成分更高;另一方面,就其功能来看,数字机器既保留了替代人进行物质性生产活动的功能,还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智力,替代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脑力劳动,将“物质生产的自动化拓展到思想生产的自动化”[1]。
其二,数字技术使劳动者的劳动对象发生改变。正如“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2]115;数字技术的发明使得网络上形成的关于“主体的情感、认知、经历”[3]等分散各处的数据资源进入人类的视野,成为劳动者的劳动对象。劳动者的数字劳动,作用的主要不是实物存在的劳动对象,而是以虚拟形态存在的数据,实际是技术的发展使更多有用物进入人类的视野。
其三,数字技术使劳动者的劳动形态发生改变。数字劳动是一种以数据公司员工和网络用户为主体、以数字化设备为劳动工具、以数字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为劳动场所,将数据资源加工成数据产品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的出现表明了技术对劳动者的劳动形态的巨大改造作用。在数字劳动中,劳动者将为其所创造的数字机器放在自己和需要加工的数据之间,不仅能够借助数字机器极大地减轻计算、分析所要付出的脑力劳动,甚至能由人事先设置算法,使数字机器自动地作用于劳动对象,使人站在数据生产过程的旁边。
数字技术渗透进生产力的各基本要素,使劳动者的劳动工具、劳动形态和劳动对象得到了新的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为数字资本主义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前提。
二、延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数字化
数字技术改造了生产力各要素,刺激新生产力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数字化,并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造成掩蔽。其一,数字劳动似乎与马克思口中的人直接作用自然、从而进行“物质变换”的劳动相去甚远;其二,数字劳动过程主要依赖于数字技术的自动处理功能,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我们无从得知;其三,由于第二点,数字劳动过程似乎不涉及剥削。但实际上,数字资本家对数字技术的推崇和膜拜,只是掩盖和遮蔽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而这是经不起理论拷问的。
首先,数字劳动实际表明有用劳动的具体形式发生变化,其出现没有证伪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劳动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人使用劳动资料改造自然物(劳动对象),从而制造使用价值的目的性活动,体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4]215。通过对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分析,马克思指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和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其中,前者生产商品体的使用价值,其形式以不同的劳动目的、工具、对象和结果为转移;抽象劳动指的则是抽象掉人类有用劳动的各种形式所剩下的人的体力与智力的凝结,它形成商品的价值。就数字劳动而言,它固然因为具有虚拟性、非物质性的特征而有别于以往的劳动形态,但这种差别只是在“不同质的有用劳动”意义上的。也就是说,相较于以往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不同的劳动目的、工具、对象和结果,但它依然是人的劳动力的有目的的消耗。
其次,数字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并不创造新价值,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罗德戴尔曾认为,“资本本身离开劳动可以创造价值”。罗德戴尔的观点彻底地背离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基于彻底的劳动价值论立场,认为“以机器体系为其物质存在或使用价值的资本——是最能使他们的肤浅谬论貌似有理的形式”[5]194。一如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数字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将凝结在自身中的价值部分地转移到新形态的产品上,另一方面又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进而使工人的劳动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价值。但在根本意义上,价值只来源于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最后,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过程具有两重性,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一方面,就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而言,数据资源是数字劳动要加以提取与使用的一种特殊原材料,它虽然不是具有可观性的实物资源,但无疑是客观存在的、“靠自己的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4]47,其使用价值包括但不限于:人们可以通过它清楚地掌握自身有机体的各项指标,企业、政府和国家也可以通过它来了解自身的各项情况、实际运作状态,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决策和制定发展规划。另一方面,就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增殖过程而言,数字技术被数字资本家垄断和把持,“通过(有可能是间接地)雇佣劳动,为了利润而被投入生产”[6],人们的数字劳动以及最终的数据产品隶属于数字资本家,构成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与剥削。
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生产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只不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劳动形态变化,成为了资产阶级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本质的辩护遁词
三、后果: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状况得到深化
资本主义变革了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将这种存在方式指认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5]59。接着,马克思明确了何为“抽象”:“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5]59。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现实的个人”最根本的存在事实就是受作为物质关系的商品、货币尤其是资本的“抽象统治”。而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商品、货币与资本在形式上取得新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现象得到了深化。
其一,数据商品的诞生使商品拜物教现象得到深化。在资产阶级社会,“商品交换”是使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将自身确证为社会总劳动之一部分的唯一途径,私人生产者商品的价值必须间接地表现为另一私人生产者商品的一定量的使用价值。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便被物的关系掩蔽。数据商品作为一种新的商品形式,其本身是非实物性的虚拟存在,更为彻底地过滤掉了不同商品的独特的实物内容,强化了商品间的形式相同性,因而数据商品的“等价形式”更加使人难以琢磨。随着数据商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不断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更为虚拟化的数字商品间的关系所遮蔽。
其二,数字货币的诞生使货币拜物教现象得到深化。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似乎天然地具有表现其他全部商品的价值的属性,所以当商品的“等价形式”与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相结合,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商品的等价形式具有“天然的社会属性”的“假象”就完全形成了[4]112。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深化。货币形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与数字经济和数据商品交换相适合,金、银乃至纸币(实体性存在的代用货币)渐渐淡出日常的交付手段,而取而代之的是数字货币。可以说,货币形式从实物货币到数字货币的发展,体现的是对不同商品经济阶段中商品“等价形式”的“假象”的持续掩盖。
其三,数字资本的诞生使资本拜物教现象得到深化。资本拜物教的神秘性质就在于:以货币、商品、生产资料等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资本本身,似乎具有“自行增殖”的魔力。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社会生产关系。首先,资本总是呈现为原材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等劳动产品,具有“积累起来的劳动”的性质。其次,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7],资本关系以“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的形成为前提。最后,资本是以物的形式出现的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使活劳动成为“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2]726的社会生产关系。数字资本的产生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变得更隐蔽。一方面,数字资本家除了雇佣一定数量的数字工作者从事数字劳动,还通过提供免费的网络服务在数字平台上网罗了一大批网络用户为其生产数据商品;另一方面,人们为数字资本家生产数据商品的活动贯穿了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基于此,数字资本的增长似乎变成一个合规律的、与人的劳动无涉的自动过程。
可以说,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生没有使人的存在境况得到改善,而是既保持了“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对人的“抽象统治”,又开拓了“拜物教化的人类非物质产品”对人的“抽象统治”。在这一意义上,从工业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抽象的历史”[8]。
四、数字资本主义的实质
数字资本主义是标志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样态的范畴。从构词上看,“数字资本主义”由“数字”和“资本主义”组成,它既包括“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社会形态维度,又包括数字“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维度,这就构成了以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经典分析对之加以把握的合理性基础,进而使我们也能在人的发展或主体的社会形态的意义上展开进一步考察。
首先,从技术的社会形态维度看,数字资本主义建立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在马克思看来,技术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力与技术发展的水平状况,以及与之相适合的产业结构为标准对社会形态做出的划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数字资本主义形成的时代,“新生产力形成的根本标志是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信息技术在长期积累、各自推进的基础上,日益融合、相辅相成的大数据技术体系”[9]的形成。数字资本主义建立新的技术基础之上,并形成了与新的技术基础相适合的以加工数据资源为主的数字产业。
其次,从经济的社会形态维度看,数字资本主义仍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运行逻辑。经济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关系的性质为标准对社会形态进行的划分。根据这一标准,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物种依次演进的经济社会形态,即“五形态”学说。技术发展必然要求经济社会的相应变革[10],但两种变革并不同步发生,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以技术为标准划分的技术社会形态实际反映的是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广度与深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形态”并没有严丝合缝的对应关系。数字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武装下的生产力高度发展,无法掩蔽其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最大化、资本扩张主义的社会景观。
最后,从主体的社会形态维度看,数字资本主义仍是一种“物的依赖性”社会。在马克思看来,“物的依赖性”社会对应于商品经济的社会经济形式,在这一经济形式中,个人摆脱了自然经济中“人的依赖关系”,获得了个体独立性,但由于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直接目的并非满足人的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对商品的拥有变成人们一切活动的出发点,所以个人的这种“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人和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还原为数据并被交换,也只有依赖于将自身和自身的行为还原为数据,人才能够融入数字化时代的生产、生活,并自由地在网络空间中驰骋。数据具有物质根源,人对数据的依赖表明数字资本主义仍属于“物的依赖性”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技术结构的发展主要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要素的结合不仅要借助于一定的技术结合形式,还要依赖于把生产力诸要素结合起来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依据生产关系标准,才能够把握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具体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事实上,数字资本主义不过是以新兴的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数字资本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只是进入数字化时代的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