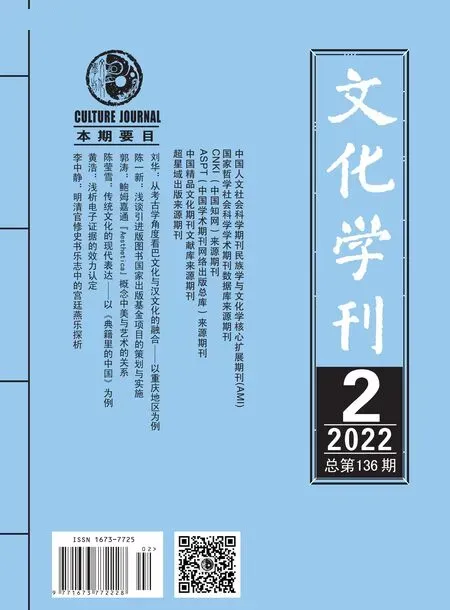《史记·滑稽列传》讽谏研究
马小玉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记淳于髡、优孟、优旃事八件。《索隐》按:“滑,乱也。稽,同也。谓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以言俳优之人出口成章,词不穷竭”[1]2307。《正义》云:“其智计宣吐如泉,流出无尽”[1]2307。皆谓滑稽为善辩。俳优之辈,常被视作祸国之徒——类似“近优而远士”“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2]的记载屡见不鲜。司马迁却从六义谈起,赋之高评:“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岂不亦伟哉!”[1]3203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3297,太史公亦如是。三位滑稽人物出身低微,“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矇诵工谏之义。”[3]
一、起于微末而胸有丘壑的滑稽人物
赘婿淳于髡,乐人优孟,侏儒优旃,皆起于微末。却能在自己的本职——插科打诨、调笑戏谑之外,附加更多责任,将调笑外化,内核实为进谏。淳于髡择威王所好,以大鸟不飞不鸣隐语劝谏。楚兵伐齐,威王使髡请兵,赍持却少。淳于髡大笑,似故作他言,讲农家穰田所持狭而欲者奢。威王即益赍车马黄金,髡借来精兵十万,楚兵退。而后酒宴,淳于髡又以酒量悬异巧谏威王“酒极则乱”。低微之身,供人调笑之职,实际有着士的担当和丘壑。所谓善辩,不妨谓之苦心孤诣。
楚国优孟,讽谏之外尚有忠厚。优孟曾得楚相孙叔敖善待。孙叔敖过世,其子如父亲所料,果真贫困。照父亲嘱咐,寻忧孟。优孟听罢缘由便“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1]3201岁余,仿之甚像,左右不能别。祝寿时引楚王注意,痛陈孙叔敖生前“以廉治楚”[1]3201一片忠心助楚得霸,亡故后其子无立锥之地。楚王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忧孟尽心竭力完成孙叔敖临终所托,躬行忠信,以德报德。
共有的讽谏之外,优旃兼备以仁。不忍陛楯郎淋雨,佯装嘲谑:“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1]3202实是讲予秦始皇,助之陛楯郎。“仁远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4]仁者,爱人。达者兼济天下是仁,小民心怀同情,施以援手,一念之善也是仁。
此三者所行,旨归司马迁心目中的“滑稽”,符合他对滑稽人物的心理期待。“虽居弄臣之列,而所言皆足以匡君,故一则曰‘常以谈笑讽谏’,一则曰‘合于大道’,各于传首揭出眼目”[5]169“冒主威之不测,言廷臣所不敢,谲谏匡正。”[6]善辩、机敏、多智,皆是其次,首要当是合于大道。敢于承担不可预测的风险,为大道挺身而出,兼备忠厚,持之以仁,以德报德。起于微末,却胸有丘壑,心系天下,进朝臣所不敢谏。他们是供君调笑的弄臣,也是苦心孤诣的谏臣和履仁蹈义的仁者[7]。
二、犯险进谏的缘由追溯
俳优,是王室或诸侯豢养的专供娱乐调笑的艺人,“身份是奴隶……是种奢侈奴隶,或有生命的工具”[8]96-99。但在《滑稽列传》的俳优身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奴性。相反,他们似乎以最不严肃的身份与形式承担了最为严肃之事。而这是极有风险的。他们的进谏,或是在君王喜不自胜时浇将凉水,或以奇言怪喻尖刻猛锐直指君王错谬。总之,合大道而逆君王意——生命可能随时被终止。因讽谏丧生者不乏先例,但仍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俳优冒性命之忧行以讽谏。
单看优谏,实有两方面不合理性。其一,于滑稽人物而言,他们供上层娱乐消遣,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若只求生存,泯然众人是最安全的选择。长期身处宫廷,见惯帝王的喜怒无常、生杀予夺,没有理由凭一腔热血便罔顾性命,站在君王的对立面,指摘君王的不是。其二,以优谏劝阻君王实是对政治的干预。没有政治权利却强行参与,实为僭越。这样的与政方式能为统治者接受,绝不只是不为人重视,说话便可不受限制的“我优也,言无邮”,否则市人奴隶皆可对朝政畅所欲言。现象的存在必有其赖以存在的思想文化支撑。优谏这一行为,应当为彼时的文化、社会心理认同,具有文化上的合理性。
优,俳优、倡优、优伶,一般被认作演员的前身。关于优的起源,多数研究者采纳了冯沅君的看法:优起源于巫,社会不断演进,巫的职能也逐渐分化,“倡优就是承继它们的娱神的部分而变之娱人的”[8]14。而“巫觋之兴,虽在上皇上世,然俳优则远在其后”[9]。巫优之间,相间甚久,且二者地位悬殊,其间当有演变过程。黎国韬对此提出新解:“此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忽视巫与优之间曾有一种过渡人物,亦即乐官。乐官从巫官中出,而优又从乐官中分化,较为合理的发生序列应为:巫——乐官——优——演员。”[10]226-227有了乐官作为巫与优的过渡,优之进谏便有了传统上的合理性。“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1]1236我国古代,政治以礼治为本,乐以辅礼。是故礼乐并重,乐与政通。乐官掌乐,当也具备政治功能。
《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1]
《大戴礼记·保傅》:“有敢谏之瞽,瞽夜诵诗,工诵正谏”[12]52。
《淮南子·主术训》:“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13]
箴师,“箴刺王阙,以正得失也”;诵,“以声节之曰诵”[12]11“谓箴谏之语也”[12]53。《周礼·瞽矇》郑注:“讽诵诗,主诵诗以刺君过……以戒劝人君也。”[14]箴谏之人多是“师”“瞽”。而师、瞽矇,位列《周礼·春官》,是周官官制中乐官之属。由是,乐官有箴诵之职,优谏传统当源于乐官的箴诵谏诲。乐官兼具教育功能与政治功能[10]141,当乐官转变为优,这两个功能也应有所承继,而优谏,正是继承这两个功能的最好体现。优谏与箴诵虽形式有别,但功能基本一致。有古代乐官进谏的先例,故而优人的讽谏虽有时得罪君主,却无需深受责罚,大抵便是优施“言无邮”——优人微末之身犯险进谏的心理认同与文化合理性。
三、以“伟”称道的太史公用意
对于司马迁所选的滑稽人物、滑稽故事,过往的研究者在两方面提出质疑。一方面,“迁为滑稽列传,序优旃事,不称东方朔,非也。朔之行事,岂值旃、孟之比哉。而桓谭亦以迁为是,又非也。”[1]3205在仲长统看来,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皆幽默风趣,都应入《滑稽列传》。褚少孙在补《滑稽列传》中又加入他人事迹,说明褚少孙也持此观点。另一方面,以“实录”质疑该传的真实性。一则是时间错谬。齐威王于公元前378年—公元前343年在位,优孟与楚庄王(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1年在位)当在其前。再则,“楚大发兵加齐”实属乌有(1)[日]泷川资言 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04页,引钱大昕云:“案《世家》及《表》,是年无齐楚交兵事。此传之言,多不足信。”。
其一,就选人而言,实是仲长统褚少孙与司马迁对滑稽人物的定义、期待不同。二者之别,在补录的评点中可见一斑:“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悦”[1]3204。褚少孙所补的滑稽人物主要是郭舍人、东郭先生、王先生和西门豹。他们辩才出众,言辞流畅,但目的是和悦人主、为己谋利。卖弄灵敏机变、逞口舌弄巧,长于计谋。持之以仁、为大道挺身而出之言行不复存在。反观司马迁笔下的滑稽人物,淳于髡劝威王奋进,罢长夜宴饮;优孟提醒并制止庄王厚马薄人;优旃劝止秦始皇拓扩园囿,打消了二世油漆城墙的念头,合于大道。此外,太史公盛赞滑稽人物,还因其“莫害于人”。历史上不乏“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1]2080悲剧收场的忠义之士。他们坚守原则,直言敢谏,却总因心直口快、不合君王心意遭受莫须有之罪。嘴上纹理有饿死相的周亚夫便是最令人心痛的代表。“不流世俗,不争势力,上下无所滞凝,人莫之害,以道之用”[1]3204。司马迁的选择标准道之分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蝇营权势利益,沟通上下不至滞塞,能不受迫害保全自身,最重要的,是能遵守道义。其二,以“实录”质疑《滑稽列传》的真实性。首先,关于时间错乱,周言的考证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错简。“若按每简28-29字排列,则只须调换各章编连次序就可得出正确的人物年代次序。”[15]其次,“实录”是后人的总结,以后人之见要求前人有失妥当。《太史公自序》曰:“以拾遗补异,成一家之言”[1]3319;《报任安书》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6]2735。前者“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3319-3320整理学术的发展演变。后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怀之理”[16]2735。实录固然是司马迁记史立传的基本原则,但“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无动于衷、完全被动地直录事实,而是和他的著述理想密切联系的。”[17]《滑稽列传》的真实性固然有待商榷,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思想性。对于某些细节,应是回顾真实事件后的合理想象,而非子虚乌有的虚构。这些补充,或许没有“考信于六艺”,却都“折中于夫子”,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的重要部分。
节人之《礼》,发和之《乐》,道事之《书》,达意之《诗》,道化之《易》,道义之《春秋》,都是为“补短移化,助流政教”以达“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1]1175-1176太史公高评滑稽人物“伟哉”,是因为其在六艺之外而合乎大道。滑稽之人以微末之身承担本不该由他担负的责任,那么原本应该担负起这些、职责所在应该如此的人呢?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彼时尊儒正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似乎应是儒人刻在骨血中的责任与担当。可惜的是,汉武帝对儒学真正感兴趣的,是加强皇权威严的礼乐制度,诸如封禅、郊祀、改正朔、易服色等。他所尊奉的“已经不是先秦孔孟的原始儒学,而是一种为专制政权装点门面的货色”[18]。
儒学在汉代的发展已经与原始儒家产生偏离。从文士欲图抬高儒学地位开始,便有意识地用实用主义诱之当权者:“书不必起自仲尼之门,药不必出自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19]。儒家的理想主义向实用主义靠拢,儒者之思想学说也向意识形态倾斜。无论是叔孙通靠制定宫廷礼法收获成功,还是虚伪圆滑的公孙弘缘饰儒术晋身,都昭示了儒学的偏离,甚至是向儒术的转型。政治权力介入,附带未知又充满诱惑的实在利益,曾经的理想沦为进阶的工具。一批汉儒顺从武帝心意,思路渐渐从天上掉到地下,流于世俗,蝇营势力,依靠儒学获得官职,却并不发挥儒学干预现实的批判精神。在他们手中,儒学已经失去了儒家追求的“仁政”的内核,只剩下对堂皇气派的礼乐制度的大肆炒作。儒生对权力的谄媚迎合,权力对儒学的利用扭曲,早已丧失了原始儒家的精义。儒家看似胜利,成为官方承认的学问,“但实际上却使它逐渐丧失其独立的批评与自由”[20]271。
在君王“一人有庆”绝对权威之下,道统与政统逐渐融合。知识阶层与官僚系统合二为一,从前“以自由思想为职业的文士不得不承认官僚行政系统的政治正确性”[20]265,原有的知识与精神的独立性立场也被逐渐消解。“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21]的士人、儒者或主动或被动地渐渐忘记、放弃“大道”,身居庙堂而失去了自承道统的担当,而那些地位低微的俳优赘婿,却以自己的方式,以极不严肃的滑稽调笑,行严肃之事、担“大道”之责。在与儒士本应该但没有的比对之下,滑稽人物苦心孤诣、躬行忠信、持之以仁、谏之为国的言行更为可贵,也算是给予以道自任的太史公一丝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