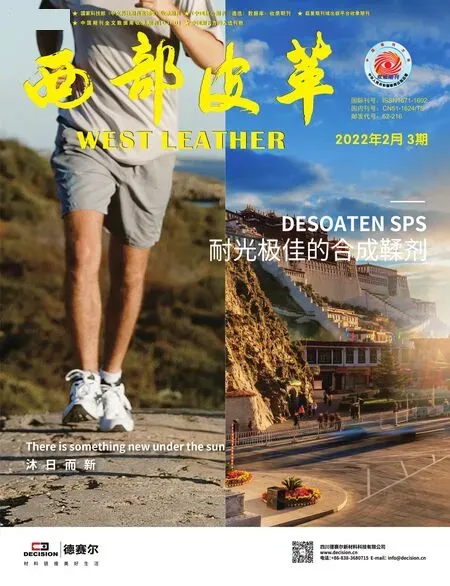中西合璧《缎子鞋》
文 北京/全岳
2012年3 月,余中先先生翻译的中法文化之旅系列丛书《缎子鞋》的出版,令国人领略到普箩艾丝与罗得里格邂逅相识后的爱情悲剧;领略到中西文化中的缎子鞋真谛,更领略到一个翻译家因《缎子鞋》而收藏鞋子的故事。
绫罗绸缎,是中国的国粹;用绸缎制作的缎子鞋,同样是中国的国粹。然而,一本名为《缎子鞋》的戏剧名著,却是法国外交家、作家保尔·克洛岱尔所作。
这部《缎子鞋》不仅是最著名的剧本,而且它以全世界为舞台,展现了16 世纪末至17 世纪初以西班牙为中心的殖民帝国的巨幅画卷,呈现了西班牙重臣唐·罗得里格与贵妇人堂·普箩艾丝的爱情悲剧。该剧描写了上至王公大臣,下到世民百姓、三教九流等七十多个人物,可谓洋洋大观之作。
普箩艾丝与罗得里格邂逅相识,一往情深。她不顾丈夫的反对,与罗得里格约定在海滨旅店幽会,但罗得里格却因途中遇险而爽约。普箩艾丝逃脱家庭的樊篱赶往情人的家中,却始终不敢与罗得里格见上一面。
经过激烈的、自己对自己的一番心灵较量,普箩艾丝在天主的启示下,终于悟出了灵与肉的道理,毅然赴非洲要塞摩加多耳担任天主教国家给她的使命。与此同时,罗得里格则去美洲总督府赴任途中借道非洲邀她同行。
然而,已献身天主的普箩艾丝,毅然决然地回绝了罗得里格。这两个情人从此天各一方,却心心相印。十年后,已成寡妇的普箩艾丝被迫嫁人。又一个十年后,罗得里格失宠于西班牙国王,被卖作奴隶。整个剧情跌宕起伏,舞台色彩斑斓,人物极其众多,体现了宗教与戏曲艺术的和谐之美。《缎子鞋》面世后,首先在电台连播,此后在舞台演出,最后拍成电影而风靡欧洲。
一个外国作家,把中国的缎子鞋作为他的书名,实属罕见。《缎子鞋》这个剧本,是他离开中国担当日本“诗人大使”的1919年至1924 年期间创作的,其字里行间中仍蕴含着一丝丝扑面而来的中国文化气息。作为法国作家的保尔·克洛岱尔,缘何以中国的缎子鞋作为这部巨著的书名?这要从著者的人生经历说起。
保尔·克洛岱尔(1868-1955),法国诗人、作家、外交官。在1895 年后的14 年里,先后任驻华上海领事、福州领事、使馆首席秘书等,堪称一个“中国通”。在中国生活如此之久的“中国通”,对中国特有的绫罗绸缎,中国特有的缎子鞋合有关缎子鞋的故事,必然特别关注,甚至情有独钟。
作为一个久居中国的文化名人保尔·克洛岱尔,一定知道缎子是一种源于古老中国的华贵丝织品,一定知道中国女性“三寸金莲”之足和美轮美奂的缎子绣花弓鞋,或许知道晚唐诗人温庭筠的《锦鞋赋》和其中“耀粲织女之束足,婉嫦娥之结璘,碧繶缃钩,鸾尾凤头”的缎子鞋,或许知道牛郎织女和嫦娥奔月等有关缎子鞋的民间故事。当他离开中国这块他所熟悉的国度之后,必然无法割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缎子鞋》,就是他对中国情结最生动的见证;《缎子鞋》,无疑隐藏了诸多的中国文化元素;《缎子鞋》,更是中国文化元素的一件物证。
当保尔·克洛岱尔到中国的第二年,也就是1897 年就创作了一篇名为《钟》的散文,其中就写到了绣花鞋。他所描写的是中国一个铸钟匠,多年来为皇家铸造的大钟质量总不合格,原因是缺少某种精魂。他的女儿又见其父唉声叹气,并得知铸钟失败的原因后便在心里有了主张。一天,她见父亲再次为皇家铸钟,便精心打扮了一番后,穿上漂亮的绣花鞋,趁父亲不注意的时候,纵深一跃跳进烈焰灼灼的金属溶液。当父亲飞步向前施救,但为时已晚,只抓住了她的一只绣花鞋。少女的气血顿时化为大钟的精魂。铸成的这尊大钟顷刻间发出了最美妙的和谐之音。
保尔·克洛岱尔的《钟》,源于在中国流传的“大钟娘娘”的故事。他在《钟》的文字里,还写了自己的感悟:“一个灵魂注入了大钟之中,而生命的基本力量赢得了巨响,大钟拥有了一钟贞洁处女的优雅仪态,连带还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流动性。”更重要的是,“大钟娘娘”中的绣花鞋,启迪了他创作《缎子鞋》的心灵。
《缎子鞋》的中文本译者余中先先生说,保尔·克洛岱尔自己承认《缎子鞋》的主题就是对牛郎织女传说的借鉴。织女离开天庭而下凡,普箩艾也欲为天主一死;织女拗不过天命被迫分离,普箩艾丝自愿亡命天涯;七夕的传说颂扬平凡的爱情而鞭挞无情的天神,《缎子鞋》则通过主人公牺牲爱情服从天主来宣扬基督精神的胜利。
《缎子鞋》中的普箩艾丝,为追求私情而准备偷偷逃跑时,她脱下了一只缎子鞋,挂在了圣母雕像的手上,叹道:
“我把鞋子交给了你,圣母玛利亚,把我可怜的小脚握在你的手中吧……当我试图向罪恶冲去时,愿我托着一条瘸腿!当我打算飞跃你设置的障碍时,愿我带着一只残缺的翅膀!”
在西方文化史上,鞋子,常常是一种契约的见证。克洛岱尔在中国文化中也无疑发现了鞋子的象征意义。缎子鞋,就是一件物证,就像灰姑娘足下的水晶鞋一样的物证;水晶鞋和缎子鞋,无疑都是中西合璧的见证。
余中先先生翻译的中文本《缎子鞋》,也是中西合璧的见证。他在法国留学时,当第一次看到《缎子鞋》后,立即被普箩艾丝的爱情故事所征服,于是成为他最早的翻译作品,从而有了中法文化之旅丛书之一的《缎子鞋》。
余中先先生在法国留学时,曾将保尔·克洛岱尔《钟》的故事,讲给了同学们听。一个韩国女留学生对“大众娘娘”的壮举十分钦佩,还将一双高丽风格的绣花鞋送给了余中先作留念。从此,保尔·克洛岱尔的《缎子鞋》和韩国高丽风格的绣花鞋,激起了余中先收藏鞋子和鞋子艺术品的强烈欲望。
余中先先生,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世界文学》主编。在他的书房兼工作室,有一面书墙,其中有一个书橱放的都是他翻译出版的作品。在他的电脑中,分门别类建立了许多文件夹,整理了一份自己的翻译档案,把什么时间翻译了什么书,什么时间出版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翻译的《缎子鞋》这个法文剧本,不仅体现了他对保尔·克洛岱尔的崇拜,更对中西合璧的中国的缎子鞋充满着的不了之情,收藏中国鞋子和鞋子艺术品“乐此不疲”了30 年。他说,每次外出旅游,自己总要在宾馆或景点的卖纪念品的地方寻找小巧玲珑的鞋子,慢慢地鞋品就多了起来。自己的收藏原则是:“不求贵,只求小;不求能穿,只求好玩;不求齐全,只求有意思;更求小而精,方便家中摆放。”
他颇为得意的收藏品,是分布在书架橱窗等各处的各种工艺品鞋款。当对来访者如数家珍地详细介绍每双鞋子的来历与特色时,总是喜形于色地说:
“这些鞋子有些是我买的,有些是我妻子买的,有些是朋友、学生送的。材质有陶瓷的、金属的、石头的、玻璃的、玉石的、水晶的、塑料的、布料的、竹子的、毛线的、橄榄壳的等等,产地特色的有鄂伦春的鱼皮靴、青海土族的绣花鞋、日本的小木屐、俄罗斯的芭蕾舞鞋、墨西哥的尖头鞋等等,造型有烟灰缸式、化妆盒式、笔筒式、酒杯式、盐瓶式、胡椒瓶式等等,鞋款有高跟鞋、矮跟鞋、虎头鞋、轮滑鞋、木屐等等,有大的更有小的,如拇指小、如放大镜可见,又贵的如玉鞋、玻璃鞋、水晶鞋,更有便宜的,如下岗女工用毛线编的小绒鞋、农民用手打的小草鞋、用竹篾编的小竹鞋,都不会超过5 块钱……”
余中先先生还说,他三十年前最早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就是保尔·克洛岱尔的《缎子鞋》。克洛岱尔是现代法国文坛向法国人介绍中国的第一人,出于对他的《缎子鞋》和其中文译作的某种纪念,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喜爱鞋、收藏鞋的习惯。独具特色的缎子鞋,是织女的也是普箩艾丝的,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岂能不喜?中西合璧的《缎子鞋》,是克洛岱尔的也是自己的,也在牛郎织女的凄美传说里,更在普箩艾丝的爱情悲剧里,岂能不爱?好不夸张地说,《缎子鞋》堪称融合中西服饰之鞋,堪称中西合璧的艳丽奇葩。
(下期刊载《高跟皮鞋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