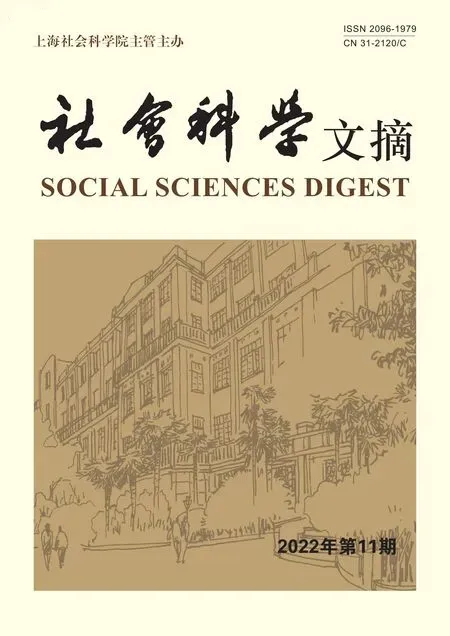生态批评与“民族”
文/龚浩敏
美国学者琼妮·亚当姆森(Joni Adamson)与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提出,“第三波生态批评”需要“承认民族和国家(ethnic and national)的独特性,且超越民族与国家边界”。他们对生态批评中“民族和国家”问题的关照与汤姆·林奇(Tom Lynch)的“新生态区域主义”(Neo-Bioregionalism)、厄休拉·K.海斯(Ursula K.Heise)的“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以及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生态全球”(Ecoglobal)等观点遥相呼应,构成了当下在不同空间光谱中考察生态写作的重要趋势。
生态批评学界对于地理和社会空间议题的关切,显示出在以“当地/在地”“地区”“民族—国家”“区域”“全球”“星球”等概念所构成的光谱中,生态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空间层面的聚焦,其焦点变动不居,不同焦点间构成或对话或对抗的张力。它还揭示出空间问题之于生态批评更为紧要之处,即身处具体地理与社会空间中的人群的认同政治问题:一方面,人群所组成不同的政治认同体与自然环境构成不同关系,对自然和环境产生不同影响,也由此形成认同体之间多种方式的互动和角力;另一方面,人群在自然环境中的活动乃至对自然环境的调控和操作,又形塑了他们政治认同的方式与过程,影响甚至重构了认同体之间的边界。
在上述认同空间中,“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无疑仍是当今世界族群认同最重要的层面,仍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最关键的认同指标,以及其他各认同层面几乎无可回避的参照对象。然而,“民族—国家”又是当今世界最具争议的政治认同架构,其生成与获得现代政治合法性和普世性的过程,与欧洲文艺复兴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历程紧密相连。对于如中国这样在近代被强行嵌入这一现代性架构之中,但仍受传统结构影响的政治体而言,如何理解和处理自身与该架构之间的关系,关涉到该政治体怎样在复杂的全球政治中获得与之相匹配的话语权,以及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第三波生态批评特别关注“民族”问题,显示出学界对于认同政治在民族—国家(以及在次民族[sub-national]和超民族[supra-national]等)层面与生态问题的深层联系日益密切。但同时,“民族”这一概念仍亟须在理论与现实层面上厘清。在中国或东亚具体语境与实践中,“民族”在怎样的意义上与在欧美文化语境中所言的“民族”相契合与不相合?当今世界以西方为主导的生态批评话语中的民族问题有哪些洞见与不见?其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与内里的哲学思路是什么?与之相应,作为东亚传统民族关系架构中核心政治体的中国,其当代生态话语中“民族”与前者具有哪些相似或不同层面的意涵?它所发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以及所遭遇的政治与思想结构碰撞又是怎样的?对此,我们需要一个比较的视角,对“生态”与“民族”的概念历史化、语境化和政治化,理解它们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与实践经验,从而更准确地在全球语境中把握其话语定位与现实意义的复杂性。
西方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民族”“Ethnicity”“Nation”
布伊尔在《生态全球主义情感》一文中提出,面对全球性的经济与社会进程,我们需要以“环境的或生态的”和“‘对抗’和‘超越’民族性(nationness)的”方式来思考。海斯在《地方意识与星球意识》中指出,当今全球环境问题早已冲破地域分野,也非当地社群乃至民族国家等依靠其自身力量所能完全解决,因此,我们需要在“星球”的层面来审视和应对。她倡导“生态世界主义”,超越“邻近的伦理”(ethic of proximity),如此方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环境生态问题。与之相对,林奇在《旱生生物:美国西南文学中的生态批评探索》一书提出“新生态区域主义”,与海斯的“生态世界主义”形成了理论上的对话和拉扯。“新生态区域主义”视跨区域和全球性贸易为地方生产和在地文化的威胁,因此,他提倡“一定程度上的地方的自我依存”。
在这些对地理、社会、文化空间的讨论背后,不难看到一种生态媒介下的社群认同政治,以及社群认同政治的生态影响。一方面,认同体在不同层面上的行为和表现,体现了它们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不同认识和展望,影响到它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案与路径以至成效。另一方面,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演变以及人们想象这些问题的方式的改变,影响到社群认同边界的变化,打破、超越、重组认同体的范围和结构。
这些讨论中的核心认同层面是“民族”(ethnicity)。“民族”问题从生态批评形成伊始便存在,贯穿整个发展过程。笔者认为该问题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美国生态批评话语中的“民族”问题,其最基本的依据是“种族”(race),这从“第三波生态批评”兴起时期的出版著作可见一二。
第二,以种族边界为区分视角,在生态批评中引发令人担忧的“生态种族本质主义”倾向,其表现为在生态环境议题上对特定种族的浪漫化或妖魔化。所谓“落后”的少数族群往往被视为与自然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所谓的“高贵的野蛮人”;反之,将特定种族与负面生态现象相联系的情形也屡见不鲜。不论是浪漫化还是妖魔化特定种族,对于我们理解生态环境都会产生扭曲与偏颇。
第三,作为美国社会最核心问题之一的种族平等问题,与其他平权议题交织一起,构成其社会正义的基本面相。生态正义作为社会正义的一个层面,在生态批评中备受关注,成为当今生态批评的主流话语。学者讨论不同人群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所承受的环境压力差异的背后,有关种族、性别和阶级等的深层原因,思考资本主义与现代性所造成的全球不平衡如何引发生态退化与危机。既然“全球”已然被纳入各类资本的系统结构,那么或许我们需要以一种“星球”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的世界。
第四,当众多学者呼吁超越“当地”来面对生态问题之时,有学者再次强调“地方”对于种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第五,种族问题有着明确的历史根源,即西方的殖民主义历史。这段历史往往是有关生态正义争论的中心话题,但它又常常在讨论非西方的民族与生态问题中缺席。西方对于非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殖民,出于其资本主义的极速扩张,伴随着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卖、对原住民的种族屠杀、对东方文明古国的大肆劫掠等行径。对美国生态批评而言,其讨论最多的黑人、印第安人和亚洲人所经历的生态非正义的问题,正来源于此。在当今世界,经过20世纪轰轰烈烈的废奴、平权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之后,以实质强权为依托的实际土地占领式的殖民主义已然退去,但依靠葛兰西意义上的经济、政治、文化霸权,或福柯所提出的知识权力,抑或萨义德所阐明的东方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成为受压迫民族和种族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力量。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资本力量的无远弗届,生态不平衡问题显得愈发突出且更为吊诡。
第六,在美国生态批评话语中,相对于“race”的指涉有较为明确的共识,“nation”的意涵则显得有些暧昧不明,有时与“ethnicity”交互使用,并无特别区分。
构成当今世界基本政治格局的“民族—国家”体系,是基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背后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物质媒介诸多因素。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进程,以及资本全球化的强力驱动,这一西方现代性的政治体系将世界其他地方尽数纳入其中,在政治上为资本畅通运行确立规则,扫清道路。
美国作为历史较短、早期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新兴移民国家,一方面迅速融入民族—国家体系,成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它的民族(national)意识与传统欧洲的民族意识又有着巨大的差别。传统欧洲的民族是基于地理、历史、语言、宗教信仰、经济活动、政治联系、文化交流等诸多复杂因素所形成的认同体;民族构成主权政治的主体,民族边界与政治边界大体一致,形成“一民族一国家”的基本政治格局。而美国是多种族、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新型民族—国家,其在主权国家层面上的民族认同最基本的因素是美国式民主政治认同。
而在以中国为代表的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民族问题有着极为不同的历史、政治、文化内涵与现实关照。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考察民族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我们需因应具体情况采用相应的思路和与当地实际相适应的路径。
中国生态批评话语中的“民族(Minzu)”“少数民族”“中华民族”
以比较的视野讨论中国生态批评话语中的“民族”问题,首先会遭遇“民族”一词在技术和概念上的困难:我们该如何翻译“民族”?中国语境中的“民族”对应英文中哪个词汇——“race”“ethnicity”抑或“nation”?如何在英语及相关文化中处理“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中的“民族”问题?这些问题与中文语境中的生态批评发生怎样的内在关联?它们与西方生态批评话语可以产生怎样的对话关系?对在真正“世界”或“星球”意义上关照生态批评有何启示?笔者将从两个方面考察这一议题。
首先,“种族”不是中国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中国的民族观念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种族问题有过不同形式的纠缠,但根本上,中国不以种族差异为基础来区分和建构民族。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其多民族共和的政治愿景得以实现,正是以批判与摒弃种族和民族对立为前提的。因此,美国生态批评话语中以种族为核心的民族问题,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问题,对于中国生态批评而言,虽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无法构成思考的起点。
但同时,种族主义观念又以另一种形式浸入中国的民族生态文学作品和批评之中,即“民族的种族主义化”或“民族的本质主义化”倾向。该倾向放大族别的差异,强调民族构成中的种族性因素,从而遮蔽民族在历史流变、认同机制、交流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复杂性。这一种族主义的思维方式试图以一种本质性的种族决定论,代替社会心理建构的民族观念,从而固化族群边界,取消民族融合的可能。
在民族生态写作中,这种倾向表现为“双重偷换—遮蔽效应”:一方面以所谓独特的民族个性或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口号,偷换对复杂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另一方面以具有戏剧性和冲击力的生态图景或风行的环保理念,遮蔽对相交织的其他问题的丰富呈现。
其次,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生态批评的关系。中国是在晚清外来帝国主义入侵与内在变革驱动之下,由一个前现代“天下”体系中的中央王朝走向现代“全球”体系中的民族—国家。作为宗主国的中央王朝与其藩属国之间所构成的朝贡体系,被全球性主权国家体系所代替。作为现代政治、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观念,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型。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今天学界理解中国民族问题最为深刻的理论依据。
笔者提出“自然与民族的相互构建”观念:一方面探讨中国民族——包括少数民族族群、汉族和中华民族等各层面上的民族形式——在现代性的洗礼过程中,各人群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如何形塑各民族的认知与认同,即自然和生态在民族形塑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另一方面考察中国不同层面上的民族形式的人群,对于自然和生态有着怎样相似或不同的态度和对待方式,如何影响了自然和生态,并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和文化后果。这是一个自然与民族双向着力与互相影响的过程,动态地塑造着对方,也动态地为对方所塑造。
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下,这一过程也必然是政治的和历史的,同时关照生态话语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当代全球生态批评的空间意识明显强于时间意识。时间维度不仅体现在罗伯·尼克森(Rob Nixon)所说的“慢暴力”,学者对“人类世”起点的历史溯源,抑或对某地区的环境生态史的梳理与考证之中,也存在于从生态的视角对民族历史的思考以及对现代性展开、殖民主义扩张和后殖民理论霸权的反思之中。只有经过这样一个历史化的过程,生态之于民族以及民族之于生态的内在意涵才可能真正有效地展开。
结论
中国民族文学的生态批评实践中,生态问题与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往往显影于当代现实的两端:前者作为富于戏剧张力且具有国际气质的通货,举重若轻地象征化了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而后者作为被高度普适化的西方身份认同话语,化身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便利贴,一劳永逸地承担了上述问题之对症良方的不情之请的义务。而处于两者之间的中国当代最大的被遮蔽的现实,则是新时期的“发展主义”。在经历了从非异化式的民族关系向民族—国家形式的倒逼式的现代化转型,以及高度政治化、体制化的社会主义主体改造的民族实践之后,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市场化时期个人被资本原子化重构后,人民主体乏力的表现,是“去政治化”的必然结果。发展主义带来环境问题,亦会激发民族和民族主义情绪,但要真正应对发展主义的问题——不光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需要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从生态危机中释放出来,形成有效政治动员力而不应被民族主义所误导。
从比较的角度来审视当代生态批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既看到西方生态批评话语对民族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追求,也认识到由其具体语境所决定的对非西方世界的民族问题理解的盲点。我们只有将“生态”与“民族”永远动态化,不断地在不同语境中追问它们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具体实践中检验论述的有效性,才能真正建立起对它们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