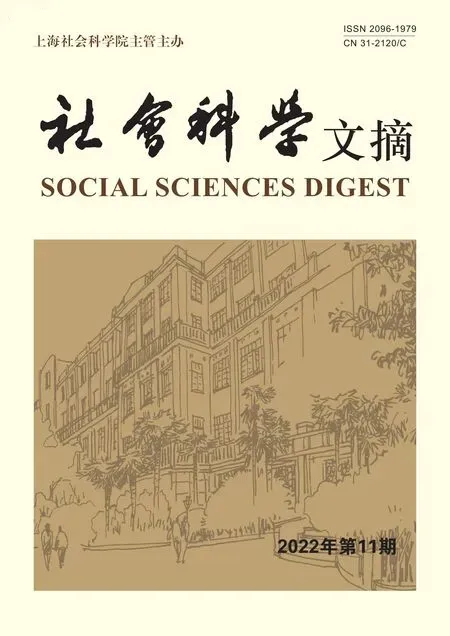现代中国“同情”诗学的起源
——以周作人为例
文/宋夜雨
1920年前后,“新村”时期的周作人开始频繁地以讲演的形式就文学与社会问题发言。1920年11月8日,周作人应北京师范学校纪念会之邀赴之演讲。讲演中,周作人不仅从“我们”与“不幸”的联结中看到一种命运共同体感受构造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借助文艺的培养从“不幸”中翻转出一种同情机制。由此,“同情”问题开始在他的思想中频繁闪现。此时,在不同文化场域之间来回穿梭的主体痕迹也明显地投射于他的一系列文学行动中,二者之间呈现出深刻的互文性和对话性。尤其是新诗,此时占据着周作人颇多心力,一方面,新诗的同情机制内含着文艺打通社会、联结彼此的改造能力,由此构成了周作人介入现实、想象社会的手段方法;另一方面,正是在对社会现实的具体处理上,新诗的内部空间得以打开,同情机制得以延展伸缩,而新诗的形式面貌也由此获得。
周作人围绕“新村”的一系列行动在当时的青年中间激起极大的反响。郑振铎积极回应周作人的“新村”实践,同时他也与耿济之、瞿秋白等人充分注意到俄国文学中“人道的同情”,而这正是他们所看重的“诗歌之力”。由此,“同情”问题迅速蔓延开来。
诗歌之力
周作人“五四”前后的主体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同情”展开的,而文艺或者新诗则被周作人看作是实现“同情”的主要方式。1919年,周作人全力投入“新村”的社会理想的构造中,而此时也是他新诗写作颇为集中的一段时间。自1919年1月13日写作第一首白话诗《两个扫雪的人》,周作人陆续写就一系列具有鲜明社会景深的新诗作品。此时的新诗不仅是他思想行动的一个倒影,同时也被他看作是实现以“同情”为根底的社会理想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而他的新诗选择及其内在逻辑与日本“新村”的文化策略或许不无关联。除了公社式的集体劳动之外,他们不仅出版个人著述,宣扬新村精神,同时也创办与之相合的同人刊物。而无论是《白桦》《新村》这些综合性的刊物,还是《生长的星群》《诗》相对专业性的刊物,诗都是其中重要的文类构成。“五四”前后,这些刊物频繁出现在周作人的日记中,由此,“新村”与“新诗”之间的情感辩证,周作人很容易感受和领会。周作人对“诗力”的偏重,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新生”时期的文化思路,只不过此时因为“新村”而被赋予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想视景。
此时对周作人的“新村”理想抱有深刻认同的郑振铎也对“诗歌之力”颇为信服。在郑振铎的“新社会”设想中,“同情”是一种重要基底,这与他此时建立起来的社会学视野密切相关。借力社会学的知识视野,郑振铎在“同情”与“新社会”之间勾画出了一条相当清晰的通达路径。诗人的“同情”并非一种道德主义式的慈善怜悯、一种自上而下的道德训育,而是一种“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的替代激情”,诗人不再是封闭的抒情自我,而是情感的代言人,借助于诗歌的抒情口吻和人称语气将普通民众由分散、孤立的情感困境植入一种共通的情感体验之中。由此,阶级、身份、性别、种族甚至是不同的生命形态等障碍装置都将被拆除、化解。因而,无论是“新村”还是“新社会”这种平面横向的空间共同体,它所依赖的不仅是情感的分享与流通,事实上首先是依赖诗歌的抒情机制打开“事物的内部与灵魂”。然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其中的同情机制是如何在诗的技术层面落实的;借助于对同情的展演、实现,新诗是如何完成自身的形式构造的。
爱与憎:同情的张力
1922年2月22日,郑振铎陪送爱罗先珂乘火车由沪北上,在返程的途中完成了《厌憎》《两件故事》的写作。虽然是相似的主题、人物,两首诗前后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抒情态度。而正是在前后情感的反转中暗含着诗的同情机制实现的可能。《厌憎》一诗,从标题即可体会其中的情感底色,但在具体的展开中情感的流动也并非线性无阻,反而时时暴露出裂隙和挣扎。虽然情感的曲折、挣扎既张布了整首诗的叙事结构,也构成了抒情张力的起承转合,但不难发现诗人始终沉浸在一种内视角中,整首诗的展开都基于诗人“看”“凝视”等主观视角对外在世界的摄取进而又回收到主体的心理内在,正是这种观看机制的设定决定了诗与社会之间仍然是隔绝的、封闭的。《两件故事》则以“听”的方式建立起了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同情完成了由讲述者到接受者的偏移,但同情的生产并未就此实现,而是指向了对一个反思性自我的唤醒。换言之,同情的实现不只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一种无障碍的横移,而是首先依赖于一个反思性自我的产生,抒情主体只有发现自我,才能与他者进行情感的接受和分享。可以说,由“看”到“听”的转换,既是主体自我的觉醒,也是同情实现的开始。
周作人也有两首处理士兵题材的诗,其中也投注了对同情的设想和理解,与郑振铎的两首相比,无论题材内容,还是写作方法,周作人的诗都极为相似,同情在其中既有相当的效力,也有一定的限度。《背枪的人》写于1919年3月7日,而《京奉车中》则于一个月后发表于《每周评论》。在《背枪的人》中,周作人采用了一种转折结构。从“背枪的人”到“朋友”“兄弟”之间的称谓递进,周作人实现了从“我”到“他”再到“我们”的共同体构造。某种程度上,这种情感模式可以看作是“五四”前后周作人的人格理想和主体自我的实现方式,他希望借助情感的再造穿透阶级、身份、智识之间的隔膜,以实现知识与大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但是整首诗的结构仍然是内置在一种“看”的内视点,同情的达成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想象。这样的危机很快在《京奉车中》中得到了印证。同样是面对兵丁,周作人开始也在为同情的发生进行情感预热,但这种准备不仅没有进一步深入,反而暴露出其中情感的障碍。事实上,不是理性阻碍了同情的发生,而恰恰是情感本身的问题。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清晰呈现出了“爱与憎”的复杂辩证。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基于外在行为的情感认同的脆弱性,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情感始终是一种基于“看”的主体投射,而并非一种基于对话、理解的情感交流。“看”的机制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周作人“五四”时期的人格缩影,同情的失效其实也可以看作其后他思想危机的一种预演。
周作人两首诗的抒情目标不是不断制造情感的起伏,而是努力拆除一切的情感障碍,实现一切的和合。这一目标显然不仅左右了诗的结构层次,更决定了更为具体的诗歌技法。与《小河》高度的结构性、象征化相比,《京奉车中》和《背枪的人》无论在结构上还是技法上都大幅度减缩,它们紧紧集中在自我与他者遭遇时的情感直写。这样的写法鲜明地呈现出新村时期新诗对于周作人的独特意义,它不是个人情怀的抒发或者抽象的文类形式,而是一种建构社会理想的文化策略和形式手段。
1920年前后,周作人开始频繁地对千家元麿的诗文进行译介,可见其在周作人文艺思考中的重要位置。周作人从《虹》中摘译的《苍蝇》和《军队》两首诗典型地呈现了千家元麿的诗歌风格。在千家的诗歌构想中,不仅人力之内的阶级身份失去规训隔绝的效力,就连苍蝇、老鼠这种卑微甚至让人厌恶的动物也在其中获取了平等的生命意义。而其方法则在于同情在诗歌中的植入及扩散。感情构成了千家的诗歌起点,他既以此把一切的生命形式纳入自我的理想世界中,通过文法句式赋予这些生命形式以平等和谐的位置,又依托诗歌感受性的扩张来冲击人类之间的隔膜冷漠,构造起一种以情感为基底的和谐社会。这种设想不仅设定了诗歌的抒情姿态和思想内容,同时也决定了具体的技法使用。与周作人的写法类似,两首诗抒情的展开并不太注重技艺的难度,相反它要求一种自然与流畅,因而,语词多是日常事物的复写,句式语调多贴近说话。自然流畅与同情真挚是千家诗歌风格的一体两面。而这种主张与艺术上的一致性并不稳固,山宫允从中看出过分强调真挚同情导致了“拖塌之弊”。艺术上的这种裂隙,在武者小路实笃看来恰恰是千家无法解决的心之动摇。从千家元麿那里,周作人获得了“主义与艺术一贯”的诗歌视野,他不仅共享了同一的同情感受,更借助翻译吸取了诗与同情的辩证关系以及以怎样的技法呈现同情的内在机制,进而将这些经验转化到自身的新诗写作中,做到了技法与同情、形式与思想的统一。但这些情感经验与形式方法并非周作人对同情理解认知的全部,在他的设想中,想象能力的培养也是至关重要的。
想象与“同情”社会
1918年,周作人一方面从当时流行的日俄文艺思潮中辨识出一条同情社会的道路,另一方面他更从所接收的文艺资源中整合出具体的实现方法,即以“想象”实现同情,联结社会。可以说,“想象”构成了当时周作人文艺观的重要维度,在此过程中布莱克显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布莱克不仅构成周作人的重要思想材源,更为其对想象的理解提供直接的诗歌体验和感受契机。
周作人从对布莱克诗歌的理解中领会到“想象”对于以同情为底色的理想社会达成的关键作用。在周作人的认知中,布莱克“特重想象(Imagination),将同情内察与理想主义包括在内,以为是入道的要素”。他又引述斯布勤的话进一步解说。斯布勤又以布莱克《无知的占卜》五六两联作为参考,对比来看,周作人采用了一以贯之的直译方式。两联开始于猎兔的场景,却并不重点描摹“猎”的过程,而是集中于兔被猎之后的痛苦反应。而兔的叫声显然不只是自身痛苦的抒发,更激起了生灵界一系列的同情共感。而“兔”“叫天子”“天使”三种高度之间的层进,以及同情实现的可能,都是基于一种有机的想象。正是依靠想象,对愚弱者悲惨处境的感知,开启了同情机制,以情感认同为基础,不仅激发出实际的行动,当爱与理解成为一种普遍的能力,这种行动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而一个同情社会的达成也就顺理成章。
周作人对斯布勤关于布莱克的阐说理解也极为认同,除了五六联,他还将《无知的占卜》的序文及前十联倾力译出。在他看来,这首长诗内含着布莱克“思想的精英”。而序文四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思想原点的作用,这四句与《华严经》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说法极为相似,都涉及“小”与“大”、现世与天国、时间与永恒之间的转化和辩证。这种相互转化的关节在佛教义理中依赖某种顿悟,而在布莱克的理解中则是一种有机的想象。周作人把它看作一种走向联合、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
在经历1921年前后的思想危机之后,在对雪莱的译介中,周作人仍然对同情式的想象大加推崇。雪莱不仅把想象与人的创造相关联,更从想象的同情理解中看到一种新宇宙诞生的可能。1922年5月30日,周作人译出了雪莱的《与英国人》,一个多月后又写就了《诗人席烈的百年忌》。他将雪莱与拜伦并举,但与拜伦的革命性、破坏性相比,他此时看重的是雪莱的建设性:“在提示适合理性的想象的社会。”这与周作人“五四”时期对诗歌之力的信服极为相似,都强调以文艺移人性情、改造社会。雪莱的政治思想集中在两首长诗《伊思拉谟的反抗》和《束缚的普洛美透斯》中,前者记述反抗者以身殉义,而后者则借用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呼唤一种自由的复得。对此周作人引述了第三幕的诗段,这样理想的人、理想的社会事实上正是周作人“五四”时期投入“新村”的动力根源。而在接下来的第四幕中,周作人更从中整理出了一条可供实现理想的坚实道路,即一种“无抵抗的反抗主义”,依靠“忍受”“饶恕”“爱”等超强的意志品格“希望下去”,“直至‘希望’从他自己的残余创造出他所沉思的东西”。这样“纯朴虔敬”的思想让周作人很自然地将雪莱与布莱克相联结。与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思想方法相比,这其实就是一条培养同情与想象的道路。
由此可知,周作人的“新村”理想并不是完全幻灭了,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他此刻认识到文艺之力并不能兴起直接的政治行动,相反,政治在文艺那里以同情式的想象得到一种新的形式转化。在这样的视野调整中,文艺的效力不是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不断萎缩,而是自身的能动性重新得到激活,而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也随着想象与同情的合理归位反而具有更为切实的实现可能。
郑振铎在社会改造的热情退散之后,也开始对诗歌文艺中的“想象”加以关注,它意味着新诗的成立不仅要依托于情感的真实直接,更需要一种复杂曲折的结构,需要想象在诗歌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条自由出入、相互改造的情感通道。
结语
“五四”时期,周作人重新拾取以文艺改造社会的信心,他从当时流行的日俄文艺思潮中辨识出从“不幸”中翻转出一种同情机制的知识视野,而新诗所内含的同情效力与想象能力则被看作实现“同情”社会这一理想的重要手段。由此,新诗与新社会构成了一种深刻的互文关系,正是在对新社会的构想中,早期新诗获得了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动性,这不仅决定了早期新诗的内容组织,也支配了它的形式机制;而“五四”“社会改造”的理想远景也借助早期新诗的内部延展和形式伸缩获得了一种有效的实现路径。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早期新诗的同情效力也暴露出一定的限度和裂隙,同情的失效不仅可以看作是周作人其后思想危机的一种预演,事实上也可以看作是“五四”一代知识人整体性的危机寓言。这意味着,早期新诗、“五四”一代知识人、“社会改造”事业都将面临新一轮的调适和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