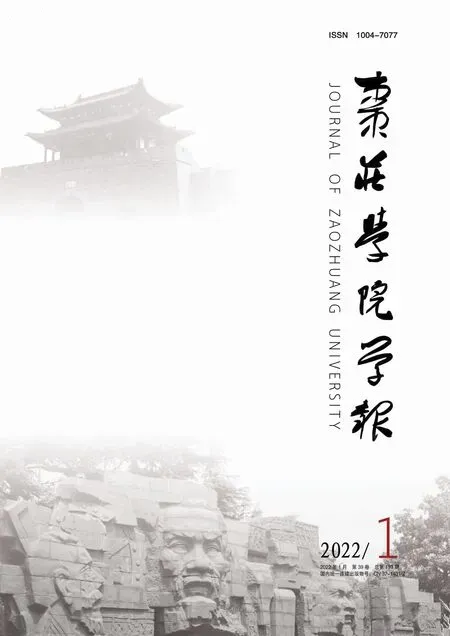《天瓢》:在美的羽翼下超越仇恨
张燕婷
(北京语言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3)
《天瓢》是曹文轩出版于2005年的一部长篇小说,和他以前的小说相比,这本小说有些不同,因为他此前大部分小说都可称为儿童小说,而这本小说显然是一本讲述成人世界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小说的十二章是用雨串联起来的,香蒲雨、金丝雨、枫雨、梨花雨、哑雨、痴雨等形态各异的雨,将小说中地处江南的乡村油麻地笼罩在一片水与雾的诗意世界中,也让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的命运交织在雨水的天地里。作家营造的这个湿润的、朦胧的、唯美的雨世界已然是他所钟情的具有古典浪漫主义艺术世界的延续。
毫无疑问,在《天瓢》构建的这个湿漉漉的雨水世界里、以成人为主体的乡村世界中,男人占据着主体地位,他们在这片巴掌大的湿润土地上争权夺势,陷入了时代与人性共同铸就的嫉妒与仇恨的情感泥潭当中,他们在仇恨中一边制造着动人心魄的事故,一边推动着油麻地历史的发展。而这部以男人为主体的小说也塑造了一个看似不起眼、实则寄予了作家理想主义情怀的女性——程采芹。程采芹身上有诸多美好的人性光辉,她是这片土地上美的象征,她身上充满了爱的光泽,她是仇恨世界中的一束光和一湾泉,融化着冰冷,滋润着心田。程采芹的形象因其理想主义的呈现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她是作为男性的作家笔下的理想女性,正是因为她身上传递的理想情怀,使得她的性格特征不够立体化,有些理念化。她既如阳光一样默默给予爱的温暖,也如大地一样无言地承受痛的现实,她的被动与静默使得她身上缺少生命的能量。
一、苦难世界中美的化身

程采芹的美是油麻地滋养出来的,同时也与油麻地保持着距离。程采芹出生于油麻地的地主家庭,物质上富足,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作为独女,她的父亲程瑶田对她宠爱有加,母亲也对她温柔呵护,可以说,她从小浸泡在爱的环境中。而采芹所生长的油麻地,充盈着雨水、花草、树木、芦苇、河流、虫鸟,自然景物,风情涌动,万物融汇在情与景交织的世界中。采芹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只有三四岁,那是她第一次见到作品中的头号男主人公杜元潮,作者这样写第一次见到杜元潮的小采芹:
“这小女孩一眼就看到了杜元潮,两粒黑晶晶的眼珠像两只落在青枝上的小鸟,落在了杜元潮的脸上。”“她不笑,也不哭,略带一点羞涩和怯意。这个小女孩长得极为清秀……明眸如星,两点清纯的亮光,无声地闪烁。”[2](P13)
小采芹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纯真和秀美,一如曹文轩其他作品中童真世界里的孩子,与成人世界保持着距离,那里是一种更为纯粹的原始天地,这个天地中的孩子与植物、鸟虫、河流、天空更加近,在自然的天地里追逐更本真的所在,所以,他作品中的孩子喜欢听昆虫的鸣叫、河水的潺潺、雨滴的鸣唱,看白鸟的穿行、云朵的形状、湿漉漉的花朵。那也是人类童年想象中的诗意和愉悦。童年世界中采芹的美是清新脱俗、灵动宜人的。在细雨蒙蒙中,一株枝繁叶茂的老槐树下,一池清香袭人的荷花池边,稚气的采芹第一次朦朦胧胧地感受到男女之间的别样情爱,赤身裸体的采芹“像一朵在晨露中开放的花苞,慢慢地开放了”[2](P29)。这朵含苞待放的花,开放的过程是美妙的,同时也渗透着苦难和忧伤。
不同于其他小说营造的纯粹的童年世界,《天瓢》中的世界有浪漫和诗意,更有苦难和仇恨。采芹被爱包裹着的世界并不长久,油麻地被卷入了阶级斗争的风波中,大地主程瑶田的家产被瓜分,一家人战战兢兢地躲避着批斗,年纪尚小的采芹亦被扣上了“小地主”的帽子,遭到歧视和谩骂。“小地主”的身份中其实也包含着人们的嫉妒和孤立,在阶级斗争的时代浪潮中,被压抑的仇富心理被激发,富者被意指为富不仁,于是,向来宽厚的程瑶田被殴打指责,乖巧善良的小采芹也遭孤立欺辱。她身上的优点反成缺点。在油麻地孩子眼中,“采芹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像是被晶莹的白雪洗出来似的”[2](P55),即便采芹跌落他们中间,“她还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的洁白无瑕,那么的与众不同”[2](P55)。这样纯洁美好的采芹因其与众不同而被孤立,被憎恨,于是乎,作者将采芹写成“唯一的一朵白云,在空无一物的天上,空悠悠地飘着”[2](P55)。可见,在作者眼中,孤独、纯真的采芹即便身在一个充满恶的环境中,却出淤泥而不染,远远地超越了恶。她成长的温柔的环境赋予了她善良和干净,她不得已而为之地与人群保持着距离,充满喧嚣、恶意的环境反衬了采芹的纯美与善意。采芹身上所具有的这种不着尘埃的美感与小说中的诗意自然世界融为一体,这样纯粹的美在那个滋生恶意的时代里,显得高贵而卓然,“将恶放在美的羽翼下处理”[3](P89)成为作家的一种写作策略,让人在美的感染中去超越人间的仇恨,消解内心的狭隘,在美的熏陶下实现心灵的净化。
曹文轩的作品尽管是诗意的,但总是涌动着苦难的尘埃。作者曾在《美丽的痛苦》一文中写道:“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将继续延伸下去。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4](P262)《天瓢》中,尽管采芹美得脱俗,但是她却不断地遭遇苦难,又不断地直面并消解苦难,她也一直保持着一种隐忍却又优雅的姿态。采芹儿时家庭从富裕中跌落,变得一贫如洗,母亲早早病故,因贫穷学业中断,从事繁重的农事,爱情不如意,婚姻为无奈之选,但她从来没有在这些苦难中沦陷。成年后的采芹“由于磨难与劳动,既增添了几分迷人的忧郁,又增添了几分动人的健康”[2](P67)。她面色红润,两眼流盼,黑发柔亮,腰肢柔韧,更有风韵,她依旧独自一人,与人群保持着距离,即便是采桑叶,采芹的动作也独具美感。出嫁后的采芹在杜元潮眼中“还是那样的姿态——风情流转不衰的姿态,让人面热心慌腿软却又不敢顿生邪念的姿态”[2](P135)。丧夫后的采芹“悲哀洗尽了风尘,只剩下冰肌玉骨,瘦劲却又柔弱地在天地间沐浴着清风”[2](P194)。获得期望已久的爱情后的采芹脸色苍白中透着红润,双眼忧伤中含着“妩媚而纯静的明亮”[2](P200)。即便五十多岁的采芹,依旧是“一副柔韧的身段,肤色越发的白净”[2](P280),举止非同寻常。
采芹面对苦难的优雅姿态来自于她内心的纯粹、安宁和善良,而她这样的内在品质令她呈现出一种羞涩之美。在舍勒看来,“羞涩是美的,因为它是一种美的、完全直接的美的承诺。它的承诺方式是‘美的’,因为这种承诺是无意的承诺,通过对美的东西的掩饰,它才无意识地指出美的品质的隐秘存在。(灵魂的)羞涩想要掩饰的是善”[5](P216)。羞涩的情感始终与采芹如影相伴,孩童时的小采芹眼中的怯意和赧然自不必说,即便她成人,依旧保留着这份羞怯。青春期的采芹因情窦盛开、身体发育脸上染上了红晕。出嫁以后,她依旧时常满脸绯红、难掩羞涩。“真正的羞始终建立在对肯定的自我价值的感受之上。”[5](P215)这种自我价值是对善的守护,也是对爱的呵护,羞涩令生命变得高贵,也具有了审美的属性。采芹的羞涩正是因为她保存着心灵世界的善良与纯真,她的羞涩与她所处的那个暴露的、直白的、仇恨的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在面对苦难,采芹始终是静默的,她内心尽管有忧伤,但始终安宁,丝毫没有沾染上环境中的怨恨与仇恨。她始终如一朵静静盛开的花朵,在大地上舒展而自如,默默承受,毫无怨言。在她从富家小姐变成农家村姑时,她也只是安静地从事着农事,没有怨恨周围人对自己家庭财富的剥夺。在她即将嫁给一个不爱的人时,她安静地坐在院子里做鞋、做衣服,“她的心里会流过一丝温暖,同时也会流过一丝伤感”[2](P110)。她的爱人杜元潮没有选择她,她内心悲痛,却没有质问和痛哭,她只是“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只是“感到疲惫和衰老”。[2](P95)采芹身上呈现出的这种静态美是古典的,哀而不伤,悲而不戚,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属性。她独特的美的气质连同诗意的自然也为那个喧嚣杂乱的土地保留了一些纯静。曹文轩认为,“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会成为常识,甚至会衰老与死亡,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具震撼力与杀伤力的并不是思想,而是美”[6]。作家在作品中构筑的这种无声的美感本身也是一种思想和反抗,是对人世间因欲望和争斗造就的丑与恶的无声批判。
二、仇恨世界中的爱之精灵
《天瓢》中的世界是浪漫唯美的,也是凶狠残酷的。在油麻地这片土地上,仇恨的阴云笼罩,权力的浓雾蔓延。自大地主程瑶田被打倒之后,李长望、杜元潮、邱子东、李大国连番在计谋与仇恨的推动下争夺权力。黑格尔等思想家都认为,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油麻地却也是在恶的推力下气喘吁吁地前行。这个恶的面目主要表现为嫉妒与仇恨。舍克在《嫉妒与社会》中谈道:“人是一种嫉妒的生物,如果没有在被嫉妒者身上随之而产生的社会抑制,那么人就不能发展社会制度。”[7](P1)嫉妒是人的天性,嫉妒并不仅仅产生恶的结果,但没有节制的嫉妒,便会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仇恨与暴力便是其负面影响。在油麻地上,李长望激发了村民的仇富心理,即便地主程瑶田并没有欺压百姓,也令村民心中燃烧起仇恨的火苗,这是贫穷对富裕的仇恨。于是,抢夺、殴打开始了,嫉妒变成了仇恨,仇恨变成了暴力。在这个仇恨的环境中,杜元潮、邱子东、李大国深受影响,只不过,他们的仇恨是深藏于心的,他们更工于心计,更善于手段。于是,仇恨造就的一班班领导班子在油麻地不断更换,推动着油麻地的前行。
程采芹是个例外,这个例外源于她是一位女性,一位在这个仇恨的世界里没有沾染一丝仇恨的阴翳却内心充满着爱的女性。在浸染着仇恨的权力天地中,男性永远是主角。历史是由男性创造的,目光炯炯的男性在欲望的支配下气势汹汹地向外部世界拓展,去攫取更多的资源和利益的同时也推动着有形世界的改观,他们以征服的方式获取力量,既征服世界,也征服女人,在男性构建的家园里,充斥着视力所及的一切,却缺少视力不及的东西。而善于倾听的女性驻守在情感的空间里,召唤着男性的回归,呼唤在外部世界驰骋的男性去瞭望他们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女性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亦是情感的守护者,她们默默守护着原初的家园,谛听着生命的律动。《天瓢》中的程采芹始终与男性权力的视觉世界保持着距离,而驻留在情感的领地,默默地给予爱,也默默地承受痛苦。程采芹对杜元潮的爱,便是一种温柔包裹着的给予。童年时的采芹便格外喜欢这个与自己家庭背景悬殊的男孩。遭遇变故后在苦难的环境中长大的采芹,再也不是富家小姐,且早早辍学在家务农,但她内心温暖如初。采芹与杜元潮相互爱慕,青春期的他们含蓄羞涩地表达着感情。但当事业和爱情摆在杜元潮面前时,杜元潮选择了事业,油麻地书记的身份远远大于程采芹丈夫的身份。采芹对杜元潮没有选择自己这件事并没有怨恨,只是默默承受。她自知自己地主家庭出生,不愿给杜元潮带来麻烦。对于杜元潮,采芹不仅表现出情爱,也有母性的一种温柔的爱意。在她即将嫁人时,她第一次主动地来找杜元潮,只是她并没有质问杜元潮的选择,而是表达她内心的情感、给予她宝贵的东西。采芹将自己赤裸的身体展现给杜元潮,像是某种爱的仪式,一种心甘情愿的付出。她的身体在月光下、苹果香气中、粉末样的雨丝里、潮湿的草丛中,在萤火虫点亮的微光里,美得炫目。她知道她的身体是自己最宝贵的,也是杜元潮最渴望的一样东西。采芹的这个行为是爱的表达,对爱的主动献身,此时她对杜元潮的爱不仅仅关乎情爱,还有一种母性的温存,她只是想给予他最渴望的东西。
“采芹笑了——杜元潮虽然不能看见,但他分明感觉到了。她笑得像一个怜爱弟弟的大姐姐,尽管实际上杜元潮大于采芹,且平素采芹在杜元潮面前也一直是小妹妹样。然而,今晚,这细雨霏霏的今晚,无论是采芹自己,还是杜元潮,都觉得两人颠倒了一个个儿:她是姐姐,他是弟弟。”[2](P106)
这里的采芹所呈现出来的形象,俨然包含着一定母性的情感。这种母性的情感中蕴含着更多的是深广的爱与同情。作品还有类似的情感流露,比如,采芹“觉得这一时刻的杜元潮,像一个婴儿”[2](P233)。采芹对杜元潮的爱更多的是一种给予,而非自私地占有,“以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所体验到的爱是对‘爱’的对象的限制、束缚和控制。这种爱情只会扼杀和窒息人以及使人变得麻木,它只会毁灭而不是促进人的生命力”[8](P35)。爱一个人应该去给予、去关心、去承认对方,此过程便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谈道:“爱是一种活动,不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它是‘永恒的’,而不是‘坠入情网’。用最通俗的方式可以把爱的积极性表述为:爱主要是‘给予’,而不是‘接受’。”[9](P25)正是在给予的行为中,才体验到人的能力,感受到生命力和潜能带来的快乐。采芹的这种无我的给予始终如一,她无声地认可了杜元潮做出的在权力的角逐场争夺的选择,而默默退守在情感的边缘地带,去呼唤、包容、安慰着在男性世界中驰骋着的疲惫不堪的杜元潮。当杜元潮在婚姻选择上需要她,将她看作唯一的依靠和知己,她心甘情愿地去做红娘,帮助拉近杜元潮和艾绒情感距离;杜元潮家里遭到一次次的变故时,她体贴地帮助他和艾绒,并安慰杜元潮;当权力稳固的杜元潮向采芹求爱时,她又一次满足他,抚慰他在官场和家庭中疲惫不堪的身心;即便在杜元潮的生命尽头,采芹早就为他准备好了入棺的新衣鞋袜。采芹的爱是感性的、被动的,也是无私的、宽广的,这爱中包含着无言的守候与痛苦的承受,是女性传统的宁静的守望之爱。在爱的边缘地带观望着的采芹,不会过问并插手杜元潮的权力之争,唯独在杜元潮和邱子东的明争暗斗中,表现出了关切之情,因为他们二人都是她的朋友。采芹不止一次地劝说杜元潮,让他放邱子东离开油麻地,也多次劝说邱子东,让他离开油麻地,因为“一根牛庄上拴不了两头牛”[2](P137)。只是,被仇恨和权欲折磨着的杜元潮和邱子东,无论如何都不会听从采芹的劝说。他们一直暗暗较劲,通过阴损的手段打击对方,而结局却是两败俱伤。在男性的历史中,女性的话语总是微弱的,力量是渺小的,对于女性情感的呼唤,男性早已失聪,无法听到她们心灵的召唤。“视觉的执拗远征来自于其无休止的欲望,它中断了本源同未来的联系。基于此,唯有回到女性那里,男性方能重新找到自己的未来。”[10](P98)所以,小说中程采芹的意义便是爱的呼唤,呼唤男性从理性的权力世界淡出,因为这个世界仇恨遍野,险恶丛生,无益于人的积极意义上的成长,只能带来悲剧。因为,“生命本身即善,恶的存在也必须首先借助善的力量”[10](P139)。
采芹的爱还体现为对待杜元潮妻子艾绒的方式,这种爱是一种女性之间的温柔爱意。女性的情感细腻而丰富,更富有同理心,她们拥有更多的共同性的生存体验和情感体悟,因而,“女性的经验产生着更多的关爱契机,而这些契机又引发了个人对于那些受困之人的同情之感”[11](P159)。而且,“女性被认为比男性更体贴、更温柔、更有爱心,因此更适合做朋友”[12](P8)。而采芹和艾绒因为对同一个男人的爱,而命运相连,采芹丝毫没有觉得艾绒的出现剥夺了杜元潮对她的爱,在采芹眼里,艾绒“可爱得让人心疼”[2](P164),她对艾绒有一种姐姐对妹妹的怜爱和亲昵,她们两人都性情柔和、温顺,她从艾绒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让她对艾绒有一种身为女人同病相怜的感觉。她们初次见面便同床而睡,采芹向艾绒讲述着杜元潮的小时候的故事,难以入睡的采芹“用手抚摸着艾绒一条露出被外的不安分的大腿。她没有用粗糙的手掌去摸,而是用手背轻轻地摩挲着。她觉得艾绒的皮肤十分的光滑……”[2](P167)这里,采芹再次表现出一种母性的爱,这种宽厚的爱超越了一切嫌隙和怨恨,将女人之间的猜忌洗涤一空。此后,“她们以姐妹相称,采芹称艾绒为‘绒妹妹’,而艾绒则称采芹为‘芹姐姐’。她们喜欢这样叫着,这样叫着的时候,会有一种暖流从苦涩的心田甚至是从苍白的灵魂流过”[2](P168)。这是两个女人因对同一个男人的牵挂而生出的一种同理心,她们之间更加能感受彼此的内心,那是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所致。采芹在杜元潮和艾绒唯一的孩子琵琶不幸落水身亡后,艾绒一蹶不振,采芹主动对杜元潮说:“她心里难过,你一个男人家,总该知道安慰安慰她。她心里苦,比油麻地任何一个女人心里都苦。”[2](P255)采芹对艾绒的关爱让杜元潮感动,以至于久在权力场上角逐的他生出了“一种柔和的、温热的感觉,甚至有点儿感动,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让人有点儿悲悯”[2](P260)。这种女性之间的爱无意间感染了杜元潮,令其内心生出一种温柔的情愫,甚至荡开为悲悯的情感,这也是他微弱地聆听到的女性情感的呼唤,事实上,“女性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中一直担当着原初意义上的‘第一性’的性别角色。正是她的召唤萌生了男性的回应,让他在孤独的巡视中学会了借助倾听发现他用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10](P96~97)。
在油麻地这片土地上,采芹的爱如这里的土地,默默地承受且给予,也如油麻地充沛的水一样,滋润万物,润物无声。水也是曹文轩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上善若水,遇圆则圆,遇方则方,水有弹性,水的力量比看上去比有力量的东西还要强大”[13]。水的力量也是善的力量,大善如水,尽管看上去柔和,却有无法阻拦的力量。世间的恶不是绝对的,但爱却是永恒的。永恒的爱、善、美也是曹文轩作品中一直呈现的主题。
三、喧嚣男性世界中的静默“他者”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采芹身上寄予了作家的理想主义情怀,她身处仇恨遍野的世界,却一直与仇恨、纷争、粗野的人群保持着距离,洁身自好。她优美恬静、善良柔和、包容宽厚,姿态优雅,有一颗高贵的心灵,她是爱与美的化身。但是,也正是因为作家在采芹身上赋予了太多美好的品质,承载了太多理想的元素,以致于程采芹这个人物形象不够饱满而丰富,从而流于理念化。她微弱的声音和内心的苦楚很难被听到被看到,她只能成为男性坚硬世界里的温柔点缀。
波伏娃认为,“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14](P9)。在油麻地,程采芹相对于男性主体而言,亦是他者,是客体,是非本质。她永远在边缘的地带或凝视、或陪伴着男性,她不去改变也不参与作为主体的男性的事业。她属于家庭,不属于政治生活,不行使公共职权。因而,女人“这种纯粹情感的生物的角色,就是妻子和家庭主妇,她不能与男人竞争”[14](P161)。男人一直在行动,女人则总是在爱。因而,在《天瓢》中,男性人物更多也更饱满,诗意浪漫的油麻地上响彻着男人的脚步声和呐喊声,而女性人物量少且单薄,她们薄弱地镶嵌在雄性的世界里,声音微弱,内心萎顿,无言守候,她们是被观看的,而不是被聆听的。
采芹作为理想的化身,尽管身上积聚着爱与美的光辉,但作为一个人鲜活的姿态,却呈现不足。她在男性的世界里从来不是主体,而只是陪衬。采芹的爱是一种无私的给予,默默付出自己,这让她的爱宽容而博大。但是正是这种无私,使其缺失了自我,这种无我的爱令其内心苍白而单薄。安·兰德认为,“只有理性的自私者,只有自尊的人,才能够爱——因为只有他能够持有坚定、一致、不妥协、不背叛的价值。不珍视自己的人也不可能珍视其他任何事物或任何人”[15](P22)。采芹对杜元潮的爱正是缺少了自我,她的无私造成了她的爱缺乏理性,从而对自我不够尊重。“从爱中追求并赢得的正是个人的、自私的幸福,这种幸福来源于爱。”[15](P38)
而采芹只一味地付出,被动地等待和接受,不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不去为自己的幸福争取什么。当采芹发现对自己有感情的杜元潮开始疏远自己时,她“心中不仅是疑惑,还有失望、哀伤,甚至还有一种令人心灰意懒的失败感。她很想直截了当地问杜元潮到底是为什么,但她终于没有问”[2](P95)。在她出嫁前,她内心始终渴望杜元潮的出现,但也仅仅是“一份期待,似有似无的期待”[2](P110)。当她丧夫以后,杜元潮情难禁地在她丈夫坟头占有了她,她也只是被动地接受,此后她接受着权力傍身的杜元潮一次一次对她身体的占有。采芹对杜元潮的爱是给予,但也是被动和接受,她对杜元潮的爱胜于对自己的爱,正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爱的缺失,令她的爱变得有些单一,令她的心灵有些苍白。所以,采芹在小说中总是发出轻轻的叹息声,在她爱而不得时,她“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心头掠过一阵悲凉”[2](P95);她出嫁前,心里流过一丝伤感,双眼微微发红;[2](P110)她帮杜元潮促成婚姻时,心微微作痛,泪水从眼角滚落。采芹无声地承受着太多的苦楚,在感情中压抑着自己,她的沉默和被动令她缺少个人的主体性。这令她的形象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道德阴影,一个完美的女性,却不够真实。
曹文轩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其叙事立场也是男性立场。他对采芹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杜元潮和邱子东的眼睛塑造的,程采芹的形象中凝聚了男性的目光。在对采芹的身体描写上,包含着男性凝视下的欲望目光,采芹光泽的黑发,无声流盼有了水性的双眼,向上翻起湿润的上唇,线条清晰的下巴,不大不小圆鼓鼓的臀部,扭动着的柔韧的腰肢,白嫩的面容,胸边的血珠样的红痣,风情流转的姿态等等,这些身体描写的背后都暗含着一道男性欲望的目光。小说有很多对采芹外形、神情的描写,却淡化了其心理上的描写,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采芹的形象缺少了复杂性和深刻性。在男性的凝视中,采芹不仅性感迷人,单纯羞涩,而且善良温柔,无私奉献。她身上富有着传统的道德美,而这种美好的品质主要表现在她是男性的抚慰者和避风港,是男性眼中的理想女性,这种理想女性只能是作为情人、妻子、母亲的统一体存在,作为仁慈、救赎、奉献的化身存在,而不能是公共场域的历史主体性存在。因而,男性眼中的理想女性也注定要守候在家园里,而被边缘化和工具化,“女性既是男性的自我观照、移情之对象,是男性目光有意制造出来的美好品德,同时也是他们的占有之物,即男性欲望需要美好女性的抚慰和关怀,而且也是一种单向度的占有和凝视。凝视的眼睛一直亢奋地向前寻找着、膨胀着、占有着。”[16](P53)这是采芹这一形象的缺陷所在。
不过,男性的凝视之眼也有某种超越性的所在,他们依旧在女性身上寄予了梦想。“女人是有巨大诗意的实体,因为男人在她身上投射了他决定不愿成为的一切。她象征着梦;对男人来说,梦是最内在又最外在的在场,是他不愿意要、不愿意做却又渴望和不能达到的东西。”[14](P253)这种梦是抽象的善良、仁慈的温柔,虽然她们是他者、边缘者、抚慰者,却也是缪斯、女神、圣母,是大地、水、家园。所以,《天瓢》中采芹身上尽管包含着男性欲望化的凝视,是作为男性抚慰者的他者,但仍然散发出巨大的女性的爱与美的能量。尤其是在充溢着仇恨与暴力的土地上,她那种超越性的人性光辉如夜空中的辰星闪烁着光亮。作者曹文轩亦是很诚恳用心地塑造了程采芹这一女性形象,正是通过这一形象作者告知我们,爱永远比恨更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