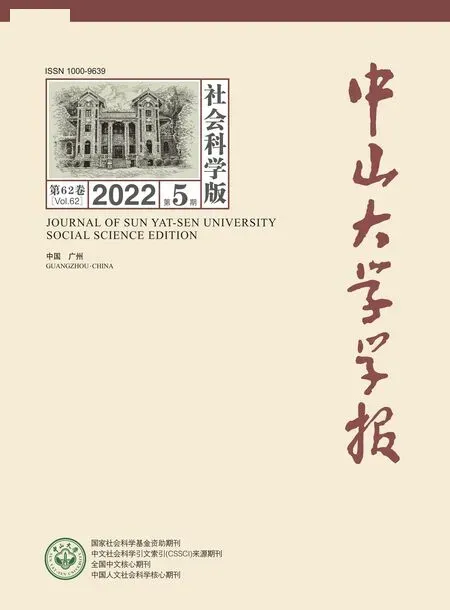超越实在论与观念论*
——胡塞尔超越论的观念论新探
谢利民
在“观念论”这一名目下,人们最常想到的是贝克莱式的主观观念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验观念论。胡塞尔一再将现象学宣称为观念论(Idealismus),乃至超越论的观念论(transzendentale Idealismus)①Transzendental 一词由于在欧洲哲学史上得到不同哲学家的运用而具有了各依语境的不同含义,这也导致国内学界对该词的汉译莫衷一是。概言之,译见有三:一、康德的译者邓晓芒、李秋零悉作“先验的”,孙周兴更是主张该译法对于不同哲学家的通用性(参见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1页及以下);二、王炳文在《第一哲学》与《危机》中译作“超越论的”,并维护该译法在胡塞尔翻译中的适用性,倪梁康则更是期待该译被纳入康德翻译(参见倪梁康:《TRANSZENDENTAL:含义与中译》,《南京大学学报》2004 年第3 期);三、王庆节则介于二者之间,主张一词两译,即在康德哲学中译作“先验的”,于胡塞尔哲学中作“超越论的”(参见王庆节:《“Transzendental”概念的三重定义与超越论现象学的康德批判——兼谈“transzendental”的汉语译名之争》,《世界哲学》2012 年第4 期)。私以为,由康德和胡塞尔的主要著作来看,将transzendental 通译一词,理据不足。康德所谓transzendental 乃针对认识方式的先天性而言,而非意识的自身超越的特征,宜作“先验的”;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把论域限制于经验范围内,transzendent不超越经验,transzendental 也不先于经验,而是指涉对意识之超越活动及其结构的反思,宜作“超越论的”。因此,笔者在此暂行一词两译。值得注意的是,倪梁康最近重提transzendental 的翻译问题,并预告将翻译《哲学概念历史辞典》“transzendental”条目(参见倪梁康:《“Transzendental”:含义与中译问题再议》,《学术月刊》2022 年第4 期)。这一系列动作将引发学界怎样一轮新议,又将带给这个难题怎样一番前景,值得期待。,不过对他而言,是笛卡尔而非贝克莱或康德,首先通过开启“我思”这一作为一切认识之绝对基础的内在领域,创立了超越论的观念论。胡塞尔的这一追认引发了人们关于他对世界之实存的(哪怕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怀疑论立场的长期质疑,这种嫌疑通过《观念I》中那个著名的“取消世界”的思想实验似乎彻底坐实。学界对这一质疑已有不同的回应,回应的方式最终取决于回应者对胡塞尔超越论观念论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解释。围绕胡塞尔的形而上学立场问题,学界目前形成了几种对立的观点:观念论、实在论、反实在论和形而上学中立①Jeff Yoshimi,“The Metaphysical Neutrality of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in Husserl Studies 31,2015,pp.1-15.。胡塞尔超越论转向的最主要批评者恰是胡塞尔的早期追随者(慕尼黑和哥廷根现象学圈成员),他们批评胡塞尔的超越论转向背叛了现象学的实在论立场。然而吊诡的是,当今的多数胡塞尔辩护者无论持上述何种主张,都不仅无意挑战批评者实在论的预设立场,反而致力于消除超越论转向所引起的紧张关系,要么主张超越论观念论是一种变相的实在论,要么主张二者至少是相容的。笔者认为,超越论现象学根本不在从观念论到实在论的形而上学光谱之中,也不在如下意义上“形而上学中立”,即它原则上可与包括观念论和实在论在内的各种形而上学立场相容。既不持论,也不中立,那该如何评判其形而上学立场呢?答案是不可评判。因为超越论现象学通过悬搁观念论与实在论的共同预设,使一切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和观点都失效了。为使胡塞尔规避怀疑论嫌疑,根本无须求诸实在论,相反,超越论现象学原则上恰恰与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立场的实在论绝不相容,但这种不相容性并不会使前者落入主观观念论的窠臼。
“观念论”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被胡塞尔赋予不同含义,准确地说,是因不同的论证方式而含义各有侧重。本文通过系统辨析胡塞尔观念论的各个面相,试图澄清他如何在实在论与观念论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胡塞尔因为悬搁实在论的设定失去了一个神秘的自在世界,又因为拒绝观念论的虚构失去了一个虚假的表象世界,然而却通过揭示实在客体及其世界的超越论意义,最终赢回了在超越论反思中自身显示因而真正可理解的现象世界。这个现象世界不是在上述“两重世界”之外的第三重世界,而就是“两重世界”的自身构造。
本文分为三部分:首先,胡塞尔通过超越论还原破除素朴的实在论立场,揭示的是实在世界与纯粹意识的本质关联,据此设想的取消世界的可能性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设想性;其次,胡塞尔把观念论的中心从纯粹意识转移到现时在思的意识,以现时意识的一致性经验确证了实在之物及世界的现实存在;最后,实行着现时意识的超越论自我的事实,不是实在世界中的经验事实,也非绝对观念论的精神实体,而是一种在超越论构造中显现出来的,先于自然与精神、实在与观念之分的原事实,先于一切现象之分的原现象。
一、从承诺实在到“取消世界”
在《逻辑研究》中,现象学就被理解为一种观念论,但不是指类似传统观念论那样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教条”,而是指“这样一种认识论形式,它不是从心理主义的立场出发去排斥观念之物,而是承认观念之物是所有客观认识的可能性条件”(Hua XIX/1,112)②凡本文所引Husserliana,皆只在正文附注德文全集版卷数和页码。本文所引Logische Untersuchungen(Hua XVIII,XIX)参考倪梁康译:《逻辑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他在这里先做了一个否定表述,再在与被否定的立场相对的意义上正面立论,这是因为观念论的核心意涵——观念之物作为客观认识的可能性条件——是通过对胡塞尔本人曾奉行过的心理主义哲学立场的突围实现的,而这种把一切对象还原为主体内在的心理表象的心理主义,是一种贝克莱式的主观观念论。因此可以说,胡塞尔的观念论与心理主义的区隔就是现象学突破的真正内涵所在。
“范畴直观”或“本质直观”的发现冲破了康德为感性与知性,直观与范畴所划定的界限,使范畴能够在直观中原本地被给予,因而具有了自明性,并使得在康德那里始终悬而未决的范畴本身的正当性最终得到了自身证明。胡塞尔观念论之所指(即便限于《逻辑研究》),仅仅在于接受范畴和本质这类普遍之物吗③威拉德给出了明确的肯定回答,参见Dallas Willard,“Realism Sustained? Interpreting Husserl’s Progression into Idealism”,Quaestiones Disputatae 3(1),ed. by Kimberly Baltzer-Jaray,2012,pp. 20-32。?当然不是,问题还在于普遍之物或观念之物何以构成一切客观认识的可能性条件。我们知道,传统理性主义用以标识这种条件的概念是“先天”,如康德就把范畴视为理性的先天形式条件。如果观念之物是在一种直观中被给予的对象,而非一种内在于主体的、规定其认识行为的主观条件,那么它如何担保我们对客体之认识的客观有效性呢?答案就是现象学对“先天”的改造。为了解释意识对象的形态,以间接推论的方式(如康德的先验演绎)回溯到一个处于意识之外或之前的非直观领域(主体性的内在领域),这在胡塞尔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学的“先天”不是先于一切可能经验的纯粹主体行为,而是通过本质直观的明见性自身被给予的本质,它作为客观认识的可能性条件,不是从意识之外给我的意识行为强加一种必然性,而是就在意识经验之中当下在场并使得经验对象得以作为某物显现出来,在此,作为“先天”的本质或观念是经验对象在意识中自身构造的环节。任何一个完整的意识行为(无论本质直观还是感性直观)都是观念直观行为(Ideation),当然不是说仅以观念为意向对象,而是说每一个意识都是对被意识到的内容的同一化(identifizieren),而意识内容的这种观念性的同一(Identität)才使得客观的对象性成其自身①戴维·史密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主张胡塞尔超越论的观念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意向性指向如何依赖于观念性的含义(David W. Smith,Husserl,2. edn,Oxford:Routledge,2013,p. 166)。。
当然,这还不是胡塞尔观念论的全部含义。《逻辑研究》侧重探究意识活动的意向性和观念性特征,尚未关注实在之物及其世界与超越论主体性的先天相关性,因而此时的观念论还只是一种“认识形式”(Hua XIX/1,112),尚未获得其完整的超越论形态及明确的形而上学意义。《逻辑研究》的形而上学立场也是学界热议多年的一个话题。莫兰认为,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立场有些含混,但对感知行为直接把握实在客体的强调表明他此时还是倾向于经验实在论②[爱尔兰]德尔默·莫兰著,李幼蒸译:《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2—143页。。扎哈维则旗帜鲜明地主张《逻辑研究》的形而上学中立性,理由是胡塞尔此时明确拒绝任何有关独立于心灵的外部实在的问题③Dan Zahavi,Husserl’s Legacy. Phenomenology,Metaphysics and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 32 ff.。首先必须指出,莫兰与扎哈维立论所针对的问题并不完全重合,前者指向的是《逻辑研究》隐含的形而上学立场,后者则强调胡塞尔此时自我标榜的形而上学立场,这使二者没有表面上那么针锋相对。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确实声称“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和自然的问题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Hua XIX/1,26),明确把它从作为纯粹认识论的现象学中排除。然而胡塞尔在《逻辑研究》时期并未明确反对其追随者的实在论解读,在超越论转向时期又回头批评《逻辑研究》的心理主义残余,从这些事实都不难看出,《逻辑研究》时期的胡塞尔仍然不自觉地倾向于一种朴素实在论的立场,即主张意识直接把握实在客体的经验实在论。不过要注意区分经验实在论与形而上学实在论,实际上,前者并不是一种明确的形而上学立场,因为它只是肯定了心灵与实在之间在知识学上的符合关系,但并未包含对实在的存在学地位——即依赖于或独立于心灵——的论断。
为了破除《逻辑研究》中隐含的实在论立场对超越性世界与超越论主体的先天相关性的遮蔽,胡塞尔引入了一种新的本质直观,即超越论还原。于是,《逻辑研究》中着眼于意识活动的本质结构的观念论就深化为《观念I》中探讨对象性本质与主体性本质的先天相关性的超越论的观念论,即超越论现象学。
如前所述,胡塞尔现象学的超越论转向并不见容于他的一些追随者,他们视之为现象学创始人向主体主义形而上学的倒退。英伽登(Roman Ingarden)就坚决捍卫世界的自在性,认为胡塞尔对实在论的背叛使他陷入与日常信念相悖的现象主义④Roman Ingarden,On the Motives which Led Husserl to Transcendental Idealism,trans. by A. Hannibalsson,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5,pp. 5 ff.。海德格尔也把《观念I》中意识的绝对性理解为“主体性先行于一切客体性的优先地位”,并将之定性为一种“新康德主义意义上的观念论”①Martin Heidegger,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GA 20,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79,S. 145.。然而这些批评并未使胡塞尔做出丝毫妥协,直到1930年他还不惮于“明确宣称,对于超越论现象学的观念论,我一字不易”(Hua V,150—151)。同时期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也毫无保留地把超越论构造的现象学视为“超越论的观念论”,然而明确排除了心理学观念论与康德式的观念论,并对这种全新意义的观念论做出了解释:“它只不过是以系统的本我学的科学形式所前后一贯地实行的一种自身解释,即把我的自我解释为每一种可能认识的主体,也就是说,就存在者的每一种意义而言,存在者只有以此才能对我这个自我有意义。”(Hua I,118)
存在者对我的自我的依赖关系基于《观念I》中的一个基本观察,即事物与体验这两个存在区域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体验实项地包含于与之同属一个体验流的对体验的内感知,事物则仅仅是意向地而非实项地“包含于”外感知之中。这两种存在的不同被给予方式决定了二者之间的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物的世界的撤销并不影响体验流的存在,因为不管意向得到的是充实还是失实,意向的对象是被确证还是被推翻,意向活动本身依然发生了,“因此,内在的存在无疑在如下的意义上是绝对的存在,即它在本质上不需要任何‘物’的存在(nulla‘re’indiget ad existendum)”(Hua III/1,104);相反,超越之物作为经验关联体总是某种确定有效的意义统一体的关联体,而意义统一体又只有通过意向性意识的赋义才得以形成,所以意识对于实在存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在以上这种超越论的观念论的模型中我们不难发现笛卡尔主义的影子,其实《观念I》这种通过“取消世界”来获取作为现象学剩余的绝对意识的做法,确实也被视为超越论现象学的笛卡尔式道路。然而胡塞尔批评笛卡尔把自我偷换成作为取消物体后的世界剩余物的心灵,从而无法在意识与超越之物这两种存在者之间建立起超越论关联。这种批评其实已经把纯粹意识与笛卡尔的我思区分了开来:前者不再是在世界之内的实在的“心理物理”关联体,而是“独立的存在关联体,一种绝对存在的关联体”(Hua III/1,105);后者则不是纯粹的本质关联体,而是具体的、个体性的实在意识,其存在不具有纯粹本质的必然性。作为经验事实,我思必然具有时间性的特征,是在时空中发生的自然事件,因此只具有相对于纯粹意识的第二级的和相对的意义。
然而通过排除笛卡尔式的心理主义嫌疑,是否又如何能够规避对胡塞尔关于世界之实存的怀疑论立场的质疑?根据胡塞尔的说法,超越论的观念论就是超越论的主体主义,其任务是理解一切可能对象与超越论主体的先天相关性。这种本质现象学只能论证对象的观念可能性,无法保证其现实性,也就是说超越的对象及其世界有可能并不实在。但是这绝非一种笛卡尔式的“取消世界”,因为实际上胡塞尔从未否定,甚至可以说毫不怀疑世界的存在。首先,胡塞尔在《观念I》中设想消除的只是“超越之物”和“物的世界”(Hua III/1,104),并未排除观念对象的被给予性,而如第一部分所述,现象学的观念不像在笛卡尔那里一样属于内在领域的心理之物,而是在世界视域中被给予的对象,因此作为一切对象之总体视域的世界也就未受到怀疑。其次,即便对于超越的物和世界,超越论还原也只是悬搁而非否定其实在的存在,换言之,胡塞尔不是像笛卡尔那样,在事实的我思的基础上怀疑世界存在的现实性,而是根据纯粹意识的本质规定承认世界不存在的可能性。扎哈维认为,实在世界不存在的可能性实质上就是非意向性经验的可能性②Dan Zahavi,Husserl’s Legacy. Phenomenology,Metaphysics and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p. 103.。这种理解值得商榷,因为对胡塞尔而言,意向性是一切意识的本己特性,任何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实际上,“取消世界”的可能性相应地只意味着持续行进的经验过程的不一致性的可能性。一个世界的存在只是一些经验联结体的相关项,而这种联结体形式不可能在单个的、孤立的经验直观中获得,只能在经验的一致性的连续综合中形成。如果经验中充斥着自身不可调和的冲突,那么一致性地维持物的设定这一要求就无法得到满足,世界的存在也就无从谈起①经验过程的不一致性并不排除意识行为的意向性:“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可能的是,某种程度上大致的统一构成物得到了构造,这就是物直观的单纯类似物的瞬时的直观支点,因为它们完全不能构成常存的‘实在’和持续统一体,这些实在或统一体‘自在存在,不论它们是否被人感知’。”(Hua III/1,103—104)。不过即便是这种根据意识经验的特定的可能形态设想的世界不存在的可能性,也将被现时在思的自我的现实经验事实地排除。
二、现时意识与物的实存
胡塞尔对纯粹意识的执着很快发生了变化。根据贝尔奈特的研究,相较于1913年出版的《观念I》,在同年所作的“第六研究”修改计划中,“胡塞尔的兴趣发生了转移”,而且正是这种兴趣的转移使在改版的“第六研究”中的一种“关于现象学观念论之意义的新的沉思”②Rudolf Bernet,Conscience et existence,Perspectives phénoménologiques,Paris:PUF,2004,p. 147.得以可能。这里指涉的就是从纯粹意识到现时(aktuell)在思的意识的兴趣转移,以及使对观念论的思考着眼于我思的事实必然性。其实这种新的沉思早在先于这份修改计划的《观念I》中就已初露端倪了,在对意识做出本质规定时,胡塞尔如此解释事物对意识的依赖性:“超越之‘物’(res)的世界是完全依存于意识的,即并非依存于什么在逻辑上可设想的意识,而是依存于现时的意识的。”(Hua III/1,104)③“现时性”(Aktualität)概念在哲学传统中常与“潜能性”(Potentialität)相对,意近现实性(Wirklichkeit)。胡塞尔继承了这一用法,通常在意向分析中以此概念标识意识的一种特殊的对象把握方式。现时意识指的是当下原本把握对象的课题性意识,与未关注地朝向其对象的背景意识相对。然而很明显,这段引文中的“现时意识”之“现时”虽表面上仍是与某种“潜能”(“可设想的”)相对,但与通常用法截然不同,它在此不再指涉意识把握对象的方式,而是直接关乎意识本身的存在方式。这里的“现时意识”指的是现时在思的意识,即现实发生着的意识行为,与之相对的不再是背景意识,而是“逻辑上可设想的意识”。下文亦皆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现时意识”一词。我们知道,按其本质来理解的意识就是纯粹意识,其观念普遍性特征决定了它就是所谓逻辑上可设想的意识,那么为什么作为现象学剩余的纯粹意识无法承担超越之物的存在,反而要诉诸现时在思的事实意识呢?因为着眼于意向性意识的构造本质得到考虑的纯粹意识,承担的超越之物只是作为意义统一体的对象本质,而非具体的实在性。
胡塞尔在《观念I》中表现出的向事实意识的兴趣转移,在其同时期的其他若干文本中得到了决定性的确证。这些文本与其他一些相关文献被合并作为《胡塞尔全集》第36 卷(Hua XXXVI)④以下本书引文只在正文中附注页码。出版,这一卷作品正如其名“超越论的观念论”所示,乃致力于对超越论的观念论的“证明”(Beweis)。这一证明不再把超越论的观念论局限于超越之物对于内在之物在本质结构上的依赖关系,即不再局限于把超越之物的存在按其本质理解为通过意向性意识的赋义而来的意义统一性,相反地是从事物本身在现象学还原中被悬搁的实在性入手,探讨实在的实存与现时在思的意识之间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不是可能对象与相应意识方式的普遍相关性,而就是实在的实存对于现时在思的事实意识的具体依赖性。
《超越论的观念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现实世界’不是意识中的所思,若它应能合法地作为现实世界而对意识有效,那它如何在所思中——因而在法庭(Forum)上,它必须在这一法庭上证实(ausweisen)自身——证实自身的存在?”(S.7—8)通过对我们前科学的经验的反思,胡塞尔发现,超越的实在存在的意义的构造条件在于,超越之物必须能够通过经验证实自身。这里的证实始终与直观相关,而直观正如其在哲学传统中一贯的意义,乃指认识与事物之间最直接的关涉,一种原初的被给予性。“凡是者,必被带入被给予性;每一个在最宽泛意义上理解的可能对象,都有一个可能的直观作为其相关项,它在其中能如其所是地被直观,因此这个直观原则上是一个原初给予着的直观,对象在其中能亲身(leibhaft)被把握。”(S.73)这一原则对胡塞尔而言乃不易之理,毕竟它在《观念I》中就已被树立为现象学的“一切原则之原则”。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关于直观,在此得到强调的不是意识的意向与充实的本质结构所保证的认识的有效性,而是实在之物的当下亲身被给予性,它必然与一个现时在思的事实意识相关。现时的经验或者说现时经验着的意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经验形式(感知或交流)使实存之物成为可经验之物,因而实存之物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其对现时意识的关涉。
就与现时意识的关涉而言,最宽泛意义上的可能对象中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区分”(S. 73),正是这一区分描画了超越论的观念论所具有的迥异于《观念I》中的超越论现象学的新形态。那就是观念对象与个体对象的区分,这个区分决定了可证实性原则,即着眼于事实意识的直观原则在两类对象上的不同表现形式。“一个个体对象不能实存,除非一个自我,即一个‘已关涉’它的现时意识实存。然而一个观念对象仅仅要求一个能关涉它的意识的可能实存。”(S. 73—74)像数、种类、范畴这些观念对象的实存并非在时空中的实在存在,而是以观念的方式存在,它们可以通过本质直观向任何一个可能的意识给予自身。这种证实的观念可能性意味着向偶然性开放的本质必然性,它们本身并不依赖于其偶然的现实化,因而不依赖于向某个具体的、偶然的现时意识的证实。
这种证实的观念可能性也适用于想像对象,对此胡塞尔举了半人马与美人鱼作比。想像对象显然与数、种类等观念对象有本质区别,它们不具有观念上的普遍性,而是个体对象。正如空间性的物理之物一样,想像对象也以自身映射的方式显现。譬如我在自由的想像中通过一些虚拟的直观一致性地表象一匹半人马,在这个想像中,我走近它,从各个角度打量它所有的面,以各种方式去确认它的存在。在这一整个过程中,这个对象保持着它一致的统一性,而且是通过那种虚拟直观的序列向实行这些虚拟直观的虚拟自我显现其统一性。“我自己的实存在这里也不重要了;半人马的可能性并不要求我的实存。”(S. 75)那个虚拟自我并不能等同于现实的自我,因为虽然那些想像直观是现实自我虚拟的,但是在想像世界中实行这些直观的并非现实地虚拟这些直观的自我,而是那个走近半人马,从各个角度打量它的想像的自我。“只要是一个单纯虚拟的事物,即纯粹的观念可能性,那么与之相关的意识和意识—自我也相应地仅是虚拟的,是单纯的观念可能性。”(S. 76)胡塞尔也预料到了这种质疑:“然而或许有人会说:‘我在那里是以这种方式存在,即我把自己想象到想像空间中,到想像的美人鱼出现于其中的想像景观中去’?这大概可以。然而如此我便放弃了我现时的实存而不再是现实的自我。”(S. 113)想像的图像不是进行着想像的现实自我的对象,因为在想像中对对象所做的一系列直观都不是自我现实地实行的。现实自我只是打开了一个想象空间,然后把现实的经验关系以一种虚拟化的方式“投射”进去,于是就产生了虚拟对象与对之进行虚拟直观的虚拟自我。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的区分要回溯到现实对象与虚拟对象的区分,而后者又必须回溯到证实的实在可能性与观念可能性的区分。“像半人马这种事物的单纯观念可能性,并不排除无限多的别的在实存中互不相容的观念可能性”。每一种观念上可能的存在都有一个一致性感知的系统,这些相互一致的感知共同构成了一个可能对象的显现。所谓不相容性是指,当一个可能对象被设定为存在者时,在这个存在中其他可能性就被排除了。然而想像不受这种条件的限制,同一匹半人马我既可以想象为金发独眼,也可以想像为黑发双眼,虽然这两种情形明显不能相容。在实在可能性领域中不能相容的这两种情形,作为观念可能性却是“同样可能的”(S. 75)。
实在可能性的情况则截然相反。任何一种实在可能性都是一种观念可能性的实在化,不过这种实在化在把相应的观念可能性从其他诸可能性中突显出来的同时,也排除了与这种观念可能性“同时可能”却不相容的其他可能性。某物能够实存的原则可能性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决定了某物根据其存在能够证实自身?“现在一个物的存在就包括了,它可以被外在地经验。先天可知的是,一个这种类型的存在必须显现,即必须能在各个角度的显现中被给予,而且这类现象的本质还包含着另外的确乎无限的感知关联,在这些关联中超越之物一再根据新的显现展示自身并进一步规定自身。”(S. 74)然而上文讨论的想像对象同样能够自身映射,即在角度中显现为外在对象,它又何以区别于实在之物呢?当我们把单纯可能的感知自我替换为现时在思的现实自我时,后者对原本只是可能的事物具有了某种特定的现实经验与现实判断,其他无数平行的可能性由于与这种现实经验的矛盾而不再能够被设定于存在之中。现实经验与判断的课题“在处于现时经验的持续进程中的现实自我—意识中保持着一致,所以它不再仅仅是现实自我—意识中一个接一个的过程:相反,这个事物实存着因而是现实的”(S. 74)。对一个实在之物从各个角度所实现的经验共同构成了一个一致性系统,在此系统中,每进一步的经验都必须与当下实现的现实经验保持一致。与这个无限延展的一致性系统相应地,实在之物的各个方面也是前后一致地完全确定的。
既然实在之物自身映射,即在每一个当下只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显示它的一个面,那么相应地,每一个当下在思的自我也只能使这一个面得到证实,换言之,实在之物的完全证实所包含的经验的无限性不可能在一个现实的意识中现实地实现自身。那么实在之物的全方位的确定性又从何来呢?正是源于当下现实的经验所属的一致性系统。对于实在之物的实存而言,首先有一个现实地经验着的意识在当下对此物有一个经验,而且“在此现实意识中,实在的动机引发的可能性为可能的进一步证实而被预先描画出来。从现时的、锚定于现实被给予性的可能性中涌现的经验可能性就不再是纯粹观念的和完全任意的,而是被存在命题绑定的可能性”(S. 77)。现时经验着的自我对事物的当下经验就像一个锚点,这个经验所属的那个无限的一致性系统就像一条缆绳,而实在之物的实存就如天边的那艘船,无论缆绳有多长,只要锚定在一个固定点,这艘船就被限制了,被确定了。实在之物只要被当下现实的意识所经验,就能通过一个经验的一致性系统得到确定,因为根据这种一致性,每个当下被经验者总是预先刻画了进一步经验的特定风格,而只有在诸经验的这种环环相扣的一致性中一个现实统一体才得以构成。虽然这个确定的一致性系统无限延伸因而不可能被当下实在化,但是现实意识中朝向进一步经验的动机引发的可能性已经被预先规定了。所以胡塞尔说道:“事物的实存对现时意识而言始终是一个理念(Idee),但不是像数、种类这样的纯粹观念存在意义上的理念,而是康德意义上的(多维的)理念。”(S.77)事物实存的理念不能通过本质直观直接被给予,而是一个对现实的经验过程起着调控作用的极限概念。在实在感知中,从一个现时被经验者出发的实在的动机引发,其步伐被以调节的方式引导到那个要处理的事物上。
作为康德意义上的理念的物之实存并非单纯观念的可能性的一致性系统,而是某种实在的经验与其预先刻画的进一步经验共同组成的一个各方面都已被确定的系统。这个区分的关键就在于作为锚点的那个当下的现实经验,正如胡塞尔在一份手稿中所言:“一个实在之物或者说在既定的实际自然的背景下的实在之物,是在与这一实际自然的连结中得到特殊的可能性的。在前一情况中,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变量、诸可能性的无限性,但现在自然是固定的。这一固定是通过现时经验才得以实现的,现时经验有其开放的、或多或少未定的视域及相应的‘诸可能性’,这不是指任意的可能性,而是锚定于经验中、包含经验主题的可能性。”(Hua LXIII,88—89)任何实在的经验都是现时经验着的意识的经验,所以“一物之现实存在,及一个实在世界的现实存在……要求一个内容被突显的现时自我,一个现实存在的意识连同现实的经验和经验命题”(S. 78)。只有在这个现实意识所实际执行的现实经验中,实在的动机引发的可能性才被预先刻画,而只有通过动机引发的可能性,一个无限的一致性系统才得以被明确地规定,由此一个各方面都被确定的事物才最终构成自身,即获得现实的存在。
三、先于实在与观念的原事实
综上所述,胡塞尔超越论的观念论的核心意涵就在于物之实存对于一个现时在思的事实意识的依赖性。这种依赖关系显然是单向的,“实在世界的存在对意识的存在而言是偶然的。即便没有一个超越的实在性存在,作为可能的内在存在领域的意识也能实存,而超越之物的存在则完全依赖于意识的存在”(S. 78)。或许有人会质疑,这不就是在《观念I》中确立的纯粹意识与超越存在之间的本质性的构造关系吗?更准确地说,实在之物对现时意识的实际依赖关系不就是超越存在对纯粹意识的本质依赖关系的一个个例吗?一个个例性的事实只是本质必然性的一种偶然的现实化,并不能排除其他的观念可能性,因此“取消世界”的可能性不是依然得到了保留吗?如果单纯从本质现象学来看,本质可能性确实无待于其任何现实化的存在与否,换言之,个别的事实可以别样地存在甚至不存在,这都不影响作为其理性根据的本质自身的有效性。然而胡塞尔指出,超越论自我的事实与本质的关系是一种特殊情况:“若无事实的超越论自我,超越论自我的本质就是不可思议的。”(Hua XV,385)与一般的经验事实不同,超越论自我是绝对自身被给予的,我的现实存在是“一个绝对的、不可撤销的事实”(Hua XIV,155)。超越论自我的一切本质可能性都与我的现实性此在地相关,都只是后者的可能变式。这些变式若与我的现实存在相互矛盾,它们作为实在可能性就被排除了,沦为纯粹理论上的观念可能性。既然物及实在世界通过我的现时意识的现实经验实现自身,即如其被经验那般地存在,那么它也就最终实际地排除了“取消世界”的可能性。
关键的问题是,超越论自我的事实具有怎样的存在学性质?如果把它仅仅理解为日常经验意义上的个体化的世间存在者,而如上述,现实世界的实在性又取决于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有把超越论现象学歪曲为施蒂纳式的绝对唯我论的风险。更一般地说,把世界整体建基于它的一部分之上,这无异于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如果我们顺着胡塞尔赋予的“绝对事实”这个标签的指引,把超越论自我理解为黑格尔式的作为精神实体的绝对主体,那么胡塞尔的超越论观念论就只不过是德国古典绝对观念论的一个心理学化版本①因此,被扎哈维当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只是在超越本质可能性的意义上共享“形而上学”之名的课题来处理的问题,即实在对心灵的依赖性与超越论生活的事实性(Dan Zahavi,Husserl’s Legacy. Phenomenology,Metaphysics and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p. 203),在胡塞尔本人那里其实最终是同一个问题。。
很奇特的是,与大多数胡塞尔批评者坚持第二种解释不同,大多数胡塞尔辩护者倾向于采纳第一种解释。这番理论景象显然是20 世纪以来自然主义主导欧美(尤其英语)学术界的产物。当然为了规避上述明显的唯我论陷阱,研究者通常选择弱化实在世界对超越论自我之依赖性的形而上学意义,声称这种依赖性不是一种存在学上的还原关系,而只是在现象学态度下的构造关系。对于超越论构造与实在世界的关系问题,研究者们的理解也各有不同。有的认为悬搁排除了世界的存在问题,超越论主体构造的是世界的意义②David Carr,The Paradox of Subjectivity:The Self in the Transzendental Tra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 74,p. 108.,现象学首先是一种意义哲学③Steven Crowell,Husserl,Heidegger and the Space of Meaning,Evanston,Il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1,p. 5.,当然完全可与实在论立场相容;有的则主张超越论还原使自然态度下构造的客观性作为现象显现出来,加深了我们对自然生活的理解,因此现象学不仅不反对,而且“保护”④蔡文菁:《在先验观念论与常识实在论之间——胡塞尔与麦克道尔》,《哲学研究》2016年第11期。乃至“辩护”⑤赵猛:《胡塞尔的唯心论与实在论》,《哲学动态》2018年第11期。了日常经验的实在论。按照这类观点,既然胡塞尔所谓超越论自我对世界的构造只是对自然生活的意义结构的解释,也就不仅没有否弃,反而保留了自然态度,那么现象学就必然接受自然态度下的一个基本事实:超越论自我首先是在世界之内现实存在的,而且自我的这种实在存在是它从事一切活动包括现象学还原的前提。
首先,超越论现象学不关涉存在问题因而形而上学中立的说法显然不成立。胡塞尔公开宣称:“如果对存在的最终认识真的可以称为形而上学的,那么单子论的结果就是形而上学的。”(Hua I,166)单子论的形而上学结果,就是客观世界被把握为由我的唯一的、确然事实的自我所规定的唯一的单子共同体拥有的唯一的世界,这正是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已然隐含的结论。
超越论现象学“辩护”实在论的论调,则因为涉及现象学态度与自然态度的关系,更为复杂。这种观点的核心理由是:超越论还原虽然悬搁了自然态度对世界存在的设定,但是并未彻底取消实行着这一设定的自然生活,反而以之作为反思的课题,使存在设定活动本身作为现象被给予,即获得最终的有效性。这种解释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存在设定作为一种意识活动的存在有效性与存在设定作为一种存在学观点的哲学正当性。虽然通过把经验世界的实在性还原为超越论自我对其所构造之客体的存在设定,现象学确实揭示了自然态度的事实性,但是这并不代表现象学接受自然态度蕴含的实在论的存在学立场,“相反,我们使所有这些论点都‘失灵’了,我们不介入它们”(Hua III/1,106),“我们不生活在它们中,不实行它们,而是实行朝向它们的反思活动,而且我们把它们本身把握为如其所是的绝对存在”(Hua III/1,107)。现象学反思者不实行设定活动,还如何朝向它们呢?换言之,如果设定活动实际发生了(因而总以某种方式被我实行了),那么我还如何使之失效呢?这就要厘清超越论反思中的一个内在区分:实行着超越论反思的自我,即做着现象学的自我(phänomenologisierendes Ich),把目光朝向实行着存在设定的超越论自我及其纯粹意识。然而我不可能同时实行两个关注性的意识行为,所以反思只可能是一种回顾式的后思(Nach-Denken)(Hua VIII,89)。这就意味着,当下实行着现象学反思的自我,朝向的是过去实行存在设定的超越论自我。正是由于这段间隔,所以虽然被反思的自我实行存在设定因而生活于自然态度中,但是实行着反思的自我仍然可以拒绝存在设定的效力,使设定活动仅仅作为纯粹的现象显现。据此,我们可以大胆断言:进行着超越论反思的现象学自我不实行存在设定,不生活于自然态度中,因而也不再是在世界之内自在存在的实在个体。如果说这听起来很荒谬,那大概是因为我们总已习惯于自然生活,总会不自觉地预设自在的实在客体性,而把现象学限制为一种对预先有效的客体世界“无害”的意义解释。然而超越论现象学的课题“不是认识的主体性如何在理论上继续规定它在经验和经验信念中事先拥有的客体性,而是它如何在自身中已经达到这种拥有”(Hua VII,67)。超越论的研究“原则上不可以使客体的已被预先给予、客体的绝然在此有效”(Hua VII,68)。当然,人们还可以尝试借助现象学对自然生活的反思本身辩护自然态度的实在论。既然现象学反思揭示了我们在自然生活中何以总是实行存在设定,这就从哲学上说明了自然态度的合理性,辩护了其对于意识主体的事实性①Lilian Alweiss,“Beyond 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21,2013,pp.448-469.。做着现象学的自我也是一个实行着意识行为的人的自我,必然也总已生活于自然态度中,处于实在世界之内。然而这种把现象学的实事建基于人的某种类本质的做法,早已被胡塞尔指斥为人类学立场,后者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广义的实在论(如舍勒)。或许还有人会质疑道:胡塞尔本人坚持自然态度与现象学态度之间的平行论,我们可以在二者之间自由地切换,而无损于我们的自我及其世界的事实性(Hua I,159),因此这两种态度似乎具有平等的、至少相互独立的效力。然而平行并非平等,它不过意味着这两种态度下的课题并非——像传统哲学中的物质与精神那样——包含不同的实在内容,而只是经受着一种“目光的转向”。实际上,正是这种目光转向决定了自然态度与现象学态度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存在学差异:现象学态度把自然态度下的实在存在者还原为现象,即如其所是地自身被给予的绝对存在。可以说,现象学态度因为关涉的不是实在,而是实在的存在,所以相较自然态度具有存在学上的优先性,代表着超越论现象学的形而上学立场②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扎哈维坚定地宣称超越论现象学的形而上学立场是反实在论(Dan Zahavi,Husserl’s Legacy. Phenomenology,Metaphysics and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p. 208)。。
既然超越论自我不是生活于世界之内的实在个体,又被胡塞尔标识为“绝对”,那它似乎只能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实体了。然而胡塞尔本人一再宣称,超越论现象学与包括德国观念论在内一切传统观念论立场都完全不同。首先,就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而言,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自在且自为的无限实体,在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创造一切有限的实在事物,并包含于自身之中,此意义上的实在是概念化的;相反,胡塞尔的超越论主体对世界的构造(Konstitution)不是一种创造(Kreation),而是对象在纯粹意识中的自身构造,即对象朝向超越论主体的自身被给予性③Robert Sokolowski,The Formation of Husserl’s Concept of Constitution,Martinus Nijhoff,1970,pp.196-197.。究其根本,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仍然建基于笛卡尔所奠定的心物二元论之上,只不过是使形而上学思辨完全立足于精神一方,把一切物质存在都消解于精神之中——作为精神实体的样式,于是精神就成为自在自为、至大无外的整体,成为“绝对”。然而,精神首先还是抽去物质实体后的剩余物,并对称性地获得了同样的“实体”标签,于是精神就是从物质一方反向地得到存在学规定(Hua VI,81—84)。因此,在胡塞尔看来,自笛卡尔以来的一切形而上学——无论实在论还是观念论——都与笛卡尔本人的哲学一样预先受到客体主义的支配①从学界至今都还在实在论—观念论的二元框架中争论胡塞尔的形而上学立场这一理论状况,我们正见证着客体主义对人类思想根深蒂固的支配。。通过现象学还原,精神及其生活的各种形态,与自然一样都被揭示为在意识中自身构造的现象(Hua VII,408)。或许有人会质疑:把一切实在都还原为意识之内的现象,这不仍然是一种主观观念论吗?这种质疑跟传统哲学一样犯了心理主义的错误。通过现象学还原,“意识在此不再是人的意识,尤其不再是一种经验意识”,“意识”一词“失去了一切心理学意义,人们最终被引回到一种绝对,它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是既非物理也非心理的存在。然而此一绝对在全部现象学考察中就是被给予性场域”(Hua XXIV,242)。通过悬搁加诸自身的实在性设定,意识不再是人的经验意识,不再是心理体验,而是一切心理的和物理的实在的自身被给予性,即实在的存在本身,胡塞尔称之为“纯粹意识”。作为纯粹意识的实行主体,超越论自我当然也不再是作为自然之对立面而预先受到自然的存在学规定的心灵或精神。那么,一个既非自然又非精神的自我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它是一个何种意义上的“绝对”?
精神作为与自然相对的实在,首先就不可能是绝对,而且精神对预先规定自身的自然的消解还造成了悖谬。相反,纯粹意识作为包括自然和精神的一切世间之物的构造基础,才是真正的“绝对存在”。问题是,超越论反思作为一种本质直观,所把握的纯粹意识只是一种本质关联体,后者本身无法排除取消世界的可能性。那么排除了上述的自然和精神之后,超越论自我之事实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事实?这一问题当然不能仰赖形而上学的设定,还是要诉诸现象学的明见性。“在反思时,我发现‘我在经验着这个那个’,而且当我完全描述性地理解‘我在’这一表达时,我是绝对的。”(Hua XXXV,69—70)此所谓“绝对”首先指涉超越论自我的被给予方式:做着现象学的自我通过自身时间化活动把同属一个体验流的被反思自我认作自身,这种自我同一化的前提在于,被反思的自我及其意识生活在其实行的当下就已经被意识到了,所以超越论自我的绝对就是自身意识或自身显示②Dan Zahavi,Husserl’s Legacy. Phenomenology,Metaphysics and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p. 106.。“绝对”更重要的含义是超越论自我之事实的原初性。作为超越论生活的实行者,超越论自我不仅不是作为本质之偶然现实化的经验事实,反而还承担着并因而先行于一切本质可能性,毕竟任何明见性最终都必须直观地得到实行。于是胡塞尔后来改写了《观念I》中著名的“一切原则之原则”:“相反,‘我在’这一原理才是真正的一切原则之原则。”(Hua VIII,42)胡塞尔在30年代把绝对自我的观念拓展为一种关于“原自我”的思想。原自我与触发它的原质素处于不可分割的相关性之中,这种原初的相关性结构被胡塞尔称为“原事实”(Urtatsache)(Hua XV,385)。原自我与原非我(原质素)的相关性因为原初不可分割,所以并非一种现成的对象性的关系,相反,一切主体性及其对象性,他们的世界和精神生活最终都在这一原事实中成其自身③交互主体性世界及其目的论历史在原事实中的自身构造问题,限于篇幅在此无法展开,笔者对此已做了一些初步探讨。参见谢利民:《从描述到建构——论胡塞尔形而上学的观念、动机和方法》,《哲学研究》2021年第4期。。我们不能再向原事实背后追问任何理性根据(Hua VII,188),因此这一非理性的超越论事实就是现象学所面向的最终实事——原现象。
——兼论现象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评介
——论胡塞尔对布伦塔诺时间观的继承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