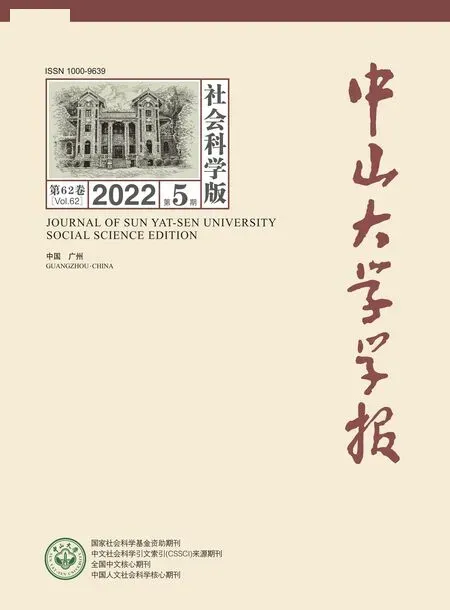人性与方法*
——胡塞尔论伦理生活
蔡文菁
“方法”是胡塞尔哲学中尤为重要的概念。一方面,在其著作与手稿中,胡塞尔曾不断论述、反思和修正对现象学方法的理解,这意味着对哲学探究进程本身、对自身作为哲学家的反思。另一方面,“方法”对胡塞尔而言不仅关涉哲学研究,而且有着远超越于此、更为根本的意义。在1922 年为日本期刊《改造》(Kaizo)所撰写的文稿中,胡塞尔曾将人类生活的本质结构标识为“泛方法主义”(Panmethodismus),也即把我们的伦理生活本身视作方法,将方法作为人性的构成要素①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ed. by T. Nenon,H. R. Sepp,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p.39.。如何理解方法与人性之间的本质关联?现象学的方法与作为方法的伦理生活之间又具有怎样的联系?
本文将从对现象学方法的考察切入上述核心问题。从古希腊语词源来看,“方法”一词意味着沿路而行。每一条路都有起点和终点,那么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来说,从哪里出发,又要往哪里去呢?就起点而言,它往往蕴含着对特定终点或模糊、或清晰的指向。因此,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看,那成为现象学探究之动机、被现象学思考所先行预设的,是对其目标的指向。本文试图表明,这一现象学从中产生又最终所指向的乃是我们的生活。而充分领会现象学方法的一种方式便在于澄清现象学与自然生活或生活世界之间的双向关联。现象学何以从自然生活中超脱而出?它又将把我们引回怎样的一种“别样”的生活?这两个问题提示出现象学探究在两个彼此紧密关联的方向上的工作,一方面它涉及现象学之动机引发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关乎现象学的实践或伦理面向,或对于实际生活可能的改造。
本文将首先探讨现象学从自然态度中引出自身的动机。现象学致力于成为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这是由于真正的哲学攸关一切科学理论奠基于其上的生活世界以及普遍人性,后者展现了现象学的深层动机。借助胡塞尔对伦理生活之本质结构及特征的思考,本文进而阐明伦理生活何以是方法,以及“方法”概念在胡塞尔哲学中的独特意义。这一考察也将充实我们对现象学动机的理解,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以及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反哺最终建立在人性向着最高价值奋进这一根本上可能的生活样式之中。
一、从自然态度出发
现象学最初展现为一门有关本质的描述心理学。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 卷(以下简称《观念I》)时期,胡塞尔对现象学方法论有了更自觉的检视,并逐渐转向了先验现象学:现象学不仅是对意识之本质的考察,更是对意识作为先验维度的揭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向并非仅仅为意识附加上某种功用,而是揭示了一个崭新的对象域。具体而言,先验意识不再只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并列的存在区域,现象学的工作也不只是对这一区域进行本质描述。在现象学的观照之下,意识是世界如此显现的可能性条件,意识内在地关联着世界。在胡塞尔看来,要把握意识的这一先验特性,就必须展开先验还原。
先验还原的第一步在于“悬搁”(Epoche)。胡塞尔虽然借用了这一古代怀疑论者的概念,但现象学悬搁的对象与意义却不同于皮浪学派。现象学家所要悬搁的不仅是对于具体事态的判断,更是自然态度下对存在的一般设定,或者说,对存在的牢固信念。自然而然地,我们相信面前的事物和他人的存在,相信不能亲见的事物的存在,甚而相信一个世界整体的存在,它广袤无垠,跨越古今。这样一种信念再“自然”不过:它根深蒂固又令人毫不察觉,作为一切个别信念或认知的背景而存在。如何能够悬搁这一态度或信念?在《观念I》这一向先验现象学转向的重要著作中,胡塞尔借助了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方法。在笛卡尔那里,怀疑的念头一起,有关世界中各类事物的信念便渐次产生了动摇。对笛卡尔而言,如果不凭借理性之光,怀疑的入侵便会时刻来袭,使我们无法心安理得接受世界。而在胡塞尔这里,怀疑的方法并不导向怀疑的消除,或者说,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不同,现象学并不试图凭借理性重铸有关世界的信念。现象学“悬搁”的真正含义在于使得自然态度下的信念失效。因为,当我们由此进入一种“非自然”的态度中,暂时不让这些信念发挥作用时,便能够回溯到信念本身及其产生的源头,也即先验意识那里。
事实上,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过渡到先验还原,这只是胡塞尔所思考的通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之一。当然,它无疑是贯穿胡塞尔思想始终的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以至于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胡塞尔写道,“笛卡尔的沉思是哲学反思(思义)的原型”①Edmund Husserl,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ed. by E. Ströker,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p. 3.。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②例如Sebastian Luft 在他的文章“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revisited:an attempt of a renewed account”(Anuario Filosófico,XXXVII/1,2004,pp. 65-104)中所指出的,胡塞尔并没有用生活世界的道路替代笛卡尔式的道路,而是展现了现象学的两种不同的旨趣和面向。本文则试图将这两条进路联系在一起,表明胡塞尔的哲学理想何以最终奠立在他对于普遍人性和伦理生活的理解上。,胡塞尔从未真正放弃笛卡尔式的进路,这意味着对胡塞尔而言,先验现象学是对笛卡尔哲学动机的彻底化,并且现象学还原可以在特定意义上被理解为笛卡尔沉思的某种变形。
胡塞尔在最后一本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以及先验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也谈及另外两条通往先验还原的道路,即心理学的道路和生活世界的道路。在胡塞尔看来,除了对笛卡尔哲学进行彻底化,也可以从现象学心理学以及对生活世界的考察中逐步转向先验还原。对胡塞尔而言,这三条道路乃至更多的进路殊途同归,或更确切地说,无论是笛卡尔式的对最确定无疑的知识的理性辩护,还是心理学对人类心灵领域的追问,或者理解生活世界的本体论企图,都最终会走向在胡塞尔心中作为第一哲学以及哲学终极形态的先验现象学。
不管从哪一条道路出发,先验维度的显现总是与自然态度的转变联系在一起。这一态度不仅包括我们对事物的日常态度,也包括进行科学探究的理论态度。而自然态度之所以成为出发点,恰是由于先验维度不在其外而在其中,它总是静默地发挥着作用从而实现着自然态度本身。换言之,为了能够识得“庐山真面目”,观察者必须从中走出来,以便获得一个外在视角,悬搁便是确保这一视角的手段。在《危机》中,胡塞尔曾用“平面生活”和“深层生活”来分别形容自然态度与先验态度下的状态①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d.by W. Biemel,1976,Den Haag:Martinus Nijhoff,p. 121. 中译本参考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在胡塞尔看来,平面上任何一处都不可能使我们获得关于这一生活运转方式的全貌,除非能够跳离它,在“高处”或“深处”检视它。正如胡塞尔自己后来反思的,这一譬喻远比《观念I》中“排除世界以获得剩余物”的说法来得准确②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1923/4). Zweiter Teil:Theorie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1959),ed.by R. Boehm,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p. 432.。先验现象学所寻求的并非去除掉世界后所剩余的意识领域——这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某种误解,也并不只是剥除了偶然性的本质之物,而是整全者,或存在者之整体。凭借现象学还原,我们从对局部对象域的聚焦中解放出来,从向来置身于其中的背景视域即世界中跳脱出来,从而看到事物何以并不只是它自身而必然关联于一个构造着它的意识生命,以及进一步地,这一构造着的主体何以在一开始就处在一个预先被给予的、与他人共在的生活世界之中。在这里,存在者整体既不是自然态度下素朴的实在论者们所见的实存物的全体,也不是与世界切割开的主体意识领域,而是先验主体—世界这一关联整体。
因此,胡塞尔现象学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在于,世界之所以如此这般,并非因为它将其自在的形貌原封不动地加于我们的头脑之中,而是意识成就的结果。这一成就并不必然是意识主体主动的赋义,也绝不仅仅是认知层面上的成就,而是关乎我们身体性的存在、在历史与传统中习性的被动养成、与他人的共在等等。胡塞尔现象学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影响着后来无数思想家,恰是因为他为这一“成就”所赋予的丰富内涵。当我们用“意向性”一词来统括这一成就时,必须谨记这一概念事实上包含了不同层级和样式——感性与知性的生命有多丰富,意向性就有多丰富。
我们会在这里遭遇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某种奇特之处,虽然把对自然态度的悬搁作为还原的第一步,但这第一步却并不容易迈出。悬搁作为开端似乎隐含了某种循环:一旦悬搁了自然态度下的存在信念,实际上就已经在进行还原了。或者说,先验维度的呈现并不跟随着悬搁而来,而是已经蕴含在了悬搁之中,悬搁本身就是揭示,悬搁甚至预设了揭示:如果想要把某样东西放到括号中,我们难道不必须先看到它吗?
本文虽然探讨了还原的步骤,但是却并没有完全回答还原之动机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初始的现象学家,一个总是已经在自然态度中生活着的思想者,是什么促使我们离开这一生活进行悬搁和还原呢?或者说,自然态度本身有怎样的“不足”或“匮乏”使得我们要去超越它?胡塞尔在追求一种别样的生活吗?现象学最终将把人类引向哪里?
二、现象学的深层动机
从胡塞尔对笛卡尔的肯定中,可以找到现象学的部分动机:一种有关哲学的理想。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一开始,胡塞尔就表明了笛卡尔的沉思对今天的哲学生活仍具有意义。在胡塞尔的解读中,笛卡尔的目标在于为哲学确立一种全新形态:哲学必须成为一门建立在绝对基础之上的科学。胡塞尔将他所处的时代类比于笛卡尔的时代,并指出这一时代的哲学亟需革新,一如笛卡尔推动了当时的哲学革命那般。胡塞尔写道:“我们所有的并非同一的、充满活力的哲学,而是无限生成着、但却彼此毫无关联的哲学文献;并非相对立的理论之间真诚严肃的辩论——它们虽然处在论争中但却传达着内在的联系、其在基本信念上的共通性以及对一门真正哲学的不可动摇的信仰——而是流于表面的援引和批评,而非真诚的共—思与为彼此而思。”①Edmund Husserl,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p. 7.在胡塞尔看来,一门得到彻底的奠基、具有客观有效性的哲学既是“个人的事务”,又必须在哲学共同体中完成。一方面,哲学之为个人的事务,乃是在于每一位严肃真诚的哲学家都必须如笛卡尔那般自始至终凭借个人明见的体验获得知识。通达真理的方式与真理是什么彼此关联且同等重要。哲学家的使命便在于以哲学的方法确保真理在明见的体验中向人们显现自身。另一方面,虽然哲学对于每一位哲学家而言首先是一条独行的道路,但它并非哲学家的一己之见。哲学的真理若要超越个别哲学家的视野而获得普遍性和客观有效性,就必须能够在共同体中经受批判。如同普遍本质在一系列相异又相近的个别对象中显现为共同的形式,哲学的真理同样在个别哲学家的理论中呈现为普遍的思想。若将这两方面统括起来,那么,在胡塞尔看来,唯有在哲学家个体负责、自主的态度下获得的洞见才能够在共同体中变得有价值,从而最终揭示普遍真理。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胡塞尔持有的这一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理想仅仅来自一种理论的兴趣吗?为什么要进行哲学思考,为什么要让哲学成为一门彻底的、获得最终奠基的学问?哲学何为的问题进而把我们引向胡塞尔现象学更深层的动机,即对于某种理想生活的追求。正是对这一层动机的思考令人意识到,现象学还原的目标并不只在于理论地揭示自然态度下生活世界得以构建起来的结构形式和可能性条件,同时也在于推动一种可能的实践层面的改变。或者说,这一对先验维度的理论性揭示,指向了伦理和文化生活的更新。
除了不满同时代的哲学处境,胡塞尔也在《危机》中表达了对整个日常以及科学世界的担忧。或者更确切地说,日常生活与科学的危机也同时是哲学的危机。这一危机在于,自然生活、科学与哲学不再紧密相联为一个整体。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时代,哲学为诸多分支科学提供基础并与科学一道塑造人们的生活形态,哲学回应着一切科学和生活的意义追问,那么胡塞尔在彼时的时代精神中所看到的是一种整体的瓦解和割裂。生活、科学与哲学成了彼此关联甚微的领域。一方面,以自然科学为主导的现代科学失去了与其意义来源——即生活世界——的联系,近代实证科学的发展一再将自然数学化和理念化,以至于“这件‘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理念的衣服”,“使得我们把指示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有,而这种方法本来是为了在无限进步的过程中用科学的预言来改进原先在生活世界实际被经验到和可被经验到的领域中唯一可能的粗略的预言的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②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p. 51,11.。由此,“自然”失去了其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意义,而成了“自然主义”的。另一方面,哲学也丧失了作为普遍科学的奠基性意义。在胡塞尔看来,对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对理性信仰的崩溃”,而“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此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③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p. 51,11.。我们将更清楚地看到,哲学与人性的关联何以为这一系列信仰提供支撑,哲学对真理的追寻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人性对自身的关切,是摆脱虚无主义时代的解药。
胡塞尔深信,哲学实践是回应和改变这一时代危机状况的恰当方式。然而,正如他在一战之后写给学生梅青格(Metzger)的信中所写的,作为哲学家的胡塞尔清晰地认识到,他的任务绝不是给出政治上的建议或产生政治影响,不是成为领导人民走向“有福生活”的领袖,而是做一名“科学的哲学家”,把文化更新或改革的可能性作为哲学论题来思考④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11-1921),ed. by T. Nenon,H.R. Sepp,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1987,p. XXXII. 中译本参考倪梁康译:《文章与讲演1911—192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正是这一向生活世界的回返,构成了现象学从自然态度中跳离的重要动机。
就此而言,对于自然态度,先验现象学态度既非彻底否定也非纯粹旁观。一方面,现象学家不可能抛弃此世,过某种“在别处”或彼岸的生活;另一方面,现象学家又绝不只是冷眼观看而不去推动某种改变。现象学的姿态毋宁类似柏拉图在《斐多》中所说的“对死亡的练习”。柏拉图深知任何人在生前都不可能让灵魂完全摆脱肉体,正如胡塞尔的现象学家不能跳脱自身的处境而成为一个彻底的“无兴趣的旁观者”——或者说,彻底的还原是不可能的。除了把哲学家对死亡的练习理解为死亡的未达,柏拉图也同时赋予其更重要、更积极的含义:练习死亡是一种生的姿态,是此世的哲学家与真理或超越维度相连的方式,是生命趋向自我克服的样式。在相似意义上,现象学家朝向彻底的悬搁与还原的态度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形态或“人格”,这一形态将她置于某种张力之中:作为“世界之子”,她总是被世界所吸引,被自然态度所牵绊;而与此同时,她又受到某种超出自身和世界的理念的召唤。胡塞尔因而总是称呼她为“初始的现象学家”,这暗示着现象学的未完成性与往复性:现象学家不仅在一种不完满性中出发,且她总是一再被拽回到起点,需要一再积攒勇气来克服自身。我们将看到,这样一种居间的状态作为人性之本质而表现为朝向理想奋斗的、自我超越的进阶道路,也即展现为通往理想终点的“方法”。
三、伦理生活
除了《危机》之外,胡塞尔曾在几处重要的文本中谈及现象学所致力于的“改造”以及它所朝向的人性理想,例如,1917年有关费希特的人性观念的三个讲座,以及1922—1924年间为《改造》所撰写的系列文章(以下简称《改造》文)。这几篇文稿一方面如同《危机》那般表明了现象学思考的实践旨向;另一方面也更清晰地展示了这一旨向最终所系的某种“人之为人”的理念。
胡塞尔把对于理想人性和生命样式的哲学思考作为哲学伦理学的最高任务,正如他在第三篇《改造》文中所指出的,纯粹伦理学是这样一门本质科学,它关涉“伦理生活在纯粹(先天)普遍性中的本质及其可能样式”。作为伦理学的对象,伦理生活“依据其本质是有意识地处在更新之理念之下、自愿地由这一理念所引导和构型的生活”①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20. 倪梁康在《胡塞尔的“改造文”与“改造伦理学”》(《世界哲学》2015 年第2 期)一文中指出,胡塞尔的改造文具有“规范伦理学”的色彩,而有别于现象学伦理学,后者是对于伦理或道德现象的本质结构的考察。按,笔者部分地赞同这一观点,即胡塞尔在改造文中的确展示出了有别于一般现象学分析的实践或伦理旨趣。不过,在笔者看来,胡塞尔在改造文中所进行的工作仍然隶属于现象学或纯粹伦理学,它的探究对象是狭义(或严格意义上)的伦理生活的样式,即以最高理想为目标、在理性的规范下的生活。胡塞尔在此试图展现一种隶属于人之本质的、可能的、且作为理想的生活形态。这样一门“纯粹的伦理学”并不直接探讨具体的经验规范,但却能够为规范伦理学奠基。;胡塞尔也在文中另一处补充道,“在普遍的以及最宽泛的意义上,我们把每一种与伦理目标理念之定言要求相符的自我规范的生活称作伦理的生活”②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39,42.。值得一提的是,胡塞尔在这一定义之下赋予了“伦理”以及伦理学以宽广的内涵,伦理统摄了一切理智与实践的行动,也即在所有领域中都能践行某种伦理的生活。此外,胡塞尔也把伦理的生活视为规范性的源泉,不同寻常地强调了伦理的奠基性:“唯有伦理的正当性才是最终的正当性。那被称作自在的价值或自在的善的事物,仅仅是因为满足了特定的根本性条件,它们要求把这一价值先天地视作伦理生活框架内价值考量的积极的价值要素,而非从一开始即排除它。”③这意味着对胡塞尔而言,只有在伦理生活之中,我们才能面向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例如真、假、善、恶,等等,它们并非仅针对某一个体,而是有着绝对价值和自在的特性,即“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如此。唯当个体践行伦理的生活时,某种在共同体中普遍的事物或价值才可能产生。哲学的真理在胡塞尔看来也是这般需要在个别哲学家的伦理生活中被赢得的。
很显然,并非一切类型的生活都在严格意义上是“伦理”的,或如胡塞尔有时所言,属于“真真正正的人”的①胡塞尔称,宽泛意义上的“伦理生活”也包含了一切严格意义上“非伦理的”生活或行动。但在《改造》文中,他用“伦理生活”来指涉一种作为高阶的、符合理性之绝对命令的生活样式。。出于热爱而选择的志业生活(Berufsleben)在胡塞尔看来只是一种前伦理的生活形态。当真正的艺术家或科学家(哲学家)受到他们所热爱之事的呼召,他们的生命便以投身于这一事业为原则。尽管这一生活形态也处在某种“普遍的自我规范”之中,胡塞尔却认为,它还并非伦理的生活。这是由于这一生活所遵循的原则来自一种或许非理性和盲目的热爱,而由此被赋予价值的事物也因而并不具有绝对性②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 28,30,30,268.。胡塞尔在此谈及了某种可能的“价值的失落”(Entwertung),即我们可能随后落入某种“尴尬的认识”中,发现“所追求的‘善’只是所谓的善;为之献身的工作是无用的,而对它的喜爱也是毫无意义的”③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 28,30,30,268.。一方面,价值的失落与意义的丧失是现代人随时可能面对的境地;另一方面,正如胡塞尔所相信的,人性对永恒价值的追寻使我们从价值失落中获得某种走向伦理生活的动机,后者试图拯救我们于虚无主义的泥沼。就此对胡塞尔而言,前伦理的生活形态内在地蕴含着对自身可能的批判,也因而向着伦理生活本身而敞开:“在此,有着这样一种在根本上可能的动机,它表现在一种普遍的朝向完满生活的奋斗中,即一种在其一切行动中都完全得到辩护并确保了纯粹、持久的满足的生活。”④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 28,30,30,268.
依据胡塞尔的表述,伦理生活的本质特点之一在于,它包含了至高的完满生活的理念。在《改造》文中,他一再指出,人之为人在于拥有理念(Idee)与理想(Ideal)。胡塞尔有关伦理生活与人性理想的理论深受康德与费希特的影响。早在1917 年有关“费希特的人类理想”的三次讲座中,他就曾慷慨致意偶像,把费希特所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视为哲学实践的典范。在讲座开篇,胡塞尔列举了近代以来思想史上的一长串人名,并指出在群星璀璨的时代,哲学思考曾为人们提供了共同的目标和理想。在他看来,“精确科学以及由之所规定的技术文化”造成了理想与信念的失落,使得理性所规范的哲学逐渐失去了引领时代精神的地位。胡塞尔这里的批评可与《危机》中的批判类比,他尤其提到了“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也即抽离掉了与日常生活之关联意义的方式。因而自然主义的倾向与虚无主义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后者迷失于一个失落了意义与价值的世界之中。尽管如此,胡塞尔在当时仍寄希望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困苦以及对胜利的渴求,期待“理念与理想重又在行进中,重新寻找到敞开的胸怀”,而“单面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失去它们的力量”⑤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 28,30,30,268.。这也同时意味着,哲学能够重新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方向与意义。
胡塞尔将“理念”与“理想”并举,暗示出这两个相近的词语所传达的不同侧面。“理念”或“观念”一词指向某种必然、普遍、绝对的事物。我们通常在认知层面上理解胡塞尔的先验观念论——只有在主体的意识生命中,感知和认识对象才显现为独立自在的超越事物。然而这一观念论也同样体现在伦理领域内,或者也可以说,胡塞尔持有一种“伦理观念论”:在伦理行动中,行动者必然会设定某种绝对价值或完满性⑥Yoshikawa 在他的文章中将胡塞尔的伦理思想表述为一种“伦理观念论”。参看Takashi Yoshikawa,“Husserl’s Idealism in the Kaizo Articles and Its Relation to Contemporary Moral Perfectionism”,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German Idealism and Phenomenology,2021,pp. 233-256。。与此相应,“理想”一词凸显出这一理念的规范性意义,它是规定着行动之方向、我们力求无限接近的至高目标。正如在认知领域内,有关自在事物的理念激发人们一再推进有关它的认识、在明见的体验中揭示其更多的侧面;在实践行动中,完满生活的理想也驱使着我们为之而奋进。作为理念的理想并非外在于个人,毋宁说,它先天地内在于主体自身,是主体必然设定和追求的最高价值,或如胡塞尔所言,是“绝对的极限,超越一切有限性的极,一切真正人性的奋斗所指向的,神的观念”①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 34. 胡塞尔有关“神的观念”的思想或许受到费希特的影响。在“费希特的人性理想”一文中,胡塞尔谈及在费希特哲学的特定阶段,伦理人与宗教人是完全重合的,也即神的观念即是最高道德秩序的观念,因而神显现在伦常生活的无限追求之中。。胡塞尔因此把人理解为这样一种有限的存在者,她在自身中携带着“无限性的印记”——无限是其自身构成性的本质要素,它为生命向上向前提供了动力与意义。
四、作为方法的生活
“拥有理想”的伦理生活因此具有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本质特征,它展现在“更新”(Erneuerung)这一观念下。正是这一特征构成了人类生活样式的别具一格之处,并使得胡塞尔将其理解为“方法”。
由“更新”的理念所引导的伦理生活可以通过胡塞尔对理想的双重意义的探讨得到界定。在第一重意义上,它所指的是绝对理想,即前述的极限概念,完满的目标与终点。这意味着伦理生活总是朝向终极理想的恒久追求与奋斗(Streben),它是一条不断进阶的道路,绝非坦途。有限的、奋斗着的主体知晓,他与这一终点的距离“总是无限遥远的”,他永远无法拥有绝对完满的生活②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 34,37,43,36,34.。第二重意义上的理想则是“相对的”,它关涉一个比起当下而言“更好的自我”,或更完满的生活。我们总是在对相对理想的追求中接近绝对理想。于是“更新”便指示出一种自身关联,它是着眼于当下自我的自身超越。胡塞尔因而写道,伦理的人“同时是奋斗的主体和客体,是无限生成着的作品,是他自己的杰作”③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 34,37,43,36,34.。
追随古希腊哲学家,胡塞尔将伦理的生活刻画为始终处于内在张力之中的过程:它“依据其本质是与下降的倾向之间的斗争”④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 34,37,43,36,34.。换言之,向人性至高理想奋进的道路不仅漫长,且阻力重重,这一阻力首先并非来自周遭环境或人,而是生自人性自身之中,胡塞尔有时也称其为我们之中的动物性的素朴状态或被动的驱力。如前所述,人们始终被自然世界所拽引,沉迷于世界乃是生活的某种基本的可能性。然而这一内在张力却同时表达为人性最突出的特点,即与自身的关联,胡塞尔在不同的地方将其进一步表述为自我反思(Selbstbesinnung)、自我观察(Selbstbetrachtung)、自我教育(Selbsterziehung)、自我规约(Selbstregelung)等。康德的伦理学在此对胡塞尔的思考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胡塞尔而言,上述自身关联或自我更新并不仅仅是任意的行动,而是在“定言命令”之下、出于意愿的行动,这一绝对命令可以表述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过一种你能够彻底明晰地为之辩护的人生,出于实践理性的人生。”⑤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 34,37,43,36,34.与康德一样,胡塞尔在此提供的是伦理生活的形式定义;就内容而言,每一个主体自然可以有其具体、特定的定言命令以及在其引导之下展开的独特人生。而相比康德理论所涉及的道德领域,胡塞尔所关切的伦理生活包括了更多,实践理性统摄了理论理性——即便是理论工作者,例如那些为真理而献身的科学家们,也在探索理论真理的实践理性的指引下践行着力图为自身彻底辩护的人生。
有趣的是,胡塞尔把这一处在自身关联之下的理性人与所谓的“天堂人”进行了对比。在他看来,后者虽然是无罪或无错的,但这全然是盲目与偶然的,也即是说,天堂人并不凭借自我意识以及自我超越而为其行为辩护,因而他们虽然呈现出某种美好的生活形态,却完全处在“无反思的天真素朴中”,他们“对于理性、对于批判性的明见以及辩护一无所知”⑥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 34,37,43,36,34.。从这一对比中,胡塞尔表明了实践理性之绝对命令下的生活的对立面,也即一种素朴无反思的、无法为自身辩护的生活。自然态度下的生活在特定意义下可与之相比拟。然而严格说来,处在自然态度下的人并不与天堂人相同,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会犯错,更因为作为理性人,他们始终具有跟从理性的绝对命令从而走出素朴性的可能。在这一意义上,现象学从自然态度中的离开是一次自我更新,是朝向为自身辩护的人生的道路,也是蕴含在自然态度中的根本上可能的生活样式。
就此而言,胡塞尔对伦理生活和人性的论述进一步充实了我们对于现象学动机的理解。此前所谈及的动机——无论是塑造一种科学的哲学形态还是通过哲学来回应时代的精神危机——由此成了内在动机。换言之,真正的哲学攸关时代与生活,这并不是为了从外部为我们的精神状况寻求良药;对于胡塞尔而言,素朴的生活本身就有着对自身的关切,对至高理想的向往,以及对理性的绝对命令的感应。一旦将自然态度与现象学态度视作自我超越的奋进道路上的两个阶段,那么,现象学的开端——处在自然态度的素朴性中的人们何以抽身离开——便不再是一个悖论。现象学的态度并不构成自然态度的对立面或与后者的决裂,反而可以被理解为力求走出素朴性、从而令自己置于批判之下的自然态度。我们需要现象学的态度和哲学来回应精神危机,这无非是因为它体现了人性的自我更新的力量。
胡塞尔把如此这般处在更新之理念下的伦理生活称为“作为方法的生活”(ein Leben der Methode):“真正的人的生活,在无尽的自我教育中的生活,即是‘作为方法的生活’,通往理想人性的方法。”①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 38.就其必然关联着起点与终点,“方法”展示了一种居间的、尚未抵达的状态。但正如胡塞尔所竭力表明的,这一居间性不仅是未完成,更是出于意愿地、自由地自我超越。方法是唯有理性的人才能展开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在现象学视角下,“方法”是目标对象的某种不可越过的本质性的展开过程或通达方式。胡塞尔将明见的体验视作通达世界的方法,是世界显现自身的样式;同样,作为方法的伦理生活则是无限完满与绝对价值展开与实现自身的样式。澄澈的真理、普遍的善、完满的人生、极致的满足等等,并非孤悬在某处的实在,也非个别主体纯粹主观的投射,而是只在伦理生活的践行中才得以如此这般显现。它们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观念,而是在每一次努力、每一个抉择中作为准则、命令规约着人们的行动。
我们由此可以在双重意义上理解“方法”。就方法指向终点并保持与后者的距离而言,方法的践行者总是有限的,他以无限为其标尺衡量自身。胡塞尔哲学的目的论面向便是以此展开的。现象学总是在途中,朝向一门彻底的、为自身奠基的科学。但“方法”在第二重意义上却是积极的,它是目标对象得以呈现自身的无可替代的独特方式。思考“方法”的问题即是思考对象就其本质而言如何显现自身,如何具有其别具一格的存在样式。对这一意义上的“方法”的把捉似乎构成了现象学传统的某种共识。我们可以在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萨特、列维纳斯等哲学家的思想中找到截然对立的主张、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域、所宣称的不同的现象学样式,但或许能够将他们统一起来的是对于“方法”无一例外的关注:这不仅在于对现象学工作进程的反思,一种为己辩护的努力,也在宽泛意义上在于对现象自身显现之方式的探究。
结 语
综上所述,现象学的动机首先在于建立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它基于确然的明见体验并能够为自身奠基。这一动机体现在从笛卡尔思想走向现象学的道路中。而胡塞尔的这一哲学理想又进一步基于哲学与生活的内在关联,真正的哲学能够为生活提供意义与方向,它虔敬地指向了永不失落的价值。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从生活世界走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既不是对笛卡尔式道路的舍弃,也非全然独立于后者;换言之,哲学向生活世界的返归以及哲学作为严格科学是同一工作的两个面向,它们进而奠基在人类别具一格的伦理生活之本质结构中,后者作为通往理想人性的方法或道路,昭示出终极的意义与价值,并且展现为在自我关怀中以此极限为锚的奋进的人生。在胡塞尔看来,这一伦理生活不仅必然是可能的,同时也是某种典范,它示例于真正的哲学家的生命中。现象学也由此展开了其作为伦理学的一面,它把伦理作为最源初的、根基性的领域,作为一切绝对价值——包括哲学和科学所尊崇的价值——显现的来源及场所,哲学在其中成就自身,并以显明与守护它为己任。
——论胡塞尔对布伦塔诺时间观的继承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