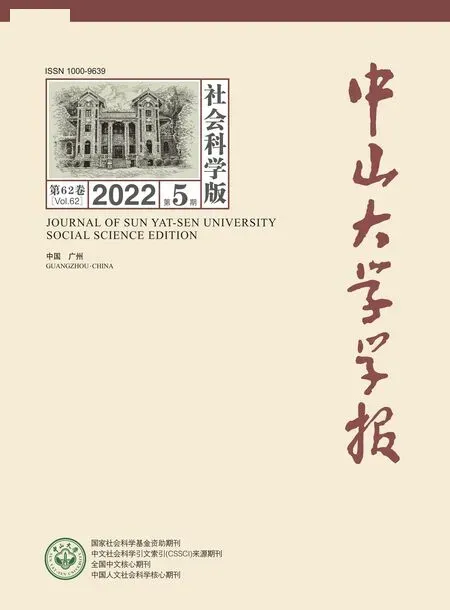和平与战争的张力*
——关于康德、尼采和老子的比较
杨玉昌
和平与战争不仅是人类历史上不断交替上演的戏剧,同时也是哲学家一直探索的主题。康德、尼采和老子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哲学史上具有代表性,它们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是学界讨论相关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康德和尼采都隶属于西方哲学传统,但他们一个用理性建构永久和平,另一个则从权力意志出发为战争辩护。这种对立表明他们与其说是解决了,不如说是深化了和平与战争的难题。事实上,由于立足点的根本差异,康德与尼采之间的张力很难化解,甚至难以沟通,处于东方哲学传统中的老子思想可以为此提供新视角。一方面,老子贵和、尚柔,反对战争,与康德的和平主张相似;另一方面,老子并没有康德那种通过不断理性启蒙达至永久和平的思想,而是认为万物都处于永久的循环运动之中,这与尼采的永恒轮回相接近。这使得老子有可能沟通乃至超越康德、尼采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反过来说,对康德和尼采之间张力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老子思想中的问题,发掘其现代意义。从总体上看,尽管康德和尼采分别主张和平与战争,但他们的主张都以肯定人的主体性即人对知识和欲望的追求为前提。相反,老子的和平思想是以反对人的主体性,主张“道法自然”,无知无欲为基础的。这样,康德、尼采与老子之间就构成了关于和平与战争的另一种张力:是通过肯定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永久和平或战争,还是通过消除人的主体性回归自然的和平状态?因此,对康德、尼采和老子关于和平与战争思想的比较,实际上是在东西方哲学之间展开对话,希望由此加深东西方的相互理解,更好地应对当下的战争危机,确保人类的和平与繁荣。
一、康德与尼采:和平还是战争
康德和尼采分别在其著作中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相反观点,前者肯定和平,后者肯定战争。对于康德来说,人具有理性和感性,同时生活在理性和感性两个世界中,但理性优于感性,理性使人终将克服感性的盲目支配,构建起理性秩序下的和平状态。理性是左右意志的能力,“意志的功用就在于单单采取理性不顾个人爱好而认为在行为上必然的(即好的)行动……一个意志必须遵从的客观原则的提出就是理性的命令”①[德]康德著,唐钺译:《道德形上学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9页。。由于感性源于人的自私自利的动物本性,从感性出发容易使人陷入相互冲突之中,而理性却可以使人服从一种普遍原则。因而从感性到理性就是人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进步,这种进步使人类从战争过渡到和平并最终到达永久和平。
康德是从理性目的论立场来看待人类历史的,他试图像牛顿发现自然的普遍规律那样去发现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用一条原则作为理性的线索取代令人绝望的偶然性。他认为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秉赋都注定会充分并合目的地发展出来,而人作为大地上唯一有理性的被创造物,其自然秉赋的宗旨就在于使用人的理性,令自然秉赋在类中而非个体中得到发展。“一个被创造物的身上的理性,乃是一种要把它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规律和目标都远远突出到自然的本能之外的能力,并且它不知道自己的规划有任何的界限。”②[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7,14页。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只要这种对抗性最终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康德看到人身上具有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双重属性,人正是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这些非社会性驱使才跨出从野蛮进入文化的第一步,并且开始持续不断的启蒙。“这种思想方式可以把粗糙的辨别道德的自然秉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化为确切的实践原则,从而把那种病态地被迫组成了社会的一致性终于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③[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7,14页。这就是说,人作为一种动物,由于其自私自利的动物本性必定会对他的同类滥用自己的自由,因而当他与其同类一起生活时,他作为有理性的生物就希望有法律来规定大家的自由的界限。这样人类就会逐渐建立起可以使人人都得以自由的普遍有效的意志,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由于相互抗衡的武装耗尽了共同体的一切力量,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而尤其是由于经常维持战备的需要,人类的自然秉赋在其前进过程中的充分发展确实是受到了阻碍;然而另一方面,由此而产生的灾难却也迫使我们这个物种去发掘一条平衡定律来处理各个国家由于它们的自由而产生的(而其本身又是健康的)彼此之间的对抗,并且迫使我们采用一种联合的力量来加强这条定律,从而导致一种保卫国际公共安全的世界公民状态。”④[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7,14页。康德基于这一立场设想了人类未来将形成各民族的联盟,一个伟大的国家共同体。康德认为哲学的千年福祉王国学说尽管还异常遥远,但绝不是虚幻的。他还提出了不同于律法共同体的伦理共同体概念,强调伦理共同体遵循的不是作为外在强制的普遍的法则,而是内在的德性法则。
尼采对康德的和平思想的批评源于他对理性的批判。不同于康德仍处于理性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之下,尼采继承和改造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认为权力意志才是人身上最真实的东西,理性只是服务于权力意志的需要。尼采与康德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人的本能,是如康德所言人的本能会随着人类的理性启蒙而逐渐消退,以至于人最后将彻底理性化、道德化,还是人的本能始终伴随乃至支配着人类理性的发展?人类真正需要和追求的是安全感还是权力感?尼采所持的正是后一种观点。查拉图斯特拉与大智者的辩论可以视为尼采同康德和叔本华的辩论:“我的权力意志也紧跟着你的求真理的意志……凡有生命处,就有意志:但不是求生命的意志,而是——我要如是教你——求权力的意志!”⑤[德]尼采著,孙周兴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81页。康德认为人的非社会性的存在说明建立普遍法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人类在经过人的概念、经验和善意的发展之后会构建起普遍性的公民社会状态,实现永久和平。而在尼采看来,既然人的非社会性才是人的动力和源泉,我们就应该并且必须始终肯定人的非社会性,而不是试图否定和取消它。如果和平本身是依靠人的对抗性才得以实现的,我们如何能够达到永久和平呢?如果和平只是人的力量因战争而衰竭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和平是否还值得我们肯定和向往,而体现人的力量的战争又是否需要加以完全否定和排斥呢?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和平只能是两种或多种力量之间相互抗衡所形成的暂时平衡。我们必须接受我们只能永远处于由“不合群性”所导致的对抗和战争状态,而不可能指望这一状态会有朝一日转变为不再有任何对抗和战争的永久和平。康德认为对抗和战争阻碍和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迫使人类“寻求平静和安全”。而尼采提出人真正需要和追求的其实是权力意志,人愿意为此去投入战斗,不惜冒险和牺牲。“人是某种应当被克服的东西。那么就过着你们服从和战斗的生活吧!长命又有何相干!哪个战士想要受到保护!”①[德]尼采著,孙周兴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67,58,66页。由于权力意志总是在追求更多更大的权力,而只有力量的对抗和战争才能使权力意志更加强大,由此人类的未来只能是更多的对抗和战争。“不是满足,而是更多的权力;根本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不是德性,而是卓越。”②[德]尼采著,余明锋译:《敌基督者》,《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10页。在尼采看来,战争始终是所有过于内向和过于深沉的英才的大智慧,即使有所伤害也不乏疗效。这样尼采就基于其对权力意志的肯定,针对人类的未来提出了一种与康德正相对立的理想:不是由理性和道德进步带来永久和平,而是由权力意志较量形成永恒轮回。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和尼采在肯定和平或战争具有终极意义的同时又不得不做出让步,承认对方的某种存在形式。康德虽然看到战争对人类文明的威胁,主张通过理性启蒙构建世界公民状态以维持和平,但他也肯定了战争作为通向和平的手段的积极意义。“在人类目前所处的文化阶段里,战争乃是带动文化继续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唯有到达一个完美化了的文化后——上帝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永恒的和平才对我们是有益的,并且也唯有通过它永恒的和平才是可能的。”③[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75-76页。康德希望建立的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并不是取消了对抗性的社会,而是同时具有最高度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抗性亦即对人的自由具有精确规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的自由可以与别人的自由共存从而使得每个人的自然秉赋都得到发展。他用森林里的树木的比喻来形容,通过公民的结合,使得人的自私自利的倾向性表现出良好作用:每一株树木都力求攫取别的树木的空气和阳光,于是就迫使双方都要超越对方去寻求,并获得美丽挺直的姿态。不约而同的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也使用了“山上的树”的类似比喻:“它越是想长到高处和光明处,它的根就越是力求扎入土里,扎到幽暗的深处,——深入到恶里去。”④[德]尼采著,孙周兴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67,58,66页。可见,康德和尼采都关注人类的成长和未来的命运,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及其益处,只是康德同时关注个人和社会,在肯定人的非社会性的同时也肯定人的社会性,而尼采更加关注个体,把“成为你自己”当成人类的最高价值。与此同时,尼采对和平也并未一味否定,而是把和平当成是由于双方力量均衡而导致的一种暂时的状态。“你们当热爱和平,以之为新战争的手段。而且当爱短期的和平甚于长期的和平。”⑤[德]尼采著,孙周兴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67,58,66页。这与康德所谓和平是依靠人的对抗性才得以维持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康德只是肯定战争作为手段的价值,其理想仍是人类通过理性的道德法治建构实现永久和平,而尼采则肯定战争本身的价值,把人类的战争视为永恒轮回,和平只是通向战争的手段。尼采希望实现人的本能的神圣化,他心目中的超人典型主要是哥德等艺术家,而非战争狂人。这与康德要求通过发展人的理性和道德避免战争造成人类科学艺术的毁灭并不矛盾。可见,虽然康德和尼采分别倾向于和平和战争,但他们在偏重其中一方的同时也对另一方做出了让步和妥协,承认了对方存在的某种合理性。尽管如此,他们分别把和平与战争作为终极目的仍有其偏颇。和平与战争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只是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并最终选择其一,实际上不仅不能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反而加剧了两者的紧张。试图依靠理性和道德超越人的本能达到永久和平,或将人的本能神圣化以美化战争,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从这一点上看,康德和尼采关于和平与战争的认识都有各自的局限,两者的张力将这种局限充分暴露出来。只有从新视角加以考察,才有可能摆脱局限,平衡张力。
二、老子:思考和平与战争的另一条路径
尽管康德和尼采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表现出对立倾向,但他们作为西方哲学家都对人的主体性持肯定态度,希望通过肯定人的理性主体或意志主体为人类确立一个新的目标,从而彻底解决和平与战争的问题。然而,他们之后的人类历史表明他们所确立的目标不仅并不容易实现,而且在其实践过程中难免被扭曲。与康德和尼采不同,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为而不争”,为我们克服康德和尼采之间的对立,探索解决和平与战争问题的新的思路提供了启示。
康德和尼采作为现代哲学家,都反对传统基督教神学对人的统治,呼唤人的觉醒,前者完成了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从客体转向主体,突出了人的中心地位,后者提出“上帝死了”“超人将至”,进一步用人取代了上帝。康德把人视为目的,肯定求知能够使人不断获得启蒙和进步。尼采要求人为自己确立目标,不断“克服自己”“成为自己”。这种对知识和欲望的肯定使得他们都相信“战争”的必要性,把永久和平或者永恒轮回作为人类的终极目的。康德和尼采对知识和欲望的态度并不相同,前者认为求知会使人超越本能欲望之上成为有理性者,后者则认为求知应该服从于人的本能欲望的升华,但他们都企图在肯定知识和欲望的前提下,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战争)。与他们不同,老子解决和平与战争问题的思路并不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从一开始就怀疑并批判知识和欲望。在老子看来,既然知识和欲望是导致人陷入战争困境的根源,那就只有取消它们,使人重新回到无知无欲的状态才能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如果说康德和尼采的思考是“向前的”,老子的思考则是“向后的”。老子主张“无知无欲”,反对战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三章》,以下只出章名)①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90,35页。老子看到了知识给人类带来的恶果,对知识保持高度警惕,反对任何人为的主体性:“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②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90,35页。道的运动是一种循环,不断地回归自身:“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十六章》)③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90,35页。老子多次提到的“归”“复”和“静”,都是用来形容道的运动状态,他认为人生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也应遵循这种天道,顺其自然。
显然,康德、尼采与老子对于知识和欲望的态度之间存在张力:前者从知识和欲望出发走向对它们的超越,后者则要求取消知识和欲望回到自然之中。康德也看到了他与老子的分歧:“在这里他的理性并不理解它自己本身以及自己所要求的东西,但却流连忘返,而不愿像与一个感性世界里的智性居民所相称的那样,把自己限制在这个感性世界的限度之内。由此便产生了至善就在于无这一老君体系的怪诞,亦即就在于感觉到自己通过与神性相融合并通过自己人格的消灭而泯没在神性的深渊之中的这样一种意识。为了获得对这种状态的预感,中国的哲学家们就在暗室里闭起眼睛竭力去思想和感受他们的这种虚无。”④[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90,75-76页。从康德对老子思想的这一批评来看,他的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有着巨大差异。由此看来,尼采称康德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把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等同是有偏颇的。其实尼采和康德的学说都是启蒙时代的产物,他们都试图把人从基督教的“另一个世界”引回大地,使人从信仰上帝转向肯定自身,只是康德诉诸由理性和道德进步所决定的人类的普遍历史,而尼采则诉诸由权力意志所决定的个人的自我超越。在此意义上说,他们都肯定人有向上的追求,从而赋予战争以推动人类发展的积极意义。康德认为中国由于其地理位置,无须害怕什么强大的敌人,从而没能发展出自由,并由此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一个社会在其文化刚开始之际就完全摆脱了外来的危险,这对于一切文化的继续进步都是一种障碍,并且会陷入无可救药的腐化⑤[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90,75-76页。。与康德相似,尼采认为拥有敌人的价值在于能够使人与以前不一样地行动和推论,一个新的创造物,比如一个新的帝国,比之需要朋友,更需要敌人,放弃了战争也就是放弃了伟大的生命①[德]尼采著,卫茂平译:《偶像的黄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9页。。由此可以理解尼采何以像康德一样对中国传统思想持否定态度,他形容“末人”为“一种中国人”②[德]尼采著,孙周兴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7,80页。。尼采批判康德的理性和道德,并不是要人回归老子式的清净无为,而是要使人实现自我超越。他担心人在失去上帝之后会变成无所欲求,只知享乐的末人,于是提出超人作为人的新目标。这样看来,康德和尼采实际上都继承了西方哲学的传统,把求知和欲望视为人的起点,否定人回归原初状态的可能性和正当性,强调人要不断向前追求,努力成为更成熟的人,建立起更成熟的社会。
康德、尼采和老子对自然的看法形成对照,虽然他们都推崇自然,但他们对自然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康德把人的理性化和道德化视为大自然赋予人的目的,战争的灾难扼制了人类的自然秉赋,只有发掘一条平衡定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构建世界公民状态才能实现自然的目的。尼采要求克服人的理性化和道德化,肯定人的身体和意志,实现人的自然化。老子肯定“道法自然”,要求人尊重和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排除任何人为干扰。可见,康德和尼采的自然都是人向前的成长,而老子的自然却是向后的回归。表面上看来,人的成长要比人的回归更为可取,其实却未必尽然。康德关于人从动物性到人性的发展预设了对人的理性与动物性的区分,认为动物性是低级的,不完善的,将随着人的理性化的发展而被克服,人将成为完全理性化与道德化的完善的人。这种对人的认识预设了纯粹有理性者才是完善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指责人的动物性的不完善。这种预设仍是以上帝为根据的,脱离了人在大地上真正的生活。相反,尼采颠倒了康德的认识,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身体、生命和大地看作唯一真实的存在,理性是人追求权力意志的工具,人要做的是使自己的本能神圣化,而不是取消人的本能。这种预设看似比康德的纯粹有理性者更加真实,接近大地,但也同样失之偏颇,因为它忽略了人的理性的特殊性,有使人丧失理性的反思能力,沦为只知有本能的动物的危险。既然人并非只有理性或本能,而是同时具有理性和本能,那么无论试图把人变成纯粹有理性者,还是把人的本能神圣化,是否可以称为人的成长就都是可疑的。其实,正是康德的唯理论召唤出了尼采的唯意志论。这两种哲学尽管相互对立,实际上却如影随形。“想要驱赶魔鬼的不在少数,自己却落入猪猡堆里了。”③[德]尼采著,孙周兴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7,80页。尼采用这个比喻来讥讽那些追求贞洁而又难以做到的禁欲者,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也同样适用于竭力批判理性肯定本能的他自己。事实上,康德和尼采的人的成长都具有西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特性,在强调人的主动性(知识、欲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遮蔽和扭曲了自然,他们把人理解为造物主的目的或超人,都偏离了人的本然状态,这种偏离需要并能够借助老子的自然加以揭示和纠正。
老子的“不争”、无知无欲恰好构成康德和尼采的战争、知识、欲望的反题。康德和尼采强调主体性和目的性将人置于无尽的分裂、矛盾、斗争和痛苦之中,老子的思想为此提供了一剂解药。“夫唯不争,故无尤。”(《八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二十三章》)④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20、122、57,181页。老子思想与西方批判传统以逻各斯(Logos)为中心的形而上学,高呼“人死了”的后现代哲学相呼应并不是偶然的,看似回归和落后的中国哲学在此具有了惊人的超前性。“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七十三章》)⑤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20、122、57,181页。,这种通过“不争”获胜的哲学是以战争为起点的康德和尼采哲学所难以理解的,却也是处于战争毁灭威胁中的现代人所正需要的。可以说,康德和尼采分别将老子所反对的知识和欲望两种倾向发展到了极致,这在使人类获得前所未有的“进步”的同时也使现代人面对着越来越大的战争威胁,从而使得彻底反思人类对知识和欲望的追求本身成为必要。这就需要跳出以追求知识和欲望为基础的西方哲学传统本身,从老子等东方哲学家的思想中获得不一样的洞察。因此,正是对康德和尼采关于和平与战争思想中存在问题的揭示,彰显了老子思想的积极意义。在这场关于和平与战争、知识和欲望的论争中,老子留下的话语,似乎就是针对康德和尼采而发的,提出了对他们的问题的另一种解答。老子从无知无欲出发,既反对由求知所引发的人偏离自然的欲望,同时也并不否认人的合乎自然的欲望,所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三章》)。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五十五章》)。老子肯定和平,但并不完全排斥战争:“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三十一章》)①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8、145、80,77—78、80、190、56页。这样就克服并超越了康德和尼采在理性与本能、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对立和偏执,帮助陷入迷途的现代人探索一条更加健全的道路。在康德和尼采的故乡德国,老子思想一直受到广泛欢迎,《道德经》有多种德文译本,这充分验证了老子思想对于现代德国人的意义。
然而,这并不表明老子已经完美地解决了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康德和尼采的哲学呈现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张力,前者主张用战争手段达成和平目的,后者把和平视为通向战争的手段。老子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虽然没有表现出这样明显的张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完全没有张力。一方面,老子厌恶和反对战争,赞赏和支持和平。“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三十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三十一章》)他的理想社会是“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八十章》)。另一方面,老子也认识到战争在现实社会中是难以避免的,“不得已而用之”,这样一来,战争对于老子也就像对于康德一样成了达成和平的手段,尽管这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手段。与此同时,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②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8、145、80,77—78、80、190、56页。“不争而善胜”等也蕴含着把“无为”“不争”当作获胜的手段的思想,“无为”“不争”也由此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为”和“争”。有人据此认为老子并不是真正主张和平,事实上后来兵家从老子思想中发展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级谋略,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在战争中取胜。中国先秦思想中关于这方面的大量极其实用的阐述,其根源大都来自老子。也许正是由于无法解决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张力,并且看到当时的社会正在向着“争”的方向发展,与其和平理想背道而驰,老子才最终选择了脱离现实社会的独自隐居,然而这与其说是对矛盾的解决,不如说是对矛盾的逃避。老子思想后来在中国历史上颇为盛行,但这并未防止中国长期陷入治乱循环的怪圈。这表明老子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同样有其不足,它并不能使人类社会实现长期的和平与繁荣。由此看来,正视人类的知识和欲望,并尝试在此基础上解决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康德和尼采的哲学,就成了老子思想的有益借鉴,正如前述后者之于前者。这样我们就有了在两者之间开展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场对话同时也是在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之间展开的。既然无论是康德和尼采所代表的西方哲学还是老子所代表的东方哲学都并未提供解决人类当下面临的和平与战争问题的现成答案,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东西方已有的思想资源当作出发点,通过两者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取长补短,去探求新的答案。
三、东西方哲学关于和平与战争的对话
康德、尼采和老子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植根于他们对人的主体性、自然、知识、欲望的不同立场,其中康德和尼采所代表的西方哲学与老子所代表的东方哲学有着明显差异,甚至南辕北辙。问题在于如果他们在今天相遇,他们之间会如何交流呢?这其实正是当今人类的基本处境:尽管思想传统迥异,东西方却不得不同处一个地球村,如何处理和平与战争,确保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探讨这一课题需要我们在东西方哲学之间开展一场深层对话。
理解康德、尼采与老子哲学关系的困难在于,前者既领先于后者同时又落后于后者。从与理性的关系上看,老子“尚未”进入理性启蒙,康德努力“进行”理性启蒙,尼采则试图“超越”理性启蒙。这就造成了他们三人的思想之间的复杂关联:康德在老子前面,尼采在康德前面,而尼采在反对理性启蒙上又与老子产生共鸣,从而将前后顺序完全颠倒过来。首先看康德与老子。如果把理性启蒙视为人类无法逃避的进步,那么,康德就领先于老子,他肯定了理性启蒙对于人类的积极意义,认为理性的觉醒虽然从个人角度看是损失,但对于大自然的安排来说却是人类这一物种的整体收获。在康德看来,人类脱离所谓最初的天堂,是从单纯动物的野蛮状态过渡到人道状态,从本能的摇篮过渡到理性的指导,从大自然的保护制度过渡到自由状态。这对于物种来说是一场走向完美状态的进步。相反,如果把理性启蒙视为从原初安宁状态的倒退,甚至是一场灾难,人类理应尽力避免,那么,康德就落后于老子。老子早就指出知识会带来混乱与纷争:“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①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43、150页。西方在经历康德等人所代表的18世纪的理性启蒙之后并未如愿进入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而是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陷入各种精神危机和战争危机。这一方面是对老子思想的验证,另一方面也反证老子的智慧可以为西方提供某种启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少西方哲学家将目光转向东方。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提出,为了让智慧重新充实起来,也为了区别智慧与哲学,人们必得到东方游历一番,希望能够在另一种光(一种斑驳之光,斜射之光)的照耀下,让智慧站出来与理性对峙,以便重新审视理性的偏见②[法]弗朗索瓦·于连著,闫素伟译:《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页。。其实,康德自己也看到了理性的觉醒会使人类陷入骄奢淫逸,但是,他认为人一旦尝到自由的滋味,就不可能再返回到奴役即受本能支配的状态。随着理性的逐步发展,人类终将意识到自己才是自然的目的。康德肯定文化与人类天性的冲突的正面价值大于其负面作用:“所以从这场冲突里面就产生了压迫人生的全部道道地地的灾难以及玷污人生的全部罪行。可是,使人们因之而犯罪的那种冲动的本身却是好的,并且作为自然秉赋而言乃是合目的的。”③[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69-70页。
这样看来,康德与老子正是在理性启蒙这一人类的十字路口分道扬镳:“康德哲学从头到脚都是意识哲学。他在其分析中尝试去澄清一切知识的先验条件,由此整体认识先天地就被分割到纯粹知性认识的要素中去了。那去分析之物正是‘统觉的源初综合之统一:我思’。在康德那里,出发点是主体,它分析自己的先验意识基础……在老子思想中没有主—客体分离的话题,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被避开了,如果人们依循着‘道’来生活和处事的话。因此,这两者在源头上的引导性发问就是有基础性差异的,就此而言也妨碍着任何的切近。”④[德]R. 艾尔伯菲特著,朱锦良译:《德国哲学对老子的接受——通往“重演”的知识》,《世界哲学》2010年第6期。尽管如此,康德和老子都把战争视为对人类的威胁并试图阻止战争以维护和平,因而他们之间仍可以进行建设性对话。在如何实现和平的问题上,康德和老子都并非单纯用和平否定战争,而是看到战争本身尽管难以完全避免,却可以成为达成和平的手段,只是他们分别赋予这种手段以积极和消极的不同意义。对于康德,战争使人类意识到理性和道德的意义从而构建起法治下的和平。对于老子,战争使人认识到知识和欲望的恶果从而回返原初无知无欲的自然的和平状态。在现代社会,战争正愈来愈具有破坏性,防止战争维护和平变得日益迫切。无疑,没有以理性知识为基础的道德和法治,人类要实现持久和平是不可能的。然而道德和法治也并非万能,正视其局限性,肯定人的自然性和整全性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康德和老子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虽看似相互反对,实则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其次看尼采与老子。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正文第一节“三种变形”对理性和欲望做了反思和批评,表现出与老子思想的某种相似性,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两者其实相距甚远。精神的三种变形中的骆驼、狮子和孩子分别代表“你应”“我意愿”(“我要”)和“我在”(“我是”)。“你应”是指遵从具有普遍性的客观规律,社会由此构建起秩序与和平;“我意愿”是指遵从自我的意愿,社会由此陷入相互冲突和战争状态。因此,从“你应”到“我意愿”是从追求和平到追求战争的转变。为什么“我意愿”还要向“我在”转变呢?这是因为我并不能意愿过去,“它曾是”对于我是一块不可推翻的石头,“我意愿”其实仍被囚于时间的牢笼之中,并不自由。只有将“我意愿”转变为“我在”,我的意志能够对我的过去说“我曾如是意愿它,我将如是意愿它”,我才接受了我的过去,与时间达成和解。这也就是尼采所谓“命运之爱”。“我在”看似是对“我意愿”的解救,而实际上这种解救正是通过永恒轮回实现了对“我意愿”的永恒肯定,这也同时是对战争的永恒肯定。由此理性对于意志的统治就被彻底推翻,战争吞噬了和平,黑暗吞噬了光明。尼采本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走向自己发疯的悲惨结局。与尼采不同,老子面对人的欲望始终保持清醒,主张用自然加以制约和平衡。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六十八章》)“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四十五章》)①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90—91、125、171—172、123,22—24,19、6、129、40页。。这样,与尼采对欲望的超越导向对战争的永恒肯定相反,老子对欲望的警觉通向了自然的和平。
尼采从“你应”向“我要”和“我在”的转变表现出西方哲学在经历主体性危机之后试图超越主客对立的倾向。在反对主客对立这一点上,尼采与老子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立足点完全不同:老子是“尚未”,尼采是尝试“克服”。这体现在他们喜欢使用的一个相近的隐喻之中。尼采用孩子代表精神的三种变形的最后阶段,老子则用“婴儿”来形容道的自然无为状态。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十章》)②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90—91、125、171—172、123,22—24,19、6、129、40页。这里的“婴儿”是一个主客尚未区分的形象,婴儿的活动是自然的,呈现出无知和安宁。与此相应,道的循环运动也是朝向安宁的不断复归。相反,尼采的“孩子”指向未来,表现出主动性和创造性,孩子被视为一个新的开端,一个自转的轮子。尼采称救赎过去的意志是“创造性的意志”,尼采的永恒轮回不是向过去的回归,而是面向未来的自我创造。洛维特说:“尼采彻底经历和思考了《圣经》的‘你应该’向现代的‘我要’的转变,但却未能完成从‘我要’到宇宙小孩的‘我在’的决定性步骤……作为一个现代人,他是那样绝望地告别了任何原初的‘对大地的忠诚’,和在天幕下永远安全的情感,以至他那把人类命运与宇宙宿命统一起来,并把人‘改写回大自然’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③[德]卡尔·洛维特著,李秋零、田薇译:《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7页。如果不能实现从“我要”到“我在”的转变,人类就会停留在由“我要”所引起的持久的战争之中,这种战争因为不再有“你应”的制约而对人类变得无比危险。尼采个人的不幸命运同时也预示着人类正在陷入前所未有的战争深渊而难以自拔。
尼采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施特劳斯的看法相对比较公允:“理解尼采对我们这些社会科学家来说有额外的益处,在这种理解过程中,我们能够理解法西斯主义最深刻的根基。但尼采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只是尼采所意指的东西的一个愚蠢缺陷。可以说,尼采与法西斯主义有某种联系……某种程度上,尼采是法西斯主义之父这个粗浅的表述含有真理成分。”④[美]施特劳斯讲疏,[美]维克利整理,马勇译:《尼采如何克服历史主义——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讲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页。尼采鼓吹超人和战争,他没有充分预见到现代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战争不仅不能使人伟大,反而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现代战争的毁灭性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老子的和平思想,后者正是对尼采的战争狂热的有力纠正和平衡。从老子的角度看,仅从“我思”和“我要”转向“我在”仍是不够的,因为只有“我在”,就必定会与“他在”形成对立,引发冲突。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七章》)王弼注曰:“自生则与物争,不自生则物归也。”只有消除人的自私和由此引起的战争,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⑤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90—91、125、171—172、123,22—24,19、6、129、40页。这就要求从“我在”进一步转向“自在”,也就是每一个人与他人和世界的共在。老子的“为无为”包含着无主体的主体性,这对于西方哲学在尼采之后进一步克服主体性危机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另外,老子反对任何“我要”,从而阻止了发展现代性的要求和可能,这就需要借鉴尼采的“我要”从而脱离一种原始的混沌状态,只是这种“我要”不能与自然完全脱轨,以免重蹈尼采的覆辙。可见,尼采与老子虽然对待“我要”的态度相去甚远,但他们之间却可以并且应当展开使双方都受益的对话。
从康德的主客对立和尼采尝试克服这一对立的努力中,可以看到西方哲学在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向是向老子哲学的贴近。然而,能否通过回归原初自然的主客未分的状态来解决主客分离带来的问题,仍是一个疑问。如果说康德想通过战争使人精疲力竭从而迫使人类建构持久和平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而尼采肯定战争能够使人伟大则是另一种危险的幻想,那么,一种与他们不同的、从一开始就排斥知识和欲望的原初状态的和平能否实现,同样令人起疑。康德的永久和平、尼采的永恒轮回和老子的天道循环都根源于对立面的冲突引起的推动。因此,东西哲学之间尽管有对立和冲突,但也是相互启发的,而非相互代替的,它们共同构成和推动人类的精神向着更丰富的方向发展。随着知识技能的进步,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充满各种冲突的不确定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像以往那样只靠肯定或排斥知识和欲望已经无法解决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为此人类既需要肯定康德所代表的知识、尼采所代表的欲望,同时也需要倾听老子对知识和欲望的警告以及回归自然的呼唤。老子的思想并不像康德和尼采所以为的那样只具有消极性,同时也有为人类指引未来的前瞻性。也许人的成长与回归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对立,而是有共存的可能。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到海德格尔的发展,可以被理解为在笛卡尔那里主客分离的彻底撕裂,和海德格尔那里对主客分离的基础存在论上的克服之间的张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标志着主客体之间的空前对立和紧张,尼采则将主体性哲学发展到极端并开始尝试克服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所以他们都对老子在一切主客体对立之前取得的无为给予否定。而海德格尔则真正开始走出主客体的对立,从而在其反思并批判康德和尼采的同时,与老子思想产生了共鸣:“老子的诗意运思的引导词语就是‘道’(Tao),‘根本上’意味着道路……人们把‘道’翻译为理性、精神、理由、意义、逻各斯等。但‘道’或许就是产生一切道路的道路,我们由之而来才能去思理性、精神、意义、逻各斯等根本上也即凭它们的本质所要道说的东西。”①[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语言的本质》,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第1101页。海德格尔曾这样谈到他与一个中国学生一起翻译老子的经历:“我相信,在挺过荒漠化的几个世纪后,[这种对话]会为未来准备根本性的东西。”②[德]R. 艾尔伯菲特著,朱锦良译:《德国哲学对老子的接受——通往“重演”的知识》,《世界哲学》2010年第6期。海德格尔从其与道家的对话中看到了通向未来的可能性,他在一次访谈中展望中国有一种“思想”的古老传统苏醒过来,它帮助人们,使得通向技术世界的自由关系得以可能。这也反过来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思想要想在现代“苏醒”过来,也不得不改变其形式,从而演变成一种新的思想。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来自西方哲学的刺激和影响必不可少。我们只有不断致力于开展和推进东西方哲学关于和平与战争的对话,才有可能应对人类在现代所面临的战争危机。正如康德、尼采和老子的对话所揭示的,由于东西方哲学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地迥异,两者之间的对话将注定是困难的和长期的。也正因如此,我们就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