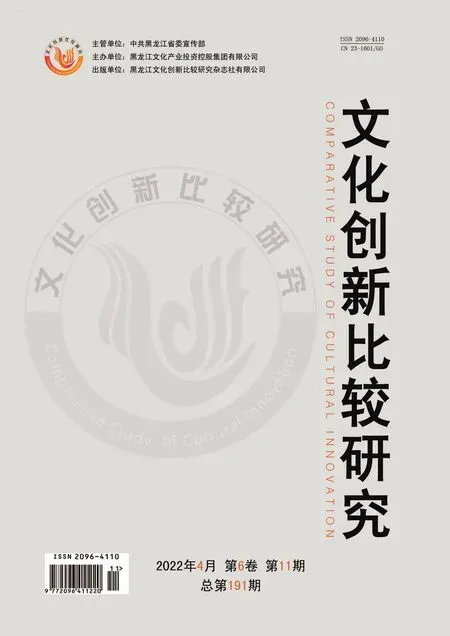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数字化保护模式的选择
罗兰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港口管理学院,浙江舟山 316021)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海洋非遗”)是人类在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实践中所创造的非物质成果的总和[1]。传统艺术类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作为海洋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在海洋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以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存在的全部非物质成果的总和。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包括舟山锣鼓、舟山渔民号子、舟山船模、舟山渔民画等多种类型,具有鲜明特性的艺术特性以及历史、文化、艺术、经济等独特价值[2]。随着舟山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在艺术领域的应用,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保护同样面临许多现实问题与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实现从以静态化、固态化和物理储存为特征的传统保护方式,向动态化、活态化、数字化、产业化、大众化为特征的现代保护方式转变,创新保护模式,优化保护策略,增强保护效果。
1 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的概况与特性
1.1 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概况
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标准,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分为四个大类:一是民间文学类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民俗类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传统艺术类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四是传统技艺类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3]。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遗的分类,又可将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划分为民间音乐类、民间舞蹈类、民间美术类以及曲艺四个类别。
舟山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境内分布海域面积22 000 平方公里,陆域面积1 371 平方公里,拥有2 400 多公里的海岸线和1 390 多个岛屿[4],以及独特的人文历史环境,包括从河姆渡时期开始的久远文明,从田螺山遗址先民开始迁徙而来的居民,在经历长期曲折复杂历史变迁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包括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在内数量众多的、海洋特色鲜明的非遗。
目前舟山已经建立了县(区)、市、省、国家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和舟山非遗代表名录体系,其中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5 项、省级名录38 项、市级名录79 项,县(区)级非遗名录246 项。
在列入国家级非遗的项目中,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共有2 项,即民间音乐类海洋非遗舟山锣鼓、海洋号子——舟山渔民号子,占目前全国国家级民间音乐类非遗项目总数的2/7,占目前浙江省国家级民间音乐类非遗项目总数的2/3。
在列入省级非遗的项目中,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共有14 项。其中省级民间音乐类海洋非遗4 项,即舟山锣鼓、舟山渔民号子、嵊泗渔歌、渔工号子;民间舞蹈海洋非遗2 项,即跳蚤会(定海)、跳蚤会(普陀);民间美术海洋非遗4 项,即民间绘画(普陀渔民画)、舟山贝雕(定海)传统技艺、船模艺术、普陀船模艺术;曲艺海洋非遗4 项,即翁洲走书、定海布袋木偶戏、岱山布袋木偶戏、唱新闻等[5]。
在列入市级非遗的项目中,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共有31 项。其中民间音乐类海洋非遗5 项,即舟山锣鼓、舟山渔民号子、舟山渔歌、舟山佛教音乐、贺郎调(定海);民间舞蹈海洋非遗7 项,即跳蚤会、马灯舞、打莲湘、踩旱船、舞龙(白泉舞龙)、跳蚤舞、马灯舞;民间美术海洋非遗13 项,即舟山渔民画、临城剪纸、舟山船模、舟山贝雕、普陀木雕、书法木雕艺术、普陀根雕、舟山船模、嵊泗海洋剪纸、灰雕、普陀刺绣艺术、鱼骨塑画(岱山)、舟山船模(岱山船模艺术);曲艺海洋非遗6 项,即布袋木偶戏、翁州走书、舟山新闻(唱蓬蓬)、舟山走书、布袋木偶戏、布袋木偶戏(临城木偶戏)。
1.2 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的特性
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相对于一般艺术类非遗和一般非遗而言,因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海洋实践活动而呈现出自身独特的艺术特性。舟山群岛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构成了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和空间,也是其艺术特性形成的自然地理因素。舟山群岛居民的海洋实践源于其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是他们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行为,具有高风险性、合作性、高科技性、海陆一体性等特征。具有这种特性的海洋实践活动是包括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在内的海洋非遗乃至整个舟山海洋文化形成的根本源泉,也是影响和形成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艺术特性的实践因素。概而言之,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具有如下特性。
(1)地域性。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根植于舟山群岛的广阔海洋海岛地域,是舟山人民在海洋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形成和创造的海洋文化艺术成果,具有鲜明的海洋海岛地域性特性。舟山传统音乐类海洋非遗中的渔歌号子,是由舟山群岛渔民群体在生产实践中自己创作的;舟山传统舞蹈类海洋非遗大多是为了开船庆典、祭祀海神、祈佑出海平安、庆祝渔业丰收等;舟山传统美术类海洋非遗也是以海洋群体及其活动为主题的,比如,产生于舟山渔场的普陀船模艺术,就是舟山世代以捕鱼为主、终身以渔船为伴的海岛渔民创造的;曲艺类海洋非遗中的舟山锣鼓则产生于庆祝渔业丰收的过程中。
(2)多元性。首先,从文化来源看,舟山群岛从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东渡至此,到明清“海禁”恢复,内陆移民陆续迁入,不仅有浙江境内的越文化、浙东文化、吴文化的影响,还有闽南文化甚至境外文化的渗透,从而构成了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来源的多元化特性;其次,从文化元素看,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具有传统音乐、舞蹈、美术、曲艺和戏剧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再次,从区域差异看,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的同一种艺术形式的不同区域表现也是多样的。比如,就舟山渔民画而言,从所处区域可以分为普陀渔民画、定海渔民画、岱山渔民画、嵊泗渔民画等。这些不同区域的渔民画同属一个非遗编号,在类别上同属舟山渔民画非遗,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同属传统绘画艺术,但不同区域的渔民画表现形式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比如在画面特点上,普陀渔民画刻画相对细致,常用线条勾边;定海渔民画内容来自真实场景,使用大民机色块平涂;岱山渔民画大多以描绘海洋生物为主;嵊泗渔民画多为神话故事题材,常描绘民俗场景。由此形成了舟山渔民画多元共生、求同存异、百花齐放的现实状况。
(3)无形性。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具有海洋非遗的共同特性,它是一种无具体形态的、依附于人而存在的文化遗产,是海洋文化思维抽象化的产物,代表着海洋非遗的精神高度。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中的渔民号子、舞蹈、绘画、曲艺等都是无具体存在形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贝雕、船模等虽然是有着具体形态的,但都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着的,其自身的无形性与传承过程中依靠于实体或人的有形性其实并不冲突,它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中产生,通过人身传递得以传承,随着人的实践改进而创新,从而得以与时俱进地发展。
(4)互动性。舟山海洋实践活动合作性、协调性和同舟共济特征,决定了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具有明显的互动性特征。比如,舟山传统美术非遗中有关海洋生产和生活题材的内容,常会出现多人协作,相互配合开展活动的场景和画面;传统音乐类海洋非遗中的海洋渔歌、渔民号子等多是以互相邀歌的形式进行的,一唱一和,是需要渔民的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展开和完成;传统舞蹈类海洋非遗也多是以群体舞蹈为主,通过多种角色的协作与配合,才能形成完整的庆祝丰收或祈祷出海平安等大型舞蹈活动。
(5)娱乐性。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具有艺术非遗的共同特性,传统音乐、舞蹈、美术和曲艺等海洋艺术非遗都来自涉海群体生活,扎根渔民社会,紧跟时代潮流,符合海岛民众口味,是对渔民生活智慧的凝练和升华,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一方面,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题材和内容中涉及的很多元素和故事都很生动有趣,比如舟山渔民画中“菩萨穿灯笼裤”的传说;比如舟山传统民俗舞蹈“打莲湘”,用一根长约三尺、比拇指粗的竹竿,两端镂成三个圆孔,每一孔中各串数个铜钱,涂以彩漆,两端饰花穗彩绸。另一方面,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源于渔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渔民在这种实践活动中愉悦心情,享受劳动快乐,陶冶审美情趣,提高劳动效率。舟山渔民号子就是舟山渔民捕鱼劳动的直接产物,这种传统音乐充分体现了渔民参加捕鱼劳动的愉悦心情和欢乐情景。
2 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数字化保护模式的选择
分析和研究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的特性和活态流变共性,是选择其保护模式的前提和依据。在此基础上,需树立大保护理念,遵循活态化保护思路,把握数字化保护取向,采取基因式保护策略,选择最佳保护模式。
2.1 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保护的大保护理念
关于非遗保护概念的界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了一个相对宽泛的广义保护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给出了一个狭义保护的界定。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关于“保护”一词的定义,非遗广义保护的内涵,是指确保非遗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6]。但这并非是要对所有非遗不加区分一律都要传承、弘扬,而是要贯彻党和国家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界定,非遗狭义保护的内涵是指“传承、传播”行为。所谓“传承”是指将优秀的艺术类海洋非遗列入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由政府资助该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交流活动,培养后继人才,从而使该项非遗能够世代相传下去,不会消失。所谓“传播”是指对列入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优秀艺术类海洋非遗进行宣传、展示和合理开发、利用,从而弘扬优秀传统艺术类海洋文化,促进社会文明进步[7]。相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关于“保护”一词的定义,上述界定的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保护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
笔者认为,非遗保护包括狭义保护和广义保护两层含义,是两者的有机统一。因此,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保护应当树立大保护理念,将狭义保护和广义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将非遗的保存保持性保护、传承传播性保护、开发应用性保护结合起来,构建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保护体系,才能达到其全面、科学、规范、有效保护和传承的目的。
2.2 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保护的活态化思路
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因其特殊海洋海岛自然条件、相对封闭的传承环境、独特的文化属性及其表现形式,使其具有地域性、多元性、无形性、互动性、娱乐性等鲜明特性。无论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其都是借助人们的行为活动来体现,所以都是活态的,是活在民间的艺术文化遗产,是联系舟山群岛民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纽带。在海洋经济时代,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保护传承要尊重、保持和保护其特性,就应当遵循和选择活态化保护的思路[8]。
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活态化保护的理论依据是其所具有的活态流变性。具体来说,这一本质特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活态”特性,它决定保护需要确保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的传承,确保非遗主体(传承人和群众)的参与,确保非遗存活在当代,只有尊重并基于这一特性进行活态化保护,才能形成科学理性的保护思维,才有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二是“变化”特性,它决定保护要提倡创新,提倡发展。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活态化保护,无论是其历时态的纵向传承还是其共时态的横向传播都是一个动态过程,是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结合。继承就是要充分尊重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的独特个性,创新就是在不改变其原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重塑。这就需要依托多种现代化技术,采取多样化手段,将传统海洋艺术文化形式与各种载体有机结合,顺应海岛民众的文化艺术兴趣,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使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继续活态再现于海岛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延续舟山海洋文化的血脉,生生不息。
因此,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活态化保护,就是针对其活态流变性的特点,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以人为本,注重传承人的保护;注重文化空间的保护;重视观念创新;重视立法和制度建设;重视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构建政府、学界、民间组织和民众共同参与的合作体系;注重适度开发和产业化。
2.3 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保护的数字化取向
所谓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数字化保护,就是运用数字技术将其转化为数字化形式,采取各种方式加以保护。即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运用数字设备对其进行信息获取、存储、加工、输出、传播等操作的保护方式。包括通过计算机系统建立相关的数据库,实现资源的信息共享,既有利于信息的保存、修复整理、学习研究,又有利于传统艺术非遗的传播与传承。这种数字化保护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介入非遗保护领域的应用,对于维护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的原真性、活态性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方式。与传统保护方式相比,这种数字化保护更具有安全性、资源共享性、应用便利性、传播广泛性、增强互动性等优势和特点。
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数字化保护的重点在于,基于自身的特点建立和健全一个适合时代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活态传承机制,使得在现代科技下非遗仍然能够得以传承。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主要由传统艺术海洋文化活动及其文化空间组成,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只有建立和谐的非遗表现形式并处理好与文化空间的内部关系,才能保证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完整性。所以,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数字化保护就必须依附于一定文化活动或表现形式,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并通过“开发”和潜移默化的“实践”来构建适宜的文化空间,实现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文化活动的“重生”和再现。
2.4 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保护的基因式路径
当前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数字化保护仅限于非遗艺术形式的表层数字化,对非遗的本真性、原生性、活态性的数字化保护还不够。艺术类海洋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不只是简单地整理、记录、编纂各类艺术类海洋非遗文字资料,也不仅仅是录音、录像,保留一些静态的资料,而是要对其进行活态地、完整地、本真地再现。过去那种图片加文字说明或视频记录保存的简单传播方式显然不能满足非遗的传播要求。特别是在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和新媒体时代,传统的传播方式难以使艺术类海洋非遗得到更加广泛高效地延续和发展。这就需要从以往注重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项目的抢救性保护,向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转变。实现这一转变将解决如何有效地保护艺术类海洋非遗的活态性、如何选择并建构适宜的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保护模式、如何保证其数字化保护传承和传播的科学性等问题。
然而,认识和传承非遗,本质上指对非遗中起决定作用的本生态的认识和继承。笔者认为,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的数字化保护的根本问题是其起决定作用的构成元素的数字化保护问题,这些构成元素才是艺术类海洋非遗的文化基因、记忆基因。对这些元素的数字化保护是一种深层的基因式保护,也是一种根本性的、持久性的、战略性的文化保护,意义重大而深远。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关于海洋非遗特性与价值、保护传承与传播、数字化保护与开发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关于海洋文化艺术遗产的抢救性保护、海洋民间艺术的传承途径及其产业化前景、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保护与开发、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保护与开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则较少;而关于舟山传统艺术类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方面的研究成果尚未见到。因此,关于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元素的数字化表达,建立舟山海洋非遗元素数据库并利用其可扩充性和专家知识共享的优势,再结合现有的数字化艺术技术,将会开辟一条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创新之路。
2.5 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最佳模式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基于元素数据库的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数字化保护模式,立足于舟山传统艺术类海洋非遗的活态流变性特征,体现了非遗大保护或广义保护的理念,顺应了非遗活态化保护的趋势和价值取向,选择了非遗数字化保护这个现代化保护方式,抓住了非遗的基因式保护这个根本路径和治本之策。这种保护模式不仅相对于传统的群体和个人保护、原生态保护、图书馆和博物馆馆藏、传统教育方式等非数字化保护模式,而且相对于其他数字化形式进行保存、传播和传承的模式,者是最根本、最适宜的非遗文化基因保护模式。
构建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元素数据库是实现其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基础和关键,对于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文化保护及其行业应用带来的融合与创新意义更为深远。为此,必须在深入研究舟山并针对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特点和发生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分类法与标签法科学解析舟山渔民画的构成元素,深入研究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元素的数字化表达方式,精心设计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元素数据库平台的基本结构及其构建方案。
开发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元素数据库应用系统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基于元素数据库的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开发性保护。这就需要应用现代艺术设计理论对舟山艺术类各种形式的海洋非遗元素进行抽象和分类总结,将其研究结果进行数据库概念设计和数据库逻辑设计,开发基于现代艺术设计理论的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元素数据库应用系统,并将其进行数字化表达,实现舟山艺术类海洋非遗元素的检索、浏览、结果显示与处理、信息管理等功能。这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付出长期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