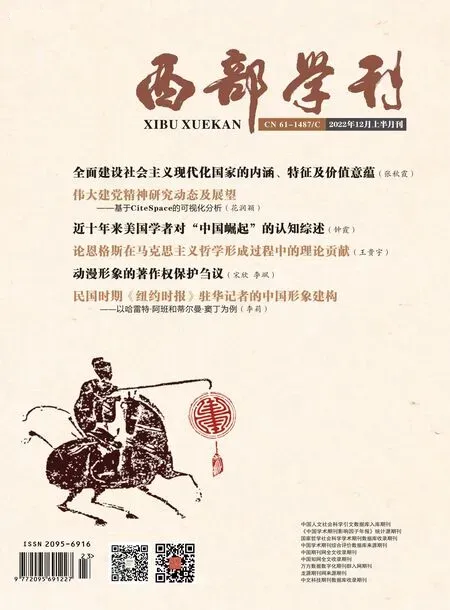民国时期《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中国形象建构
——以哈雷特·阿班和蒂尔曼·窦丁为例
李 莉
美国《纽约时报》的中国报道肇始于十九世纪中叶。民国成立以后,《纽约时报》开始持续向中国增派专业的新闻记者,前后总数高达16人[1],规模相当可观,在美国新闻业同行中遥遥领先。这些职业驻华记者的中国报道构成了民国时期美国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的重要力量。正如美国研究者伊罗生所言,报纸是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知识来源,尤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中国的报道绝大部分是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2]《纽约时报》及其驻华记者名副其实地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主流新闻业打造中国形象的关键力量,深刻影响了美国舆论的对华态度以及美国政要的外交方略,意义深远。
一、哈雷特·阿班和蒂尔曼·窦丁及他们的中国报道
在《纽约时报》十余位职业驻华记者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哈雷特·阿班(HALLETT E.ABEND,以下简称阿班)和蒂尔曼·窦丁(F.TILLMAN DURDIN,以下简称窦丁,也译为德丁),他们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抵达中国。阿班于1927年开始担任时报首席驻华记者,常驻上海从事日常新闻报道,窦丁于1937年加入时报,主要在武汉、南京和重庆等地从事战地报道。他们入职《纽约时报》的时间相差十年,但都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中国新闻,全面报道了国民党北伐、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西安事变、重庆大轰炸等重大历史事件,是民国时期驻华记者中的典型人物。他们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不同以往,报道主题更加凝重,新闻框架更加清晰,立场态度更加鲜明,充分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美国社会中国形象认知的重大转变。
(一)阿班的中国报道
阿班于1926年初来华,之前他一直在美国的地方报纸供职,在多家地方报纸做过记者和编辑,甚至当过总主编,后来还去好莱坞从事过写故事和编字幕,最后才辗转抵达中国[3]。正如研究者所言,阿班是一位不甘寂寞、喜欢冒险、跃跃欲试的职业新闻人,他对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深恶痛绝”[4]2。虽然阿班已经在美国报界打下良好的基础,可是中国仍然成为他理想的逐梦之地。阿班抛家舍业、毫无保留地奔赴远东,开启了自己长达十五年的中国旅程。
知名在华新闻人、《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JOHN B.POWELL)曾经这样评价:“哈雷特·阿班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也是最早为美国报纸读者带来了大量有关满洲和远东局势新闻的美国记者之一。”[5]据统计,在华期间,阿班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中国报道总计高达一千两百余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个面向,对中国时局的分析鞭辟入里,全面、生动地勾勒了民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恰如杨植峰所言:“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到《纽约时报》,传递给美国大众、全球大众。”[4]2
整体上看,阿班的中国报道以硬新闻为主。他常驻上海,平日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层官员交往密切,甚至亲自采访过宋庆龄和蒋介石,因此经常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重大新闻线索。虽然阿班在中国的名望远不及美国记者“3S”(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但是,他的报道能够反映出二十世纪初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新闻生产的常规机制,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二)窦丁的战地报道
根据《纽约时报》的记载,窦丁在去中国之前,曾经是哈佛大学的尼曼研究员,先后在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地方报纸担任记者,1930年抵达中国[6]。1930至1937年,窦丁先后在中国本土的几家英文报纸供职,1945年离华,在中国旅居的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与阿班有所不同,窦丁是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才为《纽约时报》工作的,他主要活跃在南京、武汉和重庆等地,以采写战地新闻见长,是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最早向世界进行播报的西方新闻记者之一。
整体上看,窦丁的中国报道主要集中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尤其在1938年驻扎重庆后,他向《纽约时报》发回近百篇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新闻,成为书写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时局的关键性人物。窦丁性格内敛,不善言语,为人谨慎,但却不惧艰险,总是亲临新闻现场,在枪林战雨的第一线进行报道,他用客观冷峻的笔调为世界书写了一幅立体全面的中国画卷,与阿班一起成了《纽约时报》民国时期中国镜像的重要执笔人。
二、《纽约时报》中国报道的框架和话语策略
从整体上看,西方媒体塑造中国形象的主要方式是新闻报道的框架和新闻话语的策略。报道框架主要是指报道文本的组织手段和方式,它既可以表现为新闻记者对某个议题不同层面的强调程度,也可以表现为记者在进行报道时所依赖的价值观或者抽象原则[7]。话语策略则是指新闻从业者潜在信念和主观态度在文本中的直接或间接表达,包括主题的控制、词汇的选择以及信源的调用等多个方面[8]。新闻的报道框架和话语策略对于如何塑造中国形象具有非常重要影响,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报道框架就有什么样的中国形象,有什么样的话语策略,就有什么样的中国故事。
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阿班还是窦丁,他们对于中国形象的建构都是基于明显的新闻报道框架和话语策略选择的。
(一)全面危机的视角
报道框架决定了新闻记者采用什么样的视角看待报道对象。在多种多样的新闻体裁中,新闻评论是报道框架最直观的体现。阿班特别善于从整体上分析中国的时局,他的报道文本有十分之一以上的篇幅都属于新闻评论,这些评论既包括阿班对于中国局势的分析判断,也包括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和推论。从整体上看,阿班并不看好中国,他甚至认为中国已经处在摇摇欲坠、行将就木的边缘,总体呈现出一种全面危机的中国报道框架。
概况来说,这种新闻框架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阿班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直观体验,另外一方面则来自于阿班作为一名美国记者所保有的西方价值观念。1926年抵华后,阿班采访的第一站就是广州,时值北伐战争的前夜,国民革命运动正在那里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抵达广州的当夜,阿班就亲身经历了流弹的袭击,沙面岛的紧张气氛更是让他“震惊不已”[4]9。可以说,阿班从一开始领略到的中国就是一番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景象。在广州的所见所闻立刻颠覆了阿班来华之前积累起来的对于中国认知的美好想象,这种深刻的第一印象在激发起阿班强烈的新闻敏感的同时,也在第一时间让他看待中国的视角被一种全面危机的框架所定格。
此后,阿班接连采访了大连、牡丹江和哈尔滨等地,亲眼目睹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随后又于1928年赴山东采访,独家报道了济南惨案,初次“尝到了战争的滋味”[4]75,这样的采访经历让阿班看到的是一幕幕不断上演的中国外交危局。在此期间,阿班的经历加深了他对中国军阀的了解,让他深刻认识了中国的内政问题。1927年底,阿班在时报发表《中国沦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一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庞大的军事机器正在将中国人的性命碾碎。……正是因为地方军阀的独断专行和军事管制法的蔓延,全国的形势才渐趋分裂。”[9]阿班直言道:“以我的管见,中国的整体局势,预示着将有连绵不绝的内战。”[4]78
可以说,初来乍到的采访经历给阿班的中国印象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促使他的报道从一开始就锁定了一种负面的中国报道框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阿班先后报道了“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淞沪会战等重大历史事件,每一次的采访和报道事实上都是对中国负面认知的一次强化和深化,让“全面危机”的中国视角愈加清晰和稳定。
此外,固有的西方价值观对阿班报道中国的新闻框架产生了影响。可以说,阿班始终是在以美国的标准和立场打量中国,包括广州国民革命浪潮中的反帝运动、东北地区日本势力的扩张、中国农村地区的“赤化”、长江贸易中的税收盘剥以及饥荒、洪水、弃婴的发生等议题均在美国二十世纪以来进步主义、门户开放以及救赎全球心态的普遍关照之下。不难想象,在美国国家优越感和海外扩张野心的支配下,阿班看到的势必是一个“千疮百孔、危机重重”[5]的中国。
不仅阿班如此,谨慎寡言的窦丁也一样对中国充满忧虑。窦丁于1930年来到中国,在这样的多事之秋,他的所见所闻可以说与阿班并无二致。战事连绵的现实很难让窦丁对中国产生美好的印象,特别是在1937年底亲眼目睹过南京大屠杀之后,窦丁对中国的时局状况完全悲观绝望了。他在采访南京大屠杀的电文中写道:“南京的被占领,是中国军队遭到的大失败。在近代战史上,也是一次最悲剧性的军事毁灭。……将来如何?眼前的将来不会有光明。”[10]加之后来在重庆大轰炸中的长期战地采访经历,让窦丁对于中国危局的认识更加深刻和清晰,通过“迅速准确而全面地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首都重庆不断承受日军轰炸且遭到重创的血腥场面”[11],窦丁也同样打造了一个危机四伏的中国形象,与阿班的报道框架达成基本共识。
(二)苦难灰白的底色
在新闻话语策略的选择上,阿班和窦丁的侧重点不同。阿班善于调用那些灰色、消极的词汇来描述中国。在他的报道中,随处可见叛乱镇压(crush)、控制(control)、反抗(rebel/rebellion)、暴动(riot/revolt)、冲突(conflict/clash)、入侵(invade/invader)、危险(fear/danger/peril)、战斗(fight/battle)等高频词汇。它们基本上都属于负面的、否定性的消极词汇,反映出一种高度的紧张和对立,一般用于对反常社会现象的界定和描述。正如研究者所言,新闻话语在达成社会意义的过程中,“褒贬善恶、区分正常与反常、赋予价值涵义,以最终形成符合主流意识的规范化角色。”[11]这些词汇的频繁使用明显意在说明中国的无常和动荡。
与阿班不同,窦丁比较善于通过大量的数词来刻画中国的苦难。例如在1937年12月18日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电文中,他写道:“在难民区的一个建筑物里,被抓走了四百个男人。日本兵把他们五十人一排,绑成一串,由拿着步枪、机关枪的日本兵部队押往屠场。”“记者在12个小时中,就三次目击集体屠杀俘虏。有一次是在交通部附近防空壕那里,用坦克炮对准一百余中国士兵开炮屠杀。”“记者在登上开赴上海的轮船的前一刻,在江边马路上看到二百个男子被屠杀。屠杀只花了十分钟。”[10]在1939年报道重庆大轰炸时,窦丁还在多篇报道的标题中采用罗列数字的方式——“数百人在重庆空袭中丧生”“一枚炸弹将300人掩埋”“受害者人数估计有3000至10000人”“200万人口只留下了30万”[12-13],这些数词生动展示了日军野蛮的疲劳轰炸和中国军民所处的悲惨情境。
不难发现,在阿班和窦丁的新闻记录中,苦难灰白的中国底色非常突出。实际上,在阿班担任《纽约时报》首席驻华记者期间,他连续撰写出版了《苦难的中国》(1930)、《中国能生存下去吗?》(1936)、《中国的混乱》(1940)三本有关中国时局的新闻评论集。可以看出,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阿班对于中国的看法都是相当惨淡的,正如他在书中所言,中国已然是一具“痛苦之身”[14]vii,正在遭受各种顽疾的折磨,包括边疆冲突、武装土匪、财政破产,以及饥荒和疾病、鸦片和文盲等在内的多种社会问题已经耗尽了中国全部的积累,“希望业已演变成令人愤怒的绝望”,“中国最终可能被迫陷入国家毁灭之中”[14]84。
三、《纽约时报》对华典型新闻报道分析
在阿班和窦丁十余年的中国采访报道实践中,他们都曾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头号西方报道者,对于重大新闻事件的采写和报道能够更加充分地说明《纽约时报》中国形象建构的框架和路径。
(一)阿班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从12月13日开始至12月28日,《纽约时报》总计在头版刊发了十五篇由阿班所撰写的有关“西安事变”的中国新闻,这样的报道规模实属罕见。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十年,阿班的中国报道并没有太多机会登上头版,正如他自己所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美国的公众对于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事情,一概兴趣寥寥。”[4]4
那么,“西安事变”为何会获得《纽约时报》如此高度的关注?究其主要原因,根本在于阿班对“西安事变”的报道采用了一种高度戏剧化的报道方式。他从一开始就将“西安事变”描述成了一场事发突然、情节曲折、结果令人意外的政治闹剧。这一方式迎合了美国商业报刊的市场原则,离奇惊险的新闻故事无疑更能引发人们的普遍趣味和广泛关注。事实上,在充满西方霸权的世界新闻话语体系中,“东方国家中的战争、冲突、灾难等负面新闻始终是国际新闻的卖点”[15],《纽约时报》也难逃其外。正如阿班自己所言,“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首脑居然遭到了劫持,且危在旦夕”“这是则头等重要的新闻”[4]192。在他看来,“西安事变”恰恰是中国动荡不安的真实写照,正是他致力于塑造全面危机中国形象的有力注脚。阿班通过设置悬念、连续报道、文学性描写等多种方式,把一个他并未在场的新闻事件打造成了一个让人充满惊叹的中国故事并成功引发了美国关注,并成为中国在二十世纪逐渐走进世界舞台的典型事件。
(二)窦丁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报道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窦丁和美国多家知名媒体的记者一起进入重庆采访,大轰炸一度成为重庆时期有关中国报道的重大议题。根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2年间,《纽约时报》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报道总计达到了一千五百余篇,窦丁撰写了大量的战地消息,他的报道有近一百篇,是塑造危难中国形象之中的典型报道。
窦丁长于战地报道,他特别能够通过细腻、全面、立体的视角来揭示重庆大轰炸的惨烈情境。比如,1939年5月5日,窦丁这样描写了大轰炸后重庆市区的场景:“火光和烟雾一直覆盖着弯曲狭长的城墙,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口血红的棺材,重庆正在日军连续两天空袭造成的灾难中挣扎,大火穿过了整个市中心并在附近的街区不断蔓延燃烧,消防员、战士和志愿者前仆后继地灭火,可是大片的土地仍在肆意燃烧。救援的士兵竭尽全力地为伤残人员寻找医院、拯救废墟中的受困者并集中掩埋死去的人们。”[16]生动再现了大轰炸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1940年5月27日至31日,窦丁连续刊发来自轰炸现场的目击报道,他通过叠加的手法立体呈现重庆所遭受的重创——“约有93架战机轰炸市郊”“约200人死亡,300人受伤,大部分是平民”“160架日本战机对重庆进行史无前例的连续六小时轰炸”“轰炸重庆成为例行公事”[17-21]。
有研究者指出,窦丁的报道“如日记般细致周密地记录了一个城市在轰炸中的生存状态”[11],而这样的记录方式建构起了世界舆论对于中国的基本认知框架,迅速准确地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一种全面危机的中国媒介形象。
四、结语
正如研究者所言:“正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前半叶,美国编辑和记者作为一个职业团体在中国活跃起来。”[22]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西方大报均已形成比较稳定的驻华记者群体,并对国际新闻报道进行了大笔注资①。凡此种种均提升了在华美国记者新闻传播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他们的中国报道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作为这一时期《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中的重要代表,阿班和窦丁通过十余年的中国观察和采访报道,以职业新闻人的视角持续建构起一种悲观的、苦难的、危机的中国国家形象,不仅引发了美国舆论对于中国的普遍同情,也促成了美国政府对其远东外交策略的全面调整,他们的中国报道构成了美国媒体中国镜像变迁的重要历史链条。
注 释:
①事实上,《纽约时报》正是凭借杰出的国际报道为其奠定世界性声誉的,无论是在阿道夫·奥克斯掌管期间(1896—1935年),还是在阿瑟·海斯·苏兹伯格主持期间(1935—1961年),时报一直都不惜代价地维持着对战争和国际新闻的高比例报道量,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代加大了对国际新闻生产的资金投入。(参见:苏珊·蒂夫特,亚历克斯·琼斯.报业帝国——《纽约时报》背后的家族传奇[M].吕娜,陈小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