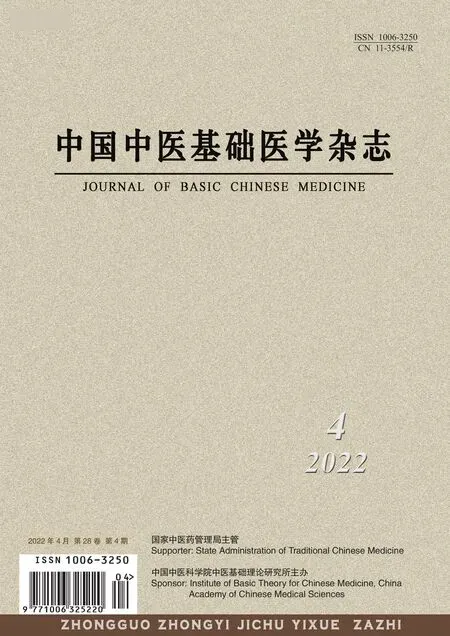新安医家程鉴生平考及其学术成就探析*
邓 勇,梁 媛,王旭光,王梦雅,陈德超,程 新△
(1.安徽中医药大学,合肥 230012;2.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程鉴,字明心,号芝田,清嘉庆至同治年间徽州府歙县(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槐塘程氏医家,生卒年月不详。程姓为徽州望族,《新安名族志》将程姓列为诸姓之首,槐塘作为程姓祖居首村著录。明清时期槐塘程氏儒医众多,医著丰富,除本文所论程鉴外,尚有程琎、程玠、程衍道、程应旄、程林、程正通、程秉烈、程曦、程镜宇及《松崖医径》(程玠著)、《迈种苍生司命》(程衍道著)《圣济总录纂要》(程林著)等众多医家医著为后世所知[1]。程鉴为名医程正通后人,幼承家传医术,精悉历代医籍,学术造诣颇深,撰有《医法心传》1卷和《医约》4卷。程鉴曾于浙江衢州行医,传道雷逸仙,逸仙之子少逸得父传,为程鉴再传弟子,少逸之子雷大震与歙县程曦、三衢江诚等人皆受业于少逸,学术传承脉络清晰。
1 程鉴及其著作考证
1.1 程鉴生平考
程鉴具体生卒年不详。刘国光《医法心传·序》[2]说程鉴“嘉道间悬壶于衢”,假定程鉴于清道光元年(1821)至衢州,另外从其《悼亡》诗之二“书来一棹到衢州,五女临歧泣不休”,可知其有五女。清代男子普遍在15岁左右结婚,程鉴第五女出生应在22岁以上。后程鉴离家至衢州时五女已略通人事,“临歧泣不休”,此时程鉴应当在25岁以上。由1821年上推25年是1796年(嘉庆元年),故程鉴应生于1796年以前。另《医法心传》末有程鉴所写跋文,署明写作时间为“同治贰年孟春吉旦”,清同治二年为公元1863年,这是目前唯一能够确定程鉴生平活动确切年代的记载。若按此前推设程鉴生于1796年以前,至同治二年已在六十有七以上,应与去世之年相差不多。
程鉴为槐塘程氏主要代表医家之一,生平主要见于三处。其一,民国年间衢州郑永禧著《衢县志》中所录《西安怀旧录》。民国《衢县志》卷二十四《人物志四·流寓》:“程鉴(《西安怀旧录》),字明心,号芝田,歙县诸生,名医程正通之后,游学来衢,尝亲炙余朗山、春台两先生,能文工书。医本家传,因贫行道,著《医法心传》一书,余凤喈为序。授其徒雷逸仙,逸仙子少逸为刊行之……又著有《写忧诗草》及《家训诗》,未梓。[3]”其二,刘国光《医法心传·序》记载:“其尊人逸仙先生,则受学于程芝田先生也。一日,少逸出芝田先生《医法心传》一书,问序于余。且言曰:程先生为新安人……其家世业岐黄,于医理尤精,嘉道间悬壶金衢,着手奏效,衢人有绘杏林春色图赠之者。[2]657”其三,程鉴于《医约·序》序末署“同治贰年孟春吉旦柯城芝田程鉴题于如渔舟书舍”[4]。
据上所述可以综合为:程鉴,字明心,号芝田,歙县人,槐塘程氏主要代表医家之一,名医程正通后人,嘉庆年间秀才,家世业医,曾悬壶于金华、衢州等地。至衢州行医后,收徒雷逸仙,雷逸仙传子雷少逸,雷少逸收程正通之后程曦为徒,并传子雷大震,少逸外孙龚香圃亦承其外祖之遗志,著有《医法心传》1卷、《医约》4卷。
1.2 程鉴著作考
程鉴著有《医约》4卷、《医法心传》1卷。又著有诗集《写忧诗草》和《家训诗》,郑永禧说未刊行,现仅有4首诗存于《医法心传》卷末,另有19首存世,其余诗篇均已亡佚。《医约》和《医法心传》尚存。
1.2.1 《医约》 《医约》原名《医学津梁》,成书于同治二年(1863),由程芝田原著,龚香圃补略,因书名同于明·王肯堂之《医学津梁》,印行时改名《医约》。龚香圃《医约·序》曰:“约之云者,取其精华而去其敷衍之谓也。[5]”程鉴以之授门人雷逸仙,再传雷少逸。龚香圃有志于医,承外祖雷少逸之遗志,对是书朝稽夕考,本其心得,增补按语,辑成是书。据程鉴《医学津梁·序》,知本书原为1卷,龚香圃排印时改1卷为4卷。前3卷列内科证治36门,卷四列妇科证治12门,卷四后附龚氏所撰《死候概要》1卷。综观全书,其所举之证皆为常见之疾,所用之方亦多常用之方。且正文每门先述程芝田原著之言,后由龚香圃加以评按,言简意赅,条理清晰[6]。
1.2.2 《医法心传》 共有医论12篇,全书不及万字,却不但于五行之说颇有创见,而且囊括伤寒、温疫、痢疾、痘科及损伤等病证病机要点和辨治要领。作者学验俱丰又有革新思想,故论述多有新意,强调“医宜通变”,随证处方。又认为诸家之方多为化裁而来,总不出古方范围[7]。郑永禧曾有按语:“芝田,新安名医程正通之后也。寓衢,雷逸仙曾师事之。著《医法心传》一书,旧有余凤喈序,少逸为刊行于世。[8]”
2 学术思想与特色
程鉴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多见于《医法心传》《医约》二书,其推崇张仲景之学,认为张仲景伤寒方论本可统治杂病,其“颠倒五行”的学术观点,结合五行学说来阐释相关理论深刻而全面;其临证之时擅于悉心察病,随证应变,灵活执方,以获良效。
2.1 探本溯源,实证仲景之学
程鉴对张仲景之学研究有素,认为分论《伤寒杂病论》之言有违张仲景原意。故《医法心传·医法长沙》开篇即有云:“仲景先师为医中之圣,其著《伤寒杂病论》,堪为千载之准绳是矣。[2]661”张仲景著书之初,是为伤寒与杂病共同立法,其方本身亦是为伤寒、杂病合论而设。但因原书未传,在历史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以致后人亦分而论之,言《伤寒》治外感,《金匮》疗杂病。程鉴推崇柯韵伯之说,力辟以《伤寒论》为外感病专书之说,从伤寒杂病未尝分书谈起,揭示张仲景伤寒杂病合论之旨,并以临床实际力证张仲景伤寒方论,本可统治杂病。“谓《伤寒论》独治伤寒一病,叔和乱之于前,诸家仍之于后。千百年来,莫能出其窠臼,甚至仲景之方,世不敢用,以为宜古不宜今。各承家技,自立新方,虽有仲景之名,而无仲景之实”[2]661。
2.2 尊古不泥,创新五行之说
程鉴集前人之所学,并以《黄帝内经》《难经》为基础,进一步丰富五行相生相克之说。《医法心传·颠倒五行解》有云:“五行有相生相克……此为顺五行,人所易解,无庸细述,惟颠倒五行生克之理,人所难明。[2]662”一方面阐述当下通行的五行理论,即以木、火、土、金、水之间递相资生又相互克制的关系为主,赞同历代医家皆以此作为运用五行生克关系阐释机体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以及解决临证辨治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借通行理论进行延伸,创造性地提出五行间可能存在着特殊的相克相生规律,即“颠倒相生说”,五脏之间在生理上除有一般次第相生的关系之外,每一个子行亦能对其母行有着反向的滋生作用,母行子行间生理上联系密切,病理上能够互相影响,即“水亦能生金……木亦能生水……火亦能生木……土亦能生火……金亦能生土”[2]662-663。因此,在治疗上除对病变本脏进行处理外,并可通过调整与其有关的母脏或子脏以达愈病。换言之,既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也”,又可“虚则补其子,补子以实母”,如壮水生金、益金扶土等法。就相克而言,五行之间除有历代医家通行观念中一般次序和关系之外,其所言“木亦可克金……土亦可克木……水亦可克土……火亦可克水……金亦可克火”[2]662-663,在阐述生理、分析病理和指导治疗方而作了发挥。
2.3 心如明镜,审察病机之要
《医约·原序》中有云:“古之所谓百艺之中,惟医最难。何为难也?难莫难于辨证用药。[4]”从医之难,莫过于辨证施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程鉴深刻体会到临证辨析准确、因证立法的重要性,指出凡病不拘寒热虚实,病证难免有相似之处;凡药不论寒热温凉,功效亦有相近之品,故而立法处方应心如明镜,盖因“设或投治少差,存亡在于反掌”。历代前贤所著医书包罗万象,其方可治病救命,其法可遵可传,但并非只一方一法。临证之时医者应遵医理悉心察病,坚持从病证出发、随证应变,灵活运用执方投剂以获良效。在《医法心传》和《医约》两书中,程鉴将历代医家的临证辨治思路做了详细分析与解说。如《医法心传·仲景伤寒论可统治男妇小儿杂病说》中,以为女子“其胎前产后,亦不外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之法。《经》云:妇人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六经诸方俱可通用,因症加减,不必拘方,所谓遵张仲景之法,不必执仲景之方是矣”[2]666。此言充分体现其信古而不泥的学术精神。
3 临床经验撷萃
程鉴研习经典,造诣颇深,且临证经验丰富,其强调悉心审辨,药稽本草,验之有得,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探本溯源,揭示张仲景伤寒杂病合论之旨,即张仲景伤寒方论本可统治杂病;集前人之所学,进一步探本溯源、尊古不泥,并以临床实际力证其对伤寒、温疫、痢疾、痘科及损伤等病证的独到见解,在当时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1 巧用升麻、葛根治痘症
关于痘症辨治,程鉴在《医法心传·痘科救偏》中有言:“攻毒而不知补气血,何异揠苗助长?欲希其不槁,未之有也”[2]670,明确指出:“升麻葛根汤,内用升麻,提毒外出,葛根透肌疏表,鼓舞胃气,生津止渴,又恐过开腠理,用白芍理和阴血,用甘草解毒和中。只此四味,气血并治,表里兼调,神妙无比。且云见点后忌用升、葛,恐重伤其表也”[2]670。升麻味辛、甘,性微寒,功能发表透疹、清热解毒、升阳举陷,主治疮痈肿毒、斑疹不透等;葛根味甘、辛、性凉,有解肌退热、透疹、生津止渴、升阳止泻之功,常用于表证发热、麻疹不透、阴虚口渴等证;白芍味苦、酸、性微寒,功能养血调经、敛阴止汗。方中再以性平味甘之甘草清热解毒,调和诸药,可见程鉴用药之慎重。
3.2 善用参芪治虚劳
程鉴治疗虚劳病证时补肾不忘补脾,且尤以补脾为重。如《医约·虚劳门》言:“虚者宜补,补其虚也……若阳不补则气日消,阴气不补则血日耗,古人所以举出脾肾为虚证之本。且肾主蛰藏,水为天之元;脾司仓禀,土为万物之母。孙思邈云‘补脾不如补肾’,许学士云‘补肾不如补脾’,二法皆是。[4]5”《医约》一书中收录治疗虚劳病证之方7首,共用人参、黄芪者有3首。程鉴认为临证辨治虚劳须牢牢把握病机,探求疾病的本源,切不可投以大寒大热之药。盖因大寒则愈虚其中,大热则愈竭其内,故而宜取滋阴降火、消痰和血之法,以参、芪等药澄其源。人参味甘,性微寒,主补五脏;黄芪味甘,性微温,可益正气,壮脾胃。参、芪共用,“故脾土旺而生肺金,金生肾水,二脏安和,而诸症自起矣”[10]。此法与新安医家孙一奎强调脾肾同治虚损有异曲同工之妙。
3.3 悉心审辨治痢疾
历代医家多认为痢疾发病与脾肾二脏有关,程鉴认为痢疾病性包含寒热虚实各方面。《医法心传·痢疾要旨》有云:“故痢未有不因停积而成者,但积有热有寒。热者因受湿热而成,寒者由食生冷而得。[2]668”他将痢疾病因归纳为或受湿热或食生冷等,并指出热者“脐下必热,且拒揉按”,寒者“脐下必寒,且喜揉按”。寒性病证常表现为虚证,热性病证常表现为实证,故医者应辨清证候之寒热虚实而论治。治疗方面,热积当用大黄下之,寒积宜用巴豆霜下之。既有粪下则不用下法,只须调气养血,热者用黄芪芍药汤之类,若兼血虚可与四物汤、六味地黄丸等同用以滋阴养血;寒者用佐关煎之类,若兼气虚可与温胃汤、胃关煎等同用以扶阳益气。古人治痢多以脾肾为主,而程鉴独辟蹊径,重在脾胃二经,谓其“一阴一阳”,并指出“肾命二脏,一水一火。若脾命虚者,是当补阳;胃肾虚者,是当养阴也”[2]669,强调在临证治疗时必须先审查阴脏阳脏,再以症状辨以寒热虚实,其之言丰富了痢疾病证的辨治体系,其所撰《医约》一书设“痢疾”专篇,亦对后世辨治该病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3.4 治瘟疫
明·王履《医经溯洄集·伤寒温病热病说》有云:“伤寒与温病、热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热,固不必求异;其发表之法,断不可不异也。[11]”由明至清,温病、疫病等研究已经能够独立于伤寒研究之外。至清代,叶天士在《温热论》等书中提出了卫气营血4个阶段辨证论治纲领;薛雪《湿热条辨》和吴瑭《温病条辨》则提出了三焦辨证理论[10]。对于温疫的认识,程鉴在诸贤基础上亦有发挥,其在《医法心传·瘟疫原考》中认为,温疫之症不同于伤寒:“温疫之病,从血分传出气分,阳症居多而无阴症,必内溃,然后从里达表,战汗而愈。非同伤寒,从气分传入血分,有寒有热也。[2]668”一方面伤寒病程较为缓慢清晰,多由表入里、从气入血;瘟疫病情较为凶险,有发病迅速、旋即入血之特点;另一方面伤寒由表入里,有寒化、热化之分;温疫感邪多属阳邪,其临床表现亦多阳证而无阴证,二者殊为不同。而治瘟疫之法程鉴认为,“治温疫,得其窍,较治伤寒颇易;若不得其窍,较治伤寒更难。[2]668”鉴于瘟疫之邪,常表现为热胜毒盛之征,他以“存津液”作为治疗要旨,颇有留一分津液,多一分生机之意。故又云:“虽非一端,其要旨在存津液。如初起忌表汗,恐伤津液也。继则清解攻毒,早下之以存津液也。至补阴诸方法,何莫非养其津液哉。盖疫毒煎熬,最伤津液。惟恐津液烧枯,邪毒不能传化而出,至成下闭上脱之危候,则不可救治矣。[2]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