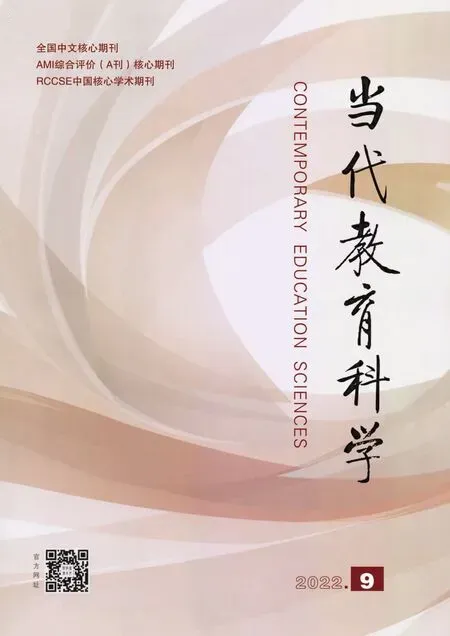儿童数字身体的自由失度与教育重构
●戴唯信
OECD 启动的“21 世纪儿童项目”指出,21 世纪的儿童已然是“数字原住民”,一出生便带有数字化特征。[1]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儿童生存境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儿童在数字世界中的生存以数字身体为基准。从存在的意义上讲,“数字身体”是儿童存在的一个“元素”或者“方式”,用以承载儿童在网络世界中行动的主体性和意志,是儿童数字身份建构的具身化形式。[2]数字身体包含了儿童在数字化生存中作为独立个体与关系性个体的人格、行动与发展动态,蕴含着个体数字身份背后承载的责任与义务。
然而,“数字化全景监狱范式”对人的动态干涉势必使儿童的数字身体失去原本该有的自由。根据以赛亚·伯林的观点,自由是“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儿童以数字身体的数字化生存是儿童在一定范围内免受他人强制的自由。儿童的数字实践品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数字人的实践品性。在不可逆的数字化趋势下,如何构建儿童数字身体的自由体验,是教育有力回应社会与未来的责任担当。
一、儿童数字身体的自由
在数字世界中,“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区别已经完全消失了”,肉身的限制被非远景、不限时空的、无死角的数字监视顶替。[3]在此背景下,儿童数字身体的自由是免于数字化控制的自由。“自由的基本意义是指免于枷锁、囚禁和被别人奴役,为个人自由而奋斗就是力求消除他人的干预、剥削与奴役。”[4]儿童数字身体的自由应当是免于过度干预、过分“保护”的自由。
在个体存在与交往的不同层面,自由有不同的表现。作为独立的主体存在,个体生存自由体现为尊严自由;作为关系性的存在,个体关系自由体现在处理他者与自我中表现出来的选择自由;作为社会主体的存在,其自由的意涵为交往中的社会关系自由。在此基础上,儿童数字身体的自由体现为:儿童数字化生存中的尊严自由不被侵犯、儿童选择自由免于干预,以及儿童虚拟社会关系的平等。
(一)儿童数字化生存尊严自由不被侵犯
尊严是个体对存在状态的肯定,是人应当享有的人格自由和尊重。生命尊严和人格尊严构成了人的自由的基础。[5]儿童数字化生存中的尊严自由体现在将儿童视为生命个体,而不是数字符号;儿童在数字世界中不被轻视、侵犯、侮辱诽谤等。正如康德所言:“尊严并不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目标,而只代表着一种根植于人的自我或个体性的最基本的需求……尊严就是指不被侮辱的权利。”[6]
尊严是儿童在数字境遇中自由生存的保障,对儿童尊严的呵护有助于他们不断探索数字世界中的新境遇与挑战,体验超越肉身限制的优越感与新鲜感,不断激发儿童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实现其作为人的价值与追求。儿童虽然处于不成熟状态,容易犯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人就可以无限干涉、侵犯其人格尊严。作为发展中的个体,儿童在数字化生存中应当享有与成人相同的尊严自由,也应当被尊重为独立的个体,不受成人所创造文化的逻辑和想法牵制,免于成为他人的附属品。尊重儿童不仅表现在对儿童有公正态度,更表现为社会应有信任儿童的态度,相信他们具有自我控制、自由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并积极引导。儿童享有的尊重与尊严,是其在数字化生存中获得存在感与真切感的首要条件,儿童尊严自由不被侵犯为儿童数字身体自由奠基。
(二)儿童数字身份选择自由免于干预
作为关系性的存在,儿童数字身体的自由体现在数字身份选择自由免于强制和奴役。[7]随着自我意识与社会认知的发展,儿童在个体活动中力求实现自我选择的自主权利。数字身份的选择自由能够保证儿童作为独立主体的实现,使其逐渐走向独立,在数字洪流中不随波逐流,达成自我同一性。在网络空间中,儿童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某一种身份或者面目,或者同时“召唤”出多重身份和面目。选择基于认知,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在丰富而不受肉身限制的数字空间里,儿童可以通过数字身份的选择激发其新颖而富有创造力的思维,在不同的挑战中提升社会认知,发现“我”更多的可能性发展。
此外,数字身份多重扮演关涉个体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波斯特认为,数字空间中“参与者—作者”等多重身份切换可以使主体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全新的身份操演,进而加强主体了解不同身份的规范与准则。[8]儿童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对每个数字身份规范与准则的认识与评价,并进行选择。因而,儿童数字身份选择的过程也是塑造价值观的过程。价值观是个体对某事物于人而言所具有的意义的总评价和总认识,它对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行为起着导向和制约作用。[9]儿童数字身份选择的自由是儿童逐步走向自我认同的过程。尤其是在数字化生存中,现实与虚拟的交织,每一个数字身份选择都影响自我认识和自我价值建构。意愿和兴趣的选择能够帮助儿童认识到“我”与他人的区别,认识“我”想要的是什么,从而知道“我”是谁。儿童在享受数字身份选择自由的同时才能主动承担“我”的身份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与规范。
(三)儿童虚拟社会关系的平等
儿童虚拟社会自由体现在与其他儿童、成人平等交往的自由,具体表现为不妨碍他人地位和权利范围内所享有的自由。齐美尔认为,人类具有一种基本的身体驱力,要进行社会交往。融入“与他人之间的结合”,能够使人们获得内在的满足感。[10]儿童在网络的社交互动体现出其具身性主体的社会能力(social capacities),摒弃了功利性与权力分化。由此,儿童能以在这种虚拟关系中获得社会地位的平等,体验“社会最深层的实在的意义与力量”。[11]平等的虚拟社交满足儿童作为数字具身性主体所持有的内驱力,充当着儿童融入社会关系的进入之钥与能力之源。
自由和友谊在印度日耳曼语系(Indogermanistik)中拥有同样的词源,在此意义上,自由是一个表达关系的词汇。[12]没有平等,个人社会自由会异化成“我”的自由,也就是自私。现实生活中,成人权威的施加无形中会使儿童在社会关系中被动屈从于他者,无法享有平等的社会自由。为迎合他人而进行的交往与联系,都不是真正关系上的自由。此外,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也不利于儿童的社会自由。有些儿童随意散漫、为所欲为,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网络上肆意散播对他人不利的谣言;为博取关注,不惜将欺负他人的图片或视频传到网络上博取流量,都不利于儿童虚拟社会关系自由的实现。
当然,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只有物欲和外部规范而没有理性和自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13]儿童享有的自由应当有其限度,明晰自由的底线,在不侵犯他人及群体自由的范围内,实现个体的自由与解放。这样,儿童才能更完整地感受作为数字实践主体的真实存在。
二、儿童数字身体操演的自由失度
儿童的数字身体有能力自由地创造信息、传递信息,进行数字身体的操演。“数字操演性”强调互联网运用技术等手段来促进身份的操演,而这种操演超越了生理肉身的局限。[14]儿童以社会行动者的身份和面目被召唤出来进入公共生活,这样的一种询唤所带出的自我也存在忧患。数字个体的隐蔽性容易使儿童因稚幼而遭到网络暴力,对儿童的人格造成无法磨灭的伤害,导致其尊严自由受到侵犯;数字算法使成人文化极易侵蚀儿童世界,儿童由此失去独立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自我发展的选择自由;数字虚拟化使儿童社会关系变得不真实,为获得他者认同,在交往互动中儿童会自我隐蔽并一味表演自我,最终失去平等的社会自由。
(一)网络暴力侵害儿童的人格尊严
在数字世界中,儿童往往处于预先设定的强迫与枷锁之中。譬如,成人过度规范、限制儿童行为,这实际上是将儿童视为被塑造的作品而非被尊重的独立个体。此外,较成人的权威与权力而言,儿童处于弱势地位,容易陷入被他人轻视、被侮辱、被侵犯的环境中。在公共数字空间中,言论个体的隐蔽性使得恶意肆虐,导致诽谤、侮辱的肆意传播。身置这一处境之中,儿童不堪遭受网络暴力造成心灵创伤甚至做出过激行为的新闻比比皆是:美国13 岁的少女梅根·梅尔(Megan Meier)因不堪忍受网友的恶毒辱骂在家里自杀身亡;[15]巴西互联网督导委员会调查显示每四名巴西儿童和青少年中,就有一人受到网络暴力的困扰。[16]网络暴力无孔不入,正侵蚀着儿童的身心健康。2019 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显示:青少年在上网过程中遇到过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为28.89%。其中,暴力辱骂以“网络嘲笑和讽刺”及“辱骂或者用带有侮辱性的词汇”居多,分别为74.71%和77.01%,其次为“恶意图片或者动态图”(53.87%)和“语言或者文字上的恐吓”(45.49%)。[17]2021 年发布的《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1)》显示:18.7%的小学生和23.6%的初中生在观看视频时曾遇到不良信息的侵害。[18]
网络暴力的背后映衬的是数字个体的隐蔽性,模糊了儿童与成人的界线,诱发儿童遭遇不平等待遇的现象。儿童中间网络谣言的兴起反映出其理性的缺位。此外,儿童容易因迎合大众,盲目与无思地被社交媒体“绑架”,失去作为独立思考个体的权利。儿童有时因稚气、未成熟以及容易犯错而遭遇其他儿童或成人的不屑与调侃甚至欺凌,这悄然侵犯了儿童的尊严自由。在这种“一边倒”的舆论攻击中,儿童若是缺少判断力而盲目跟风,利用片面浅薄的信息在虚拟世界中发泄、施暴,以为能够“安全地”隐藏在屏幕背后肆意妄为,却实则也身陷其中,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为避免恶意的尊严伤害,儿童会通过制造不真实、非本意的假象赢获他人的羡慕与恩宠,通过赢取他人的点赞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从而获取存在感、成就感。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观察别人生活时,很容易得出“别人的生活都比自己好”的错觉,这是典型的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心理:当缺乏客体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往往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价自己。[19]儿童没有充分的客体标准去衡量自身的生活,在跟他人比较产生挫败感后,自我掩饰的假象需要不断地编造与伪装,最终陷入盲目跟风的状态。进言之,由于儿童没有建立正确的价值判断,盲目迎合,最终会陷入失控的境遇,成为社交媒体的傀儡,失去自我存在感与意义感。网络暴力与过载的信息侵蚀着儿童作为数字具身性主体的人格,使儿童无法体验独立个体的尊严感。
(二)数字算法奴役下的身份离身困境
如今,基于精确计算和优化决策的数字算法技术给人们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利用用户的“历史行为数据”来推荐信息产品与匹配度。数字算法一方面服务于数字个体,另一方面也是在控制个体。服务与操纵在同时进行,个体的具身能动性转变为数字算法的能动性和意志。[20]在现实生活中,儿童的思维发展、身份选择基于身体认知,以感知觉以及身体情感作为基础。在数字技术的背景下,儿童数字身份的喜好选择、价值观的树立都被精细的算法“喂养”长大。长此以往,处于认知发展关键期的儿童容易出现社会认知窄化甚至愚化的困境,思维的活力与创造力都消失殆尽。
为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数字算法多匹配消遣、娱乐、搞笑或煽情等信息以刺激他们的感知觉。隐匿在屏幕后的是精神文化的贫瘠与冲突。它就好似一颗“糖衣炮弹”,削弱着个体儿童的社会思考与选择能力。低质量的互联网信息例如标题党、段子、伪科学等,以及大规模生产劣质信息的平台,使儿童的思考能力在不知不觉中被钝化,只在意流量而不在意质量,只在意关注度而不在意价值尺度。在此背景下,数字身份只是“我”作为个体人博取关注的一个手段,而不是达成“我”作为一个公共人实现的社会价值。“我”是谁的问题被“我如何获得更多关注”代替,自我同一性与社会认知对于儿童来说已然不重要。若是长此以往,儿童对自我、对社会失去认同,会产生认知的混乱,在真假交织的数字世界中迷失方向。儿童的主体性被“降维”和“虚置”,成为机器和技术所建构的数据模型进行程式化计算的对象。[21]
数字算法基于儿童浅薄思维而为其提供过多的娱乐消遣信息,不仅禁锢了儿童的社会认知,更是过早地干涉了儿童的价值观发展。网络调查显示,如今“00”“10”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中,主播、网红有54%的支持率。网红的世界传播着一种“只要红就有钱”“勤恳读书工作不如成为网红有关注度”的消极价值观。网红世界中渲染的单一价值观不利于儿童健康价值观的形成。成人在网络倡导的“唯金钱论”误导着儿童实现自我的价值观。又如,当今网络流行一种“丧”文化现象:无使命感、无动力,随波逐流。这种“丧”文化实际上是少数成人在生活遭遇中抒发不满的一种调侃现象。儿童缺少相应的生活经验,容易过早地被这种“丧”文化消耗本该有的童真与热情、活力与生命力。在成人文化中过度“浸泡”的结果是儿童区别于成人的界线逐渐模糊。儿童一味地模仿成人的行为、复制其价值取向容易导致其价值判断与价值秩序的颠覆,无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儿童虚拟自我的表演化与社会关系的脆弱
儿童从与他人建立关系中获得对自我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虚拟空间建立的关系无法为儿童带来安全感时,他们便会陷入对自我的怀疑。
儿童在网络中的身体,完全是用文字、图片建构起来的,可与肉身不存在关联性。因而,虚拟数字身体的自我建构赋予了儿童前所未有的创造度,但由于缺少对自我的全面认知,儿童的虚拟自我容易失真而产生本体性安全危机。吉登斯指出,本体性安全(ontologic security)作为“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是儿童自我认同的重要条件。[22]本体性安全的获得意味着儿童对其所处的环境具有一种自然而恒常的信任与信心,使儿童与社会环境达成和谐一致的安全状态。数字身体的表演性与断裂的不确定性造成儿童对自我的怀疑、对他人评价的过度依赖,无法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儿童若表达出与同龄或所谓大众“主流”言论不符的观点或言行,则常遭到语言攻击甚至侮辱。为建立与他人的联系,儿童会去迎合某种文化模式而进行人格自我塑造,也就是戴上面具的人格表演。儿童隔着屏幕,在社交网络中塑造着希望他人看到的自我,与周围环境的相像使他们不再觉得格格不入、被孤立。这种圈子文化甚至会产生一种强制性力量,成为该群体多数人必须追求的理想化状态。一旦有人明显不符合其基本规范和标准,便容易被划入落伍的异类,儿童便会产生与其他人的疏离感和孤立感,造成自我认同的焦虑。
数字时代中,儿童社会关系的建立主要依托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在这种虚拟时空中,儿童建立的社会关系具有便捷性与脆弱性。这种表演附带的不真实性使社会关系变得脆弱。[23]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下,各种噱头不断、光怪陆离的网络行为层出不穷。当儿童所创造出来的数字身体-身份意识的空间、机会和资源越来越多元化的时候,某些重要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互动联结的排他性作用会呈现弱化。[24]换句话说,数量上增多的社会关系网络扩大了不同类型间关系及互动的作用替换机会,儿童在认识到身份意识存在更多数字来源之后,对亲密关系的承诺和坚持会变得松懈。儿童在社交活动中自由表达自我的想法,但无法完全地信任对方,建立稳固的社会关系。数字世界中的交往常是表层的交往,缺乏深层次交流的条件。作为生长中的个体,儿童需要在理性交往的社会关系中建立联系而获得安全感与自我认同感,从而实现社会关系的平等与自由。
三、儿童数字身体自由的教育重构
身体本身是一种主动赋义的感觉结构,其不仅是外部世界刺激感觉而被动接受的结果。儿童依靠作为意向性的身体知觉来获取身体惯习与意义。同样,数字身体置身于公共的数字空间之中,连接着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粘连着儿童独特的情感发展与生命意义体验。迈克·瑞布把数字公民教育分成尊重(Respect)、教育(Educate)和保护(Protect)三个核心主题。尊重包括数字礼仪和数字法律,教育包括数字素养、数字交流,保护包括数字权利与责任和数字健康等。[25]没有限度的自由会造成强者对弱者的剥削,最终导致社会的混乱。[26]儿童作为发展中的个体,缺少完全的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享有在数字空间中发展的自由。洛克认为,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意志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的理性为基础的。[27]儿童数字身体的自由的限度与其理性的发展、对他人尊重程度、对网络规则的遵守以及承担责任的能力相关。实现儿童数字身体的自由发展在于呵护儿童数字实践理性生成;培养儿童克服算法的具身智慧;唤醒儿童虚拟关系中的责任担当意识。
(一)呵护儿童信息实践理性的生成
信息实践理性避免儿童成为网络暴力的主导者与参与者,在遭遇网络伤害时能够积极寻求帮助。儿童处于情绪化向理性化发展的过渡状态,如何保护儿童在数字空间的实践中不依照情绪,而是根据已经掌握的信息辨别新信息,这是使其成为被尊重的个体、实现其尊严自由的关键。数字化背景下衍生出后真相时代是“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时代。[28]儿童情绪更容易被言论情感激化,只寻找情绪的共鸣,不利于儿童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信息的碎片化使得假新闻、反转新闻、轶事绯闻呈病毒式传播,立场和情绪逐渐取代真相。虽然信息的真相与真实性获取成本高,但我们更应当重视培养儿童学会分析、质疑、理解与接收信息的理性能力,不随波逐流,在信息实践的过程中获得道德感和理性程度的进步,保障儿童的尊严自由。
马克思认为,实践规定着人的自由本质。实践理性使人成为自由的个体。[29]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所谈到的,互联网为个体提供大量信息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教会儿童理解纷繁芜杂的信息,鉴别可靠的来源,质疑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30]如何在大量的信息中去分析问题、有效地交流思想是发展理性的关键。
信息实践理性具有个体与公共两面。其个体性在于立足自我,思考“我”在数字化生存中的价值与尊严为何;其目标在于如何实现自我价值与体现“我”作为独立个体的内在意义。信息实践理性的公共性立足“我与你”,思考“我们如何在一起”,其目标是公共的善与根本性正义,体现人与人之间在数字空间中的道德和情感上的关怀。[31]儿童的信息实践理性在个人理性方面体现在对信息缘由的把握、对信息目的的理解,培养儿童追求真相、追求真理、不断探索的精神。在公共理性方面体现在理解且遵循正当秩序。我们需要保护儿童在发现创造、收集掌握、储存传递各种信息的过程中享有被尊重、被信任的权利,不被过分干预,使儿童在信息实践过程中深化对自身、对他人、对世界的理解,从而彰显自我。
(二)培养儿童克服算法的符号具身智慧
个体的主体心灵和意识驱动行为产生身份行动的意义。正如梅洛·庞蒂所言:“身体用它的各个部分作为关于这个世界的一般符号系统……我们因而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理解它,并发现它的意义。”[32]儿童在数字具身认知过程中通过表达与创造符号意义建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虚拟的数字身体与内在的心灵意识通过符号意义得以联结起来。在数字表达的过程中面临算法的主体性消解语境,但正如约翰·彼得斯所坚信的那样:“一切交谈都是带有信念的行为,其基础是相信将来会出现我们追求的世界。”[33]
符号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意义,因此要注重儿童基于具身体验的具身身份表达与交往,在与他者的交往中勇于表达与创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符号具身”体现出的交往理性是儿童克服数字算法、向主体性复归的本真路径。交往理性能够帮助个体学会理解其所遇到的矛盾、领会交往中的责任与要求。[34]交往理性突出个体身份自由的主体间性。当儿童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意志开始萌发,这种意志与成人意志冲突时,儿童获得自由的意愿也就萌芽了。这种内生性的驱动力才会激发儿童基于自我意识与具身符号表达追求自由的意愿、发展创造自由的能力。在数字时代,儿童容易受到他人的鼓动,看似是自由的个体,但在没有形成完全理性的状态下,儿童容易盲从而被算法和流量迷惑并裹挟。教育对儿童的引导应当使儿童清醒地意识、警惕网络中的价值观陷阱。儿童担任各种数字身份的过程应当是发现自我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通过表达自我,忠于具身自我,主动争取自由、创造自由。在数字算法技术的影响下,儿童主体性被囚禁在狭窄的自我意识内部,完全丧失了对所谓意义与价值的探索。要克服数字奴役,儿童基于符号具身对意义的追寻才是作为人类主体的终极本质。可以说,儿童只有通过符号具身的自我表达与创造,与世界通融,在认同中寻找“我”的意义,才能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
(三)唤醒儿童虚拟关系中的责任意识
正如每个身份背后都有相应的规则条件,儿童数字身体与他人进行社会关系的建立时,也需要遵守与之相对应的规则。虚拟的社会关系中享有的社会自由与平等需要儿童有相应的责任担当。因此,加强儿童权责一致的数字责任意识,是儿童在数字时代享有社会自由的必要条件。儿童自由意味着儿童逐渐从母体和他人的关联中独立出来。然而儿童在独立的过程中,容易因失去与他人关系的联系而缺失安全感、从属感和踏实感。因此,儿童在寻求社会自由的过程中,需要建立新的与作为“前个体存在(pre-individualistic exsitence)”不同的关联,从而获得社会关系中新的安全感。[35]这种新的安全感不在于社交人数的增多,而在于儿童在勇于承担责任中与他人建立深厚的关系。
在数字时代,人们借助移动媒体进行跨时空的社交与信息流通,话语权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儿童能随时随地将在场的信息传递到虚拟空间,延展了现场的时空性。移动媒体可以跨越空间的沟通消解误会、化解冲突,也可能激化矛盾。因此,夯实儿童在虚拟空间交往中的责任担当十分重要。责任意识能够保证每个个体的社会自由。儿童的责任担当体现在互联网中的规则意识培养,这是促进儿童积极交往的基础。遵守规则能使儿童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产生的后果,以对他人产生尊重。遵守规则不是约束、限制儿童的自我表达,相反,鼓励儿童遵从规则、承担责任是对他们的保护。
培养儿童遵守日常纪律的意识与习惯有助于其社会自由的实现。纪律是为了维护正常秩序而要求人们遵守的规则,是儿童学会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36]没有纪律就没有自由,自由因纪律而更加理性、自觉。《说文解字》认为:“律,均布也。”律意味着平等。处于社会化的过程中,儿童学会遵守纪律的过程也是其社会化的过程。儿童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实现社会自由的平等,让儿童从外在的规定走向自我管理。纪律是对集体利益的维护,是对极端个人主义的约束,由此保护每个儿童社会平等的自由。
在服从规则的前提下,成人应当给予儿童更多的信任、认同和尊重。信任是儿童获得自由的条件。儿童在被信任的条件下拥有充足的勇气去坚持自我的观点,通过与他人于信息时空中的交往理性——尊重他人、理解他人,提升自我德性,才能在高尚中成人;在自我反思中提升表达与创造自由的能力;以宽阔的胸襟、不惑的理性、不忧的活力、不惧的勇气,在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实现社会自由的平等。
唯有为自己言论负责、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与他人建立更加真实友好的关系,儿童才能在数字空间中找到自己的真实感与安全感。对于儿童而言,数字身体的自由不再是肆意妄为,而是具体的责任与义务;数字身体再不是随意无序,而是尊重秩序,升华德性。数字身体的自由向度,乃是将权利与责任放至天平的两端衡量后所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