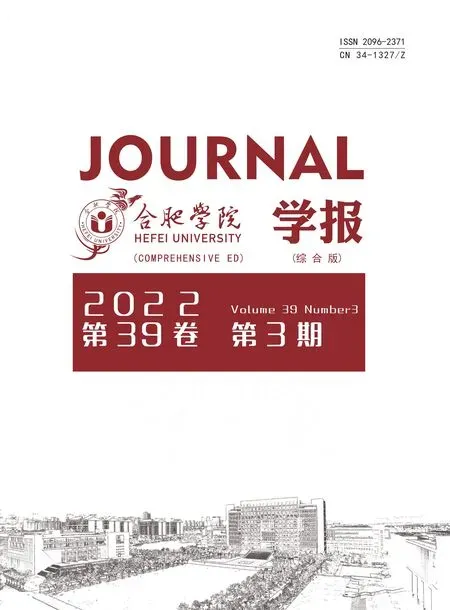从迷茫到顿悟:《无声告白》中内斯的成长突围
李 澜
(阜阳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成长是人类文学永恒的主题。芮渝萍认为,“成长过程指的是青少年在历经一系列生活的磨砺和考验之后,获得了独立应对社会和生活的知识、能力和信心,从而进入人生的新阶段——成年。”[1]3张国龙指出:“成长既表征为生理、心理的日趋成熟,又关涉个性、人格的日臻完善,从而确定自我的社会坐标,实现与社会生活环境的和谐共生。”[2]简言之,成长就是青少年从天真到成熟,在经历很多磨难和痛苦后,努力获得自己的人格和身份的过程。一般而言,成长小说的主题就是探索青少年从少不更事到成熟老练的成长过程,青少年主人公不再通过向社会妥协来寻求主流认可,而是在社会中为成长意识和自我价值努力挣扎和奋斗。
伍绮诗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香港移民家庭,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小时候会因为自己的亚裔身份感受到小伙伴的敌意。“我的家庭就是美籍华人,我们用筷子吃中餐,但我将自己认同为美国人,我接触的绝大多数流行文化元素都是美国的。”[3]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视角下,她创作了《无声告白》一书。这部作品思想内涵深刻,一经出版便得到众多好评。作品讲述了来自跨族裔婚姻家庭的新生代华裔在美国多元化社会中经历了巨大的精神危机,作为“他者”和“边缘人”在社会夹缝中生存,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社会化、族裔化、个体化交织的成长模式,既要反抗社会,也要追求生命价值。文章旨从《无声告白》主人公内斯的成长经历,分析探讨了来自跨族裔家庭的华裔混血子女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走出困顿,寻求自我,最终走向成熟。《无声告白》的成长主题研究不仅能引导新生代华裔美国人对社会、文化进行深刻思考,也能激励其他生活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少数族裔秉承“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原则[4],追寻自我,实现人生价值。伍绮诗通过对主人公成长历程的描述,不仅表达了对美国新生代华裔生存环境的剖析和批判,同时也实现了她对美国华裔文化的建构和参与。
1 成长的焦虑:从家庭禁锢到社会歧视
作品主人公内斯在成长初期,得不到父母关爱和社会认可,有限的社会认知束缚了他的思想,被动地在他人的设定下生活。在经历了一次次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后,因家庭矛盾、文化背景、身份认同受到心理创伤,陷入了焦虑与迷惘。
1.1 矛盾的家庭背景
家庭环境是影响孩子性格形成的源泉,“亲人是儿童成长的第一参照,儿童在亲人身上观察和体会社会的含义”[5]107。生长在跨族裔婚姻家庭,拥有一位不断想要融入主流社会的华裔父亲和一位标榜与众不同的白人母亲,主人公内斯在幼年时期是非常孤独和矛盾的。父亲詹姆斯·李是跟随祖父,以“纸儿子”的身份来到了美国,然而不论詹姆斯如何努力,并且在哈佛大学读了四年本科和三年研究生,他仍然在这个所谓的美国“大熔炉”环境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不愿意和邻居、同事有过多的交流,“只认识几个熟人,没有朋友”[6]46,并且自认为是“瘦骨嶙峋的弃儿,吃剩饭长大,只会背诵课文和考试,还是冒名顶替的骗子”[6]49。詹姆斯经常强迫内斯参与各种体育运动,“硬把他逼成不同的人”[6]90来证明内斯不像自己一样懦弱,借此得到宽慰。青春期通常是一个人关心自己是谁以及要成为谁的时候[7],而原生家庭“是个人安全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自我认知的开始”[8]。青少年在挫折面前容易产生自我怀疑,缺少长者正确的指引,成长途中会碰到很多弯路。成年人的鼓励和开导,是帮助认知能力较弱的儿童、青少年走出迷茫,重拾自信,构建自我价值的指明灯。然而,詹姆斯对内斯并没有正确履行父亲的责任,他在外没有保护内斯的自尊感和自信心,在家没有培养内斯健全的人格,甚至在一次学校体育运动会上,因内斯没有获得奖项,他便觉得儿子就是自己当年的“缩影”,感到“难过和羞愧”[6]152。内斯的母亲玛丽琳是一位独立自主的白人女性。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以及主流对女性的普遍歧视使她一直在追求“生活和自我的标新立异”[6]248,而嫁给这个具有神秘东方色彩的男人詹姆斯就是展示自己最“与众不同”的方式。即便她的母亲非常反对两人的结合,告诉她“想想你将来的孩子们,你们在哪里都不会合群”[6]55。最终玛丽琳因为怀有了内斯,被迫放弃学业,嫁给了詹姆斯,变成最“平庸”的家庭主妇。家庭的禁锢和事业的打击使她将所有的期望寄托在和自己外貌最为相像的女儿莉迪亚身上,而对儿子内斯的优秀却经常视而不见。詹姆斯想融入其中,玛丽莲却不断想脱颖而出,内斯没有得到来自父亲和母亲的正确引导和关爱,在这种矛盾而又孤独的家庭环境下小心翼翼的成长。
1.2 被“边缘化”的社会环境
1958年,盖普洛进行第一次针对跨族裔婚姻态度的民意调查时,仅有4%的人表示支持。直到1967年,马里兰州首先取消《反异族通婚法》,此后的30余年时间里,其余各州才陆续取消该法案。但是,社会对异族通婚的舆论与态度受到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影响,至198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跨族裔婚姻比例才有了较明显的增长。在反映种族问题的小说中,创伤的根源往往来源于对边缘人物的侮辱与排斥,种族歧视的存在严重制约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主人公内斯出生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跨族裔家庭中,尽管他生长在美国,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明显东方人特征的孩子,内斯始终处在文化、身份不确定的状态,在社区生活中得不到尊重和认同。当内斯开始学习游泳时,和同龄小伙伴一起玩耍,因拥有亚洲外貌被所有人嘲笑:“中国佬找不到中国啦!”[6]88从周围人的眼睛中,内斯看到了自己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的亚裔身份符号,这是抹不去的民族痕迹。内斯7岁那年,母亲玛丽琳因无法忍受庸庸碌碌的生活,选择离家出走,追求自我价值。李一家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城镇,偏僻和闭塞使镇上的居民彼此非常了解。母亲玛丽琳的出走,让本就显得“格格不入”的跨族裔家庭成了小镇里被暗中排斥的“他者”和“边缘人”。年幼的内斯承受着与年龄不符的屈辱以及无法和群的挫败感,持续不断的担忧和恐惧加剧了他的心理创伤。
2 成长的觉醒: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
“成长小说中的顿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日常小事中自发产生的感悟,另一种是生活中震撼性事件在主人公的精神上触发的感悟。”[1]149主人公在经历了困惑和迷茫后,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产生顿悟,对自己和事物的本质有了崭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与典型的成长小说一样,《无声告白》同时呈现了主人公内斯自发产生的顿悟和来自震撼事件的顿悟,两种顿悟引导内斯完成认识自我的成长过程。
2.1 自发性顿悟
内斯能够从创伤中恢复,首先源于他自身的努力。作为一名生长在美国的孩子,接受西方文化的多元化教育,并深受西方“自由平等”价值取向的影响,内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个人价值、尊严与差异的重要性。面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压制,他不再像父辈詹姆斯传统性格那样盲从和胆怯,而是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用个人的力量反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迫。内斯的成长展现的实际是中西方教育与文化特征的不同与冲突。“一个人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一切,会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难以摆脱的影响。”[9]对于年幼的内斯来说,在外,他是很难融入社区和学校的“他者”,在家庭中,他是“宠儿”莉迪亚之外的“透明人”。屡次遭受打击之后,内斯意识到,只有抽身逃离这个压抑失衡的家庭,才能拥有完整的人格,以“新的自我开启新的人生”[6]260。内斯从小的梦想便是成为一名宇航员,即使詹姆斯因内斯的“宇航员”之梦感到厌憎,并“用力扇了儿子一巴掌”[6]131,内斯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而大学就是他探索未知地方的跳板,是他飞向太空的中转站。当内斯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哈佛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彷佛得到自由的承诺,满心里都是“我做到了,我要走了!”[6]166
2.2 震撼性顿悟
当玛丽琳离家出走又归来后,莉迪亚逐渐成为全家的中心,父母唯一重视的孩子。作为长子,内斯被玛丽琳和詹姆斯忽视了。当他的母亲问莉迪亚数学问题时,虽然内斯知道答案,但他不允许回答,甚至当他想要一个煮鸡蛋的愿望都会被无视。对于一个孩童来说,这种不公的待遇让内斯对莉迪亚充满了嫉妒。夏天的一个下午,内斯将莉迪亚推入湖中。但他并没有如释重负,反而感到“一阵彻底的分离”[6]150,他意识到自己误解了莉迪亚。她并不愿意吸引父母如此多的关注,占据他们所有的爱,事实上,这种畸形的爱已经成为莉迪亚生活的沉重负担,是一种无声的禁锢。此后,怀有相同秘密的两人成为了对方最依赖的伙伴。但是,莉迪亚最终因为母亲的过度期望、父亲的婚外情、内斯的即将远离以及对杰克错误的迷恋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芮渝萍认为,成长的过程是一个有得有失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得到了知识、伙伴、自我、社会地位和爱,另一方面失去纯真、失去过往、甚至失去亲人。[1]95莉迪亚的突然离世给内斯带来沉重的打击,这是他无法接受却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莉迪亚的死成为内斯成长历程的转折点,他开始思考如何接受自己的双重身份,建构新的自我。
两次顿悟让内斯意识到建立个人人格的重要性,他决定不再逃避,与家庭、父母、社区、以及自己的身份和解,开始崭新的生活。
3 成长的达成:从认识自己到身份重建
3.1 内斯的情感成长
每个青少年的成长都不是独立完成的。在成长的道路上,他们都会有一些人的陪伴,即成长伙伴。他们随着主人公一起长大,一同分享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迷惘、困顿和快乐,倾听主人公的内心并帮助他们做决定,最终见证他们的成长。生长在同一个家庭环境中的妹妹汉娜,与内斯有着同样被“边缘化”的经历,是内斯成长路上的忠实伙伴。当内斯依然沉浸在莉迪亚之死的悲痛中时,是汉娜阻止内斯和其他人无谓的争斗,并且“做好了倾听的准备”[6]119。从汉娜的身上,内斯看到了莉迪亚的影子。汉娜给予了内斯足够的精神慰藉,内斯通过妹妹的帮助,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面临的问题有了全面的认识,并且有了改变的勇气。内斯因为父母的无视而缺乏关心与呵护,因为莉迪亚的死充满愤怒和无助,是汉娜给予了内斯爱和归属感,满足内斯的安全需求,实现了其情感成长。
3.2 内斯的心理成长
成长仪式是个人成长经历的缩影,“这种仪式的意义在于向年轻人预示人生中的种种艰难困苦和考验,经受了考验之后的年轻人被接纳为成人”[1]84。内斯的成熟经历了一个成长仪式,当他充满愤怒去殴打杰克,不小心落入莉迪亚自杀的那个湖中的时候,他从湖底仿佛看到了光明。成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伴随成长启蒙的是失落、挫折、死亡,克服一个个失败就成为青少年主人公在寻求和接纳自我过程中心理上的宝贵经历。内斯对莉迪亚之死进行了反思,预示着他童真的结束,标志了他成熟的开始。内斯的成长结局既愉快又充满希望,他不再冲动,而是回归家庭,通过接受莉迪亚已经去世的事实,接受不完美的父母,接受自己的亚裔身份,与家庭和解。这意味着内斯实现了其心理成长。
3.3 内斯的社会成长
为了生存和发展,个体必须遵守社会法则,适应社会环境,参与社会活动,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是,当社会环境的弊端对个人成长造成不良影响时,个人如何在顺应社会、与他人和谐共处的前提下,充分开发个人潜力,实现自我,是成长过程中尤为重要的难题。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几乎“每个华裔心底里都怀揣着不被人理解、被人排挤的恐惧感,在陌生的土地上找不到自己的归属”[10]。内斯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同学们的嘲讽与捉弄,对白人社区是抗拒的状态,以至于他对唯一向自己示好的同学杰克一直保持敌对的态度。在内斯看来,杰克代表了美国白人社会对自己的排斥与不公平。内斯坚信,是杰克把莉迪亚带到湖边,推入水中,是杰克代表的美国文化造成了莉迪亚的最终死亡。“青少年通常在与他人的互动与冲突中认识自己。”[5]79在与杰克的一次次接触和冲突中,内斯了解了莉迪亚死亡的真相,从7岁时对杰克充满敌意,到最终“拉起杰克的手”[6]286,可以看出内斯已经同美国文化和解。故事结束于内斯踏入哈佛大学的大门之际,他最终用优秀的学习成绩和生活方式完成自己的身份定位,与他的华裔美国根重新联系。从“被当成动物园里的动物”[6]248,到敢于向白人挑战,到最终与社会和解,从弱者到胜者身份的改变,颠覆了华裔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无能平庸、逆来顺受的刻板印象。内斯突破成长围城,为了生命的意义而奋斗,这是一种伴随着自信的成长。正如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这样一层愿望:华裔美国人应学会接受和吸取来自白人社会的正面影响,挑战和抵制负面影响,以获得在美国土地上生活的合法权利,并运用这些影响构建自我价值,以及和谐生活环境的信心。在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内斯与社会达到了平衡,实现其社会成长。
4 结 语
回归后的内斯开始用更加成熟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生存法则,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敞开心扉接受这个多元的世界和不完美的家庭,接受自己的东方特征和双重文化身份。这不仅是作品中人物的成长,也是作者伍绮诗的一种美好愿望——希望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迷茫与顿悟、逃离与成长,为新生代华裔子女面临的困境寻求一条出路。正如《无声告白》鼓励读者:“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不论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内斯,还是作者,亦或是整个美国华裔群体,在迷茫与顿悟之间奋力反抗,都是为了成为优秀、具有个人人格的,顶天立地的人。
——《园丁》阅读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