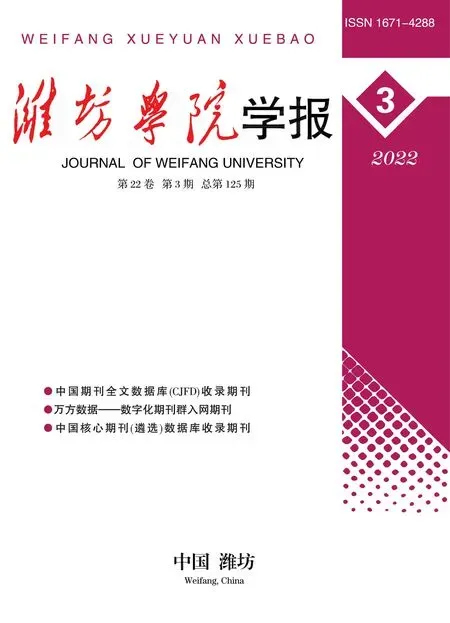莫言小说的“白日梦”创作风格探析
马美琴
(潍坊学院 传媒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近年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莫言的作品做了大量研究。综观评论界对莫言作品的研究,是由表及里、由宏观到微观渐次深入的,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本人通过对莫言作品的仔细研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莫言的很多部小说其实都是以“白日梦”的形式创作而成的,其创作风格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白日梦”文学创作理论非常吻合。
一、弗洛伊德“白日梦”文艺创作理论概述
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文学创作进行了分析。他把作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利用现成的素材进行创作的作家,像古代的史诗作家和悲剧作家”[1](P21),另一类是原创性的作家。他认为原创性作家的富于想像的创造正如“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游戏的继续及替代。因为人们长大以后,停止了游戏,但却难以放弃自己从游戏中得到的快乐,于是用幻想代替了游戏。他们非常认真地创造了一个幻想的世界,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在空中建造城堡,去创造所谓的白日梦”[2](P19),通过这个想象创造出的虚幻世界,使他们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暂时得到虚幻的满足。这种欲望,一般分为进取的和情欲的两种。作家本身既是幻想的制造者,也是幻想的产物,那些小说中的主角就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创作,实际是在叙述自己的白日梦。因此,在小说中通常会有一个卓尔不凡的、永远不会出事的英雄主角,这个英雄正是作者理想中完美自我的化身。而且这个角色常常会对周围的人和事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如同旁观者一样。因为,这些白日梦都是作者被压抑的本能欲望的满足,那些欲望在作者看来是不会被世俗观念所接受的,因而故意让主角表现出置身事外、与己无关的旁观态度。至于这类作家是如何在幻想中进行创作的,弗洛伊德认为“创造性作家由当下的强烈体验唤起了早期的记忆(通常是来自孩童时代),由此产生了一个愿望,并在创作过程中寻求满足”[3](P23)。所以其作品中涵盖了近期诱发事件的各种元素以及作者儿时的回忆。
二、莫言小说的“白日梦”创作特征
(一)莫言小说中塑造的一些令人敬佩的英雄男主角形象,符合“白日梦”作品的创作特征。
弗洛伊德认为,以白日梦形式创作的作品中“大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英雄,作家总是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赢得读者对这个英雄的同情和尊敬,而且总是使他受到特殊的保护”。如果在小说的某一章的结尾,这个英雄身受重伤、流血不止、神志昏迷或生死未卜,那么肯定会在下一章的开头让他得到精心的照料而逐渐康复,或奇迹般地获救。他永远不会出事,具有刀枪不入、英雄不死的特征,每个英雄都是一个唯我独尊的自我,且“小说中的所有女性都会无可救药地爱上那位英雄”[5](P22)。按照弗洛伊德的分析,这个英雄就是作者心目中自己最希望成为的那个人,也即幻想中的完美自我。这个英雄的形象往往是外貌高大英俊、性情刚正勇敢、男性魅力十足的,而且会因为坎坷的经历更加赢得女性的同情和关爱。
莫言多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正是如此。《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尤为典型。他活着时是个勤劳俭朴、乐善好施、心地善良的开明地主。既聪明正直、顽强不屈,又英俊魁梧、仪表堂堂。他历尽劫难而不真死,得以六次转世投胎,虽前五次均为畜牲,但都是同类动物中的杰出者和大英雄。第一次转世为一头世间少有的完美驴子,有力量、有智谋、有勇气,竟能勇敢地战死两只恶狼,被誉为高密名驴;第二次转世为牛,威风凛凛,非同凡响,是一头流芳百世的义牛;第三次转世为猪,风光无限,是一头地位极高的猪王、猪精,因勇救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第四次转世为狗,雄壮有力、聪明勇敢,是高密县城的狗王;第五次转世为一只聪明伶俐、疯狂护主的猴子。总之,作者赋予了主人公有关男人(或雄性动物)的一切优点,并让所有的女人(或同类的雌性动物)都爱他,正如小说中的蓝解放所说:“西门闹这样的男人,是降服女人的魔星”[6](P118)。
《红高粱》中兼土匪头子、抗日英雄、风流情人三重身份于一身的热血男儿余占鳌,是个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硬汉。他做事果断干练、沉着冷静、野性十足,敢爱敢恨、重情重义。是个令人敬佩的英雄豪杰,身上透射着中华民族久被压抑的生命活力。他还是个百战不死、遇险化安的幸运之人。
这些男主角都是阳刚粗犷、正直爱国、敢做敢当、颇受女人爱慕的真正男子汉,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些形象是作者理想中的自我形象,作者把生活中自己难以实现的梦想,通过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加以展现,以获得精神的畅快和虚幻的满足,在虚幻的世界里弥补现实中的缺憾。
(二)莫言小说中超脱现实的梦幻描写,透射出他近乎癫狂的“白日梦”创作状态。
白日梦是指清醒时的脑内所产生的幻想及影像,通常是开心的念头、希望或野心,它是一个人漫无边际的幻想创造、是人在幻想中愿望的满足。它与人们平时的睡梦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人在清醒时候的想入非非,与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以及潜意识里的愿望有很大的关系。它产生的原因往往是个体的受挫,于是企图以虚构的方式应付挫折,获得满足。它的思维是超脱现实、打破时空、不合正常逻辑,幻想出现大量虚构和错构的内容。
莫言的很多小说中都有此类的白日梦描写。《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动辄陷入白日梦的幻想之中:由眼前的地瓜田想象到“这种地瓜是新品种,蔓儿短,结瓜多,面大味道甜,白皮红瓤儿,煮熟了就爆炸”[7](P203),由看到的红萝卜而出现幻觉:“那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8](P229),小黑孩一直生活在极度饥饿孤苦的环境中,无法实现吃饱穿暖、得到温情的愿望,因而红萝卜在他眼中幻化成了象征着光明、美丽、温情、美食等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在白日梦中得到了向往的一切。
《蛙》中那段关于青蛙向姑姑索命的描写也具有鲜明的“白日梦”特征:姑姑万心在退休的那天晚上喝醉了酒,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千万只青蛙的进攻。当时她听到了四周的洼地里传来了此起彼伏的蛙声,“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9](P221)她感到“无数的青蛙跳跃出来,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她团团围住”[10](P222),它们用坚硬的嘴巴啄着她的肌肤,对她发起袭击,直到她挣扎到桥边遇到了捏泥娃娃的艺人郝大手并被其救助为止。这些描写读来非常魔幻恐怖、不真实、不合常理。姑姑之所以在微醉的状态下出现这些幻觉,与她在现实生活中的“受挫”经历有关,体现出她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几近崩溃的恍惚状态。姑姑年轻时是“计划生育”政策最坚决的执行者,曾葬送过2800 多个胎儿的性命。晚年的她为此背负上了极大的心理负担,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因而会被青蛙的鸣叫吓得昏厥。之后她与救命恩人郝大手的相遇、结婚以及一起捏泥娃娃忏悔,正是她的救赎之梦得以实现的途径。
《怀抱鲜花的女人》也采用了超脱现实的梦幻描写,小说中有很多不合逻辑的人物言行描写:女主人公从头至尾都没说过一句话,只是一直保持着迷人的微笑,偶或有惊恐和流泪。无论男主人公——海军上尉王四怎样骂她吓唬她企图甩掉她,她都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追随。不管上尉及其家人怎样苦口婆心地劝她离开,她都毫无反应,只知道永恒地微笑着,如同膏药一样粘着上尉。故事的结尾,她终于排除了所有障碍,如愿以偿地与王四在一起了,两人却没有好好相爱,反是相拥而死。这些描写,都显得不合情理。其实,那个“怀抱鲜花的女人”只是王四幻想出来的一个美丽神秘、乐观温情的影子而已,整个故事就是他的一个“白日梦”。这个“白日梦”体现了王四内心里的欲望和理性、梦想和现实的激烈矛盾冲突,表现了人们想摆脱现实而又无力超脱的生存窘境。
上述这些幻想描写,都具有想象漫无边际、思维超脱现实、内容虚构错构、情节不合逻辑等特点,具有典型的“白日梦”特征,透射出了作者近乎癫狂的“白日梦”创作状态。这种虚构梦的状态,让作者迷醉而快乐、兴奋而满足。正如莫言所谈他创作《酒国》时的感受那样:“当我面对着稿纸时,我就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我的心中充满了儿童的趣味,我疾恶如仇,我胡言乱语,我梦话连篇,我狂欢,我胡闹,我醉了。”[11]而这正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创造性作家的每一件作品就像一个白日梦,是童年游戏的延续,也是童年游戏的替代”[12](P23)的写作状态。
(三)莫言小说中主人公的旁观者状态,契合“白日梦”小说的叙述特点。
弗洛伊德认为在白日梦形式的小说中,主角会像旁观者一样,冷眼观看身边的人遭受痛苦,“自我在其中满足于自己的旁观者角色”[13](P23)。他认为,梦是人们被压抑的欲望通过伪装之后实现的满足,而这些欲望之所以被压抑,是因为它们不能被世俗的伦理道德、审美观念和法律规范等所接受,起码作者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在他们创作的“白日梦”式的小说里,主角常常会像旁观者一样,冷眼旁观身边发生的各种事件,以显示其事件与己无关,来求得心灵上的安宁和慰籍。莫言多部小说中的主角都有该特点。
《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正是一个旁观者的形象,他不管身边的人经历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当他初次被带到滞洪闸工地时,大家都在认真地听公社干部刘副主任慷慨激昂地训话,他却早“提着羊角铁锤,蔫儿古唧地走上滞洪闸”[14](P202),望着水底下的石头,想他的心事去了。周围所有人说的话,他都一句也没听到,也一概不关心;他在工地上砸石子时,身边的女人们都以他为话题议论着人世的艰难,他却一点也听不见,就象入了定一样,导致砸破了手指,鲜血直流;菊子姑娘看他拉风箱又累又热,好心好意拉他再回工地砸石子,他却不知好歹抗拒不回,且狠狠地咬伤了菊子的手腕;他在小石匠和小铁匠打架时拉偏架,帮助经常欺负他的小铁匠,并因此导致菊子姑娘的一只眼睛被石片扎瞎,黑孩却没有对此表现出一点痛苦和歉疚。黑孩这种不可理喻的恩将仇报的行为极为冷酷,因为他整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不在乎身边人的感受。
《生死疲劳》中地主西门闹第六次转世的蓝千岁也是这样的角色。他是整个故事的最主要讲述者,是西门闹魂灵的始终贯穿者、六道轮回的见证者。他是个患有先天血友病的大头儿,动辄出血不止,百药无效,身体瘦小,脑袋奇大,有极强的记忆力和天才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小说第二章的结尾蓝千岁初次出场:“年龄虽小但目光老辣,体不满三尺但语言犹如滔滔江河”[15](P18)。蓝千岁作为故事的主要讲述者,讲述了小说的第一部分“驴折腾”、第三部分“猪撒欢”及第四部分“狗精神”的一部分,他讲的故事很多,大都牵扯到他的西门家族,很多人物都曾是他前世西门闹的妻妾、仆人和子孙,他讲故事的态度是客观冷静的,神情是冷漠的,如同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在记录故事,以超故事叙述者提供故事。他在与蓝解放的谈话中时常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成熟和冷静,如眯缝着眼睛“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在鼻下嗅着,噘着嘴,不言语,仿佛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16](142),俨然是位理性的成年男子。听他客观冷静的语气,好像这些故事都与他以及身边的人无关,比如“如果你对猪的生活不感兴趣,那我就给你讲述狗的生活......接下来的事情,极其纷纭复杂,我只能拣要紧的、热闹的说给你听。”[17](P217)牵扯到他自身的痛苦回忆时,他也很少表现出激动和痛苦。当蓝解放试探地说:“你作为一头驴,被饥民用铁锤砸破脑壳,倒地而死。你的身体,被饥民瓜分而食时”[18](P99),大头儿也没表现出多少悲愤之情,只是用略带着忧伤的腔调说蓝解放猜得很准。大头儿综合运用人和动物的视角,旁观者一般,冷静地讲述了许多生动有趣、离奇曲折的故事,把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丰富、客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三、莫言“白日梦”创作手法的成因探析
莫言多部小说中折射出的他本人影子,揭示了其“白日梦”创作手法的内在动因。他这种创作风格的形成,跟他的生活经历有关。
弗洛伊德说:“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幻想,只有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才会幻想。幻想的动力来源于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实现,是对不满意现实的矫正。”[19](P20)白日梦或幻想产生的根源在于刺激其产生的事件以及勾起的回忆。对现实的不满或对往事的回忆,是白日梦产生的潜在动因。而通过对莫言小说及其人生经历的研究,可以看清其“白日梦”创作手法与其潜意识愿望的关系。莫言少时家贫,生活中多有坎坷,外在形象也不甚完美,心中自然会有一些压抑的、难以实现的愿望和梦想。加之社会现实中所见的诸多生存艰难和无奈,亦会让他产生遗憾和痛苦,于是便以“白日梦”的方式虚构内蕴丰富的文学故事,来塑造完美的个性形象,构建从容自在的生活方式,以满足他潜意识中对理想人格和理想生存状态的追求。
《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忍饥挨饿、极度渴望食物而又沉默倔强的小黑孩身上,明显地透射出童年莫言的影子。莫言在现实生活中有过饥饿的经历,也有过因为长相不佳而被人嘲笑的经历,他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感言里曾说:“我的想象力还是不错的,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童年时赶上自然灾害,为了填肚子,野草、树皮,什么都吃,甚至连煤块都敢啃。”说自己生来相貌丑陋,经常被村里人嘲笑,被学校里的同学欺负。还说《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和感受能力的孩子”是他全部小说的灵魂,后来写的很多人物,没有一个比黑孩更贴近他的灵魂。
《枯河》中那个因惹下滔天大祸被哥哥和父亲轮流毒打的男孩小虎身上,也透着少年莫言的影子。莫言12 岁那年因饥饿偷拔了生产队一根红萝卜,而被押到工地挨批斗,还被父亲用蘸了盐水的鞭子狠狠毒打。
《生死疲劳》中那个辅助蓝千岁讲故事的线索人物“莫言”与作家本人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的出生时间、性格特征、职业特点等都很相近。小说中把少年时期的“莫言”描写为一个相貌奇丑行为古怪、乱编顺口溜骂人、偷看人家婚外情、奇馋无比、令人厌烦的小丑。但同时又写了这个孩子的可贵之处:拥有不凡的才气、出口成章、头脑聪明、勤奋好学、喜欢读报甚至能够背诵。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他表现出了对知识的先天向往。正因为他的刻苦努力,长大后成了一名作家。这些描写都与作家自身的经历有很高的相似度。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莫言只上了五年小学就失学了,但他非常迷恋读书,经常找闲书看,“莫言从小记性好,看书速度很快,一遍看完,书中的人名就能记全,主要情节便能复述,描写爱情的警句甚至能成段背诵”,[20]莫言看了小说或电影,听了说书或故事,都会回家给母亲和奶奶复述,“难免会有忘记的地方,这就需要往下编,他自己变成了编故事的人。”[21]
另外,小说《生死疲劳》中还有对“莫言”这个人物直接评价的一段话:“莫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农民,他身在农村,却想念城市,他出身卑贱,却渴望富贵,他相貌奇丑,却追求美女,他一知半解,却冒充博士,这样的人竟混成了作家。”[22](P323)这个更可以视为作家的自嘲。虽然作者对小说中“莫言”的态度是调侃的、嘲弄的,但在这个以自身为原型创造出的形象身上,却明显地渗透着作家对少年时光的深深追忆和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莫言”这个人物,在《生死疲劳》中起着补充丰富故事情节、讲述故事进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他的存在既是作家的一种新型叙述方式,也是作家对自己少年生活的深情回望。通过这个形象,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作家莫言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
由上述分析发现:从孩童时代到成年后的很长一段人生经历中,作家莫言对他的自身条件及生活状态并不满意,甚至有很多缺憾,却又无力改变、无法摆脱。所以他才经常梦想自己能有理想的外貌、完美的性格、出色的本领、强烈的男性魅力、无忧的生活环境和美满的生存状态。才有了在白日梦的创作状态下诞生的一个个极具阳刚之气的、魅力十足的男性形象,也有了黑孩眼中那个神奇的“透明的红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