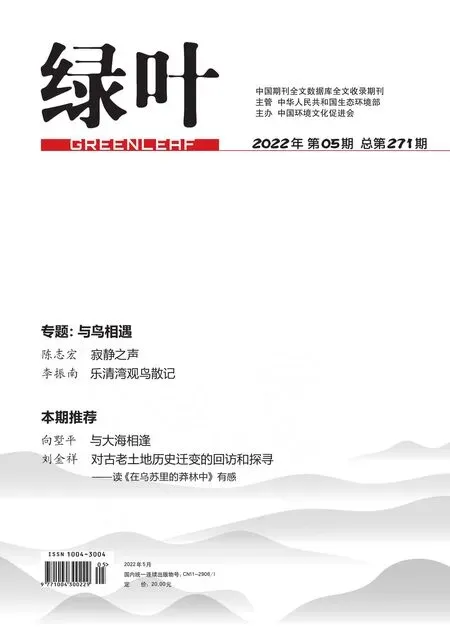那山·那水·那情怀
◎了了
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海洋大于陆地,山地大于平原。
我出生、成长、生活的地方,群山簇拥,处处屏障,犹如如来佛的神掌,山把我的世界围得团团转转。山是那样庞大,人是那样渺小。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即便费尽心思地腾转挪移,也仍然在大山的皱褶里翻滚,难以摆脱大山的庇护与束缚。
1965年,我出生在兰坪一个不太大的小山村,坐落在滇西北那南北纵贯的横断山系的某个山梁上,这里的一座山就绵延几百里,且山高谷深,山势犹如斧砍刀切一般陡峭而险峻。我是山的儿子,在我的生活里,山就是永恒的世界。
俗话说:开门见山。生活在群山的怀抱里,山即是大地的代名词。山不仅是我须臾不能离开的支撑与依托,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世界。是大山养育了我,接纳了我,也包容了我。今天的我虽然生活、工作在县城,但县城仍旧是在山的怀抱里,可以说,我的人生从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包围。大山始终是我成长的摇篮,生活的领地,忙碌的场所,歌唱的舞台。
俗话说得好:土生土长。正如城市里孩子的童年是山里孩子所无法企及的那样,山里孩子所拥有的童年,同样是城里孩子所无法想象的。山能给予每一个孩子的乐趣与记忆是恒久的,难以磨灭的。因为山的世界无穷大、无限量,让人无法知晓的太多,更无法掌握全部。山是最自然的所在,也是最广博的世界。山有生命的四季,时光的轮回,自然的眷顾和生存的加持。
开门就见山,出门就爬坡。作为山里的孩子,可以说,从走出家门那一刻起,人就在山上开始了一天的摸爬滚打,不是奔波在山路上,就是在山上干着各种农活,从小就见识并经受了大山给予人们的出行之艰难。小时候,放牲口、找猪食、砍柴火、耙松毛是最常干的活儿。这些活儿都得到山上、田野里去完成,常常需要走很远的路。而作为农民的孩子,除了日常的活儿,每年的秋收时节,总要跟大人一起到地里收割庄稼,然后把粮食用背篓背回家里。村里的地最远的要数“跃进坝”了,有四五公里远,一个来回就是八九公里的路程,每天从早到晚也只能背三四趟,需要连续几天才能把所有的粮食背回家。身上的负重,路途的遥远,行进的艰难,始终考验着稚嫩的肩膀与心力。小小的年纪,就得承受生活的重压,汗流浃背地负重前行,不断地品尝着汗水的辛咸味道。虽然看着自己的汗水一颗一颗地滴落到脚下的泥土里,但绝不放弃身上的重担,绝不半途而废。我就是在这样生活环境的磨炼下,渐渐养成了一种面对挫折毫不气馁、面对困难坚忍不拔的性格。
常言道:靠山吃山。大山给予人的山珍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山里有各种各样的树、各种各样的花、各种山茅野菜、各种野生食用菌、各种野果,还有各种各样的鸟和各种野生动物。山是无私的,只要你是勤劳的,只要你不怕吃苦,你就会在山里找到无数的珍宝。
山上一年四季都有着各种山珍,在那物资贫乏的年代,山里的孩子总是少不了找野菜的经历。就我而言,大多数是摘蕨菜,也有几次是寻找长在深山里的野菜。蕨菜总是随着夏天的来临,在向阳的山坡上长得密密麻麻,有时随手就能采摘一些;而要找野菜就得起个大早,带上晌午的干粮,爬到高山上有竹林生长的地方才能找到。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吃野菜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像现在,野菜倒成了城里人爱吃的稀有佳肴。
在六七十年代,尚没有禁猎限令,山里的男人们都有过打猎的经历。那是一种充满刺激、挑战和乐趣的行为,也是男子汉勇敢和智慧的象征,许多山里的汉子对打猎都是乐此不疲的。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猎犬的追逐下,在一阵人声的鼎沸中,一只麂子被猎人从山上撵到村子边上的田地里捉住了。人们常说“打到猎物见者有份”,可是一只麂子够几个人分呢?猎人们为了逃开太多的人,就远远地躲到树木繁盛的松坡林里去了。
男孩子们虽然没有机会打猎,但却特别喜欢掏鸟窝。有的鸟把窝搭在树上,有的在石头下面,有的则在草丛当中。掏鸟窝,那是在夏天进行的把戏。还有一种捕猎鸟雀的方法,那是在深秋过后的冬天,每天早晚总有成群的鸟雀集中在烂水塘周围。男孩子们就会采摘一种叫作“旺奈”的果子(至今我都不知道汉语该怎么称呼,实际上那是一种寄生草),然后用石头把它砸碎,去掉果皮,里面的青灰色果泥就会粘连在一起,就像糯米面团一样。然后就把这些像黏胶一样的果泥敷在木棍或者树枝上,在水塘边的树上架好后,就躲在一边观察。当发现吸水的小鸟飞到树枝上被粘住,就飞也似的跑过去爬上树去捉拿。如此这般反复十几次,就可以捕到十多只小鸟,一顿喷香可口的饭菜就有了。
山里人与大山总是结合得那么紧密,人与自然的关联是那么融洽。山里孩子的成长与大山也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人的性格与品行总是在劳动中、在与大山的亲密接触中渐渐形成。人们长期与山为伴,身上也就有了某些山的秉性和自然的属性。山是裸露的,也是坦然的;山是粗犷的,也是朴实的;山是自由的,也是慷慨的;山是放任的,也是无私的;山是危险的,也是豁达的……
同时,山也是冷酷无情的。山重水复不仅隔阻了交通,阻挡了视野,拉远了距离,人也变得那么渺小,常常面对大自然的威力不得不俯首称臣。有道是:山高路自远。山还是最能考验人的意志和体能的所在。当你不得不徒步行走,并需要翻越几座大山才能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便会体会到这山的巍峨庞大。毕竟,用脚丈量大山是一件极其艰苦的事情。在山的世界里,人是如此渺小。有时,山的无情,会让人哭天喊地,或者欲哭无泪。如果村里有老人生病或者什么人受到意外伤害,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送出去医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抱怨路途的遥远,抱怨时间的急迫。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村里的一个同学在回家的路上,被山上的滚石砸碎了脚掌,为了治伤不得不休学从而完全影响了学习,在人生的道路上无异于碰到了一个天大的“拦路虎”,并从此被彻底改变了命运。我想,如果不是这个变故,他也许同我一样,顺利地完成学业,从而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而不是最终只能留在村里,成为像父辈一样辛苦的人。
由此,我曾时常思考我们的先人为什么要选择在深山老林里定居,突然有一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从前人们还处在小农经济社会,那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的世界,人们只要衣食无忧、祖祖辈辈平安健康就行,对于城镇街道的依赖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人们选择的是安居乐业、与世无争的生活,而需要逃避的是战乱、瘟疫等灾祸。所以,我们许多民族的先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山。山是一种艰难的险阻,阻挡了视野,也阻挡了出路,阻挡了梦境的拓展,阻挡了闯荡的雄心。但人们靠山吃山,沉迷在山中的岁月,不思外界的诱惑,恰如《桃花源记》所记载的那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而现在的人,宁可选择在城市里奔波、拼搏,即使陷于困顿、无助的境地,也不愿在经济上贫穷、文化上困乏的大山里栖居。许多地方的年轻人,出去打工,一去就是几年、十几年,有的一去无回。农村里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也许,这只是时代的不同罢了。可是,无论身处什么时代,人生的选择始终是一道让人不易破解的难题。当生活的常规一旦被打破,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阵痛。这是必然的,这同样是时代发展所不可回避的课题。
说起在山里的日子,总会有着无尽的感慨。山是绵延无际的,也是无限包容的。山是沉默无语的,却又是鸟语花香、声色无尽的。山就像一本厚重的书,有时浅显易懂,一目了然;有时又神秘莫测,奥妙无穷。山这本书,对于每一个山里人而言,一旦打开了扉页,就是一本没有结尾、没有尽头、永远读不完的书。毕竟,人们对于大山的认知总是有限的。
有山就有水,水是生命的源泉,自古以来,人类总是逐水草而居。就是在大山里,人们依山而居,也必定要选择一个有水的地方,哪怕只是一小股溪流,然后才能生息、繁衍。坐落在半山阳坡上的故乡始终是珍藏在我心底的那一幅最美的图画。不论我走到哪里,身处何方,总是忘不了故乡的山,忘不了故乡的树,忘不了故乡的人,忘不了故乡的情,忘不了太多的童年往事……忘不了的实在太多太多,但最难忘的还是故乡那永不干涸的山泉。
我的家乡有着两股从山肚子里冒出的山泉水,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其中的一股冬暖夏凉,特别神奇。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而又难忘的童年记忆。
那是一股特别清澈、甘甜如饴的山泉水,汩汩地从山肚子里直往外冒。平时就有小腿般粗的一股,要是到了雨季,就会有人的大腿般粗了。村里人用石块围了三个水塘,最上边的是饮用的,中间的洗菜,最下边的洗衣。说来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股山泉不仅甘甜如饴,从不枯竭,而且还冬暖夏凉,就是在冬天最寒冷的早晨,人们洗衣被照样洗得不亦乐乎,因为越洗就越能感觉这水的温暖,就像是温水一般。而到了炎热的夏天,就算家里的水缸里有水,人们碰到有人刚背水回来,也会在背桶里舀一瓢喝喝。那个清凉甘甜而又解渴的劲儿呀,真真是说不出的爽。
而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股山泉水里还有一种大如米粒的粉红小虾。以前,村里人少不了要找野菜,吃得最多的是蕨菜。蕨菜可以新鲜的时候煮着吃,也可以晒干储存起来以备后用。平时,煮一大锅蕨菜或者干板菜,人们都喜欢拿来在泉水里浸泡一夜,然后再拿回家。如果是夏季,第二天就会发现这些在泉水里浸泡过的菜里夹杂着一些小虾,拾掇出来会有一小饭勺那么多。但也许是小虾的数量太少的缘故吧,村里人从来不打小虾的主意,从来没有人抓这小虾。
村里有这么一股山泉,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惬意的事情。实际上,一年四季来洗衣服的人总是很多,所以,村里的山泉始终很热闹。特别是春节前夕,为了辞旧迎新,家家户户都要进行大扫除,把全家所有的被褥、衣服都要洗个遍才罢休。人们总是习惯把洗好的衣物晾晒在山坡的树木或者草地上。如此,只要有人洗衣服,不出个把小时,山坡就被不同颜色的衣服、被褥所覆盖,花花绿绿的,煞是好看。
在我们丰登片,有四个自然村:上丰登、下丰登、松坪、松木场。在这四个自然村里,我的家乡下丰登是唯一饮用自然的山泉水的村子,其他三个村喝的都是出水量很少的渗水塘里的水,水质不太好。要是遭逢干旱的年份,常常需要排队打水,有时竟然严重到半夜起来排队背水的地步。后来,这三个村就喝从玉龙箐挖过来的水利上引来的水。可是,有一年旱情特别严重,这条水利全干了,这三个村的人们就得到更远的地方去背水。松木场是距离我们村最远的,有六七公里的路程,我的一个堂姐就嫁到那里。干旱这年,她就常常跑回村里来背水,背一趟来回就得跑十二三公里的路程。来的时候是下坡,回的时候就是上坡,那个辛苦就不用说了。
虽然,从村子到山泉的直线距离没有超过200米,可是,由于这山泉的出水口位置太低,在村子的下面,且地势有些坡陡,路线一曲折拐弯就超出了一公里多,背一桶水就成了一件比较吃力的活儿。在农村,每天都要烧水、煮饭、喂猪、喂牲口,这就需要大量的水。所以,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安置一个大水缸或者水槽,并用大木桶来背水,每天起码要背三四趟。背水不仅是一件重活儿,也是一件讲究控制技术的活儿。有一句俗话:满桶不摇半桶摇。村里的孩子到十二三岁开始就要学习背水。可是,对于初学背水的人,桶大了或者水多了就背不动,可水少了又会摇晃得厉害,走起路来细腿杆子直哆嗦。一不小心,从桶里漂摇而泼出的水就会从头上浇下来,把人浑身浇个透湿。为了控制水在桶里晃荡,等背桶里的水打到八成满以后,再折两三根树枝放在上面,这样就能有效地压住水的摇晃。如果再控制好行走的节奏,如此这般,很快就会掌握背水的技术。我十几岁的时候,从头到脚被水泼湿过好多次后,也就在不经意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背水。
包产到户以后,有的人家养起了毛驴,就用塑料桶装水让毛驴来驮。山泉在村子下方,山泉下面就是更陡的悬崖,所以,这山泉除了喝水、洗衣,几乎就没有更大的作用。那么好的泉水,就这么白白地浪费了。
家乡的泉水就在人们的叹息声中淌过山坡,跳下山崖,融入啦井河了。啦井河就在村子下方一两公里的地方,一路携带着来自不同山谷的溪水,继续朝南奔流十多公里后,就被卷进了澜沧江的滚滚激流。不择溪泉,汇聚河流,终成大江。因为啦井河是距离故乡最近的河,也是唯一的河,村里放牧几乎都要到河对面的草山,所以啦井河就成了村里人必经的河流。夏天,村里的牧童就会跳到河里乱游一气,可在这淹不死人的河里,总也练不出什么技巧来,不过是降降暑热罢了。
由于啦井盐矿的存在,这河里也少有什么鱼。不过,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仍然有着捉鱼的经历。记得有一次,村里的大人们带着小孩子去捉鱼。人们先摘来许多核桃叶在大石板上砸出汁液,然后同时弄到河里,不一会儿,就有鱼儿漂了出来,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在河水里捉拿它。一时间,欢声笑语在河汊山谷间阵阵喧哗回荡开来,是那么开心和快乐。那会儿,只有六七岁的我也捉到了两三条鱼。因为专注于捉鱼,而忽略了太阳的毒辣,一个白天下来,瘦瘦的脊梁和小小的胳膊都被晒蜕了一层皮,火辣辣地生疼了好多天……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故乡的山,留下了令我难忘的成长足迹;故乡的水,留下了我许多欢乐的时光;故乡的山水,镌刻着我太多太多无法抹去的记忆。生于山中,长于山中,终生与山水相伴,自己的身上也就有了山的秉性与气质。可以说,山与水,铸就了我柔中带刚的性格,揉捻成了我敦厚深沉的情怀。山是一种厚重的沉积,山是一份憨实的纯朴,山的无言,让人沉静;山的强大,给人力量。山的裸露,使人坦荡;山的给予,让人无私。
而正因为山是我终生的陪伴,山的博大赋予了我人生最深刻的内涵。山里的人生,很早就让我懂得:人生犹如爬山路、攀山峰,时而向上,时而朝下;时而沟坎,时而平坦;时而直线,时而曲折;时而邻渊,时而通幽。但不论路径如何,不论沿途有没有迷人的景色风光,跋涉的脚步始终离不开山的背脊,行走的步伐始终不会那么轻松。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聪明人通达事理,反应敏捷而又思想活跃,性情好动就像水不停地流淌一样;仁厚的人安于义理,仁慈宽容而不易冲动,性情好静就像山一样稳重不迁。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
山为地之胜,雄伟高峻、博大精深、巍然屹立、气势磅礴,无欲则刚;水为地之灵,上善如水,水柔和至极,其性执着,善于默默积蓄力量,水滴石穿,历险致远。兼收并蓄,和谐共生,山与水构成了自然的和谐统一。
山水,是天地的文章,是情怀的放纵。
哦,那山依旧青翠葱茏,那水依然流淌不息,那情怀依然无限缱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