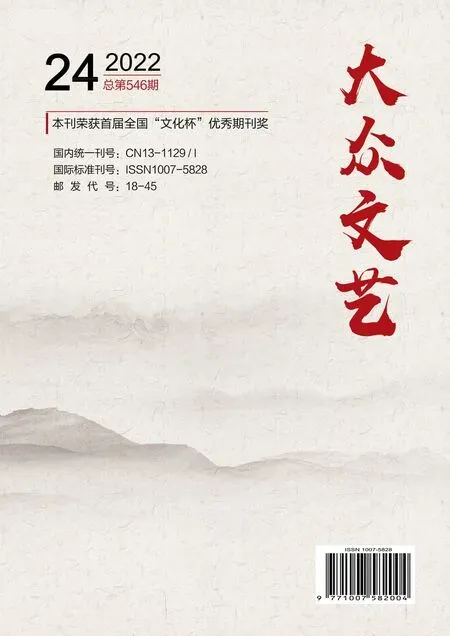《尼亚加拉之行》中的身份协商
汪婧一 贺安芳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宁波 315000)
一、引言
《尼亚加拉之行》写于1828年,正是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美国真正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美国对资金的需求进一步加强,开始实施以发展对外贸易为核心,以聚敛财富为宗旨的经济政策,因此独立战争后联邦政府一直推崇的“重商主义”也在该时期达到顶峰。[1]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城市化进程,随之而来的西进运动引发了美国新一轮的移民热潮。移民带着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来到美国,与当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发生碰撞,再加上重商主义对战前的价值观的冲击,给新生共和国的身份认同带来危机,为各族裔的身份构建也带来困难。
剧中,英国贵族小姐阿米莉亚·温特沃斯和她哥哥在美国旅游期间停留于纽约,阿米莉亚对新世界的一切充满热情,而温特沃斯则很反感。表哥约翰·布尔向阿米莉亚提议假扮法国人、美国佬治疗温特沃斯对美国的“偏见病”。于是一行人沿哈德逊河而上,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在旅行途中遇到了来自爱尔兰的农民丹尼斯·多尔迪,多尔迪的出现给偏执的温特沃斯带来了一些乐子。除了多尔迪,剧中唯一的黑人乔布·杰里森的出现让本就不“和谐”的旅途“雪上加霜”。温特沃斯(英国人)与多尔迪(爱尔兰人)、布尔/法国人、布尔/美国佬,和杰里森(黑人)四类民族人物同时聚集在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的路上。不同文化、宗教、性别和族裔的人物同在一个旅行中,定义了旅行是一次跨文化身份协商的旅程。
二、成功的身份协商
美国学者丁允珠(Ting-Toomey)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提出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身份”意指“每个人从家庭、性别、文化、种族和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反思性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2],因此身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人们在和社会的互动中通过自我认知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过程中,自我评价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因此人们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正如霍米巴巴解释的,“身份不是固定的,是一个永远向着总体性形象不断接近的复杂过程。”[3]身份的首要功能之一在于它对群体内外界线的划定。在研究身份认同时,“我是谁”这一基本问题会伴随着每一个初来乍到的移民在不同的文化碰撞中逐渐得到解答。而“协商”是一个交流互动的过程,处于跨文化情境中的个人试图在该过程中维护、明确、改善、挑战或支持个人和他人的理想形象。[4]因此,“身份协商”,指的是在不同的情景下,对身份进行管理,无论在哪种文化和社会情境下,“人们都渴望得到一个正面的自我身份,更希望得到一个良好的群体身份。”[5]
《尼亚加拉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来自英国贵族温特沃斯和“美国佬”乔纳森之间的矛盾。温特沃斯先生,其妹妹阿米莉亚和表兄布尔都来自英国,但三人对于“新世界”有着迥然不同的态度。在英国强大的绅士文化和森严的等级观念的影响下,温特沃斯认为美国佬的“礼貌”让他被当成猪一般随意对待。习惯了尊卑有序的温特沃斯认为以乔纳森为代表的“美国佬”是没有规矩的野蛮人。温特沃斯对美国人的偏见恰恰反映了当时英国贵族传统文化和美国早期共和时期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不同。
阿米莉亚与温特沃斯恰恰相反,她不故步自封,带着自身文化、族裔和阶层的优越性来到“新世界”。尽管阿米莉亚一时也无法完全接受美国式的礼仪,却选择了入乡随俗,用开放和热情迎接差异,调整自我认知。她善于欣赏并捕捉美国不同于英国的活力,比如美国的自然风光,比如哈德逊河、荒原、田野、森林。与她哥哥欣赏的英国古老的纪念碑、城堡、塔楼不同,她认为新世界里这些待开辟的“景观”最值得来自旧世界游客的注意,并认为如果美国能从欧洲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么成为世界的骄傲指日可待。[6]
文化认同影响着各类移民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选择,指导人们行动,影响人们对他人的期望和行动的预测。阿米莉亚和布尔之所以对纽约之行感到愉快,是因为他们对美国文化具有认同感。这份认同感逐渐影响了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美国文化的温特沃斯。一开始完全抵触美国人的礼仪、否定美国的建筑和自然风光、鄙夷美国的文化到后来认为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看法是有失偏颇的,旅途中“美国佬”乔纳森的出现,推动了温特沃斯的转变。他开始礼貌地对待每一个人,对美国的看法逐渐由坏变好。当看到了壮观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后,温特沃斯终于承认了美国是个光荣而伟大的国家。阿米莉亚、布尔对新世界的包容以及温特沃斯最后的妥协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自己英国人的身份。尽管他们在与美国社会和文化互动的过程中改变了自我认知,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但他们并不是完全彻底地放弃了个人的身份认同,无论是阿米莉亚和温特沃斯都只是“美国的游客”。
三、失败的身份协商
伊利运河的开凿、运河系统的发展推动了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移民的涌入。加之19世纪上半叶30、40年代爱尔兰发生大饥荒,一时间爱尔兰移民大规模涌入美国,掀起一股爱尔兰移民热潮。在爱尔兰移民大规模移入之前,美国人口的主体是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和黑人奴隶,而前者在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爱尔兰人大都是忠诚的天主教徒,与移入国主流的新教格格不入。加之生活习惯、行为举止、肤色貌相的差异,爱尔兰移民的大量涌入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恐慌和排外情绪,他们在新大陆受到大规模的排挤,往往是爱尔兰人搬入哪里,哪里的本地人就都搬走了,爱尔兰移民逐渐成为城市贫民的代表,很多人进了工厂,或修铁路、挖运河等危险的苦力工作,生活水平甚至低于很多南方黑奴。爱尔兰人聚集的地区脏乱差,疾病横行,因此爱尔兰人大多生活在生活的最底层。19世纪30、40年代爱尔兰饥荒的爆发时引发很多爱尔兰人逃荒到美国,而当时跨越大西洋的船只不是蒸汽机船,而是借助风力的帆船,航行时间非常漫长。很多爱尔兰人挤在狭小的船舱里,死亡率非常高。
邓拉普祖上是爱尔兰人,他关注热爱自己的同胞融,其创作的作品中至少有七部作品包含有爱尔兰人,除了《尼亚加拉之行》,还包括《达比归来》《哥伦比亚的荣耀》《波拿巴在英国》《蒙特布兰科的刘易斯;或移居的爱尔兰人》《两个丈夫的妻子》和《美国佬的年表》六部作品。邓拉普笔下的这些爱尔兰人是一群特别不靠谱的人,带着爱尔兰口音,满嘴胡说八道,成为美国民族戏剧形成时期舞台上特别受欢迎的一类角色。通过嘲笑、讽刺爱尔兰移民,邓拉普聚焦爱尔兰新移民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身份协商中所遭遇的困境。
在《尼亚加拉之行》中,邓拉普刻画了一个爱尔兰佃农丹尼斯·多尔迪。他听闻美国土地便宜便想来安家落户,但自从他踏上美国的土地,就过得不顺心。多尔迪在美国的不愉快经历折射了大部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的遭遇:
“我是来这里安家落户的,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因为土地很便宜。我有一些钱,我打算买块地。但我并不想住在教堂的院子里;或者为一小块种植园讨价还价。在我登陆的第一天,我就看到卖棺材的商店。哦,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棺材随时卖给那些刚登陆上岸的人。我想,在我离开爱尔兰之前,我的棺材就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甚至连量尸的仪式都没有。”[7]
多尔迪去教堂的时候又发现教堂的墓地埋的大部分都是爱尔兰人,而且年龄都没有超过30岁。多尔迪的自述带有夸大的描述,但是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爱尔兰移民在移入国不受待见的处境,不仅从事又累又脏报酬又低的工作,还遭受疾病和歧视的困扰,英年早亡。不愉快的身份认同经历加重了多尔迪作为逃亡的失落感,从而促使他在新大陆上寻求与同胞之间的联系。当他发现来自英格兰的温特沃斯与他同样讨厌美国的一切的时候,他犹如找到了救命稻草,多了拒绝融入移入国新身份的理由。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多尔迪的自我认知,多尔迪最终放弃了新身份的协商,选择逃亡英属殖民地加拿大,继续做英王的臣民。
与多尔迪同样经历了失败身份协商的除了多尔迪,还有阿米莉亚的女仆南希。南希迫切希望早点回到英格兰,习惯了主仆关系的南希并不喜欢看到黑人杰里森与她坐着相似的工作,而且一副彬彬有礼的主人样非常难受,“我不喜欢待在仆人们都是黑奴的地方,那会让一个仆人还不如一个黑人。”[8]南希并没有受到新大陆平等朴实之风的影响,而是依旧带着旧大陆贵族社会人分三六九等高低贵贱之分的思维。南希直呼杰里森为“黑鬼”,并在面对杰里森的求婚时感到不适甚至愤怒,觉得辱没了自己的身份。身份认同是社会的产物。一方面社会赋予个体身份的内涵,而另一方面身份认同也需要在交往中逐步建构和完善。贵族社会等级之分赋予南希仆人的角色,而南希也内化了这个认同,她的自我认同并没有因为社会环境文化地域的改变发生动态的建构和完善。
与南希形成对比,杰里森在文化、种族和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反思性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认为谁也不是自己的主人,自己也不附属于谁。杰里森的身份协商反映了黑人群体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时后,依旧努力维持身份独立,并确立自己的社会价值。因为黑人的社会地位卑微,在早期共和时期并没有经常被搬上戏剧舞台,剧中的杰里森是邓拉普塑造的黑人角色唯一现存的例子。在北方自由氛围的影响下,这位黑人绅士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有祖辈族裔类型特征,他说话的样子完全像一个主人的样子。杰里森的出现标志着邓拉普尝试在民族戏剧的舞台上塑造一个受过教育正面的黑人形象,反映了剧作家尊重黑人、反对蓄奴制思想。
四、与美利坚民族的身份协商
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进程。美英第二次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身份认同的关键时期。身份认同既有地理空间认同,也有文化的认同。从地理空间上讲,新共和没有欧洲古老的城堡、宏伟的纪念碑,爬满常青藤的古迹和遗址,但是有广袤的荒野、森林和平原。这些美国独有的地理特征、自然风光已融入了美国人的身份意识。以温特沃斯为代表的“美国的游客”抱怨在美国看不到古老的塔楼废墟和华丽的教堂,看到的只有“繁荣的城镇和欢笑的居民”。[9]随着一行人离尼亚加拉瀑布越来越近,“美国游客”对美利坚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接受度越来越高。
邓拉普在剧中创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来自英国的约翰·布尔。布尔是阿米莉亚的表哥,是阿米莉亚的爱慕者。他比阿米莉亚早几年来到美国,同阿米莉亚一样,对新大陆自然美景、物质繁荣、平等自由报以开放的认可姿态,对当地人的热情和善意都得到充分的回应,让他对这个新国家的喜爱和好感与日俱增。尽管他“并不指望这个国家能像自己的国家一样完美”,他也觉得密西西比河无法和泰晤士河相媲美,尼亚加拉大瀑布也无法和沃克斯豪尔花园的大瀑布相提并论,[10]但是他对新大陆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接受和包容,从游客变成了一个美利坚人。初来乍到美国,再从缅因州到路易斯安那州,布尔随着时间、空间变化不断改变自我认知,协商身份,努力理解、靠近美国人,并以此判断美国和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布尔向阿米莉亚打赌,他一定能治好温特沃斯的“爱找碴的病”。布尔采用乔装打扮的方式先后在剧中扮演了三个角色,除了英格兰人,还有法国人和美国佬乔拉森。布尔游刃有余地在三个角色之间的成功转换不仅创造了温特沃斯认识、了解和接受新共和国身份的机会,治好了他对美国的“偏见病”,同时象征着早期共和时期各种民族人物与美利坚民族认同进行身份协商的丰富过程。
而且,邓拉普让一个对新生美国抱着偏见的游客把“偏见治疗”归功于自己的同胞,有效地阻止了美利坚民族身份在自身构建过程中引发的各种不快,并且为法国人或美国佬民族人物中的不完美提供了借口,因为两者的代表都是英国人。
个体与民族认同的身份协商是一个动态过程,受到时空、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尼亚加拉之行》剧中各类民族人物在与整个美利坚民族身份协商的过程中的成功或失败,顺利或困境都印证了这一点。作为美国民族戏剧形成时期最重要的剧作家,邓拉普的最后一部作品《尼亚加拉之行》揭示了早期共和时期各类族裔人物在认同或抗拒统一的美利坚民族身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