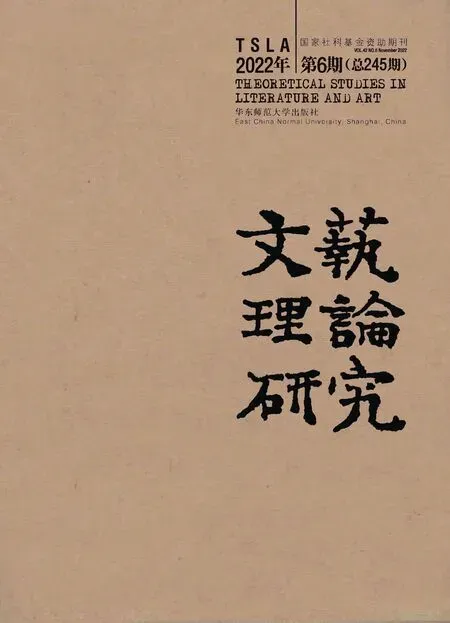论文学在地理学研究中的价值
——以法国地理学家对文学的研究为例
赵 佳
引 言
西方地理学家对文学的广泛关注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零星的地理学家论及过文学与地理学的关系。如1904年,法国现代地理学鼻祖维达尔(Paul Marie Joseph Vidal de La Blache)就研究过《奥德赛》中的地理。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莱特(John Kirtland Wright)指出地理学可以借鉴文学的素材。部分地理学家将文学视为区域地理学研究的补充。但60年代对“科学性”的过度追求使地理学家对文学不置可否,对文学的借鉴相应减少。70年代初,人文地理学开始崛起,与马克思主义批评一起,构成对地理学计量方法的反冲。人文地理学对文学的召唤是出于“现象学的目的,旨在重新将主体、意义和价值这些被弃之一边的概念放回到地理学的中心”(Brosseau18)。此时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更多将文学视为对历史和社会的见证,文学中的地理指涉为某一地区的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文献。必须指出的是,60年代盛行的结构主义方法助推了人们对语言的关注,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获得了格外的关注。
法国地理学家对文学的研究起步比英美晚。将地理学和哲学融合起来的地理学家达尔戴勒(Eric Dardel)在50年代研究过诗歌中的地理情感,区域地理学研究者朱亚尔(Etienne Juillard)分析了司汤达小说中的国土治理问题。70年代,此类研究日益增多,如行为地理学家韩贝尔(Sylvie Rimbert)和巴依(Antoine Bailly)分别探讨过文学中的城市感知问题。80年代初,文学地理学出现蓬勃之势,地理学家对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凡尔纳(Jules Verne)、克拉格(Julien Gracq)等作家的地理书写以及法国乡土文学进行了研究。法国地理学家对文学的关注围绕着“生活空间”(espace vécu)这个概念,即人们“感知或经验到”的空间,关注“人和地点间的心理关系”(Frémont,“Recherche sur l’espace vécu”231)。地理学家更多是从本学科出发,将文学作为印证学科观点的手段;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文学的见证功能是此类研究的出发点。以地理学家为主导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启发了后来以文学研究者为主导的“地理批评”(géocritique)和“地理诗学”(géopoétique)等批评流派。
本文以法国地理学家对文学的研究为例,探讨文学在地理学研究中的价值。首先探讨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地理文献是否可靠,从而分析文学与地理现实之间的多维关系。然后从语言和叙事的角度分析地理学家对文学话语独特性的研究。最后探讨地理话语中的“文学性”以及地理学对自身的反思。
一、文学:一种不可靠的见证?
文学之于地理学研究的价值首先是其见证功能。地理学家什瓦利埃(Michel Chevalier)在《地理学与文学》一文开篇便提到“文学作品的文献价值”。他借用地理学家弗雷蒙(Armand Frémont)之口说: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比地理学家“能更好地唤起人类生活的场景”(Chevalier,“Géographie et littérature”13)。地理学家把文学当作反映地理风貌、记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文献。他们关注文学对一个地区的地理现象、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再现能力。什瓦利埃通过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国乡土文学、城市文学、工人文学和游记,指出文学对地理现实的描写可以为地理学研究提供支撑,比如乔治·桑的小说《笛师》呈现了布瓦肖地区的田地、饮食、服装、农业技术等;法国普罗旺斯地域文学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再现了今日已经消失的风俗;农民文学的代表勒茹瓦(Eugène Le Roy)在其代表作《雅克的起义》中精确再现了19世纪上半叶的农民生活。
然而,地理学家对文学见证的可靠性持保留态度。且不说文学是想象、灵感、情感的产物,而且作家并非专业的地理学家,他们拥有的地理知识有限,“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作家对高山乡村生活的复杂性或对一个大港口的社会和职业结构缺乏清晰的认识”(Chevalier,“Géographie et littérature”14)。此外,还存在置换、篡改、故弄玄虚等常见的文学手法。比如《红与黑》中的佛朗克-孔岱地区其实是以司汤达的故乡多菲内为原型的。以巴尔扎克和左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作家,即便他们标榜自己在写作之前查阅了大量资料,他们对资料的掌握程度也并不完全可信。比如左拉因其记者的职业特点,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显示出仓促、浅显的特征。一战以后乡土文学的史料价值日趋降低,小说家们并不关心现代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更多通过描写乡村表达怀旧之情。城市文学和工人文学的见证价值也是有限的,因为大多数工人文学的作家并非无产阶级出身,他们体现的是精英的视角,他们所描写的无产阶级或者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或者单纯强调其悲惨的一面。两次世界大战中涌现的大量无产阶级作家,他们受教育程度有限,作品文学价值不高,“在民粹主义文学和体力劳动者稚嫩的自传叙事中,地域的特色和城市的特性被抹去了”(Chevalier,“Géographie et littérature”51)。因此,此类文学并不能真正揭示一个地方的社会结构。什瓦利埃总结道:“求助于文学作品总是棘手的,需要对见证进行小心翼翼的批判。”(Chevalier,“Géographie et littérature”15)
什瓦利埃虽然对文学的忠实再现有所怀疑,但他仍肯定了文学的价值。他认为真正的地理学必然是区域地理学,而文学在“一个地区或一个省份形象的形成[……],地域意识的产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Chevalier,“Géographie et littérature”11)。几年后,布洛索重拾这一话题,也认同作家忠实再现一个地区的能力应被置换为他是否能“把握住一个地区的‘个性’”(Brosseau29)的能力:他是否能对所呈现的地方和人们的生活有一个统合的视角,并能穿透表象,深入机理,描述不可见的结构。因此,文学之于地理学研究的第二个价值便是把握和揭示一个地方的个性和深层结构的能力。福楼拜擅长用寥寥几笔,简洁准确地展现诺曼底地区的地理面貌。但福楼拜的价值不只是对诺曼底地区的地理学描写,他“揭示了任何剖面图都不能复原的东西:人、社会关系、在这个小小的地区中整个的社会”(Frémont,“Flaubert géographe”58);“福楼拜向他所熟知的地区投向锐利的目光,他把握住了该地区的基本结构,该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63)。福楼拜准确呈现了诺曼底地区的经济结构和收入来源,揭示了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渔民各自的特点:小城市资产阶级故步自封,在工商业方面缺乏创新精神;农民阶层和土地所有者一样爱好享受,缺乏投资的动力;渔民虽然更有进取之心,但年轻一代选择远离故土,奔赴工业发达之地谋生。通过对这三个阶层的分析,福楼拜敏锐地抓住了诺曼底地区衰败的趋向。虽然这样一种社会地理学的见证是通过文中人物的主观视角,但并没有减弱福楼拜对该地区社会关系特点的全局把握。弗雷蒙认为,任何地理学家的分析都无法和福楼拜的叙事比肩。文学能在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中把握社会和文化的机制,在此意义上,“对文学素材的应用能够带来真正的人文深度”(Chevalier,“Géographie et littérature”63)。
文学不能仅对现实进行呈现和分析,它还应当具有批判现实的能力。布洛索在论及地理学对文学的应用时,专门提到了“批判现实和主流意识形态”(Brosseau42)“与‘既定现实的垄断’形成对立”(43)的功能。60年代开始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关注社会不平等现象,地理学赋予自身新的使命:地理学“不仅要描述和解释世界,厘清社会和空间的关系,也要对现状进行批评”(42)。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利用文学反对社会弊病,追求社会公正,他们对文学的研究体现了女性主义、地域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生态主义等的诉求。因此,文学之于地理学的第三个价值是其社会批判的功能。例如,地理学家贝达尔(Mario Bédard)以科幻小说为例,指出文学和人文地理学共同的价值追求。科幻小说描述人类借助科学实现的扩张野心,部分小说揭露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类扩张的失控所导致的末世危机。它们“共同揭露了对科学的无序利用,超速发展形成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层面的霸权,人们对时间的理解被破坏,对空间徒劳的纯粹象征性的占领,一切都导向人群的异化”(Bédard31)。科幻小说从现象学和东方哲学中获取灵感,致力于恢复对周期性时间的感知,强调多元文化以及人和自然间的和谐共处。科幻小说可以帮助建立一种新的地理学实践,恢复地理学对未知的预见和对思想的敏感。文学在此视角下是人文地理学展示自己价值宣言的一种工具。
无论是对地域个性的把握还是对现实的批判功能,文学始终被视为对现实世界的反射。有些地理学家认识到,文学不仅反映物质性的世界,它还可以通过高度象征性的符号反映人类的精神结构,并通过分析精神结构,揭示人和环境的关系。文化地理学家克拉瓦勒说:“文学最充分地揭示了书面文化中对世界的呈现的复杂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对文学素材的运用[对地理学来说]是最具有前景的。”(Claval,“La géogrpahie et les chronotopes”121)也就是说,文学的最大功能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通过呈现现实,揭示“呈现”作为一种精神结构的复杂性。行为地理学家韩贝尔也认为,地理学家“不能局限于自然主义的描写视角中,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人,他就需要通过投射在社会空间中的精神结构”(Rimbert69)。文学是社会空间中的精神产物之一种,这种以形象化的表达为特征的精神产物又高度凝缩了某种文化中普遍的精神结构。比如,“新小说”派作家格里耶(Alain Robbes-Grillet)笔下城市的迷宫形象既符合心理学上的某些普遍原型(如母亲子宫的形象),又反映了现代城市中个体特有的迷失感。迷宫形象是一种主观感受,但它比任何一种客观描述都更有力地揭示出现代城市的特点。巴依说:“主体所偏爱的最具有唤起作用和最令人安心的符号[……]能够让我们抓住城市环境的特点。”(Bailly13-14)地理学家充分认识到想象不是局限,在想象和梦幻中深层的心理结构才会浮现,借由这些象征符号,我们才能更有效地理解人和环境的关系。因而,文学之于地理学的另一个功能便是探查一个环境中人的精神结构,进而揭示这个环境的特点。
地理学家从最初研究文学作品的现实主义意义过渡到对主体的感知的关注。后起的“地理批评”学派承继了对文学和现实关系的思考,并进一步提出文学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性。“地理批评”学派创始人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提出,“地理批评”要回答的问题是:“被文学再现的空间是否脱离了外部世界[……]还是与其进行互动?”(Westphal,Lagéocritique,réel,fiction,espace162)他认为,文学不是单纯的再现,外部世界和文学空间具有复杂的关系,甚至互相生成。文学通过对现实空间进行观念和逻辑上的重构,将外部世界从混沌的状态中拉出来,给予其形貌,挖掘其可能性。“文学将[人类空间]引入互文性的网络中,给予其一个本质性的想象的维度。”(Westphal,“Pour une approche géocritique”21)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转换,不是文学因为重现现实而获得现实主义的品格,相反,是现实因为文学而获得想象的维度。作家通过虚构改变人们对一个现实空间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描写重塑了被命名的地点”(Roudaut57)。文学对地理学而言不再仅只是具有回顾性质的见证或对现状的揭示,文学对空间具有“创建性”(Collot29)。文学不再只是被动地再现现实中的地理,虚构和现实之间具有双向的互动关系。
二、对文学话语的研究:文学话语的地理特性
布洛索认为,将文学视为单纯的文献,这种工具论导致了“语言可能的媒介作用和它的抵抗被遗忘”(Brosseau36),文学独立于外部指涉的内在话语没有得到地理学的充分关注,文学的空间叙事研究似乎更多是文学研究者的任务。但地理学家们也并非完全忽略文学话语,部分地理学家以及后来的“地理诗学”派研究者关注地理空间如何塑造文学的叙事和语言,即文学叙事和语言如何获得地理特性。
文学叙事可以和所呈现的地理互为镜像,尤其体现在文本的结构上。布洛索在研究美国作家多·帕索(John Dos Passos)的《中转曼哈顿》时,揭示了“话语的形态和城市再现之间的关系”(Brosseau131)。小说分为三个均等的部分,每个部分内部又分为五个部分。小说采用了蒙太奇的手法,将断裂的时空并置在一起,不同的场景依次呈现,展现了纽约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帕索善用省略的手法,在时间中制造空白,读者需要通过反复阅读才能将时间线拼凑出来。作家希望通过断片式的叙事反映城市生活断裂的特性。地理空间不只是叙事发生的背景,叙事从形式上“再现”了与其对应的现实空间的结构。断裂的空间因为人物的移动互相产生联系,人物在大都市中的相遇、在不同空间中的穿梭、在同一空间中的反复出现让不同的故事线得以交叉。人物如同一个功能性的叙事因子,串联起不同时空,将无序的断裂整合为有节奏感的流动,纽约的整体形象通过一系列断裂的个人命运被唤起。布洛索试图通过文学自身的多维话语来揭示帕索小说中的纽约形象,而这正是其他文献所不能替代文学的地方——“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形式内部表现偶然和非因果关系的能力”(147)。除文本结构外,叙事视角也可以体现某种地理性。布洛索在分析法国作家克拉格(Julien Gracq)的作品时,援引克拉格本人的话:“思想更多是可以被模仿,而不是被表达的东西。”(Gracq,180—181)他以克拉格作品中“无人称”的叙事视角为例,指出人和地理的融合这一生态地理思想在克拉格的小说中不是通过逻辑语言被表述的,而是浸润在叙事视角中。小说在描写风景时,虽然从人物的眼睛看出,但却用了一种“无人称”的视角,说明主观性消融在环境中,个体的视角被风景自我的铺展代替。
文学语言也可以和地理呈现相同的形态。语言本身就具有空间性。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所指依照其在系统中的位置、与其他所指的差别和关系而获得自身的意义。“结构”“系统”“竖轴”“横轴”这些概念将语言系统类比为空间系统,体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空间性的意识,索绪尔及其后继者强调了语言所特有的空间性的存在方式。书写语言在空间的铺陈形式强化了语言的空间特性,热奈特认为“书写的这种明显的空间性可被视为语言深层空间性的象征”(Genette45)。今日的文学主要是书面文学,因而文学的空间性大部分建立在书面语言铺陈的形式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尤其是马拉美、阿波利奈尔等法国诗人在诗歌视觉形式上的探索挖掘了文学的图像潜力,他们使我们更加关注“在我们所说的文本的同时性中符号、词、句子和话语的非时间性和可逆的编排”(Genette45)。
地理学家和后来的“地理诗学”派研究者秉承了语言具有空间特性这一想法,分别从语言的节奏和形态、地理词汇和地图的运用、修辞手法、诗歌对抽象空间的建构等多方面深入分析了文学语言的地理性。
首先,语言的节奏和形态可以模拟自然的节奏和形态。“地理诗学”的创始人、法语诗人怀特在论及辛格利亚(Charles-Albert Cingria)的诗歌时指出,辛格利亚的诗歌具有土地的节奏,我们能够听到潺潺溪流在石间流动的声音,或是秋叶在风中飘落发出的音乐般的律动(Collot119)。法语诗人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在谈到安的列斯地区的诗歌传统时,也指出热带地区单一的季节如何赋予当地的诗歌单一的节奏,如丧歌一般单调而尖锐的吟唱“建立了一种新的表达结构”(Glissant344)。布洛索依然以克拉格为例,说明有些思想不易通过语义表述,但可以借助语言的形态模拟。比如,“短”(bref)这个词既在语义上表示短,又通过词形的短直观地揭示了短的含义。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解释语言形态对地理的模仿。如克拉格惯用长句,但又在不经意处对句式进行中断,有如克拉格小说中常有的山的意象,绵延曲折、突兀嶙峋。
其次,在词汇运用层面,一个受过地理学训练的作家不自觉地会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地理学词汇。比如克拉格在大学期间学的是地理学,经典地理学对优美文风的追求在克拉格身上打下了烙印。他的小说语言是优美的文学语言和训练有素的地理学专业语言的结合。地理学家提斯耶(Jean-Louis Tissier)在多篇文章中研究了克拉格的地理文风,指出他如何熟练运用“沙丘地带”“冰原石山”等地形学专业词汇。而且,克拉格会在作品中频繁提及地图。比如他的人物在观察风景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注意到风景和风景之间的边界,以及每片风景的特殊属性。他们尤其偏爱地图,时常在地图中定位他们在现实中观测到的风景的界限。这些无疑是作家的地理学专业训练在创作中打下的烙印。
再次,修辞手法也可被视为对地理的模拟。热奈特早在1969年便指出修辞手法的空间特性:“表达并不总是单义的,它不停地在分裂,比如一个词可以同时有两个意思,修辞学把一个称为本义,一个称为转义,在表面意义和真实意义之间挖掘出语义空间,一下子取消了线性话语。”(Genette47)修辞学中的“转喻辞格”(trope)(如隐喻、提喻、寓言、象征等)最能体现这种语义空间的延展性,它在字词的表面意义之外建立了另一个意义,当真实意义和表面意义之间的距离越远,语义空间就越广阔。不光是转喻辞格,任何修辞在热奈特看来都包含了意义的分裂,只要有风格存在,就有意义的分层,哪怕是表面上最透明的字词,在文学语境中也可以是多义的。随后,地理学家们对修辞的空间特性进行了细化。比如布洛索指出《中转曼哈顿》中运用的修辞手法可以对应于人物的空间实践:转移法(paratopisme)对应于步行路线的突然变化,省略连词(asyndete)对应于路线的不连贯,多义的手法对应于路径的分杈。“地理诗学”的代表人怀特的诗歌中运用了大量的列举和首语重复法(anaphore),罗列自然的物象,形成句式上的反复,以此形成视觉和语义层面的空间感。
最后,诗歌语言的地理特性还体现在诗歌语言如何在抽象意义上拓展了世界的疆域。“地理诗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德吉(Michel Deguy)在《世界的终结》一书中认为诗歌与生态主义具有相同的旨归。生态主义不是单纯的保护环境,它旨在将人类从即刻的环境中脱离出来,在此时此地之外找到人类赖以诗意栖居的彼处。诗歌的意义正是在于收集大地之美,它具有土地的属性,强调物质性、身体性和形象化,通过类比的思维,在物和物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形成一种空间结构。这种强调此时此地的物质性的空间结构具有无限的延展功能,人类能够在诗歌中打开存在的向度,向永恒敞开。诗歌语言和地理的同构体现了人类希望赋予地理空间以超越的意义,以及在美学中建构人类的居所的愿望。诗意的栖居之地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也是语言所创造的多维度的存在空间。
文本和地理的同构既体现在文本中,也被阅读行为所建构。不光是叙事和语言,阅读行为也时常被类比为地理实践。布洛索指出,阅读时目光在纸面上的移动类似于人物在城市空间中的移动,尤其是像《曼哈顿中转》这样断裂的文本需要读者反复阅读,才能拼凑出整本书的全貌,正如城市空间实践者需要通过不断的漫游,穿梭于城市大街小巷,才能获得城市的全貌。阅读与地理实践间的镜像关系得到“地理诗学”派的弘扬,怀特在对汉学家谢阁兰的解读中说:“首先,要快速阅读文本;其次,认真地读,包括脚注;再次,只读脚注;最后,再通读一遍全文。阅读的四个步骤使我们能够通向书的中心,我们就能在精神上完成一次中国之旅。”(White,Segalen.7)怀特将阅读比作精神上的旅行,这并不是一个俗套的比喻,而是指出了阅读和漫游两者切实的相似性。反复阅读以求不断逼近文本中心的行为很像怀特所倡导的流浪式的地理实践,通过反复漫游某地来体悟该地的特性。流浪式的阅读用不同的方法反复阅读一个文本,将阅读行为视为动态探索的过程,强调移动性和开放性。“居住于一个文本中,就是不断穿梭其间,沉浸于一个由于阐释而不断发生变化的符号空间中。”(Bouvet135)伴随阅读而产生的阐释行为是对文本意义的不断重组,正如在每一次漫游中人们都能发现熟悉之地的不同面貌。
三、地理学的“文学性”及地理学的自我反思
1872年到1939年是法国地理学的“诞生时期”和“直觉时期”(梅尼埃1),地理学家在维达尔的带领下,专注于区域研究,研究地域的个性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注重自然和人文的联系。提斯耶提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地理学“被打上了经典人文科学的烙印”(Tissier56)。经典地理学和文学之间是相容的,它们都注重具象的事物,并试图拥有一个综合的视野。彼时的地理学家以拥有优美的文风和细致的描写能力为荣。“地理学家是一个拥有众多能力和独特好奇心的人文学者。他将他的方法用于观察这个世界。他是实战者而非空想家。他的文化和经典文化互相渗透。地理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互相影响,甚至地形学家都很难拒绝美学的召唤。”(Tissier59)
50年代开始,地理学家们对传统地理学的方法感到不满,认为它是一门解释性的学科,未形成通则性的法则,缺乏预测能力,无法适应新的需求。二战后,控制机械学、计算机和遥感探测技术的发展,统计和数学工具的应用以及逻辑新实证主义的出现使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现代化。新地理学派认为“好的统计方法和练达的数据处理足以解决任何问题”(克拉瓦尔166)。
60年代,出于对城市不平等和日益凸显的生态问题的认识,地理学家们开始意识到新地理学缺乏社会内涵。马克思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在英美获得了发展,“意义开始被认为如同解释及因果机制一样重要的一个面向”(克拉瓦尔168),人本主义革命虽然未在法国如火如荼地发生,但法国地理学家从未放弃对意义问题的追寻,社会和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注重文化的取向,生活空间地理学注重知觉的研究。地理学再次诉诸文学传统,反对系统的思想,强调感知的重要性;借助于现象学,倡导想象力和隐喻在地理研究中的作用。通过文学,“想象能够成为地理学的新方法,使之从日常生活中汲取更多养分”(Bédard26)。法国地理学家将目光投向自身的语言,探讨地理学的“文学性”,并借此对地理学科的发展进行反思。文学不再是被动的研究客体,而是用自己的话语积极作用于其他学科。
地理学的“文学性”首先体现在文学手法在地理描述中的运用,我们以描写和隐喻为例。法国著名地理学家斯庸(Jules Sion)对其老师维达尔的语言进行分析,维达尔对一个地方的描写穿透表象,“让人感受到这个地方深层的生命,以及塑造这个地方形貌的力量”(Sion480)。他的论述兼具科学性和文学色彩。当他描写风景时,并非精确细致地描述其形貌,而是具有“唤起”的功能,即风景的描述能够激发读者的感受。他对风景的描写更多诉诸想象和回忆,而非理性。在作者看来,只有通过无意识的力量,才能抵达一个地方真实的情感。我们可以想象维达尔在法国乡间孤身漫步,沉浸于风景中,感受一个地方独特的个性,在漫游神思中把握这个地方的灵魂,并将直觉与感受诉诸笔端。而这不正是文学写作的经历吗?就语言风格而言,维达尔力图在科学和文学之间找到平衡。他的风景描写简短、朴素,很少使用形容词或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用语,使描写有机融入于整体的学术语言中。同时,他也小心回避过于学术化的语言或是地理学的专用词汇,以免出现风格上的断裂。他的句子具有音乐性和节奏感,比如:“从熠熠发光的草原到绿荫丛丛的穹丘,绿色交响曲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直延伸到蓝灰色的天空中。风景所散发出的深沉的魅力无法掩盖土地天然的贫瘠。”(Sion486)在这个例子中,具有诗意的语言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风景地理特性的分析。斯庸说:“维达尔的艺术是古典的,有着思想和表达惯有的精确和节制,以及对法式风景的热爱,目光足以把握这些清晰和谐的线条。我们很乐意称之为雅典式风格,因为它清晰和神经质般的简洁,相较于华丽,更偏爱贵族式的利落。”(487)
除描写外,隐喻在地理学中也有重要作用:“隐喻能够为还未成型的思想提供素材,使思想在观察、实验和阐释中穿梭,如此,学者可以表达他的直觉,迈出对所研究对象进行可能的重新概念化的第一步。[……]思想通过隐喻建立,把科学和诗歌创作联系在一起。”(Berdoulay,“La métaphore organiciste”577-578)地理学中的常用隐喻之一是“有机论”,即把地理现象类比为生物机体,有机论在19世纪地理学中占有主导地位。有机隐喻将地理现象视为业已形成的整体,地理学家用分解生物体的方式分解地理整体,比如将社群这个最小单位比作细胞,将整个地表比作生物体,每个地理层级内部遵循生物体的组织原则。有机体正常运行的标准之一是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和谐。同样,地理学有机体的正常运行标准是人和环境之间的融洽。“没有与土地有根一般的联系,就没有健康的地理机体。”(Bachimon88)地理学家白什蒙以此为依据,指责资本主义发轫时期工人背井离乡,与土地失去联系,处于失根状态。有机隐喻的引入体现了地理学的人文关怀和地理学家们对社会机制失衡的敏感。有机隐喻体现了“科学和意义问题结合的愿望”(582),它是生态主义的萌芽,因为人和其他单位一样被视为地理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组织、和谐、整体、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则。白什蒙引用作家罗曼·罗兰的话,认为有机隐喻使地理学甚至成为一首“泛神论诗歌”(Bachimon585),整个地球如上帝一般成为整体,所有存在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并和整体融为一体。通过有机隐喻的例子,我们看到文学思维使地理学成为一门将直觉和逻辑结合的科学,甚至具备了哲学的高度。正如地理学家达德尔认为的那样,哲学和现象学能够给予地理学高度,地理学同样可以思考:“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如何达成给予他们存在的意义?”(克拉瓦尔217)
法国当代地理学面临的另一问题是与大众的脱离。在历史学科中,学院派历史学和科普历史之间并未有绝对的分隔。年鉴学派知道如何利用大众媒体宣传历史学科,历史学家们习惯于投身历史科普,因而很多大众历史读物兼具文学性和专业性。地理学家将自己束缚于象牙塔中,不愿屈尊进行大众地理科普,而大众地理读物(即边缘地理学)因为缺乏专业的指导沦为“作为景观的地理学”:“当涉及美国的时候,我们喜欢展现人类壮举和壮美风景组成的景观,当涉及异国情调的国家时,我们喜欢展现民族情调和人类学视角。”(Chevalier,“Géographie et paragéographie”10)在什瓦利埃看来,地理学和大众的分隔在法国具有特殊性,因为在传统的学科设置中,文学院和地理学系的关系并不紧密,作为后来者的地理学在其他人文学科面前显得有些战战兢兢。地理学被局限于学科内部,缺乏社会政治层面的交集。1965年后,地理学走向新实证主义,为了维护自身的科学性,地理学家们彻底放弃了“区域描写的艺术”(17)。
如果要重新恢复和大众的联系,让更多人喜欢地理学,诉诸“文学性”是一个有效手段。其实在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具有文学性的地理读物,很好地弥合了和大众的鸿沟。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时,出现过一批旅游手册,描述一地的历史风土人情,这是“混杂的类型,既接近经典旅游文学,也具有高等教育用书的质量”(Chevalier,“Géographie et paragéographie”11)。另一种具有文学性的边缘地理学类型是“专注于描写”的地理学作品,是“对某一地区内人类生活的阐释”(14)。但令人遗憾的是,此种边缘地理学更多是作家、记者和其他人文社科学者在写作。贝杜雷(Vincent Berdoulay)也同样认为,具备文学性的地理话语类型能使地理学拥有更多受众,文学类型对地理话语的最大作用在于扩大“[地理]学科的社会影响力”(Berdoulay,“Géographie”249)。地理话语类型除“区域地理学”“土地治理”等外,也包括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类型,比如游记和以史诗《奥德赛》为代表的“诗歌神话”类型,后者在诗歌的形式中包含了地理知识。地理学将文学类型纳入自己的话语框架中,既体现了地理学走出狭隘的“科学性”和学院视角的决心,也说明地理学家对语言之于思想表达的重要性的认识,因为文学类型不尽然只是外部形式,形式决定了思想如何被表达。
本文探讨了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于80年代达到顶峰的法国地理学对文学的研究。这一时段构成了法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开端,它应和了同一时期西方学界的“空间转向”,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等的空间主题批评研究,叙事学和符号学领域的空间研究一同构成了二战后法国学派的空间研究的主流。法国地理学家对文学的兴趣也和彼时地理学科研究方法的转变有关,新的计量方法不再能够满足地理学对意义和社会问题的叩问,地理学家试图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对科学性的反冲。文学在地理学研究中的价值首先是它的见证功能,地理学家将文学和报刊、广告、电影等其他符号系统视为同等重要的文献资料。作家的地理描绘、对一个区域社会结构的认识为地理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法国地理学具有区域描写的传统,对文学作为文献的价值也集中在作家是否能够深入揭示一个地方的个性的能力判断上。虚构作品虽无法完全精确再现一个地区的地理面貌和风土人情,但作家可以透过表象,把握一个地区的深层结构。法国地理学家对知觉研究的兴趣也使他们关注文学中的城市知觉问题,对个体的主观感受、心理原型和精神结构的关注取代了对作品再现现实能力的关注。法国地理学家认识到,文学不仅是再现的工具,也是被组织的话语,同一时期,法国结构主义者在叙事学和符号学领域所作的文学空间研究为地理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地理学家将目光投向文学话语的独特性,探讨地理如何被编织在文本机理中,他们尤其关注文学叙事和语言的地理特性,即文学如何通过自身的形式模拟所呈现的地理形貌。反之,他们也探讨地理学科的文学性,即地理学如何借用文学手段,为想象在地理学研究中的价值正名,并弥合了地理学和大众的鸿沟。文学话语和地理话语之间互相渗透,互相生成,文学超越了单纯的工具论,成为和地理可以双向影响的、具有能动性的话语。90年代后开始兴盛的“地理批评”派深化了文学和现实空间的复杂关系的研究,“地理诗学”进一步探讨了文学语言和地理间的关系,他们秉承并推进了文学地理学的先驱们所提出的基本命题。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chimon,Philippe.“Physiologie d’un langage.L’organicisme aux débuts de la géographie humaine.”EspacesTemps13(1979):75-103.
Bailly,Antoine S.Laperceptiondel’espaceurbain,lesconcepts,lesméthodesd’étude,leurutilisationdanslarechercheurbanistique.Paris:Edition du Centre de Recherche d’Urbanisme,1977.
Bédard,Mario.“Plaidoyer de l’imaginaire pour une géographie humaniste.”CahiersdegéographieduQuébec82(1987):23-38.
Berdoulay,Vincent.“La métaphore organiciste:Contributionl’étude du langage des géographes.”AnnalesdeGéographie507(1982):573-586.
由表1可以看出,国内移动阅读研究的核心作者中茆意宏、高春玲在移动阅读兴起阶段就开始了研究,且发文量较多。移动阅读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且主要以高校的信息管理学院(系)、管理学院、信息科技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图书馆为主。
---.“Géographie:lieux de discours.”CahiersdegéographieduQuébec32.87(1988):245-252.
Bouvet,Rachel.Versuneapprochegéopoétique.Québec: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Québec,2015.
Brosseau,Marc.Desromans-géographes.Paris:L’Harmattan,1996.
Chevalier,Michel.“Géographie et littérature.”Lalittérturedanstoussesespaces.Ed.Michel Chevalier.Paris:CNRS Editions,1993.2-84.
---.“Géographie et paragéographie.”L’Espacegéographique1(1989):5-17.
Claval,Paul.“La géograhie et les chronotopes.”Lalittérturedanstoussesespaces.Ed.Michel Chevalier.Paris:CNRS Editions,1993.103-121.
---.“Les langages de la géographie et le rle dans son évolution.”AnnalesdeGéographie518(1984):409-422.
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郑胜华、刘德美、刘清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EpistemologyandtheHistoryofGeographicalThought.Trans.Zheng Shenghua,Liu Demei and Liu Qinghua,et al.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5.]
Collot,Michel.Pourunegéographielittéraire.Paris:Editions Corti,2014.
Deguy,Michel.Lafindanslemonde.Paris:Hermann,2009.
Frémont,Armand.“Recherche sur l’espace vécu.”L’espacegéographique3(1974):231-238.
Genette,Gérard.FigureII.Paris:Editions du Seuil,1969.
Glissant,Edouard.Lediscoursantillais.Paris:Gallimard,1997.
Gracq,Julien.AndréBreton.Quelquesaspectsdel’écrivain.Paris:José Corti,1989.
安德烈·梅尼埃:《法国地理学思想史》,蔡宗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Meynier,André.TheHistoryofFrenchGeographicalThought.Trans.Cai Zongxia.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9.]
Rimbert,Sylvie.Lespaysagesurbains.Paris:Armand Colin,1973.
Roudaut,Jean.Lesvillesimaginaires.Paris:Hatier,1990.
Sion,Jules.“L’art de la description chez Vidal de la Blanche.”Mélangesdephilosophie,d’histoireetdelittératureoffertsJosephVianey.Paris:les Presses Françaises,1933.479-487.
Tisser,Jean-Louis.“De l’esprit géographique dans l’oeuvre de Julien Gracq.”Espacegéographique1(1981):50-59.
Westphal,Bertrand.Lagéocritique,réel,fiction,espace.Paris:Les éditions de Minuit,2007.
---.“Pour une approche géocritique des textes,esquisse.” Ed.Bertrand Westphal.Lagéocritique,moded’emploi.Limoges:PULIM,2000.9-40.
White,Kenneth.Segalen.Théorieetpratiqueduvoyage.Trans.Michelle Tran Van Khaï.Lausanne:Alfred Eibel,1979.
---.Leplateaudel’albatros.Le Roque d’Anthéron:Le mot et le reste,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