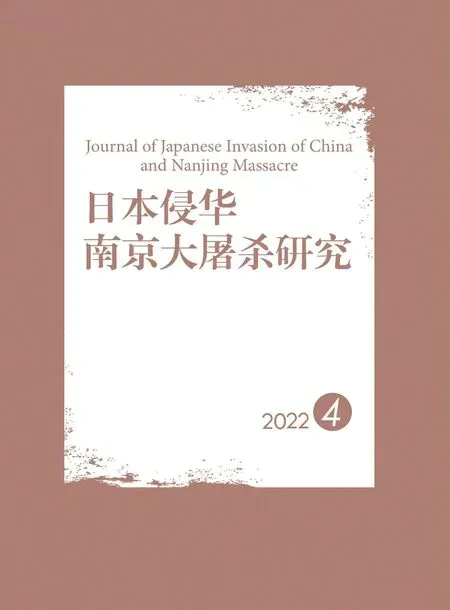个体与国家:南京大屠杀前后难民的民族情感探微
杨雅丽
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在南京肆意屠杀难民,强奸妇女,掠夺财产,焚烧房屋,日军的暴行给难民带来深重的伤害。有学者已注意到南京大屠杀恐怖氛围下民众的复杂心理,并从社会心理、社会心态、精神创伤等角度探究战争影响下难民的心理变化和异常。(1)张连红最早对南京大屠杀与市民心理进行研究,他通过《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四篇文章对南京大屠杀中受害者的心理创伤进行深入研究,指出日军的暴行不仅加深了难民的抗日情绪,还对难民的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生的《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进一步指出南京大屠杀所带来的精神伤害深刻地改变了受害者的人生,其影响从当时延续到现在。美国学者Mark S.Eykholt的博士学位论文《沦陷时期南京民众的生活(1937—1945)》(Living the limits of Occupation in Nanjing,China,1937—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1998)、姜良芹和吴润凯的《从市民呈文看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郭昭昭的《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市民生活秩序变迁研究(1937.7—1938.4)》(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卜正民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孙浩伟的《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与南京秩序的重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等从市民的生活入手,探究大屠杀后市民的生活及其心理变化,他们都关注到了生存与妥协之间的关系。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第六章第四节专门探讨大屠杀中的难民心理:在日军暴行下,恐惧使得难民进一步寻求西方人士的帮助,并开始通过信奉基督教缓解心灵创伤。张连红、王卫星、刘燕军、杨夏鸣合著的《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进一步深化了安全区的研究,其中第四章《安全区的难民组成和难民心理》深入探究躲避于安全区内的难民的心理,难民一方面依赖西方人士的庇护,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日军的胁迫之下生存,有些人消极逃避,有些人敲诈告密。上述研究成果展现了南京大屠杀前后民众心理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南京大屠杀前后难民的民族情感的变化和发展。不过,相关研究对于南京大屠杀期间难民民族情感的变化关注较少。(2)相关成果可参见张连红《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民国档案》2007年第4期;卜正民:《中国日占区的事仇民族主义》,卜正民、施恩德编,陈诚等译:《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张福运:《如何评判沦陷时期的南京民间社会——“抗争”与“灰色地带以外”的视角》,《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李宁:《哀鸣与反抗: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程瑞芳日记〉解读》,《日本侵华史研究》2016年第1期。还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20世纪早期的反日情绪中,对外国侵略军的仇恨更多是一种政府舆论引导下排外的情感,而非主动的民族情感。(3)卜正民:《中国日占区的事仇民族主义》,卜正民、施恩德编,陈诚等译:《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第195页。南京大屠杀期间,零星的反抗、个别的“合作”、多数人的沉默和顺从也引起了学者对民众民族情感的质疑。事实上,民族情感是个人在日常情境中产生的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生活区域等的热爱,它的产生与个人的生存密切相关。(4)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25页。因此,研究南京大屠杀前后难民的民族情感,不能只关注难民在危机状态下是否作出反抗,而应该回到历史现场,聚焦于难民具体的日常生活,关注难民具体言行之中的情感流露。
日军暴行造成的苦难既是人性的试金石,也是民族情感的催化剂,一方面,它能瓦解人的意志,使人变得消极、自私、冷漠;另一方面,它也能激发人们团结一致,共渡难关。探究难民情感,除了关注到暴行下难民的痛苦、麻木外,难民们的守望相助也不容忽视。本文拟以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难民群体(5)“难民”在词义上是指因遭受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在人口学上指的是因天灾人祸等种种原因而被迫强制迁移的人。因此,广义上的难民是由于天灾或人祸而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的人。为中心,考察难民个体层面民族情感的联结过程,探索南京大屠杀前后难民情感的纠结与困顿。
一、风雨摇摆:南京沦陷前难民的情感波动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不久,日军即发动对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的空袭。在空袭之下,南京民众切身感受到战争带来的强烈冲击。据统计,从1937年8月15日到10月15日,南京共遭受空袭65次,造成392人死亡,438人受伤,1949间房屋被毁。(6)《南京市长马超俊就本市被日机空袭损伤情况致行政院呈文》(1937年11月4日),经盛鸿等编:《战前的南京与日机的空袭》,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其后,日军的空袭仍然连续不断。空袭不仅带来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对民众的心理安全感造成巨大冲击。在空袭下,每个人都可能丧命,这使得南京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恐慌。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的王子壮曾在日记中记录了空袭下的恐惧:他正准备睡觉时突然听到了防空警报,来不及躲进地下室,感受到刹那间,狂风暴雨般的呼啸声、爆炸声在耳畔响起,房屋震动,周围火光四起。他形容自己“已受死刑之宣告”,“今日已知其(空袭)之百怖”。(7)《王子壮日记》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236页。连日的警报声使得民众担惊受怕,王子壮的家人因此“食眠俱废”。(8)《王子壮日记》第4册,第232页。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家里的女工一听到飞机的声音就战栗不已,连家犬也被炸弹和飞机的声音吓得不敢吃东西。(9)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王子壮形容当时南京民众的心态:“人现恐怖之态,是‘死’之一念震动人心。”(10)《王子壮日记》第4册,第274页。
与此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恐日病”情绪蔓延。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的王世杰就发现:“首都一般人士深感大战爆发后之危险。无知识或无责任之人,感觉身家危险,有知识者则对国家前途不胜恐慌。”(11)《王世杰日记》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版,第82页。
战争的阴霾笼罩在南京民众的心头,人们每天都生活在紧张、压抑的气氛下,日常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除了频繁的空袭所造成的恐惧,还有对未来前途的迷茫:这样的日子将会持续多久。金陵文理女子学院负责人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文名华群)有一天在路上偶遇一位陶姓农民,这位农民称炸弹的爆炸声使他感到害怕,并问魏特琳是否认为战争有望很快结束。另一位慈祥的老农也向魏特琳询问战争要持续多久的问题,“他噙着泪水说,穷人忍受不了多久了”。(12)[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恐惧驱使一些难民逃离南京。行政院参事陈克文观察到,由于连续数日遭受敌机空袭,行政院的工作人员感受到严重的心理压力,他们或告病请辞,或偷偷离开南京。(13)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第109页。魏特琳也观察到,“城里的人似乎也被吓坏了,许多人溯江而上到一些小地方,甚至去了农村”。(14)[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11页。
不过,在部分市民逃离南京的同时,不少外地难民陆续进入南京,他们中有的来自沦陷区,如北平、天津,有的来自上海、苏州、无锡等交战区。许多人以南京为落脚点,在这里稍作停留继续西进,其中的不少人因川资不敷,不得不滞留南京。更有人认为南京是首都,比较安全。难民张玉英的父亲张慰曾在北平电话局工作,他认为“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应该比较安全”,于是举家从北平迁到南京。(15)《张玉英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面对蜂拥而至的外地难民,南京市政府积极组织,成立南京市难民救济委员会,收容、救济来到南京的难民。
在日军的空袭下,政府还加强防空宣传,修建大量的防空洞供市民避难。在政府的引导下,许多市民也开始自建防空洞。据日本情报人员观察,面对日军的空袭,南京全市秩序井然,空袭时,“路上行人全都进人地下室避难,车马停在一定地点,街上全无人影”。在军警和防护团的积极疏导之下,“一般市民已习惯空袭,面无惧色,态度冷静”。(16)《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马振犊等编:《南京保卫战》,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日军的空袭给南京市民带来了切身威胁,但并没有压垮南京市民的意志,对此,魏特琳感慨道:“日本人正在让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得更紧密,他们要是明白这一点就好了!以前我从未见过中国人的这种勇气、信心和决心。”(17)[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76页。
早在全面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就在南京开展了广泛的抗战宣传,南京各机关、团体成立了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负责统筹协调社会各界人士的抗日活动。抗敌后援会开展慰军活动,支援物资,筹募捐款,征集志愿者进入救护队、运输队等。(18)《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统一全市救国运动》,《中央日报》(南京版)1937年7月20日,第3版。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还制作相关的抗敌救国幻灯宣传片交由各影院放映,以增强民众的抗敌救国意识。(19)《京市各界筹组抗敌后援会》,《中央日报》(南京版)1937年7月14日,第7版。各种表现亡国奴惨痛生活、刻画爱国者反抗斗争的戏剧和电影在南京不断上演,如军委会政训处抗敌剧团的剧目《我们的故乡》《八百壮士》在南京香铺营中正堂公余联欢社连续上演数天。(20)《军委会政训处,抗敌剧团公演,今日起连演三晚,在公余社中正堂》,《中央日报》(南京版)1937年11月12日,第4版。南京街头各种抗日宣传也相当普遍,抗日漫画、标语随处可见,“市内各处涂刷很多抗日标语,多数都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致团结抗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等词句”。(21)《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马振犊等编:《南京保卫战》,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册,第39页。抗日情绪通过表演、图文等传播媒介,从精英阶层传播至下层民众。据日本情报人员反映,无论是农民,还是市内市民,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抗日宣传的影响,同时,“特别因飞机不断轰炸,抗日宣传效果很好”。(22)《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马振犊等编:《南京保卫战》,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册,第38—39页。“抗日”已成为南京市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国民政府还发动民众参与反汉奸斗争,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国民政府不断加强谴责汉奸的宣传力度,劝告民众:“勿贪一时小利,危害国家,如因失业可求政府救济。”(23)《京市府劝告汉奸》,《中央日报》(南京版)1937年9月6日,第3版。无论是报纸上,还是大街上,都充斥着痛斥汉奸卖国的标语,如:“做汉奸就是出卖祖宗!做了汉奸不得好死!做了汉奸遗臭万年!做了汉奸子孙不能做人!”(24)《中央日报》(南京版)1937年10月13日,第3版。在国民政府的引导下,南京市民反对汉奸的情绪高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娄遵宜对魏特琳说:“魏特琳小姐,如果我们被打败的话,那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缺乏勇气,而是我们的队伍中有汉奸。”(25)[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36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民众逐渐适应了空袭下的生活,甚至对空袭日感麻木,按部就班地开展生活,就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花匠老邵,“他几乎无法理解这场战争,要他相信战争会持续一年,或是更长的时间,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继续为明年春天种豆子、白菜和生菜”。(26)[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123页。这种“事不关己”的心态在底层民众中比较常见,由于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他们对于各种政治角力的反应通常不会过于激进,而是采取保守的心态和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27)张福运:《如何评判沦陷时期的南京民间社会——“抗争”与“灰色地带以外”的视角》,《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他们之中有一种普遍的思想,“‘民族’和‘国家’只支持在少数知识分子手里,于四万万平民大众有何干系?”(28)文木:《恐日病——制造汉奸的酵粉》,《立报》1937年9月30日,第2版。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会和他们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南京城内,失败颓唐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11月13日,陈克文发现上海的报纸已有四五天没有送达,南京的报纸虽然每天都送到,但也没有人阅读,没有人愿意打开收音机,虽然日军没有空袭,但民众不像往常一样偷闲作乐,精神上受压迫的痛苦比遭受空袭时更为严重。(29)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第127页。
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机关公务人员的撤退、日军向南京的快速推进、有关日军残暴传说的流传、沪宁线及城郊地区难民的持续涌入等等,这些使南京城中的民众真切地体验到了战争的氛围,恐慌与不安渗透到每个人的心中。(30)张连红:《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大量的民众选择迁移,形成“全民大出逃”的浪潮。魏特琳后来在报告中写道:“数周以来,人们一直在撤离南京。先是富有的人家开始撤离,所有的卡车、小汽车都派上了用场,成千上万的人沿江驶向汉口或更远的西部。接着是中产阶级开始撤离,最后是穷苦人。多少天以来,你可以看见人力车满载着箱子、铺盖卷和乘客经过。所有能这么做的人都逃出了南京,穷苦人往往是带着儿女躲到乡下,把老年人留下看家。”(31)华群:《第一个月的评述(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13日)》,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这种凄凉的景象让民众深受触动,陈克文哀叹道:“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不图宋室南渡,与明末播迁之景氛,竟令吾人身受之也。”(32)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第128页。
在很多人选择迁移的同时,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民众选择留在南京。他们或是没有财力迁移,或是担心迁移会造成财产损失,或是担心迁移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他们大多数是贫困穷苦人家,文化水平较低,每天忙于生计,只能被动地接受时局的变化,无奈地面对战争的到来。
日军的来势汹汹让留在南京的难民们慌乱无措,他们迫切希望政府能够抵挡住日军的进攻。拉贝(John H. D.Rabe,中文名艾拉培)在1937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刚刚传来的一条消息说,最高统师决定将防守部队的前沿阵地确定在城外50里处。这个消息受到了欢迎,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它。一旦防线被敌人突破,人们将撤离这座城市。我无法判断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从军事角度看是否可信。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它毕竟听起来不错!”(33)[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此外,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断重申坚决抗战、防卫南京的立场。(34)《蒋委员长发表重要谈话》,《申报》1937年11月26日,第2版。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更是进一步提出“与南京共存亡”的口号。(35)《南京将变战场我军抱牺牲决心》,《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11月29日,第2版。这些宣传多少让留守南京的民众感到安心。
1937年12月初,中国军队大规模溃退、南京外围战事逐渐吃紧的消息将民众从理想拉回现实。与此同时,西方人士在南京开设的安全区(又称难民区)对外开放了,惊慌失措的难民潮水般地涌向安全区寻求庇护。中国军事当局也劝说市民进入安全区避难。人们在逃难途中互通信息,相互效仿,形成一波前往安全区避难的“难民潮”。难民张家勤在回忆自己的逃难经历时说,“逃难的人除了知道有个外国人办的难民区外,谁也说不清更具体一点的情况。好在人多胆壮,全都随大流”。(36)张家勤:《我在难民区的所见所闻》,《南京史志》1987年特刊(总第25期)。
难民们普遍感到焦虑——因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37)[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190页。部分难民依然认为日本的侵略与以往的军阀战争相似,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是一场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的民族战争。一些人根据以往军阀战争的情形判断,认为南京沦陷后仍会是“三天安民”:“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三天以后才出安民告示”。(38)郭岐:《陷都血泪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同时,安全区内的难民相信外国人成立的安全区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认为日本人不能轻易进入安全区。(39)张家勤:《我在难民区的所见所闻》,《南京史志》1987年特刊(总第25期)。
中国守军出于战事需要,在城郊清理路障、烧毁房屋,迫使一部分民众流离失所。一些人因此对军队十分不满,他们常常拒绝配合军队,觉得“果真日本鬼子来了,只怕也不过如此吧!”(40)郭岐:《陷都血泪录(节录)》,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180页。
很多难民心存侥幸,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做好了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准备,“许多贫穷或富有的住家门口都挂起了日本国旗……以期获得较好的对待”。(41)[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193页。不仅是中国人,西方记者斯提尔(Archibald T.Steele)也在报道中写道,“我们这些被围困在城墙内的人只希望能尽快而没有痛苦地度过这一时刻”。(42)《当地人涌入“安全区” 翰旋策图救南京城》,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南京沦陷前,南京难民们在风雨摇摆的局势下,心理情感几经波折。乐观与恐惧的情感随着人们接触到不同的信息而不断变化。在空袭的侵扰和流言的发酵下,恐慌是留守市民情感的主基调。对战争的恐慌驱使众多难民迁出南京,留下的多是社会的底层民众,大多没有文化,思想相对保守、落后,迫于生计,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的生活,没有认识到战争与个人命运的关联,不少人对日军还心存侥幸。
二、风雨同舟:南京大屠杀期间共同体情感的生成
南京沦陷后,日军持续数周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彻底击碎了难民们的侥幸心理。安全区对日军暴行的阻挡有限,日军在安全区内外连续不断地屠杀平民、焚烧房屋、抢劫财物、奸淫妇女。在日军的暴行下,难民生活悲惨。鼓楼医院总务主任麦卡伦(James H.McCallum)发现,“许多人一无所有,只剩下一件单衣。他们无依无靠,手无寸铁,任凭日本兵摆布,后者已被允许到他们乐意去的任何地方游荡”。(43)《麦卡伦致家人函》(1937年12月19日—1938年1月15日),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第205页。
在陷落的南京城内,难民们深刻地感受到命运被他人支配的绝望。日军的肆意纵火让难民的家园尽毁,部分难民失去了生活的希望。难民张家勤回忆道,“那时,使我们更为惊恐的却是日本人在城南一带纵火……在这不是人过的日子里,人们最大的愿望便是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中去,不再担惊受怕。如果没有了家,难以想象今后如何生活”。(44)张家勤:《我在难民区的所见所闻》,《南京史志》1987年特刊(总第25期)。一位难民痛苦地写道,“在暴戾、凶狠、残忍的敌人铁蹄下的人们,命运已经抓在他们的手里,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有结束的可能。我们只有……听最后的宰割了”。(45)汝尚:《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537页。金陵文理女子学院的舍监程瑞芳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此如同瓮中之鳖,他爱怎样就怎样……四面消息不通,真是走头〔投〕无路”。(46)《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23页。魏特琳也十分悲痛:“悲哀的是,我们看不到未来。这个曾经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首都,现在几乎是一个空壳,可怜与令人心碎。”(47)[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206页。
在这种情况下,恐惧成为难民生活的常态。在恐惧之下,难民们本能地顺从,避免直接对抗导致死亡,即使遭到日军的劫掠,难民们也不敢反抗,对于“陷于恐怖几乎习以为常”。(48)《麦卡伦致家人函》(1937年12月19日—1938年1月15日),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第205页。部分难民甚至因惊恐万分而失去思考能力。住在干河沿难民区的马明喜外出找食物时被日军撞见,被迫跟随前往他人住处劫掠,帮助拖运东西。日本人进屋抢劫,马明喜就站在外面机械地等待,经外人指点才想起来可以逃跑。(49)《马明喜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在恐惧中,许多难民为了自保变得畏缩、怯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员邬静怡因为受到日本兵的威胁而害怕不已,她想混入女难民群里,却遭到难民们的排斥。邬静怡明白难民们不欢迎她的原因是害怕她的出现会危及自身。(50)邬静怡:《东西方相会》,陆束屏编译:《血腥恐怖金陵岁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外人士的记载》,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827页。这种对可能带来风险的求助的排斥极为普遍,尤其是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排斥,更是如此,有难民直率地对前来避难的中国军人表示:“你不能住在我这里,我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一家子!”(51)郭岐:《陷都血泪录(节录)》,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180页。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在日军肆虐的恶劣环境下,保护好自己的家庭是首要任务。
但是,当暴行涉及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时,一些难民会不顾一切地作出反抗。大屠杀期间,日军强奸了众多无辜的妇女,有时还会在受害人家人面前强奸,甚至有时强迫受害人家庭亲人间乱伦,侮辱难民,以此取乐。(52)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7页。这种行为突破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底线。连贩夫走卒都认为日兵强奸妇女是一种卑劣的行为,“是国家民族切骨的深仇,应该不顾一切,誓死起来反抗”。(53)蒋公穀:《陷京三月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62页。难民刘培坤(音译)为保护妻子,使其免遭奸污而痛打日军面颊,不幸被日军枪杀。(54)《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277—278页。金陵大学蚕厂有4名试图保护自己妻子的男子也被日军用刺刀刺伤。(55)《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1937年12月22日),[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208页。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G.F.Rosen)在报告中记述了反抗者的悲惨下场,“在中国的家庭里,如果有受害人的家属敢于反抗这些恶匪,在很多起事件里,他们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56)《南京局势及日本暴行》(1938年1月15日),[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354页。
日军的暴行给难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对于遭遇日军凌辱的妇女而言,她们面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侵害,还有心理上的耻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被奉为圭臬。大部分被强奸的妇女虽然内心充满愤恨和痛苦,但是她们认为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害怕在难民群体中受到异样的眼光,也羞于向他人叙说自己的遭遇。(57)[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266页。部分妇女甚至在羞愤之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亲人遭到奸污,家中的男性也不愿让外人知道,许多人都尽量掩盖妇女遭到强奸的事实。(58)《南京地区战争灾祸》,姜良芹、郭必强编:《前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5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因为这对于家庭而言也是一种耻辱。程瑞芳作为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中国女性,非常理解这种苦痛,她不止一次痛斥日军的残暴无道,“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59)《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17页。程瑞芳有意使用“用”来代替“奸”,这种微妙的改动既隐晦地表达了妇女的悲惨命运,又弱化了强奸暴行对女性尊严的伤害。有学者研究指出,这是同为中国女性的程瑞芳所能做到的对受害者人格的一种言语保护。(60)李宁:《哀鸣与反抗: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程瑞芳日记〉解读》,《日本侵华史研究》2016年第1期。日军的暴行在难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这种创伤不仅在于强奸的实际伤害,还在于无法反抗的悲痛。
在多数的情境下,面对手持刺刀的日军,手无寸铁的难民的反抗可能并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反而使自身面临被杀害的风险,相当多的难民只能眼看着亲人被侮而不敢反抗。“谁无父母?谁无子女?当父母被日军任意凌辱时,做儿女的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父母,这种痛苦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61)《王如贵证言》,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第104页。这种暴行下的无力感,让难民陷入深深的痛苦。
在人人自危的状况下,悲惨境遇的相似性更容易引起难民之间的共鸣。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姜正云看到日军公然羞辱妇女,“到处都充满了呜咽声”,而自己毫无任何方法阻止她们哭泣,对此他感到非常无奈。(62)《姜正云给菲奇的信件》(1937年12月17日),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程瑞芳同情难民的遭遇,对于日军惨无人道的杀戮行为表示愤慨和无奈,“这些难民跑到此地来躲,他们硬到此地来拖,气死我也”。(63)《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17页。军医蒋公穀与他的长官金诵盘感伤在难民区不能有所作为,“忠勇的正气,寻不到一条发泄的方向”,“不禁迸出一行行热泪”,放声痛哭,感到“痛楚深深地激动了我们”。(64)蒋公穀:《陷京三月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65—66页。他们看到难民们的悲惨遭遇,感受到他们的悲痛情感,感到深深的悲愤和无力。
无助的难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自暴自弃,“很规矩的人,乘此机会,好打牌的大打牌,好推牌九的大推牌九,好抽大烟的大抽大烟,好嫖的人也是(个)机会”。(65)郭岐:《陷都血泪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37—38页。难民收容所内出现流氓,敲诈勒索的事件多有发生。有的难民甚至成了日军的帮凶,他们或向日军告密,或前往难民收容所为其索要妇女。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史迈士(Lewis S.C.Smythe)无比愤恨地说:“这些无赖只会带来无尽的麻烦!”对于这些日军的帮凶,不只西方人士感到不快,大部分中国人也咬牙切齿,然而他们都对此无能为力——所有人都害怕日本兵的报复。(66)《史迈士致妻子函》(1937年12月20日—1938年1月9日),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第242页。
苦难一方面会摧毁人的意志,使人消沉堕落;另一方面它也能够激发难民们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程瑞芳感慨道,“现在中国人,不[被]抢过也不行、日子难过,非要自己奋斗才行”。(67)《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45页。在人群聚集的难民收容所里,为恐惧所包围的难民们聚集在一起。在拉贝的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偎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为了加强保卫安全,拉贝安排难民轮流守夜。拉贝在1937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记述道:“我的小小的院内收容所充满了祥和与安宁,只有12个岗哨悄无声息地沿着院墙来回走动。换岗时,几个手势,断断续续的话语,谁都不想打搅患难兄弟姐妹的睡眠。”(68)[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151、226页。
团结互助的经历加速了难民情感的凝聚,同病相怜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难民之间的情感联系。当时避居安全区内的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郭岐与几位同仁一起住在意大利大使馆,“沦敌之初,我们无法测度下一分秒的遭遇,更无从决定未来的去向与命运,愁云惨雾,弥漫心头,焦灼恐怖,无时或已,我们就只有相互慰藉,相互支援,如像亲人骨肉一般,表现出迥乎寻常的友爱”。为了维持生活,保障安全,他们更是毫不迟疑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69)郭岐:《陷都血泪录(节录)》,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148页。同一境遇下的难民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与触动。郭岐发现在经历了大屠杀之后,难民们突然醒悟过来。“日本鬼子兵腥风血雨的压力,终于提高了我们民对军的爱心,南京难民口口声声的说:‘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条命,还分什么彼此,讲什么你我啥。’”(70)郭岐:《陷都血泪录(节录)》,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180页。
为了保护放下武器的士兵和难民,难民收容所的管理人员积极开展工作。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帮助逃入收容所的中国军人掩盖身份,为他们提供自己的衣物,并动员难民捐出换洗的衣服,帮助他们换下军装,并将军装拿到厨房烧掉。(71)薛贵才:《一段令人难忘的辛酸往事》(2007年9月26日),《金陵中学校友通讯》第53期,2007年9月,http://app.jlhs.net/DisplayInfo.jsp pageID=8945&menuID=341,2022年9月25日。部分难民受到西方人士和中方管理人员善行的感染,表现出了一定的牺牲精神,他们愿意为不相识的人在危难关头承担风险。在日军进行“难民登记”大肆搜捕青壮年时,不仅难民管理人员积极营救难民营中的青年,部分老人和妇女也主动认领青年当作自己的家人,挽救了一批人的性命。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有一个老太太认领了3个人,“其实她不认得他们,她就是要救他们”,“还有一个年轻女子也出来认她的哥哥,回到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72)《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25页。此类认领事件在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等地也多次发生。患难见真情,这种团结互助的经历令难民之间产生了独特的情感联结,难民不再只关注自身的生存,而开始愿意为他人冒险。
中西方人士悉心守护安全区,让难民有了安身之所。在安全区与难民收容所这一特定空间区域内,难民们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形成了某种形式上的集体情感。这种情感不仅表现为对内部集体的归属感,还表现在对外部群体的排斥感。(73)Christian von Scheve and Sven Ismes,“Towards a Theory of Collective Emotions,”Emotion Review,Vol.5,No. 4(2013),p.411.1938年2月,日本外交协会代表高木富五郎在考察南京及其他城市后发现,“现在的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即使是无知的苦力都有强烈的反日意识……中国民众的反日意识已经融进了他们的血肉中。他们只是因为所谓的‘没法子’而保持沉默”。(74)「52.満洲、北支、中支の皇軍慰問並に現地見聞の一端(高木富五郎)」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919900、本邦対内啓発関係雑件/講演関係/日本外交協会講演集 第四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而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德士(Miner Bates)在大屠杀之后面向南京市民所进行的调查也显示,“在未来的50年中,这个地区的人民决不会相信任何有利于日本的词语”,因为“日军的所作所为,对每个家庭——包括那些为了不致饿死而在傀儡政府工作的人——的生活伤害得太深了”。(75)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魏特琳也观察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使他们在道义上陷入失败,并“永远失去今天居住在南京的居民的尊敬”。大多数人相信日本永远不可能成功,“没有哪一个残暴的民族能长久”,人们普遍相信,“中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的”。(76)[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197、446、512页。
在强烈的反日意识下,难民们普遍对日军的政策态度消极,拒绝与伪政权合作。当日军试图解散安全区、组织难民收容所管理人员担任伪职时,多位管理人员不愿服从安排,拒不参加日伪政权组织的会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第七区区长张永生更是直接退回伪政权机关的公函,拒不担任伪职。(77)《张永生声明不是第七区区长职务呈案》(1938年1月),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档案,南京市档案馆藏,1002-019-0002。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义工刘文彬(Liu Wen—pin,又译刘文宾)因不愿做日本领事馆警察的翻译而被日军带走,后遭到迫害。(78)《贝德士致朋友函》(1938年1月10日),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等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19页;《史迈士致朋友函》(1938年3月8日),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日军当局一度逼迫西方人士解散安全区,关闭难民收容所,强迫难民返回原居住地。但难民们拒绝返回居住地,他们声称“与其我们回家被人杀死,还不如留在这里,等到2月4日日本人来驱赶我们,被他们杀死在难民收容所好了”。(79)《事态报告》(1938年2月1日),[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457页。
虽然难民们不会冒险直接反抗,但他们仍会对日军的暴行作出一定程度的抗争。一些难民收容所中方管理人员将目睹的日军暴行一条条记录下来,定期汇总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西方人士,通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递交给日本大使馆,希望对日军暴行有所约束。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姜正云著有“南京金中难民收容所记录”一册,记录着日军在收容所侵害难民的情形。(80)《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通译员档案》(1946年),江苏省档案馆藏,1047—003—1585。此外,即便难民们受到了日军的威胁,但还是有许多人站出来向贝德士等人报告日军的暴行事实,并为之作证。(81)《给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信》(1938年2月22日),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第130页。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当局因自身暴行不断受到难民的敌视。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西方人士因充当阻止日军暴行、保护难民的角色得到了难民的信赖。(82)张连红:《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民国档案》2007年第4期。日军的暴行与西方人士的义举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在危难时刻,西方人士的善举更能激起难民内心的认同和感激。在此之前,南京的民众常常称呼魏特琳等外国人为“洋鬼子”。在“鬼子”之前加“洋”,既凸显了“洋鬼子”的异质特征,又表达了他们对于外来侵略的反感。(83)许龙波:《从“鬼子”词义及其指称变化看近代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全球史评论》2021年第1期。但经历了这次浩劫之后,难民们对于安全区的西方人士的情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魏特琳日记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小男孩看到魏特琳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84)[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331页。无独有偶,福斯特也有类似的经历。(85)《福斯特致妻子函》(1937年11月23日—1938年2月13日),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第122页。在许多难民心里,这些救济难民的西方人士是“菩萨”,而非之前的“洋鬼子”。用“菩萨”这个词来称呼西方人士或许有些不伦不类,但这正说明了难民们将在宁西方人士看成是自己人,不再是野蛮的“他者”。而“鬼子”这个词被难民用来称呼日本人。“日本鬼子”在继承了“洋鬼子”的野蛮、残暴的内涵后,又呈现出一种更加鲜明的侵略性。魏特琳觉得这并不令人惊讶,“他们觉得侵略者就是野兽”。(86)[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331页。
日军的暴行对南京原有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也改变了难民们的人生。大屠杀使难民感受到恐惧和绝望、愤恨和耻辱,也促使难民们团结一致,谋求生存。同一空间下的相似境遇促进了难民间的情感融合,相互间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感。同时,在日军的暴行下,难民间的命运相互联系,彼此的善意帮助会让他们产生归属感和凝聚力,难民群体初步产生了一种集体情感。面对共同的敌人,这种情感使得难民常常追随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揭露日军的暴行,抵制日方的政策。换言之,难民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以维持生存为主要目标而形成了临时性的共同体。虽然在难民收容所中也存在着纷争和矛盾,告密和诬告的情况时有发生,但难民之间还是存在某种友谊,而这种团结的精神与个体寻求生存的本能是共生的。
三、同仇敌忾:生存危机下民族情感的凝结
南京大屠杀期间,难民目睹了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的丑恶行径,认识到侵略者的凶恶面目,“原来日本人真是这样凶狠毒辣啊,早知如此,鬼子兵攻城的时候,我们就该统统到城墙上去,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比如今这样等着他们来宰割,来烧杀,岂不是要强多了吗?”(87)郭岐:《陷都血泪录(节录)》,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179页。
同样面对日军,难民和西方人士的处境完全不同,这对难民们的思想认识带来冲击,“对中国难民来说,欧美人士是更‘高’的存在——不仅仅是生理性的,在文化、精神上亦如此——他们面对日军和日本外交人员的不卑不亢,日本人对他们的敬畏,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8)张生:《死神面前的“不平等”——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中国难民内部分层》,《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第6期。面对日军的暴行,姜正云在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George A.Fitch,中文名费吴生)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虽然有拯救难民们的心愿,“却没有这种权威”,“是一个地位处境微末的人”。(89)《姜正云给菲奇的信件》(1937年12月17日),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第92页。在难民们的眼中,西方人士的权威源于他们的国家,而中国积贫积弱,他们处于国破家亡的境遇,只能忍受痛苦。
相同的难民身份,同样的境遇使得部分难民在遭受磨难的过程中,将个人、群体的苦难引申到民族、国家层面。程瑞芳在日记中写道:“这种亡国奴的苦真难受,不是为民族争生存,我要自杀……中国人为何要做〔受〕这种罪”,“想到自己国家不强,受到这种耻辱,何日能雪耻”。(90)《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16—18页。屠杀记忆和生存困境不仅强化了难民对敌我双方不同群体的情感,还加强了难民的身份认同——“中国人”。
在困境中,难民们一方面为未来感到担忧、沮丧和失落,一方面还对未来抱有希望。对于难民而言,西方人设立的安全区不仅提供了暂时的容身之所,还充当了情感的庇护所。安全区使得部分难民能够避免生活在日军完全控制的区域,这对于国破家亡的难民而言是一种慰藉,军医金诵盘直言:“我们今日虽被困在沦陷区内,但始终未在敌人的旗帜下去苟求生活,这总算是聊称心意的事。”(91)蒋公穀:《陷京三月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68页。
安全区的背后还有国民政府的影子,这也给予难民心理上的慰藉。部分难民知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粮食和资金有一部分来自国民政府的支援,他们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国民政府相联系。(92)郭岐:《陷都血泪录(节录)》,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178—179页。在大屠杀的恐怖环境下,这样的流言让难民感到慰藉。这番看似天真的言论,却蕴含着底层民众对家园故国的依恋之情。在失去国家的保护后,难民们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对于民众而言,国家与政府并非只是想象的共同体,更是个体与家园的保护者。
在日军的胁迫之下,难民的生活被恐惧的氛围所笼罩。有的难民发出自己的疑问,“谁人能救我们出险?谁能救我们的国家?”(93)《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45页。在恐惧和悲痛之余,难民渴望复仇,渴望从日本人的残暴统治中解脱出来,期盼中国军队的到来,他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念叨:“中央军为什么还不来啊!”(94)郭岐:《陷都血泪录(节录)》,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180页。1938年1月2日,中国轰炸机重回南京上空,这让“苦日军已久”的难民看到了希望。他们手舞足蹈,高声欢笑,异口同声地在向天空上的飞机喊叫:“炸呀,炸呀!多投几颗大炸弹,把鬼子兵统统给炸死吧!”“炸炸炸!多炸死些鬼子兵,那怕连我炸死在里面,我也心甘情愿!”(95)郭岐:《陷都血泪录(节录)》,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181页。难民们积郁多日的怨气仿佛在一瞬间找到了发泄口。
1938年1月初,部分日军调离南京,南京城内的日本士兵数量减少。拉贝观察到街上的日本宪兵确实减少了很多。(96)[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296—297页。这一现象使得部分难民更加相信南京即将收复的流言,甚至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工作人员韩湘琳也对此事信以为真。他拒绝从日军那里购买米面,认为只要南京被收复,就可以无偿得到米面。(97)[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296—297页。1月8日,有人声称已经在城里看到中国士兵了,甚至还有人称中国军队已经临近南京城,日军想借平民衣服化妆逃跑……“谣言传播起来像野火一样迅速”。(98)[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308页。难民们“真如发了疯一般,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欢呼欲狂,大家都以为国军就要攻入城来了”。(99)范式之:《敌蹂蹦下的南京》,“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123页。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扔掉了日本旗子和日本臂章。(100)[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308页。军医蒋公榖认为这是难民们“民心一致、同仇敌忾”的表露。(101)蒋公榖:《陷京三月记》,“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83页。不仅如此,一些难民看见一些在日本大使馆洗衣的妇女抱着东西离开,误以为日本人已经逃离大使馆,于是便想去“打劫”大使馆。(102)《威尔逊书信(日记)》(1937年12月5日—1938年1月9日),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第350页。这一方面是出于报复心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贫困的难民希望能够从中获得物质利益。
1938年2月初,中国军队进城的谣言又起。街上的民众多次“要[将]手上的日本袖[章]脱下去,又未看见什么,心里望我军进来心切”。(103)《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40页。此外,南京城内还流传着“游击队进城”的信息,避难于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的教导总队工兵团第三营营长孙宝贤在市场闲逛,听到有人在市场上喊:“我们游击队进城了,你们还不赶快把日本旗取掉”,“于是悬挂日本旗的,马上把旗取下,臂上缠日本臂章的,一面跑,一面撕臂章,霎时日本标帜全没有了”。在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门口,两名青年在驻守的日本宪兵面前撕毁了良民证并说:“我们游击队进城了,要这东西没有用了。”孙宝贤派人每夜在高楼上瞭望,打算万一真有游击队进城发动攻击时,配合游击队“出其不意地给日军一个痛击”。(104)孙宝贤:《南京沦陷前后及被难脱险经过详情实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109—110页。
尽管南京城内仍充满了谣传,但是西方人士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检验信息的真假,相关的流言多次被证明是不确实的。(105)《威尔逊书信(日记)》(1937年12月5日—1938年1月9日),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第350页。与西方人士相比,难民的知识水平和消息渠道都很有限。在客观情况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处于不安和忧虑之中的难民更愿意相信蕴含着希望的流言。这种流言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一方面驻扎在南京的日军人数减少,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江南地区游击队比较活跃。此外,由于日军的暴行对难民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难民借流言来宣泄对日军的愤怒与仇恨,获得心理的平衡,在流言中获得慰藉和希望,获得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因此,一旦城内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难民将其解读为游击队反攻回城的征兆,然后流言迅速传播,对难民产生广泛的影响,以至于西方人士担心流言会引导难民们发起骚乱,招来日军的杀戮。(106)[德]约翰·拉贝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第308页。
此外,难民们也寄希望于城外大刀会、红枪会、花篮会等帮会武装。这些帮会原是民众为防御土匪及军阀骚扰而自行组建的,大多规模不大且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有一位从外地回南京的难民告诉魏特琳,外地的村庄都由大刀会保护,“这些人身背大刀,眼睛里流露出奇特的目光,村民们很尊敬他们,为他们烧香磕头”。(107)[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254页。更离奇的是花篮会,“听说是乡下女人左臂上挎一只篮子右手拿一把扇子,如有子弹飞来,他一扇即将子弹扇入篮中”。还有一些流言声称帮会成员刀枪不入,让日军闻风丧胆。“一般兽兵对我红枪会畏惧极了!他们说:‘中国有装甲人——铁皮人——大大的我们不能回国了!’”(108)郭岐:《陷都血泪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48—49页。虽然这些流言带有传统的迷信色彩,但它们真实反映了难民们希望打击侵略的日军,渴望回归正常生活的情感。
虽然难民内心充满对日军的仇恨,但他们深知自己无力直接反抗日本的统治。在传播中国军队收复南京、帮会武装有效攻击日军的流言之外,他们对于日军的合作者更加愤恨与不满,认为这些人是“叛徒”“走狗”“汉奸”。这些带有道德批判的词语的使用体现了原有文化基础上超越地域的族群意识的存在——事敌是对原有族群的一种背叛。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能够较为生动地反映难民这种情感态度:
有一回一个中等汉奸在路上作威作福的走着,被一个老百姓在路上当面吐口水,他当时大怒,请日本宪兵队来抓他。当时日[本]宪兵队就问那个老百姓:“你为什么看他不起!”老百姓狡猾地答着:“我吃的是日本皇军的饭,为什么要看得起他!”日[本]宪兵队笑笑把他放走,汉奸碰了一鼻子灰,也莫〔无〕可奈何。(109)林娜:《血泪话金陵》,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571页。
部分难民为蝇头小利而不顾气节的行为会受到有识之士的谴责。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些中年妇女争抢日本妇女发的糖果、霉苹果和几个铜板。对此,程瑞芳十分愤怒,“我真气死了,我骂他们,华也骂他们,有的难民也骂,这些人简直不要脸,这一点东西值什么,还要叫、还要抢,不是叫人家笑话吗?这样不值价,也不知日本鬼是他们的什么人,就是饿死也不要吃他的东西,小孩子们要还可以,这样大的人做这种事,这些无知的中国人”。(110)《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27页。对此,郭岐亦有同感,“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呀!当然那些少数无知的妇女所干的事儿虽小,影响很大。人家亡你国,灭你种,你全都不计,反而受他糖果的小惠,这是多么无耻的事儿!”(111)郭岐:《陷都血泪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53页。无知难民的软弱和卑微刺痛了程瑞芳和郭岐。
不过相对于麻木无知的贫民,程瑞芳更无法原谅知识分子事敌的行为,“中国前途的希望很少,要想到那些智〔知〕识分子做汉奸,这班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比较有可容的地方”。(112)《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27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往往对知识分子抱有较高的道德要求,因为知识分子历来是社会中坚和民族良心,其立场和行为对底层民众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113)张福运:《如何评判沦陷时期的南京民间社会——“抗争”与“灰色地带以外”的视角》,《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然而此时,部分知识分子竟然投敌,这样的麻木和背叛激发了有识之士的批判,其间,民族主义情感被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正义,成为人们理应遵循的道德追求。
然而,在战争状态下,完全遵循这种道德规范十分困难。在惊恐与不安之中,“活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核心。因此,即便心有恨意,面对生存的压力,部分难民仍然会选择为日本人工作,因为“未被敌人杀死,便要活下去,便要吃饭,而在南京找饭吃又是那么困难”。(114)白芜:《今日之南京》,南京晚报出版社1938年版,第54页。沦陷后的南京有大量普通劳工从事军需或运输领域的服务工作,还出现了“满足日本士兵各种不正当需要的行业”。贝德士感喟道,“我早已不愿谴责一个苦力,他替祖国的敌人服务只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或是一个姑娘为了免于饥饿而做任何事情,只要他们不给别人带来太多直接的伤害(譬如参与武装劫掠或贩卖海洛因、吗啡等)。因为高尚的道德难以抵御生活本身的基本需要,战争早已给我们带来数以百万计的经济的与社会的破坏”。(115)贝德士:《致朋友的传阅函》(1938年11月29日),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第49页。
但这些为生存而选择为日本人工作的难民并非完全接受日军的统治。伪政权招募的不少警察都不甘心事敌,他们一有机会便想要回到国统区,因此,常常有警察穿便装逃走。(116)李克痕:《沦京五月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510页。有人因为感受到屈辱,辞去了日伪政权开办的“傀儡学校”的高薪工作,转而“在一个教会机构中拿糊口的工资”。(117)[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第427—428页。贝德士1941年在纽约演讲时提到,伪政权中的一些工作人员是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不得已而就任伪职。他们内心有愧,却无可奈何,因此他们常常在岗位上消极怠工。(118)贝德士:《在纽约的演讲记录》(1941年6月25日),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第58页。对于多数人而言,这种生存策略可能是暂时的妥协。
事实上,“苟活”本身并没有多少可以谴责的地方,对生命的眷恋本身也并不意味着罪恶。相反,人在战争状态下卑微而强烈的生存渴望才是构成情感共同体的基础。在这些昏暗的时日里,难民们遭受了太多的凌辱和灾难,他们表现出了异常的忍耐力。战争强化了难民们的情感融合,促使他们团结起来应对共同的危险。诚如西方人士所观察到的:“未来如何?近期的未来绝不会是光明的,但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最终必将赢得胜利。”(119)《费吴生日记》(1937年12月10日—1938年1月下旬),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第117—118页。
在沦陷的南京城内,个体的不幸与民族、国家的苦难命运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加强了民族情感的凝结。如同袁一丹在对北平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在民众基本生活秩序遭到破坏,自身或家人受到切身的威胁,才会摆脱看客的位置,认识到沦陷与个人的关系。(120)袁一丹:《北平沦陷的瞬间——从“水平轴”的视野》,《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日军的入侵使得难民认识到个人的安危与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国家军事的失败导致难民的原本的生活遭到破坏。一位覃姓难民叹息道,“这回我所受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四五个月在死与恐怖中生活着,感不到一点祖国的温软”。(121)林娜:《血泪话金陵》,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第572页。日军暴行下的恐惧与异族统治下的屈辱共存,使难民们内心滋生着对侵略者的敌意,认识到民族国家政权的意义。难民的民族情感由此产生。值得注意的是,民族情感不同于民族主义,它并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向和理论形态,更多是一种由共同的遭遇所唤起的,基于地域、语言等方面的认同而形成的带有某种自卫或攻击性的情感倾向。这种民族情感并不能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反抗行为,在沦陷区的特殊背景下,一般的难民首先考虑的是仍是生存。而出于生存目的而选择事敌的难民,也并非完全丧失民族情感。相反,沦陷区内的生存危机使得难民从敌我的区分中开始逐渐明白“中国人”的含义。对家园与和平生活的向往使他们形成一种情感依恋,部分难民将个人身份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民族情感的潜流正在默默汇聚。
四、结语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改变了难民们的命运,给难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冲击。无论是南京沦陷前的频繁空袭,还是南京沦陷后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都让难民们陷入恐惧。鲍曼(Zygmunt Bauman)在对纳粹大屠杀的研究中提到,在一个残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会变得惶恐不安,相互猜疑,离群索居,他们只能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逆来顺受,甚至成为“生存的木偶”。(122)[英]鲍曼著,杨渝东、史建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8—10页;郭景萍:《情感社会学:理论·历史·现实》,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2页。鲍曼观察到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下,恐惧抑制了个体的情感表达,人们基于生存的本能而被迫对暴力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鲍曼忽略了这种集体的静默有可能只是一种假象。实际上,服从表象下也包含着对强权情感上的抵触和疏离。日军的暴行打破了留守南京难民的侥幸心理,使得他们认识到日军的丑恶面目,难民们的仇日情绪不断增强。
难民们都经历了日军的暴行,境遇相同,情感相通。在人道主义的感召下,难民基于生存而相互帮助,和衷共济,共同抵制日军的暴行,形成了情感共同体。同时,一般老百姓“虽没有学问,却懂得人与奴之差别”(123)茅盾:《人权运动就是加强抗战力量》,《茅盾全集》第16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页。,难民们感受到,由于国家军队的失败,才导致日军暴行的泛滥,自身的生命受到威胁,尊严遭到践踏,生活受到破坏。国家的缺位,难民和西方人士境遇的不同,使得难民们认识到国家的兴亡与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仇日情绪、共同体情感和国家意识,难民们的民族情感有所增强。不过,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处于恶劣生存环境下的难民们的民族情感表达受到限制。趋利避害是人的生存本能,对于难民行为和情感的分析,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境,既不能单纯以难民是否直接作出反抗为判断标准,也不能刻意夸大难民群体的民族情感。一方面,难民们选择向西方人士报告日军的罪行,传播中国军队即将收复南京、游击队进城、帮会武装打击日军等流言,这些行为既是难民的生存策略,也真实流露出难民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南京难民所形成的民族情感更多的是基于个人生存层面需求的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并不完全是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想象的共同体”,若要产生真正的、具有强大社会凝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则需要长期的制度、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支持。
南京大屠杀在战时不仅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抗日决心,还使西方各国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今日,南京大屠杀不但是民族的创伤记忆,而且是人类的苦难记忆,既承担着凝聚民族情感的功能,又有反思战争、维护和平的功能。
——聚焦各国难民儿童生存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