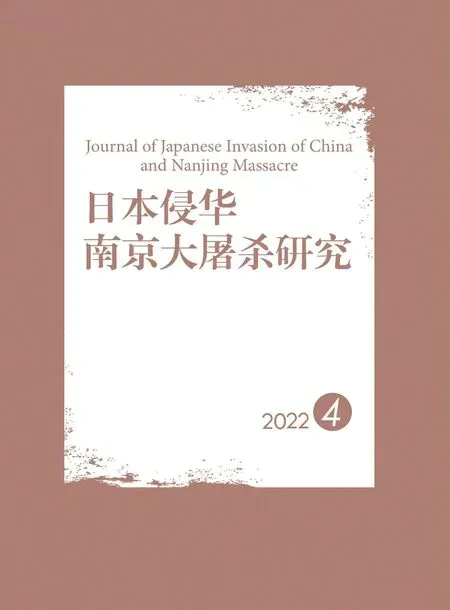日据台湾初期的军用“台湾语”教科书
——以《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台湾语》为中心
崔 蒙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为从语言上策应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野心,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日本编写了大量军用汉语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绝大多数都是北京官话教科书,汉语方言教科书相对较少。而在1895年侵占台湾以后,日本为了消除闽南方言带来的语言障碍,便于实施殖民统治,开始对所谓“台湾语”(即台湾闽南话)的学习和研究,编写了不少教科书和辞典。“台湾语”教科书的数量因此迅速增加,在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中占有不小的比例。
国内学界对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1)如寇振峰:《甲午战争与日本军用汉语热探究——以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出版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1期;王宇宏、吴长安:《〈亚细亚言语集〉与日本近现代军用汉语教科书》,《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寇振锋:《甲午战争时期日军〈兵要支那语〉探究》,《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3期;王宇宏:《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1867—1942)军事词汇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寇振峰:《甲午战争时期日军参谋本部编〈日清会话〉探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0年第1期等。,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北京官话的汉语教科书,对汉语方言教科书少有涉及。日本学者对“台湾语”教科书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内容却相对全面,包括资料整理、历史背景分析、辞典编纂、语言政策等方面(2)如園田博文『台湾の日本語教科書と中国語会話書の研究——昭和20年まで』、武蔵野書院、2021年;富田哲「日本統治時代初期の台湾総督府による「台湾語」の創出」、『国際開発研究フォーラム=Forum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11号、1999年3月、155-166頁;樋口靖「領台初期の台湾語教学(1)」、『文教大学文学部紀要』25-2号、2012年3月、23-40頁;村上嘉英「旧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言語政策の一考察」、『天理大学学報』36号、1985年3月、21-35頁;村上嘉英「日本人の台湾語学習と研究の事始め」、『中国文化研究』21号、2004年、21-56頁等。,但对军用教科书及其性质的论述较少,鲜有对单本教科书或某一时期教科书的深入分析。
本文以《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和《台湾语》两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为研究对象,梳理日据台湾初期日本对台湾民众语言“同化”政策及学习“台湾语”的背景,介绍这两本教科书的编写情况,分析其语言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归纳日据台湾初期日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的性质,并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语言政策加以讨论。
一、日据初期日本殖民者的“台湾语”学习
日本殖民语言政策有其独特的历史根源。明治维新前,日本各藩彼此封闭隔绝、方言不通,当时的日本人大多只有藩国意识而没有国家意识,更没有“日本人”的意识。(3)张维佳、崔蒙:《日本20世纪国语政策的嬗变及其背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4年第2期。明治维新后,日本结束幕府统治,由封建国家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并很快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统一的民族语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身份认同作用。许多日本学者就确立“国语”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身为国语学者和文部省官员的上田万年主张以中央集权的方式统一语言(4)张维佳、崔蒙:《日本20世纪国语政策的嬗变及其背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4年第2期。,认为可以通过“国语”塑造“国民”与“国民精神”,最终形成“国家”。上田赋予“国语”极高的政治意义,认为“日本国语,正可谓日本人精神之血液”(5)亀井孝、大藤時彦、山田俊雄编『日本語の歴史6·新しい国語への歩み』、平凡社、1976年、204頁。,其论文集《为了国语》的扉页上也写着:“国语乃帝室之藩屏,国语乃国民之血液。”(6)亀井孝、大藤時彦、山田俊雄编『日本語の歴史6·新しい国語への歩み』、31頁。上田的主张符合当时日本高涨的国民意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较大的影响力,其在日本的学校教育和殖民地语言政策中都有所体现。
在侵占台湾之前,日本并没有一块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台湾就成为日本实行殖民统治和殖民语言政策的“试验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机构——台湾总督府第一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的理念与上田万年可谓一脉相承,主张通过教育同化台湾民众,使之成为“日本国民”,而语言同化是重要的路径之一。伊泽赴台后在台湾开办“国语”传习所,之后又建立“国语”学校,向台湾民众教授日语。伊泽在台的时间虽然不满两年,但其“国语”教育政策却贯穿于整个日本据台湾时期。随着“国语”教育的强制推行,台湾的日语普及率逐渐增加,在日据后期的“皇民化运动”中,台湾民众更被迫放弃汉语,使用日语。
伊泽修二虽然带着实践“国语教育”的“雄心”赴台,却没有了解台湾的语言状况并做好充分准备。也许不仅是伊泽,当时大多数日本官员和学者都错误地判断了台湾的语言状况。曾有去过台湾的日本测量师表示,“在熟蕃和中国人居住的商业地区,会汉语的日本人可以交流无碍,如果不会汉语,也可以笔谈沟通”。(7)樋口靖「領台初期の台湾語教学(1)」、『文教大学文学部紀要』25-2号、2012年3月、30-31頁。这里所说的“汉语”指的应当是北京官话。然而在当时的台湾,会说北京官话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占比极少。
台湾的人口构成并不复杂,除少部分被统称为“高山族”的土著居民之外,日本侵占台湾之前的人口主要是明清两代由大陆渡海迁入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广东这两个沿海省份,据统计,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福建泉州、漳州,人数约占大陆汉族移民的80%,还有一部分来自广东的潮汕、惠州等地,人数约占15%。(8)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页。在汉族移民来源地中,福建泉州、漳州和广东潮汕地区使用闽南方言,广东惠州则主要使用客家话。整体来看,当时台湾绝大多数汉族人都使用闽南方言(9)闽南方言主要使用于厦门、漳州和泉州等地,参见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音字汇》,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154页;李如龙:《闽南方言语法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163、193—208页。。
在汉语诸多方言中,闽南方言保留了入声、-m韵尾等中古汉语的语音特征,韵母和声调尤为复杂,词汇也与北京官话有所差异。由于对闽南方言毫无准备,日本军队和官员在台湾遇到了很大的语言障碍。伊泽修二带着100多名翻译随行赴台,但抵台后却发现“历来熟稔官话底翻译官之属亦几乎不能发挥其作用”。(10)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台湾总督府中的9名翻译官中没有一人能听懂台湾当地话,与当地人的沟通往往需要通过北京官话或英语进行二次翻译。(11)樋口靖「領台初期の台湾語教学(1)」、『文教大学文学部紀要』25-2号、2012年3月、32頁。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深切地感到:“在台官吏若不通晓台湾话,就不能直接接触本岛人,履行职务就有很多不便。不仅如此,还会缺乏与台湾民众的意志沟通,并在施政上感到极大的障碍。”(12)村上嘉英「旧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言語政策の一考察」、『天理大学学報』36号、1985年3月、23頁。在此情况下,尽管日本欲通过“国语”教育同化台湾民众,但在侵占台湾初期,日本人不得不学习“台湾语”。
为了便于与台湾当地人沟通,台湾总督府迅速组织日本人学习“台湾语”。从1895年12月起,日本殖民当局开设“台湾语讲习所”,供日本总督府人员学习。同时,培养日语教师的“国语学校师范部”也设有“台湾语”课程,课时占到每周总课时的三分之一。(13)村上嘉英「旧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言語政策の一考察」、『天理大学学報』36号、1985年3月、24頁。为实行殖民统治,学习“台湾语”的群体主要是日本军队和警察。1898年成立的“警察官及司狱官练习所”即设有“台湾语”课程,台湾总督府也编纂了多部军用教科书。
关于“台湾语”一词,在此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自侵占台湾以来,日本就以“台湾语”指称台湾民众普遍使用的闽南方言。日据时期编纂出版的闽南方言教科书、研究专著和辞典也大多冠以“台湾语”或“日台”等名称。即使现在,日本研究者仍然沿用了这一名称,但这一称谓显然并不恰当。从汉语方言分区来看,台湾汉族人口使用的闽南方言属于汉语闽南方言泉彰片,是汉语闽南方言的典型代表,将其称为“台湾语”是极不准确的,准确的称谓应该为“台湾闽南话”。
“台湾语”这一名称的使用显然带有政治目的。如前所述,日本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认识到统一语言的重要作用,“如果可以证明某一社团语言不仅区别于相邻社团的语言,而且具有一些内部融合的因素,那么,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民族的标志”。(14)苏·赖特著,陈新仁译:《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1页。日本殖民统治者无视汉语方言这一事实,借由“台湾语”这一名称刻意割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语言文化纽带,使台湾“孤悬海上”,再通过强制推行日语和“皇民化运动”,将台湾彻底日本化,并最终实现长期侵占中国台湾的目的。
二、日据初期的两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
日本侵占台湾后,在短时间内编纂了多部“台湾语”教科书。日本学者很重视对这些教科书的整理和研究。2006年,日本学者中田敏夫在论文中以图片形式介绍了两本新发现的日据台湾初期的“台湾语”教科书——《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和《台湾语》,并简要介绍了这两本教科书和编纂者的基本情况。(15)中田敏夫「故折井秀治氏蔵台湾統治初期言語資料『軍隊憲兵用台湾語』『台湾語』——資料並びに解説」、『国語国文学報』第64巻、2006年3月、81—114頁。本文拟就这两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的编纂体例、编纂者、教学对象等进行论述,并分析两本教科书的语言特点。
关于教材编纂体例,上述两本教科书均为手写体,绝大部分字迹都可以清晰辨识。《军队宪兵用台湾语》的封面右上部注明了发行时间:明治二十八年九月上旬,即1895年9月上旬,而《台湾语》则没有注明发行时间。
两本教科书在体例编排上颇为相似。《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分为单词和会话两部分,《台湾语》分为“普通会话”和“散语”两部分,也都采用汉语、日语对照形式。页面上半部分以汉字书写台湾方言词句,下半部分以日语书写对应释义。汉语汉字旁以日语片假名标注读音。两本教科书中绝大多数汉语汉字都标有片假名注音,而《台湾语》的标注比例更高,几乎所有汉语汉字都有注音。
关于两本教科书的编纂者,《军队宪兵用台湾语》没有标明编纂者,仅在封面左下角写有“微笑生平井”,《台湾语》则清晰标明了编纂者——其封面右侧写有“通译官平井数马编纂”,封面左下角还有签名“平井幸三郎”,应为该本教科书的所有者。据中田敏夫考证,“微笑生平井”即平井数马,是宪兵队长平井幸三郎的弟弟,中田认为这两本教科书极有可能为同一人编纂,即平井数马。(16)中田敏夫「故折井秀治氏蔵台湾統治初期言語資料『軍隊憲兵用台湾語』『台湾語』——資料並びに解説」、『国語国文学報』第64巻、2006年3月、83頁。本文暂且采用中田敏夫的判断,以平井数马为两本“台湾语”教科书的编纂者。
关于教材的使用对象,正如其名称所示,《军队宪兵用台湾语》是一本专门为军队中的宪兵编写的台湾闽南话教科书。《台湾语》虽然看似是一本通用教科书,但其封底右侧写有“台湾宪兵队第六分队”字样,可见该教科书同样是面向宪兵的。
这两本教科书完全是为军队和军事活动编写的,其内容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台湾语》的内容相对生活化,以“讲价”“打扫”等日常用语为主,但也包含了少部分军事活动用语,而在《军队宪兵用台湾语》中,日常用语占比极少,绝大多数词汇和句子都与军事活动有关,如军备物品、军队官职、侦察用语、询问用语等,可以说是一本与军事密切相关的专门教科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教科书中多使用台湾地名,其语句也表现出竹林、河流等台湾自然地理特点。例如:
我不识台湾话(我不懂台湾话)
这处到东港几里路(这里到东港有几里路)
路里有竹围(路上有竹林)
我是鹿港来(我从鹿港来)
我是新竹人
关于这两本教科书的使用顺序,笔者认为《台湾语》极有可能是《军队宪兵用台湾语》的前置教材。首先,从汉语汉字注音情况来看,一些《台湾语》中注音过的字词在《军队宪兵用台湾语》中再次出现时,已不再注音标记,说明学习者已经掌握了部分汉语汉字的发音。其次,在内容编排方面,《台湾语》以日常生活为主,辅以少量军事用语,而《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则以军事用语为主。这种内容设计也符合语言教学先易后难、先普遍再专门的规律。
综合考察两本教科书的汉字、注音等内容后,笔者发现《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和《台湾语》在语言方面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首先,具有鲜明的闽南方言口语特点。通过与闽南方言的对照,可以发现这两本教科书不仅反映了闽南方言的语言特点,而且具有浓厚的口语色彩。
就音系而言,两本教科书中绝大多数汉语汉字注音都与厦门话音系高度一致,只有个别文字采用漳州话发音。从声母看,其全部采用日语片假名注音。日语片假名中カ、タ、サ三行中的塞音、塞擦音不区分送气和不送气,不能完全对应闽南方言中的送气音和不送气音,但这两本教科书中没有使用任何附加符号加以区分,而以ガ行对应鼻浊音声母,以パ行对应双唇清塞音。从韵母看,其同样采用日语片假名注音,单韵母以ア、イ、ウ、エ、オ标注;复韵母中ia、iu、io以ヤ、ユ、ヨ标注,其他复韵母均按照实际读音以多个假名组合标注。入声韵尾-p、-t、-k以プ、ツ、ク标注,喉塞音韵尾以ツ标注,鼻韵尾-m和独立鼻辅音音节以ム标注,前后鼻音韵尾均以ン标注,鼻化韵音节一般有特殊标记,即在第一个假名右下角标注小写的ン。从声调看,尽管闽南方言有七个声调,但这两本教科书都没有使用任何附加的声调标记,更没有涉及轻声和连读变调问题。从文白异读看,除少部分军事用语(如“前攻后夹”)、军队官职(如“把总”)等词语使用文读音,其他军事用语和生活用语基本为白读音。
就词汇句法而言,两本教科书中不仅出现了“厝”(房屋)、“无采工”(没有用)等闽南方言的特有词汇,其他词汇也反映出闽南方言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词尾“仔”:顽小仔(笨蛋);也然仔(有人吗)
句末语气词“无”:溪有桥无(河上有桥吗);在这社内有好的粮草无(这村子里有好粮草吗)
“无……无……”并列四字格:无礼无数(无理之人);无法无度(不方便)
能愿动词“会晓得”:我讲甚么你会晓得否(我说什么你明白吗)
能愿动词“敢”:就会死我亦未敢讲(就算死我也不说)
连词“共”:共阮讲老实(对我们说实话)
述补结构:这处扫去清洁(这里打扫干净)
另外,有些词句明显受到北京官话的影响,其注音对应的却是表示同样含义的闽南方言口语发音,例如:
写下这张纸(シャ ロ- チッ ティュン ツゥア)
这所叫甚么(チレ- キョウ シ ミ)
是如此不是(シ アネ ム シ)
其中“张(ティュン)”“这所(チレ-)”“如此(アネ)” 的注音完全是闽南方言口语发音,这种注音方法其实已经相当于日语中的训读了。
其次,含有大量军事用语,面向军事活动。日据台湾初期,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遭到日本殖民者的强力镇压,岛内战火时有发生。日军要在军事活动中获得信息以及与台湾民众沟通,就需要掌握军事用语中的台湾闽南话。两本教科书的内容都包括了军事用语,而《军队宪兵用台湾语》更涵盖了军事活动的诸多方面。其中有较为全面的军队官职,如兵丁、千总、守备、游击、协台、镇台、把总、管带、提督、统带、元帅、撑号、报马/探马等,还有武器和军用物品词语,如火药、天炮子、剑、马鞍、马踏镫、铁马蹄、帅旗、量天尺、枪尾刀等,以及一定数量的军营活动和战斗词语,如前攻后夹、叠兵、退围、交战、围城、攻破城墙、查营、排队、巡查等。两本教科书中还有大量的侦察用语,如“有步兵及马兵无”“讲这处有地雷火炮无”“这处有甚么粮草”“统带官是何人”“他占在溪里那一边岸”(他们在溪的哪一边)、“有几多兵在彼处”“军兵在何处”“你要去甚么所在”等等,以及威胁、命令的话语,如“漏出军机你着受军法警戒”“着缴你之军器”“你有归降否”“若是你想走你会被枪打死”等等。从这些军事用语不难看出,当时台湾的抗日力量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相当的武器装备,同时也反映出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侵略本质和对台湾民众的压迫。
再次,具有强烈的殖民统治色彩。日本侵占台湾后,建立了军政一体的总督专制殖民统治体系,对台湾民众实行严苛的管控,台湾民众生活在高压和歧视之下,备受欺辱,这在两本教科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除军事用语外,日常生活用语也大多是命令、威胁等语气,或者是斥责之语,如“你若讲白贼你之世命难得保”(你如果说谎话就性命不保)、“你若照本傚你就能允当”(你老实干活就好)、“赶紧做不可怠惰、典你打”(赶紧干不可怠惰,否则打你)、“你若不须趁阮就要准犯人办你”(如果你违抗命令就抓你)等等。而一些所谓“恩威并施”的语句,则反映出日本殖民统治者营造“慈善”形象、收买台湾民众的活动,如“我与你钱银”“做工艺有钱与你”“请你如此做”“日本之君子人不曾讲白贼话”(日本的君子不说谎话)等等。
三、日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的性质
全面分析两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可以看出日据台湾初期日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的性质,即日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教科书,而是为了消除语言障碍、实行殖民统治而匆忙编写的速成会话手册。正是由于这一性质,使日据台湾初期的日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显得相对粗糙,两本教科书存在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一,教科书中没有任何声调标注。闽南方言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声调系统相对复杂,共有七个声调,但两本教科书中没有任何声调标记,其原因在于日本侵占台湾初期对当地语言的迫切需求。为镇压台湾民众的抗日斗争,教科书只需满足基本的军事和日常沟通需求。由于日语是无声调语言,日本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学会声调,于是两本教科书都忽略了声调,只记录对方能听懂的闽南方言发音。
第二,两本教科书在汉语汉字使用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同一汉字在不同词语中注音不同,如“攻”在“攻营”中注音为コゥン,有介音,而在“强攻强夹”中注音为コン,没有介音;二是汉语汉字存在异体字写法,如“做”有几处写为“傚”;三是同一闽南方言词汇存在不同写法,如分别使用汉字“居”和“息”表示“休息”之意,但从其注音“ヒョッ”判断,更接近“歇”的白读音;四是使用同音异字,如将“性命”写为“世命”;五是存在较为明显的日语训读写法,如将指示代词“这”写作“此”等等。樋口靖认为这是因为当时日语汉字的用法较为随意,日本人在学习和研究“台湾话”时延续了这一习惯。(17)樋口靖「日治時代台語漢字用法」、『文教大学文学部紀要』11—01号、1997年、第1—2頁。笔者认为,日语汉字的影响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也可能是闽南方言、北京官话和日语相互影响的结果。
随着日本对台湾闽南话研究的深入和多本“日台”辞典的编纂,与这两本教科书相比,以后的“台湾语”教科书要完善许多,也更符合语言教科书的特点,当然也不会再出现上述问题。
从整体看,日据台湾初期日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作为闽南方言和日语的对译材料也具有一定的方言文献价值。同时,据台初期日本殖民者对“台湾语”的学习,也让我们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语言政策有了新的认识。以色列学者博纳德·斯波斯基指出:“‘占领者的语言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显著的办法,一是给士兵教授被占领地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二是强迫被占领的人们学习占领者的语言……但这两种办法都代价昂贵,而且需要以长期占领为前提。”(18)博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语言管理》,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77页。一直以来,研究者普遍认为日本在台湾采取的殖民语言政策是强迫台湾民众学习日语,以实现语言同化。但在侵占台湾初期,日本殖民者实际上是双管齐下的,一方面日本军队、警察等群体学习“台湾话”,另一方面也在台湾强制推行日语。
从本质上说,日本殖民者学习“台湾语”是为了便于殖民统治。在台湾,日本殖民者始终将推行日语作为重点,对此他们毫不遮掩。1901年,时任台湾总督府参事官长的石塚英藏在国语研究会做了题为《新领土与国语教育》的演讲,其中提到“内地人(日本人——引者注)无论官民都应该学习土语,这虽是当然的,但毕竟只是一时的手段而已,长远的目的是在台湾普及我国国语”。(19)村上嘉英「旧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言語政策の一考察」、『天理大学学報』36号、1985年3月、24頁。随着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逐步稳定和日语在岛内逐渐普及,“台湾语”教学也让步于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国语”教育。尽管需要直接接触台湾民众的日本警察还保持了一定数量的“台湾语”学习课程,但“国语学校师范部”所设的“台湾语”课程的课时却逐渐减少,而到日据台湾中期更成为选修课。(20)村上嘉英「旧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言語政策の一考察」、『天理大学学報』36号、1985年3月、24頁。到了日据台湾后期,日本殖民统治者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强制台湾民众在公共场所和日常生活中必须使用日语,而面向日本人的“台湾语”教学自然也就不再提及了。
结 语
日本侵占台湾初期,日本殖民统治者不仅学习“台湾语”,迅速编写了多部“台湾语”教科书,还开始对台湾闽南话进行调查,并陆续编纂了多部台湾闽南话-日语辞典,在日据中后期也出版了一些台湾闽南话会话读本和研究专著。这在客观上记录了当时的台湾闽南话,为后来的闽南方言研究提供了资料。
然而日本殖民者对台湾闽南话的学习和研究,始终是在实施殖民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殖民统治相对稳定后,日本借助高压和军事手段,强制要求台湾民众转用日语,试图在语言上割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让台湾彻底成为日本“领土”。但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强制推行日语,仍然无法割断台湾民众的母语情感。1945年台湾光复后,很快便清除了日语的影响,闽台两地的方言虽然存在些许词汇差异,但依然沟通无碍。时至今日,语言在群体身份构建与心理、文化认同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仍然值得深入思考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