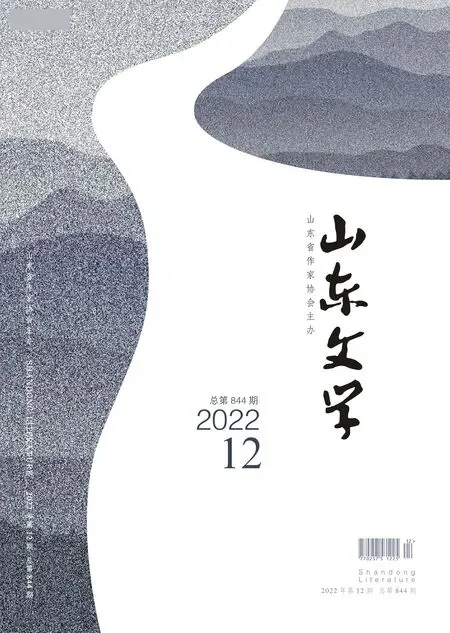蒿子的成人礼
吴玉龙
十八岁那年,蒿子决定和过去做个了断。他认为自己已长大成人再也不能过以往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按照一个很诗意的说法,就是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就像那个说书的瞎子说的那样:“从蒺藜上滚过去,做个硬人。”
入 伙
蒿子喜欢听书,那是他唯一的精神生活。为此,他曾着魔般跟着一个说书的瞎子四处云游。书里的故事开启了他最初的心智,为他打通了与现实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书中的人物他最心仪刘邦。同样出身于卑微、贫穷的家庭,刘邦从一个爱玩带点侠气的懵懂少年起步,最终开创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汉王朝。他渐渐明白了那个瞎子为何一说起刘邦就慷慨激昂,热泪长流。他们都对刘邦从街头混混脱胎为千古一帝的传奇经历心驰神往。蒿子一直牢牢地记着说书瞎子送给他的那句话—从蒺藜上滚过去,做个硬人。
受此启发,蒿子也开始做一个“涉足行伍,崛起阡陌”的千秋大梦。离蒿子家乡不远就是水泊梁山,此地尚武之风盛行。众多的年轻人无所事事,以刀枪剑戟消解过剩的荷尔蒙,彰显自己的存在与血性。就和当年的梁山好汉一样,蒿子决定入伙。其实入伙也是他唯一的出路。在他们那里,入伙相当于成人礼,男孩子没有入伙的经历就不能算是男人。在乡人看来,入伙也有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意思,通常一个人瞧不起另一个人总会说:“你到伙里混几天试试?”
但到底心里没底,蒿子去找彩凤商议。彩凤比蒿子大几岁,是村里仅有的愿意和蒿子亲近的人。说来彩凤这人也很隔路,村里那么多少年,她偏偏和蒿子走得近乎。她在村里开了个剃头铺子,平时挣个毛儿八角的,手头较活泛,傲得不得了。但只要是蒿子来剃头,她分文不取,并且还给蒿子剃得格外仔细、利索。别人都不理解,说彩凤对蒿子好简直就是鬼迷心窍。彩凤才不管这些,只有她自己知道为啥喜欢蒿子。与其他动辄剑拔弩张的少年不同,蒿子低沉得近乎卑微,特别是他那标志性的忧伤、落寞的表情让她着迷。彩凤对蒿子的想法深感忧虑,她说:“你走路都怕踩死蚂蚁,怕是蹚不了伙里的浑水。”蒿子不以为然,说:“不下水哪知道深浅。”其实,彩凤心里也赞成蒿子去闯闯,她一再提醒他要多加小心。
那时候,村里的团伙被蛤蟆统领着,自称“封神派”。寓意他们功高盖世,将来必升天封神。团伙里皆是鸡鸣狗盗之徒,啥货色都有。但自诩替天行道、行侠仗义。蒿子自有主意,自己入伙只是“卧薪尝胆”,不是“落草为寇”,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按说,蒿子与蛤蟆是死对头。两家曾因争夺土地反目成仇。他们的田地毗邻,今年这家多种一垅,明年那家多占一畦,渐渐分不清地界,便起了纷争,打得不可开交。蒿子家人多势重,把蛤蟆家打得落花流水,并占有了争议土地。蛤蟆家不甘失败,伺机报复,苦于没有机会。巧的是,蒿子却主动送上门来。
蒿子硬着头皮去投奔蛤蟆。蛤蟆长了满脸的疥疮,疙疙瘩瘩坑坑洼洼,像是在娘胎里就掉进了炉灰渣。也不知有啥病,肚子一鼓一鼓的,像个漏气的风箱。本来这称呼前头还有个“癞”字,可没人敢这么叫他。蒿子找到蛤蟆时,蛤蟆很是不屑,都不正眼瞧他一下。蒿子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并向蛤蟆表达了臣服的强烈愿望。
蛤蟆打着哈哈说:“‘封神派’里都是纯正的贫农子弟,你奸商后代算哪根葱呢?”
蒿子一再坚持,又说了许多类似于“粉身碎骨”“当牛做马”那样表决心的话。这些话都是他从说书的瞎子那里学来的。蛤蟆似乎被感动了,想了想说:“入伙可以,但得递投名状。”
蒿子心里不禁一紧:“啥叫投名状?”
蛤蟆看他紧张兮兮的样子,轻蔑地一笑:“生瓜蛋子!”又说,“你要真想入伙,就得干点事表示你的决心和忠诚。”
蒿子偷偷地松了一口气,只要不让他出钱,让干啥都行。他说:“不就是想考验一下我嘛,考验吧,考验吧,您尽管考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俺也愿意。”蛤蟆满意地一笑,眉头一皱动起了坏心眼儿。他高深莫测地说:“你知道少林寺吧?和尚入门学艺都要先挨一记“杀威棒”,在咱这里皮肉之苦就免了,给你安排点轻生活儿,你去给我把大鸭脖喊来,你要是能把这件事干利索了,咱们以后就是兄弟了。”蒿子想这事可太简单了,不就是喊个人嘛。他问:“大鸭脖是谁?”蛤蟆说:“邻村的,正在咱村串亲戚。”蒿子又问:“男的还是女的?”蛤蟆很不耐烦,挥挥手说:“你话可真多,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滚蛋。”蒿子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有点太不识相:问这么多干嘛,怎么说蛤蟆也带领着一支队伍呢,是队伍肯定就会有机密的。
蒿子大模大样地去找大鸭脖了,带着一点赴汤蹈火的自豪与悲壮。这是他的第一次任务,他一定要圆满完成露露脸儿。但蒿子不知道大鸭脖是谁家的亲戚,只好在大街上扯着嗓子乱喊。蛤蟆带着众喽啰跟在后面看热闹,同时监视着蒿子的一举一动。蒿子乱喊着走过了大半个村子,嗓子都要冒烟了,也没见到大鸭脖的影儿,有点泄气。他正想找户人家讨碗水喝,却听到一声粗重的怒喝如天雷滚滚:“谁他娘的敢喊姑奶奶的坏名字!”蒿子扭头看见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从一座大门里旋风般掠出,她脖子长长的,鸭子般朝前伸着。好一个李逵式的亮相!
蒿子原以为大鸭脖是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少年,无意间却调戏了一个比他大好多的妇女,非常紧张。他口不择言地说:“不是我叫的,不是我叫的。”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等于不打自招了。大鸭脖逼近他,两眼冒火,一把抓住领子把他提溜得老高,冷笑着说:“不敢承认了吧,真是软蛋啊。就你这个样,还敢出来混呢。”蒿子被她勒住脖子都快憋死了,可怜巴巴地看着蛤蟆,希望他带着喽啰一哄而上把大鸭脖掀翻在地,最好能扒掉她的裤子。可蛤蟆根本就没有搭救蒿子的意思,甚至还跳着脚儿叫好,挑唆大鸭脖弄死他。蒿子肺都气炸了,真他娘的不讲义气,干脆把他们出卖得了。蒿子朝他们胡乱一指,对大鸭脖说:“是他们让我叫的。”也许大鸭脖看蒿子太面了,觉得没劲,便放过了他,又冷笑着一把抓住旁边的一个喽啰,问:“你也叫了吧?”那小子都快吓尿了,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没叫。”他又慌乱地一指,继续无耻地嫁祸于人。等大鸭脖试图去抓另一个人的时候,蛤蟆却发出一声怪异的唿哨,一干人马立即没命地溃逃。大鸭脖站在那里,两手卡腰,厉声喝道:“都他娘的别跑,要是被姑奶奶追上,就砸断你们的狗腿。”一帮人就真的定在了那里,像被施了魔法。一个个哭丧着脸儿等待着大鸭脖的发落,就连平时神气活现的蛤蟆也瘪了,成了一只泄了气的癞蛤蟆,脸上贴着一层死灰色,央求道:“高抬贵手吧,大家都是在道上混的。”大鸭脖看着这么多人都俯首帖耳的,感觉太没劲了。她晃着拳头示威道:“逃过了初一,逃不过十五,下次谁还敢乱喊,就把他的嘴巴扯烂。龟孙子们都记住喽,老娘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苟名雄,叫苟雄。”说完便探着长长的脖子趾高气扬地走了。
后来,蒿子才知道,大鸭脖她爹年轻时是这一带的地头蛇,没人敢惹。
蒿子出师不利,战战兢兢地等着蛤蟆的惩处。出人意料的是,蛤蟆竟和颜悦色地说:“以后你就是咱伙里的人了。”蒿子大喜过望,连蛤蟆脸上的奸笑都忽视了。
盗 油
就这样,蒿子混入了“封神派”的队伍。以重用的名义,蛤蟆不断向他分派很多高难度的任务。蒿子则使出浑身的解数让他满意。每完成一项任务,蒿子就认为又证明了自己,又向高升迈进了一步,沾沾自喜。
蛤蟆是个阴险的家伙,他是在用杀人不见血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譬如,他想吃鱼,就命令蒿子到水深流急的河里去摸鱼,说那里的鱼最好吃。还给蒿子戴高帽儿,说伙里数他水性最好,并送他一个“浪里白条”的浑号。蒿子对他的用意自然心知肚明,但毕竟有了更多露脸的机会,别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鄙视他,也算有所斩获。
于是,蒿子豁出命去表现自己,出尽了风头。他虽艺不高但胆儿肥,掏鸟窝的时候,他会爬到树的最高处那些细得几乎不能承载他的树枝上,在命悬一线的摇摇欲坠中掏回几个鸟蛋。要是被鸟儿碰上,必会顽强抵抗,代价则更加惨重,被啄得遍体鳞伤,眼睛都差点被鸟儿啄瞎。再如,每年夏天,河里都发洪水,蒿子浮沉于惊涛骇浪,不顾一切地捞回从上游冲下来的西瓜,去孝敬蛤蟆。他的肚皮经常被水下的树枝划出纵横交错的血道子,还差点被隐藏的玻璃碴子割去鸡鸡,可最后连舔西瓜皮的份儿都没有。蛤蟆每每吃得心满意足,不疼不痒地表扬蒿子几句。蒿子并不以为意,他认为自己受到的“重用”越多,翻身的机会就越多,出人头地的希望就更大。他甚至暗下决心,总有一天会把蛤蟆打翻在地并踩上一脚,到时让他把吃进去的全都吐出来。
蒿子的付出似乎有了回报,蛤蟆让蒿子做了他的贴身随从。这个角色俗话叫跟屁虫,就是整日里倒背着手跟在蛤蟆腚后头狐假虎威。蒿子一厢情愿地认为诡计多端的蛤蟆这次失算了,这是在养虎为患。他阴险地想,自己都与蛤蟆“贴身”了,“上位”已指日可待。
一天,蛤蟆的队伍正在村头演练,远远的一个黑点移动过来。蛤蟆说:“有情况。”那黑点越来越近,终于能看得清楚。这是一个和蒿子仿佛年纪的少年,手里提着只油罐子,东张西望地走着,如鬼子进村。蛤蟆认得他是东村的金刚,也是一个孩子王。两个村子向来都是死对头,历史上积怨颇深,曾多次发生械斗,蛤蟆和金刚在械斗中曾有正面冲突,两人不共戴天。
蛤蟆说:“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钱,不能让这小子过来。”蒿子主动请缨,要大显身手。一个叫磨眼的喽啰也站了出来。两人一直在暗中较劲,今天刚好碰上一决高下的机会。蛤蟆命令两人向金刚投掷石块。众喽啰蚂蚁搬家般一会儿就攒起了一个石头堆。蒿子临危受命,用上浑身的力气抡圆了胳膊左右开弓,石块密集地飞出,在金刚的周边蹦蹦跳跳。金刚突遇险情,呆若木鸡,双手捂住脑袋,那只油罐子完全暴露在蒿子的打击范围之内。突然,一阵刺耳的破碎声传来,那只油罐子被击中了,四分五裂地摔在地上。蛤蟆及众喽啰欢呼雀跃,蒿子得意洋洋地看着磨眼,他终于赢了他一回。
金刚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还疯了似的打了几个滚儿,其哀痛之惨状像是他被打碎了一般。蒿子吓坏了,对蛤蟆说:“坏醋了,打破了他的油罐子,怎么办?”蛤蟆这时也觉得事情很棘手,他是个能惹不能兜的主儿,这时候又想做甩手掌柜了。蒿子急得跳脚,催他快想办法。他烦躁起来,一推六二五:“是你打破的,管我屁事,你自己寻门去。”
这时候,金刚已从地上爬起来没命地奔来,他两眼通红,如孤注一掷的困兽,张牙舞爪,随时准备攻击他的敌人。他厉声喝问:“娘的,刚才谁扔的石头。”蒿子早被他狰狞的表情吓坏了,身子一缩往蛤蟆身后藏去。谁知蛤蟆却一把将他拉出来卖给了金刚,说:“不管我事,都是这小子干的。”金刚家势力很大,是打个喷嚏方圆几里都能感冒的那种主儿,蛤蟆权衡利弊当然是舍卒保帅。蒿子又向四周睃睃,向别人求助,几个小喽啰早就吓破了胆儿,远远躲开去。蒿子意识到自己再次陷入孤立,只好惊恐万分地向金刚道歉。金刚两眼冒火,咬牙切齿地说:“你就是喊我爹也没用,老老实实赔我一个新的油罐子还得带上半罐油,要不我就刨你祖坟。”蒿子一听,差点昏死过去,这得花多少钱呢?他嗫嚅道:“你还是打我一顿算了,我哪有钱还你。”金刚恶狠狠地说:“就是打死你也抵不了我的半罐油钱,甭他娘的废话,我只要罐子和油。”他目露凶光,令蒿子不寒而栗。随后又放出狠话:“要是不还,我就让俺爹踏平你们村子,到时寸草不生鸡犬不留。”说完,飞起一脚把蒿子踹倒在地,骂骂咧咧地走了。
蒿子六神无主地看着金刚越晃越远的背影,强忍着没有倒下去。他的魂都被收走了,身子虚软得像面条。他艰难地回想着金刚刚才说的话,每一个字都像定时炸弹随时都会把他炸得粉身碎骨。蛤蟆看事情闹大了,也慌了手脚。他对蒿子说:“要是引起了两村械斗,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你必须到东村去负荆请罪,息事宁人。”蒿子不敢去,怕东村人要了他的小命。蛤蟆打气说:“不会的,只要你答应金刚赔罐钱油钱,他就会饶了你的。”提到“钱”字,蒿子更是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浑身止不住地发抖,像得了疟疾。蛤蟆看蒿子那样,厌恶地直皱眉头。但为了说服蒿子去东村,他忍着恶心说够了好话,甚至答应帮蒿子给金刚还钱。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东村就是龙潭虎穴也不得不去了。蒿子知道此去必凶多吉少,流着泪和蛤蟆说了几句告别的话竟像是在安排后事。他拖着两条灌了铅般的腿,顶着发麻的头皮,提心吊胆地来到东村,涕泪俱下的求饶。可金刚不为所动,将他一顿暴打。
蒿子浑身是血地回到蛤蟆面前,声泪交加地控诉:“我都被人打成血葫芦了,差一点就报销了,你得给我撑腰。”蛤蟆冷笑:“奸商狗崽子挨点揍算什么?还想让贫农撑腰,你的脑子生锈了吧。”旁边一群喽啰也跟着打趣:“以前都说奸商的血是黑的,怎么也是红的呢。”有人还真的从蒿子身上揩了血来看,引来一片哄笑。蒿子无奈,又低声下气地哀求蛤蟆道:“不撑腰就算了,你可是答应过帮我还钱的。”蛤蟆冷笑得更加瘆人:“我说话是放屁,从来不算数的。再说了我让你死你会去死吗?你要是再在这里胡搅蛮缠,就叫你见阎王爷去。”喽啰们也在一旁给蛤蟆帮腔。
蒿子这才明白他又被蛤蟆算计了。本来,磨眼是有名的神投手,可刚才他表现得太反常了,投出去的石头都离目标十万八千里的,明摆着是在把蒿子往坑里带。
蒿子一筹莫展,也不敢回家。他到河沟里潦潦草草地洗了一下身上的血迹,便蹓跶到村外的场院上。天黑了,他蜷缩在场院上的柴禾垛里,饥肠辘辘,倍感孤独。更让他难过的是,家里竟没人出来喊他回去。他终于忍不住了,大放悲声,要哭出所有的委屈。清冷的月辉里,蒿子形单影只。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拧着蒿子的耳朵把他整醒了。蒿子吓了一跳,以为是金刚寻仇来了。他睁开惺忪的睡眼,透过眼屎看见彩凤正站在他的面前。蒿子爬起来,一见到彩凤他就灿烂了。更吸引他的是彩凤手上捧着的一块烤红薯,他嬉皮笑脸地一把抓过来,几口吞下去。还舒舒服服地打了一个长嗝。
彩凤的鼻尖上沁着一丛晶莹的汗珠儿,她已经听说了蒿子的遭遇,转悠了一早晨才找到这儿。她气呼呼地对蒿子说:“我还以为你被野狗叨走了。”接着又心疼地轻拭着蒿子的伤口。
蒿子见到彩凤只高兴了片刻,烦恼就像块黑色的云彩又笼罩在他的头上。他无计可施,连连叹气,只好和彩凤讨主意。
彩凤说:“赔他一个油罐子倒也容易,可那半罐油太金贵了,我们哪有钱去买。”
蒿子乞求她说:“想想办法吧,除了你我还能指望谁呢。”
彩凤叹了口气,真是拿他没辙。她想了半晌说:“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也只能是碰碰运气。去俺奶奶家偷油吧。”
蒿子一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就催着她立马去偷。彩凤犹豫着,作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一跺脚,两人就鬼鬼祟祟地直奔她奶奶家去了。
两人蹑手蹑脚地走进奶奶家的堂屋。奶奶是个瞎子,正倚在炕上打盹,呼噜响得似拉风箱。呼噜声每每飙到高处便戛然而止,似要闭过气去,怪吓人的。彩凤似一只身经百战的耗子轻车熟路地找到了油壶,拿起来一掂量却是空的。两人失望透顶,上吊的心思都有。小心翼翼地溜出来,彩凤琢磨了一下说:“看来俺奶奶也断油很长时间了。要不这样,我们偷几颗盐粒儿给金刚送去,把他的油给顶上。”那时候,油和盐是同样金贵的东西。这样尽管没把握,但除此之外毫无办法,也只好侥幸一试了。他们又贼一般潜回屋里,找到了盐罐子。那罐口小得可怜,只有把罐子竖直了才能勉强倒出盐粒来。里面共有四颗盐粒,蒿子全倒了出来,彩凤示意他放回去一粒,给她奶奶留点响声好蒙混过关。这时她奶奶放了一个响屁,空气中立刻就弥漫了一种食物发酵后的不良气味。他俩吓了一跳,赶紧逃之夭夭。
蒿子和彩凤手捧三颗盐粒,像捧着稀世珍宝,去东村找金刚。蛤蟆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拦住他们盘问了半天。蒿子嘀咕:“咋就这么巧呢?”彩凤说:“他肯定一直在跟踪我们。”
见到金刚。金刚先是不怀好意地盯着彩凤看,看得彩凤都低下头脸红了。他又看看那三颗盐粒一阵冷笑:“亏你想得出,拿这个来糊弄老子。”蒿子低头看看手上的盐粒,它们越发得小了,大部分已和手上的汗水化在了一起。他心疼得要命,竟情不自禁地舔了掌心一下,那味道又酸又咸,刺激得他龇牙咧嘴的。
这时,金刚色迷迷地走近,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摸了彩凤的脸蛋儿。蒿子的脸涨红了,当面调戏他的女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但蒿子的脾气在肚子里转了一圈,就从屁股里溜走了。他说:“金刚,你揩了我女人的油,我们就算两清了。”金刚不屑地说:“这算个屁呀,我那半罐油钱都能把你的女人买了。”他变本加厉地继续用不怀好意的眼光上下打量彩凤。蒿子真是受不了了,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也不要欺人太甚了。”金刚啐他脸上一口唾沫,说:“小气鬼,我摸她一下,她连根毛也少不了。”说着就又凑上来,恬不知耻地伸出手去。蒿子眼睁睁看着彩凤受辱,心急如焚,但敢怒不敢言。彩凤急了,指着金刚的鼻子骂道:“臭流氓,我不去告发你,就算是抵了你的油钱,要不我跟你没完。”金刚怕她告发,被震住了,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抵了就抵了,老子根本就不在乎那点油钱。”说完,吊儿郎当地做了一个鬼脸。
一场关于油的纠纷以意料之外的方式解决了,蒿子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怀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和彩凤兴冲冲地往回走去。这时天已黑了,大地即将陷入海潮般起伏的鼾声。田野里有星星点点的磷火飘浮不定,乡村的夜晚充满了神秘的鬼魅气息。离村子老远,他们便听到高一声低一声的叫骂,那声音在阒寂的夜晚突兀而又尖利。彩凤一下就听出来了,是她奶奶那沙哑的破锣嗓子。从那上气不接下气的怒骂声能判断出,她至少围着村子骂了三圈,累得嗓子眼都快冒火了。
彩凤紧张地说:“不好,露馅了。”
蒿子说:“也难怪,一粒盐和四粒盐的声音差别可太大了。”
彩凤说:“事到如今,只有死不认账,俺奶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没事了。”
两人惴惴不安地分头摸回村去。蒿子回家就睡,一觉醒来,已是子夜时分。大街上仍断断续续传来彩凤奶奶的骂声。他发现自己下身湿乎乎的,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竟在睡梦中紧张地尿湿了裤子。
第二天一大早,彩凤奶奶就骂上门来。蒿子被她从被窝里拽出来,裤子都来不及穿。她恶毒地诅咒蒿子家断子绝孙,又跑到鸡窝里掏走了几个鸡蛋。
蒿子知道,肯定是蛤蟆向彩凤奶奶告了密。
梦 杀
蒿子偷油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村里人都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大叫驴拍着手儿叫好,兴灾乐祸地说:“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王八生不出龙蛋,上梁不正下梁歪哩。”这一下就直接骂到蒿子爹身上了。
蒿子爹气不打一处来。他自己不济也就罢了,可偏偏又有个不成器的儿子给他丢人现眼。
蒿子爹把蒿子薅过来,吹胡子瞪眼地怒喝道:“跟老子到祠堂去!”
蒿子看看爹的脸色,心里“咣咣咣”打鼓,小声嘟哝道:“不年不节的去祠堂干啥?”
爹咬牙切齿地蹦出三个字:“少废话!”口气硬得像石头,扭头前面走了。
蒿子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他看见爹的手上拖着一根细细的柳条儿。柳条儿在地上蛇行,荡起一溜烟尘,那些烟尘看起来都气势汹汹的。蒿子脸色变了。
到了祠堂,蒿子站立在祖宗的牌位前,两股战战,他知道大难将要临头了。爹在他身后怒喝道:“脱裤!”蒿子犹豫着松开裤带,裤子一下出溜到脚踝处。爹冲他的腘窝飞起一脚,他两膝一软,跪倒在地。
随后,爹扬起柳条儿,没命地抽打蒿子的屁股,翻飞的柳条儿掠过空气发出尖利的哨音。与粗木棍相比,这种细柳条儿特有一种力道,落在身上似刀割。蒿子忍不住惨叫起来,他的惨叫声似乎鼓励了他爹,爹打得更起劲了。到后来,蒿子不叫了,他咬紧牙关,每挨一下柳条儿,他的身体便猛得抽搐一下,脸都扭曲起来。
爹打累了,把柳条儿扔到地上,大声喘着粗气,说:“不肖子孙,辱没祖宗。老子再不济也没偷没抢。”又说:“以后你的脸上就刻上了‘贼’字,再也甭想抬起头来!”说完,踹了蒿子一脚,骂骂咧咧地走了。
一个“贼”字从爹嘴里说出来相当刺耳,蒿子心上像被人剜了一刀。他顿觉受到了奇耻大辱,眼前这人要不是他爹,他非得拿刀宰了他不可。
蒿子的屁股火辣辣地疼。他摸了一下屁股,屁股上的伤痕高高地肿起来,纵横交错,感觉像多长了几个屁股。他勉强地提上裤子,一瘸一拐地去找彩凤,每挪动一步都要倒吸几口凉气。
彩凤拿出冬天储藏下来的雪水帮蒿子治伤,心疼得直掉泪,说:“你爹可真下得去狠手,你到底是不是他的种儿。”雪水敷在伤口上杀得更疼了,蒿子龇牙咧嘴的,骂天骂地。
彩凤说:“骂有啥用?重要的是以后不受蛤蟆等人的欺负,不再跳进他们挖的坑里干坏事。”
蒿子说:“对!人都是肉长的,都没长三头六臂,他们凭啥欺负人,老子不跟他们混了。”
彩凤支持他:“你早就不应该跟他们混了,趁早干点正经事吧。”
蒿子找到蛤蟆提出退伙。蛤蟆皮笑肉不笑地说:“你把老子这里当成车马店了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又揶揄道:“翅膀硬了,想单飞?”
蒿子说:“不干了就是不干了。”
蛤蟆说:“我知道你想混出个人模狗样,可是别着急,留在队伍里,总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蒿子不语,用沉默表示自己退伙的决心。
蛤蟆说:“入了一次伙,不弄出点动静就打退堂鼓,不怕人笑话?”他对蒿子察颜观色,又说:“得,算你走运,现在就有一桩好事。”
蒿子想知道蛤蟆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便听他说下去。
蛤蟆说:“村里刘老太有个黄花梨的首饰盒,被一个古董贩子知道了,让我想法搞到手,这事你去干吧。”又拍拍裤兜说:“订金都付了。”蒿子瞥见了蛤蟆裤兜里冒出来的花花绿绿的钱的边角,看起来不少。
蒿子当然不干,直接拒绝。
这时候,磨眼说话了:“你不干谁干,队伍里就数你最会做贼。”
蒿子听了头皮不禁一炸,这个“贼”字太刺激他了,他下意识地抿紧了嘴巴攥起了拳头。磨眼怕挨揍,似一只逃命的老鼠,“嗤溜”一下钻到了蛤蟆身后。
蛤蟆继续苦口婆心地对蒿子做工作:“不是让你去偷,是让你去搞。无论用啥办法能搞到手就行。”
蒿子本想再次拒绝,可转念一想,他竟答应下来了。蛤蟆大喜过望,立马对蒿子开出空头支票,说:“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把黄花梨首饰盒搞到手,定有重赏。”
蒿子没理他,径直去了刘老太家。他一进门便闷头忙活起来,打水、扫地、劈柴,忙得不亦乐乎。刘老太又惊又喜,一个劲地拉蒿子坐下来休息,夸他越来越懂事了。
蒿子忙完了,坐下歇口气,问:“奶奶,您是不是有个黄花梨的首饰盒?”
刘老太一听,脸上顿时放出光来:“有的,有的,那可是我家祖传的宝贝,当年我结婚的时候陪嫁过来的。”言罢,转身要去屋里拿出来。蒿子连忙制止了她,说:“你可得保管好了,有贼惦记着呢。”
刘老太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蒿子起身,又找来钳子、铁丝、钉子、锤头,帮刘老太加固了篱笆门。临走时,他一再叮嘱刘老太把黄花梨首饰盒保管好。
蛤蟆催得急,接连追问了几次。蒿子采取缓兵之计,以种种理由敷衍他。转眼就到了年关,蛤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要是再搞不定黄花梨的首饰盒,古董贩子就要收回订金了。
蛤蟆明白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他从兜里摸出几张毛票塞给蒿子,说:“先给你点儿,事成之后,卖黄花梨首饰盒的钱一人一半。”顿了顿,又用力握握蒿子的手,加重语气说:“一言为定,绝不食言!”蒿子把钱接了,那几张毛票已被揉搓得不成样子。他想: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蛤蟆看蒿子收了钱,更加有了仗势,便强迫他说出搞定黄花梨首饰盒的最后期限。蒿子依旧含混地说:“年后吧。”
蒿子把那几张毛票揣进裤兜里,去找彩凤。说了蛤蟆让他偷黄花梨首饰盒的事。他忧心忡忡地说:“刘老太的黄花梨首饰盒早晚得玩完儿。
彩凤说:“不如把黄花梨首饰盒拿过来,我们替刘老太保管。”
蒿子说:“不行,万一在我们手上有个闪失可就说不清了。”
彩凤说:“那可咋办?”
蒿子突然脱口而出:“最好把蛤蟆做了,一了百了。”
这话从蒿子嘴里出来,吓了彩凤一跳:“你要杀人?”说完,她掩住了嘴。
蒿子沉默。
彩凤说:“你想过没有,杀人会有啥后果。”
蒿子说:“做了蛤蟆,咱俩就一起远走高飞。”
彩凤一边仔仔细细收拾着剃头推子,一边说:“说得轻松,咱俩出去怎么活?”
蒿子说:“咱守着剃头挑子还怕没饭吃,天底下的人哪个不剃头?”又说:“挑着剃头挑子到处跑又咋了?好歹也算是直起腰来了。”
彩凤笑了,觉得蒿子太异想天开。其实,蒿子的话她一点也没往心里去,她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只是想发泄一下愤怒的情绪。
年后,蛤蟆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凶相毕露,对蒿子说:“你快滚吧,把给你的钱退给我,我派别人去搞定黄花梨的首饰盒。”又说:“伙里一向赏罚分明,你没完成任务当该受罚。”蒿子做好了挨打的准备,蛤蟆却没有动手的意思。他说:“二月二那天,你让彩凤免费给弟兄们都剃一次头,就当罚你了。”
蒿子听了差点失声叫出来,那么多人,彩凤得损失多少钱啊。他愤恨地对蛤蟆喊叫道:“我他娘的还下不了贼船了?”蛤蟆见蒿子不肯,恶狠狠地威胁道:“要是不干,我就荡平彩凤的剃头铺。”
蒿子知道蛤蟆说到做到,只好去找彩凤商议。彩凤安慰蒿子说:“破财免灾,就给他们剃一次头吧。好在那些人都是一色的青皮,费不了多大工夫。”蒿子点头,突然又没头没脑地说:“你把剃刀磨得快点。”
二月二的头天晚上,蒿子竟无端紧张。他躺在炕上烙大饼,难以入眠。爬起来偷偷喝了几口酒才马马虎虎地睡着。可刚一合上眼睛便陷入了以下的梦境。
二月二那天,天不亮,蛤蟆就来到了剃头铺子,他要抢先第一个“龙抬头”。
蛤蟆舒服地躺在椅子上,彩凤给他围上白色的围裙,利索地给他剃完头。蛤蟆却躺着不起来,又让彩凤帮他剃胡子。彩凤嫌麻烦,说:“你胎毛未褪,剃啥胡子?”蛤蟆说:“这你就不懂了,胡子是越剃越棒,我就是想要又浓又密的大胡子。”
彩凤仍在犹豫,蒿子却发话了:“好事做到底,给他剃!”他一直坐在对面的一个矮杌子上,盯着蛤蟆的一举一动。蛤蟆对蒿子伸了伸大拇指,便闭上眼睛,美美地打起了呼噜。
彩凤白了蒿子一眼,用刷子蘸了肥皂水抹在蛤蟆的下巴上。她拿起剃刀,在帆布上“噌噌噌”磨了几下,又习惯性地用大拇指拭了拭刀刃,开始为蛤蟆剃胡子。
突然,蒿子一跃而起,如一只矫健的豹子。他猛地抓住彩凤的手,用力将剃刀往蛤蟆的脖子上摁下去,又迅速横着锯了一刀。血瞬间从蛤蟆的伤口喷涌出来,喷了蒿子满身。蛤蟆猛地直起身子,却又瞬间跌了回去,只是沉闷地喊出了半声。
彩凤失声尖叫。那把剃刀掉在石板地上剧烈地弹跳,发出刺耳的声响。蒿子双眼通红,瞪着那把鲜血淋漓的剃刀,一字一顿地吼道:“老子就是想站着过几天舒心的日子!”
蒿子叫喊着从梦中惊醒,浑身大汗淋漓。他的尖叫声惊吓到了院子里的那只大狗。大狗立即焦躁不安地狂吠起来,紧接着全村的狗都焦躁不安地狂吠起来。狗叫声连成一片。
一个月以后,蒿子仍旧走不出那个杀人的梦境。他看见蛤蟆的秃瓢上又长满了头发,像长了一头乱蓬蓬的杂草。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蛤蟆:“你还敢去找彩凤剃头吗?”
蛤蟆觉得奇怪又好笑,瞪着眼说:“老子有啥不敢的呢,别说剃头,就是剃蛋老子也敢去。”
蒿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用力拍了拍蛤蟆的肩膀,说:“下次再去我一定让彩凤好好侍候你。”
——话说黄花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