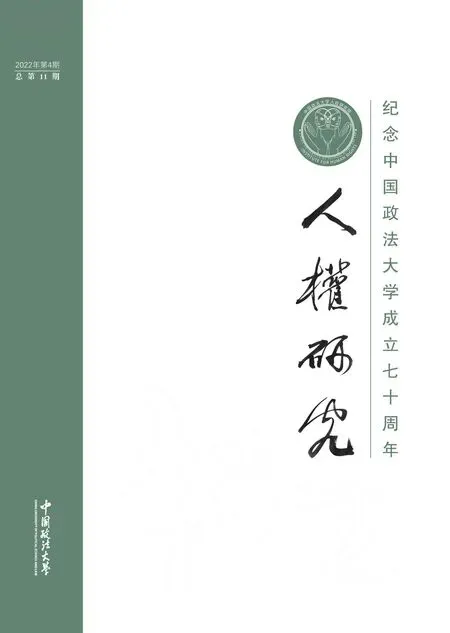私有化与经济、社会权利
奥菲·诺兰
刘林语** 译
一、引言
对于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来说,私有化已成为一种日益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外包、公私合营以及其他负责或协助国家提供有关经济、社会权利的商品和服务的私营部门,正在国家和超国家层面上积极推进私有化,其中国际金融机构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然而迄今为止,在与经济、社会权利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中对私有化的关注相对较少,从而导致规范和实证方面存在大量空白。这一差距可能是最突出的,也是最令人担忧的,尤其是在那些根据国际法来解释和适用经济、社会权利标准的国际机构的工作中。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以尊重、保护和实现义务框架来阐述经济、社会权利所对应的义务;以此为起点,本文考虑了该框架以及在工作中使用该框架的人权条约监督机构如何从经济、社会权利角度来讨论私有化问题。笔者认为上述方法过度强调保护的义务而排除其他层次的义务,未能对私有化进行全面概括并适当反映国家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权利的法律义务框架在私有化背景下有效地发现侵权行为的能力。笔者主张将上述方法转变为实现义务,这种替代方法将有助于极大提升经济、社会权利的法律效力,因为它能够发现和应对私有化情况下全部国家决策及其作为或不作为。
本文首先讨论了私有化及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心作用,其正被国家更加普遍地适用于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领域以不同程度地实现经济、社会权利。在简要概述了国际人权法中经济、社会权利与私有化的关系后,本文考查了国际上现有的经济、社会权利模式,以及解释和适用相关模式的机构。运用尊重、保护和实现框架的规则,本文评估了这些机构是如何发展和利用这一框架来概念化和应对私有化的。本文首先追溯了被授权处理经济、社会权利的联合国条约监督机构的做法,然后介绍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最近在其制定的“关于国家在工商活动中履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中详细处理的私有化问题。1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4 on State Obligation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Business Activities, E/C.12/GC/24 (2017), paras. 15-16, 32-33.本文的目的是,评估当前主流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充分发现私有化背景下损害经济、社会权利的行为,从而确定应如何改进这种方法,并根据第24号一般性意见评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实际上是否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21世纪的私有化
在过去的30年里,政府通过“私有化、外包和减轻公共责任”,放弃了一系列过去在本质上被视为“公共”的职能,从而大幅度地向“更小”或“缩小”的国家转变。2Chang Kil Lee & David Strang,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Public Sector Downsizing: Network Emulation and Theory-Driven Learning, in Beth A. Simmons, Frank Dobbin & Geoffrey Garrett eds.,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Markets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41.讽刺的是,这种职能重新配置的国家3See David Kinley, Civilising Globalisation: Human Right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6.(注意到公共职能外包的后果实际上更多地与公共权力的方式和形式有关,而不是与公共权力数量的减少有关,并且正确看待私有化涉及的重新配置,而不是否定国家。)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在行使与人权有关的职能方面的执行责任(如果不是法律责任),而这种国家概念的发展恰逢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将经济、社会权利视为法律标准从而在实现这些权利方面对国家施加约束性义务。
基于下述理由,私有化已被证明是合理的,包括“效率、竞争、创新和赤字削减”4Danny Nicol, Swabian Housewives, Suffering Southerners: The Contestability of Justice as Exemplifi ed by the Eurozone Crisis, in Dimitry Kochenov, Gráinne de Búrca & Andrew Williams eds., Europe’s Justice Defi cit?, Hart Publishing, 2015, p. 156, 168.。从经济、社会权利角度来看,如果私有化促使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实现经济、社会权利,1Se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6 December 1966, 999 U.N.T.S. 171, Art. 2, para. 1.或者能够利用私主体的能力或专业等,从而“迅速”和“有效”地实现经济、社会权利的不同要素,2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3: The Nature of States Parties’ Obligations, E/1991/23 (1990), para. 9.那么私有化可能会(甚至应该)受到欢迎。依据经济、社会权利的多种要素来描述私有化的所有模型所带来的机遇和风险,远远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3关于私有化对经济、社会权利(包括教育权、住房权、社会保障权、水权和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影响,参见 Koen De Feyter & Felipe Gómez Isa eds., Privatis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Intersentia, 2005.但是,私有化潜在地有助于增强“创新和社会供给形式的多元”,从而加强了国家“对需要帮助人们的全面反应能力”,4Martha Minow, 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s: Accounting for the New Religion, 116 Harvard Law Review 1229, 1230 (2003). 米诺(Martha Minow)关心的是确保私有化符合适当的公共问责要求。这一点是经济、社会权利倡导者不能轻易忽视的。
本文中,私有化是指由非政府或非国家行为者提供某些类别的商品和服务,或由这些行为者实现某些类别的职能,替代原本习惯上完全或主要依赖国家办事处和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服务。5Adapted fromFrank I. Michelman, Constitutionalism, Privatisation and Globalisation: Whither the Constitution?, 21 Cardozo Law Review 1063 (2000). 笔者将“组织”替换为“行为者”,以避免与一种特定的非国家行为者混淆:非政府组织(NGOs)。私有化涵盖一系列模式和程序,从纯粹私人拥有资产的所有权模式,到国家保留所有权但将公共服务承包给私营行为者的模式(即机构或服务的运作是私有化的)。6这也被称为“外包”。这些模型被应用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经济、社会权利相关部门。
在2010年6月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时任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独立专家更愿意使用“私营部门的参与”一词而不是“私有化”,理由是前一术语“通常用于指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一系列包罗广泛的合同安排,涉及在不同程度上提供水和卫生设施的私营公司。它们根据资产所有权、对资本投资的责任、风险的分配、对操作和维修的责任以及典型的合同期限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虽然特许权的模式将投资的管理、风险和责任转移给私营部门,但是私营部门的参与也仅限于政府将某些管理或服务外包的情况。在许多情况下,不能把体系认定为完全公共的或私人的,而是呈现一种混合的性质,也是具有合资企业的形式”7Catarina de Albuquerque,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Related to Access to Safe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A/HRC/15/31 (2010), para. 9 (footnote omitted).。
毫无疑问,如果不承认私营部门参与提供经济、社会权利相关商品和服务的复杂性和多种形式,就无法有效地对上述情况进行基于权利的充分分析。然而,“私有化”是在考虑到描述私营部门在提供传统上由国家提供与经济、社会权利有关服务方面的作用时常用的术语。因此,本文将采用“私有化”这一术语,尽管该术语是用来涵盖一系列涉及私营部门不同作用和参与程度的模型和过程的。其中包括私人参与者是区别于国家本身的不同的法律实体,即国有公司的情况。然而,本文将不讨论未获得政府正式授权但提供服务的非正式私营部门行为者。1这并不是说,就提供一些与经济、社会权利有关的服务而言,这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关于这一部门在水权方面发挥的作用,参见Catarina de Albuquerque & Inga T. Winkler, Neither Friend Nor Foe: Wh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Water and Sanitation Services Is Not the Main Issue in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17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167 (2010).同时,本文也不会探讨“隐性私有化”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家停止公共项目和政府脱离特定种类的责任,发生了部门的私有化。2Paul Starr, The Meaning of Privatization, 6 Yale Law & Policy Review 6, 16 (1988). 这种隐性的私有化形式可能由于一系列原因而发生,包括国家资源或能力的不足,或政府热衷于在特定情况下取消供应。最后,本文不会直接论及自由化和/或放松管制导致私营行为者更多地参与经济、社会权利实现的情况,3借用科斯莫·格雷厄姆(Cosmo Graham)的观点,笔者认为自由化“意味着将竞争引入一个行业的过程,而放松管制则意味着放宽一个行业开展活动所依据的规则”。Cosmo Graham, Human Rights and the Privatisation of Public Utilities and Essential Services, in Koen De Feyter & Felipe Gómez Isa eds., Privatis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Intersentia, 2005, p. 33, 35.因为国家没有特别授权这种参与。诚然,本文的分析肯定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这些私有化形式,但是,鉴于笔者对本文所研究的机构未能有效地处理私有化的复杂性的批评,笔者不想犯同样的错误——采用对私有化的形式“一刀切”的分析模式。
私有化经常被认为是当代全球化的一个基本要素,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4See, e.g., Statement by CESCR,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Enjoyment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May 1998), para. 2 (emphasis added).它已经与一系列具体的趋势和政策产生密切的联系,其中包括对自由市场日益加剧的依赖、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确定国家政策重点的可行性方面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国家作用及其预算规模的缩小、以往被认为是完全属于国家管理的各种职能的私营化、为便于投资和奖励个人行为而开放一系列活动、私人经营者在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及民间社会中的作用和责任的相应加强。CESCR, Report o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Sessions, E/C.12/1998/26 (1999), para. 515. See also Maastricht Guidelines on Violation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26 January 1997), para. 2,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8abd5730.html.《 关于侵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行为的马斯特里赫特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强调: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区都有减少国家作用和依靠市场解决人类福祉问题的趋势,往往是为了应对国际和国家金融市场产生的情况,为了吸引财富和权力超过许多国家的跨国企业的投资。人们不再想当然地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行动,尽管根据国际法,国家仍然对保障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负有最终责任。该《准则》载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文件《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实质性问题》,E/C.12/2000/13,2000年,第16页。下面的文章提供了私有化和域外义务的为数不多的处理办法之一。Manisuli Ssenyonjo, Ref lections on State Obligations with Respect to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969, 988-989 (2011).及其同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念中。5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发展,参见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Raymond Plant, The Neo-Liberal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niel Stedman Jones,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Hayek, Friedman,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关于当代全球化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讨论,参见Paul O’Connell, Brave New World? Human Right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Mashood A. Baderin & Manisuli Ssenyonjo ed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Six Decades after the UDHR and Beyond, Routledge, 2010, p. 195, 198-204.关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公共服务私有化发展的讨论,参见Colin Crouch, 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Polity, 2011, p. 20-21, 71-96.私有化从“玛格丽特·撒切尔1979年英国选举宣言中的一种反传统的政策理念发展为20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Beth A. Simmons, Frank Dobbin & Geoffrey Garrett, Introduction: The Diffusion of Liberalization, in Beth A. Simmons, Frank Dobbin & Geoffrey Garrett eds.,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Markets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 3. 然而应当指出,在此之前,一些国家通过了私有化方案。See Dónal Palcic & Eoin Reeves, Privatisation in Ireland: Lessons from a European Economy,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12-15.。在私有化相关的政治经济思想全球盛行的背景下,2更多关于私有化全球扩散原因的不同观点(包括美国经济学家以“扩散者的扩散”为前提的观点),参见Bruce Kogut & J. Muir MacPherson, The Decision to Privatize: Economis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as and Policies, in Beth A. Simmons, Frank Dobbin & Geoffrey Garrett eds.,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Markets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4.国际捐助者、国际组织3一个例子就是尼科尔(Danny Nicol)所说的“欧盟强制私有化政策”。尼科尔说:《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106条关于欧盟竞争法在公共事业中的适用,被欧盟法院解释为取消成员国保留其公共部门某些活动的能力。该判例法随后被欧盟自由化指令加强和扩大。……这种自由化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私有化程度,因为往往是私营部门在利用自由化的权利。Danny Nicol, Swabian Housewives, Suffering Southerners: The Contestability of Justice as Exemplifi ed by the Eurozone Crisis, in Dimitry Kochenov, Gráinne de Búrca & Andrew Williams eds., Europe’s Justice Defi cit?, Hart Publishing, 2015, p. 167-168.和金融机构4这些观点是由独立专家和当时的水和卫生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提出的。See, e.g., Catarina de Albuquerque,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Related to Access to Safe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A/HRC/15/31 (2010), para. 6.应在捐助办法和国际政策的范围内理解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的参与。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倡导各国减少公共开支,避免大量投资。导致私营部门更多参与的一些改革是通过贷款或援助条件、债务重新规划或贷款豁免实施的。的贷款条件与政策(私有化是《华盛顿共识》的核心要素之一),以及对2007年至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经济约束和国际反应等因素加速了私营部门参与对人权有影响领域的趋势。私有化似乎已成定局:《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指出,公私合营关系和更广泛的私营部门将成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部分,5See, e.g., UN President of the G.A.,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17.17, para. 43, http://www.un.org/pga/wp-content/uploads/sites/3/2015/08/120815_outcome-document-of-Summit-for-adoption-of-the-post-2015-development-agenda.pdf. 应该指出的是,成果文件将私营部门的角色广泛地解释为“从微型企业到合作社再到跨国公司,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和慈善组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41段)。民间社会、工会和社会运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设想的“全球伙伴关系”中的私有化、公私伙伴关系和企业主导以及其对可持续性和不平等的影响表示关切。See e.g., Spotligh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claiming Policies for the Public (2017), https://www.2030spotlight.org/en/book/1165/chapter/0101-reclaiming-public-policy-space-sdgs.这一点在《亚的斯亚贝巴筹资问题行动议程》中被较为详细地重申。6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313. 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A/RES/69/313 (2015), para. 48.
三、私有化与国际人权法:概述
众所周知,国际人权法本身并不排除私有化。鉴于在起草和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载有经济、社会权利的其他条约时,非国家行为者在提供与经济、社会权利有关的商品和服务方面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比如许多国家的宗教教派和其他私营行为者在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载有经济、社会权利的其他文书所规定的总体义务,缔约国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1See, e.g.,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6 December 1966, 999 U.N.T.S. 171, Art. 2, para. 1;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20 November 1989, 1577 U.N.T.S. 3, Art. 4;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13 December 2006, 2515 U.N.T.S. 3, Art. 4, para. 2.事实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起草者承认存在私营行为者提供经济、社会权利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的情况,但前提是各国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干涉非国家行为者建立和指导教育机构的自由。2Se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6 December 1966, 999 U.N.T.S. 171, Art. 13, para. 4;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20 November 1989, 1577 U.N.T.S. 3, Art. 29, para. 2, for a similar provision.如下文所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强调: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承认的权利“在各种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背景下是很容易实现的”,3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3: The Nature of States Parties’ Obligations, E/1991/23 (1990), para. 8.私有化可能是各国鼓励用来弥补经济、社会权利相关商品和服务之不足的“授权战略”之一。4See, e.g.,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4: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E/1992/23 (1991), paras. 14-15.这种私人供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权利相关商品和服务领域的一个特征。这就是说,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人关注私营部门参与提供传统上与国家有关的服务对人权的影响,包括监狱运营5例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监狱项目的工作重点关注的是美国的私人监狱。2016年8月,美国司法部向联邦监狱局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告诉工作人员要么在私人监狱运营商合同到期时拒绝续签合同,要么以符合法律的方式“大幅度缩小”他们的“范围”,并减少监狱局的囚犯人数全面下降的情况。Memorandum from the Office of the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for the Acting Director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2016), http://www.justice.gov/archives/opa/fi le/886311/download.备忘录指出:“私人监狱根本不提供相同水平的惩教服务、计划和资源;它们不会大幅节省成本。”2017年2月21日,司法部长杰夫·赛申斯(JeffSessions)撤销了该备忘录。、社会照料、儿童保护6例如,关于英国政府将儿童保护和其他社会护理服务私有化的争论,参见Andy McNicoll, Minister: “We Won’t Privatise Child Protection or Politicise Social Work”, CommunityCare (7 July 2016), http://www.communitycare.co.uk/2016/07/07/minister-wont-privatise-child-protection-politicise-social-work/; Patrick Butler, Labour Fears Potential Privatisation of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 Guardian (13 June 2016),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jun/13/labour-fears-potential-privatisation-of-child-protection-services.和移民7See, e.g., Nick Evershed, Ri Liu, Paul Farrell & Helen Davidson, The Lives of Asylum Seekers in Detention Detailed in a Unique Database: The Nauru Files, Guardian (10 August 2016), http://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ng-interactive/2016/aug/10/the-nauru-fi les-the-lives-of-asylum-seekers-in-detention-detailed-in-aunique-database-interactive[提供了在瑙鲁的澳大利亚拘留营(“区域处理中心”)中被拘留的儿童(和成人)所经历的侵犯人权的详细情况]。这个营地由一家名为广谱(Broadspectrum)的私人公司经营,其他私人公司向囚犯提供健康和其他服务。See, e.g., Australia: Appalling Abuse, Neglect of Refugees on Nauru, http://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6/08/australia-abuse-neglect-of-refugees-on-nauru/.。
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的相关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指出,人权在私有化问题上并不是“中立的”,因为有效履行国际人权义务需要各国和国际社会发展、维护、逐步改善一定水平的公共基础设施,使所有人都能有效地享有和实现所有人权。1Manfred Nowak, Human Rights or Global Capitalism: The Limits of Privatization, Universti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7, p. 2. 例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显然是以先进福利国家的模式为基础的(参见本书第42页)。同样的观点,人权,特别是经济与社会权利,“需要国家的大量参与,才能充分和有意义地实现”,参见Paul O’Connell, Brave New World? Human Right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Mashood A. Baderin & Manisuli Ssenyonjo ed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Six Decades after the UDHR and Beyond, Routledge, 2010, p. 209.然而,鉴于国际人权法允许私有化,本文重点关注相关法律,以确定符合权利要求的私有化范围,而不是将其视为对人权本身的侵犯而直接予以拒绝。但是私有化在实施方式(即私有化进程中不遵守人权规定)和结果(即私有化对个人享有人权的影响)方面,存在明显侵犯经济、社会权利的情况。2当然,对经济、社会权利语境下的私有化的关切不仅限于具体的私有化进程和结果不符合经济、社会权利的要求;相反,它们在更广泛的当代法律和政治背景下,还关注私有化对经济、社会权利意味着什么,以及落实这些权利所需的进程和机构。这些关切包括私有化对公共参与和对实现权利的共同责任的影响(导致作为应被国家保障的法定权利的含义受到侵蚀)、对公共问责的影响(导致事实上如果不是合法的话,国家对提供权利的责任减少),以及对经济、社会权利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影响(导致人们对自身作为公共产品和以人的尊严为前提的法律权利地位的认识降低)。更为深入的研究参见Aoife Nolan, Privatisation: The Dangers and Opportunities for Human Rights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on fi le with author).虽然经常有人强烈地坚持,某些与人权有关的服务和职能从根本上说是政府或公共性质的,3关于人权相关职能是政府本身所固有的判例,参见The Decision of the Israeli Supreme Court in HCJ 2605/05 The Human Rights Division, The Academic Center for Law and Business v. Minister of Finance (19 November 2009).法院认为管理和运营监狱的权力从国家移交给作为营利企业的私人特许公司,这当然侵犯了监狱囚犯的人权。在此,法院详细讨论了国家为执行刑法而普遍运用强制力和剥夺个人人身自由的垄断问题。关于与权利有关的职能本质上是政府职能的政治主张的一个例子,参见“爱尔兰水权运动”关于水权的工作,该运动在爱尔兰寻求通过相关的宪法修正案,要求规定:“政府应集体负责公共供水系统的保护、管理和维护。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应确保这一资源继续属于公共所有和管理”。Right2Water, Policy Principles for a Progressive Irish Government (2015), http://www.right2change.ie/sites/default/fi les/media/Right2Change%20 Policies.pdf.有关经济、社会权利背景下的“公共”服务的深思熟虑的讨论,参见Marlies Hesselman, Antenor Hallo de Wolf & Brigit Toebes, Common Challenges for Socio-Economic Human Rights and Essential Public Services Provision, in Marlies Hesselman, Antenor Hallo de Wolf & Brigit Toebes eds., Socio-Economic Human Rights in Essential Public Services Provision, Routledge, 2017, p. 1, 4-6.但这些观点在实践中受到私有化不断深入和扩张的挑战。具体而言,从经济、社会权利的角度来看,在与经济、社会权利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包括与健康4See, e.g., Interim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the Enjoyment of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67/302 (2012), para. 3(强调“卫生系统私有化的全球趋势”)。有关私有化和健康权的更多信息,参见Audrey R. Chapman, Global Health, Human Rights and the Challenge of Neoliberal Polic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教育5See, e.g.,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Education, A/69/402 (2014), para. 32(强调“私有化教育的爆炸性增长”)。、水和住房6See, e.g., Raquel Rolnik,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Adequate Housing as a Component of the Right to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on the Right to Non-Discrimination in This Context, A/67/286 (2012), para. 2(强调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住房政策转变,“从北美和欧洲开始,随后是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前计划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这些经济体在“主流经济学说的支持下将活动从国家控制转移到私营部门以及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相关的商品和服务)方面,私有化供应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本文以国家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行为者这一事实为出发点,并由此展开以下讨论。1有关非国家行为者在国际人权法中的地位的概述,参见Jan Arno Hessbruegg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rising from Conduct of Non-State Actors, 11 Buffalo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21 (2005); John H. Knox, Horizontal Human Rights Law, 102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19 n. 86 (2008); Manisuli Ssenyonjo, The Applic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o Non-State Actors: What Relevance to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2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725 (2008).这并不是要忽视非国家行为者在国际人权法层面承担直接义务的近期进展,包括“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与人权的关系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其任务是“在国际人权法中,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以规范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的活动”2Human Rights Council Resolution 26/9, A/HRC/RES/26/9 (2014), para. 1. 关于该工作组工作的细节参见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WGTransCorp/Pages/IGWGOnTNC.aspx。有关在工商业和人权领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方案的政治可行性的概述,参见Olivier De Schutter, Towards a New Treaty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1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41 (2016).;坚持国家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行为者也不是要忽视这些明确跨国公司责任的文件的作用,诸如通过《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3John Ruggie,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A/HRC/17/31 (2011). 有关执行《指导原则》特别程序任务的工作详情,参见 http://www.ohchr.org/EN/Issues/Business/Pages/WGHRand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andotherbusiness.aspx。有关《指导原则》学术研究和与之相关的问题的有用收集,参见Dorothée Baumann-Pauly & Justine Nolan eds.,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From Principles to Practice, Routledge, 2016.(以下简称《指导原则》)或提高国际组织(例如国际金融组织)对国际人权法下义务的认知,特别是在域外义务方面。4See, e.g., CESCR, Statement on Public Debt, Austerity Measur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C.12/2016/1 (2016). See also Maastricht Principles on Extraterritorial Obligations of States in the Area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Principle 16, https://www.f idh.org/IMG/pdf/maastrichteto-principles-uk_web.pdf.然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经济、社会权利及其所施加的义务被学者、倡导者、国家以及负责将经济与社会权利标准应用于私有化背景的国际机构根据国家作为(和不作为)来概念化。5例如,参见下文讨论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工作。在私有化背景下,有关经济、社会权利的国际执行机制同样主要以国家为重点。此外,即使国际人权法普遍承认了非国家行为者的直接义务,国家最终仍有义务确保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因此,国家责任将始终是兜底的。
事实上,国家仍然是扶持和实施私有化的关键角色,这也使得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变得更加合适。必须认识到,私有化不可能在没有国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国家必须采取必要的授权或者撤销措施(尽管它们在执行这些政策的决定时可能不是自主行动的)。这反映在对国家在经济、社会权利语境下建立和维护公私分野的作用的理解越来越细致。例如,在英国,提供食品类产品的食品银行一般是私营机构(除受国家监管外,还会受到慈善法和当地环境卫生条例的约束)。与此同时,这些私营机构大多采用凭证制度,凭证是由包括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工作者在内的国家行为者发放的。6有关食物银行运营的更多信息,参见例如Jane Perry, Martin Williams, Tom Sefton & Moussa Haddad, Emergency Use Only: Understanding and Reducing the Use of Food Banks in the UK(CPAG, Church of England, Oxfam GB & Trussell Trust, 2014), https://www.trusselltrust.org/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6/01/foodbankreport.pdf.因此,虽然食品银行及其活动明面上属于“私有范围”,但它们是公共部门行为者确保食品可获取性的重要手段。本文会着重关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弱化国家”,以及(特别是较贫穷的)国家与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相对权力差异。事实上,有争议的是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国家权力的缺失[正如哈维(David Harvey)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市场和法律制度,新自由主义就无法发挥作用”1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17.],而是国家如何以及通过选择哪些中介力量来行使权力2Jessie Hohmann, Principle, Politics and Practice: The Role of UN Special Rapporteurs on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ight to Housing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Aoife Nolan, Rosa Freedman & Thérèse Murphy eds.,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Procedures System, Martinus Nijhoff, 2017, p. 271, 287, citing Saskia Sassen,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19.——以及来达到何种目的。因此,关注这些选择及其对经济、社会权利的遵守情况是重要的,而不是只关注那些在损害经济、社会权利的私有化背景下确保有效问责的机制,这些机制的有效性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本文参考了国际人权法目前的规则,但应充分认识到这些规则正在审查修订中,而且确实也应该修订规则,从而有效监管影响经济、社会权利的私营行为者。
我们讨论的最后一点是关于本文所研究的私有化形式,其中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在私有化情况下,国家决策和行动的不同阶段或地点都是有争议的。当涉及国家剥离或外包所有权或管理权时(这是本文所考虑的主要私有化形式),国家在私有化之前、期间和之后对人权都产生影响。3这并不是说与私有化有关的国家决策是孤立的。如上所述,超国家的金融机构和公司等其他行为者可在激励或形成私有化安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如上所述,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国家在履行人权义务方面的作用。私有化之前的国家决定和行动,包括决定审查私有化的可能性、后续实行私有化的行动以及在特定情况下采用的私有化模式(这可能包括私有化应采取的具体形式,并确定评估私有化“成功”的机制和基准)。私有化期间的国家决策将主要集中在确保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实施私有化。国家在私有化后期的作用将主要是监督和监管:确保私营行为者遵守其承诺和职能,并根据预先确定的标准评估私有化的总体成功情况。任何合理的私有化概念都必须承认这些决策和行动的不同阶段的存在,以及其与经济、社会权利的相关性和保障这些权利所应当履行的义务。4当然,它还必须认识到国家能力在实现其义务(例如有效机构或可用资源)方面的潜在限制,以及其他行为者在私有化方面的作用和责任。然而,本文将不广泛讨论这些问题,将其保留在今后植根于私有化具体实例的工作中,以便更充分地加以探讨。本文的重点是与私有化有关的经济、社会权利框架的缺陷,而不是各国在实现该框架的义务方面面临的实际挑战。
四、私有化与经济、社会权利义务
在研究国际人权法规则如何有助于确认和应对私有化给经济、社会权利带来的负面影响时,本文的出发点是经济、社会权利的义务框架,即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中经济、社会权利框架下的“硬法”及相关准司法条约监督机构的解释。1显然,其他行为者(如特别程序)在促进对保障经济、社会权利的相关义务范围的理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有关卫生权,参见Inga T. Winkler & Catarina de Albuquerque, Doing It All and Doing It Well? A Mandate’s Challenges in Terms of Cooperation, Fundraising and Maintaining Independence, in Aoife Nolan, Rosa Freedman & Thérèse Murphy eds.,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Procedures System, Martinus Nijhoff, 2017, p. 188)。然而,本文将侧重于条约监督机构,因为这些机构是负责监督履行条约具体规定的经济、社会权利保障义务的行为者,而特别程序的任务并不总是直接涉及具体人权文件。在相关报告中从三个框架(尊重、保护和实现)方面处理私有化与经济、社会权利问题的特别程序的例子,参见Kishore Singh,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Education, A/70/342 (2015), para. 75; Catarina de Albuquerque,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Human Right to Safe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A/HRC/27/55 (2014), esp. paras. 25-34; Dainius Puras,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the Enjoyment of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71/304 (2016), para. 35.特别报告员强调在经济、社会权利语境下实现义务的重要性的一个重要例子,参见Leilani Farha,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Adequate Housing as a Component of the Right to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on the Right to Non-Discrimination in This Context, A/HRC/37/53 (2018), para. 121.
(一)描绘义务的部分图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私有化的工作
第一个真正应当考虑的关键机构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没有忽视私营行为者在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作用。有八项一般性意见明确载有涉及“缔约国以外的行为者的义务”2See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3: The Right to Education, E/C.12/1999/10 (1999), § 3;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E/C.12/2000/4 (2000), § 5;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5: The Right to Water, E/C.12/2002/11 (2003), § VI;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7: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Benefi t from the Protection of the Moral and Material Interests Resulting from Any Scientifi c, Literary or Artistic Production of Which He or She Is the Author, E/C.12/GC/17 (2006), § VI;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8: The Right to Work, E/C.12/GC/18 (2006), § VI;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9: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E/C.12/GC/19 (2008), § VI;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1: Right of Everyone to Take Part in Cultural Life, E/C.12/GC/21 (2009), § IV;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3 (2016) on the Right to Just and Favourable Conditions of Work, Doc. E/C.12/GC/23 (2016), § III(E).的单独章节,以及广泛提及私营/非国家行为者的内容,这些对私营或非国家行为者的广泛引用表明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部分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方法。3See, e.g.,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4: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E/1992/23 (1991), para. 14(设想扶持战略,包括让私营部门参与解决住房短缺问题);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7: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Forced Evictions, E/1998/22 (1997), para. 9(强调“一些国家政府大幅减少其住房部门责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9: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E/C.12/GC/19 (2008), paras. 5, 13(设想私人社会保障计划以及私人和混合医疗保健计划)。关于健康权的第14号一般性意见一再提到私营医疗保健提供者的作用,包括提到国家的义务涉及“提供所有人都能支付得起的公共、私营或混合健康保险制度”。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E/C.12/2000/4 (2000), para. 36.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若干一般性意见中明确指出,各国需要与私营行为者合作,从而将私有化隐含在它所称的落实经济与社会权利的“法律纲要”中。1See, e.g.,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E/C.12/2000/4 (2000), para. 56;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5: The Right to Water, E/C.12/2002/11 (2003), para. 50;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9: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E/C.12/GC/19 (2008), para. 72.例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关于适足住房权的第4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一缔约国履行其义务所制定的措施可能会交融混合公共和私营部门认为合适的措施。在一缔约国,公共住房资金可能最有用地用于直接建造新住房。在多数情况下,经验表明,政府无法完全利用公共建造住房来弥补住房之不足。各缔约国促进‘授权战略’,辅之以全面致力履行适足住房权利所规定的义务的做法应予以鼓励。实质上,这种义务应表明,从总体上来说,所采取的措施足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大限度的资源实现个人的权利。”2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4: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E/1992/23 (1991), para. 14.
这就是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已明确认识到私有化对经济、社会权利的潜在负面影响。例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的第22号一般性意见中强调,国际援助不应“推动受援国采取私有化模式”3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on the Right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E/C.12/GC/22 (2016), para. 52.。在其他一般性意见中,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特别关注私有化对平等和不歧视地享受经济、社会权利方面的影响。例如,其在关于残疾人权利的声明中提到,“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安排正日益私营化、对自由化市场的依赖程度之高属前所未有的情况下,有必要使私人雇主、商品和服务的私人提供者以及其他非公营实体受到与残疾人相关的不歧视与平等准则的约束”4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5: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1995/22 (1994), para. 11.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接下来表示:“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就往往会出现自由化市场的运行对残疾人个人或群体产生不利影响这一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酌情采取措施,减轻、补偿或消除市场力量造成的这类不利影响。”(第12段)这一观点在下列文件中得到重申: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E/C.12/2000/4 (2000), para. 26.,并强调国家有义务监督并管制非国家行为者的行为,以确保这些行为者不侵犯男女享受经济、社会权利的平等权利,这“适用于部分或完全私有化的公共服务部门”5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The Equal Right of Men and Women to the Enjoyment of Al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C.12/2005/4 (2005), para. 20.。
尽管发布了这些意见,但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一般性意见或其他工作中没有深入探讨私有化形式、过程、产出、结果和权利影响。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虽然在其报告指南6CESCR, Guidelines on Treaty-Specif ic Documents to Be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s 16 and 17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C.12/2008/2 (2009), para. 15(b)(“促进工人特别是妇女和长期失业工人再就业的措施的影响,这些工人由于公共和私营企业的私有化、缩编和经济结构调整而被解雇”);该指南第30段(说明上述公共社会保障计划是否由任何私人计划或非正式安排补充。如果是,描述这些计划和安排及其与公共计划的相互关系);该指南第48(c)段(“为确保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私人或公共供水服务而采取的措施”);该指南第56(b)段(“即无论是私人提供还是公共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和医疗保险的费用对每个人都是可以负担的,包括社会弱势群体”)。中对缔约国提出了一些与私有化有关的问题,但在其对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关于私有化的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针对性的,1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截至2014年11月的结论性意见中提及私有化的有用概述,参见The Global Initiative for Econmic, Socia and Cultural Rights (GIESCR), Privatisation and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November 2014) (on fi le with author).最近的情况更加聚焦在教育方面,体现的是两个非政府组织在这一点上的一致倡导。2相关非政府组织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全球倡议”和“受教育权倡议者”。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教育和私有化声明的更多信息,参见GIESCR, Human Rights Bodies Statements on Private Education September 2014- November 2017: Synthesis Paper—Version 9, http://globalinitiative-escr.org/wpcontent/uploads/2016/10/GIESCR-CRC_CESCR_CEDAW-synthesis-statements-on-private-actors-in-education.pdf.安特诺尔·哈洛·德沃尔夫(Antenor Hallo de Wolf)在2012年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结论性意见中有关私有化的做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私有化的广泛关切非常明显,《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保障的权利受到的威胁也应该予以适当注意。然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处理私有化问题的方式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3Antenor Hallo de Wolf, Reconciling Privatization with Human Rights, Intersentia, 2012, p. 379.在哈洛·德沃尔夫所分析的结论性意见中,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均没有注意到私有化是如何影响相关权利的;相反,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只注意到私有化可能(或已经)对权利的享有产生某种负面影响,而没有用数据或具体案例适当地证明这些结论。4Ibid.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最近关注受教育权的工作确实超出了哈洛·德沃尔夫认为的范围,其向国家提出了有关私有化的问题,并在结论性意见中关注私有化对权利具体要素的影响。5更多细节参见例如GIESCR, Privatisation and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November 2014) (on fi le with author).还有一些迹象表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开始在其他经济、社会权利语境下采取类似的办法。6See, e.g., CESCR,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Fourth Periodic Repor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E/C.12/KOR/CO/4 (2017).其中,根据第2(1)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将包括私营供应商在内的行为者服务提供方面的缺陷与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源的义务(第11—12段),以及“高度私有化的卫生系统”方面存在的问题(第44—45段)联系起来。然而,探讨私有化的具体形式和过程的证据仍然非常有限:关键的国家决策机构未经审查,不同的私有化模式没有得到认定和评价。7例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2017年关于澳大利亚的结论性意见中对私营公司表示关切,如在瑙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寻求庇护者区域处理中心的服务提供机构,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负有责任,并且这些私人机构缺乏适当和独立的调查以及投诉机制。See CESCR,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Fifth Periodic Report of Australia, E/C.12/AUS/CO/5 (2017), para. 13. 然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没有讨论具体的安排或义务,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的补救措施。这种缺乏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该委员会在国家报告过程中面临的限制(时间、信息和报告字数),但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结论性意见中较为有效地讨论了其他领域的私有化,这表明它可以作出改善。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于2017年6月发表重要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之前也没有详细讨论私有化问题,特别是在其2011年“缔约国关于企业部门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义务问题的声明”中没有明确提及私有化。1CESCR, Statement on 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Parties regarding the Corporate Sector and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C.12/2011/1 (2011). 在讨论实现义务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到缔约国必须“获得企业部门对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支持”(第6段),但这与明确提及私有化相差甚远。因此,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框架如何识别侵犯人权的私有化程序和行动方面,仍有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在更详细地考虑经济、社会权利框架处理私有化的能力时,本节将重点讨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三类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作为一般性意见的一部分而发展起来)的背景下对私有化的处理。2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作出的一些决定涉及国家在私营行为者关于经济、社会权利活动中的作用,包括保护的义务。然而,这并不是在本文所设想的私有化背景下进行的。See CESCR, I.D.G. v. Spain, Communication No.2/2014, E/C.12/55/D/2/2014 (2015)(关于在抵押止赎案件中,缺乏有效的司法途径来保护充足住房的权利);CESCR, Mohamed Ben Djazia and Naouel Bellili v. Spain, Communication No.5/2015, E/C.12/61/D/5/2015 (2017)(关于私人租房者的适足住房权)。应当指出,这不是用于考虑私有化处理经济、社会权利义务的唯一办法。例如,人们可以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的国家有义务逐步实现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的角度来看待此现象。然而,这并不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私有化工作中采取的主要办法,也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3私有化问题和最大可利用资源的义务在下列文件中讨论过:Aoife Nolan, Budget Analysi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in Eibe Riedel, Gilles Giacca & Christophe Golay eds.,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Challen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369.参见下文第123页脚注3。
三类义务构成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工作的核心部分。自1999年关于食物权的一般性意见通过以来,它成为涉及实质性权利的所有一般性意见的一个惯例,4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2: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E/C.12/1999/5 (1999), para. 15.并作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界定缔约国义务的重要框架依据,包含在私有化的语境下。三类义务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被学术界、倡导者广泛采用。下文将讨论联合国其他行为者在经济、社会权利方面开展的工作。因此,该三类义务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概述的经济、社会权利规范性框架的核心要素,反映了该机构对经济、社会权利概念的理解及其相应的义务。
三类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5演变的一个关键点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工作中概述的实现义务的不同要素。有关详细信息,参见 Ida Elisabeth Koch, Dichotomies, Trichotomies or Waves of Duties?, 5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81 (2005).但关键要素可以概括为:尊重义务,要求各国不要干涉个人的经济、社会权利;6Maastricht Guidelines on Violation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26 January 1997), para. 6,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8abd5730.html.保护义务,要求各国采取措施防止他人干涉经济、社会权利的享有;7有关保护义务的更多定义,参见下文。实现义务,要求各国采取适当的立法、行政、预算、司法、宣传和其他措施,以充分实现经济、社会权利。1Paraphrased from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E/C.12/2000/4 (2000), para. 33.实现义务包括促进、便利和提供,2See, e.g., ibid., para. 37.它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中规定的在最大程度上逐步实现经济、社会权利的总体义务3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关于健康权的一般性意见中明确指出了实现义务与充分实现义务之间的联系。See ibid., para. 36.以及该公约的最终目标(即全面实现经济、社会权利)密切相关。
当关注到与私营行为者相关的国家义务时,在三类义务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分析一般以保护义务为基础。4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2: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E/C.12/1999/5 (1999), para. 15;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3: The Right to Education, E/C.12/1999/10 (1999), para. 50;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E/C.12/2000/4 (2000), para. 35;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The Equal Right of Men and Women to the Enjoyment of Al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C.12/2005/4 (2005), paras. 19-20;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7: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Benefit from the Protection of the Moral and Material Interests Resulting from Any Scientific, Literary or Artistic Production of Which He or She Is the Author, E/C.12/GC/17 (2006), para. 31;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8: The Right to Work, E/C.12/GC/18 (2006), para. 25;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9: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E/C.12/GC/19 (2008), paras. 45-46;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0: Non-Discrimination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C.12/GC/20 (2009), para. 11;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1: Right of Everyone to Take Part in Cultural Life, E/C.12/GC/21 (2009), para. 50(b);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on the Right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E/C.12/GC/22 (2016), paras. 42-43, 60.有关保护义务的更多信息,参见Aoife Nolan, Addressing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Violations by Non-State Actors through the Role of the State: A Comparison of Regional Approaches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tect”, 9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225 (2009).也即,正如该委员会经常说的那样,国家有义务防止第三方“干涉”经济、社会权利的“享有”。5参见下文第110页脚注1、2及相应的正文。同样,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在私营部门满足与经济、社会权利相关需求问题上国家所起到的作用的讨论,大部分集中在对这些行为者的规管上——这一问题在讨论保护义务的背景下十分重要。6See, e.g.,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7: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Forced Evictions, E/1998/22 (1997), para. 9;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2: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E/C.12/1999/5 (1999), paras. 19, 27;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3: The Right to Education, E/C.12/1999/10 (1999), paras. 58, 59;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E/C.12/2000/4 (2000), paras. 26, 49;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5: The Right to Water, E/C.12/2002/11 (2003), para. 44(b);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The Equal Right of Men and Women to the Enjoyment of Al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C.12/2005/4 (2005), para. 20;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7: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Benefi t from the Protection of the Moral and Material Interests Resulting from Any Scientifi c, Literary or Artistic Production of Which He or She Is the Author, E/C.12/GC/17 (2006), paras. 32, 55;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8: The Right to Work, E/C.12/GC/18 (2006), para. 35;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9: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E/C.12/GC/19 (2008), para. 46.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私有化的最广泛的声明,特别是在三类义务的背景下,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发表的。例如,健康权的保护义务包括“保证卫生部门的私营化不会威胁到提供和得到卫生设施、商品和服务,以及这些设施、商品和服务的可接受程度和质量”1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E/C.12/2000/4 (2000), para. 35.;保护工作权的义务包括“确保私有化措施不损害工人的权利”2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8: The Right to Work, E/C.12/GC/18 (2006), para. 25.。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以该方式关注私有化背景下的保护义务,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这种关注意味着私有化主要涉及的是非国家行为者在没有国家参与的情况下自行采取行动对权利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仅需要国家干涉来预防和解决影响。但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讨论的,私有化直接涉及国家(以及国家的作为/不作为),不能在没有国家允许的情况下发生,3事实上,对于私营行为者非正式的提供(商品或服务),“隐性私有化”以及由于放松管制和自由化而导致的私有化,也可以提出同样的论点,因为这发生在国家允许私营行为者作为提供者介入的情况下。尽管国家可能并非自发决定实施此类政策。4如果国际金融机构授权私营部门进行危害人权的私有化,这可能会影响这些组织成员国领土外的经济、社会权利保障义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强调:“如果缔约国将权力转移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机构,并允许它们在没有确保人权不受侵犯的情况下行使这些权力,则这些缔约国将违反其义务。”CESCR, Statement on Public Debt, Austerity Measur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C.12/2016/1 (2016), para. 9. 这肯定会扩展到贷款条件,导致违反经济、社会权利的私有化。关于各国作为政府间组织(包括国际金融机构)成员的义务的更多信息,参见Maastricht Principles on Extraterritorial Obligations of States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Principle 15, https://www.fi dh.org/IMG/pdf/maastricht-eto-principles-uk_web.pdf.因此,在笔者看来,旨在提供经济、社会权利相关商品和服务的私有化,可以而且应该被视为国家选择采取行动来实现经济、社会权利的一种手段。对于较不发达经济体,这种对私有化的理解尤为重要,因为国家无法以高效的方式向所有(或大多数)权利人提供与经济、社会权利有关的商品和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仅仅通过关注在私有化进程中保持现有的经济、社会权利享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义务。相反,更恰当的做法是将私有化视为国家选择的一种机制,从而提高经济、社会权利的现有水平。事实上,这种私有化的观点与世界银行等主体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它们主张私有化(尽管不是从权利角度),理由是相比于国家提供商品和服务,私有化将降低成本,提高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并确保在与经济、社会权利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交付方面有更好的表现。5更多(以及在与一系列经济、社会权利有关的公用事业方面对私有化进行的有用的、可利用的讨论),参见Ioannis N. Kessides, Reforming Infrastructure: Privatization,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4.
对保护义务而不是实现义务的高度重视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一个错误,或者至少未能理解私有化全貌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实现义务首先更好地体现了国家的私有化决定,而保护义务的重点在于保护现有的权利享有,注重解决私有化现状下的问题。6尊重的义务对私有化也有影响,因为它影响经济、社会权利的现有行使。由于篇幅的限制,这将不是本文的重点。此外,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从以下角度对私有化进行概念化和研究:私有化是各国为促进或加强与经济、社会权利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而采取的积极措施,而不是促使国家干预这些商品和服务现有的享有。这种方法优先考虑实现和保护的义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仅在一次关于尊重义务的情况下提及私有化。参见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1: Right of Everyone to Take Part in Cultural Life, E/C.12/GC/21 (2009), esp. para. 50(b).除指出各国有义务“尊重和保护一切群体和社区的文化遗产”外,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强调,“应特别注意全球化、产品和服务不适当的私有化,以及放松管制对参与文化生活的负面影响”。从实现义务的角度分析私有化问题,比保护义务的覆盖范围更加宽泛,而且要求国家从一开始就考虑私有化是否符合经济、社会权利,还需要评估私有化对经济、社会权利实现的整体影响。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仅在两个场合下在讨论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义务中明确提到私有化问题——分别是2000年“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的第14号一般性意见”和2003年“关于水权的第15号一般性意见”。在上述讨论中,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强调“其他义务包括提供所有人都能支付得起的公共、私营或混合健康保险制度”1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E/C.12/2000/4 (2000), para. 36.,各国必须确保“供水设施无论是私人还是公共组织经营”,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2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5: The Right to Water, E/C.12/2002/11 (2003), para. 27.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他一般性意见中也作了类似的声明,但未明确说明实现的义务。See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5: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1995/22 (1994), para. 11.然而,这两项一般性意见都在各自的章节中对私有化下的保护义务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并指出,“保护的义务,主要包括各国有责任通过法律或采取其他措施,保障有平等的机会得到第三方提供的卫生保健和卫生方面的服务;保证卫生部门的私营化不会威胁到提供和得到卫生设施、商品和服务,以及这些设施、商品和服务的可接受程度和质量”3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E/C.12/2000/4 (2000), para. 35.。
此外,“如果供水设备(如供水管网、储水罐、河和井的取水口)由第三方经营或控制,缔约国必须防止它们损害以平等、经济、便利的方式获取足够、安全和可接受的水的权利。为防止此种滥用行为,必须按照《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本一般性意见建立有效管理机制,包括独立监督、真正的公众参与和对违约的处罚等”4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5: The Right to Water, E/C.12/2002/11 (2003), paras. 23, 24.。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注的问题也经常在学术文献中被提到。5See, e.g., Felipe Gómez Isa, Globalisation, Privatis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Koen De Feyter & Felipe Gómez Isa eds., Privatis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Intersentia, 2005, p. 9, 21(“处理私有化,保护的义务是最相关的义务,因为它要求各国防止第三方侵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旦私营行为者接管了这些服务,各国必须确保这些权利得到一贯的保护”)。See Khulekani Moyo & Sandra Liebenberg, The Privatization of Water Services: The Quest for Enhanced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37 Human Rights Quarterly 691, 700 (2015).国家保护人权不受非国家行为者侵犯的义务经常被作为反对承认非国家行为者直接承担人权义务的必要性的论据提出。保护的义务要求国家积极采取行动,规范、防止和补救非国家行为者的干涉。在水权范围内,国家保护的义务要求国家“规范私人交往,确保个人不被其他私人和团体任意剥夺其享有的水权”。如(本文)前一节所述,私营部门参与供水可能引起一系列人权问题,使国家的保护义务成为必要的。(Footnotes omitted) (quoting Matthew Crave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 Perspective on Its Development, Clarendon Press, 1995, p. 112.) 安东·科克(Anton Kok)在关于《南非宪法》规定的获得充足水的权利方面的文章,为普遍不注意水权规定的“实现”(实际上是“尊重”)义务提供了一个例外。See Anton Kok, Privatisation and the Right to Access to Water, in Koen De Feyter & Felipe Gómez Isa eds., Privatis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Intersentia, 2005, p. 259, 282(“在适当的情况下,法院也可能会发现国家已经‘实现了’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私有化计划来促进获取水资源的义务”)。同样在水权方面,丹伍德·奇尔瓦(Danwood Chirwa)对水私有化背景下尊重和实现人权义务的影响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See Danwood Mzikenge Chirwa, Privatisation of Water in Southern Africa: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4 African Human Rights Law Journal 218, 232-240 (2004).在介绍私有化和人权领域的主要文献时,科恩·德费特(Koen De Feyter)和费利佩·戈麦斯·伊萨(Felipe Gómez Isa)引用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99年“关于公共部门活动私有化”的报告,1本文没有完整地引用该文:Koen De Feyter & Felipe Gómez Isa, Privatisation and Human Rights: An Overview, in Koen De Feyter & Felipe Gómez Isa eds., Privatis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Intersentia, 2005, p. 1.描述了政府在私有化的背景中从生产和提供服务的角色转向扶持和管理的角色。2Ibid.对德费特和戈麦斯·伊萨来说,“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当国家在提供服务方面的角色发生变化时,国家如何能够确保履行其人权义务”3Ibid., p. 2.。这无疑是主要问题。但是,在评估各国履行其国际义务的情况时,有必要对各国关于选择服务提供的决定采取质询(必要时采取批评的观点)。这不是简单地说:“这是我们选择的模型,所以现在让我们根据它来分析国家的义务。”国家采用私有化模式作为其最终实现经济、社会权利的总体努力的一部分;就保护义务的产生而言,它是在作出私有化的决定之后才发生的,(而)最初进行私有化的决定(本身)也会影响经济、社会权利。德费特和戈麦斯·伊萨认为:“国家不能通过将服务委托给私营行为者来免除其国际人权义务。即使相关服务已私有化,国家仍应根据人权条约承担责任。……然而,国家为避免违反其人权义务而需要在国内层面采取的行动确实发生了变化。……在私有化之后,国家需要更加重视提供保护的责任,以防止第三方(即接管提供服务责任的私营行为者)对人权的侵害。只有国家制定了监督私营机构提供服务对人权之影响的工具,以及在侵害人权时介入的工具,国家才能提供保护。”4Ibid., p. 3. 应当指出,在这项研究中德费特和戈麦斯·伊萨概述的三类义务不同要素的定义存在一些重大问题,有人认为尊重义务涉及“人们可以自我提供的权利”和当“人们不能自我提供时”予以实现该权利的义务。这不符合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任何一般性意见中对这些义务的界定。讽刺的是,这些作者都将保护的义务视为“防止第三方侵犯人权”,这更接近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该义务的当代处理方式,而不是委员们提出这一观点时的状况。
尽管德费特和戈麦斯·伊萨明确指出“在私有化后预先关注监管能力的维持是必要的”5Ibid., p. 4.,但这种预先关注也应被视为实现义务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保护义务。在教育权的研究领域,丰斯·库曼斯(Fons Coomans)和哈洛·德沃尔夫指出:“在私有化领域,国家保护的一般性义务似乎特别重要,因为国家必须确保一旦私人机构负责教育服务,学习的人仍可以充分享有受教育权。”6Fons Coomans & Antenor Hallo de Wolf, Privatis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Right to Education, in Koen De Feyter & Felipe Gómez Isa eds., Privatis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Intersentia, 2005, p. 229, 239 (emphasis added). 有趣的是,从本文讨论的角度来看,库曼斯和哈洛·德沃尔夫继续指出“在教育领域开始私有化的决定……从人权的角度来看,不应增加社会的不平等,而应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第240页)。他们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有义务尊重现有的保护水平,或者换句话说,放弃那些在特定时刻会降低受教育权保障程度的措施”(第240页)。这种对国家义务的理解似乎带来了尊重和实现经济、社会权利义务的要素,但库曼斯和哈洛·德沃尔夫没有在该部分研究中探讨甚至提及这些义务,尽管他们确实承认,如果私有化政策不满足教育的可获得性、可及性、适应性和可接受性的要求,那么“国家有责任放弃这些措施(换句话说,国家有义务尊重受教育权的享有)”(第253页)。
关注保护义务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历来处理这一义务的核心是防止和解决第三方“干扰”个人对经济、社会权利的享有。1See, e.g.,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2: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E/C.12/1999/5 (1999), para. 15(“保护的义务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确保企业或个人不得剥夺个人取得足够粮食的机会”);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3: The Right to Education, E/C.12/1999/10 (1999), para. 47(“保护的义务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防止第三方干扰受教育权利的享受”);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E/C.12/2000/4 (2000), para. 33(“保护的义务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防止第三方干预第12条规定的各项保证”);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5: The Right to Water, E/C.12/2002/11 (2003), para. 23(“这类义务要求缔约国防止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干预水权的享有”);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6: The Equal Right of Men and Women to the Enjoyment of Al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C.12/2005/4 (2005), para. 19(“本《公约》第3条对缔约国规定的保护的义务主要包括……通过法律消除歧视,并防止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地干涉这项权利的享受”);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7: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Benefi t from the Protection of the Moral and Material Interests Resulting from Any Scientifi c, Literary or Artistic Production of Which He or She Is the Author, E/C.12/GC/17 (2006), para. 28(“保护的义务意味着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防止第三方干涉作者的物质和精神利益”);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8: The Right to Work, E/C.12/GC/18 (2006), para. 22(“保护的义务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防止第三方妨碍享有工作权利”);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9: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E/C.12/GC/19 (2008), para. 45(“保护的义务要求缔约国防止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干预社会保障权利的享有”);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1: Right of Everyone to Take Part in Cultural Life, E/C.12/GC/21 (2009), para. 48(“保护的义务要求缔约国采取步骤,防止第三方干涉人们享有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on the Right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E/C.12/GC/22 (2016), para. 42(“保护的义务要求国家采取措施,防止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干涉享有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3 (2016) on the Right to Just and Favourable Conditions of Work, Doc. E/C.12/GC/23 (2016), para. 59(“保护的义务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确保包括私营部门雇主和企业在内的第三方不干扰人们享有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并遵守自己的义务”)。这影响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处理私有化对经济、社会权利造成损害的能力,而这些损害不是由“干涉”造成的。即使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处理了由第三方运作或控制与经济、社会权利相关的供应体系的情况,但在其一般性意见中对保护义务的判例,基本上国家都是被动的:国家被要求确保当事方不损害与经济、社会权利有关的商品和服务的享有或获取,而不是被要求在授予私有化许可时,首先详细审查当事方对权利的遵守情况(以及确定这种许可的适当范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明确表示各国必须确保私有化不“构成威胁”、干扰或破坏与经济、社会权利有关的设施、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获取、可接受性和质量时,2See, e.g.,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2: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E/C.12/1999/5 (1999), para. 15(“保护的义务要求国家采取措施,确保企业或个人不剥夺个人获得充足食物的权利”);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3: The Right to Education, E/C.12/1999/10 (1999), para. 50(“一国必须……保护教育的可获取性,确保第三方,包括父母和雇主在内,不阻止女童入学”);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E/C.12/2000/4 (2000), para. 35(“保护的义务,主要包括各国……保证卫生部门的私营化不会威胁到提供和得到卫生设施、商品和服务,以及这些设施、商品和服务的可接受程度和质量”);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5: The Right to Water, E/C.12/2002/11 (2003), para. 24[“如果供水设备(如供水管网、储水罐、河和井的取水口)由第三方经营或控制,缔约国必须防止它们损害以平等、经济、便利的方式获取足够、安全和可接受的水的权利”];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8: The Right to Work, E/C.12/GC/18 (2006), para. 25(“保护工作权的义务,除其他外,包括缔约国有责任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确保平等获得工作和培训,确保私有化措施不损害工人的权利”);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9: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E/C.12/GC/19 (2008), para. 46(“如果社会保障计划,无论是缴费性还是非缴费性的,是由第三方经管和控制的,缔约国必须负责管理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并且确保私营行为者不会损害平等的、适当的、可负担的以及可及的社会保障”);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2 (2016) on the Right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E/C.12/GC/22 (2016), para. 42(“保护的义务要求国家制定和执行法律和政策,禁止第三方的行为造成身心伤害或有损充分享有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包括私人医疗保健设施……这包括禁止暴力和歧视性做法,例如在提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时将某些个人或群体排除在外”);Ibid., para. 60(“国家必须有效地监督和规范特定部门,如私人医疗保健提供者……以确保它们不会破坏或侵犯个人享有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其所使用的措辞似乎表明,这类设施、商品和服务的可用性、可获得性、可接受性和质量是默认所需的,而私有化潜在地违反了这些要求。虽然这可能仅仅是言语选择不当的问题,但这种措辞的效果是,国家未能将私有化作为一种积极的举措,这包括对第三方进行授权(在某些情况下是激励),而非由其自发出现,且国家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被动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用尊重、保护和实现三类义务处理私有化是没有问题的,“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的第14号一般性意见”1参见前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健康权和水权的一般性意见。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当国家没有进行相关审查时,那么在私有化的关键阶段,决策与执行会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尊重、保护和实现义务对私有化的(错误)定性,会缩小私有化下的人权保护范围。
萨米拉·默西(Sharmila Murthy)所说的“保护和实现存在着一种相反的关系:一个国家越是将其责任委托给一个非国家行为者,其保护的义务就越大”2Sharmila L. Murthy, The Human Right(s) to Water and Sanitation: History, Meaning, and the Controversy over Privatization, 31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9, 143 (2013).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默西在文章的其他地方明确指出,“国家不能通过涉及私营部门而逃避其责任,而是保留其保护、尊重和实现权利的义务”(第148页)。并不准确;虽然国家可以将其责任委托给第三方(从其运营意义上来说),并在保护义务方面加强行动,但其在国际人权法方面负有的实现义务仍然与以前一样。进行私有化不会使得实现义务仅在没有非国家行为者参与时才生效。相反,实现义务首先和国家进行私有化的决定直接相关,与之相关的还有任何此类私有化安排所采取的形式,以及评估该安排在推进或破坏经济、社会权利整体实现方面的成功与否。鉴于在私有化问题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历来强调“干涉”情况,而不是非国家行为者在私有化背景下对经济、社会权利享有造成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因此该委员会在关注保护义务时,未能有效考虑到上述私有化决策。
虽然实现义务在私有化过程中是基础并与私有化密切相关,但保护义务[这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传统理念,并反映在亨利·舒(Henry Shue)、阿斯布佐恩·艾德(Asbjørn Eide)等人的文章中,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基础工作方法]3See Henry Shue, The Interdependence of Duties, in Philip Alston & Katarina Tomaševski eds., The Right to Food, Martinus Nijhoff, 1984, p. 83(强调“保护免受剥夺”的义务);UN Sub-Commission on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The Realiza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Report Updating the Study on the Right to Food Prepared by Mr. Asbjørn Eide, E/CN.4/Sub.2/1998/9 (1998), para. 9(关切“国家的义务要求国家采取积极保护措施,以防其他争强好胜的主体——更为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侵害他人权利,如防止欺诈行为,防止贸易和契约关系中的不道德行为,以及防止推销或倾弃有害或危险产品等”)。有关舒和艾德的作品在三类义务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其他三类义务概念的更多信息,参见 Ida Elisabeth Koch, Human Rights as Indivisible Rights: The Protection of Socio-Economic Demands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Brill, 2009, p. 14-17.主要在经济、社会权利语境下发挥作用。被授权履行与经济、社会权利商品和服务提供有关的职能的行为者(如前所述,本文仅关注有正式授权的情况),其提供的行为会威胁或损害现有权利的享受,例如,私营公司将价格提高到超出可承受的水平,从而影响现有的权利享有水平。由于上述行为者未能促进经济、社会权利的享有(这将涉及履行义务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的逐步实现的首要义务),那么它们将不能够参与私有化。如果我们考虑私有化不会干扰(即减少/消极影响)在私有化之前经济、社会权利享受的情况,那么从保护义务的角度来看,私有化是可行的。事实上,这种私有化并没有使得国家在实现经济、社会权利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这并不是问题。然而,从实现义务的角度来看,如果重点是实施积极措施从而全面实现目标,那么上述维持现状的做法是否可行就是值得怀疑的。当然,这不属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的逐步实现的义务,除非国家能够指出其他补充措施,确保国家“尽可能有效地迅速”实现“充分实现经济、社会权利”的目标。1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3: The Nature of States Parties’ Obligations, E/1991/23 (1990), para. 9.笔者并不是说,第2条第1款规定的逐步实现直接对应于实现的义务。然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所设想的两者之间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家努力确保按照第2条第1款逐步实现的义务所设想的增强对权利的享有的背景下,实现的义务在明确国家义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从实现义务的角度考虑私有化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应根据实现义务的组成要素——便利、促进和提供的义务——来考虑这种活动。在私有化进程之前、期间和之后提出的问题将包括:私有化安排是否能够帮助个人和社区享受有关的经济、社会权利(即是否会为该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提供便利)?私有化是否会导致对有关经济、社会权利的教育的增加或公众意识的增强(即是否会促进该经济、社会权利)?私有化是否有利于为那些无法通过现有途径实现自身权利的人提供保障(即是否会提供经济、社会权利)?2在一系列一般性意见中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描述了实现的义务,这些问题是以委员会在其中所使用的语言为基础的。这种义务分类方式是在第12号一般性意见中介绍的。只有在第14号一般性意见中,“促进”义务的组成部分才被加入,以补充第12、13号一般性意见。See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2: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E/C.12/1999/5 (1999);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3: The Right to Education, E/C.12/1999/10 (1999);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E/C.12/2000/4 (2000).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的充分实现经济、社会权利的最终目标,评估国家将在多大程度上构想和采用私有化,以促进经济、社会权利的享有。
(二)从不同角度(有时)得到相似结论?联合国其他条约监督机构在经济、社会权利与私有化方面的工作
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以外的涉及经济与社会权利职责的条约监督机构,即使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私有化的讨论相对有限,也比从种族、残疾、移徙工人和性别平等角度评估经济、社会权利落实的四个联合国条约监督机构更为深入。这些机构在其一般性意见/建议,或者一般性讨论/专题讨论建议日中,在处理私有化的形式、进程、产出和成果方面或详细说明私有化的具体负面影响方面,都没有取得比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更大的进展。1哈洛·德沃尔夫注意到:“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的做法一般都承认私有化是各国可以采取的一种措施,但有时可能会对享有人权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并不总是清楚一些条约机构在什么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私有化可能对人权产生不利影响,或在何种特定条件下可能发生这种情况。”Antenor Hallo de Wolf, Reconciling Privatization with Human Rights, Intersentia, 2012, p. 394-395.虽然哈洛·德沃尔夫在2012年提出了这一点,但此观点在2018年仍然是正确的。本节的分析仅侧重于一般性意见、建议和一般性讨论日,因为这些是机构们涉及经济、社会权利与私有化的关键内容。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委员会已明确表示,私营行为者可能制造和加剧经济、社会权利享受方面的歧视,2Se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CER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XXIX on Article 1, Paragraph 1, of the Convention (Descent), HRI/GEN/1/Rev.9 (Vol. II) (2008), p. 300, ch. 7; CER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XX on Article 5 of the Convention, HRI/GEN/1/Rev.9 (Vol. II) (2008), p. 282, para. 5(重点关注“私人机构”对“权利的行使或机会的获得”的影响)。See generally CER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XIX on Article 3 of the Convention, HRI/GEN/1/Rev.9 (Vol. II) (2008), p. 281, paras. 3-4.特别是教育方面,3See CER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XXIX on Article 1, Paragraph 1, of the Convention (Descent), HRI/GEN/1/Rev.9 (Vol. II) (2008), p. 301, ch. 8; CERD,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4: Ra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 CERD/C/GC/34 (2011), para. 62.即使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私有化。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也关注私营行为者对教育的影响,特别是包容性教育,指出“缔约国必须确保残疾人能够平等地在公立和私立学术机构接受教育”4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General Comment No. 4 on the Right to Inclusive Education, CRPD/C/GC/4 (2016), para. 24.。在这方面,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强调,保护的义务“需要采取措施,例如防止第三方干涉权利的享有。例如……防止私立机构以残疾人的缺陷为由拒绝招收残疾人”,但也强调实现的义务“需要采取措施,使残疾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例如,确保教育机构的可获得性,以及教育系统与资源和服务相适应”。5Ibid., para. 39.这可能适用于私立教育系统,因此暗含对私有化的讨论。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确保经济、社会权利相关商品和服务(包括私有化的商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其明确指出:“重点已经不再是拥有建筑物、交通基础设施、车辆、信息和通信以及服务之‘人’的法人地位及其公共和私人性质。只要货物、产品和服务对公众开放或者向公众提供,它们必须能够为所有人利用。……根源是禁止歧视;剥夺无障碍利用的机会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歧视性行为,不管这种行为者究竟是公共实体还是私人实体。”6CRPD, General Comment No. 2: Article 9: Accessibility, CRPD/C/GC/2 (2014), para. 13. See also CRPD, General Comment No. 5: Article 19: Living Independently and Being Included in the Community, CRPD/C/GC/5 (2017), para. 53.
遗憾的是,从三类义务的角度来看,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私主体行为的语境下对三类义务的不同要素的理解有些混乱。例如,在“关于独立生活和融入社区的第5号一般性意见”中它指出,尊重义务的“积极方面”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9条所赋予的权利不受国家或私营实体的侵犯”。7Ibid., para. 40.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似乎将尊重和保护的义务混为一谈,尽管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一般性意见中对后一项义务进行了广泛讨论。8Ibid., paras. 50-54.
移徙工人委员会还讨论了移徙工人及其家人因私有化而面临的风险,强调了私人经营的移徙者拘留中心在监督上造成的“特殊困难”,并明确提出,“对移徙工人的行政拘留通常应在公营场所进行”,以及“缔约国并不能因为将拘留个人的活动承包给私营商业企业而免除国家所应承担的人权义务”。1Committee on Migrant Workers, General Comment No. 2 on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in an Irregular Situation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CMW/C/GC/2 (2013), para. 39.另参见移徙工人委员会关于移徙工人在非正常情况下遭受私营行为者暴力的声明,第21段。移徙工人委员会与儿童权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一般性意见,强调了私人服务提供者在适足生活水准权方面的作用,但是指出“各国应制定程序和标准,在公共或私人服务提供者(包括公共或私人住房提供者)与移民执法机构之间建立防火墙”2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and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Joint General Comment No. 4 (2017)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and No. 23 (2017)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Human Rights of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MW/C/GC/4-CRC/C/GC/23 (2017), para. 52.移徙工人委员会还强调,各国应确保私营行为者(如房东和民间社会组织)不会因帮助非正常移民儿童行使住房权而被定罪。这包括私人住房的提供者。。然而,移徙工人委员会并未明确探讨私有化背景下的三类义务。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仅相对有限地提及私有化,尽管《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2(e)条提到了私有化,以及缔约国有义务“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任何个人、组织或企业对妇女的歧视”3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dopted 18 December 1979, G.A. Res. 34/180, U.N. GAOR, 34th Sess., U.N. Doc. A/34/46 (1980), 1249 U.N.T.S. 13 (entered into force 3 September 1981).。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一次在一般性建议中使用“私有化”一词是在2016年:在“关于农村妇女权利的第34号一般性建议”中,它指出,缔约国“应该消除包括私有化……在内的经济政策给农村妇女的生活及其权利的实现造成的消极和有差别的影响。同样,发展伙伴也应确保其发展援助政策侧重于农村妇女的具体需要”4应当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似乎是指“落实”,而不是实现义务。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4 (2016) on the Rights of Rural Women, CEDAW/C/GC/34 (2016), para. 11.。
从三类义务的角度来分析,积极的一面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明确将私有化视为能够对国家尊重、保护和实现义务产生影响的因素。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其第24号一般性建议中对妇女与健康专题进行分析时指出:“尊重的义务要求各缔约国不采取阻碍妇女为寻求健康而采取的行动。”5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Article 12 of the Convention (Women and Health), A/54/38/Rev.1 (1999), para. 14.其中包括“缔约国应提供报告,介绍公私营保健部门如何履行它们尊重妇女获得保健权利的责任”6Ibid.。然而,这是一个相当含糊的说法。根据国际人权法,尊重的义务属于国家,而不是私营医疗提供者。如果要将这样的说法解读为符合对这一义务的理解,那么“它们(尊重妇女获得保健权利)的责任”就必须理解为是针对国家,而不是针对提供者。虽然在保护的义务范围内未明确提及私有化,但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明确表示,该义务要求各缔约国“采取行动,防止个人和组织违反这些权利,并对违反行为进行制裁”1Ibid., para. 15.。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私有化最详细的声明是在该一般性建议中讨论实现义务时提出的,它关切的是:“各国正在将保健职能转交给私营机构,从而日益明显地表明它们正在放弃自己的责任。缔约国不能通过将这些权力下放或转交给私营部门的机构来免除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责任。因此,缔约国必须报告它们做了什么,以组织政府系统以及各种机构来行使国家权力促进和保护妇女健康。它们应报告采取了哪些积极措施,以制止第三方侵犯妇女权利、保护她们的健康,以及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提供此类服务。”2Ibid., para. 17.
尽管如此,根据有关《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2条的第28号一般性建议所划定的缔约国核心义务,针对私营行为者的禁止歧视义务只是一种保护的义务。3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on the Core Obligations of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C/GC/28 (2010), para. 9.在该一般性建议中,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强调,各国需要防止和解决私营和公共领域的歧视问题,以使其明显适用于私有化的情况。4Ibid., paras. 10, 25, 34.此外,同样不是在三类义务的背景下,讨论防止私营行为者的歧视归咎于国家的“尽职调查”义务时(一般与保护义务有关),5See Aoife Nolan, Addressing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Violations by Non-State Actors through the Role of the State: A Comparison of Regional Approaches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tect”, 9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225 (2009).有关尽职调查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保护的义务之间关系的最新示例,参见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0 on Women in Conflict Preventio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ituations, CEDAW/C/GC/30 (2013), para. 15.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第24号一般性意见中也提出了这种联系。See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4 on State Obligation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Business Activities, E/C.12/GC/24 (2017), paras. 15-16, 32-33.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强调:“缔约国有义务采取的适当措施包括,在涉及教育、就业、医疗的政策和做法、工作条件和工作标准,以及例如银行和住房等由私营行为者提供服务或设施的其他领域中,对私营行为者的行动进行监管。”6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on the Core Obligations of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C/GC/28 (2010), para. 13.在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后来关于国家法律授权的私营行为者“行使政府权力的部分,包括提供保健或教育等公共服务的私营机构”7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5 on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Updating General Comment 19, CEDAW/C/GC/35 (2017), para. 24.的工作中,也明显体现了类似的做法。这也可以理解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概述了在目前私有化语境下与保护有关的措施。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于2017年11月提出的“关于女童和妇女受教育权的一般性建议”直接涉及私有化问题,强调了将教育外包给非国家行为者与经济危机之间的联系。8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6 on the Right of Girls and Women to Education, CEDAW/C/GC/36 (2017), para. 38.在这份建议中,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指出“私有化对女童和妇女具有特定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来自贫穷家庭的女童,使其无法受教育”,并敦促各缔约国采取一系列行动确保使用费和其他隐形费用(以及在私营行为者提供教育的情况下所施加的费用)不会对女童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产生负面影响。1Ibid., paras. 38, 39.然而,它并没有把私有化的讨论放在三类义务的框架下进行。这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随后的一般性建议中讨论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它认为缔约国应“采取监管措施,保护妇女免遭私营企业行为者造成的侵犯人权行为,并确保其自身的活动,包括那些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合伙进行的活动,尊重和保护人权”2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7 on Gender-Related Dimensions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CEDAW/C/GC/37 (2018), para. 51(d).。
归根结底,上述几个委员会的做法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一样,都是对私营行为者影响的根本关切,但除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24号一般性建议外,对私有化如何涉及三种义务的不同要素的考虑有限。除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外,迄今为止最关注私有化问题的联合国条约监督机构是儿童权利委员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我们迄今一直在讲述的关于联合国条约机构参与处理这些问题的做法截然不同的版本。儿童权利委员会明确指出,私营部门和私有化安排可在“提供和管理对儿童享有权利至关重要的服务方面发挥作用,如清洁水、卫生设施、教育、交通、保健、替代照料、能源、安全和拘留设施等”3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 General Comment No. 16 on State Obligations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Sector on Children’s Rights, CRC/C/GC/16 (2013), para. 33.。然而,儿童权利委员会认识到,服务私有化进程可能对认识和实现儿童权利产生严重影响,并强调了私有化进程必须达到的标准。4CRC, General Comment No. 5: General Measure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GC/2003/5 (2003), para. 42.
儿童权利委员会对其工作与“非政府组织或传统国企”的“高度相关性”表达了关切,因此在2002年举行了“一般性讨论日”(Day of General Discussion)。5CRC, The Private Sector as Service Provider and Its Role in Implementing Child Rights, contained in CRC, Report on the Thirty-First Session, CRC/C/121 (2002), paras. 630-53, 633.该讨论日的核心是将考虑私有化安排对“充分实现”6Ibid., para. 634 (emphasis added).儿童权利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放在首要和核心位置。与会者一致认为,《儿童权利公约》第4条的总体义务要求各国“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落实这些权利”7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20 November 1989, 1577 U.N.T.S. 3, Art. 4.,而“缔约国在处理非国家服务提供者问题时应将第4条也作为一项基本规定予以考虑”8CRC, The Private Sector as Service Provider and Its Role in Implementing Child Rights, contained inCRC, Report on the Thirty-First Session, CRC/C/121 (2002), para. 645.。一般性讨论日确立下来的目标是“具体规定缔约国在私有化和/或私营部门筹资方面的责任,确保以不歧视的、公平的和可以承受的方式提供服务,特别是为边缘化的群体提供服务,同时确保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可持续性”9Ibid., para. 634.。此外,儿童权利委员会还规定了“有关管制和监测私营部门活动的义务,其中包括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采用以权利为基础的做法”10Ibid.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目标是“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确定和加强对于营利或非营利的私营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和义务的认识”。这里将不对此进行讨论。。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当时特别强调了“包括旨在满足卫生保健、教育和饮用水等基本需要之服务提供的私有化趋势的增加”,并指出这引起了“许多困难和复杂的问题,而且问题尚未充分得到解决。事实上,人权条约机构从来就没有处理过这些问题”。1CRC, The Private Sector as Service Provider and Its Role in Implementing Child Rights, contained in CRC, Report on the Thirty-First Session, CRC/C/121 (2002), para. 640.这一声明可被视为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工作委婉的侧面批评。在该一般性讨论日中,儿童权利委员会向国家提出的广泛建议的部分内容,最终分别在1年和12年后纳入儿童权利委员会第5号和第16号一般性意见。2一般建议日讨论还载有对非国家的服务提供者的建议和评论,ibid., para. 653. 这里将不对此进行讨论。
在“关于执行《儿童权利公约》的一般措施的第5号一般性意见”中,儿童权利委员会强调“使私营部门具有提供服务、经管机构等能力,绝不能减少国家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儿童的所有权利得到充分承认和实现之义务”3CRC, General Comment No. 5: General Measure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GC/2003/5 (2003), para. 44.第3条第1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共还是私营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第3条第3款要求主管当局(有适当法律权限的机构),尤其是在健康以及工作人员数量和资格方面,制定适当的标准。这就需要实行严格的检查措施,以确保《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得到遵守。儿童权利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应建立一种常设监督机制或过程,以便确保所有国家和非国家服务提供者都能做到遵守《儿童权利公约》。。而且儿童权利委员会认为“确保非国家服务提供者按照《儿童权利公约》规定行事的义务,从而使此种行为者也承担间接义务”4CRC, General Comment No. 5: General Measure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GC/2003/5 (2003), para. 43.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对国家施加责任,以确保非国家行为者按照《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行事,从而对这些非国家行为者产生“间接义务”。。根据国际人权法的规定,这些义务对这些私营行为者不具有强制执行力。5这与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确定的非国家行为者的其他职责一致,例如父母和儿童的法定监护人的职责。Se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20 November 1989, 1577 U.N.T.S. 3, Arts. 5, 18, 27.然而,在私有化语境下的国家义务方面,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缔约国“负有按照《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尊重和确保儿童权利的法律义务,包括确保非国家服务提供者按照《儿童权利公约》规定行事的义务”6CRC, General Comment No. 5: General Measure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GC/2003/5 (2003), para. 43.。该一般性意见建议,应建立一个常设的监督机制或过程,以确保所有非国家服务提供者都遵守《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7Ibid., para. 44.
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其2013年“关于商业部门对儿童权利的影响方面国家义务的第16号一般性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儿童权利公约》与私有化之间的关系。8CRC, General Comment No. 16 on State Obligations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Sector on Children’s Rights, CRC/C/GC/16 (2013), para. 15.为了突出私有化的发展趋势,9Ibid., para. 1.儿童权利委员会表示,“各国必须确保影响商业活动和业务的立法和政策,如私有化……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核心”10Ibid., para. 15. 关于这一观点的更多内容,参见CRC, General Comment No. 14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Have His or Her Best Interests Taken as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CRC/C/GC/14 (2013), paras. 1, 12.。此外,虽然儿童权利委员会没有规定提供经济、社会权利相关(和其他权利相关)服务的形式,但它强调,各国在外包或私有化影响儿童权利实现的服务时,不能免除其在《儿童权利公约》项下的义务。儿童权利委员会明确讨论了三类义务,重申各国在委派或外包其职能时,不能免除其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及议定书承担的义务。1CRC, General Comment No. 16 on State Obligations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Sector on Children’s Rights, CRC/C/GC/16 (2013), para. 25.在这样做时,它强调了尊重义务“意味着国家不得直接或间接为任何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提供便利以及协助或教唆实施这类行为”;此外,国家还有义务确保所有行为者尊重儿童的权利,包括在商业活动和业务中。2Ibid., para. 26.
考虑到我们在其他条约监督机构的做法方面所看到的情况,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但从本文提出的与三类义务有关的讨论以及条约监督机构所愿意给出的意见所具有的较宽泛的性质来看,却是令人失望的)。儿童权利委员会强调:当考虑到各国在商业部门方面的义务时(当然,这些义务超出了私有化的范围),保护义务“极其重要”,并明确要求国家采取一切“必要、适当和合理的措施,防止商业企业造成或促成对儿童权利的侵犯”。3Ibid., para. 28.根据儿童权利委员会的说法,这些措施可以包括“通过法律法规、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采取政策以规定商业企业如何影响儿童权利”4Ibid.。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保护义务的声明并未具体提及私有化,在阐述该义务所需的具体措施时,它非常注重建立一个有效的规范性法律框架。5Ibid., para. 32.
在为儿童权利提供服务的背景下审视国家义务时,6虽然该讨论在关于实现义务的一般性意见一节之后进行,但可以理解为与该义务有关,因为儿童权利委员会先前强调“实现的义务要求各国采取积极行动,以便利、促进和提供享受儿童权利”[Ibid., para. 29 (emphasis added)],以及第33段末尾所指的“实现”儿童权利。但是,笔者不愿意断言,儿童权利委员会只因本节所列措施与尊重和保护的义务也有明确的关系,则特意将本节与实现的义务联系起来。儿童权利委员会规定,各国必须“采取考虑到私营部门参与提供服务的具体措施,确保《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权利不受损害”7CRC, General Comment No. 16 on State Obligations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Sector on Children’s Rights, CRC/C/GC/16 (2013), para. 34.。这包括一项义务,即“制定与《儿童权利公约》相一致的标准,并予以密切监督”8Ibid.。这可被视为与保护和实现有关的要求。儿童权利委员会还明确表示,“服务的提供特别根据免遭歧视原则,不会基于歧视性标准而影响儿童获得服务”9Ibid.。在私有化和更广泛的范围内(“针对所有服务部门”)10Ibid.侵犯权利的补救措施方面,国家应当确保(在所有服务部门)为儿童提供独立监测机构和申诉机构,并在必要时诉诸司法。在先前第5号一般性意见的基础上,儿童权利委员会建议“应当建立常设监测机制或程序,以确保所有非国有服务提供者都能制定和实施符合《儿童权利公约》的政策、方案和程序”11Ibid.。
这些都是儿童权利委员会就私有化发表意见的关键实例,它也在有关儿童早期议题的文件中谈到了这一问题,其中儿童权利委员会在不同的一般性意见中分别用专门的一节讨论“私营部门作为服务提供者”12CRC, General Comment No. 7: Implementing Child Rights in Early Childhood, CRC/C/GC/7/Rev.1 (2006), esp. para. 32 on “the private sector”.、少年司法13CRC, General Comment No. 10: Children’s Rights in Juvenile Justice, CRC/C/GC/10 (2007), para. 20.、健康等内容,在相关一般性意见中列入了“非国家服务提供者和其他非国家行为者”内容;1CRC, General Comment No. 15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the Enjoyment of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CRC/C/GC/15 (2013), paras. 79-85.预算方面,在不同一般性意见中,儿童权利委员会多次提到外包,呼吁各国确保有资源和能力对外包给私营部门的服务2CRC, General Comment No. 19 on Public Budgeting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CRC/C/GC/19 (2016), paras. 85, 100.,包括对移民3参见上文关于儿童权利委员会与移徙工人委员会联合文件的讨论。、街头儿童的服务进行监督和预算分析。对此,儿童权利委员会在相关一般性意见中说明国家在非国家行为者的责任、规定和协调方面的作用,并概述国家建立、维持和监督非国家行为者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以及支持、提供资源、授权、规管和监督非国家行为者的义务。4CRC, General Comment No. 21 on Children in Street Situations, CRC/C/GC/21 (2017), paras. 15, 47.在“关于儿童将他或她的最大利益列为一种首要考虑的权利的第14号一般性意见”中,儿童权利委员会明确,为遵守《儿童权利公约》第3(1)条规定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私营社会福利机构”包括“私人机构——不论是营利还是非营利性的机构——均发挥着作用,为儿童享有其权利提供服务,代表政府或作为政府服务的备选”。5CRC, General Comment No. 14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Have His or Her Best Interests Taken as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CRC/C/GC/14 (2013), para. 26. See also CRC, General Comment No. 5: General Measure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GC/2003/5 (2003), para. 44.
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儿童权利委员会从不同义务的角度认真考虑了私有化的方式,并认识到私有化不仅仅是一个控制独立的、主动干预儿童权利的第三方的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国家对充分落实儿童权利的选择。虽然儿童权利委员会没有明确地将私有化与三类义务的任何层次联系起来,但在概述三类义务的每个要素时,儿童权利委员会通过其一般性的表述明确表示私有化可能涉及其中的任何一个或所有要素,而不是狭隘地或隐含地将私有化问题的考量限制在保护义务层面。全面理解私有化对经济、社会权利的影响,是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历来采用的只重视“保护义务”的做法以及对我们讨论过的其他机构分析方法的重大进步。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做法证明了桑德拉·利本伯格(Sandra Liebenberg)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复杂的职责模式适用于国家实施的私有化计划,在此基础上,国际人权法下的法律框架概念不能仅限于一套职责。6E-mail from Sandra Liebenberg, H.F. Oppenheimer Chair in Human Rights Law, Department of Public Law,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to author (20 October 2016) (on fi le with author).相比之下,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主要关注的是国家义务中间接横向的保护义务,而不是国家义务中直接纵向的实现义务,这意味着它没有意识到国家义务在私有化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情境下的多种参与方式。
五、私有化与经济、社会权利的新曙光?
本文的大部分内容都批判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处理与经济、社会权利相关的措施方面的表现,以及在三类义务方面私有化可能产生的危害。虽然私有化是一个复杂、多方面的现象,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未能根据三类义务的不同要素对其进行充分概念化,严重限制了国家行为者、经济与社会权利倡导者等主体确保私有化符合经济、社会权利的能力。因此,在结论部分,本文将分析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2017年6月发布的“关于国家在工商活动中履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中对私有化进行的最新和广泛的讨论。1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4 on State Obligation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Business Activities, E/C.12/GC/24 (2017).这一最近的干预行为可否被视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处理该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从义务的角度来看,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保护义务的理解与其在先前文件中的理解大不相同,而且范围要广泛得多:“保护的义务是指缔约国必须有效防止工商活动中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侵犯。这要求缔约国采取立法措施、行政措施、教育措施和其他适当措施,有效防止工商活动中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保护的权利的侵犯,确保为公司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提供有效补救。”2Ibid., para. 14. 在讨论域外义务时采用了同样广泛的保护的义务办法(第30段)。
通过改变传统上对保护义务的理解,即只关注第三方对经济、社会权利享受的干预,将其理解扩展到“防止在商业活动中侵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义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似乎扩大了上文讨论的保护义务下国家义务的范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声明也明确了保护义务的范围,国家如果“未能防止或应对企业的某些行为,从而导致权利受到侵害,或可预见权利将受侵害”,那么缔约国就将违反保护公约权利的义务。3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4 on State Obligation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Business Activities, E/C.12/GC/24 (2017), para. 18.
在第24号一般性意见的“保护义务”一节中,有证据表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已选择将该义务作为与非国家行为者有关的所有国家义务的总和,即使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所列举的行动也可以被视为与实现义务有关,甚至可能更适合如此看待这些行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声明:“因此,国家始终有责任对私营行为者进行监管,确保其提供的服务对所有人开放,且服务是充足的,得到定期评估,以便满足公众变化的需求,并能照顾这些需求。”4Ibid., para. 22.另一个例子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保护义务需要更多的“直接监管和干预”,5Ibid., para. 19.敦促缔约国考虑采取以下措施:“限制某些产品和服务营销广告,以保护公共健康……打击性别角色定型观念和性别歧视;按照保护人人享有适足住房权的要求,对私营住房市场实行租金管制;按照基本生活工资和公平报酬标准,确立最低工资;对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受教育权、就业权和生殖健康权有关的其他工商活动实行监管,有效打击性别歧视;逐步消除经常致使相关员工得不到劳工法保护和社会保障的非正规或‘非标准’(即很不稳定的)就业形式。”6Ibid. (footnotes omitted).
从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义务角度来看,这些措施也是恰当的——正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后来发表的声明所述,“应禁止私营保健提供者拒绝提供负担得起的充分服务、资料或信息”7Ibid., para. 21.。
与先前的做法一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明确表示,从私有化的角度(事实上,在经济、社会权利以及商业活动更普遍的情况下),1Ibid., para. 10.保护义务是一项关键的义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第24号一般性意见的“保护义务”一节中针对私有化指出:“私营行为者在诸如保健或教育等传统公共领域的作用和影响日增,对缔约国遵守公约义务构成新挑战。私有化本身不受《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禁止,甚至传统上公共部门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领域也是如此,例如供水供电、教育卫生等。但私人供应商应遵守严格的规定,规定其承担所谓的‘公共服务义务’:在水电供应方面,这可包括服务的普遍性和连续性、定价政策、质量要求和用户参与的要求。”2Ibid., para. 21 (footnotes omitted).
在概述由于私营部门在公共领域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加而给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方面带来的挑战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强调了其特别关切:“由于产品和服务由私营部门提供,享有基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可能变得难以负担得起,或因追求利润而有损于质量。”3Ibid., para. 22.它强调私营行为者提供享有公约权利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时,不得使支付能力成为享有公约权利的条件,否则就会形成新形式的社会经济隔离现象;并且对享有公约权利至关重要的商品或服务的私有化可能造成问责缺失,“应采取措施确保个人有权参与评估这类产品和服务提供是否充分”。4Ibid.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些挑战和所需的国家应对措施是作为保护义务进行论述的,但其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义务。
在概述违反保护义务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强调了与私有化有关的几个例子,包括未在公共合同中纳入与残疾人合理便利相关的要求,以及某些项目或某些地理区域对公约权利保障的法律豁免。5Ibid.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还提出了国家未能监管房地产市场和在该市场上运作的金融领域行为者的影响,“以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和充足的住房”。6Ibid.同样,很有可能的是,甚至也许更有道理的是,把这些视为在未来扩大权利享有的举措,而不是在现有权利享受的情况下实现义务的固有措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明显正打算用保护义务来承担私有化方面的繁重工作,这一点也可以由下面内容证明。第24号一般性意见在“补救”一节的开头表示:“缔约国在履行保护责任时,应建立并执行适当监管和政策框架。”7Ibid., para. 38.然而,没有理由认为国家在补救方面的义务仅来自这一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实现义务并不是完全缺失的。在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部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表示“这可能需要寻求工商企业的合作与支持,以落实公约权利,并遵守其他人权标准和原则”。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私有化,但私有化显然是在“合作与支持”的理解范围内的。8Ibid., para. 23.而且,相较于以往的做法,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举
动非常值得鼓励。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指出,实现的义务“也要求政府指导工商实体努力落实公约权利”1Ibid., para. 24.。这一点表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私有化的讨论已超出保护义务,是一个潜在的重要进步,但因没有继续探讨,结果没能认识到与私有化相关的实现义务。
总而言之,一般性意见表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错失了以整体方式处理私有化问题的机会,没能将其单独作为一个问题置于三类义务下考虑,而是试图将不同的权利问题置于不同的义务下;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不同层面义务所要求的行动之间存在重叠,以及私有化可能对三项义务都产生影响。尊重义务和实现义务也关系到国家如何启用、监督、监管和惩罚侵害权利的违法者及相关程序。如果要解决私有化与义务有关的全部问题,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通过采用基本上“一切照旧”的方法,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延续使用了“私有化”“国家行动”和“国家义务范围”的概念。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也对保护义务进行了不必要的重新概念化,以便解决实现义务可以处理的问题,因此,在私有化的背景下限制前者,后者也便失去了关键意义。
然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文件中有一个重要的新元素,它提出了一个“新领域”,即从以国家为中心的角度来识别私有化引起的与经济、社会权利相关的损害,这里必须加以考虑。这可能将损害权利的非国家行为者视为“国家机关”,理由是该行为者“是按照国家的指示行事,或在国家指挥或控制下行事”,从而造成其被视为应当由国家直接负责的行动。2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with Commentaries, A/56/10 (2010), Art. 8, cited in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4 on State Obligation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Business Activities, E/C.12/GC/24 (2017), para. 11.在强调国家在某些情况下承担直接责任的可能性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特别提到签订“政府合同的情况”。该委员会还提到了“工商实体由缔约国立法授权行使政府某些权力”下,国家承担直接责任的可能性。3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4 on State Obligation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Business Activities, E/C.12/GC/24 (2017), para. 11 (citing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Art. 5).虽然这在涉及经济、社会权利的法律方面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创新,4实际上,从条文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新颖的。例如,关于第5条和第8条的原始评注没有提及任何与经济、社会权利相关的例子。See James Crawford,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Introduction, Text and Commenta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00-102, 110-113.并且在满足这些要求的私有化背景下,人权法肯定具有“找到”非国家行为者的潜力,但这种方法会遇到更多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会认定国家指导或控制的程度足以导致将非国家行为者视为国家指定机关?如何定义“国家权力”?5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将责任直接归于国家的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情况要求在官方当局缺席或违约的情况下行使政府职能”[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24 on State Obligation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Business Activities, E/C.12/GC/24 (2017), para. 11]。在此不讨论该情况,因为其不属于本文所定义的私有化。应该指出的是,此处“政府职能”的确定问题也适用于在上文第四章第(二)节中讨论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一般性建议中采用的方法。这些是国际人权法领域中备受争议的问题,并且其中已经存在不少学说。6例如,参见关于第8条在私营安全行为者方面实践情况的讨论,Nigel D. White,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of Conduct: Developing a Responsibility Regime for PMSCs, 31 Criminal Justice Ethics 233 (2012).国内宪法判例和相关学术研究已经广泛分析了关于为行使与经济、社会权利相关的义务而将非国家行为者指定为“国家机关”或“公共当局”的类似的宪法学说。1关于这些理论讨论的例子,参见Tsvi kahana & Anat Scolnicov, Boundaries of State, Boundaries of Rights: Human Rights, Private Actors, and Positive Oblig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Stu Woolman, Application, in Stu Woolman & Michael Bishop eds., Constitutional Law of South Africa, Juta & Company Ltd, 2d ed. 2007, updated as of 2013, ch. 31.关于何时以及如何产生这种责任,存在着巨大的争论,在实践中被认定为产生这种责任的例子也很有限。2对于南非和英国的两个例子,参见AllPay Consolidated Investment Holdings (Pty) Ltd v.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South African Social Security Agency 2014 (4) SA 179 (CC), paras. 52-60[重点关注《南非宪法》第239条所界定的“国家机关”的义务,考虑根据第27(1)条私营公司在旨在提供获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援助)的权利的公共合同背景下,其所具有的宪法义务];R (Weaver) v. London and Housing Quadrant Trust [2009] EWCA (Civ) 587, [2009] 1 All ER 17(根据《1998年人权法案》第6条,认为住房公司监管的注册社会房东属于“公共权力机构”,其某些职能“具有公共性质”)。
诚然,对于像私有化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复杂现象,在更广泛的一般性意见的一个章节中进行不可避免的有限处理,是否能够“治愈”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迄今为止对这一现象的不当处理,是值得商榷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第24号一般性意见毫无疑问地扩展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之前对私有化的解决方法,但可以说,它是通过对保护义务进行“另起炉灶”来实现的,并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决策的不同阶段、国家作为和不作为的不同形式,而这些都是综合解决私有化与经济、社会权利问题所需要包含的。总的来说,很遗憾,当私有化及现有的、完善的义务框架(如三类义务)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问题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纳入国家/政府问责理论的方法反而会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3例如,在这方面,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可以并且应该利用一般性意见作为一个机会,更密切地考虑私有化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1)条要求之间的关系,该条要求各国在其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逐步实现经济、社会权利。如上所述,尽管第2(1)条是公约义务的核心规定,但私有化与本条款之间的联系尚未成为委员会深入审议的主题。对这种关系的考虑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不应认为这意味着笔者不认为它重要。特别是考虑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其他国际人权机构在经济、社会权利语境下应对私有化工作的影响。根据以往的做法,那些在私有化和经济、社会权利方面采取不成熟做法的机构(即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移徙工人委员会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很有可能不加辨别地采取相同的方法,导致它们处理私有化问题的工作缺乏连贯性,造成更多问题。4在写作的时候,它还处于早期阶段,到目前为止,毫无疑问,这方面的证据是有限的。发布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24号一般性意见[见第四章第(二)节]之后的一般性意见或建议均没有引用此一般性意见,这些条约机构继续在私有化背景下以不协调和不一致的方式探讨三类义务。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未能将第24号一般性意见纳入考虑是由于这些声明在第24号一般性意见发布之前已经基本完成(如果不是完全完成的话),但其他后面的声明的发布时间足以让相关起草者考虑第24号一般性意见。 [See notably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and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Joint General Comment No. 4 (2017)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and No. 23 (2017)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Human Rights of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MW/C/GC/4-CRC/C/GC/23 (2017);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and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Joint General Comment No. 3 (2017)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and No. 22 (2017)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Human Rights of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MW/C/GC/3-CRC/C/GC/22 (2017);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7 on Gender-Related Dimensions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CEDAW/C/GC/37 (2018).]扩大构成国家行动的范围,以规避私有化对人权构成的挑战,这具有足够的诱惑力,但这是一条只有非常谨慎才可以成功的道路。
六、结论
本文一开始明确指出,私有化既不是完全地违反,也不是绝对遵守国际经济、社会权利框架。然而,毫无疑问,目前在国家仍然是主要行为者的人权系统中,私有化的实施带来了重大的人权问题。德费特和戈麦斯·伊萨表示,“从法律角度来看,由于私有化的决策,人权容易受到侵犯的程度在不断增加,因为到目前为止,人权法尚未充分发展,无法应对私营行为者接管提供对人权至关重要的服务的情况”1Koen De Feyter & Felipe Gómez Isa, Privatisation and Human Rights: An Overview, in Koen De Feyter & Felipe Gómez Isa eds., Privatis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Intersentia, 2005, p. 8.。虽然“不断”的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但人权体系目前显然未能让私营行为者充分参与,也未能就其在私有化语境下对人权的不利影响进行有意义的问责。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体系的主要监督机构没有处理好私有化在三类义务下的形式、程序、产出、结果和权利影响。正如上文所述,这不仅仅是由于在国际人权标准的执行中存在经常被引用和普遍承认的缺陷,还可以归结于迄今为止学者、倡导者和联合国条约监督机构未能开展必要的规范性工作,以使包括三类义务在内的现行国际人权法框架在私有化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尽可能集中和有效。本文只讨论了一些被描述为私有化的国家行为(或不作为),并且只详细讨论了国际经济、社会权利框架的义务要素;但是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我们需要更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私有化所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