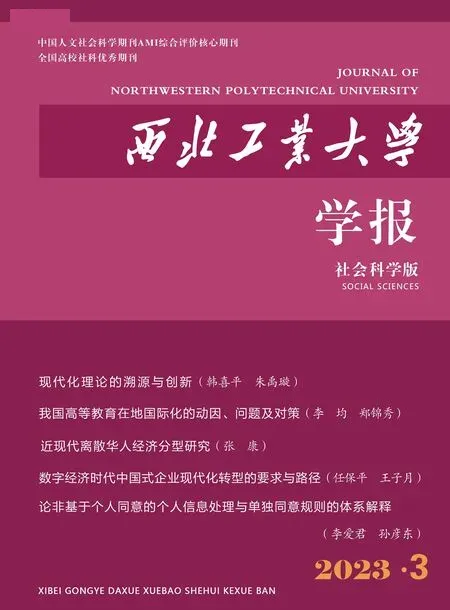近现代离散华人经济分型研究
张 康
20世纪90年代以后,离散研究因移民热潮和全球化语境渐成显学。Diaspora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原意为“播撒种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曾用于专指背井离乡、渴望重归其“应许之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其特殊的种群经历被视为经典的离散经验。此后,这一概念逐渐泛化,用来描述那些因故移居他乡,具有一定数量规模,拥有共同的血缘、语言、文字、人文传统与历史记忆,在现居国社会保留族裔特色,并与祖籍国维持多重联系的特殊群体。以此定义比照海外华人,除那些因移居年代久远,仅存有部分中华民族血统,为当地文化深度同化,对中华文化已毫无知觉的群体之外(如南美、中亚等地的早期中国人混血后代,非洲肯尼亚的“郑和船员后裔”①等),其余大多都可纳入离散华人的范畴,其区别只在于离散的程度与类型不同。相比于中国自有的“华侨-外籍华人”研究体系,离散概念的文化属性回避了国籍区分,仅着眼于离散者与祖籍国的各类牵系和根性崇拜,对借助国际前沿移民理论讨论华侨华人问题并与世界其他离散族群进行比较研究大有裨益。
无论是犹太人或三角贸易中被贩卖的黑人奴隶那样的古典型受难者离散,还是近代因世界殖民体系扩张而带来的劳工离散,抑或是穆斯林、佛教徒在遥望麦加与蓝毗尼之间所形成的宗教离散等,这些离散行为表面看来似乎源于个体选择或命运,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有结构性的因素在背后推动。在影响华人离散者与母国关系的诸多因素中,离散的类型分属非常关键。伴随华人移民数百年来延续不断的海外播衍,其全球离散的主体类型也在不断演变,并在离散华人的经济行为中得以充分体现。
天下熙攘,皆为利往,生计与金钱是侨民移居他乡的最初动因。中国曾长期属于农业社会,国人多安土重迁,历史上的大迁徙多与灾荒或人口增长带来的生产资源失衡有关,像较为著名的“走西口”“闯关东”都属于此类。中国知名侨乡往往是人稠地狭之所。宋代谢履《泉南歌》有云:“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处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当土地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就迫使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们将目光投向远方。千百年来,华人因各种原因移居海外,或因生计所迫漂洋过海,淘金寻梦;或因天灾人祸辞别故土,在异国他乡开拓新天。读书与经商是海外华人行走天下的两件法宝,书卷承载文化,商贸维系生计,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织就了今日全球华人世界的轮廓。
本文尝试在罗宾·科恩(Robin Cohen)等学者的离散族群分类方法基础上,对不同时期海外离散华人的经济行为类型进行梳理,并分析祖籍国态度、政策在其离散模式塑造中的重要作用。考察的维度大致从19世纪中期至今,除较早前的零散移民外,这一时间段基本已可涵盖华侨华人大规模向外迁徙的主要过程。
一、华人离散类型的划分
在其代表作《全球离散族群》(Global Diasporas)一书中,英国学者罗宾·科恩提出了在传统血缘纽带之外划分离散族群的另一标准,即依据迁移离散的主要原因将其分为五种类型:受难型(Victim)、劳工型(Labour)、帝国型(Imperial)、商贸型(Trade)和文化型(Cultural)。笔者以为,这一分类的科学性和普适性仍有待商榷,至少在离散华人的特殊语境下,似应做一些必要修正。
首先,在科恩看来,除了受难型离散是被迫而为以外,其余几类离散形式都是行为主体主动选择与谋求进取的结果。但事实上,虽然以华工为代表的契约劳工与三角贸易中被贩卖的黑人奴隶的强征劳作有所区别,绝大多数劳工契约的签订确属华工自愿,但结合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一“自愿”毋宁称之为“无可奈何”。鸦片战争后,晚清内外交困,民不聊生。中国粤、闽等沿海地区由于人地矛盾突出,大批平民在极度贫困中急于寻找新的出路。此时,美洲与东南亚等新兴地区的开发,太平洋铁路和巴拿马运河等重大工程的兴建,特别是1848年、1851年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座金山”②的相继发现,都迫切需要大批劳动力补充。在此背景下,国势衰微而劳力富集的中国自然成为弥补缺口的最佳选择。在当时,选择卖身作“猪仔”③者多是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很多华工在蛇头描绘的“金山”愿景下被蒙骗签订合同,在历经千辛万苦抵达目的地后才发现真实情况与预期大相径庭。不少人最终客死他乡,甚至根本未能见到想象中的“新世界”。就此而言,所谓的劳工型其实与受难型并无二致,因而在华人离散的模型中,我们将两类离散纳入一目,一并探讨。
其次,“帝国型”离散的说法并不适用于华人群体。与大英帝国在鼎盛时期鼓励国民移居开发殖民地不同,移民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为政府所认可,极少在官方层面予以推动。事实上,无论是自由出洋还是契约华工,中国近代移民的高峰恰是实施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的明清时期。明清两代大多数时间均严格限制国人出海及与外邦番民交往。④华侨在外不仅无法得到国家庇护,反而被视为“乱民”。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释放了积压已久的出洋需求,加之华工贸易的兴盛,才共同促成了清末民初中国人移居海外的鼎盛。因此,近代华人离散的形成与“中华帝国”之强大并无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天朝上国”的强势存在和传统观念抑制了华人对外移民的势头。而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特质以及中华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则是海外华人“落叶归根”思想的核心来源。中国政府对离散华人的积极政策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成熟定型。基于上述考虑,针对当代海外华人所呈现的主要离散特质,特别是其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可称之为“大国型”。
最后,科恩将全球化时代下日益显现的以跨国华人为代表的新兴离散模式统称为“文化型”。由于“文化”概念的庞杂,这一类型划分过于模糊且难以操作。此外,离散族群的题中之义即在于承载文化的迁徙行为,对任何一种离散类型而言,文化都是未曾剥离的。笔者认为,虽然文化因素在离散族群的行为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个体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逐仍是跨国迁徙的主要动力。因此,本文中不再将“文化型”离散华人单独作为一类进行探讨。
综上,对华人离散群体的分型可整合修正为“劳工型、商贸型、大国型”三类,在后文中,我们将对这三类华人离散类型的经济行为分别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全球各地的华人族群在移居历史长短、侨社人数多寡、经济实力强弱、社会地位高低等方面各不相同,往往存在明显的同时代差异性。例如,当19世纪末部分华商已在东南亚把控地区贸易与经济命脉之时,北美的铁路华工与英国的华人海员仍在从事近乎奴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此外,并非所有的侨民社会都具有完整的发育过程,在某些国家和地区,部分发展阶段可能被跳跃或叠合存在。因此,某一国或某一时期的离散华人可能兼具多个类型的特征。本文试图完成的,是在华人移民发展史的基础上,对其离散经济一般性宏观演变规律的探讨。
二、从“猪仔”到“三把刀”——“劳工型”经济离散
中国人自何时开始移居海外?据传,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灭殷,箕子不肯臣周,遂率其治下子民徙居朝鲜。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平壤郊外的牡丹峰下仍有箕子陵古迹。⑤这应是有记载以来,华夏先民最早移居海外的记录。此后,历朝历代均有中国人漂洋过海,延续不绝,但数量都十分有限。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海运技术的发展与航道的畅通带来了一拨下南洋的小高潮。据估计,从明代起至19世纪中叶,中国人移居海外者在100万人以上。[1]但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移民都是小规模和分散的,近代史上中国人大规模移居国外的高潮始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基本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从1881年到1930年到达海峡殖民地(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中心的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约有830万,其中约600万属于契约劳工;同期被运往美洲的华工有13万之多,运往非洲的约有7万;此外,1906—1910年,从山东、河北、东北等地运往沙俄远东地区的华工也有55万。[2]早期华侨多为生活贫苦的农民和小生意人,以签约劳工的身份来到异国他乡,出卖自己的劳力赖以为生,从事一些当地人嫌弃的最艰苦、收入最少的工作。
以赴美华人劳工为例,1862年,美国开始修建著名的太平洋铁路。在工程建设的七年间,最为艰险的路段几乎都是以华工为主修建完成。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人薪水发放记录中,华工比例在工程后期甚至高达95%。据美国移民局历史资料显示:仅在1865—1869年就有近10万中国人移民美国,其中有14000多名华工参与了筑路工程,4000余人客死他乡。[3]大多数华侨仍期盼在身故后魂归故土,据记载,仅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至十八年的短短四年间,由广东新会籍侨团从旧金山运回葬于黄坑海槐义冢的华侨骸骨就达387具。[4]
对早期华人劳工而言,在积聚了少量启动资本后,大多数人便将目光投向一些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三把刀”,即菜刀(厨师)、剪刀(裁缝)与剃刀(理发匠),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服务对象大众化,适应面广。菜刀、剪刀、剃刀等行业都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无论是哪国人,不管男女老少、地位高低,肚子饿了必然要下馆子吃饭,而异国风味的美食往往颇受欢迎;身上的衣服破了、旧了,必然要置换新的行头;头发长了,自然要洗理梳剪一番,人同此理。只要在人群聚集之地,这些服务行业就可开张营业,招徕生意。此外,从事这些行业可与当地居民面对面打交道,也有利于侨民在语言、风俗、文化等方面迅速融入当地。
二是风险较小、转产灵活。“三把刀”职业大多依据市场需求自然分布,较少遭遇来自当地同行的竞争;大多采用现金交易,日日有进账,对创业初期缺乏资金,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华侨从业者来说尤为重要。此外,与其他行业相比,“三把刀”职业无需大量先期投入,运营成本也较低,因而可以较快积累资本、转型换代。
三是由于移民政策的限制,一些侨居国政府对移民种类有严格规定,“三把刀”往往成为初期移民的不二之选。如1899年日本政府就曾发布352号勒令,规定只允许厨师、理发师、裁缝和商人等有“特殊技能”的外国人移入;在农业、渔业及其他杂业,一律禁止从事简单劳动的外国人务工。[5]
在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中国近代移民高潮中,近千万中国人在国际殖民体系的驱动下迁移至世界各地,对其中绝大多数人而言,无论是无可奈何的背井离乡,还是初到异地的困苦生活,对故土家乡的思念眷恋,这一离散的经验多是较为悲凉的,几乎人人都怀有“落叶归根”的心态,属于典型的古典离散族群。⑥早期华人所从事的“三把刀”行业,“剪刀”由于现代制衣业的高度集成化与机械化,基本已退出历史舞台,而仅限于一些高端定制和民族服装的小众领域;“剃头刀”从其诞生起便主要服务于侨社内部,伴随近年来华侨华人逐渐走出唐人街、中国城,这一行业也日渐式微;而“菜刀”则依托中餐文化在海外不断弘扬光大,成为当今海外华人的支柱行业。与其先辈初来乍到、小本经营的情况不同,今天的不少中餐店已具有大中型企业的潜质,并与物流、仓储、酒店等行业结合发展,在此意义上显然已超越了“劳工型”离散的范畴。
三、移民版图的开拓者——“商贸型”经济离散
王赓武认为,华商形态是中国移民最基本、占统治地位的形态,也是1850年劳工潮出现前仅有的重要形态。[6]从早期东南亚海上贸易的萌芽到19世纪中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全球化,再到20世纪中后期的资本全球化过程,作为华人“商贸型”离散的主要群体,海外华商的角色始终与时代相适应,其自身的定位与作用也在不断变化与动态调整中。
事实上,早在西方殖民者主导全球贸易之前,华商就已在东亚贸易圈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一贸易圈以庞大的中国市场为中心,北起蒙古国、朝鲜、日本,南至印尼、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包含了广义上环中国海的全部地区,是当时全球贸易量最大、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性贸易市场。早期海外华商网络的形成始于南宋。在当时,宋室南渡导致中国经济中心南迁,大量南方的土地得以开发,以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倡功利之学,从思想上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加之航海技术的进步,诸多有利因素叠加使得宋代商品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此后数百年间,中国成为当时亚洲乃至全球商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早期中国对外移民多为华商,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
第一,资源丰饶的东南亚地区当时还停留在相对落后的阶段,其“商业运作和市场交换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给华人提供了很多机会”⑦。中国商贩们携带丝绸、陶瓷、铜铁器和各类手工艺品前往东南亚的大小岛屿,向当地部族换回当地盛产的沉香、龙涎香等香料,以及珍珠、玳瑁等价值不菲的土特产品。由于海上贸易获利颇丰,从商者进出愈加频繁,部分商人、水手开始在当地定居下来,成为第一代华侨。
第二,华人大多是因生活窘困而被迫出洋谋生的贫民阶层,漂洋过海时往往只携带少量衣物和金钱,多数人并没有长期定居的打算,在他乡劳作打拼只为有朝一日能衣锦还乡,“华人移民来到东南亚是为赚钱而非定居,他们在国内的成功与地位是由他们寄回家乡钱数多少来衡量的”⑧。因而,能产生快速回报和资金流动性强的商业自然成为首选。基于上述身份特征和侨居心态,大多数从事农耕的华人在移民海外后便普遍“华商化”了。
鸦片战争以后,华商在东亚地区的商业地位遭到挑战,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广大地区先后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贸易中继地,被纳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在西方宗主国主导的殖民地贸易体系中,华商受到殖民地政府和资本家的盘剥与限制,地位十分脆弱。直至二战前,海外侨民中大多数仍为工人、店员、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社会底层人员。同期虽也有一些华侨资本家、企业家,但为数不多,实力亦不甚雄厚,且绝大多数分布于东南亚。但是,殖民体系的串联也为华商带来新的机遇。一方面,东亚被带入欧洲主导的全球贸易网络之中,中国商品因而得以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由于无法直接在中国沿海建立贸易据点,来自欧洲的商人不得不经由东南亚华商的中介来完成交易;另一方面,由于华商对东亚区域商业文化的熟稔,宗主国在发展贸易和开发殖民地的过程中常常有赖于华商精英的经验和支持。如此,在东西方经贸交流与东南亚开发的大背景下,广大华商逐步由货物贸易升级到商品生产和加工领域,华商网络的范围也从东南亚沿海扩展至内陆地区。伴随同期出现的华工移民潮,华商的足迹也开始涉足北美、澳洲、欧洲乃至非洲、拉美。凭借吃苦耐劳、勤俭守业的品质,华商经济开始逐渐起步,这一时期的“商贸型”离散华人经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是商贸活动与移民迁徙的双向互动。伴随区域贸易的兴盛,日益增长的交易量和丰厚利润促使更多中国沿海民众加入海外华商的队伍,从而在东南亚各主要港口和贸易中心形成早期海外华人社会的雏形。19世纪中期,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总数约为150万左右,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一数字已跃升至500万以上。[7]反过来,由于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移民社会的日渐成形,华商贸易也因而获得较为稳定的内部市场和人力供给,依托移民地本地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市场也不断发展。此外,二战后,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相继成立,各侨居国政府对移民政治效忠的担忧也迫使海外华人在融入当地与回归故国的问题上作出选择。在经济、政治双重因素的驱动下,华商贸易本地化与国际化的进程在此时期同步进行。
二是经济圈多以“华埠”为中心,经营行业单一,影响辐射范围较为有限,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华商以华人社区为服务对象,其经济行为也主要以华埠为核心展开。如上节所说的“三把刀”,其主要服务范围仍在华埠内部及周边地区。此外,早期华商因缺少资本,且在语言、人脉等方面均无优势,所从事行业多集中于服务业和轻工业。以旅美华商为例,1866年旧金山的雪茄厂半数为华人所办,所雇用的工人中华工也达90%以上;在餐馆、洗衣店、家仆等低薪行业中,华人均占据较大比例。[8]此外,出于抱团取暖的需要,商会组织也在此时大量涌现。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人大多势单力薄,抗风险能力极弱,为了团结互助、联防自卫,同时也便于沟通商务、联络感情,各类基于血缘宗亲、地缘同乡及业缘行会基础的商会便应运而生。[9]商会的产生极大促进了侨社内部网络的形成,并日益成为“商贸型”离散华人经济的支柱与缩影。
三是与祖籍国的联系起伏曲折,但从未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从外交大局和华侨华人的长期生存发展考虑出发,实行了单一国籍的制度,数千万海外侨民在祖籍国与侨居国之间作出了选择。此后,由于中国政府取缔私营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海外华商被视为“资产阶级”,成为与“地富反坏右”并列的打击对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海外华商与中国的直接经贸关系几近中断,在东南亚与中国之间持续数百年的移民活动也基本停息。在此期间,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华人离散者与内地贸易和输送侨汇的天然中转站。据统计,1949—1990年,仅东南亚华商对香港投资就达730亿港币,超过美国和日本同期的投资总额。[10]在1975年南越政权倒台后的第一个月里,每天便有价值50万美元的黄金从越老柬三国汇入香港。在此时期,各方华商资源的集中汇入使得香港成为全球华商网络的核心以及资源、信息的交换站。通过香港这一中继点的联结作用,在内地最为封闭的那段岁月里,海外离散华人群体依然通过小规模的经贸关系维持故土情怀的曲线表达。
四、在现实利益与祖籍情怀间——“大国型”经济离散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海外华人离散族群的同步成长和成功互动有目共睹。虽然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但不可否认,至少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中国政府对海外侨资的成功吸引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全球化寻找市场的进程中,中国以近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以及吸纳外资的各类优惠政策聚集了全球资本的目光,也对因整体封闭而与祖籍国阔别多年的华侨华人群体产生巨大吸引力。在巨大的市场与利益驱动下,加之与祖籍国亲近的天然需求,于母国经济的复兴中寻找机会成为离散华人经济升级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面临全面转型,产业升级换代以及原材料、能源的紧缺都迫使国内企业“走出去”。而在此过程中,由于海外华商对侨居国经贸政策与投资环境的熟悉,在当地较为雄厚的可调动资本,较为成形的市场分销网络,以及与中国企业相通的语言、文化背景和经商规则等,大量华商在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争取国际项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不仅帮助初出茅庐的中国企业规避在国际贸易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也在中企开拓各国市场的过程中发挥了“转换插头”的适配作用。在此背景下,除了延续以往直接投资获益,来华寻找商机的传统形式外,越来越多的华人离散者开始搭乘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大船,在祖籍国与侨居国之间发挥优势,施展己能。作为今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海外中国”的营建离不开遍布全球的华人网络,而大量“中国制造”畅销全球的同时也为离散群体带来丰厚的利润和事业拓展的新机遇。与此同时,母国的实力攀升与国际地位提高也极大地增强了离散者的族群自信和文化认同,为其在侨居国更好生存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在“大国型”经济离散的模式中,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无疑具有核心意义,这也是其有别于“商贸型”离散的主要方面之一。邓小平同志较早认识到海外离散者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意义,也是在其着力推动下,中国政府从1978年起实施对外经济开放,向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外部世界敞开大门。在1992年视察上海时,邓小平曾提及:“那一年(1980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11]1977—1991年的14年间,邓小平先后会见海外华商达46次。[12]在他看来,“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13]。
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国务院侨务工作会议部分代表时指出:“侨务部门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通过重点做好华人大企业家、专门人才和行业协会的工作,以及以侨引台、以侨引外、侨台结合、侨外结合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办几件大事的想法。”⑨1999年,江泽民同志强调:“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广大海外同胞中,既有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也有成绩显著的中青年科技人才,他们在当今一些重要的高科技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广大海外同胞热情支持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是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和开展国际民间友好事业的重要促进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对加快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十分有益的。”[14]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对海外侨务资源的定位不再聚焦于经济领域,而上升至更为宏观的国家战略层面。2004年3月,胡锦涛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凝聚侨心、发挥侨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贡献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在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在开展民间外交,传播中华文化,扩大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中国梦”“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以期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方案,对国际社会担忧的中国威胁论予以正面回应。2017年2月,习近平专门就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希望侨务战线的同志们坚持胸怀全局、坚持为侨服务、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为主题,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最大限度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凝聚起来、发挥出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6]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再次提出,要“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党对海外华人资源进行正确判断和恰当引导,紧扣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将重构与离散者关联的努力与后者推动祖籍国复兴的意愿相契合。符合“大国型”离散特征的当代华人,通常会在祖籍国与侨居国之间建立起细密的各类经济纽带,与双方政府、企业维系友好互利的关系,依靠祖籍国吸引离散资本和智力资源的各项优惠政策,精准搭乘“一带一路”“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式现代化”等中国经济阶段性腾飞的每一班快车,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族群利益与离散情怀的统一。
如前所述,一个最初的祖源地或历史核心以及指向核心的强向心力是离散族群区别于一般移民群体的关键特征。类比于物理学中离心力与向心力的相生相克,正是由于远离故土,身居他乡,才会产生对祖籍国社会与文化若即若离的心态,既不会一味靠近,也未曾渐行渐远。作为散居海外的离散华人,无论其属于“劳工型”“商贸型”或“大国型”,与祖籍国实体或文化间延续不断的关联维系均是其重要特征。
虽然在零散个体的层面上,“商贸型”与“劳工型”华人离散的历史十分悠久,如东南亚华商贸易早在宋代甚至更早期即已兴起并延续至今,在同一历史时期,也可能出现几类离散模式重叠共存的现象,缺乏明显的先后顺序,但通过对上述三类离散华人经济类型的逐个分析后不难发现,在19世纪中叶至今的170多年间,海外离散华人的经济行为仍在宏观维度上呈现出“劳工型、商贸型、大国型”发展演变的整体趋势。研究这一变化规律,对理解海外离散华人族群在经济领域与祖籍国关系的互动变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的离散华人以“劳工型”为主体,满怀衣锦还乡的憧憬奔赴海外,而落叶归根成为大多数离散者的毕生夙愿。劳工型离散华人具有明显的古典离散倾向,即对于祖籍国事务高度关心,积极参与,而对侨居国社会则缺乏主人翁意识,参与有限。在20世纪,海外侨胞毁家纾难、踊跃支援全民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虽然远隔关山重洋,但中国仍被视为海外华人最终的故土与家园,显现出离散者舍小家而保大家的真挚爱国情怀。
二战后,民族解放的浪潮席卷全球,民族国家的体系在全球形成,为国家间关系和族群身份的认同搭建了全新框架。从20世纪40年代前后至改革开放前,“商贸型”离散逐渐取代劳工输出,成为该时期海外华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祖籍国与侨居国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离散华人为顺应生存、发展的需要,从长远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选择成为各侨居国的少数族裔公民。以“落叶归根”为特征的“华侨社会”逐步转变为以“落地生根”为主的“华人社会”,而原先较为封闭和保守的华侨经济也随之转变为华人经济,其经营体系与理念日益展现出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特征。对大多数选择归化于当地的海外华人而言,中国已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场所,其身上的“离散性”也伴随祖籍故土的想象而逐渐消失。然而,作为积极、主动的华人离散者,与祖籍国社会、文化的联系却从未完全割裂。借助如地缘、方言、乡土文化等原生性纽带,离散华人与祖籍国之间的各类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商贸型”离散兼有古典离散与现代离散的双重特征,也正有赖于此,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向世界重新敞开大门时,沉寂蛰伏于海外华人社会与祖籍国之间的跨国网络才得以迅速重构并愈加强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依托“入世”、举办奥运会等关键契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在多个领域日益显现出大国风范。祖籍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双重提升令全球华人欢欣鼓舞,原本已脱钩多年的离散族群再次与母国恢复了频密联系。他们高度关注中国各领域的发展,并期待在其中发挥更大影响。在此过程中,祖籍国政府正向而稳定的激励政策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国力日盛,政府在处理海外侨民事务时拥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资源,在引导离散群体与祖籍国民众形成合力同圆中国梦的同时,也将共享这一成果的预期向海外同胞予以承诺,鼓励其将发展自身事业与促进民族复兴的荣光融合起来。与主要依赖个人能力和跨国华商网络的“商贸型”离散相比,“大国型”模式下的华人离散者更加注重借助祖籍国经济上行期所带来的各项红利来实现跨国经贸活动。
在全球化弥散渗透的大背景下,大量的经济活动已无需在依托族群关系和商业信用的传统华商网络中进行。新时期离散华人的经济行为不仅具有现代离散的典型特征,其经济活动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海外华人社会或侨居国与祖籍国之间,而是追求一种跨越国界的,整合侨居国、祖籍国和第三国在内的国际资源,以实现自身发展的全球优化配置。在全球化与社会网络革命⑩的双重冲刷下,离散华人族群所赖以构建的核心关系也呈现出由“原生性认同”向“一般性认同”过渡,由“圈内”向“圈外”逐渐延伸的整体趋势。他们既深深扎根于所在侨居国,又同时维持着与祖籍地的多重联系,其日常生活也高度依赖于跨越国界的各类互动,在两个乃至更多的国家中同时构建起多重身份,成为所谓的“跨国华人”群体。
离散理论的引入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全球化时代下的国家关系与族群认同。从祖籍国的角度而言,中国政府对离散华人族群特别是其精英阶层对本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予以认可。过去数十年间所出台的各项鼓励性政策,与深植离散华人内心的祖籍情怀互相契合,不仅使民族、国家、边界等传统概念被更为灵活的跨国理念所取代,在政治、地理和文化上大大缩短了母国与海外离散群体之间的距离,也使华人离散者得以自由调配各类资源,在跨国逻辑的框架下兼顾对祖籍情怀与现实利益的双重考虑。
总体而言,中国近年来将移民事务制度性地整合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中,而具有主体意识的离散华人群体则通过各类跨国实践把个人事业发展与祖籍国民族振兴的宏图相结合。在此过程中,全球化与社会网络的双重推力开阔了民族国家与其离散子民在跨境场域中的互动空间,而离散群体的多赢经济行为也在无形中强化了后者的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作为离散华人中最具活力的群体,跨国华人凭借其身份的多元性与持续的流动性在祖籍国与侨居之国间频繁穿越,借助资本与智力资源的全球环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一方面“无以为家”,另一方面又“处处为家”,其全球离散和兼顾超越的实践,恰可成为“全球化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佳写照。
注释
①郑和船员后裔又称“法茂人(Famao)”,是现居于东非肯尼亚帕泰岛(Pate)上的一个中国人族群。“法茂”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意为“从大海中死里逃生的人”。据法茂人自述,郑和船队的一支当年在行驶至帕泰岛附近海域时失事,部分船员因而滞留当地并与当地人通婚繁衍至今。目前,已有部分考古、人类学研究发现证实了这一说法。与当地人相比,法茂人肤色较浅,面部轮廓也与中国人特别相像。此外,帕泰岛当地保有大量中国明代的青花瓷器,当地的墓葬形制以及编织手法也与中国华南的习俗极为相近。
②指美国加州旧金山与澳大利亚新金山(今墨尔本旧称)。据清末李圭《东行日记》记载:“美国卡厘方利亚省(即California)之三藩谢司戈城(即San Francisco),华人以其地产金,称为金山,嗣南洋澳大利亚亦产金,称金山,而以新旧别之。”三藩市因此被称为“旧金山”,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首府墨尔本及其周围主要金矿区则被称为“新金山”。
③又称“猪崽”,系广东方言。清末贩运被掳华工的船只多以木盆盛饭,开饭时“蛇头”呼华工一同就食,其呼声与农家吆猪进食相似,故有此蔑称。
④明代海禁政策曾历经多次调整。明初曾严禁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进贡除外)。永乐年间伴随郑和航海此令曾告取消,但嘉靖年间海贼倭寇猖獗,不得已又一度恢复。隆庆年间,明政府又重新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
⑤古朝鲜人为纪念箕子而建的衣冠冢。
⑥以色列学者加比·谢夫(Gabriel Scheffer)认为,离散族群可分为古典离散(Classical Diasporas)与现代离散(Modern Diasporas)。前者主要指那些无法完全融入所在国主流文化,不想被他人所同化,却又要在母文化中努力寻求心灵归宿的早期移民群体,如犹太人与非裔族群;而后者则是因应于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移民浪潮而涌现的,由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少数族群,在移入国生活、工作、深度融入,但与祖籍国保持着强烈的情感和物质的联系。
⑦Linda Y C Lim and L A Peter Gosling,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1,(Singapore:Maruzen Asia,1983),2.
⑧Linda Y C Lim and L A Peter Gosling,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1,(Singapore:Maruzen Asia,1983),151.
⑨参见《江泽民论侨务》,国务院侨务干部学校编印,2002年,第6-7页。
⑩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是西方社会学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分析视角。其核心观点是,在网络化社会中,人们对群体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减弱,不再将自己框定于有严格边界、以群体为中心的世界里。人们既不是毫无关联的一盘散沙,也不再是休戚相关的小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