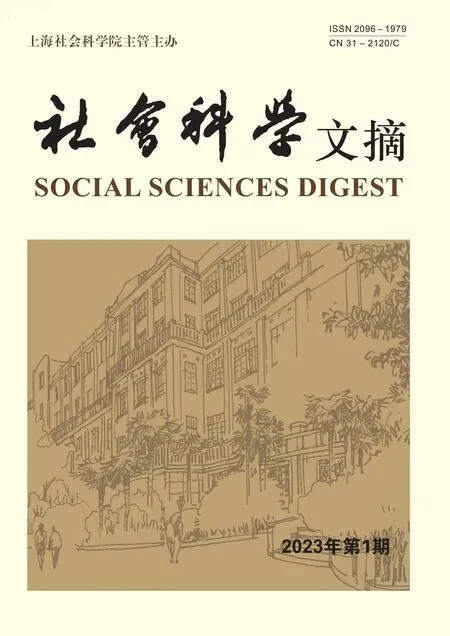书写都市:未曾缺席的现代海派新诗
文/杨新宇
未被命名的海派诗人
很少有学者专门谈论现代海派诗人或海派诗歌。许道明的《海派文学论》,为戴望舒、路易士专门列了一节,为海派诗人在这部专门研究海派文学的著作中留了两个席位。此外,仅见沈用大的著作对京派、海派诗人作了区分。
海派诗人之所以被漠视,究其原因,海派文学的命名最初大约是不包括诗歌的,“京海之争”涉及的海派作家基本上是小说家。并且海派之名,在当时被当作贬义词。因此,上海的诗人大概不会愿意被称为海派诗人,后来的研究者也很难想到将海派与诗人相联系。
另一方面,比起海派小说与京派小说的泾渭分明,海派诗人与京派诗人的某些作品也不一定有斩钉截铁的区分。这是因为诗歌相对而言本来就显得小众,因此受到商业侵蚀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小。毫无疑问,戴望舒算是最知名的海派诗人,他作品中流露的海派倾向也要比穆时英等的小说含蓄得多。
但海派文学毕竟不是只有小说,海派新诗的确是历史的存在,仍有一些诗人可以被归入严格意义上的海派诗人,如戴望舒、施蛰存、徐迟、邵洵美、朱维基、郭子雄、姚蓬子、姚苏凤、严翔、黑婴、禾金、史卫斯、刘枝、谭惟翰、何德明、郑康伯、应寸照、路易士兄弟、马博良及路易士影响下的奥耶、蓝本等。由于上海海纳百川的气魄,全国各地的许多作者,也在上海发表作品,加入海派诗歌创作的大潮,最突出的是广东诗人,如李金发、鸥外鸥、侯汝华、林英强、陈江帆、敏子,以及福建的宋衡心等。
当然,有些诗人兼有京派、海派风格的诗作,如李白凤、南星、吕亮耕、吴奔星、金克木、罗念生等。新月诗派通常被看作是京派的前身,但新月诗派中不仅有典型的海派诗人邵洵美,而且徐志摩的《别拧我,疼》等,都可视作海派诗歌。因此,对海派新诗进行研究,不应拘泥于诗作者,更应关注诗作的风格。
对都市景观的观察
与海派不同,京派诗歌被许多学者关注过。京派作家精致、纯粹,有明显贵族化倾向,即所谓士大夫气。他们的诗,虽已迈进现代主义的领域,却又与古典难舍难分。他们又多是南方人,侨寓古都,心怀隐逸之念,膜拜乡土与自然。海派诗人同样也写乡村、自然,这一点与京派诗人相似。
但与京派诗人笔下的古城风貌截然不同的都市,才是海派诗人创作中更为本真的一面。京派诗人大多久居北平,北平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但缺少现代都市感,在这种环境下浸染日久的京派诗人,不但写不了都市,而且不屑于写物质化的都市。如林庚虽写过《沪之雨夜》,但竟然把上海写出了古典感。海派诗人长期置身其中的半殖民地上海,是个洋场气息浓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上海的都市感的体验,正是众多海派诗人的灵感来源。
施蛰存曾说“《现代》中的诗”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他们是体验现代生活的现代人,对现代生活的体验理应写成诗,但海派诗人不可能整天都写这些东西,只能说上海的现代派诗出现了一些直接表现都市的作品,毕竟海派诗人还写过不少其他题材的诗。当然,这类作品的确是海派诗歌中最具标识性的。
海派诗歌中出现了对都市风景的直接展现。徐迟赞美摩天大楼上的大钟的诗作《都会的满月》,早已被许多学者写入论文;陈江帆也写过《海关钟》;禾金的《四度空间浅释》也写到了“街端的大钟”,并且写到了“车马的狂流”和“人的流”。霓虹灯是都市的象征,“它与街道、广场、舞厅、商场等都市场景紧密相连,它使都市的夜晚如同白昼,以缤纷的色彩吸引着人们的视觉注意力,对人们的心智形成巨大诱惑。它是物质的,又是虚幻的;它是绚烂的,又是凄迷的”。子铨的《都市的夜》开头就是:“年红,拨奏着颤栗的旋律:/作大爵士的合舞。”吴汶的《七月的疯狂》也写道:“年红,浓烈地抓人,/波动着爬过街头,/勾成七月的疯狂。”
上海的建筑,在海派诗歌中自然也是不能少的,常任侠的《夜》写到“一头毒蛇爬行于十五级之高楼”;张宗植的《初到都市》写了“第二十一层房顶”。禾金的《铁桥的黄昏》写铁桥这一“雄伟的建筑物底记忆”。苏州河等上海标志,也得到了表现,如番草的《桥》《苏州河的歌》等。十里洋场的上海,还出现了许多西方化的场所,如咖啡座、舞厅等。这在海派诗人笔下也多有表现,徐迟写有《年轻人的咖啡座》,侯汝华写有《咖啡店的女侍》。关于舞厅的诗则更多。
而陈江帆的《都会的版图》,更写出了都会的无厌的扩张,“起重机昼夜向海的腹部搜寻”,写到了“崭新的百货店”和“电气和时果的反射”。施蛰存甚至还在《桃色的云》中发出了对工业社会的赞美。相形之下,林徽因的《古城春景》,可视为京派诗人书写城市的代表作,但作为“新观念”矗立“在古城楼对面”的,却是“聚一堆黑色的浓烟”的烟囱,对工业文明的抵触显而易见。
对都市经验的描摹
景观还毕竟只是都市的表层,对都市经验的描摹,对都市情绪的捕捉,才是海派诗人更深一层的探索。上海只能称“市”,不能称“城”,诗人们为都市文化所深刻滋养,海派小说擅写世俗化的市井生活,海派诗歌则在触摸都市的脉搏。
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改变了时间,也为人与人的交往提供了新的空间。在机械运动的速度的裹挟下,身体与心理都出现了新的体验。名不见经传的洛依,发表在《现代》上的《在公共汽车中》,写出了新奇的都市经验。徐迟的《沉重的巴士》和鸥外鸥的《爱情乘了BUS》等,则将公共汽车象征化。万曼的《电车》发表于《青年界》,对乘电车体验的描摹可谓精彩至极,颇像新感觉派小说家的手笔。火车则将城市与城市连接在一起,而途中经过的都是乡村,火车便也具有了象征意味,火车也成为海派诗人关注的对象。
市场向来是一个没有诗意的地方,陈江帆的《减价的不良症》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将市场的音调比喻为蜂巢般嗡嗡着,市场便瞬间鲜活了起来,写出了“工业风的音调”。许久的《写字间里佝偻着的人》,以超现实的手法,写青春生命中的“执矛的骑士”驰去了,而自己困在写字间里日渐佝偻,将都市刻板的工作状态下的人生描摹得淋漓尽致。
当时的上海作家,有相当一部分是舞场的常客。戴望舒写日本舞女的诗多达三首:《百合子》《八重子》《梦都子》。这三首诗体现了很典型的海派风格,异常轻佻。严翔的《舞》,毫无掩饰地传达了舞场的肉欲气氛,并揭示了逢场作戏的舞场情感。路易士的《初到舞场》,吴汶的《七月的疯狂》将舞场完全“妖魔化”了,但舞场中触目惊心的感官刺激,的确在诱使着人疯狂地堕落。比舞女更底层的妓女,也常出现在海派诗人的笔下,侯汝华写有《卖笑女》,苏俗写有《街头的女儿》,海派诗人对这些受尽屈辱的底层女性给予了同情。
本雅明式的都市漫游者,在海派诗歌中也有体现。人和人的关联在现代社会发生着变化,尤其在上海这个都市当中。关于邂逅的主题,开始出现在海派小说中,同样,擦肩而过、转瞬即逝的短暂体验,也被诗歌所捕捉。戴望舒不仅在《单恋者》中说“人们称我为‘夜行人’”,而且写有一首《夜行者》,其《雨巷》虽有古典风味,然而又有一种现代式的期待在里面。徐迟等人的诗作中,也有对都市景观的跳跃式描绘。徐迟的《一个没有护照的侨民》,不能当作写实之作看,表现的还是孤独寂寞、无处皈依的主题。
都市生活丰富多彩,现代事物也大量出现,不用说香烟被徐迟、姚苏凤、路易士等很多诗人书写过,甚至连运动会,也开始进入诗歌,如姚苏凤在1935年全运会中写有《拟远人作》。此外,姚苏凤、路易士、禾金、陈江帆等许多诗人都写过疾病,或许是将身体的病作为病态都市的一个隐喻。海派女诗人相对少,沈旭春(笔名雨樱子)不多的诗作,就颇值得珍视。她的《无色的寂寞》写自己的梳妆台,写“富有异国的情调的灯”,写灯绢子,写各种外国化妆品。林徽因等京派女诗人,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内容。陈江帆还在《公寓》中写到在都市的生存状态,“流居在小小的公寓中”,但这公寓不是家,故乡的家是有“古典的程序”的。路易士的《都市的口味》写得非常生猛,可以看作海派诗人对都市的适应。
由于诗歌是相对更个人化的文体,而上海又是一个思想开放、生活丰富的都市,因此海派诗歌中也多有对欲望大胆的表现,而这种欲望带有明显的都市特点,等而下之的作品,也难免会有一些色情的描摹。都市中的女性成为海派诗人笔下被看的客体,徐迟在《七色之白昼》中膜拜着“胴体的女郎”,这还算是正常的欲望表达;施蛰存更在《卫生》中呈现了一种既大胆又幽微复杂的性心理。他不但妄想看到少妇华尔纱下的身体,而且运用了奇怪的通感,将女性的身体比作食物。这样的修辞为数不少,如戴望舒的《梦都子》、严翔的《葡萄》、徐迟的《恋的透明体》等。用成熟、饱满的果实来形容女性,完全将女性物化,似乎是弗洛伊德口欲期理论的完美阐释。海派诗人不但有植物化的欲望描写,更有动物化的变形,施蛰存写乌贼鱼在“作猎艳的散步”;路易士写“吻你的发的章鱼”;陈江帆说“抚慰你,/如抚慰一匹黑鹿”。邵洵美、朱维基等创作的唯美颓废的诗歌,更是海派作品中的典型。
海派诗人难免患有精神分裂症,海派诗人面对的原本就是分裂的上海,他们一边怀想着乡村与自然,一边耽溺于都市的物质享受;一边感受着现代生活,一边又被映入眼帘的社会黑暗所冲击。因此,他们在诗中表达传统风味的乡思乡愁,也在孤独寂寞中书写都市。而对都市的负面,海派诗人尽管缺少左翼诗人的批判锋芒,但也还是有所表现。
不纯粹的先锋
相比京派诗人的作品而言,海派新诗表现出的先锋性,恐有过之而无不及。京派运用的是较为传统的象征主义,而象征手法本就与中国的“比兴”传统若合符节,加之京派诗人对典雅、纯粹的追求,京派的象征主义又更多地与古典式的意境相融合。
而海派所接受的现代主义,除了象征主义外,尚有唯美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和意象派,而这些几乎是京派所没有的。海派新诗的先锋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为上海都市趋新求变的特点所决定的。早在新诗诞生期,郭沫若便在《天狗》中以惊世骇俗的诗句发出了超现实的呐喊,其后象征派、唯美颓废派,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陆续出现在海派诗人中,进行着不懈的先锋试验。
传统诗歌以内向的表达为主,京派也不例外。海派诗人的都市体验,对思绪情感的放肆表达,在含蓄、内敛、节制的京派诗歌之外,带来一种狂放不羁的新风格,写出了都市的节奏感、现代感,艺术手法虽有粗暴之处,但也带来新颖、尖锐的体验。徐迟《我及其他》中颠三倒四的“我”,彰显了年轻、鲜活、向上的生命力,是现代文学中颇为珍贵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奥耶《摄氏一百度的朗诵》仍在进行的热情似火的表达,已是40年代末海派新诗的绝唱了。此外,意象派的出现,亦是海派新诗的贡献,意象派运用了类似蒙太奇的现代手法,与都市感是合拍的,施蛰存的《意象抒情诗》、吴奔星的《失眠》等,视觉丰富、逻辑跳跃,给人新奇的审美感受。京派诗歌中只有少数,如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等,才有这样的拼贴感。
海派新诗还塞入了大量数字和符号,鸥外鸥写风“书写了一个小草的e字”;路易士则别出心裁地宣称“手杖7+烟斗6=13之我”;40年代蓝本的《整数1之分割》,更直接将分数写进了诗中,表现个体的分裂。海派新诗中又大量地出现了无诗意的学科名词,徐迟的《隧道隧道隧道》,堆积了古生物学、岩石学、层位学、矿物学、地质学等大量专业名词,却并不令人厌烦。这些出格的诗句正体现了咄咄逼人的先锋性,实验着诗歌语言的可能性,既符合陌生化的诗学原理,又带来强烈的现代感。
但海派新诗的先锋性又是不纯粹的,这同样是海派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海派文化既是开放的、现代的,又是趋利的,尽管诗歌书籍销量有限,很难带来经济收益,但趋利可以转化为趋名,仍然需要吸引读者的眼球,以怪异的意象制造耸动的效果,语不惊人死不休,以致某些海派新诗也有感官刺激的追求。海派诗人突出野性的生命力,以最接近本能的方式将情欲表现出来。
海派新诗的缺陷也是明显的,由于更外向,海派诗歌往往有热闹的外表,但在深度上有所欠缺,不像京派诗歌那样更多对生命和存在意味的探究,其优秀之作甚至上升到哲学和人类学的高度。不够从容,失去诗歌应有的节制美德,也是海派新诗的严重缺陷。比如幽微复杂的潜意识,尤其是性心理,本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施蛰存却大胆地将它呈现出来,实际上外向化了,与京派感伤的内向化情绪已不可同日而语。
结语
尽管对海派新诗的成就不宜作过高的评价,但海派新诗表现都市,仍有独特的美学价值,自有其历史意义,即使一些格调不高的诗,在某种层面上也“记录”了历史的真实。且从创作总量上来看,海派新诗恐怕是超过京派新诗的,不知名的海派小诗人似也较京派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