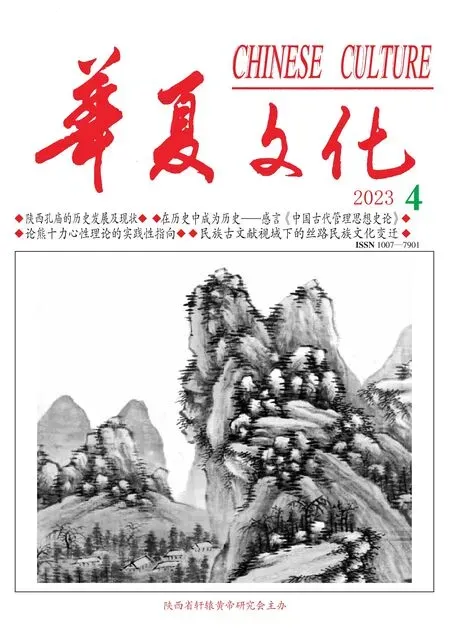民族古文献视域下的丝路民族文化变迁
□马小玲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silk road)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是连接东西方政治、经济的交通要道,更是不同文化交流的纽带。在这一文化交流要道上行进的部族至少有15个,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不少于20种。根据德国学者勒柯克(Le Coq)的调查,仅在丝路交通要冲吐鲁番就出土了19种语言的古代文献。
我国文化语言学的倡导人申小龙认为:“语言是人类文化成长的关键,其他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存在都以语言为基础。如果人类文化是一个由各种文化现象编织在一起的网络,那么,语言就是这个网络的总的结。”(申小龙:《语言的文化阐释》,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7页)质言之,一部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民族语言发展的历史,因此一种语言实质就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本文就是以语种和文献的变迁为线索,探讨丝路文化的三个历史阶段。丝绸之路民族文化的变迁主要由语言和文字来体现,其支配力量是民族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和宗教。
一 印欧文化
(一) 印欧文化的萌芽(公元前4—纪元开始)
从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之间,在黑海草原的印欧游牧民族陆续离开草原,开始了近1500年的大迁徙活动,这一活动对世界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古代印欧人种已遍布在东亚、北亚及中亚和西亚等地区,因其人种“深目高鼻”男子多须,在汉文献中被称之为胡人。今新疆早在月氏人西迁之前便有印欧人种的足迹。《山海经·海内东经》云:“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
公元前2000—前1800年之间,也就是印欧人种第一次大迁徙时期,一支从中亚草原向南迁徙的印欧人进入了丝路南北道的绿洲地区。公元前1200—前1000年之间,所谓印欧人种吐火罗人也进入丝路南北道的交汇地区。在史前时代大批印欧人种移居丝路绿洲的基础上,一些属于印欧人种的部族陆续迁入。至公元前334—前320年左右,即希腊亚历山大东征,引起大批操印欧语系语言的伊兰人进入丝路绿洲之后,印欧文化开始在丝路萌芽。
印欧文化萌芽的典型标志就是古波斯语、帝国阿拉美语、古巴克特利亚语、塞语等在丝路西段——中亚地区开始流行,阿拉美文、古波斯文、古巴克特利亚文、佉卢文、希腊文、塞文等文献陆续出现。根据哈尔玛塔(Harmata)的观点,“上述语言大多属印欧语系伊兰语支,多为印欧人的后裔在丝路西段所使用。”(Hartmann. Indrasennas Beichte Ein Sanskrit-text in uigurischer Schrift aus Turfan[J].Berliner Indologische Studien,1996(9-10):203-216)其中阿拉美铭文6处、巴克特利亚铭文5-6处、佉卢文陶片、钱币、石刻铭文若干件、希腊文碑铭、陶片、银器铭文数量也不少。塞人文献(以南部塞语方言为代表),主要是指佉卢文和婆罗密文石刻。关于这一时期的伊兰语支文献的特点,可以基本概括为行数少、内容简单、形式单一、流布地区较为集中等。例如坎大哈石刻、艾哈农阿拉美陶片等。
(二) 印欧文化的发展(公元1—6世纪)
公元1世纪前后,在丝路南北道及其周围逐步形成了若干由印欧人种部族形成的城邦之国,如楼兰、于阗、莎车、车师等。这些城邦国家的居民主要是塞人、属于印欧部族后裔的吐火罗人、粟特人以及月氏人等。
印欧文化发展的显著标志是丝路南北道印欧语族语种文献的大量出现,印欧语族语言对宗教的传播以及犍陀逻佛教艺术的诞生等。
属于印欧语族的语言有吐火罗语、犍陀逻语、粟特语、和阗塞语,它们主要流行于丝路中段,即塔里木盆地。其中吐火罗文献包含若干佛经、佛教故事、诵佛诗歌等。丝路出土的吐火罗文献主要存在于西格(Sieg)和西格凌(Siegling)刊布的《吐火罗语残卷·A方言》《吐火罗语残卷·B方言》,托马森(Thomas)刊布的《吐火罗语残卷·B方言》,其中包括《法句经》、佛本生故事、情书、护照等,以及新疆博物馆所藏《弥勒会见记》等(大约在5世纪)。除残卷外,还有一些吐火罗粗刻和碑铭。吐火罗语写就的佛教文献有:《十诵律》《杂阿含经》《一百五十赞颂》《波逸提法》等;犍陀逻语佉卢文文献主要为世俗文书,包括国王赦谕、公私信札、各种契劵、簿籍帐历。目前已知的佉卢文文献多被收录在《斯坦因在中国突厥斯坦所发现的佉卢文字集录》中,共收763件。粟特文文献主要有宗教文献、社会经济文书、钱文、印章、碑刻、壁画题记、书简等。迄今刊布的粟特语主要文献有:粟特古信、《维摩诘经》《大般涅槃经》《佛说善恶因果经》、《大悲经》等佛教文献以及景教、摩尼教文献《巨人书》《福音书》等。除穆格山文书属于7-8世纪外,大多数粟特文文献属于公元2—7世纪。和阗塞语属于中古伊兰语,它比其他中古伊兰语更古一些。大多数和阗塞语文献是佛教文献,属于佛教文献的有《弥勒授记》《妙法莲华经》《观世音陀罗尼》《阿弥陀赞》《般若婆罗密多经》《普贤行原赞》等。
从史前直到6世纪,印欧语系语言在丝路南北道都是地区优势语言,一些丝路地名就是用印欧语系语言来命名,用汉字来记音的。例如于阗(Hvatana)就是塞人一部落名称的译音(尉迟),莎车是古代塞人(Saka)族称的汉字记音,龟兹(Kuci)一名是古代西吐火罗语kutsi(意为白,古代龟兹人多姓白)汉字音译,疏勒(Suγlak)地名则属于东伊兰语支,是古代粟特语的一种方言对粟特人自己的称呼。由于佛经的翻译和汉语、印欧语系语言的接触,从而出现了一种汉语变体——佛教汉语。蒋绍愚先生研究发现,经由佛经翻译所导致的语言接触使得汉语有了完结与完成两种语义范畴的对立。汉语中的一些佛教词语,如沙门、沙弥、须弥、弥勒、佛、分卫等就是来自吐火罗语。
在这一历史时期,史称三夷教的祆教、摩尼教和景教陆续进入丝路地区,其主要传播者就是粟特人。英国贝利等人研究,“丝路诸国在接受佛教之前曾经信仰过祆教。”(Baily. KHOTANESE TEXTS[M].LONDON: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69:59)佛教在中亚的流布亦是凭借这些印欧语系语言。斯坦因(Stein)就认为:“和田和尼雅一带的佉卢文字的出现是与佛教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的。”(斯坦因:《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巫新华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
丝路的艺术形式主要有壁画和舞蹈。植根于希腊艺术的大夏、贵霜王朝的壁画在佛教诞生前就已传到丝路南北道,如尼雅就曾出土手持丰裕羊角的希腊女神狄刻。由希腊艺术和佛教艺术结合产生的犍陀罗艺术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发展的时期,这在龟兹石窟、米兰壁画或丹丹乌里克遗址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二 突厥文化
(一)突厥文化的萌芽(公元6—8世纪)
6世纪以后,丝路南北道的印欧文化影响有所衰减。造成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伊兰人的本土化、中原影响的深入和突厥文化的萌芽。
公元554—558年,西突厥与波斯联合进攻呾哒,并瓜分其领土。在占领于阗后,西突厥室点密的牙帐设在龟兹以北阿羯田山北麓裕勒都斯溪谷;611年西突厥射匮可汗也将牙帐设于此地。后突厥汗国默啜可汗于709年进行西征,并将势力扩展到丝路西段的铁门关(与大食统治范围相接壤)。古突厥文碑铭《毗伽可汗碑》《阙立啜碑》《翁金碑》也记录了后突厥对焉耆、和阗、龟兹、哈密、别失八里的战争。突厥人的入侵虽然没有改变丝路南北道主要居民的面貌,但至少使王族发生变化。龟兹、焉耆王姓本来就带有伊兰色彩,至隋唐时已开始突厥化。
佛教入唐以后又大规模逆向传于丝路南北道,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汉文化的流布。这种反哺表现在石窟壁画内容和佛经翻译上。库木吐拉千佛洞就是汉人开凿、汉僧主持的,其经变画不同于西域本生画。于阗出身的提云般若、实叉难陀、智严、尸罗达摩等翻译了大量的汉文佛经。
突厥文化萌芽的典范代表就是古代突厥文在丝路西段和中段的传播以及文献的出现,粟特人对古代突厥文的推广等。
丝路古代突厥文文献主要集中在丝路西段的七河流域和费尔干纳盆地。属七河流域的有墓石、钱币、日用品和木棒上的铭文;属费尔干纳地区的有陶器和金属器皿的若干短小铭文。在穆格山文档中还发现了写在皮革上的古代突厥文文书。此外在吐鲁番亚尔和屯、吐裕沟、火焰山公社、米兰戍堡等也发现了一些8世纪左右的古代突厥文文献。
从公元前2世纪到唐朝末年,粟特人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占支配地位。《资治通鉴》卷184载:“突厥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特别是突厥可汗,往往多信任粟特人。《资治通鉴》卷192载:“颉利又好信任诸胡而疏突厥。”在与突厥人经商共事的时候,粟特人必然会使用突厥语。惯于在丝路上行商的粟特人,进而将突厥文化传布到各地。
(二)突厥文化的发展(公元8—10世纪)
8—10世纪是突厥文化(包括回鹘文化)在丝路南北道快速发展的阶段,其突出表现在:丝路南北道地方政权的突厥化,回鹘文文献的大量创制,回鹘文对宗教传播的促进,突厥—回鹘文化的推广等。
9世纪前后,继牟羽可汗亲来丝路重镇高昌延请摩尼僧以来,漠北回鹘汗国的势力开始西倾。9世纪上半叶,在丝路上已经有了若干回鹘统辖地区。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西迁的一支回鹘(约20—30万帐)迁到别失八里、高昌及葛逻禄人居住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852年,其中部分回鹘建立高昌回鹘王国,其势力一直延伸到焉耆、库车一带。西走葛逻禄的部分回鹘促进了丝路南道的突厥化。从漠北回鹘汗国的古代突厥文碑铭来看,突厥如尼文—粟特文双语文献已出现。高昌回鹘王国建立不久,就用回鹘文逐步取代古代突厥文。回鹘文来源于古代粟特人使用的草体粟特文,而后者又来自阿拉美文。突厥人和回鹘人在与粟特人的交往中逐渐采用了这种文字。属于10世纪左右的回鹘文文献,大多属于佛教文献。多数社会经济文书、书信、历史文献以及密宗文献等应当属于10世纪以后。现存主要回鹘佛教文献主要有:《阿含经》《诸方平安经》《法集要颂》《弥勒会见记》《十业道譬喻鬘》《佛所行赞》《无量寿经》《俱舍论》《缘起论》《妙法莲华经》《八阳神咒经》等。
高昌回鹘王国建立不久,就用回鹘文逐步取代古代突厥文。属于10世纪左右的回鹘文文献,大多为佛教文献。多数社会经济文书、书信、历史文献以及密宗文献等应当创作于10世纪以后。
回鹘迁居高昌后,继承和发展了当地存在已久的佛教、摩尼教、景教和儒教文化,创造出辉煌的回鹘文化,并对丝路南北道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回鹘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混合性,即将印欧文化、汉文化、突厥—回鹘文化融为一体。由于这一形式适应了丝路南北道城邦居民的需要,从而极大地推广了突厥—回鹘文化。
自8世纪后半叶回鹘改宗摩尼后,摩尼教就成为回鹘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一环,因此许多摩尼教文献就是用摩尼文和回鹘文写就的。例如《摩尼教赞美词》、《沙卜拉干》译文残卷、《摩尼教寺院文书》、《美味经》、《摩尼教徒书信》等。
以高昌为中心的突厥—回鹘文化圈,也对丝路南北道的文化产生影响。如回鹘日历本身用粟特语写出,每日先写粟特语的七曜历,然后配列音写汉文的甲、乙、丙、定等十干名称,再用粟特语写突厥人使用的十二支兽名,最后把五行译为粟特语。由于西迁的回鹘人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人数上都占优势,突厥—回鹘语逐渐成为丝路南北道的通用语言。原著居民的印欧语系语言逐渐消亡,不再被使用。当然在这一同化、融合的过程中,原著居民的语言也给战胜的突厥-回鹘语以某种程度的影响,进而成为其底层语言。由于底层语言是印欧语系语言,它在客观上促进了突厥文化的流布。
同样,突厥文化的影响也发生在丝路西段。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地流行的粟特语、花拉子模语等伊兰语逐渐为突厥—回鹘语所取代。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通行势必会导致文化的跨界传播,从而扩大文化的影响程度。丝路突厥化的形成,使得回鹘—突厥语逐渐战胜了当地的印欧语系语言成为通用语,随之而来的就是回鹘-突厥语成为传播丝路宗教的主要工具。
7—10世纪,景教在中原内地十分兴旺。景教的传播基本上是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因此,丝路南北道诸城邦大都有景教信仰。高昌回鹘亦接受景教,并用回鹘文翻译和创作了大量的景教文献。根据宗德曼(Zonderman)、威廉姆斯(Wilhemlms)的统计,保留在德国科学院的就有50余件,如《巫师的崇拜》《圣乔治殉难记》《回鹘基督徒婚礼上的颂词》《祈祷文》等。
三 伊斯兰文化
(一) 伊斯兰文化的萌芽(公元10—14世纪)
伊斯兰文化在丝路南道的萌芽始于10世纪左右,它是伴随着丝路西线的伊斯兰化、佛国湮没和佛教没落、王朝语言的兴起、花拉子模文化的影响而同时进行的。但是,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文化多止步于丝路南道和西段。
751年在塔拉斯河畔,阿拉伯军队对唐朝军队的胜利,把唐朝在那里的影响一扫而光,从而为伊斯兰教势力的东进打开了大门。阿拉伯人对帕米尔以西绿洲的统治大大推进了当地的伊斯兰化。伊斯兰教的萨曼尼王朝不断进攻喀喇汗王朝,至迟10世纪中期,喀喇汗王朝就皈依了伊斯兰教。从11世纪史学家阿卜达勒·加菲尔的著作《喀什史》中可知:“喀喇汗王朝的萨吐克·布格拉汗首先率领其人民接受伊斯兰教。”(艾布·福图赫·阿卜杜勒·加法尔·阿勒马伊:《喀什噶尔史》,新疆社会科学院油印本1985年,第18页)
布格拉汗之子木萨对居住在巴拉沙衮的长支大汗发动宗教战争,并灭掉长支可汗,从而使丝路南道开始伊斯兰化。11世纪(1006年)时,信仰佛教的和阗王国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灭亡。自此,该地居民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公元千年左右,佛教在印度中心地区就销声匿迹了。在和阗被征服的最后阶段,印度因素再次对和阗文化生活产生影响,这一点表现在密教的产生上。随着和阗的沦陷,佛教在丝路南道的影响越来越小。这对致力于传播佛教的突厥-回鹘文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在喀喇汗王朝时期,以喀什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使用哈卡尼亚语(或曰喀什语或王朝语言)。喀喇汗王朝的伊斯兰文献是用哈卡尼亚语写就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尤素甫·巴拉萨衮的长诗《福乐智慧》。伊布拉音穆提义认为:“回鹘语和哈卡尼亚语的区别只是由于用这两种语言所写成的书面文献反映的文化不同(回鹘语书面文献主要反映佛教、摩尼教环境中创造的文化,哈卡尼亚语反映伊斯兰教影响下产生的文化)。”(依布拉音·穆提义:《维吾尔文化研究点滴》,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宗教文化的不同亦在文献中得到体现。在用回鹘语写成的书面文献里翻译或直接借用的梵语、吐火罗语及汉语名词术语比较多,而在哈卡尼亚语中吸收阿拉伯、波斯语的名词术语则较多。换而言之,哈卡尼亚语也是突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浅层混合体。
金帐汗国虽然只是在丝路西段的北部地区,但是其克普恰克-花拉子模文献对于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属于克普恰克-花拉子模文献的主要有阿布·海严的《智慧的礼品》、库特普的《胡斯劳与席琳》、花拉子米的《爱情书》等。
(二) 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公元15—19世纪)
伊斯兰文化在丝路南道的深入,在北道的发展主要与伊斯兰教的渐进东传、察合台语的形成、察合台文献的繁荣密不可分。
1347年,东察合台汗国秃黑帖木儿率先皈依伊斯兰教,其所属16万蒙古人变成了穆斯林,此举为后来伊斯兰教最终在丝路南北道占据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至16世纪,伊斯兰教在丝路南北道诸地多数居民的精神生活中完全占有主导地位。
察合台语形成于帖木儿王朝时期(1405—1502年),是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下,从哈卡尼亚语演变而成的。它主要采用阿拉伯文的28个字母、并从波斯文借用了4个字母。此外,还吸收了阿拉伯文的若干元音、辅音字母以及其他辅助符号。根据统计,察合台语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曾一度达到50%~60%。
察合台文献主要流行于丝路西段和丝路南北道。15世纪是察合台文献中的古典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代表性作品有:鲁特菲的《诗集》、纳瓦伊的《诗集》等。16世纪的察合台文献主要有昔班尼的《诗集》、哈衣达尔的《拉什德史》、巴布尔的《巴布尔回忆录》。17、18世纪,丝路南北道的察合台文学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尼扎里的《不幸人的故事》、沙伊尔阿訇的《伊斯兰之书》等。
语言不仅仅是人们用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工具,它还沉淀着历史文化的密码,因此参研一门语言,可以追溯历史,找到还原历史演变的关键。海德格尔曾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世界就在我们的语言之中,同样民族语言存在于民族体之中,通过民族语言的变化,可以推演出民族的变迁。丝路现代民族是经过数千年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冲撞与融合形成的,这一民族融合的进程从未被间断过。 “那仁”、“馕”“抓饭”“手抓肉”是丝路各民族都爱吃的美食,“坎土曼”、“皮亚孜”“冬不拉”是丝路各民族的通用词汇,“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为一特异之文化框系,与异系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页)一个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一个民族的骄傲是以具有吸引力、魅力的强大民族文化为基础的。丝路历史、文化和民族的变迁也证明了一个开放的民族,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会是一个强大的、具有生命力的民族,而一个封闭的民族终将被历史长河所湮灭。
综上所述,丝路之所以拥有如此绚烂多彩的文化,不仅是因为欧亚大陆被丝绸之路所贯通,更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片富有魅力的土壤不断进行着语言、文化、民族的融合,不断汲取着东西方文明的精华,才铸造了人文与民族的完美结合,造就了今天丝路的多彩文化。研究丝路的文化,对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意义和语言学的意义非常深远。特别是丝路东段的文化研究,为我们探寻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发展脉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