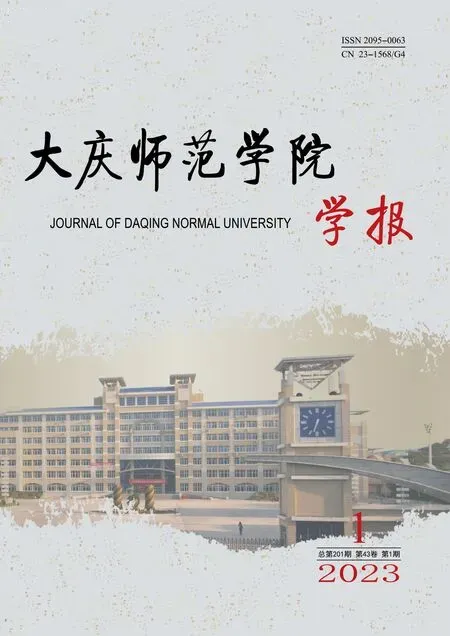论新时代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问题与应对
侯 璐
(东北林业大学 文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组织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平台经济应运而生,并且呈现出头部平台优势引领、中小平台迅速崛起、多行业平台并行发展的全新格局。这一新型经济形态在发挥其绝对优势的同时也逐渐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最有待深入讨论且亟需解决的是对市场良性竞争与消费者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平台垄断问题,以及政府通过技术分析与法律认定对其规制的反垄断问题。事实上,近两年来国家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已经充分体现了对平台经济有序创新发展的高度重视:多次会议均强调了“防止平台垄断与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性,2021年2月国家发布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下文简称《指南》);2021年4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先后对阿里巴巴与美团“二选一”行为、斗鱼虎牙并购行为、腾讯网络音乐独家版权进行了反垄断执法;2021年11月国家反垄断局的成立更是一个中国式反垄断的里程碑事件。
这一系列兼具文件指引与实践执法特色的重大举措充分表明:我国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规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精神。这要求我国相关反垄断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性,在促进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与良性竞争的同时,结合数字媒介、金融科技、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具体运行环境做出具体分析,更加审慎地甄别不同程度的垄断行为,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处理好反垄断规制中的几种平衡关系,做到鼓励竞争与防止垄断的有机结合、宏观指引与微观论证的有机结合、严谨技术分析与充分法律判定的有机结合。为此,只有在理论上深入揭示平台经济的新特点,才能全面厘清监管规范的新思路,进而实现“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新目的。
一、反垄断规制的新领域:平台经济
通常所说的平台经济是指以一定的价格机制连接不同用户群体进行产品或服务互动的双边或多边市场(Two-Sided or Multi-Sided Market),(1)参见Rysman M, “the Economics of Two-sided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23, no.3 (June 2009), pp.125-143.而这一经济形式的跨市场性(Crossing market)、动态竞争性(Dynamic Competition)、非对称定价性(Imbalanced Pricing)、交叉网络外部性(Cross-Group Externality)以及大数据匹配效应(Big data matching effect)等特征很容易形成寡头垄断的现象。(2)参见Rochet J C, Tirole J,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1, no.4 (August 2003), pp.990-1029.因为平台经济的独特性就在于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s Law),其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几何速度增长,从而容易形成赢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的局面。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的结构性垄断是平台经济的普遍特征,如全球市值前10家企业中便有8家是数字平台企业,中国市值前10家企业中也有4家是平台企业,(3)参见《全球及中国平台经济发展态势分析:2019年全球平台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20年12月29日,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2012/919697.html,2021年12月20日。可以说一家独大是数字市场结构的显著特征。但由于平台经济涉及电子商务、搜索引擎、数字音乐与视频、第三方移动支付等不同类型,每类平台各具特色,竞争与垄断状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在分析每一行业竞争态势的同时,更应具体区分经济学上所强调的垄断结构与法学上所强调的垄断行为之间的区别,因为具有垄断地位经营者的行为不同于垄断行为,即使平台经济中存在一家独大的垄断结构,也并不必然存在着《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行为。
常见的垄断行为包括电商平台的“二选一”行为、外卖平台与商旅平台的“大数据杀熟”行为以及一些头部平台的大规模并购行为。由于平台经济的杠杆效应较强,成熟周期较短,一些大型平台企业凭借资本技术优势与市场主宰权,迅速扩张规模、拓宽业务,具有超强的用户黏度,甚至利用大量资本补贴的方式排挤竞争者,继而进行价格垄断,这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大大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最终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效率、公平与福利。(4)参见Brock J W, Obst N P, “Market concentration, economic welfare, and antitrust policy,”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vol.9, no.1 (February 2009), pp.65-75.如果任由其无序发展,必然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市场失序格局。但同时平台经济领域的竞争性也异常激烈,这既表现在同一平台内部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竞争,也表现在不同平台主体之间的外部竞争。虽然平台经济容易形成一家独大局面,但由于互联网企业动态竞争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即使存在阿里巴巴、百度、腾讯这些巨头企业,但仍涌现出美团、快手、拼多多、字节跳动等这样的平台“新贵”。由此看来,平台经济领域呈现出普遍的激烈竞争与个别的垄断行为并存的发展态势,做好激励创新与规制垄断的平衡是数字经济时代动态市场治理的重要难题。为了维护市场竞争的整体氛围,执法机构应仔细甄别企业创新与平台垄断的重要区别,因此,“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必须谨慎,避免将其判定为违反托拉斯法的错误行为”。(5)Barnett T O, “Maximizing Welfare Th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vol.30, no.15 (August 2007), p.1191.
平台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对垄断行为的判定不能盲目套用传统的反垄断分析方法。一方面,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抑制个别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国家采取及时的反垄断规制显得尤为迫切。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的反垄断规制面临诸多疑难问题的挑战。虽然现有的《反垄断法》仍然适用于平台经济领域,但这一经济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对这一领域的反垄断规制思路与监管措施也必然做出相应突破。如平台经济的跨界竞争特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将传统单边市场规制理论中以质量与产品价格为中心的传统需求替代分析方法简单照搬到对平台企业定价策略的特殊性上,也不能以传统的营业额或市场份额为标准,而应以有效转化率与用户活跃数为标准来认定企业规模。特别是在界定相关市场过程中,平台企业的多用户交互特性涉及到界定多个相关市场与界定一个相关市场的问题,这便涉及到企业与市场的交互关系,而以市场份额、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等结构性指标为原则的传统反垄断分析方法已不适用于这种具有多用户归属、交叉补贴、价格歧视、掠夺定价等特征的高集中度平台经济。这要求我们在具体分析不同类型平台企业特点的基础上,本着差异化与审慎性的原则开展反垄断工作,提高反垄断执法依据的有效性。
总体而言,平台经济领域的新特点为传统反垄断规制提出了诸多理论疑难与现实挑战,涉及反垄断流程的各个环节,包括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滥用行为构成与反垄断执法实践等各个方面。
二、反垄断的首要问题:相关市场界定
相关市场界定问题是反垄断规制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方面,《指南》第4条给出了明确的规定。(6)参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2021年2月7日,https://gkml.samr.gov.cn/nsjg/fldj/202102/t20210207_325967.html,2021年12月23日。将相关市场界定视为反垄断规制的首要问题是因为反垄断规制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自由竞争,保护自由竞争的首要步骤便是识别竞争者。在互联网企业创建之初,其业务范围比较专一,或社交网络或商品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识别竞争者是一件较为容易的事,但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企业日益呈现出平台、算法与数据集中融合的趋势,如淘宝、腾讯、脸书、亚马逊等都是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平台企业,这使竞争者识别问题变得困难,市场边界问题也更难把握,由此带来了反垄断执法的重重困难,如2007年谷歌收购DoubleClick、2014年脸书收购WhatsApp中都存在相关市场界定模糊问题。(7)参见摩尔、坦比尼:《失控的互联网企业》,魏瑞莉、倪金丹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9—51页。
一般情况下,相关监管机构往往运用基于需求替代性标准的假想垄断者测试(SSNIP)来界定相关市场问题,(8)参见陈兵:《平台经济领域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审视: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4条为中心的解读》,《法治研究》2021年第2期。即通过选定合理备选市场后,实施5%—10%的涨价幅度,一定时期内观察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如在多次循环中消费者不再寻求其他替代品,这一集合即为相关市场。相关市场界定的传统分析方法主要是依据静态竞争与单边市场的状况来进行,但平台经济领域多呈现出非对称性定价、动态竞争性与多边市场性的新特点,从而降低了以往常规方法的适用效力:平台经济的非对称性定价会使以往的假想垄断者测试方法失去固有效力,基准价格为零的免费模式下的价格上涨必然损失很多免费端客户;平台经济技术创新的高频性、市场发展的剧变性以及跨界竞争性极大增加了市场边界的模糊程度;平台经济的双边、多边性也必然涉及多个相关市场,由此便需要将它们之间的网络外部性纳入考虑范围。特别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隐私与用户注意力的免费性使界定方法变得更为困难,而基于质量下降的假定垄断者测试(SSDNQ)尽管能部分解决免费与双边市场等问题,但在评估量化、基准质量标准、下降幅度等方面又难以做出准确判定,仍需技术上的进一步完善。
总体而言,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界定相关市场时应把握好宽窄适度的审慎原则,范围过窄容易漏判,范围过宽则容易错判。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跳出传统思维方式,当一家平台企业的网络效应严重限制自由竞争时,就应依据该平台整体来界定相关市场,在这方面《指南》给出了更为详实的规定。
三、反垄断主要问题:垄断行为判定
我国《反垄断法》对涉嫌垄断的行为做出了三类规定,分别是经营者集中、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些行为在平台经济领域的表现形式与传统经济领域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一)经营者集中
经营者集中是经营者以“主体合并”或“垄断协议”形式做出的一种涉嫌垄断的结构性调整行为。以往的反垄断规制是遵循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SCP)的理论路线,即认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而垄断的市场结构也必然产生垄断的市场行为,从而阻碍市场自由竞争,降低市场效率与社会福利。(9)Weiss L W,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paradigm and antitru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127, no.4 (December 1979), pp.1104—1140.但由于《反垄断法》只针对垄断行为而不针对垄断事实,因此,经营者仅有“集中”而未损害公平竞争便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有些情况下,高市场集中度往往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增加社会福利,市场结构的垄断性与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也会同时并存。由此看来,市场集中与市场竞争之间在平台经济领域有着更为复杂的纠缠关系。
传统的经营者集中主要体现在对申报程序与处罚金额方面的规定,即如未及时申报便处以上限50万元的罚款,腾讯、滴滴都有过类似的集中行为。但同时也规定了经营者集中过程中应有营业额的标准,如果经营者参与集中过程中没有达到营业额的申报标准便不予以申报,于是在平台经济领域越来越普遍地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许多处于初创阶段专注于吸收用户、扩大规模且极具潜质的平台企业并无可观的营业收入,但却成为众多大型科技公司青睐的收购对象,其根本目的是提前终止潜在的竞争对手,(10)Cunningham C, Ederer F, MA S, “Killer acquisi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9, no.3(September 2021), pp.649—702.人们俗称杀手型并购(Killer Acquisition),这一并购形式大大压缩了中小平台企业的生存空间,也大幅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消费福利,(11)陈弘斐、胡东兰、李勇坚:《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与平台企业的杀手并购》,《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这一情况对当前的反垄断规制提出了新的挑战。相关资料显示,苹果、谷歌、微软、脸书、亚马逊等所发起的一些全球市场集中行为均是在与它们类似的平台企业初兴之时进行的。(12)参见瓦姆巴赫、穆勒:《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钟佳睿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应通过主动审查的形式以是否具备限制与排斥竞争效果为标准来判定经营者集中问题,这在《指南》第19条中已经做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不应按照传统的收购方营业额标准而应以收购方收购的价值标准来判定是否需要审查。
(二)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垄断协议一般包括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的横向垄断协议以及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的纵向垄断协议两种规范类型,通常也将其称为排他性协议(Exclusive Dealing)。关于这一行为的社会效应一般存在着两种较为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它可能阻碍有效竞争者进入市场、降低市场效率,(13)参见Chowdhurry S M, Martin S, “Exclusivity and exclusion on platform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0, no.2 (April 2016), pp.95—118.同时也有研究表明这一行为并不必然造成社会福利的下降,反而会增加消费者福利。(14)参见Prieger J E, Hu W, “Application's barrier to entry and exclusive vertical contracts in platforms markets,” Economic inquiry, vol.50, no.2 (June 2012), pp.435—452.但平台经济领域中的垄断协议多数情况下并不单纯以纵向或横向的样态存在,而往往以纵横交错的协议结构形式呈现,这便构成了垄断协议的混合形式,当前这一形式已然成为平台经济领域的常规态势。但这种混合协议由于其纵横组合的松散性而对反垄断法律体系和法律解释与适用并不构成重大挑战。
近年来出现的轴辐(hubspoke)协议因其紧凑的结构、复杂的机制、多重的效果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法律规制难题,《指南》在这方面有所涉及。轴辐协议是指具有竞争关系的平台企业在数字技术促发下所进行的算法合谋行为,从而导致限制自由竞争的后果,如外卖平台以平台为轴心、以商户与骑手为辐条而形成的商品价格机制。平台经济兼具企业与市场的双重属性决定了轴辐协议的出现,即平台经济的市场性在数据与算法的助力下使平台内经营者们能够得以各自签订“轮圈”协议。因此,平台企业的激烈竞争往往遮蔽了对用户密集的数据收集与监测,激烈市场竞争的表象下也往往隐藏着一种对锁定客户群体资源的均衡分配。在此意义上反垄断《指南》对轴辐协议或算法合谋的引入具有较强的战略前瞻性。
四、反垄断核心问题: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
相对于经营者集中、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两类规定而言,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则显得更为复杂。而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首要条件便是市场支配地位的确证问题。市场支配地位一般是指企业在减少产出的同时却能够提高产品价格竞争力并能够增加利润的一种市场力量。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提升价格或改变对其自身有利的合作条件而无需担忧销售额的骤降,或这个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大部分营收具有支配性地位,或对其他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架构具有掌控性,那么这一企业便是一家具有市场力量的企业。当然,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可能会有所不同,在这方面,《指南》提供了更为合理而周全的指引。
(一)以市场份额为认定标准
传统的市场认定方法一般会将市场份额作为其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首要因素,但在平台经济领域这一考虑因素则颇具争议,其关键点是应重新理解“份额”的构成问题,因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份额”不仅包括营业额,更包括数据与用户的额度。用户多、数据广、价值高、体量大等因素都是市场份额认定的关键因素,“用户数量对我们而言何其重要,我们所能展示的广告数量、广告主眼中的广告价值、交易支付的规模费用与资本性支出都与之密切相关。用户数量的趋势变化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收入与财务指标。”(15)拉扎奇、斯图克:《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余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07页。
(二)平台企业控制上下游市场及其关联市场的能力
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平台经营者能够阻止竞争对手获得相关数据信息,抢夺数据与流量,屏蔽外链,定向封禁,以至于数据封锁成为当前平台竞争的突出问题。(16)参见孙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同时也能够以热度封锁的形式使消费者找不到相应App,还能够有意支持第三方应用程序或有意削弱其他应用程序,在这方面,欧盟对谷歌的反垄断监管最具代表性。2016年欧盟指控谷歌凭借安卓系统的市场支配地位,以各种形式强迫一些手机厂商、平板计算机制造商、移动网络运营商推广自己的搜索引擎,从而严重阻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除此之外,还表现出其他平台企业的市场进入壁垒。不同于传统市场的技术与政策壁垒,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锁定效应与反馈效应使其能够持续扩充用户、留住用户。这样用户被平台锁定后便被圈定在特定的产品区域。因此,新的平台企业很难打破固有的市场壁垒,特别是在一些优势平台企业提高用户转换成本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三)用户对平台企业的依赖度
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市场认定将经营者与经营者的依赖度作为考虑因素,但没有考虑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依赖度。数字市场时代还存在着用户对某一平台企业的过度依赖,“大数据杀熟”便是典型。平台企业在不断扩大与培养用户的同时也在不断锁定用户,不断完善用户信息,不断向用户推送信息,使其身处于信息茧房之中却拥有遨游信息海洋的幻觉。因此,用户对企业依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便是看消费者在产品消费时是否存在需求无法替代感与被强迫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独立专业机构的田野调查与用户体验报告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看来,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判定平台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诸如企业依存度、用户依赖度、用户转换成本、网络效应程度、外部选择限度等多重因素。
通常情况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可分为针对用户不公平定价的剥削性滥用与试图排除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排他性滥用,其最为典型的两种表现形式是“二选一”行为与“大数据杀熟”行为,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与个人数据的滥用也是较为常见的两种行为。
1.“二选一”行为
所谓的“二选一”行为是指平台企业通过强迫平台内经营者不得与其他平台企业开展合作的方式排斥竞争对手的行为。这一行为既损害了平台内经营者的利益也损害了消费者以及其他平台经营者的利益,从而扰乱了市场发展秩序,破坏了平台经济的营商环境,阻碍了平台经济创新创业局面的形成与规范发展。近几年来相关的司法诉讼案件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多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对因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平台企业进行调查罚款。不过,2021年4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集团“二选一”的罚款则是依据《指南》中所阐释的诸原则。这是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经济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第一案。其中《指南》第15条对“二选一”行为进行了适时且必要的回应与规定:如果平台企业以限定流量、搜索降权与屏蔽店铺等方式的限制而对他者产生利益损害即视为限定交易行为;同时平台企业以折扣、补贴等各种优惠策略而采取的限制若对公平竞争产生抑制影响,也可判定为限定交易行为。这是基于平台经济发展现状与近年来的相关执法经验而做出的合理规定。同时,也是在《反垄断法》制度框架内来判定平台企业“二选一”行为能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本着“界定相关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分析限定交易行为—判断抑制竞争后果”这一基本程序,具体分析平台企业是否利用交易规则与服务协议抑制经营者参与其他平台企业经营活动,是否抑制市场竞争后果、排挤平台内外经营者与消费者的选择机会以及是否阻碍新生市场的进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对“二选一”行为的法律规制应协调好《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同法律适用。具体而言,应以《反垄断法》分析框架为基础,在适用涉及技术分析手段时应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的相关条款。当然,平台企业可以基于数据安全、知识产权、商业机密、消费者利益以及维护合理经营模式等方面的因素对相关限定交易行为提出合理抗辩。
2.“大数据杀熟”行为
所谓“大数据杀熟”是指平台企业利用大数据算法制定消费者画像,不断完善用户信息,为不同用户提供同一服务的同时收取不同价格,越资深用户反而收取得越高,从而出现同一平台交易中同物不同价的现象,使部分交易相对人失去有利竞争优势。这种现象在一些打车平台、酒店平台、机票平台的交易行为中时有发生,甚至有研究者发现,在打车与点外卖过程中,安卓用户与苹果用户的费用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的歧视待遇行为。这种歧视性待遇尤以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最为典型,即对不同客户提供与成本无关的歧视性定价。这在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第19条、《电子商务法》第18条、《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第15条中都有明确规定。判定“大数据杀熟”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行为应具体分析其违法构成要件。具体而言,其一,该平台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其二,该平台企业是否实施了歧视待遇行为;其三,该平台企业是否以非正当理由限制或消除了竞争。《指南》的颁布与实施为判定“大数据杀熟”是否构成垄断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规制依据与分析方法,第17条明确了歧视性待遇行为的构成要素,认为根据消费者的个体偏好、消费习惯、支付能力、交易历史、隐私信息等因素的不同而采取差异性交易价格都应视为差别待遇行为。
当然,企业平台基于差别待遇行为的正当理由,如针对尊重实际需求在遵守行业惯例与交易习惯的条件下对新用户的合理优惠以及无歧视性规则的随机交易可以进行依法抗辩。因为用户的平等立场并不等同于用户的平均立场,平台经济领域允许存在个性化定价的情形,有些不同价行为并不能看作就是差别待遇行为,反而具有合理性。(17)参见梁正、曾雄:《“大数据杀熟”的政策应对:行为定性、监管困境与治理出路》,《科技与法律》2021年第2期。这里需特别注意的是应准确把握以价格歧视为代表的各种差别待遇行为的违法构成要件。通常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可以根据同一产品的市场与用途差异而实施相应的价格差异。因此,产品用途的差异性便能够作为不同交易差异性的一个重要依据,从而使平台企业依据不同的市场条件采取相应的定价行为。由此看来,合理的价格差异与违法的价格歧视之间的界限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便需要准确把握价格歧视行为的违法构成要件。一般而言,应包括行为人支配地位、价格歧视行为确证、价格歧视的不合理性与竞争损害性四个要件。这样我们便不能将一些价格差异行为,如成本差异、交易数量差异、条件变化、适应竞争等误判为价格歧视。同时,也应充分意识到“大数据杀熟”行为中获取证据与认定证据的困难程度。技术发展带来相关行为的隐蔽性与多变量性,以及消费者对平台企业算法机制与定价规则的陌生性,大大增加了判定平台是否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困难性,这便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技术分析与相关法院对平台企业更多举证责任的规制,以及相关专业团队的通力合作。
3.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
这一行为是指一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为了取得优势地位,便会以远远低于产品价值的消费福利形式倾销商品,以此排斥其他竞争者,但当经营者在市场上取得优势地位后便立即出现价格上涨与垄断,从而损害用户的相关权益。(18)参见Armstrong M, Wright J, “Two-sided markets, competitive bottlenecks and exclusive contracts,” Economic theory, vol.32, no.2 (June 2007), pp.353—380.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平台经济的非对称定价特性决定了存在低于成本定价或免费定价的普遍现象,而这并不完全是出于垄断的动机,因此也并不必然就是掠夺性定价。事实上,只有在单边市场反垄断思维模式下,这一低于成本定价的行为才被视为掠夺性定价;而在双边或多边市场中,平台企业的定价策略根本无法反映它的成本结构,自然也就不能将其归属于掠夺性定价的范畴。故此,相关反垄断执法机构不能轻率地以低于成本定价行为作为直接证据将平台企业认定为实施垄断价格的行为。(19)参见Wright J, “One-sided logic in two-sided markets,” 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 vol.3, no.1 (January 2004), pp.44—64.“对反垄断执业者来说,困难在于那些源于标准市场的传统智慧不再有效:不能再孤立地研究市场的一端,因为其定价非常依赖于市场此端新增一名成员给市场彼端成员所带来的收益。甚至一些没有市场力量的小平台也会展示出非常倾斜的定价模式:对市场一端制定低价(通常是零利润),而对市场其他端则制定很高的价格。反垄断当局不能轻率做出决定,认为这种定价就是实施掠夺和垄断价格的直接证据。”(20)让·梯若尔:《创新、竞争与平台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论文集》,寇宗来、张艳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202页。
4.个人数据的滥用
在平台经济领域还存在着以“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形式出现的服务协议问题,可能因其数据保护问题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嫌疑。由于数字经济时代个人数据的货币性特征,平台企业可能会过度收集用户信息,而用户数据收集与处理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免责性一定程度上便来自于隐私政策与用户协议。在这方面,2015年比利时竞争管理局对该国国家彩票局的罚款、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2016 年对脸书的法律诉讼具有典型意义。(21)参见摩尔、坦比尼:《巨头:失控的互联网企业》,魏瑞莉、倪金丹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4—65页。这种情况下,在平台经济领域以《数据保护法》还是以《反垄断法》来判定一家平台企业的剥削性行为则是一个值得审慎处理的问题。另外,占支配地位的平台企业在利用数据方面还可能存在几种值得注意的反竞争行为,主要包括排他性合同以限制竞争者收集数据、交叉使用此市场数据以进入彼市场、拒绝竞争对手访问数据以为己服务。
五、反垄断补救问题:免责事由判定
在相关市场界定与涉嫌垄断行为认定后,市场监管机构并不必然会对平台企业发起《反垄断法》的制裁。因为平台企业还具有一些相应的免责事由,这便涉及到反垄断分析的最后一个步骤:正负效果对比分析,即只有行为负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时才能最终被判定为垄断行为。一般而言,企业经营必要、整体效率需求与公共利益考量都可以作为具体的裁量性免责事由。这是一种具有普遍特征的法律规制原则,这在欧盟的豁免制度、美国的霍温坎普路线图以及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第17条关于具体行为豁免与前置性规定中都有体现。
(一)企业经营必要
由于生产要素方面对数据与算法的根本依赖性特征,平台企业初兴、发展与创新的每一个步骤都建立在掌握充足数据的基础上。在此意义上来说,数据是平台企业的生命线。因此,相关监管机构在判定企业短期市场支配地位甚或短期涉嫌垄断行为时应本着适时适度的审慎原则,充分考虑数字市场特性与企业经营所需,而一些为吸引用户合理期限内的补贴行为、为保护知识产权或维护合理经营模式的特定资源投入都应视为企业经营所必需。就此而言,反垄断规制的时机显得尤为重要,“平衡反竞争行为危害与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福利改善之间的关系实非易事”。(22)拉扎奇、斯图克:《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余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91页。
(二)行业整体效率提高
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规定了与行业整体效率提高相关的垄断协议免责事由,包括技术的改进与新产品的研发、产品质量的提升与成本的降低以及中小企业效率的提高。互联网时代,平台经济将市场交易效率提高至极致,平台经营者之间的数据共享、纵向协议、默认勾选、算法共谋在某种程度上都以提高效率为目的,如购物平台以提高运输与退换效率为目的的默认快递选择、手机生产商与经销商以提高售后效率为目的的纵向协议均可视为正常的提高行业整体效率行为。
(三)消费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
我国《反垄断法》的终极目的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与消费者个人利益。如果一些平台企业出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如救灾、治安、防疫等活动而进行的收集、利用用户数据的行为则应视为企业的正当性行为;平台企业涉及消费者个人利益,如用户数据隐私保护或直观用户福利的行为,都可视为涉嫌垄断行为免责的确证。由于消费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往往存在交叉与重合的现象,我们更应从用户个人利益出发判定垄断行为的正负效应,因为消费者个人利益便是市场经济领域中的人民利益。而消费者个人利益的界定在平台经济领域表现为价格利益与数据及隐私利益,毕竟对数据的垄断是平台经济最主要的垄断形式之一。(23)孙益武:《论平台经济反垄断执法中的数据因素》,《法治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5—126页。当然,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追求效率,平台企业的发展目标亦是如此,效率的提高也理应受惠于消费者,从而指向消费福利,指向作为消费者利益直接反映的价格,因此,我们应注意平台经济垄断规制的审慎与宽容,特别注意平台经济效率提高情况下,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两头通吃现象,如以外卖、打车为代表的一些平台企业在效率大大提高的情况下仍未能增加用户福利,而是损害用户利益的行为。
综合以上论述,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规制应在遵循《反垄断法》一般思路的前提下,结合互联网技术与平台企业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实现维护竞争与激励创新的平衡,秉持包容审慎的原则,为平台企业提供充裕的创新机会和必要的试错空间,促进平台经济有序规范发展。这里的“包容审慎”并非放纵违法而是有所作为,即当平台企业违法行为表现出严重危害性时,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够及时执法,精准执法,体现反垄断执法的实践智慧。这在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中有明确规定:“健全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不得简单化予以禁止或者不予监管。”(2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2021年1月31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1/31/content_5583936.htm,2021年12月25日。这在《指南》第3条中也有明确规定。反垄断规制的过度或过早干预都可能造成对平台企业发展生态的破坏,从而削弱、阻碍平台经济的创新能力与长远发展。专业执法机构应利用科学分析方法,注重对个别案例竞争损害与行为效率的分析,适时摒弃以市场结构与市场份额为根据判断垄断与否的传统分析观念,提升反垄断执法专业性,(25)参见唐要家:《数字平台反垄断的基本导向与体系创新》,《经济学家》2021年第5期,第83—92页。为平台企业提供更多自我调节、自我规制与自我完善的合法空间,促进平台经济长远发展,提升平台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鉴于平台经济的结构特征与反垄断规制的复杂性,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任意夸大,需要专业的分析与法律的审慎,从而达到强化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目的。同时,更应该辩证地认识到,对一些平台企业的反垄断调查并不是国家改变了对平台经济的支持态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引导、规范其健康发展。
六、结 论
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对平台企业的反垄断监管愈加常态化,执法力度也愈加严厉化。对超级平台与数字霸权的反垄断规制是全球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互联网将从上半场对效率的追求,转到对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的追求上来。”(26)涂子沛:《数文明:大数据如何重塑人类文明、商业形态和个人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75页。因此,我国应在借鉴其他国家反垄断执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市场竞争与反垄断法制的特殊性,对平台经济反垄断的一些基本原则与具体方法做出相应的理论革新与实践调整。这些革新与调整包括:创新反垄断监管工具,充分运用经济学分析手段,增强反垄断规制的科学性与适应性;降低界定相关市场的重要性以及高市场集中度的严重性,侧重可竞争性指标;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鼓励技术创新,增强我国数字平台国际竞争力。事实上,我们在解决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问题上拥有更大的优势,因为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指南》的颁布实施,也大大促进了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