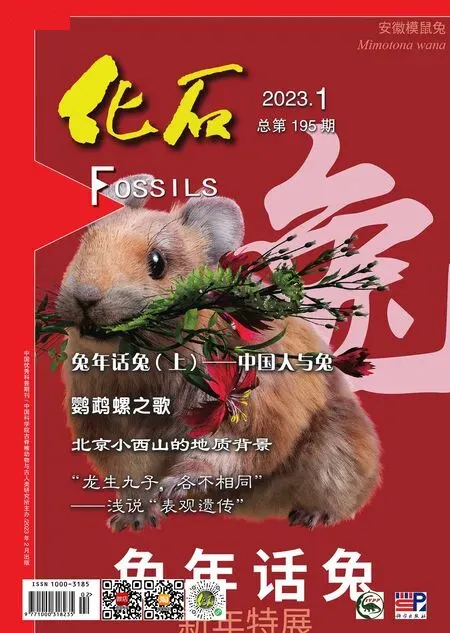记“古神经学”创始人、著名犹太女科学家蒂莉·埃丁格博士
于小波

“古神经学”创始人、著名犹太女科学家蒂莉·埃丁格博士。照片摄于1948年。美国哈佛大学恩斯特·迈尔图书馆和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档案部提供照片并授权使用
蒂莉·埃丁格(Tilly Edinger,1897-1967)博士是20世纪的著名犹太女科学家,被誉为是“古神经学”的创始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德国,埃丁格是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少数女性之一。在埃丁格之前,人们对脊椎动物脑演化的认识,几乎完全依赖解剖学家对现生动物脑结构的比较研究。埃丁格基于自己的古生物学和神经学背景,将分类学、地层年代和功能研究结为一体,单枪匹马地创建了“古神经学”这一新领域。古神经学研究化石动物的脑结构,把演化的时间概念纳入神经学的研究之中,探索神经系统在不同动物类群中的演化历史。
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权对犹太人进行的大迫害使埃丁格的生活和工作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1939年,埃丁格被迫终止了在德国充满创意的研究,逃离故乡,前往伦敦。1940年,埃丁格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埃丁格一生发表过100多篇研究文章和专业评述文章,而她发表的科普、会讯、译文等各类文章的总和则达到一千多篇。1963年,埃丁格成为美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的首任女主席。
作为备受尊敬的古生物学家,埃丁格分别于1950年、1957年和1964年获得美国卫斯理学院、德国吉森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全名为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作为一个长期受听障困扰的女性犹太科学家,埃丁格以顽强的意志冲破时代的限制,在逆境中取得成功。这使埃丁格一生的故事,在个人层面上更加具有动人心弦的震撼力。
家庭与早期教育
1897年,蒂莉·埃丁格出生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的一个富足的犹太家庭。蒂莉的父母属于法兰克福的学术和文化精英阶层。父亲路德维希·埃丁格(Ludwig Edinger,1855-1918)是著名的解剖学家和神经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创始人之一。路德维希·埃丁格是第一个描述脊髓-小脑前束和后束并区分出旧脑和新脑的学者。1885年,路德维希·埃丁格首次描述了动眼神经(第三对脑神经)的一个副交感神经节。这个名为“埃丁格-韦斯特法尔核”的神经节,具有缩小瞳孔、协调眼球会聚的作用。1914年,法兰克福大学成立时,路德维希·埃丁格成为德国第一个神经学的讲席教授。蒂莉·埃丁格的父亲不仅是成功的科学家,还是出色的教师、艺术家和知名的催眠术专家。1918年,路德维希·埃丁格因手术造成心脏血栓而突然去世。路德维希·埃丁格在法兰克福大学积累的现生脑标本,为女儿日后从事“古神经学”研究提供了比较材料。
蒂莉·埃丁格的母亲安娜(1863-1929,母姓为戈尔德施密特)是法兰克福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她热衷从事各种促进青少年福利、妇女教育、妇女参政权等社会活动。蒂莉·埃丁格是路德维希和安娜最小的女儿,她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名叫弗里茨)和一个姐姐(名叫多拉)。依照当时法兰克福富有家庭的习惯做法,蒂莉·埃丁格跟着会说英文和法文的家庭教师,在家里完成了早期教育。这使她很早就对英文、法文等多种语言产生终身的兴趣。随后,蒂莉在12岁时进入法兰克福唯一为女孩开办的一所中学。蒂莉的家是法兰克福艺术家和科学家云集的社交场所。这种环境让蒂莉接触了很多著名的知识精英。而蒂莉父亲自己的学术造诣也为她树立了倾心科学研究的典范。

蒂莉·埃丁格的父亲是著名的德国解剖学家和神经学家路德维希·埃丁格。肖像中的路德维希·埃丁格正在研究人脑标本,背后的架子上摆满各种脑切片标本。肖像由著名的德国艺术家柯林特绘制。肖像的照片属公有领域
“古神经学”的诞生
蒂莉·埃丁格在中学后继续追求自己的兴趣,在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上各种科学课程。1919年夏天,蒂莉在波罗的海度假时,读了奥地利古生物学家阿贝尔(Othenio Abel,1875-1946)所著的《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基础》,对古生物学产生了兴趣。1920年,蒂莉·埃丁格在法兰克福大学开始博士论文研究。埃丁格的导师德雷弗曼(Fritz Drevermann,1875-1932)是一位古脊椎动物学家,同时也是森根堡自然博物馆(Naturmuseum Senckenberg)的主管。私立的森根堡自然博物馆是当今德国第二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有两千多万件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动植物、古生物和矿物标本。

1926年,蒂莉·埃丁格博士在森根堡自然博物馆内测量脑化石内模。美国哈佛大学恩斯特·迈尔图书馆和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档案部提供照片并授权使用
埃丁格的论文研究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幻龙(Nothosaurus)的颚部构造。幻龙是一种已经绝灭的鳍龙类动物,头部细长,靠尖锐的牙齿在2亿多年前的浅海中捕食鱼类。埃丁格看到一个幻龙的头骨内保存了自然形成的脑内模。在脊椎动物化石的形成过程中,脑部等软组织无法保存。但是,有时脊椎动物的脑腔中会有泥沙或其他充填物进入,经过石化形成一个反映脑腔内容的“石核”。这种自然形成的脑腔内模(以及用石膏、树脂等制成的人工内模)可以用来研究动物脑表面的构造。埃丁格用现生短吻鳄脑腔的人工内模作比较,探讨了幻龙脑部的构造。1921年,埃丁格以最优秀的成绩获得法兰克福大学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她的论文部分发表在《森根堡博物馆馆刊》上,奠定了“古神经学”的第一块基石。
蒂莉·埃丁格的家庭财富,使她在经济上不必为生计担忧。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女性从事古生物学研究,而她们的工作往往不带薪水或只有极低的薪水。埃丁格于1921年从法兰克福大学博士毕业后,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地质研究所和森根堡自然博物馆做无薪工作。她工作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兴趣。当时,除了埃丁格的导师德雷弗曼外,法兰克福没有其他的古脊椎动物学家。埃丁格以通信的方式和欧洲主要的古生物学家建立联系,其中包括柏林的申德沃尔夫(Otto Schindewolf,1896-1971)、图宾根的许耐(Friedrich von Huene,1875-1969)和布鲁塞尔的多洛(Louis Dollo,1857-1931)。埃丁格早期的研究基本是描述性的,而她的工作主要受到多洛和许耐的影响。
在1920年代,埃丁格发表过有关幻龙、始祖鸟和蝙蝠的脑构造文章。她收集整理了早期文献中各种脑化石内模的记载,同时用橡胶或石膏从博物馆的标本制作人工的脑内模,用于重建化石动物的脑构造。1926年,埃丁格到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研究各地的脑化石材料并建立起更为广泛的国际联系。1927年,埃丁格成为森根堡博物馆的荣誉馆员(仍然是无薪职位),负责脊椎动物化石的馆藏管理。埃丁格花了大量时间在森根堡博物馆整理凌乱的脊椎动物化石。她还通过标本交换获得世界各地的化石材料,其中包括马什(Othniel Marsh,1831-1899)在19世纪晚期描述过的哺乳动物脑内模。马什是美国早期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曾发现过翼龙、恐龙、早期马类、带齿的早期鸟类等众多化石材料。马什曾根据中生代和新生代的脊椎动物脑内模,提出过“脑演化定律”,认为不同化石类群的脑体积在地质时期有逐渐增大的普遍趋势。
埃丁格从地层和比较解剖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比较和总结了欧洲和北美脑化石的庞大材料。1929年,埃丁格用德文发表了《脑化石》一书。埃丁格在书中,查阅、参考了280篇提及化石脊椎动物脑部和脊髓构造的文章,首次把零散的信息归纳成章,并按地层年代和比较解剖的标准对脑化石材料予以分类,试图从中推导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脑化石》一书概述了古神经学的研究方法及有待解决的问题,确立了埃丁格在德国和国际古生物学界的地位。
被迫逃离德国流亡英美
在1930年代早期,埃丁格发表了关于海牛脑部构造的三篇文章,试图重建海牛这个次生性海生哺乳动物类群的脑演化历史。海牛的祖先曾经在陆地上生活。在从陆地进入海洋的历史过程中,海牛的后肢退化、尾巴变成扁平的尾鳍。埃丁格还发表过关于哺乳动物顶骨孔等文章。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纳粹政权通过法令禁止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在政府机构任职。由于森根堡博物馆是私立机构,而且埃丁格的工作并不带薪酬,埃丁格在博物馆的工作暂时受到一定的保护,使她成为能在德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少数犹太人之一。但这并不能让埃丁格免于随时可能遭受迫害的恐惧。由于遗传性的内耳疾病,埃丁格的听力从10来岁起便逐渐减弱。她在听学术报告时,经常要坐在听众席的第一排才能听清报告的内容。1933年,纳粹政权还通过法令,要对有遗传疾病的人实施强制绝育。埃丁格的犹太身份和遗传性听障,使她陷于双重迫害的危险之中。埃丁格在此期间不得不保持低调,以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她平时到博物馆上下班只从侧门进出。她把自己办公室的名牌摘掉。她不再参加公开的学术报告会。在遇有外人到访博物馆时,她更加小心地避免引起外人的注意。
在1930年代,埃丁格的父母都已离世,而她的姐姐多拉已于1934年移居美国。但是,埃丁格一直试图推延做出离开德国的决定。埃丁格曾对朋友说:“只要他们不骚扰我,我就会留在法兰克福。这里是我的家,我母亲的家族从1560年就始终在这里生活。我向你保证,他们(指纳粹)永远不会把我弄到集中营——我随身带着剂量足以致命的佛罗拉(安眠药)。”埃丁格以死明志的决心,绝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埃丁格的亲生哥哥弗里茨即于1942年在纳粹的集中营中丧生。
埃丁格的处境随着时间而不断恶化。纳粹从法兰克福市一个公园中移除了埃丁格母亲的塑像,还拆除了埃丁格家所在街道的“埃丁格街”路牌。1937年,慕尼黑的古生物学家布罗里(Ferdinand Broili,1874-1946)来信通知埃丁格,说她为《矿物、地质和古生物学年刊》审稿的资格遭到撤销。此时,埃丁格意识到她已经失去在德国继续研究的学术环境。
1937年7月,埃丁格让她在波士顿的朋友向美国古生物学家罗美尔(Alfred Romer,1894-1973)教授探询来哈佛大学学习或研究的可能性。1938年8月,埃丁格向美国领事馆申请前来美国。罗美尔为埃丁格提供了担保证词,保证埃丁格前来美国将受到欢迎并得到研究职位。古生物学家辛普森(George Simpson,1902-1984)也给美国领事馆写信,支持埃丁格来美。辛普森写道:“埃丁格是世界各地公认的一流科学家。她在研究化石动物脑结构和神经系统、在研究脑结构演化方面是公认的学科领头人。她开创了古神经学这个新的科学领域,其研究具有显见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1938年11月9日和10日,在纳粹的怂恿下,德国各地发生了被称为“碎玻璃之夜”的暴力事件。犹太人的教堂、商家和其他机构惨遭破坏,一夜间变成断瓦残垣,满目疮痍。许多犹太人的窗户被打破,散落的玻璃碎片摊在地上,在月光下闪烁发光。当夜,有近一百名犹太人被杀害,几千人被拘禁。随后,犹太人被禁止进入电影院、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所。11月11日,埃丁格被禁止进入森根堡博物馆或其他公共建筑。埃丁格在办公室的物品被清除出去,法兰克福大学还命令她归还所有先前用于研究的图书。埃丁格在德国的研究生涯戛然而止。
由于埃丁格申请美国签证需要排队到1940年,英国的科学家救助团体在古生物学家沃森(D.M.S. Watson, 1886-1973)的帮助下,为埃丁格申请到前往英国的暂时签证。埃丁格还得到布罗里、里希特(Rudolf Richter,1881-1957)等古生物学家的证明信,说明埃丁格在欧洲古生物学界的崇高威望。1939年5月,埃丁格抛弃了家庭的大多财产,只带着手提行李,逃离法兰克福前往伦敦。
在伦敦,埃丁格挂靠在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名下,依靠翻译医学文献的收入度日,并继续进行古神经学的研究项目。1939年,埃丁格发表文章,根据海牛的脊髓构造推断在海牛演化中后肢开始缩小的历史时期。1940年,埃丁格发表了“中国蓬蒂期麝牛的脑构造”一文。这篇文章的工作主要是埃丁格在英国时完成的。她通过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Birger Bohlin,1898-1990)的安排,从乌普萨拉大学的中国化石中制作了柴达木兽(Tsaidamotherium)、近旋角羊(Plesiaddax)、乌米兽(Urmiatherium)和麝牛(Ovibos)的脑内模,予以描述和讨论。
新环境下的古神经学研究
1940年初,埃丁格等候美国签证的排期被意外提前。她乘坐“英国号”邮轮,经历危险的跨大西洋航程,于1940年5月抵达纽约,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罗美尔的帮助下,埃丁格得到哈佛大学“古生物学客座研究人员”的位置。她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编纂《北美以外的脊椎动物化石文献目录》一书。这本庞大的目录由罗美尔、内尔达·怀特(Nelda Wright,1901-1992)、埃丁格等四人一起工作了近20年,直到1962年才得以出版。埃丁格对细节疏漏无疑的专注和她对各种欧洲语言的熟悉,在目录编辑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埃丁格还继续翻译医学文献,并在卫斯理学院讲授比较解剖学。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古神经学的研究。1941年,埃丁格发表了关于翼手龙脑部的文章。翼手类是比较进步的翼龙,具有比较发达的脑部构造。埃丁格根据喙嘴龙(Rhamphorhynchus)具有增大的视叶和小脑,推测翼手龙以视觉为主并具有飞行能力。1942年,埃丁格发表了对大型脊椎动物脑垂体的研究。她还和罗美尔共同发表了关于化石两栖类脑内模的文章。1945年,埃丁格成为美国公民。
在哈佛大学,埃丁格体验到比森根堡博物馆更为轻松、融洽的气氛。在森根堡博物馆时,埃丁格在学术上是相对孤立的,因为周围的同事大多是地质学家。到了哈佛大学后,埃丁格的周围是一批朝气蓬勃、在生物学训练有素的古脊椎动物学家。她被罗美尔团队意气风发的精神和待人随和的作风所深深感动。她和同事们彼此相处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当她和许多著名古生物学家围桌而坐时,大家彼此直呼名字、谈笑风生。这在德国学术界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埃丁格感到,自己像是又回到在法兰克福埃丁格大家族成员之间轻松聚会的昔日情景。
同时,埃丁格身边的美国学者对进化机制的理解也和德国的传统截然不同,使她在学术上也走进一个新的环境。在德国,古生物学被认为是地质学的附属学科,缺乏明确的理论框架。在美国,埃丁格身边有像迈尔(Ernst Mayr,1904-2005)和辛普森那样注重理论的古脊椎动物学家,他们当时正热衷于发展“综合进化学说”的新思想。这些影响在埃丁格后来的工作中得以表现,让她更注重强调在相同支系的类群中比较化石动物的脑体积,也让她对马什提出的“脑演化定律”等传统说法不断提出批评。
在美国的第一个十年间,埃丁格最主要的研究项目是描述和分析马脑的演化。1948年,埃丁格出版了《马脑的演化》这部专著。她研究了从三趾马到现代马不同支系中脑体积和表面沟回的细微变化,提出脑的增大以及脑沟回的相同模式在哺乳动物不同目中是独立起源的。埃丁格关于马脑演化的专著,纳入很多解释性的讨论,为哺乳动物类群的分支式发展提供了的证据,把古神经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1951年,埃丁格发表了“齿颌鸟类之脑”一文。齿颌鸟类是白垩纪的化石鸟类,口内尚有牙齿。埃丁格对马什认为齿颌鸟类的脑部像爬行类的说法提出异议。她检视了马什绘制的齿颌鸟头部碎片,认为齿颌鸟具有比较宽阔的小脑和较小的嗅叶,脑的构造实际上更像鸟类。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埃丁格研究鲸类脑部在地质历史时期的变化,发现鲸类脑腔中嗅叶的印痕随着时间而变小,可以推断鲸类的嗅觉在演化中不断退化。

1951年,埃丁格和罗美尔等人在得克萨斯州野外工作时合影。从左到右为斯坦利·奥尔森(Stanley Olsen,1919-2003)、罗美尔、内尔达·怀特、埃丁格。照片由巴克霍尔兹(Buchholtz)教授提供,已故古生物学家唐纳德·贝尔德(Donald Baird,1926-2011)之子安迪·贝尔德授权使用
埃丁格研究的很多脑化石情况与马什提出的“脑演化定律”相抵触。1958年,埃丁格以海牛和蝙蝠这两个类群为例,指出脑部的“进步性演化”与类群存活的几率并非相关。1960年,她发表“古神经学中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概念”一文,再次批评马什认为哺乳动物进化的特点之一是脑量增大这种观点。埃丁格说,自己查看过数以千计的脑化石,因此指出马什错误的历史责任自然落到她的头上。埃丁格对马什的各种批评,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
1999年和2001年,卫斯理学院的古生物学家巴克霍尔兹(E. Buchholtz)教授和法兰克福大学的神经学家赛法特(E-A.Seyfarth)教授发表了有关埃丁格生平的两篇文章。他们把埃丁格的科学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德国的描述性工作阶段,第二阶段是1940年代和1950年代在美国的解释性工作阶段,第三阶段是1960年代在美国的行政性科学组织工作阶段。
在1960年代,埃丁格作为美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的主席更多地投入行政和科学组织工作。早在1940年12月,埃丁格在到达美国后不久,就参加了美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的成立大会并在学会章程上签字。埃丁格是当时与会的唯一一位女科学家。多年来,埃丁格积极参加学会的年会活动,并作为学会《新闻简报》的外事编辑,经常为《新闻简报》撰稿。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埃丁格参加学会的外国会员委员会工作,评估非美国科学家要求加入学会的申请资格。1963年,埃丁格当选古脊椎动物学会主席,成为学会历史上的第一任女主席。
1964年,埃丁格正式从哈佛大学退休,但她的研究并未停止。1966年,埃丁格完成了骆驼脑部的研究,探讨了四千万年以来骆驼脑部的演化历史。在埃丁格职业生涯的最后十年中,她积极准备编纂《古神经学注释文献目录》的工作,以便对古神经学的历史和发展现状进行全面的总结。不幸的是,埃丁格的庞大计划被一场交通意外所中断。1967年5月26日,埃丁格在哈佛大学校园内被卡车撞倒,头部重伤,次日在医院去世,时年69岁。1975年,哈佛大学的古哺乳类学家帕特森(Bryan Patterson,1909-1979)等人完成了埃丁格的最后一本书《古神经学注释文献目录》,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

1927年春,杨钟健(前排右一)曾和留德的中国同学一起到埃丁格工作的森根堡自然博物馆参观。照片由任葆薏女士提供并授权使用
在埃丁格早年拼搏的森根堡博物馆附近,有一个小的街心广场,当今被命名为“埃丁格广场”。广场的牌子上写着蒂莉·埃丁格的名字和“古神经学创始人”的字样。法兰克福这个她曾在痛苦中逃离的城市,如今用这种形式向自己的杰出女科学家表达永久的敬意。
和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创始人杨钟健院士的长期交往
埃丁格生前和世界各地的同事和朋友们保持广泛的通信联系。她遗留的大量通信,让人们得以了解她的一生、她的思想以及她和各地同事、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些通信,更让人们了解到埃丁格心中的执着、热情和有时像是孩童般的天真。埃丁格凭着坚强的个性、对科学的挚爱、以及非凡的聪颖和勤奋,赢得同事和朋友们的普遍爱戴与尊敬。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创始人杨钟健(1897-1979)院士早在德国留学时就认识了埃丁格。1927年春,杨钟健曾和留德的中国同学一起到埃丁格工作的森根堡自然博物馆参观。后来,他又在同年的秋天到森根堡博物馆,用四天的时间学习化石修理技术。1944年秋和1945年夏,杨钟健在欧美考察期间,两次到哈佛大学访问,并会见罗美尔。杨钟健在罗美尔处见到相识多年的老友埃丁格,两人谈起在德国的往事,都不胜感慨。埃丁格在给杨钟健的信件中,除了和工作相关的内容外,时常像老朋友聊天一样,提到各种话题。埃丁格和杨钟健通信时,双方还偶尔在英文中掺加上个别的德文词,勾起昔日的共同记忆。
1947年5月,杨钟健在结束欧美考察返国后,埃丁格写信给杨钟健,邀请他作为古脊椎动物学会的亚洲联络员为学会的《新闻简报》撰稿,报告亚洲古脊椎动物学的进展。1947年9月,埃丁格来信感谢杨钟健为学会所写的报道。在信中,埃丁格告诉杨钟健,她收到申德沃尔夫从德国寄来的战后第一份报道,说那里的情况“令人心碎”。埃丁格还说,申德沃尔夫打算离开柏林大学到图宾根,因为只有图宾根那里的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得以在战火中幸存。
1957年,杨钟健发表了山西榆社三叠纪的新前棱蜥(Neoprocolophon)一文,这是杯龙类化石在中国的首次发现。1958年10月,埃丁格来信,对看到杨钟健发表的新前棱晰一文感到欣慰。埃丁格特别称赞杨钟健在描述中给出了新前棱蜥顶骨孔的大小,使埃丁格从前根据前棱蜥(Procolophon)顶骨孔数据得出的推断得以证实。
1958年和1959年,杨钟健发表了贵州和广西幻龙新材料的两篇文章。1959年11月,埃丁格来信说,“我的论文和一些早期著作都是关于幻龙的,因此我特别高兴看到幻龙在贵国亦有发现。”埃丁格告诉杨钟健几天前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庆祝建馆100周年的活动情况。她还讲述了自己在1955年和罗美尔夫妇一道访问森根堡博物馆时的一件趣事。当时,罗美尔在博物馆内发现了埃丁格研究过的幻龙标本,兴奋地向夫人喊道:“露丝,快来看!这是蒂莉最钟爱的动物!”埃丁格说,她看到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发现了自己“最钟爱的动物”,让她感到非常开心。
埃丁格一生充满活力、坚守信念,有时达到固执、任性的程度。她的工作,在技术手段和理论上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埃丁格的听力,不太容易通过助听器得以改善。因此,她在谈话中时常关掉助听器。在和同事交流时,埃丁格往往偏于自说自话,让谈话的对方不便随时打断她的思路,难于进行“礼尚往来”的思想交锋。由于缺少学术交流中思想火花的即时碰撞,埃丁格在口头和书面表述观点时渐渐形成了固于己见的习惯。例如,埃丁格曾和同事书面探讨脑体积与身体大小的相关性,但她不愿听从同事的建议,拒绝使用对数曲线表述脑体积与身体大小的关系。这无疑让埃丁格的工作停留在直觉的定量分析水平上。
在埃丁格创建古神经学一百年后的今天,她当年研究脑化石的技术已经被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所超越。如今,古生物学家可以通过高精度CT断层扫描和数字化重建技术研究化石,揭示化石脑颅内部的详细结构,让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埃丁格创建“古神经学”的历史功绩值得后人永世铭记。她在逆境中表现出的惊人勇气、执着和敬业精神,更是值得后人效仿的光辉范例。

1959年11月,埃丁格写信给杨钟健,对中国发现幻龙新材料表示欣喜。她还讲述了1955年和罗美尔夫妇参观森根堡博物馆时的一件趣事。照片由任葆薏女士提供并授权使用
注一:笔者为美国新泽西州肯恩大学(Kean University)生物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注二:杨钟健院士的儿媳任葆薏女士为本文提供2张照片(P50、P51插图)并阅读文稿。美国哈佛大学恩斯特·迈尔图书馆和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档案部罗伯特·扬(Robert Young)提供2张照片(P44、P46插图)。卫斯理学院艾米利·巴克霍尔兹(Emily Buchholtz)教授提供P49插图的照片及宝贵信息。已故古生物学家唐纳德·贝尔德(Donald Baird)之子安迪·贝尔德(Andy Baird)授权使用P49插图照片。法兰克福大学格拉尔德·克雷夫特(Gerald Kreft)教授、森根堡自然博物馆迪特尔·乌尔(Dieter Uhl)教授、法兰克福城市史研究所莫妮卡·劳里亚(Monika Lauria)、耶鲁大学皮博迪博物馆丹尼尔·布林克曼(Daniel Brinkman)等协助查询资料并提供有益信息。笔者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