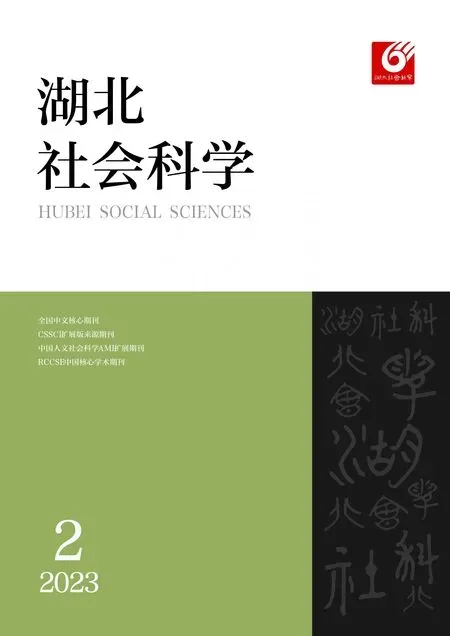论海德格尔的“视”概念
王 燕
海德格尔是西方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呈现多层主题叠加态势,对后世思想有多方面的贡献,如现象学、存在主义、诠释学、解构主义、政治理论以及心理治疗理论和神学等。海德格尔思想的独特性在于重提“存在”问题,并在其一系列著作影响下促使“存在问题”成为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的核心主题。存在而非存在者,存在亦即虚无。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解答无疑使西方哲学美学思想有了一个重大转向,特别对基础存在论的讨论,把能死者、诸神、大地与天穹聚集于一个世界的“互属”中。打破了自柏拉图开其先河,笛卡尔建立与发展,到黑格尔使其达到完善顶峰的西方主客二分式旧形而上学。旧的形而上学属概念哲学,要求说出事物是“什么”(what),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意图显示事物“怎样”“如何”(how)是其所是。“什么”——“这种传统的存在论也被叫作‘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如:柏拉图的形式观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基督教信仰的创世者、笛卡尔的广延之物和思维之物、康德的本体等。”[1](p4)“怎样”——从生存论意义上揭示出当前在场事物背后的不在场的整体关联,关联的具体内容为“何所因”“何所用”“何所去”“何所及”之间的意蕴关系。
传统存在论回答“什么”,与事物是“面对面”的对立关系,海德格尔现象学在事物之中“看”事物,与事物是“在之中”的交互关系。海德格尔“现象学”方法有赖于其独特的“视”见,不同于传统存在论如“静物”般看事物,海德格尔的“视”是“动视”。在其著作中,多处提及“视”以及通过“视”觉活动而引发的现象学思考,甚至于认为,“此在乃是在生存论上随着此的展开一道存在着的视。”[2](p171)海德格尔“视”的语言家族中主要有:对周围世界的寻视(另译为概观、统观),对其他此在的顾视或惜视,对自身洞察的透视,以及对存在之真理的观入等,不同含义的多重视域构成了海德格尔思想的深邃复杂性,共同揭示出人生在世的本真样态。
一、海德格尔对西方传统哲学中“视”的解构
海德格尔规定“视”在存在者与其本身无所掩蔽的照面时可以用于生存论含义,并认为虽然其他的感官也都在其功能领域中通达存在者和存在,但是,“哲学的传统一开始就把‘看’定为通达存在者和通达存在的首要方式”。[2](p171)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哲学以“视”这种感知方式为普遍性的通达基础。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向阿得曼托斯指出真正的哲学家,无暇顾及日常事物,而永远“关注和沉思(lookupon and contemplate)有秩序的,永恒的事物”。所谓永恒的事物即是柏拉图的“理念”“相”(idea或eidos),其词源都来自希腊语的动词:eido,看,名词指“被看到的东西”,“在看中被展示出来的东西”和“显相”。柏拉图的看不是肉眼感官看具体的事物,而是用心灵和理智看具体事物的一般定义和普遍本质,即具有统一性和实在性的普遍概念、形式和共相等。亚里士多德的通达方式是“理智灵魂”(Nous),“所谓nous(努斯),我指的是灵魂中进行思维和判断的部分。”[3](p143)他首先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作为事物的形式、实体或共相存在具体事物之中,不能在事物之外独立存在,但对柏拉图的“理念”,从动力因、目的因、认识功能和灵魂说等方面丰富其内涵。他认为感觉是一种潜在的认识能力,只有结合普遍概念的理性灵魂,才能完成对现实的认识。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道:“笛卡尔把自然物性当作首先可以通达的世内存在者,又把世界问题紧缩为自然物性的问题,这样就把问题收得更狭隘了。他臆想出一种最严格的存在者层次上的认识方式,坚持认为,对存在者的这种认识也就是通达在这种知识中揭示出来的存在者的首要存在的唯一可能的通道。”[2](p171)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把作为“思执”的“我思”与物质实体相区别,在存在论而言就是“存在”与“思维”的区别。在笛卡尔这里,物质实体在长、宽、高三个方向的“广袤”构成了其在“世界”之中的本真存在。物体只有“广袤”不能思维,灵魂可以思维没有“广袤”,他认为“广袤”的变化使感官不可靠,只有心灵之眼才可靠。“只有我的理智才能领会它。”[4](p33)即理智的直观才能把握永恒实体。
康德的智性直观(或译“理智直观”“知性直观”,词源为拉丁文intellectus)延续了自古希腊柏拉图“理念”以来的理性直观,认为感性认识不可靠,把握事物的方法应引向理性直观,体现为从已经获得的“相”去推演具体事物并展示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归属关系。康德的区别在于为“智性”与“直观”划定了边界,认为智性能力与直观能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能力。他在“先验逻辑导言”中说:“我们的本性导致了直观永远只能是感性的,也就是只包含我们为对象所刺激的那种方式。相反,对感性直观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就是知性。”也就是康德所谓的“概念+直观”。康德指出感性直观具有认识的优先性,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中认为,时空不是概念,而是先于概念被给予,是直观到的。直观是一种感官接受能力,在时间和空间的形式下人才能接受那些杂多的感官材料。海德格尔认为,康德虽然放弃了主体和内部经验在存在者层次的优先性,但他要求为“在我之外的物的此在”提供一种证明,这说明他的立足点仍在主体之中,在“我之内”。这种观念主导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西方传统哲学对事物的认识方式。
胡塞尔作为现象学奠基者,提出现象学基本原则“走向事情本身”,①胡塞尔在《观念I》中首先提出的现象学的理论基础,以一种“原始给予的直观”获得“事情本身”。揭示了客观对象与主观的“意向性”活动之间存在着“先天相关性”。即从一个已呈现出的可感知的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念假设和建构性解释出发,在这一出发点上,海德格尔与胡塞尔是一致的,同样地,他们认为现象学本质上是描述性的任务,非假设性和说明性的。但是胡塞尔的“事情”,指的是意识行为,而海德格尔讲的“事情”是人的存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阐释了两者的差异:“在胡塞尔的意义上,‘现象学’被阐述为一种由笛卡尔、康德与费希特提出的特殊哲学立场。思想的历史性全然是外在的。”[2](p51)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继承了理性主义与唯心主义,把哲学看成了一种严格的科学。事实上,胡塞尔的现象学确实以逻辑学和心理学为基础而创立。他认为现象是主体意识体验的内容,主体意识与外在对象是表征与指称的关系,外在对象通过意识活动显现出来。意向整体何以成为可能,便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方法论“范畴直观”。①在胡塞尔《逻辑研究》中,它被称作“范畴直观”概念出现,在其《观念I》中,被称为“本质直观”。为了便于解释,本文采用“范畴直观”。即“直接的‘看’,不只是感性的、经验的看,而是作为任何一种原初给予的意识的一般看,是一切合理论断的最终合法根据”。[5](p42)胡塞尔试图从哲学上证明,直观本身就是一个合法性源泉,人能够直接观看出一般性的、理智性的逻辑构造。在直观行为中,人对物的“看”并非如感官的单纯反映,而是把某些预期的内容补充到观看的对象中,这些填充的内容以一定的形式逻辑和概念范畴,加进人的意识活动中去,这些由直观直接被给予的逻辑关系和概念范畴,不是单纯的感觉获得的,而是在直观之前已经具备洞见这种逻辑的能力。胡塞尔的“范畴直观”打通了逻辑学与心理学、纯粹形式与具体经验之间的中间道路,希冀以此提供意向性洞见的根据。
海德格尔则认为现象“首先与通常恰恰不显现,同首先与通常显现着的东西相对,它隐藏不露;但同时又从本质上包含在首先与通常显现着的东西中,其情况是:它构成这些东西的意义与根据”。[2](p42)海德格尔是在物的存在活动中理解物。他通过对“讲台”②海德格尔在《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一书,第一部分“体验结构的分析”中,以最贴近的实存物(Existentem)“讲台”阐释周围世界体验,区别于胡塞尔的“侧显”意识活动,海德格尔认为人对物的认识是一下子被给予的,而且总是带着“前提”作为(As)某物出现,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有某种意义”指示着“意蕴”世界。的分析,认为人对于物的认识,不是通过各种侧显意象的叠加,而是一下子直观到的。这种直观带着物与周围世界关系的理解,物总是处于与其他物相关联的境域之中。海德格尔认为尽管胡塞尔主张返回现象本身的描述,但是“范畴直观”仍然受限于西方传统思想中的直观、在场以及时间性呈现。在海德格尔这里,现象是“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公开者”。[2](p114)现象物自身已呈现了自身,这种呈现本身是对物的揭示过程。与胡塞尔作为先验哲学的现象学不同,他把胡塞尔反历史主义的现象学颠倒过来,使“现象”还原到历史性的语境中。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现象学这个词有两个组成部分:现象和逻各斯。两者都可上溯到希腊术语:显现者与逻各斯”。[2](p33)海德格尔把古希腊的logos解释为“让人看某物”,于是,现象学就是,让人去看那些在普通观看中没有看到的东西,把隐秘不显的方面揭示出来。因此,这种“让人去看”就成为一种描述、一种解释,即解释学。海德格尔的“视”其实就是其现象学方式,也构成了其哲学的基本观察方法。
二、意蕴世界之中的“寻视”
海德格尔现象学“视”的方式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认知,他认为西方以往的认识论,以及胡塞尔的“范畴直观”只是人的存在中“视”的种种衍生样式,人的“视”要由人的存在来决定,人的存在首先是在一个具体的境域之中——Da,人在这样或者那样彼此相异却又相连的境域中存在着,这在人的存在自身中处于优先地位,所以海德格尔把日常所谓的人称为此在——Da-sein。生存境域比人的存在更原初,此在在世界中存在,被这个整体所规定。整体规定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来自于人的存在本身。由此,海德格尔指出看既不是用肉眼来感觉,也不是知觉现成事物的现成状态。“‘看’只有一个特质可以用‘视’的生存论含义,那就是‘看’让那个它可以通达的存在者于其本身无所掩蔽地来照面。”[2](p171)在这里,海德格尔否定了两种普遍意义上的视,一种是纯粹感官反应,一种是传统意义上对物的静观,即对象性的切断物与其相关连整体的关系。海德格尔的视在存在论层次上,从存在者看向存在者的存在。
海德格尔对“寻视”的分析主要在其著作《存在与时间》中,在追问世界的世界性时,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表述为“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最切近的世界就是周围世界,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表现为与周围世界的“操劳”,人的周围世界被物环绕着,海德格尔把目光看向了人身处其中的物。“世界之内的存在者是物,自然物和有价值的物。”[2](p74)这些有价值的物更本质地显示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对有价值的物的考察中,海德格尔把物分为手前之物和手上之物,因手上之物跟人的生存具有更原初的关系,他把手上之物作为主要的观察对象。首先,海德格尔否定了对物外观的“观察”,因为这种“观察”无论多么敏锐,都不能领会物的上手状态。然后,指出在操劳中人与物打交道不是盲目的,有着自己的视之方式,“同用具打交道的活动使自己从属于那个‘为了作’的形形色色的指引。这样一种顺应于事的视乃是寻视[Umsicht]”。①德文:Umsicht。打量,小心谨慎,寻视,也译作环视,循视,统观。英文翻译为circumspection。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寻视在发现着,也即寻视过程的同时被理解的“世界”已经在被显现与释义。一个用具被生产出来,是为了作……用的东西,在使用的过程中,一个用具总是指向另一个物,在这样的链条中,围绕着这一物形成了一个指引网络,这样由一物产生一个个的事件,顺着这些事件的追寻便是寻视。
海德格尔在这里举了锤子、刨子、针、鞋等许多生活用品的例子。如何寻视一个锤子,“寻视追随用具的用向(Dazu)而到用具的何所用(Wozu)”。[2](p60)锤子被生产出来之时,已经有着明确的用途,而且,我们可以直观到它的质料,质料指引的是钢、铁、木材、石头等,这些来源于自然。锤子在使用过程中,自然也同时被揭示出来,用具承载着自然,但是自然在物身上是隐而不显的。锤子在使用过程中,必然有一个使用者,这个使用者已经知道如何使用,有一种使用规范存在于公共世界之中。除此之外,锤子的锤打对象一般是钉子,当然也可以给予他用,钉子又会指向另一物,比如说木头,木头可能是作为一个房梁,房梁指向木屋,木屋为了人遮风避雨。“这个防风避雨之所为此在能避居其下之故而‘存在’,也就是说,为此在存在的某种可能性之故而‘存在’。”[6](p98)在如此这般对物的寻视中,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者,人的存在,海德格尔称“此在”,在这样的世界中显示出来。因为用具不只在空间中占有位置,而且总是服务于此在的某种目的,所有的用具都指向此在。在此,我们比较一下,手前之物与手上之物的不同“视”的方式,手前之物是一种对象化的审视方式,当一个物被理论性考察的时候,有用性的指示链条将被打断,它变成静止的。手上之物则没有被对象化,它在实践性之中,也即在物的指示链条之中,是一个“生成”中的物,这个物不断生成事件,构成其存在的真相。胡塞尔的物是一个静物,人不断转换视角去观察,把单个物体的“侧显”意象并置,然后得到这个物的整体,但这一物仍然是孤立的。海德格尔的物是在实践中活动着的物,物与人都在时间和空间的流转中不断变化,不断生成新的意义。这种寻视有想象的参与,但此种想象是构建在现实之上,以对世界的理解领会为基础,人何以能理解?根本原因是“此在”的世界性。
此在的世界性表现于此在对世界的领会,即对世界的生命体验。所有的视首先根植于领会,海德格尔指出没有纯粹的直观,“我们显示出所有的视如何首先根植于领会……,于是也就取消了纯直观的优先地位。‘直观’和‘思维’是领会的两种远离源头的衍生物。连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也根植于存在论的领会。”[2](p172)在寻视的指示链条之中,物的历史性变得可见,每一个物,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作为历史性的此在。人之所以能对当下活动进行判断、规划,也是基于历史中的体验,领会的源始来自实践活动。此在领会着的就是它的“此”,即因缘整体性作为其可能关联到的存在整体。“体验作为人的经验,始终处于生命的关联之中。因为体验只是如此发生,即它让存在者作为被设想的并向作为关系中介的自身关涉,而且由此包括于生命之中。”[7](p50)人对物的理解其实是理解物对人的意义,也即是以此在的生存来理解物的意义。人的体验总是被人的经验活动所规定,领会便由此而来。人对世界之为世界的领会,才能完成对于物的“视”。“寻视”揭示了用具为了什么存在的可能性,世界内在的结构,同时揭示出此在所属的世界性。“寻视”也可以称作“概观”或“统观”,寻视顺着其视之路径,对于手上之物不做停留,而是顺着其“为了……”的指示,对周围世界的全面审查,在如此审查中,这一手上之物的合世界性便显现出来了。
三、共同此在的“顾视”“顾惜”
海德格尔通过寻视手上之物揭示此在与物的关系及其相关联的意蕴世界,提供出世界的存在论阐释,然而物的存在方式以及它所依据的“在之中”的意蕴世界,都被日常状态中“此在为谁”所规定,海德格尔的视角从世界问题过渡到人即此在的问题。“寻视属于操劳这种对上手事物的揭示方式;与此相仿,操持是由顾视(Rücksicht)与顾惜(Nachsicht)来指引的。”[2](p142)顾视和顾惜所揭示的是人与人的基础存在论关系,即海德格尔说的此在与此在的关系。在解释关系之前,海德格尔考察了“此在为谁”,“此在的‘本质’根基于它的生存。如果‘我’确是此在的本质规定性之一,那就必须从生存论上来解释这一规定性。”[2](p135)此在根本上是它的生存,这一规定把西方传统中的主体解构了,“因为它不是笛卡尔的灵魂实体,康德的持久的逻辑主体,胡塞尔的同一的我极,舍勒的作为行动施行者的人格。”[8](p351)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果人有“实体”的话,不是肉体与灵魂的综合,而是“生存”。此在的生存表现为与物与人打交道,表现为操劳和操持,而与物打交道最终还是指向了人,因此,此在的生存结构表现为与他人的关系之中。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与他人(另一个此在)的存在方式是共同此在,而此在的生存论结构是日常的共同存在。“生存论上的共在就是‘为了他人之故’,在他们的此在之中,这种共在关系已经被揭示出来了。”[9](p159)这一结构的揭示建立在以寻视(Umsicht)为基础的顾视(Rücksicht)与顾惜(Nachsicht),①英文版中标明,寻视(circumspection),顾视(considerateness),顾惜(forbearance)这三个不同的词语在词源上有亲源关系,每个词都代表一种特殊的景象或看到的东西。海德格尔在原文中将寻视(Umsicht),顾视(Rücksicht),顾惜(Nachsicht)三个词用斜体标出,意在强调三个词在词源学上的关系,每一个词代表了一种看的特殊方式。德语Um,表示空间义为围绕、环绕;表示时间有在……时,在……前面,在……后面的意思;表示目的有为了……的缘故,为……起见。结合海德格尔在文中使用的涵义,寻视既表示空间中对周围世界的环绕式的看,又表示对所看之物为了某种目的的追寻式的看。德语前缀Rück,意为退回、倒退、向后,顾视意指考虑、顾及到他人,此在在世界之中生存,在其生存之际总是会把目光看向他人,这种看不是旁观,而是此在基本的生存方式。德语Nach,表示方向意指向、到、往,表示标准、方式方法指依照……根据,按照。根据他人来看,因此,顾惜也被翻译为宽容、忍耐之意。根据其德文词源的分析,顾视意为考虑、顾及、体谅,顾惜为宽容、放任、忍耐。顾视与顾惜指向周围世界中的人并与之建立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一点,海德格尔举例,“例如我们‘在外面’沿着走的这块地显然属于某某人的,是由他来进行保管的;这本正在使用着的书是在某处买的,是由某人赠送的,诸如此类。靠岸停泊的小船在它的自在中就指向一个已知的、用它来代步的人,即使这只船是‘陌生的’,它仍然指向其他的人。”[2](p145)在世界之中与物打交道时,寻视总是指向另一个此在—他人,其不同于上手状态的物,也不是现成之物,而是存在论上的关系,先于一切实体存在。“此在”“物”与“他人”不仅作为对象性的实体,而且,更源始的是生活世界“关系场域”中既不可或缺又变动不居的组成部分。此在共在的关系,不管我们是否意识、是否承认,“均已经在那里并成为我们思索与处理自我与周遭世界,自我与周围他人世俗关系的背景、基础与出发点。”[10](p134)即便此在处于独处状态,这种关系依然是其生存的基础。海德格尔认为独在是共在关系中的一种残缺样式,因为共在关系在根本上不是孤立的多个“主体”的共同出现,而只是展现出不管不顾和淡漠的存在方式。实际上,此在彼此间在世界中敞开一种开放的共在关系,在其中他人的此在得以在此在的世界中显现。
如果寻视的环节中主要遇到的是物,揭示的是人与物的关系,那么顾视关注的则是“他人”,突显出此在与另一个此在的存在结构,“‘此在本质上是共在’,这一现象学命题具有一种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2](p140)生存论意义上的共在不是胡塞尔意义上“共享的意向性”,胡塞尔从个人的意向状态出发对意义分析,从共有的信念那里获得共享的公共意义,以“交互的认知”为基础建立胡塞尔所谓的“交互意向性”,简单地说,即以个人出发,去找寻与他人建立共有关系的可能性。相反,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本身就处于共在的关系中,“无论是否有一个特定的他人在场,当我感知或使用工具或言说的时候,我总已被卷入一个共享的世界之中了。”[11](p179]顾视中所看到之物,不是物也不是人,而是由物及人所构成的关系,所涉及的视域不是一物、一人的意义,而是在生存论意义上的世界整体的关联性。
四、“认识自我”的透视
此在对“世界”的种种操劳(寻视)和对他人的关心(顾视、顾惜),始终已经涉及能向它自己存在和为它自己存在,海德格尔认为比对“世界”的寻视和他人的顾视更原初的是以领会(Verstehen)为基础对“自我”的“透视”,“自我认识”的透视即是此在对自我的领会,领会不是某种认识能力,而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带有情绪的对生存的领会,其他任何的认识方式都是此种领会的衍生物。此在的“此”是在世界之中生存,生存状态本身已经是其本身的展开,这种展开状态就是领会。在存在者层次上,领会意指能理解某事,进而能做某事;在生存论层次上,有所领会者(此在)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者,被附加了某种的能力,而是作为行为活动中的去存在,“此在一向是它所能是者,此在如何是其可能性,它就如何存在。”[2](p167)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可能性”不是一般逻辑上的可能或现成事物的偶然,而是此在与生存中最原初最积极的存在规定性,此在从来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存在者,而是正在存在。此在的可能性不是主观的任意选择和漂游无据,最本质上是被抛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已经被给予被定调,但对于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来说,它依然有自由以不同方式和程度透视自身存在的可能。
领会作为存在的展开为能够看到此在的可能性提供现象视域。此在的基本存在方式总是带着有所领会或无所领会去这样或那样的存在,已经知道其可能性的存在是什么。此在的存在本质上是领会,其领会的就是此在的“此”(对自我的领会,通过领会自我存在理解一般存在的意义),正因为“此”处在被抛境况和在世操劳中,其总是认错和迷失自己,被遮蔽在其境况之中。对领会的展开则可以使此在明视其存在本身的境域,因此敞开此在本身。作为展开活动的领会,关涉着“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整体结构中的各个方面,上手之物的可能关联揭示出因缘整体性中的在世存在者,以及由此意蕴展开的“统一”的“自然”。对因缘整体的领会主导着此在可能性的筹划,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可能性不假外求,而在其自身存在结构之中,“成为你所是的”就是打开自己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的视根植于领会,此在可能性的打开是通过追问其“为何之故”来领会,如前所示,寻视物的“为何之故”追问物的意义,顾视寻求共同存在的领会,领会就是此在对事物的所“视”,所有的视都是此在的生存方式,“那个首要地和整体地关涉到生存的视,我们称之为透视”。[2](p171)海德格尔用这个术语来区别于传统的“自我认识”①海德格尔还区分了自我认识(Selbsterkenntnis)与自我识认(Sichkennen),前者对自我考虑的是认识的完整性和彻底性,后者指“忘记自己”或因某事“不再知道自己”而丧失掉对自我的认识能力。参照《Being And Time》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英译本注。,表明“自我认识所说的并不是通过感知察觉和静观一个自我点,而是贯透在世的所有本质环节来领会掌握在世的整个展开状态”。[2](p171)传统主体哲学中的“认识自我”从自我那里找一个原点,主体把自我主题化,这就把自我分裂成一个主题化的我,一个被主题化的我,而主题化的自我还可以再分,这就陷入了自我反思理论的两难。“自我并非一个客体,而不如说是一个展开的事件或事情——‘在生与死之间伸展的’生命历程的运动。”[1](p303)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透视自我,指自我的认识是建立在世界的整体展开性,在世界与他人的共在中把握自我。作为去生存着的此在,原初的生存于世界之中,通过生存构建结构与他人的共同存在之中才能对自己有所见。反之,此在不能看透自己,一方面由于自我中心而造成的假象,另一方面还在于对“世界”的不认识,看“世界”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世界的展示性的洞见和领会。
五、照亮真理的“观入”
海德格尔在1949年不莱梅题为《观入存在之物》的演讲中提出“观入”①德语原文为Einblick,彭富春在《论海德格尔》中译为瞥入。另外与此相关的语词还有Einkehr(转投)、Einblitz(闪入)、Einsicht(看入),共同前缀“ein”。Einblicken,意为观察、认识、看破、识别力、洞察力,英译本为to glance。意指一见之下的洞见,强调瞬时而又能洞察实相。概念,“观入”本身发生着一种转向,由技术带来的危险转向“救渡”,海德格尔引莱辛对该词的解释,认为救渡一词“就是回置入正当之物、本质之物中去,在其中加以保存”。[12](p88)把存在之本质的真理解开保存到存在者之中,也就是从存在被遗忘状态转向存在之真理的保存。转向是突然发生的,因为存在并非在一种因果联系中进行的。“在转向中,存有之本质的澄明突然照亮自身。这种突然的照亮乃是闪烁(das Blitzen)。”[12](p90)闪烁把存在带入自身的本己光亮中,本真的是(ist)决不是所谓的存在者,而唯有自身的是其所是。在光亮中存在者的存在穿透时间与空间闪烁着涌现出来,闪烁的存在就是存在者的本质。“‘闪烁’乃是观看”。[12](p91)在一瞥中,在场之物进入其自身的光亮之中,将建基自身的不在场的东西一同带出,但是同时又隐匿于黑暗之中给予保存,好像从未被照亮一般。因此,这种照亮显现为林中空地,②德语原文为Lichtung,又译为明敞、澄明等。英译本为clearing,意为清除、清理、林中空地,Lichtung是法文词clairiree的译名,指林中空地,相对于茂密的树林。动词是lichten,指密林中开辟出的空地,使场域变得开放敞亮,成为流动自由、无限可能之境。海德格尔在文章中强调这个词与Licht(光)是同源词。自身去蔽的同时又自身遮蔽,“林中空地比一切光明和黑暗都要本原。因为一瞥意味着转入林中空地,所以,它又显现为瞥入,它是存在的真理的闪射的转入。”[7](p123)观入在此是作为思想对存在的穿透,使人对存在本性的视见成为可能,观入作为存在和思想又生成自身,人也在观入中明见自身。
观入存在之物③德语原文为Einblick in das was ist。字面意为“观入存在着的东西”,根据海德格尔在原文中的分析,对存在者(物)的观入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这一存在者(物)的存在的观入,即观入存在之物就是观入存在。首先意味着对存在真理本身的洞见,从对存在物在场的实有转向存在物的存在-有所保存的实相。“观入存在之物,这就是本有本身,存有之真理就作为这种本有与失真的存有相对待。”[12](p91-92)海德格尔认为在世界之世界化中,存在的真理为天、地、人和神四重整体的映射游戏。失真的存有乃是因为物的集-置所造成,作为技术之根本的集-置普遍而无所不包,它设置一切在场者的在场方式,使一切在场者显现为集-置的某一目的的统一性之中。一切存在之物的存在方式都成了集-置的设置中的某某—部件。“世界向集置的闪入,就是存有之真理向失真的存在的闪入(Einblitz)。”[12](p91)观入把物的存在之真理换回给物自身,打破这种技术为物规定的物之物性,使其解放,开现出保存存在之本质的世界。
其次,观入存在之物指在存在之本质中的情势。④德语原文为Konstellation。德文意指形势、局势、情况、状况等。“这一情势乃是存有作为危险在其中成其本质的那个维度。”[12](p92)“观入存在之物”不是人类从自身出发向存在着的东西投去的一道目光,不是认识存在者及对其的洞见,而是通过对集-置的悬搁迫使存在者的本有的情势涌现出来。观入是对存在者的“是”(ist)的开放,使构成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上“是”的东西展露。集-置的前期预设使物始终处在非本真的状态,物便与本应最切近的“世界”(世界是大地和天空、诸神和凡人的四重整体)相隔甚远,其落入被遮蔽的遗忘状态之中。“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⑤颂歌《帕特莫斯》第四卷,第227页。荷尔德林《全集》,诺伯特·封·海林格拉特编,后由弗里德里希·泽巴斯和路德维希·封·皮格诺特续编,第2版,柏林,1923年。危险本身即救渡,救渡意味着解开、放开、保护、庇护。物由于技术的本质被集置被遮蔽的同时,世界之光闪烁着存在的真理,“也就是当集—置在其本质中作为危险,亦即作为救渡照亮自己时,就有此情形。”[12](p92)在物的存在本质的天然预设中(预设了某物作为某物),依然有一瞥隐蔽的目光可以通达物之为物的所“是”,还原物的本来实相,而不至于完全淹没在黑暗之中。
最后,观入存在之物还指存在的真理向着失真的存在闪烁。当观入的时候,人被存在之目光击中而进入自身的本质之中,其既是观看者又成为被观看者。当人放弃人性中的固守,从自身离开,在观入中筹划自己,才能投入到天地人神四重整体的响应之中,“才得以在被保持的世界要素中作为终有一死者与神性者相对而视”。[12](p93)海德格尔解释说,四重中的每一个都在“响应”其他三者,并使之变得可理解(海德格尔说是“照亮”),“此四方的每一方,唯有同其他三者产生特定的关系,才能具有确定的特征”。[13](p170)开花结果的大地,日月运行的天空和从生到死的凡人及“神性之暗示的使者”—诸神,每一方都因着其他诸方而显露出来,每一方都在原初意义上带出其他诸方。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同时又作为被观看者——四方整体纯一性——之一的人类,只有在观看的时候,不是把自己撇开,而是投入进此源始的纯一性中,才能把人自身带入与天命(Geschick)①德文Geschick,既指做某事的技能或天赋,又指命运或定数,海德格尔认为这个词的多义性完美地诠释了技术与命运的关联,即两者源自于同时又造就了世界自身向我们展开的方式。的适恰关联中。在技术的本质中能看见存在的闪烁,这是寂静的闪烁,寂静把存在抑止入世界整体中,它使存在的真理最切近人并使人回归于自身本有。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的视,不是肉眼感官对外部世界的感性反应,也不是对一个现成之物的现成状态纯粹理性的知觉。就其最广义而言,“视”统摄着此在在世界之中一切的“筹划”并居于优先地位,视就是此在对自身生存的领会,操劳活动的寻视、操持的顾视以及对存在本身“自我认识”的透视和对真理照亮的“观入”。海德格尔以寻视、顾视、透视、观入等多视点多视域分析了人与物构成的意蕴世界,人和他人的共在关系,在理解意蕴世界与共在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对自我的透彻把握,进而对真理闪射的一瞥。海德格尔的“视”贯穿其分析在世存在的整体境域,形成了对世界整体的认识,是此在理解存在的根本方式。海德格尔独特的“视”阐释了其现象学还原,从静观孤立的存在者还原到多维且动态的存在者的存在。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中的视是一种观察认知活动,那么海德格尔的视是一种生存、存在活动,存在规定了人的视,使哲学的思考方向从对原初的生活(存在活动)进行描述、归纳和判断,转向试图还原更为原初的存在活动本身。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