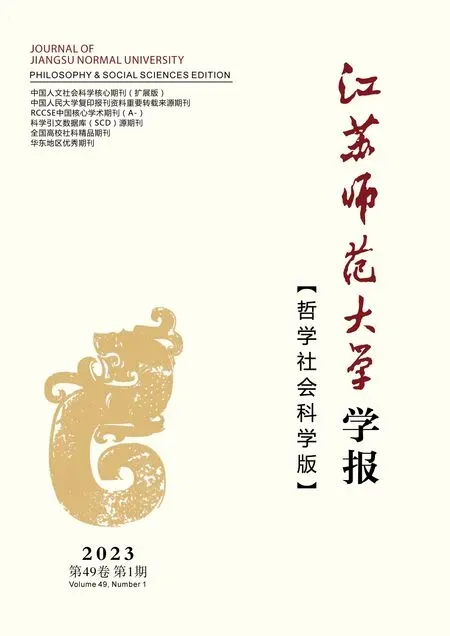人的意义,及当代性的可能
——从王昕朋小说的北京书写谈起
曾 攀
(《南方文坛》编辑部,广西 南宁 530029)
一
事实上,关于北京的书写及其论述,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当然这里并不试图去详尽勾勒这样的写作脉络和谱系,而是将当下的北京书写,置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可能意义之中,并且与当代中国形成互文,以此透析写作者面对历史的宏大与壮阔、曲折与隐微,对此一时代所报以的关切及其彰示的姿态。在这个过程中,北京书写本身所包孕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在庞大的社会/城市网络中个体/群体的处境和命运,无疑都具有显著的当代意义。“今天,当我们谈论‘北京’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国际化大都市?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百分之三十八点五的城市?很显然,‘北京’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一个充满情感蕴含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从来就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不是常数,而是变数。”(1)江飞:《作为方法的北京——以〈北京西郊故事集〉〈北京传〉为中心》,《南方文坛》,2021年第6期。也就是说,北京往往能够形成一个足够浩大的表征,构筑一种既具有地方性同时也充溢着普遍意味,既代表着城市也涵括了多元现代的方式,以此构筑认知与反馈如今的中国和当下的时代的文化路径。
我一直在思考的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变迁与演化,无论如何动荡,又或如何平静,总会存在着不可摇摆的稳固根基,这个根基如果有那必定是人的本身的意义,以及如何朝向当下现实与未来可能的尝试。从这个意义而言,王昕朋的小说布满着一种社会性与人性的思考在其中,既有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关注,同时包含着阶层的与人文的、城市的与现代的、生活的与人性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他的小说中有一种系统的理性,这对表现城市的社会网络与文化层级多有裨益,而且对应着城市传统与现实环境的纵横交错。
一直以来,王昕朋是一个始终保持敏锐的作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王昕朋的文学创作进入了成熟期,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红月亮》《天下苍生》《漂二代》《花开岁月》《文工团员》等、中短篇小说集《是非人生》《姑娘那年十八岁》《北京户口》《红夹克》《寸土寸金》等10多部,以及长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雄壮地崛起》《境界》、散文集《冰雪之旅》《宁夏景象》《我们新三届》《金色莱茵》等。可以说,在国家机关的工作经历,加之他调查研究的现实基础,当然也包括他在出版行业的工作实践以及对文学本身的求索,使得他的小说往往呈现出一种庞杂而精确的针对性叙事,以对焦城市的性征与人物的性格,结构出宏阔而幽微的精神境域。我对王昕朋作品的关注也已十年有余,细一盘点,发现他最为突出,同时也用力最勤的,是关于北京的书写。但他写北京又不是以往那种都市题材的写法,往往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将人物个体置入北京的总体性城市结构之中,二是关注底层的或曰阶层共同体的生存境况,三是采取家庭的或家族的叙事以牵涉更广泛的道德伦理,四是在以北京为中心在城市和乡土之间架设或隐或显的桥梁。
从小说的整体形态而言,王昕朋一般而言采取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他熟稔于城市宏观的运转以及微观的状况,对待地方的与城市的文化时往往显得务实而真诚,发现并周旋于人的问题与处境,且富于批判精神。具体而言,王昕朋的小说没有太多技巧的炫耀和讨巧的形式,但他对人物的那种精准的把握以及对事件走向的曲折把控,却构成了文本的中心。在这里并不是说王昕朋的小说对北京的关注具有怎样的独创性意义,或者说他在北京书写的脉络和谱系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而是他的小说对于北京及城市中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况及其所映射的社会历史、现实生活、阶层生态等具有一种开放性的与当代性的视阈,或许这其中足以能够提供某种方法论的视野。
在此基础上,更重要之处在于,在王昕朋小说所营构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装置中,何以展开对人本身的在意和关切,又如何将之推入当代中国的城市场域,指向不可确定却始终向前的文化路径。实际上,对一个地方的叙事首要考量的是这样的地域或说场域能否成为其中的主体与群体的存在之所,甚至能够成为精神的栖居之处;其次,文学所聚焦和重构的“地方”,是否能够形成自身足以滋养人、包容人,甚至再造人的文化属性;再次则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写作,能否成为一种象征的符码,构造与现实状态相对应的——当然这其中有着或背离或趋同的价值取向——理想型的城市愿景,从生存处境,到生活现场,再到精神的有效生成,而不仅仅代表某种精神的乌托邦。
细读王昕朋小说会发现,其中关切的尽管是阶层的存在与个体的命途,但是将这些人物主体摊开来看,往往又能发现种种独异的形象。也就是说,对于王昕朋而言,城与人作为一个不可分化的结构,往往细密分布在社会的多重结点上,映射出现代城市的多维症结,在这个基础上,王昕朋创生了一个北京城中不为人所共知的人物谱系,对于王昕朋而言,小说的人物或许谈不上立体,他也不擅于表达人自身的精神曲折和灵魂幽境;但却绝非脸谱化,而是充满现实况味与伦理认知的,同时小说还始终有一种当代性的意义在,而且试图完成一种经验的与价值的创生。
二
综观王昕朋小说中的北京书写,其中的主要人物常常面临着双重边缘的指认,一方面,他们从偏远的地域来到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北京,在自我认同层面时常产生难以名状乃至自觉的危机;另一方面,他们到了北京之后,实际上也是身处城市的边缘地带,成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难以得到城市认可的底层人群。这就导致了一种结果,就是他们不仅难以兼容于既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网络中,与此同时对自我内心的认知与身份的认同往往会形成内在的精神结构。这也造成了写作者内在的矛盾,从王昕朋小说在北京书写中的叙事伦理而言,其既需要认同于现存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同时又必须包容乃至悲悯笔下的人物,而他处理这样的两难问题的方式,是对于人与城、个体与整体的矛盾问题的直面与解决。在小说《北京旮旯》中,作者写的是北京城里一社区与二社区的两栋大楼之间的旮旯,却聚焦了来自大别山的外地青年张四的生活境地,他出身底层却一腔热血,要为邻里做点实事,也想成为北京这座城的一份子,自然也是为自己的谋生;但经历了来自城市管理者以及社区居民的种种误解、矛盾和危机,最终,他的韧性与城市的柔性之间,还是产生了契合,张四也得以在北京城安定下来,娶妻生子,创造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甚至深得邻里的喜爱,并得到区里的表彰,“直到今天,张四仍然待在那个旮旯里,修鞋、修车、开锁、配钥匙、洗头、理发、通下水道。他还收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称他师傅,他叫徒弟韩刚哥,有时也叫刚哥”(2)王昕朋:《北京旮旯》,《当代》,2022年第4期。,小说是相对开放的,试图打开的是外省底层青年的生存空间与未来可能,当然这一方面出自周遭居民与人群的宽容理解,另一方面则是源自个人奋斗与精神提升。
关键还在于这样的北京书写,如前所述对接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一脉,但事实上又有所不同,其区别于十七年文学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环境与人物的塑造又逾越或者说超离于既有的写作形态。这一切的关键,在于王昕朋小说对城市的系统性、主体性以及当代性的兼容。当然也不是说他在这其中写得特别完好,而是这个过程具有纵向的演变发展中未竟的与开放的城市文化形态。于此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小说又必须对于当下的社会政治状貌尤其是对北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肌理把握得细微入里。正是在这种历时性发展与共时性存在的关系网格中,人的主体性及其意义得以有效生成,并最终在叙事结构中得以发生不同程度的现实扭转。这里边就产生了特别有意味的状态,那就是人的主体性在多大意义与程度上可以和现实产生妥协?小说在表述这样的协商乃至碰撞时,如何展开自身的文化思辨及人文属性?
这就要求写作者不仅谙熟北京的城市运转,而且需要建立在广泛而细致的社会调查基础上。从这个意义而言,王昕朋并不是站在文化精英的立场上,也并没有在小说中展现智识性的与思想性的一面,而更多的是不断地将自己的叙述下沉,不断地调节对焦北京市民的生活现场尤其是精神的扭结之处。在小说《万户山》里,万户山有一万零一户人家,故名。这是一个拆迁安置性的社区,作者并不讳言这是一个五方杂处甚至是鱼龙混杂之地,生活与管理难度可想而知,里面充满了种种难以消解的矛盾,也展露出城市治理的艰难所在,如何处理这样的社区难题,依靠人抑或依靠制度,又或者兼而有之地总体把握,都是小说需要纾解的困难,但最终归于当代中国中的细微之处、之地的境况,以及寄寓其间的“人”自身的理解、认同与执行,则代表着王昕朋小说的有效性与现实意义。
三
孙郁曾区分“旧京派”与“新京派”,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端木蕻良、汪曾祺、张中行、季羡林、启功、王世襄、宗璞为代表的“旧京派”传统并一直延续至当代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陈平原、扬之水、止庵、李长声、李敬泽、靳飞为代表的“新京派”,“既非时髦中人,也非隐逸的存在,体现出的是一个敞开的舞台中的图景”,不仅如此,“随着时光的演进,这支松散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之中,近年来,格非、李洱等人也汇入其间,审美风格变得与先前略有不同了”(3)孙郁:《从京派到新京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6期。。从文学而言,新时期以来,较为重要的是陈建功的京味小说,特别是《丹凤眼》《找乐》《飘逝的花头巾》等中短篇小说,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中的北京书写。而至于新世纪的当下,近年来邱华栋的北京书写也同样引人注目,他的《北京传》将“北京”不仅看作一个由传统演化而成的现代城市,并且将之视作不断成长中的生命体,自有其肌体、筋脉、血肉,渗透出厚重而新潮的文化,在既传统又现代的意义上,包孕着人文与精神的旨归;徐则臣在北京书写中则透露出难以排解的忧虑,甚至是在现代辐射下的城市生存/精神状况中,隐现着重重叠叠的感伤和悲情。不同的地方在于,王昕朋更倾向于让那些边缘的异乡人和底层的失败者在所谓的“看不见的城市中”,“看见”北京,并以此为镜像“看见”自我及自身的阶层状态,在制度的与系统的价值中求索人的存在本质。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当代中国要表现一个城市,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城市,对其中的结构性的与系统性的探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最具难度的,尤其是当人的主体性与整个城市的纵横网络之间形成融汇或冲突时,如何表述人的内心的轨迹,并由此牵引出一个阶层、一代人,甚至是一种总体性的精神状况。可以说,不仅是北京的书写,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对于城市写作的一大难点。王昕朋常常将他的人物个体或群体,在小说的开始又或者说在小说的整体布局中置于一种难以消解与难以克服的矛盾之中,由此倒过来追寻一种社会性的症结与阶层性的痛处。这样写的好处在于既有对个体处境与精神困境的叙写,同时又能在现代城市的聚焦中呈现出复杂的与立体的现实场域。在小说《金融街郊路》里,大桂和小桂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两人从乡村进城来到北京,在金融街的停车场当收费员,然而本来出身一致且职业无异的二人,却生出了异心,小桂与同在金融街郊路看车的老伍合谋,让老伍挤占了大桂的位置,吞下了停车场的地盘,而小桂则在羊杂汤馆当了店面经理,开上了价格不菲的小车,与大桂每况愈下的底层生活相较,小桂在北京混出来了,过了更体面也更富有的生活。很显然,底层的外省人的阶层内部没有形成紧密的共同体,事实上也很难存在这样的结构,写作者对唯利是图的个体以及阶层内部的分裂进行了剖解,更重要的,这样的来自乡土世界以及底层生活的共情与同心,为城市中的物质与利益所颠覆,如何在其中重建认同的与价值的序列,无疑成为北京书写的重要命题。
在这里还必须提出来的一点是北京的书写与一般情况下的城市写作不同,当然也包括小城镇的叙事,以及乡土的表达相去甚远。这么说的意思是北京不仅有自身的独特性及其文化属性,而且在城市体量与现实复杂性上也比一般的城乡要显得特殊。因而在长篇小说《漂二代》中,王昕朋写的是写北五环外的十八里香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面临的逆境与窘境更为多样而深切,正是北京这样的城市,清晰地折射出两代北漂者的价值困境与文化两难,他们留在城市固然是为了谋生,姑且不论漂一代本身的艰困,如今又不得不面对来自后代的难题,而将代际的问题植入现代城市的治理及其文化的容量中,无疑彰显了写作的难度。更重要之处在于,无论是漂一代还是二代,在他们自身内部所存在的疑难和缺陷,事实上又突破了一般意义的底层叙事,而延伸到更为深刻的人性剖解和价值反思之上,也许以此来反观城市尤其是北京的现实意义,更能折射出当代性意义对于人的可能性的追寻,当然这其中也因为主体内部的局限而显露出了种种的限度乃至不可能性。
对于北京而言,其中的特殊性一个在于这个城市总是带着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作为政治中心,也作为社会治理的扩大化显像,最能映照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状貌;二是作为新世纪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的现代都市,北京是金融中心、经济中心,也因此在物质与欲望、人心与人性层面显现出更为复杂的状貌;三是北京的社会网络、阶层状况颇为多元,其中展开着关乎伦理指向的非同一般的维度和面相;四是在文化岩层上展露出不同的层次,甚至是在深度和广度上显示跨文化的意味,也即不同的文化在北京这样的大都会碰撞、融汇,更重要的是开放性视域中所代表着的当代中国的未来走向。因此,北京既是传统的文化古都,同时又是新兴的国际化大都市,因而基于北京的书写就不是表面那么简单,这就需要去辨别与辨析当代北京城市生活的价值走向,在此基础上去全面地考量和考察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个体处境,这样的处境,不仅仅是身处于城市的现实生活境况,更在于个体阶层在社会性的网络中遭遇的困境与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内心抉择乃至灵魂安放。王昕朋的小说《北京户口》,以个体家庭牵引城市制度,刘文革、大胖和女儿刘京生一家为了北京户口左突右奔,无计可施之际只能铤而走险,却遭遇了诈骗,拿到一个假户口,最后不得不黯然离开北京。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感兴趣的是个体如何融入或挣扎于这样的系统性设定中,他们会得到怎么样的回馈又将遭遇怎样的命运,如此折射出现代城市的价值取向,并牵引出当代中国的意义择取和伦理建构。而且随着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深,对于城市的书写无疑更能够展现出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走向。
四
总的来看,王昕朋的小说非常擅长表现阶层与社群的交互,这恰恰代表着城市治理中的核心命题,也就是说作者从人的处境到社会治理再到人本关切,这代表着写作者的价值探询的过程。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王昕朋并没有站在既定的群体立场,也没有预设某一种道德的旨归,他更倾向于在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规制中寻向人性的归属。
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的是,王昕朋的北京书写表面上看是趋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法,但是从小说的内在肌理及其对人物与命运的处理来看,又往往蕴蓄着浪漫主义的与理想主义的因素,这尤其体现在他对人的处境和命运的关切上面,他自然能够看到其中的复杂与困境,但时而又透露出他对解决问题与构想现实的乐观。如小说《北京旮旯》中,尽管作为主人公的底层小人物张四遭受了他难以纾解的困难,尽管作者也深知他的处境难以达到完满的解决。很多时候,人的境地在城市的价值系统中可能是无解的,但王昕朋依旧赋予了这样的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群落中的位置,而身份和地位恰恰是在北京的旮旯中最难以寻获的。因此,我常常以为,对于北京的认知,一方面往往包裹着一种宏大的与抽象的文化意味;另一方面,则是在社会阶层的落差中不断显现出来的新的鸿沟,而这样的落差不仅对应着北京那个似乎遥不可及却又时时身处的所在,对于底层与普通人而言,总是存在着难以企及的社会想象,而且常常对应着微弱的社会个体与庞杂的社会系统之间的脱节,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分裂造成的是种种对象化的不可能性。这个过程往往就孕育着对于一个城市的认同与否,对于共同体的寻获与否,甚至是对于自我的认知奏效与否。
从这一点而言,王昕朋的小说可以说做到了很好的平衡,当然这其中也时而显现出失衡乃至断裂。首先是作者坚信主体的危机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沟通与交互;其次是小说表述个体或群体的话语时,又常常能够勾连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的运转;再次是作者往往试图去沟通人的命运与城市的命运,并且将其放置在一种系统化的、网格化的以及关系化的形态中加以考量。这样便能在小说文本中形成这么一种内在的形态和伦理,那就是弱小的与卑微的主体,其当然往往可以排异于总体的网络之中,但却始终不曾将之割裂来看,也就是说,矛盾和问题在王昕朋那里都存在着可以松绑和调节的可能。
除此之外,还必须指出的是,也许从问题的出现到试图解决的途径的诞生,并不单单成为王昕朋小说固化的叙事结构。王昕朋还常常试图去表现这样的结构中产生的新的命题与问题。譬如在小说《金融街郊路》,包括《北京上午九点钟》《第十九层》等文本里,可以见出写作者对于阶级的认知是深刻而多元的,其将重心放在了城市中人在面对物质、欲望时的情感、心性上,一方面考察结构性与系统性界域中的命运趋向,另一方面则是探询更为普泛的精神认知和文化境况。这就意味着作者并不能仅仅止于一种阶级论式的判断,而是将这样的阶级状况与心理症状引向开放,导至当代北京乃至中国更具总体性意义的考察。
五
如前所述及的种种关于北京书写的文本,其实其中是汇聚了很多声音的,特别是从纵向的传统追溯,到横向的当代探询,都能见出如果北京书写兼具历史性与当代性,那么这里必定是有多元的文化参与在其中,甚至是政治的、资本的、权力的诸多声音在里面。不得不提及的是,从现代中国的京派文学到新时期的京味小说,再到新时代的北京书写,多元的脉络和复杂的枝叶,恰恰是文学发展流变史、美学史以至于城市史、人文史、生活史的追溯中需要处理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它的难度所在。作为一种城市/都市写作,则需要关注那些光鲜的与显像的反面,关切那些被遮蔽的声音和主体,后者更值得我们去注意,而文学史在处理当代中国的城市命题时,实际上必须辨析的现象更多,其中不得不面对的是那些微弱的、隐现的与变形的声音,这样的声音——甚至包括杂音与噪音——都需要小说文本去细致分疏处理,特别在多重维度的价值形态里,也许要处理的更加仔细,辨析得更加细致,才能真正地不让那些浮躁的、肤浅的甚至丑恶的现象去篡改人性的、精神的与文化的意义,因为后者意味着小说内在的叙事伦理,也代表着城市发展的未来径向。在《红宝马》《红夹克》《红宝石》等小说中,王昕朋更是提出了尖锐的现实质疑,如师力斌所言:“随着大城市接纳外来人口力度的逐渐加大,比如暂住证制度、移民子女高考制度,甚至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进城打工群体的利益期待也逐步提升。打工者不仅仅要赚钱,还有更深层面的利益诉求,势必介入更深层的城市生活,利益调整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理应得到相应的利益回报。我认为,这三部作品正是这一利益诉求的委婉的历史表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三部作品显示了进城叙事的复杂性和新的眼光。”(4)师力斌:《王昕朋进城系列小说:问题打工者与新进城叙事》,《文艺报》,2017年03月28日。王昕朋的小说将小人物们的滞涩的、艰难的、恍惚的声响传递出来,将其植入城市发展的社会性命题之中,试图寻求解决矛盾的途径,事实上是在描绘新的图景,构筑新的想象,当然这个过程如果更注意语言的考究和价值的多元,则也许更能表述出北京书写的意义构成。
总而言之,当代文学中的北京书写是整个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学发展史中的地方写作、城市写作以及生活性写作的关键所在,更是关乎个性的、美学的、文风的价值归属;而且在表述国族史的创伤及其修复,个体与群体的精神发展,以及投射时代的与主体的精神状况等层面中,构筑整体性的制度系统与细致化的个体人性及其所包孕的生存、审美、娱乐、语言的新变。通过这样的路径处理城市书写中的参数和变量,才能真正有效考究人的可能性命题,并在一种准确性与开放性并生的叙说中完成当代性的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