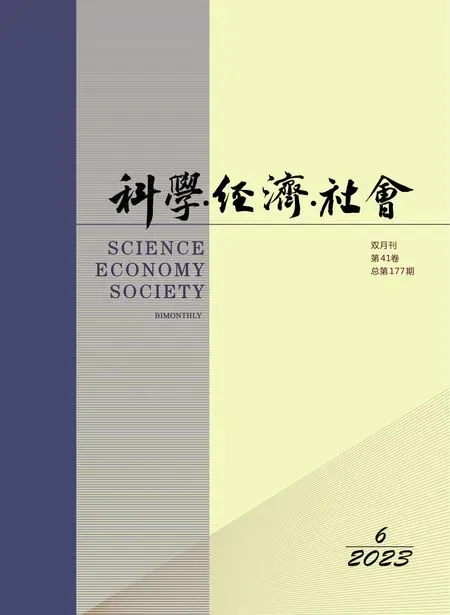“元理论”能做什么:胡塞尔现象学与传播学的元理论实践
王嘉新
作为反思现代生活的核心概念,学术话语中的“交往—传播”(communication)已经成为以“操作概念”出场的“迷思”①Eugen Fink, “Operative Begriffe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957,Vol.11, No.3, pp.321-337.。“交往—传播”概念在使用中似乎不言自明,但是却又无法作为对象性概念加以把握。面对“交往—传播”概念时的焦灼,反映出我们可能尚未充分理解过这个概念。这种焦灼当然不只是来自个体的理论需求,其背后更有着集体的“学科焦虑”。这一点明确地反应在汉语传播学界对“交往—传播”概念的新一轮反思中。潘忠党批评道:当前汉语新闻传播研究由于对“传播”概念“语焉不详”“各执一端”,导致“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学科的再生呈现出身份不显、学理支离的特色”②潘忠党:《走向反思、多元、对谈的传播学》,《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第47-52页。。对此,潘忠党给出的建议是:“我们就接受‘传播’这个对‘communication’的汉译,将之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或互动),以及使然交往、在交往中、通过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身心体验和意义。据此,传播即是关系、意义、结构等生成过程中的中介,它本身也为各种机制和技术所中介,而所谓‘媒介’,即为携带着规范符码的器具以及使之成器的体制。”①潘忠党:《走向反思、多元、对谈的传播学》,第47-52页。
这种对于“传播”大全式的界定被理解为一种传播的“元理论”(metatheory),这种元理论包含着普遍性地对世界加以澄清的倾向,因而元理论可以帮助形成学科所必需的共同趋向②传播学中的“理论”概念本身的分类和相互关联的解析参见:Carsten Winter, Andreas Hepp, Friedrich Krotz, Theorien der Kommunikations-und Medienwissenschaft: Grundlegende Diskussionen, Forschungsfelder und Theorieentwicklungen,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8, pp.10-15.。换句话说,提出“元理论”“元对话”“元话语实践”的目的仍然是试图引导学科方向,重塑学科的内部认同。本文的论点是:传播学的“元理论”必须建立在对“交往—传播”本身的严格融贯的反思之上,尽管通往这种反思的路径可以不同。具体而言,想要理解元理论的内容,实际上需要对“社会”“交往”“通过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身心体验”“意义”等这些概念进行一致性的理论澄清。想要通过“元理论”实现学科内部的融贯(coherence),“元理论”自身必须首先是融贯的。本文试图指出,这一工作在思想史上——尤其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已经有了深厚积累和丰硕成果,完全可以满足当前批评性地建构元理论的需要。如同“meta”的含义使物理学(physics)不等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s),“meta”也使得传播的元理论不等于一般的传播理论。“元理论”意味着超出理论内容而对理论的操作性概念进行反思。一方面,元理论本身一定是更高层级的反思(reflection in higher order),更一方面,它处理的对象一定是更基础的概念语义。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的“元理论”不可能不是对“传播学”的哲学思考。如果“元理论”仅仅强调多元、对谈,缺少理论的规范性(normativity),那么就只能是一种平庸的正确。本文将以胡塞尔现象学为例,指出现象学对理解和界定“交往”的元理论的可能贡献。这种贡献不仅在于胡塞尔的思想构成了传播学的元理论之一种,而且在于我们可以透过胡塞尔的思想对“元理论”本身的理解进行批评性地再规定。并且,元理论层面的理论差异会导致我们对传播研究取舍上的差异,以及对传播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或者说,帮助我们建立反思研究本身的理论的自身意识。在这个角度,我们更加有必要引入胡塞尔的理论资源,胡塞尔现象学不仅仅可以是元理论,而且是一种有竞争力的元理论。从内容上讲,文章将首先把“交往”这一概念导入到一般的理论语境之中。第二、三、四部分将从现象学的意义、交互主体性、生活世界三个相互关联的方向展现胡塞尔对“交往”的完整理解。第五部分及结尾,文章将概括胡塞尔“交往”思想的重要特征,并且指出其何以作为传播学的元理论及其启示。
一、交往—传播研究的哲学面向
人类对于人际间或更广泛的社会传播中的符号、信息、意义的讨论从未停止。尽管亚里士多德已经把人理解为“唯一具有言语的动物”,也更是“政治动物”(politikon zoon)③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但是“言语”本身尚不蕴含当代的“交往—传播”的概念。当代“交往”概念的所激起的广泛兴趣,其理论根源在于伴随着近代哲学而生的“唯我论”(solipsism)倾向。正如彼得斯(J.D.Peters)重复的那些哲学上已经耳熟能详的关于交往的观点,“交往”这个问题呈现出一体两面: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瞬间可达”的交流美梦,另一方面是个体茕茕孑立,迷宫般难以穿越的交流噩梦①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美梦”“噩梦”的修辞不应当遮蔽交往论题原初的哲学实质:个体事实上可以理解他者的心灵(思想),但是他者的心灵显然又不像我自己的心灵那样明见。如何理论地解释这一事实,如何理解交往的限度?很明显,传播学兴起为一门显学,不只是基于单纯的理论兴趣,而是来自于现代社会的结构变形中人们对传播现象产生的巨大的实践兴趣。恰如卢曼指出的,系统社会的自身生成以意义交往(Kommunikation)为前提,伴随着作为播散媒介(Verbreitungsmedium)的技术手段的不断进化和发展,“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知晓的东西,都是通过大众媒体。”②Niklas Luhmann, Die Realität der Massenmedi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6, p.1.特别是进入数字媒体社会后,人的社会生活被置入到“浸入式”的交往环境中。这就意味着对于“交往—传播”的研究等同于对所有可能的社会现实的研究。社会现实的整全式的媒介化——或者说可媒介化——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传播学作为交往研究的范围,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可以是和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结合而产生的传播(某某)学,更可以是研究技术媒介的传播学,或者技术媒介的传播效用学等;另一方面,交往本身由此成为对于全部社会现实的特征刻画,其本身的面貌却越发模糊。因此,传播学蓬勃发展的同时,隐忧也越来越明显:“弥散性的交往概念意味着整个传播学科领域在碎片化,我们同时也缺乏‘中心理论’去辩护这一学科的一致性。”③龙强、吴飞:《认同危机与范式之惑:传播研究反思之反思》,《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第73-84页。上文提到,拯救这一困难的可能路径就是诉诸于传播的“元理论”。无论我们对于“元理论”有多少不同的刻画,其基本含义都不应当是别的,而只能是对于“交往—传播”概念本身内在规定的揭示,而不是在“交往”概念之上附加其他仅仅只是与其相关的对象。
恰当地揭示交往的内在规定,不等于通过交往借助的技术手段以及交往关联的对象来界定交往,而是把交往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就其本质加以研究。在胡塞尔现象学的视野下,这项工作表现为通过现象学本质直观的方式对人的交往意向性结构进行分析。由此,也可以解决交往限度的问题或者说可交流性(communicability)的问题,即人类主体之间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交流的,并且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可交流的。胡塞尔现象学对于“交往”的研究希望提供一个交往本质(eidetic)模型,而非经验性(empirical)的结论。并且由此解释为什么在这一原型的层次上,人类主体既不需要像孤岛一样寻求和他人的交流,又不可能在“读心术”的意义上实现完全的交流。
在国际学界,现象学视野下的“交往—传播”研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欧陆传播学研究向来视现象学传统为自身的基础理论资源,这里不去讨论。即便近些年传播学界兴起的以“媒介化世界”(mediated worlds)为题的媒介化(mediation)研究的新潮流中,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胡塞尔现象学在其理论成型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石作用,以此证明现象学传统在当代传播研究中的活力。当前欧洲媒介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克豪茨(Friedrich Krotz)清楚地点明了媒介化世界概念根植于现象学的传统之中:正是基于现象学的社会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诸世界”(social worlds)的概念,我们才能够有根据地对社会诸世界的各不相同的交往形式进行研究①Andreas Hepp, Friedrich Krotz, Mediatized Worlds,Culture and Society in a Media Age, Basingstoke, Hants: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84.。现象学和传播研究不是我们需要通过摆渡联结起来的不同研究论域,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一点为专业的传播学史观察者所认可。史多格斯(Jessica N.Sturgess)总结道:“现象学是传播研究的天然之家,因为如果不把传播当做题中之意,也就是不能去做现象学。”②Jessica N.Sturgess, “In Defense of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p.1-18.在国内,哲学领域内的胡塞尔研究已经深入到各个具体的细部,但是对胡塞尔传播思想的考察,尤其是胡塞尔对于传播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的可能贡献,目前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讨论。下文将从意义—交互主体—生活世界三个关联点出发,指出现象学的传播哲学在元理论层面上的特质。
二、“意义”的交往
“现象”(phenomenon)同我们熟悉的英文词“photo”(光片,照片)有相同的词根:它们都起源于希腊文的 “phos”(光)③“Phos”, in A Greek-English Lexicon, compiled by Henry George, Liddelland Robert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1968.。胡塞尔的高徒海德格尔对“现象学”这个概念作过有趣的解说。海德格尔就构词法,把“Phänomenologie”拆分成“Phenomen”和“Logik”两部分。按照海德格尔的解读,“现象”的原意是“什么东西显示在光之中”,“现象”意味着自身显现(das Sichzeigende),而作为“logos”的“Logik”的原初意涵则是“使在语言中照面”(sehenlassen)。综合起来,现象学就是对自身显现的事情如其所显现地进行理论(语言)把握④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5-47页。。现象学不认为现象和本质有对立关系,否认现象背后还有隐藏的本质这种二元论,而是认为对象的本质就是如其所显现本身⑤萨特:《存在与虚无》,杜小真、陈宣良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页。。更进一步,向着主体意识显现的对象首先是“意义对象”(Sinnobjekte)。在现象学的语境下,所谓“意义”是指对象的原初给予不是纯粹物(bloßes Ding)或者事件,而总是已经被赋予意义(das Aufgefasste)和理解(das Verstandene)的东西,“作为”(als)意义对象而显现。桌子显现为红色的桌子,而不是与我的理解无关的自然物;罗密欧显现为朱丽叶的爱人,显现为在“爱”的意义生成中的两个相互交往的人。因此,现象学的意向性,不仅仅是指意识活动总是指向某个对象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在指向中总是已经把对象理解为意义以及意义关联中的对象。在理论反思中,把主体和对象关系首要地理解为意义关系,是现象学的独创。胡塞尔现象学对“交往”概念的深刻见解,来自于它在意向性概念下对于“意义”的扩展和改造①Garnet Butchart, “Communication and the Thesis of Intentionality in Husserl, Sartre, and Levinas”,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2016, Vol.17, No.1, pp.56-73.。现象学的“意义”概念,不仅仅是语言哲学(语义学)的概念。意义是有独立性的,意义的显现不是主体的任意创造,或者单纯的约定,相反,意义是显现给主体的,我们生存于“意义空间”之中②澄清“意义空间”(space of meaning)的概念属于哲学的核心工作。Steven Crowell 指出,新康德主义的“有效性领域”、塞拉斯的“理性空间”(space of reason)、胡塞尔的“先验意识”和海德格尔的“世界性”都是在相似的意义上刻画“意义空间”的概念。Crowell还指出,对“意义空间”的辩护是反对将一切对象的本质都还原为自然主义态度下的自然科学的遵循因果律的对象。参见:Steven Crowell, Husserl, Heidegger, and the Space of Meaning:Paths Towar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我们的生活世界首先是由意义的有效性构成的世界。在胡塞尔看来,意义的有效性领域定义着我们的“交往”领域。
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交往理论的基本论旨,在于指出交互的意义构成是如何可能的,它的条件和本质结构是什么。因此,对于胡塞尔现象学来说,现象学的交往理论,其研究对象是主体性与世界的关系本身。现象学的工作就是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出发,或者说,从反思的观察(self-reflection)出发的,对主体性(subjectivity)的交互意义构成进行考察。正如阿诺迪(Jakob Arnoldi)指出的,现象学的反思概念关注的是“作为行动者的主体的感知、解释、适应以及对他者的回应”③Jakob Arnoldi, “Sense Making as Communication”, Soziale Systeme, 2010, Vol.16, No.1, pp.28-48.。以胡塞尔现象学的奠基性著作《逻辑研究》为例,胡塞尔在第一研究中分析了符号的交往功能的重要性。胡塞尔坚持:讲出来的声音或者书写的记号是有交往功能性的(kundgebende Funktion),因为它们揭示了说话者有要表达一定东西的意向。所有的符号——包括作为表达起作用的符号、表情手势,更不用说以符号为载体的媒体——从本质上说都是交往性的,而交往总是和其他意识(主体)的交往。很明显,胡塞尔把交往概念领域拓展到了“符号—意义”的全域。
三、个体的共在
如上文所言,讨论“意义”必然将我们带到对“主体和他者”关系的论题。在自然态度下的朴素世界观里,我们通常把主体的意识和心理状态设想为内在的、私人的。这一点在哲学上被称为“唯我论”(solipsism):个人被理解为原子,相互处在一种意识的不相关的私人状态,即我不知道你的意图和思想,你也不知道你的意图和思想。在这个背景下,“交往”意味着通过媒介(medium),使我们的意图和思想的相融合,使个体走出自己意识的“黑匣子”,理解他人。由此而来,“交往”被理解为使我们能够交换各自“意向内容”(intentional content)的“行动”(action)。显然,唯我论式的自身理解是不受欢迎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反思的贡献,恰恰在于发现作为主体的“我们”,从一开始就处在与他者的原初联结之中。我和他人的关系不是后来添加的,而是与自我共生的。这种“关系”使得在现象学中凝结出了对后进的社会理论影响深远的德文术语:Intersubjektivität(交互主体性)。在现象学的反思中,交互主体性揭示的是主体同他者之间的意向性关系。主体和他者的交往在胡塞尔那里等同于主体和他者之间的意向性关系。“意向性”作为现象学的核心概念,是指意识在对象性的关系中使意义呈现的行为(noesis;making sense),或者说,是意识相关项(noema)在相对于意识活动的条件下,自身向着意识主体的呈献(self-giving of sense)①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68-173页。。具体到交互主体性,他者在意向性中呈现为另一个有意义的“我”。基于此,现象学奠基的“交往”概念,是在自身意识(self-awareness)和他者理解(understanding of the Other)的一体两面中展开的“意义关联”。与他人的交往,意味着对他者心灵的通达。他者心灵的感知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哲学话题。这里,胡塞尔既反对(1)把这种通达理解为直接的感知,又反对(2)把这种通达理解为通过类比而实现的推断。第一种观点无法接受的原因非常直观,我们并不能像感知具体的对象一样(例如,我看到一个苹果),那么确证地直接感知他者的心灵内容。他者的心灵作为感知对象有一种天然的“陌生性”(Fremdheit)。第二种观点在哲学心理学中被称为“类比推理”(Analogieschluss)。这种观点同样无法接受,因为在胡塞尔看来,我们并不是先有了自我的概念,然后简单地通过类比把我的自我投射到他者那里,从而获得我对他人的理解。换句话说,在胡塞尔看来,我对他者的理解作为人的交往活动可能性条件,绝对不能仅仅从个体经验出发,通过作为理智活动的类比推导而得到。
既然对他者的构成,或者说,他者经验(Fremderfahrung)构成了交往中的你我的基本经验。那么,胡塞尔如何证实和解释这种我与他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呢?首先,胡塞尔明确肯定,“我思”的意识领域是我理解他者经验的根本出发点,我思是我的本有区域(Eigenheitssphäre)或者说原初区域。他者通过对我的意识经由身体的触发(Motivation,“推理”的相反概念),通过我的通感的意向性经验的综合而被我理解。虽然我对于他者的通达必然是通过我的意识,这看起来与“唯我论”的立场相去不远,不过,这却不是胡塞尔的真实立场,而是传统哲学术语自身的历史重担带来的误解②长久以来,德语社会哲学家们对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理论多有批评。他们的核心关切是“社会性”(Sozialität)能否从交互主体性中获得充分理解。托尼森(Micheal Theunissen)是这种解读的始作俑者。他批评胡塞尔对他人的理解无法超出“唯我论”构成活动,因而无法真正的理解社会性构成。参见:Micheal Theunissen, Der Andere: Studien zur Sozialontologie der Gegenwart, Berlin: de Druyter, 1977.。胡塞尔强调我的本有范围,目的是指出我自身作为第一人称的视角不可替代。他人作为交往经验中的对象,只能向着我的显现。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此在是向来属我的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55页。,我不可能从他者的视角去经验他者。我的视角的优先性,不意味着我自己是一个孤立的原子,一个需要打破孤立寻求和别人交往的自我。相反,我总是已经在最基础的意义上被构成为一个共同体中的与他者共在的一个“自我”。换句话说,我正是在和他者的交往中成为“自我”。个体的自身意识与和他者的共在不是对立的此消彼长,相反,个体与他者是共同构成的。胡塞尔的这一论断,实际上在当代的媒介研究中不但得到了佐证,而且得到了拓展。例如,迪茨(Mark Deuze)指出,在媒介生活(media life)时代,即便个体在网络中经历着身份的去个体化(deindividualization),使得网络上的个体看起来与现实中的他者不再相关,但是事实上,个体对交互主体的需求仍在。恰恰是媒介(media)所代表的他者(the other in media)填补了交互主体的需要。经由媒介,他者变得更加宽广,它不但可以是社会机构、一条狗,也可以是抽象的集体思想(collective intelligence)④Mark Deuze, Peter Blank, Laura Speers, “A Life Lived in Media”,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2012, Vol.6, No.1,pp.1-37.。
更进一步,胡塞尔对交互主体性的“交往”的考察不是抽象辨析。胡塞尔发现了交往中的自身—他者关系是通过“移情”(Einfühlung)实现的。移情这个词中“ein”是“进入”,“fühlen”指感觉,从构词法上已经显示“移情”的基本意涵,即进入对他人的知觉中。胡塞尔从利普斯(Theodor Lipps)那里借用了这一概念。利普斯和胡塞尔都反对从“类比推理”的进路来解释陌生经验。二者都主张对他者经验的“有中介的”直接性,但是二者对于通感的具体机制的解释非常不同。利普斯认为他者经验是本能地把自身的体验投射到另外一个他人的身体上,而胡塞尔则认为,我们的他者经验从根本上是“非直接的统觉的移情”①Rodulf Bernet, Iso Kern, Ernst Marbach, Edmund Husserl-Darstellung seines Denkens,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16, pp.147-148.。这种移情首先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我不可能无媒介地感知到他人的经验,我的身体(Leib)和我感知到的他者的身体(动作、表情、姿势等)是交往的媒介。我和他者的交往不是读心术,我们不能隔空言说,而是有我的身体作为这种交往的媒介。我感知到他者的活的身体与我的身体之间的相似,会促发我在统觉活动中理解他者的经验内容。但是胡塞尔强调:“在相似基础上的类比的共觉知不是推论,不是思想行为”,而是“一下子的把握”②Edmund Husserl,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 2007,p.140, pp.143-145.。我的身体和他者身体的原初配对(Paarung),让我基于我的身体的原初体验来获得对他者经验的理解。我对他者经验的把握和我对他人身体的感知,在本质上是一体的,这就是胡塞尔《笛卡儿式的沉思》中通过“共觉知”(Apperzeption)、“共在现”(Appresentation)这样的术语意图表达的内容③Edmund Husserl,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 2007,p.140, pp.143-145.。
综上所述,我和他者原初的交往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感知类型。这一点惟有在现象学视野中才能得到合理揭示。需要补充的是,胡塞尔告诉我们,我和他者的基本交往经验来自于移情的结构,需要经由身体实现。不过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交往都需要身体介入,在交往的最为常见的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语言的介入。从基本的以交换命题内容为目的的言说,到网络时代的大众传媒,都属于以语言符号为主要媒介的交往活动。胡塞尔的工作强调的是身体对于交往活动的基础性特质,即任何基于语言符号的交往—传播活动都建基于身体—移情之上。胡塞尔同样分析了“交往”的意义是如何在身体—移情的基础上向上建构的。任何一个成熟的人类主体和他者总是已经处在具身(embodied)的共情层次上的交互关系(correlation)中,这是哲学式的思考“交往”意义的原点。作为共主体的个体通过意向性的交融在不同层级的意义上构成一系列群体的建制,从家庭、到族群、民族再到政治团体、国家等,并且由此衍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特质。
四、生活世界作为“交往”概念的视域
“意义”和“交互主体性的移情理论”解释了现象学对交往概念的基础规定,然而这并非全部。对于“交往”的讨论往往是在忽略视域的情境下,对于主体意向性活动的质性规定。现象学的交往概念,在胡塞尔的眼光中,需要引入作为意义语境的“生活世界”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生活世界既是交往活动发生的场域,规范着交往活动,同时也是由原初交往活动的意义沉淀所构成的。以胡塞尔晚年对“生活世界”概念的成熟使用来看,“生活世界”概念形成的动因是胡塞尔对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缘起、本质及有效性的彻底反思,以及胡塞尔通过对意义原初性的考察,试图重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统一关系的努力①Rodulf Bernet, Iso Kern, Ernst Marbach, Edmund Husserl-Darstellung seines Denkens, pp.199-201.。生活世界可以较为清楚地理解为:与客观的精确的自然科学世界相对的、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展开的世界②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Dordrecht: Kluwer, 1993, p.129, ff., 463, 466, p.127.。以理念化为前提的近代自然科学本身不是胡塞尔批评的对象,胡塞尔要批评的是:人们遗忘了理念化的自然科学的原初意义,并且把整个科学对象都置于客观的实证主义的气氛中,由此放逐了主观—相对的内容。众所周知,胡塞尔把自己的哲学称为“超越论的现象学”,其根本特征就是要通过对主体与世界的原初关联的回溯,找到客观性对象的来源。胡塞尔说:“真正第一位的东西是对前科学的世界生活的‘单纯主观的—相对的’直观”③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Dordrecht: Kluwer, 1993, p.129, ff., 463, 466, p.127.,“所有对象性的客观之物,都在其原初的、向经验主体的回溯性中给予自身”④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92页。。自然科学对主观—相对的关联性视角的遗忘会导致客观主义视角的单面地绝对化。生活世界的经验被遗忘,导致了自然科学乃至科学整体都无法理解自身的原初意义,这种糟糕的状况被胡塞尔称为“欧洲科学的危机”。这里胡塞尔不是要反对或者取消科学本身的客观性,而是批评客观视角的唯一性的霸权。由此而来实际被遗忘的也是主体的交往对于意义生成(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巨大意义。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为什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积极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生活世界的概念作为一个非特定主题的视野把文化、社会和人、具体地说,“文化的再生产”“社会融合”以及“个体的社会化”等都包纳于其中,这些论题恰好是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感兴趣的。生活世界比起“生活形式”“文化”“语言共同体”等概念更为复杂更有承载力⑤Sebastian Luft, Maren Wehrle, Husserl-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 Stuttgart: J.B.Metzler Verlag, 2018, p.334.。无论哈贝马斯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作了何种改造,“生活世界”概念都紧紧抓住了所有意义生发(Sinnstiftung)必须由之出发的前科学的有效性,保护了一个不言自明但极易遗忘的事实:即我们的日常实践所展开的世界是交往意义的源泉。
就传播学而言,胡塞尔通过对生活世界的揭示,从根本上辩护了一门有别于客观化的自然科学的传播学的领地。因其对“人的交往”的关注,这门科学不仅可行而且是必要的。它具有自身的论域和权利,但是,“交往—传播”绝对不能只是从“行为主义”“实证主义”的进路来理解,其更为本质的规定在于生活世界中的意义、历史的生成⑥胡翼青:《显现的实体抑或意义的空间: 反思传播学的媒介观》,《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第30-36页。。
五、现象学作为可用的“元理论”
触发本文写作的动机是,揭示现象学与中文语境中的传播学元理论之间的实质关联。无论学者们对“元理论”的概念的界定是宽松还是严格,是抽象还是具体。倡导元理论在实质上成功地开启元理论这一论题,成功地让对理论研究的反思本身破土而出。正如芮策(Ritzer)论述道:元理论的一个好处在于,它能够增进我们对于影响理论发展的那些因素的“理论自身意识”(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并且使得这些因素更能够经得起批判的分析①George Ritzer, “Sociological Metatheory: A Defense of a Subfield By a Delineation of Its Parameters”, Sociological Theory, 1988, Vol.6, No.2, pp.187-200.。在这一意义上,仅仅鼓吹现象学可以是一种元理论还是不充分的,毕竟对于基础层次的“交往”概念的界定和讨论不是现象学独有的,尽管现象学的界定在哲学的意义上有优势。我们还应该去展示现象学不仅可以作为元理论,而且是强势的元理论备选方案,这就需要展示现象学在建立起影响理论发展的“理论自身意识”方面的具体效用,这样才能真正说明现象学元理论不仅不是任意的,而且是有力的,对我们当前反思传播学研究的方向和话题是有益的。
当然,最为直接地阐明和辩护现象学元理论的方式是用现象学视角来分析当前传播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下面以传播学的身体研究为例。
传播学最新的研究兴趣聚焦在“作为媒介的身体”这一论题。毫无疑问,交往主体从一开始就是具身化了的主体,身体从来就是作为中介的媒介。但是,这一基本的共识在单个人作为传播主体的时代是不受重视的,而在面向未来的新技术时代,我们应当主题式地把身体当作不可或缺的传播理论要素重新纳入传播研究中来②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第37-46页。。甚至,“身体研究,正是我们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寻求学科突破创新的一个基点”③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12期,第83-103页。。身体研究对于传播学来说,如果有关乎学科性的意义,那些传播学视角必须有能力揭示新的事实,使得人们能够信服,身体概念的这个面向只能在传播学研究中被揭示。换句话说,什么是传播学的身体研究的特质?面对这个不得不提出的问题,“元理论”思维已经或隐或现地无可回避。那么从胡塞尔的现象学来看,究竟什么层次上的身体才是媒介研究应该关注和能够处理的问题域?
首先,可以相信,不少传播学者都认同利文斯通(Livingstone)的观点,没有任何东西真逃得出媒介的中介,也没有任何一个已有的学科真正像传播学一样认真对待和研究了媒介,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最终会找到道路来到传播学门前,虚心向传播学者求教应该如何研究媒介,毕竟传播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该是传播学反哺其他学科的时候了④Sonia Livingstone, “If Everything is Mediated, What is Distinctive About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1, vol.5, pp.1472-1475.。
利文斯通的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童年到战争,从政治到性别,从科学到宗教”所有的事物都是媒介化了的,到任何东西都必须通过Imprint,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认为:(1)一切对象都应该不加限制地成为传播学的研究主题(这一点毋庸置疑);(2)更重要的是,从现象学的观点来看不是所有中介化过程都一定构成对被中介对象的产生影响,以至于不研究媒介化过程,就没法研究媒介化的对象本身。简单说,并不是所有Imprint都重要,并不是对所有的东西研究与解释都需要考虑Imprint 的要素,带上眼镜并不意味着我们看到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来看,任何意向性的行为都是包含了中介性的,中介有时候是一个沉默的非主题要素,有时则对意向性关系构成决定性的影响。
在上述的意义上,身体作为媒介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应当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中介,而应是一种可以重新塑造主体和世界之间的意义关系的媒介。后者是传播学的身体研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尽管胡塞尔现象学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把主体系统地刻画为具身性的主体(embodied subject),确认了具身性是意义—交互主体—生活世界这一结构性中不可获取的结构要素,但是胡塞尔现象学本身的身体理论对事关学科性的“身体研究”不直接相关,因为胡塞尔本人并没有足够充分地关注过“变动中的身体”对意向性关系的影响。克雷格(Robert Craig)在论及现象学的媒介理论时,没有提到“身体”论题不是“遗憾地掠过了”①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第83-103页。,而是因为经典现象学(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理论并没有把身体可能发生的颠覆性的技术化当做常态来分析。即将到来的可能是一个“完全具身地置入到技术之中”②Dan Ihde, Husserl’s Missing Technologie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p.77.的时代。而这一点恰恰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变得可想象,甚至可实现。也正是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针对哲学辩护传播学的理论独特性③Friedrich Kittler, “Phänomenologie versus Medienwissenschaft”, 2023-10-01,http://hydra.humanities.uci.edu/kittler/istambul.html.。因此,在元理论视野下,我们必须重点突出的是,在根本上牵引着传播学身体研究的动力在于新技术的崛起④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第83-103页。。总结起来,不是身体忽然成了我们的兴趣点,而是技术化把沉默的身体本身放在了“座架”(Gestell)之中⑤Martin Heidegger, “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Stuttgart: Klostermann, 1954, pp.9-40.,身体问题是从根本上是媒介本身的技术化问题。这种技术化甚至已经到了取消传统哲学的“身体”概念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以身体为研究对象的知识论,以及在自然化的知识论意义上的认知科学的研究,与传播学的身体研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这一视角下,专属于传播学的身体研究的方向就是非常清晰的。哲学家们已经非常充分地说明了,身体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主体通达世界的媒介;而传播学不同于哲学家,传播学的核心命题则围绕着“身体与技术的耦合”(人机交互、甚至赛博人),把“变化的身体”纳入到实质性的考察中,考察它对主体与世界关系(包含各个层次)的颠覆性变化。对这种颠覆性变化的当下式的考察和解释,是传播学的身体研究的优势,是对规范性的常态下哲学的身体研究的批评和翻转。
其次,在方法论上,现象学元理论对建立传播研究的学科性特质有所教益。利文斯通也强调了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信息技术作为最重要媒介的环境。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媒介不是在媒介中呈现的对象。因为媒介作为研究的对象,自身是拒绝被对象化的,所以我们的研究要把媒介的媒介性揭示出来,而不是把媒介当作客观世界中的“物”来研究。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传播学的身体研究。胡塞尔的感知理论揭示了如下观点:媒介研究的对象非常特殊,就如同画作与它的画布油彩,眼镜和戴上眼镜看到的东西,只要我们在欣赏画作,作为媒介的画布油彩就是不显现的,只要我们在无障碍地观看,作为媒介的眼镜就是不被当做主题感知的,只要我们在玩电子游戏,我们的手拖动鼠标,眼球随屏幕视角的转动就根本不被关注。一旦我们希望把媒介主题化加以研究,作为活生生的媒介就消失了,一旦我们把身体对象化,作为媒介的身体就必然地变形为作为对象的客观的身体。正如胡塞尔强调的在交互主体理解中强调的第一人称视角,我们对媒介的非主题经验首先依然是第一人称的经验,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collective)。对媒介的最初理解,不能脱离第一人称的体验特征。
如果我们去研究,电子游戏这种电子产品产生的社会影响,我们不仅已经脱离了第一人称体验,而进入到第三人称的观察视角,因而已经把媒介彻底对象化为“社会—物”,并且超出了交互主体关系,进入到社会层面。从学科性的角度,对媒介的研究应当从对媒介的经验出发(medium in experiencing),至少这一经验是最切近媒介概念的,并且常常被忽视的。
六、结语
现象学的目标与指向是理解着的意识经验,即主体和世界的活生生的意义关联。正如兰斯多夫(Lerone Langsdorf)概括的:“意义总是在文化上被特殊化的,在道德上被定调的意义,在社会关系中被协商的,在地域上被界定的。因此,现象学的交往研究试图提供深入细致的描述来辩明他的活动的经验中发现的秩序。”①Lenore Landsdorf, “Why Phenomenolog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Human Studies: a Journal for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1994, Vol.17, No.1, pp.1-8.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可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严格的框架,让我们可以把人类交往中的情境、内容、实践以及体验置入批判的反思之中。
胡塞尔的这一概念框架可以作为传播学元理论的一种选择,不过这里的“元理论”首先在于帮助我们彻底理解“交往—传播”这一人类活动的根本面向,而不在于作为学科基础理论来形成学科认同。不能忘记的是,传播学的形成从一开始就是实践性质的,即便上文论及的身体研究也是在技术实践成为可能的前提下被激活的。必须说传播研究作为学科,是历史性的存在,但是它绝对不是观念史,而是社会—实践—目的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传播研究中“理论理解”与“应用实践”的分裂是由来已久的。传播学从一开始包含着关注公共言语的效用、关注修辞和完成其有价值导向的社会功能的动机,有着明显的实践导向。因此,指望任何“元理论”在重塑学科统一性和认同方面发挥作用都显得过于理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元理论”或者说“中心理论”可有可无。“元理论”能够让我们保持对这种实践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的“自身意识”。“元理论”首先是教导意义(in the pedagogical sense)上的,而非学科基石意义上的。只要不在后者的意义上诉诸“元理论”,那么各种各样的元理论就可以成为传播学发展壮大的养料,有着丰富的意义值得去发掘。在这方面,如果错过了现象学,如果不把现象学思想当下化到蓬勃发展的传播研究中,将是非常遗憾的。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