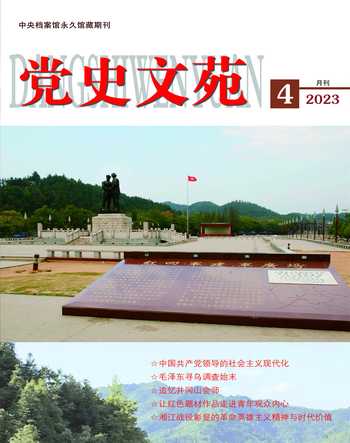廖仲恺遇刺案对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萌芽的影响
秦正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面临的凶险严酷的生存环境,让共产党人对隐蔽斗争的重要性有了与生俱来的深刻认识,从而使党的情报保卫工作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那么1925年8月发生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案,则如他山之石,更进一步警醒了共产党人,对党的早期情报保卫工作在广东地区萌芽产生了催化作用。
1925年8月20日上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从广州东山寓所出发,驱车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惠州会馆,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6次会议。
途中,遇到廖家的忘年之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党报《民国日报》社社长陈秋霖。陈秋霖所乘汽车抛锚,正沿着仓边路步行前往惠州会馆参加会议,廖仲恺夫妇遂邀陈秋霖同车前往。
三人乘车抵达惠州会馆门前相继下车,廖仲恺、陈秋霖迈步走上台阶,何香凝与一位女性熟人寒暄。
就在这时,事先埋伏在会馆门柱和栅栏后面的四五个刺客冲了出来,举枪便向廖仲恺、陈秋霖射击,一连打了20多枪。廖仲恺身中四弹,在送往东门外百子路公医院的途中身亡。陈秋霖腹部中弹,三日后不治身亡。
这就是大革命时期震惊全国的廖仲恺遇刺案的大致过程。
如今,“廖案”已过去98年,但诸多谜团仍未破解,其历史影响也还在探究之中。98年来,人们对“廖案”的方方面面都在进行着考证,却很少有人提到,更少有人知道,此案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情报保卫斗争实践所产生的影响。
共产党原本就有一根隐蔽斗争的敏感神经
“地下党”这个词,现在常常出现在文学影视作品当中,被人们用来专指隐蔽战线或情报人员。殊不知,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全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下党”,遭受到内外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人员被迫害,组织被取缔,刊物被查封。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其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时,被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逮捕、关押,其主编的《新青年》编辑部被查抄。经各界人士营救,陈独秀3个月后才获释,被迫离开北京转至上海。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往上海。1920年2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禁令,查禁了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等83种“过激印刷物”。
1921年7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住处开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正要讲话,一位身穿灰色竹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以寻找“社联王主席”为由突然闯进了会场,然后连称找错了地方,慌忙致歉后匆匆离去。隐蔽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当即提出休会、转移。后经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改到了她的家乡嘉兴南湖红船上继续进行。代表们撤离之后大约15分钟,之前假扮成“不速之客”闯入会场的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卿便带着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巡捕开车前来,堵住前后门,入室搜查,所幸一无所获而去。
1921年10月、1922年8月,时任党的最高领导的陈独秀先后两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期间,1922年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刚刚在上海成都路上挂出招牌便遭搜查,随即被英租界封闭。1922年7月,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发行了4期后就被巡捕房查禁,被迫由上海迁往北京,因北洋政府镇压革命难以立足,又于次年迁回上海,随后上海局势恶化,又被迫迁往广州。
北洋政府和租界巡捕房的查禁与抓捕,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始就面临着什么样的凶险处境,证明了一个“地下党”的“生”有多么的艰难,“存”又有多么的严酷。
面对凶险环境,共产党人在建党初期就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保密防范措施。1921年到1924年之间,中央与地方党团组织之间的绝大部分信函来往,抬头和落款已经开始使用代号和化名。普遍称上级为兄,下级为弟。中共中央用过的化名有“钟英、大兄”,团中央用过的化名有“宗菊、曾延”,中共广东区委称“管东渠”,中共上海区执委称“枢蔚”“朱坤”,香港团委称“香弟”,花县团委称“花弟”,等等。称马克思为马氏,称全国代表大会为大考,称会议代表为考生。1923年3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抬头称对方的化名光亮,落款则用了自己早年在湘乡和长沙读书时曾经使用、后来用作笔名、化名的“子任”。“五卅”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期間,经常以打麻将掩护会议。一次很晚散会后,他送与会的向警予等同志出弄堂,一面走,一面故意说:“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是不出来……”。直到弄堂的看门人打开铁门放向警予等人出去,他才不谈打牌的事了。
正是这残酷的生存环境,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伊始就有了根深蒂固的生存危机感,造就了党对隐蔽斗争的敏感神经,激发出共产党人强烈地保存自己、反制敌人的意识和能量,使后来党的情报保卫工作的产生成为历史必然。
“廖案”的发生进一步给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
如上所述,“廖案”之前,中共对自己面临的凶险生存环境已经有了认识,但只是采取了一些被动应对的自我防护措施,还没有认识到建立专职情报保卫机构主动反制敌人的必要性。
“廖案”发生后,共产党人参与了从侦缉到审判的全过程,从中深刻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直接掌握情报保卫力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后来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创建者、领导者于一身、被称为党的隐蔽战线统帅的周恩来,作为特别法庭检察委员会成员亲自参与了案件的审理过程。
中共早期活动革命家、理论家杨匏安,作为特别法庭审判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嫌犯审讯工作。在国民党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匏安代表审判委员会作了廖案侦缉情况的说明。
中共早期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杨殷,在“廖案”调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殷在案发前就得知国民党右派分子聚集在中山舰上密谋暗杀廖仲恺。他随即把这一情报通报给了廖仲恺本人,廖凛然表示:“暗杀便暗杀,余复何惧!” 廖仲恺遇刺后,杨殷利用其广州市公安局顾问的身份组织力量侦破案件,迅速查获有关凶犯胡毅生的确凿证据,使许多案情真相大白于天下。
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另一位先驱陈赓,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连续几夜没睡觉,带领他的黄埔连队迅速捕到另一涉案要犯林直勉,并搜集到大量翔实材料,终于揭开了廖仲恺被刺的黑幕,显露出过人的情报保卫才华。据说周恩来曾满意地表扬他说:“我看你会成为中国的契卡。”
廖仲恺当时是身兼诸多要职、能够影响全局的重量级人物。在国民党内,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农工部长。在广州国民政府里,他任财政部长、广东省省长。他還兼任着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和黄埔军校党代表。即便是这样权倾一时的国民党元老,在事先已有预警、随身跟随护卫的情况下,仍未免杀身之祸,这对当时的共产党人震动很大。何况,案件侦办过程中,有的嫌犯还供出,国民党右派下一步的刺杀目标就是共产党领导层,这更加剧了共产党人保卫自身、反制敌人的危机感。
廖仲恺遇刺案,使共产党人深化了对情报保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了建立自己的情报保卫力量的紧迫感。
“廖案”发生不久,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印发的系列决议案之《组织问题议决案》(八)指出:“最近各工业区军阀及资本家反动高压政策……这反动既来,我们便要在某几处地方转入秘密工作……我们应当预备秘密机关,同时竭全力去做公开的政治运动。”
中共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提出建立秘密机关,虽未明确落实这个秘密机关的具体措施,却表明当时的共产党人对于建立秘密工作机构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1926年春,广东区委决定建立情报小组,委派从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后回国的傅烈、杨殷负责,重点搜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在广东地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保卫工作。
关键少数的远见卓识起到关键推动作用
周恩来和陈延年最早从“廖案”中洞察到了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成为广东区委情报保卫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和决策人。
早在觉悟社期间,周恩来就有了隐蔽斗争意识。为避免引起反动当局注意,他提议同学们弃用原有姓名,用抓阄的方式,每人从1到50这50个号码中抓取一个号码,作为各自的化名。周恩来抓到5号,遂化名“伍豪”。这便是“伍豪”这个传奇化名的来历。
留法期间,周恩来受命秘密发展党员,暗中联络中国工友,组织护送党员和进步人士赴莫斯科学习。这期间,为躲避法国警察的抓捕,他经常走街巷、入工厂,乔装打扮,隐蔽转移,初步经历了地下斗争实践。
回国后,两次东征的经历和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职责,使周恩来在肩负军事领导工作的过程中,认识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加之这一时期,国民党右派不断破坏国共合作、肆意攻击共产党,更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和忧虑。参与“廖案”审理的过程中,周恩来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建立党直接领导情报保卫力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时任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是很早就在凶险的工作环境中树立起了隐蔽斗争意识,练就了一些隐蔽工作技能,为他日后洞察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造就了一副敏锐目光。
还是在留法期间,他就曾化名林木,从事秘密革命活动。1924年底,陈延年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同船由广州抵达上海后,陈延年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遂用暗语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与组织取得联系。郑超麟晚年回忆:“宣传部的张伯简在《民国日报》看到一则广告:‘马道甫兄:我已来到上海,住在某某地方。’ 署名是林木。张伯简知道马道甫是我的俄文名字,于是把延年接到宣传部我住的地方来。”
在广东区委工作期间,陈延年很注意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轮换使用过“林木”“陈东”等化名。在《人民周刊》《革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时,陈延年多用“林木”为笔名。参加公开活动时,则多以“陈东”为化名。1925年5月17日,他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陈东的名义,参加了青年军官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同年10月,他以“陈东教授”为名,为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班作了政治报告。
他还给自己定下“六不”,即不照相、不闲游、不谈恋爱、不滥交名人高朋、不讲究衣着、不下馆子,主要考虑之一就是要少曝光、少接触人、少被关注,体现出强烈的隐蔽斗争意识。
“廖案”的发生对身处“廖案一线”的广东区委震动最大,加之“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不断加剧,矛头进一步指向共产党人,在周恩来、陈延年的决策和推动下,广东区委迈出了探索党的情报保卫道路的最初几步。
第一步,是开展了最早的专业培训。俄罗斯历史学博士维克托·乌索夫撰写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披露,当年活跃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团,除了“按红军模式训练中国军队”之外,还肩负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使命,那就是帮助中方建立“现代情报与反间谍系统”。1925年11月,共产国际在广东举办了情报与反谍骨干速成班,课程包括武器、射击、破坏行动、秘密工作基本原理、保密规定、情报工作与反间谍工作原理、情报基本理论、密写等等。广东区委选送了一批“工会会员、农民组织成员、罢工者”参训。
第二步,是成立了区委情报小组,委派在苏联学习过政治保卫工作的傅烈、杨殷为负责人,重点搜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共产国际情报与反谍骨干速成班毕业生中,就有7个人被分配到情报小组工作。
领受任务后,傅烈带领情报小组人员,奔波于广州、黃埔、东莞、石龙之间。他有时西装革履,出没于茶楼酒肆;有时戎装佩带,进出于军港要塞;有时青衣小帽,往来于平民百姓之家。杨殷从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中挑选了一批工人骨干,派至粤港澳各地设立情报站。杨殷还安排一些同志打入反动当局的公安局、卫戍区司令部等要害部门,为及时获取敌人的行动情报,转移组织、营救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时期情报小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区委正确判断应对形势,提供了及时准确的决策依据。
广东区委情报小组,虽只是一个区域性情报机构,肩负的任务局限于搜集广东地区政情、社情、民情、军情,获取情报的手段也比较单一,在组织实施层面还缺少整体筹划,基本上靠小组成员单打独斗,也还没有形成系统、深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策略。就像乌索夫评价的那样,这个情报小组只是一个“初期”“尚不高明的谍报机关”。然而,正是这个“尚不高明”的情报小组,成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的始发站,代表了从无到有的蜕变。
第三步,就是赋予了地方党团组织以情报搜集任务。这一点,在第二次东征期间体现得尤为突出。关于这个问题,江志如同志在《党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广东早期情报工作事证》一文中,详细列举了大量有价值的史实。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显示,第二次东征期间,即1925年10月、11月、12月,根据广东区委的统一部署,潮州、汕头、厦门、顺德地方团组织连续向团中央或广东区委上报情报,内容包括敌情、政情、经情、社情、民情、舆情,还有孙文学会的详细情况,包括其宗旨、组织机构及负责人、例会、人员分组等。这其中,既有动向情报,如敌军推进、回防、驰援情况;也有综合研判,如对厦门报界态度的分析,对潮汕可能参加暴动的工农人数的推测,对北洋军阀海军战斗力的判断;还有对策建议,如怎样应对孙文学会的活动等。
从专业角度看,这些情况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而是要素比较齐全的情报材料了。这些事证,充分反映出当时广东地区从党到团、从区委到基层的情报意识和情报能力。
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整理党务案”,要求中共交出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要求各级组织接受这一要求。当黄埔军校的同志就此请示区委书记陈延年时,他坚定地回答:凡是没有公开自己身份的共产党员一律保持常态,绝不能把名单交给国民党。广东各级党组织都遵照陈延年意见,没有理睬国民党右派的无理要求。著名红色情报人员冷少农当时就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秘书,因为没有公开其秘密党员身份,后得以在北伐后打入到军政部(国防部前身)部长何应钦身边任秘书,为红军前三次反“围剿”提供了重要情报。
廖仲恺遇刺如他山之石,给共产党人进一步敲响了警钟,客观上加速了中共早期情报保卫工作的萌芽。周恩来、陈延年、傅烈、杨殷、陈赓等人的开拓性工作,更推动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从无到有的进程,从思想认识、组织机构、人员培训、实践探索等方面,为日后党的专职情报保卫工作的正式创建作了有益尝试和坚实铺垫。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员)
责任编辑/危春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