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挽歌与自然的神性
王士强
出生于1964年的韩文戈创作力非但未见衰减反而愈加旺盛,近五年已出版《万物生》《虚古镇》《开花的地方》三本诗集,而且每本都称得上扎实、厚重。韩文戈出身农村,有着长期的乡村生活经验,乡村是其精神世界的原点和中心,他如一个不辞辛劳、勤勤恳恳的农人一样,侍弄着他的诗歌田地与庄稼,建立起了独具个人特色的“纸上家园”与精神空间。
乡村对于韩文戈这一代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一定程度上他们可能是乡村文明、乡村生活集大成式的承载者和书写者。他们的乡村经验是完整的,对于乡村的感情是深厚的,而在此之后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一代的确具有评论家霍俊明所概括的“尴尬”特征,70后及以后的诗人虽然也有不少出身于乡村,但他们所经历的乡村已处于巨大的历史转型之中,已并非原生态、原汁原味的,他们对乡村与城市的感情和上一拨的写作者相比也是不同的。韩文戈这一代写作者恰恰经历了较为完整、本原状态的乡村生活,也经历了在这之后的历史嬗变与转型,他们的阅历、视野是独特的,其经验的密度、情感的浓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后来的诗人所不容易达到的。就此而言,这一代写作者对于表现乡村文明、乡村生活及其当代处境,具有先天性的优势,也有着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
韩文戈对生他养他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用情极深,可谓呕心沥血,他的写作一定意义上便是为渐成过去时态的乡村文明招魂,他的诗不断地返回起点、返回故乡、返回过往,审视之、缅怀之、歌咏之。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对于韩文戈来说正是如此,他故乡的河流便叫作“还乡河”,他的写作便是一次次地还乡。当然,“还乡”的前提是已然“离乡”,在“离乡”与“还乡”的张力结构中包含了复杂的人生况味。当今时代,农业文明的秩序面临冲击、行将式微已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过时”或者没有生命力了,实际上恰恰在历史的幽暗处、缝隙中才存留着文明的辉光与火种。无论如何,对它的书写已不能不带有一种挽歌的性质。他写自己“孤零零的故乡”:“外边来的人管那叫山,我们管那叫西关山/外边来的人管那叫河,我们管那叫还乡河/外边来的人管那叫风景,叫古老的寂静/我们管那叫年景,叫穷日子和树荫下的打盹儿/外边来的人管那叫老石头房子/我们会管那叫‘我们的家/外边来的人管那叫山谷里的小村/现在,我们会心疼地谈起它,管它叫孤零零的故乡”(《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这里面道出了在当今时代“故乡”所不得不面临的窘境。《种子》一诗写到了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在遥远的春天,幼小的我被放进/爸爸那副担子的前筐/而后筐里,他装满了种子、农家肥/以及给我
预备的水壶、零食/妈妈跟在爸爸的身后,一只母山羊/跟在妈妈的身后,它的奶汁喂养着我/这就是当年我家的写照”,这里面写过去,包含了温暖与深情。而后则写到了现在:“直到我变老,直到我们这代人一同变老/太阳向西移去,黄昏渐渐升起/不绝的种子依旧深藏人世”,这里面包含了深重的叹息,包含了“万古愁”,有着极为丰富、复杂的文化与人生内涵。《包浆的事物》写城里人炫耀把玩的珠串、小把件“有了漂亮的包浆”,作为对比,“在我们乡下,包浆的事物实在太多/比如老井井沿上的辘轳把/多少人曾用它把干净的井水摇上来/犁铧的扶手,石碾的木柄/母亲纳鞋底的锥子,奶奶的纺车把手/我们世代都用它们延续旧日子的命/甚至我爸爸赶车用的桑木鞭杆/这些都是多年的老物件/经过汗水、雨水、血水的浸泡/加上粗糙老茧的摩擦,只要天光一照/那些岁月的包浆,就像苦难一样发出光/只是我们没人挂在嘴上,四处炫耀”,写出了乡村生活“古”与“旧”、“苦”与“难”的一面,其中沉积了历史的沧桑与生存的真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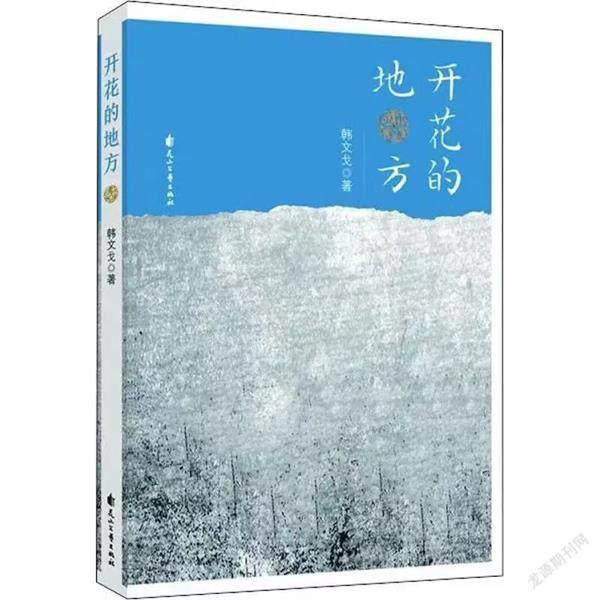
韩文戈诗集《开花的地方》
韩文戈的写作有出处、有来由,不好高骛远,不故弄玄虚,他的诗是扎根于泥土、立足于大地的,他的写作是沉甸甸、有重量的,也是严肃甚至庄重的。韩文戈以其持久地对乡村经验的书写实现了对一种文明方式、生活方式的整体性观照与审视,就其深度、规模来讲,在当代诗人中是并不多见的。这里面包含了他对乡村生活感情之深,而这种深情又是艺术化的,是保持了充分距离的,他以自然、平淡、不动声色的态度表现出来,却更具动人的力量。事实上,韩文戈的创作之所以能保持如此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也是拜乡村经验所赐,乡村生活源源不断地赋予其力量,使得作为诗人的韩文戈底盘稳、后劲足,有历史的纵深感与开阔度,有生命的锐感与厚度。“只有逝去才带来神圣的美和长久的意义”(《月白风清》),乡村文明找到了它合适的“代言者”,韩文戈则成为一个更丰富、更立体、更有深度的诗人,这是一种双向的成全。
在及物性、接地气的同时,韩文戈诗歌还有另外一个维度,那便是形而上、超越性、永恒性、神性的维度。他是《望星空》的人,感知到《朝向未知事物的光》,明白《一种隐秘的力量驱动着尘世》,知晓这一切均《在一种伟大的秩序与劳作中》……他笔下的乡土、自然往往连接更具普遍性的时空,并具有了神性的意味。《开花的地方》颇具禅意,包含了对人生的敏悟与睿识:“我坐在一万年前开花的地方/今天,这里又开了一朵花/一万年前跑过去的松鼠,已化成了石头/安静地等待松子落下/我的周围,漫山摇晃的黄栌树,山间翻涌的风/停息在峰巅上的云朵/我抖动着身上的尘土,它们缓慢落下/一万年也是这样,缓慢落下/尘土托举着人世/一万年托举着那朵尘世的花”,“尘世”之脆弱与强韧、暂短与久长均蕴藏于其中。《我说停,我说岩村》写到自己的故乡和童年:“那里是我死去的童年、少年,故去的父母/那里何其荒凉啊/终有一天,当我们都将不在/而宇宙仍如凌空的大鸟/展开双翅护佑众多星系与星球运转/它的永恒存在对短暂的我昭示着什么”,目光由具体、形而下的层面达致宇宙、星系、星球、永恒,这是对现实生存的提升,也是对终极价值的询问。在《诗的秘密》中关于自己心目中的诗歌他有如此的夫子自道:“我内心之诗的眉目竟如此清晰:/它充盈故乡的气脉,有一个石头的根/大自然的天性,以及它寄托在暂时性里的永恒/除此之外,我狭窄的视野里/还要有个地球,它在太空转呀转,一刻不停”,这里面包含了韩文戈诗歌的若干基本要素,比如“故乡的气脉”“大自然的天性”以及“暂时性里的永恒”。另外的词语“地球”“太空”也是他写作中经常涉及的关键词,在其精神世界中具有重要位置与意义。《落叶》中由“我”的孤独写到了“宇宙”:“我冷,仿佛是我落光了叶子/仿佛宇宙里只有我、树木/以及落向星球与星球之间虚空地带的铁皮叶子/其实我没资格享有这隐秘的孤独/一个人与一个空茫的宇宙/这孤独会使人感到此生尚有些许期待”,这是对于人、对于个体的根本性拷问,也由之而生发出真正的诗意。
在创作谈中,韩文戈曾谈到自己诗歌追求中的“趣味、况味、真味”,并阐释道:“从自然、天性和趣味出发,向外经由对置身其中的诸多尘世况味的咂摸与沉浸,再带着全部生活的疤痕、疼痛与欣喜,尽可能向内返回自身,抵达对生命真味的体悟、陶醉与汲取。”其中确实包含和概括了他创作中的奥秘。他还说:“我时常提醒自己,要尽可能真实生活、真诚待诗,使世俗生活、人类命运与个体存在大致保持在同一个能量场上,形成共振,尽可能去掉所谓诗人的姿态以及某种随之而来的虚荣与膨胀,朴素、自然、本色,像一棵树、一缕光、一声不经意的鸟鸣一样把身心平等放置到万事万物之中。”这里面写到的关于写作与真实生活、世俗生活的关系,个人与万物的关系等都是值得重视的。韩文戈注重“当下的诗意”,而这“当下”里,也包含了永恒,包含了超越性的爱与关怀,他有着深沉的爱,爱着这“温暖而不死的尘世”(《万物生》),虽然“写着力不从心的句子”,但仍“試图以想象的力量抵抗现实的无奈”(《愧疚》)。这是一位诗人的选择,也是诗歌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