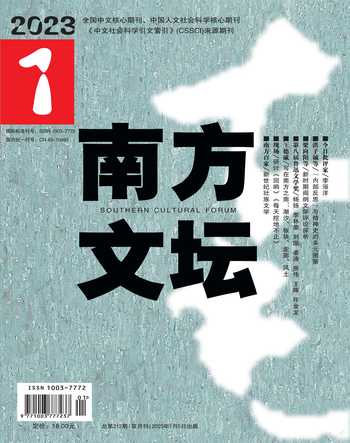学术史的自觉
李浴洋是我的师弟。不过我博士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有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是后来在北京市社科院工作的时候,才有缘认识他。最初是因为北京市社科院图书馆的资源非常有限,经常需要麻烦师弟师妹帮我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或复印资料,就经由介绍找到了他。劳烦他一两次之后,发现他非常能干,而且效率极高,总是第一时间就完成任务,心想这确实是一个“靠谱”的师弟,也就心安理得地把这份差事交给他了。
浴洋办事干练,考虑周全,在认识他的师友圈里可谓有口皆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5年秋天,博士二年级的他在北大中文系的资助和支持下,召集和组织了“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博士生与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读博的时候,由博士生来办学术会议几乎闻所未闻,何况是如此大规模的一次盛会。两天的会议,与会者差不多在一百人上下,快结束的时候,又专门邀请了退休的孙玉石老师来做演讲,把这次研讨会推向了高潮。这可以说是他在学术界的初试莺啼,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此后,浴洋一发而不可收,又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包括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和座谈会,也包括为学术刊物就某一专题组稿,平均每年都有三四次。我自己参加的,就不下十次,经浴洋之手发表的笔谈或论文,也有十几篇。
我与浴洋的合作,最持久且仍在进行中的是经营“论文衡史”学术公号。2016年6月公号创办后,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我独立编辑。翌年3月,浴洋加盟,专门负责每周一次的书訊栏目,帮我分担了很多工作。浴洋做事非常得力,总是提前就把内容准备好,编排得井井有条。这不只是一份技术性的劳动,选书本身也见出浴洋的学术眼光。他主持的书讯栏目,不仅为用户(包括我在内)提供了最新的学术信息,也开拓了他们的眼界,成为“论文衡史”公号标志性的品牌。2021年冬天,我和袁一丹分别出版了《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和《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两本著作,浴洋主动提出办一场小型工作坊,围绕两本新书,就“五四”新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可能性这一论题,邀请年轻学者一起座谈。在浴洋的操办和主持下,“新文化的射程——历史综合如何可能”工作坊在北京中间美术馆顺利进行,我也再一次见识了浴洋办会的才干。
学术活动的召集、组织和运作,不只需要处理事务的长才,更考验主持者的学术趣味、判断力乃至前瞻性。浴洋在后面这一方面也表现出色,他对话题和主题的选择,都包含了自己深入的思考。即以“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这一主题而言,浴洋意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通过“经典”的升沉起伏这一独特的视角,探讨现代思想与文化的重构,这其中显然包含了一种学术史的视野。自读博时起,学术史就是浴洋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他组织的诸多学术活动,大体都包含了这一面向。更重要的是,在浴洋那里,学术史不仅是研究的对象,也是一种实践的方式。无论是他策划或协助召集学术研讨会与座谈会,还是在报刊上组织专题的评论或笔谈,还是对当代学者的深度采访,都是在参与建构当下活的学术史,对此浴洋显然有着充分的自觉。
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浴洋做的学术访谈。自2016年起,浴洋先后为孙玉石、洪子诚、陈国球、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吴晓东、王德威、黄子平、陈平原、王润华、贺桂梅、孙郁等多位学者做过访谈,从这份名单不难看出,他们中大多数是北大中文系或有中文系背景的老师,还有几位任教于海外,但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这些访谈多围绕被采访者的著作或某一具体的研究领域而展开,然而都包含了他们对学术历程的回顾和对治学经验的总结。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鲜活的学术史文献,必将为当代和未来的学术史家所珍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浴洋的工作,就没有这些文献,他投入大量的心血,为我们这个学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做学术访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是漫无边际的闲谈,需要访谈者预先做足功课,有充分的准备。我有幸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访谈,那是2017年10月,王德威和陈国球两位老师来京开会,浴洋邀请我跟他一起,与两位老师就《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进行对谈。此前浴洋已经向王德威老师推荐我参与该书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我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与两位老师当面交流。那天下午,我和浴洋来到北大博雅国际酒店王德威老师的住处。稍微寒暄几句之后,我看到浴洋拿出几页打印好的纸,上面是他为这次访谈准备的采访提纲,我才知道他下了多么大的功夫。相比之下,我完全是抱着聊天的态度和心情来的,不免汗颜。那天的谈话愉快而尽兴,内容非常充实,这大半是浴洋的功劳①。认真的有针对性的提问才会引来高质量的回答,从而为成功的访谈提供保证。从浴洋事后整理出来并发表的访谈稿就可以看出,他对采访对象的学术经历、研究成果和相关论题了然于心,因而往往能够从细微处引出有意思和有价值的话题,激发对方的浓厚兴味,达到小扣大鸣的效果,学术史也就在这样的问答间悄然延续。
对浴洋本人来说,通过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这些一流学人的近距离对话、交流与接触,他对这门学科的光辉传统和当下面临的某种困境,也有了切近的认识和体会。在组织学术活动和进行学术访谈之外,浴洋也在当代学术史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由于这种亲身介入的现场体验,浴洋这方面的研究深入透辟,毫无一般综述或书评的肤廓之感。例如,他如此阐发钱理群老师的鲁迅研究的特点:“在‘钱理群鲁迅’中,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鲁迅’的实质是鲁迅独特的思维方式,其核心义涵是鲁迅对于‘真的知识阶级’的身份创造与道路选择,其主要的实践形态是‘鲁迅左翼’的价值立场与‘鲁迅文学’的实现形式”②;在总结陈平原老师的学术关怀和研究方法时,他指出“陈平原的治学个性更多体现为‘古典趣味’与‘现代意识’的相互滋养与涵育。他以‘现代文学’为专业,但不时思接千载;他不断跨越学科边界,但又始终抱有对于‘现代中国’的关怀”,“在‘千年文脉’的视野中重新发现‘现代文学’,是陈平原重要的学术贡献。而文体、制度与精神三者的彼此辨证,则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③。这些全局性的概括都非常精当,非浸淫日久且亲聆謦欬者不能道。需要指出的是,浴洋这些谈论师长前辈的文字并不为尊者讳,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他也会坦诚地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例如在讨论严家炎老师备受争议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之起点的新见时,浴洋对其学术观点的脉络做了细致的梳理并肯定其贡献,同时也直言“他为了强调新意,而刻意突出‘晚清’的‘起点’意义实在也是一把双刃剑。当他把自己的论述抽象成为一种主要是关于‘起点’的新说时,实际也简化了内在的历史感与丰富性。而简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可能被符号化”④,显示了一位年轻学者应有的锐气。
难能可贵的是,浴洋的当代学术史研究并非客观评述而已,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关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他对这门学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有着似乎与其年龄不太相称的关切。他曾用“学科感”一词来表达这种关切,我不知道浴洋是不是这个术语的发明者,但用它来描述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学者对这门学科曾经拥有的那种认同感和责任感,确实非常准确。浴洋在讨论钱理群作为文学史家的贡献时,特别强调钱老师在推进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方面的功绩,这“与其说是旨在突出其个人的学术成就,倒不如说是意在体现一代学人曾有的公心与热肠。因为对于学科的真情与深思曾是钱理群一辈及其前代学人的普遍情结,而今除去少数学者,绝大多数年轻学人的学科意识都已经十分淡漠。在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到第三代学者身上广泛存在过的‘学科感’与‘学科性’,不仅是在考察他们的学术思考与实践时的重要维度,对于当下的学术发展也不乏积极的参照价值”⑤。这段话读起来颇有沉痛之感,“学科感”的消失确实是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某种症结所在,而浴洋乃是为数不多的保有这种“学科感”的青年学者之一。在我看来,保有“学科感”并非固守学科边界,而是指有意识地通过参与学科的建设来维系学术共同体并使其始终保持活力。浴洋在学术活动的组织和当代学术史研究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也正体现了他这方面的努力,这也是对活的传统的自觉接续。
浴洋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现代文学学科前辈学人的贡献的考察与体认,包含着继承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自觉意识。我读他的《孙玉石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一文,感触尤深。从学科史的谱系来看,孙玉石老师属于1950至196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并登上学术舞台、学术生涯横跨“文革”前后的“第二代中國现代文学学者”。浴洋写道:“在第二代学者纵横驰骋的时代,我们尚未出生或者还在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尚不知‘现代文学’为何物;而当我们进入独立阅读或者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时,他们却已经退休多年,我们轻易不再有机会领略他们的风采——除去阅读他们的著作。在这一貌似自然而然的状态背后,其时还具有1970与1980年代之交以及1980与1990年代之交两次大的社会、思想、文化与教育变局,断裂的印记自然投射到了学术史与文学史中。于是,阅读,在体贴的阅读中展开代际对话,也就成了我们超越断裂、接续传统的学术传承方式。”⑥我比浴洋虚长几岁,还有幸听过并选过孙老师的课。包括严家炎、钱理群、商金林、温儒敏几位老师的课,我都上过,他们其实在浴洋入学前也都退休了。我有亲炙几位前辈的缘分,这是我的幸运,然而由于我生性疏懒,并没有珍惜这样的机会,课外与他们的交流并不多。浴洋却以他对学科的热忱、诚挚的好学之心和正直稳重的品格,在“体贴的阅读”之外,与几位老先生建立起日常的交往,赢得他们的信任,甚至成为他们的忘年之交。也正是这样的交往,让浴洋对孙玉石老师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优良传统,有了深切的体会和认同。
平心而论,浴洋出于学术史和“学科感”的自觉而做的这些工作,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我牺牲式的劳动。令人欣慰的是,浴洋并没有因此耽误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反而让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也不奇怪,因为浴洋关注的是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学术史,他的现代学术史研究与当代学术史实践,恰恰彼此互为支援。浴洋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人文学术专业化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的问题意识是专业化的人文学术与思想文化运动的整体方案,如何既相互借重又构成内在紧张的关系,它显然包含了浴洋的当下关怀。90年代以降日益专业化和学院化的人文学术(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否以及如何能够介入到时代的思想潮流之中,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课题,浴洋的博士论文恰可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照。
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上,浴洋没有宽泛地讨论观念和制度层面的演进,而是聚焦于具体的学人,考察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如何走上专业化的学术道路,又如何以专业的学术研究,回应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重大论题。他选择冯友兰、顾颉刚和朱自清(也许还应该加上傅斯年)为个案,细致地梳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态演变与志业选择,为我们揭示了“后五四”时期尚未完全专业化的现代人文学术所蕴含的诸多可能性。浴洋从冯友兰早期的比较文化研究中看到了讨论“东西文化论争”的某种隐而不彰的维度⑦,从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有关“烦闷”的叙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专业化的学术规范与顾颉刚的学术追求之间的张力⑧,又从朱自清“五四”之后的文体和志业选择这一新鲜的角度,为我们揭示了新文化展开过程中的挫折及自我调适的内在线索⑨。这些从博士论文中发展出来的个案研究成果,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些熟悉的对象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动荡不安而又充满活力的时代的认识。不过在我看来,浴洋有关朱自清“新文学”思想的生成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关系的研究,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对朱自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驱者地位的认定,通常都以他最早于1929年在清华大学国文系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为依据。浴洋则进一步在“后五四”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历史语境中,追溯朱自清“新文学”思想的渊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朱自清对“新文学”的界定,源于他对“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的高度肯定与体认,这就从源头处,为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恢复了一个整体性的观照与评估“现代生活”的思考背景,也为今天我们重新激活这一学科的内在活力,提供了一条历史的进路。⑩
浴洋研究的冯友兰、顾颉刚和朱自清,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学人”,我相信浴洋在与这些前贤对话时,也在探求和摸索自己未来的学术道路。浴洋的学术之路才刚刚开始,他的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和关怀,已经使得他为人为学两面都显出不俗的气象。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未来的成长所能达到的高度。最后,我想引用孙玉石老师2014年11月给浴洋信中的一段话,来为我这篇拉拉杂杂的印象记作结:“衷心希望你能够,在无论面对如何的影响、刺激,或诱惑,都能够保持自己的清醒,坚守自己灵魂的‘净土’,淡功利,多读书,深思考,真真正正作出一些有分量,有功力,有长远性生命的学问来。”11谨以此与浴洋共勉。
【注释】
①这次访谈的整理稿,见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3期。
②李浴洋:《承担意识与行动精神——“钱理群鲁迅”的提出及其核心义涵》,《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③李浴洋:《“千年文脉”视野中的“现代文学”——陈平原学术关怀与研究方法述略》,《晋阳学刊》2020年第6期。
④李浴洋:《晚清与五四——“起点”问题与严家炎的文学史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⑤李浴洋:《文学史家钱理群》,《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⑥11李浴洋:《孙玉石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
⑦李浴洋:《“东西文化论争”的“方法转向”——冯友兰文化比较观念的形成与泰戈尔的触媒作用》,《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4期。
⑧李浴洋:《在“学者自传”与“成长小说”之间——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一种读法》,《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
⑨李浴洋:《从“五四”到“后五四”——朱自清的“诗”与“思”》,《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2期。
⑩李浴洋:《“新文学”与“新国学”的互缘——“整理国故”运动与朱自清“新文学”思想的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1期。
(季剑青,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