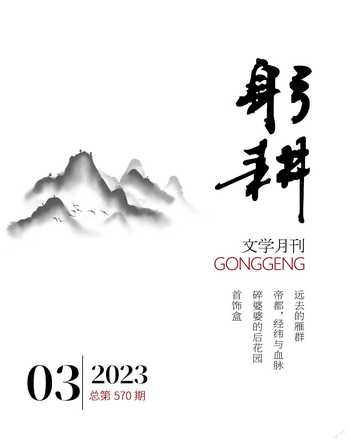一地芬芳
刘丽华
风动蔷薇一帘香
初识蔷薇,是租住在一个小院落里,当时为生活打拼的我,从没留意过身边的花花草草,许多花儿我都叫不出名字。一天,突然被窗外一蓬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的红艳艳的花朵给镇住。问先生,这是什么花?像极了我儿时扎在发上的红绸子,怎么就没完没了地开花?先生笑道,它是四季蔷薇,为你开呢,因它知道这窗口里住着一个爱美的女主人。此后,我每天会多看几眼窗外,就因为蔷薇。
晚上坐在床上,随手翻开枕边的《红楼梦》,准备用心来读几页。此时,一阵淡淡的花香袭来,我感觉不买房就租住在这儿也蛮好。当我这么说的,一直觉得委屈我的先生,笑我也太好打理了。
读到“龄官画蔷”一节,真不明白曹翁为何要给贾蔷取一个“蔷”字?难道就为了营造一个诗情画意?他让龄官蹲在蔷薇花架下用簪子划几千个“蔷”字,而隔着篱笆洞儿偷看的宝玉呆了,直到下雨了,龄官发尖滴水,衣纱淋湿,宝玉才劝不要写了,龄官这才抬头,一眼看到花栏外半边脸,误当姐姐叫了……好美妙的误导!但,这里不用蔷薇,难道用别的花不行?嘿,琢磨一下,还真不行,龄官划那么多的“蔷”字,其实就一个“痴”字,她划的不是蔷薇的蔷,而是贾蔷的蔷。曹翁这么安排,是早知蔷薇的花语是相思?或后人将曹翁当成了蔷薇花语的创始人?这就不得而知,但就此,我喜欢上了耐雨耐寒还耐旱的蔷薇。
后来,去乡下婆家,婆家的房屋不宽敞,也不明亮,好在柴門小院独门独户,院内的菜地果树花草都生机勃勃,连闲置的农具也能让你嗅到泥土的芳香,墙脚下的木墩上有农妇在陪婆婆闲扯……那时正是春天,知我者先生也,他很快将栅栏修整好,在栅栏下移栽了一排蔷薇,并在石桌凳旁搭了个棚架,栽了大半圈蔷薇,说要给我一个“满架蔷薇一院香”的婆家。我一下就爱上了这里。
一年后,等我们再去时,一进村子,走在通往婆家的田埂上,远远地看到婆家一堵绿底红花墙,那是蔷薇爬上栅栏,一枝枝垂帘般的藤蔓缀上错落有致的花朵。走进院落,先生用眼神示意:感觉如何?我深呼吸,一头钻进花花绿绿的蔷薇棚,棚里一架秋千,我坐上去,荡着秋千,从视觉到嗅觉,得到了极大满足,我陶醉地向他点头……
夜晚,躺在那间农家小屋里,风吹帘动,香袭睡美人,感觉衣是香的,被是香的,发是香的,书是香的。我对先生说:“这儿,岂止高骈笔下的‘满架蔷薇一院香?我们这不是睡在李清照那‘蔷薇风细一帘香的卧房吗?看来,我嫁了个唐诗宋词里的婆家。”先生乐了:“那你就在梦里偷着笑吧!”
桃花深处有人家
偷得半日闲,与朋友相约看桃花,踏上乡间路,没来得及赏花,听到了唢呐声。隔垄相望,远处一支迎亲乐队,最炫耀的是那顶红花轿。哟,谁家嫁女?嫁得正当时,犹如《诗经·桃夭》里的新嫁娘,有灼灼桃花一路陪伴至婆家,谁有她这般隆重?有桃花陪嫁的女子,一定命好。
朋友喜上眉梢,朝对面大喊一嗓子:“桃花出嫁了——”她那兴奋劲儿就如自家嫁妹妹。那边乐队纷纷扭头张望,其形态各异,朋友按下快门,抓拍到了自己画笔下的素材。
不知不觉,闯进一片桃林,桃花开得难管难收。我近看花容,洇染红晕,玲珑剔透,沾珠带露的花瓣,吹弹可破。难怪桃花入诗入词入画,唐代元稹说:“桃花浅深处,似匀深浅妆。”唐明皇干脆称它“助娇花”,他当年折一枝插在杨贵妃头上,使这杨美人又添了几分娇媚。我们也往头上戴花戴朵,还学着杨玉环三姐“虢国夫人”的美颜法,来一个深呼吸,想借助桃花的精气润润颜……的确,桃花的静,不关貌相,而在内功,它不是把我们引来了,还鼓动花轿里的女子动了嫁心吗?
莫非我们误入桃花源?从花林深处窜出一只小花猫,紧随一个小人儿,人儿身后尾随一条小黄狗。哪来的孩子?一问小姑娘家在哪,她指着来的方向。原来,桃花深处有人家,小女孩家的屋顶正冒着炊烟。朋友口渴,问能否去她家讨茶水喝,小家伙点头引路。
穿过大片桃林,看到了灰墙黛瓦的屋舍坐落在石头垒成的低矮院墙内,院里坐着一位含饴弄孙的老婆婆,院内几畦菜地,花儿零零星星,蜂飞蝶舞,公鸡斗殴,小鸡崽从老母鸡的大翅膀下探头探脑看热闹;院墙边,一位葱绿配桃红的女子站在凳子上,双手忙碌地往竹竿上晾晒萝卜叶子。朋友收入镜头。
见来了稀客,老人和女子笑脸相迎,女子面若桃花,搬出板凳,倒来两碗茶水,款待我们。那茶水清甜,女人说是山脚下的泉水泡的,说着,女子接过婆婆手里的孩子喂奶。寒暄间,才知女子是从另一村庄嫁过来的,当年正逢桃花烂漫,待有了身孕,桃子也熟了,酸桃、甜桃任她挑,一家子过日子就靠这片桃林……真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离开这户人家,很是羡慕。他们依山傍水,狗吠鸡鸣,外加一片桃林,这比起唐寅几间茅舍的桃花庵,岂不更仙?住在这儿,不是神仙,可胜似神仙哟。
小院葫芦入画来
进朋友家的院子,一眼看到葫芦瓜,地上躺的,墙上挂的,原生态的,手描彩绘的。朋友夫妇都是民间画家,他们的民俗画大红大绿,大俗大雅,有秧歌大扭,有炊烟大冒,有唢呐大吹……我最喜欢的是女主人的葫芦画,描眉似的,如苏东坡笔下的或“横烟”,或“却月”,或“倒晕”,来龙去脉都有交代。
春天去的时候,两夫妻正在院墙下种瓜点豆,种得最多的就是葫芦,有人说葫芦食用期不长,稍不留神就老了,不能吃了,你们种这么多葫芦哪吃得了?男主人笑道:葫芦一身是宝,可食用,也可药用,葫芦谐音“福禄”,“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是传说中的药王爷在葫芦里下过神药,而使众生免除瘟病,所以,葫芦是千百年来人们“纳福增祥”的吉祥物,身上大有文章可作。
待再次去时,已是瓜棚架下好遮阴,一架架凉棚,瓜豆起舞,花儿吟唱,苦瓜、丝瓜、扁豆、刀豆、豇豆、葫芦你来我往,黄花紫花白花你呼我应。最张扬的就是葫芦,藤蔓粗壮,叶片婆娑,大大小小的葫芦娃吊在藤上,起落有致。美女画家介绍:这是亚腰葫芦,《西游记》里不是说“头勒得似个亚腰儿葫芦”吗?瞧,腰一束,小蛮腰就出来了,盈盈一握,婀娜多姿,乐器葫芦丝就是这一款做的。它最小的才豌豆大,宜作挂件,可值钱啦,《明宫史·火集》里记载:“仍有真正小葫芦如豌豆大者,名曰‘草里金,二枚可值二三十两不等,皆贵尚焉。”听得各位一惊一叹。美女继续说:这是西瓜葫芦,水平锯开顶部,就是一只葫芦罐;这是柿子葫芦,可做葫芦壶或葫芦碗;这个是长柄葫芦,小的宜做葫芦勺,大的能做葫芦瓢;这可是并蒂葫芦,常做情侣信物……看到姿态不同憨态可掬的葫芦娃们,想象着经这一双艺人之手一点拨,那葫芦不单是瓜了,而是一块可塑之材……
《诗经·幽风》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此“壶”就是葫芦壶。因牵挂葫芦,秋日,三五朋友再次造访小院,夫妻俩正在施展民间艺术,男的负责加工制作:将外壳坚硬的葫芦采摘下来,浸泡清洗,有破损、小洞的淘汰出局,完好的去表皮,风干,用砂纸打磨光滑,用油灰填充虫眼,或保留斑驳纹络,保持外形原貌,或锯成碗、罐、壶、瓢、勺等。女的进行彩绘涂抹:以葫芦当纸,采用无毒无味的丙烯颜料,精描细绘,有脸谱,有十二生肖,有花卉图案……我一眼相中了“执子之手”,是一对并蒂葫芦,大红底,一双男女穿红着绿,喜气洋洋。美女画家说我好眼力,拿去吧,这寓意夫妻牵手白头,比翼双飞。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们人手一葫芦,得几分仙气几分灵性,欢天喜地走在街上。有人打趣:小心撞上铁拐李,他会扔掉手里的酒葫芦,来抢我们手上的宝葫芦……
短墙半露石榴红
看石榴花,就像看新嫁娘,惊艳,妖娆,炽热,喜庆。阳台上的两盆石榴,夏风一吹,开始“石榴树挂小瓶儿”,那枝枝丫丫挂着葫芦似的小红瓶,没多时就从瓶里吹出花来,花瓣似火,层层叠叠,薄透如绢。眯眼看,红花绿叶,如锦似缎,艳俗华美。
原来,小葫芦里卖的是红染料。古诗云:“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可见,古代女子的石榴裙,就是石榴花染红的。但不管怎么染,白居易的一句“裙妒石榴花”,道出了榴花的红艳,是染料不可企及的。
儿时,我住在姥姥家的小院里,院墙下有一排石榴树,一进“榴月”,榴花开了,隔墙的云婶家的榴花开得晚些,她家二丫头三丫头趴在院墙的豁口,看我们这边的榴花,笑眯眯的,时不时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够一够那些花朵。小脚姥姥在院里走动,见了,要她们别摘,说榴花是要结榴果的,会比她们家的早结,到时好给她们尝鲜。说得小姐妹一闪就缩了头,下墙去了。我自告奋勇看守花儿。可姥姥一进屋,两个小精灵又从豁口探出头来,叽叽喳喳,数着花朵,一朵两朵三朵……一不留神,榴花却戴在了她们的头上,像红蝴蝶,漂亮极了。那一刻,我也不管不顾,摘两朵别在发上,臭美……玩够了,花就掉在地上。
姥姥心疼那些“落英”,弯腰一朵一朵地拾起。但姥姥不是葬花,她没有黛玉的矫情,她是洗净,晒干,研末收藏。等谁家孩子或大人摔伤,或出鼻血,就给一点敷上,塞上,可止血。姥姥还把多余的花瓣,去蕊,漂洗,浸泡,炒一盘风味小菜,给我们开胃。
现在想来,榴花有多大的诱惑,别说小姑娘插花戴朵,就连古时女子也抵挡不住,所谓“鬓边插石榴”“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她们,该是李清照式的“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才有了“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吧。可欧阳修说“榴花照影窥鸾鉴,只恐芳容减”,是啊,不自信的女人,是不敢戴花的,尤其榴花。
抬眼间,看到一户人家半露围墙的石榴花,那一团团火焰,在密密匝匝的绿叶间跳跃,恍惚站在了姥姥的小院里,看院墙那边榴花怒放……
我这才明白,南宋戴复古笔下的“山崦谁家绿树中,短墙半露石榴红”,不正是眼前的景色?
冬枣半红美如瓷
“每天三颗枣,疾病少来找。”民间这句顺口溜,成了许多百姓的养生之道,每天的粥里,汤里,总少不了三颗枣,或枣子拌核桃肉生吃,那个甜香,妙不可言。这个枣,说的是干枣,也叫红枣、大枣,可以入药。中医就善用大枣,说生吃大枣通便,熟吃大枣止泻。
“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竿。”其时,我家餐桌上搁着一盘鲜枣,粒粒半红着青,色泽如釉,形态如罐。古代的“枣子罐”,该是这么得名的吧。鲜枣,不单美其外,还有“百果王”“活维生素丸”之美誉。随手拿一粒入口,脆甜清香。这是枣乡的阿梅真空包装快递来的。
多年前,我念一篇《打枣》的散文给大学宿舍的女生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儿时摘草莓、采蘑菇、扯笋子、掰玉米、摇蜂蜜等欢乐场景,可就是无人打过枣,阿梅说她毕业了就回家乡栽枣树,建个大大的生态园,到时每年邀请同学们去体验采摘瓜果的乐趣,大家一听,一致投了赞成票。结果,阿梅的枣子结了一年又一年,谁也没去捧场。去年阿梅以“打枣声喧隔陇闻,田头房脊晒红云”来诱惑各位,大家终于抵挡不住,一个个杀到了阿梅的枣林,赴了个甜蜜之约。
在枣树下尝枣,尝的是鲜,伸手摘一粒红红绿绿大枣,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地咀嚼,那可是甜在嘴里,蜜在心里,个个吃得眉飞色舞。“树下粮仓,树上银行”,棵棵都是枣农的摇钱树,粒粒鲜枣是碎金。其时,全青泛白的已经下树,装满了一只只箩筐,收购枣子的商家在用卡车一车车地运走。
留在树上等待我们的全是红绿着彩的枣子。阿梅说,别看沟岔坡岭,可让枣树安身立命,可鲜枣身子娇贵,皮薄,一碰即伤,不易保存,所以商家要求手工采摘,不能打枣,而且得在“脆熟期”摘,也就是着色前,即绿色减退,转为白绿时为佳,因此时的果肉水分多,味甜质脆,耐贮存,而一旦果皮转红,味则更甜,却已到完熟期……原来,那满枝万点红,是用心良苦的阿梅,留给我们过一把打枣瘾的。
可枣还没打,我开始打喷嚏流鼻涕,贴心的阿梅,给我煎煮来了一碗姜枣汤。这里的枣,不是鲜枣,是干枣,是与老姜、红糖、葱白配伍煎出来的。阿梅说,这是村里一位“枣医”最擅长的枣配方,如用大枣、甘草、小麦组成甘麦大枣汤,专治村妇们的更年期综合征,用柴胡、黄芩、人参、半夏等與大枣配成《伤寒论》里的小柴胡汤,来给村民治伤寒少阳病……我一口喝下去,全身热乎乎的,感冒去除一大半,我直呼:枣乡有枣医真好!
站在枣树下,我们忙碌着打枣的前期准备,先扫出一块干净地,铺陈地毯,然后,每人抄起竹竿,往密集的枣枝飞去,顷刻,大珠小珠纷纷坠落,在地毯上跳弹滚动,惹得各位大晒古诗,句句有枣,阿梅率先:“归来好,正芝香枣熟。”阿花接招:“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阿颜响应:“姜枣频煎药,袍衫屡换衣。”阿兰应接:“含笑对棘实,欢娱须是枣。”阿果吟诵:“新枣未全赤,晚瓜有馀馨。”只有我囫囵吞枣,无言以对。几位不饶,异口同声:“罚自作!”
逼上梁山,我把玩着手心里一半红一半绿的鲜枣,看它色如上釉,形如瓷罐滚圆,终于挤出一句:“万物萧条无颜色,冬枣半红美如瓷。”
责任编辑 郝芳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