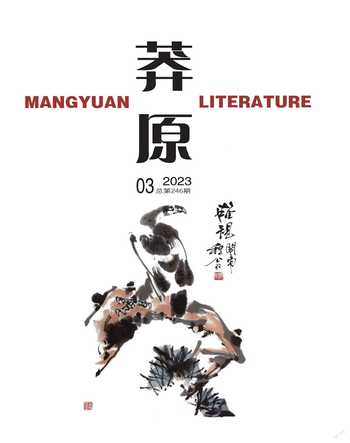拾草
刘庆祥
黄河与大海的交汇,是一场无声的相恋。大河收敛起狂放与桀骜,温柔地投入大海怀抱,身后诞生一片荒芜。入冬时节,严寒降临,百草枯萎,生活在黄河口的人们,纷纷赶赴荒原,捡拾野草枯木,用于烧火做饭,取暖御寒,也可换得一些零钱贴补家用。荒原上生命的余烬,使黄河口的严冬,炊烟照常升起,为饥寒的日子接续温暖。这是一年里,黄河对荒原最后一次的馈赠。
那年,大哥十二岁、三哥九岁,父亲为兄弟俩置办了两具大耙和一应拾草的家什。从此,兄弟俩驾一辆手推车,一人推一人拉,载起一家人的生计,加入走向黄河口拾草的队伍。
我对拾草的记忆,是睡梦中“砰然”生出的满屋香气。睁开眼,摇曳的煤油灯光里,大哥、三哥围坐着灶台埋头吃面条。睡意随浮动的油香飘散,馋涎顿生。我与六弟俯身在被窝里,下巴抵着枕头,两眼紧盯锅台,希望锅里能剩下半碗残羹,期待母亲唤我俩去喝。我俩便赤条条跳下炕,抄起勺子,一人一口,自觉、公允地喝个精光。从那时起,我就期待着快些长大,和哥哥们一样,吃一碗面条,踏上去黄河口拾草的路。
我走上这条路,是十四岁那年。当时,我升入初中,也到了“不吃闲饭”的年龄。沿着黄河大堤行走十余里,下坡到小坝子,经过王八湾、树林子、引黄闸来到荒洼,一路都是早已耳熟能详的地名。
这是黄河口的孩子们都走过的一条路。两个哥哥在我那个年龄,已经在这条路上奔波了四五年,为的是拾取一家人严冬的温暖和生存体面。后来我想,当年的体面又是什么呢?是衣可蔽体,食可果腹,是街坊邻里“那户人家日子挺好”的评价,如此,孩子到成家年龄,就可以娶到媳妇。这几乎是生活的全部。在温饱与延续香火为生活目标的年代,这条通往荒野的路,如一条天堂之路,事关能否通向那样的体面。这看似狭隘的追求,何尝不是祖祖辈辈曾经的生活目标呢?
“明天就好了。”这是大哥常说的话。
然而,第二天的情形,并不像大哥所言。我行走时,双腿灌铅,浑身僵硬滞重,每一块肌肉都撕裂般疼痛。
“直起腰,放开步子!”
在大哥驱使下,我跌跌撞撞追赶着前行的队伍。时间的“咒语”,在不知不觉中调适着身体,解开了身体的束缚。一个小时后体能充盈,疼痛消散。到了第三天早晨,痛苦魔法再次附体,不过疼痛已经略有缓解。整整一周时间,痛苦的煎熬才慢慢消散。
冬天的日头很短,通往荒洼的路很长。我想象得到,两个哥哥幼小的身影,伴着踢踢踏踏的脚步和两具大耙颠簸出的脆响,消失在孤寂落寞的黑暗里。姊妹八个中,只有三哥和姐姐没入校门,在七兄弟中三哥则是唯一,多年以后,三哥对此仍然耿耿于怀。据三哥说:他最初走上下洼这条道路的时候,经不住早起的困乏,有时行走间睡着,一步踩空,骨碌碌滚下大堤,惊惶之间困意全无,一声不吭,努力爬上坝顶,含着眼泪继续往前走。就这样,忍受着寒冷与困乏,持续走四五个小时。
到达目的地,如果太阳晴好,枯草上的霜已经退尽。他们便一刻不停,卸车、整理工具,单肩挎起大耙的拉绳,一手扶住耙杆,拖着大耙,开始作业。午间,是大耙搂草最好的时光,在大耙带起的尘埃里,干爽的枯草纷纷往耙齿上飞升。搂满一耙草,将大耙翻仰,肩扛耙杆,弓下身子,双手抓住耙梁,顺耙齿曲度往后拖拽,乘势起身,耙上的草便整齐地退下。以车子为中心,由近至远,数小时之内,车子四周分布下一个个整齐的草堆。约莫够了一车载重,抓起绳子,将草打捆,背到车子两侧以备装车。
太阳偏西,辘辘饥肠,无法忍耐对两个高粱饼子的期待,该吃饭了。吃饭也是休息。选避风朝阳处坐定,背靠草堆,从干粮布袋里掏出高粱饼子,就着几根咸菜,啃起来。间或将水壶取出,顾不得水已冰凉,咕咚咕咚喝上几口。
大约是这个缘故,大哥和三哥满口的牙齿,五十岁左右已经脱光,早早就换了整口假牙。父亲说:“唉,这俩孩子牙口吃屈太多了!”“吃”是咀嚼吞下,“屈”是咽到心里的苦涩,“吃屈”二字让我从中品出了人生况味。记得大哥不经意说过一句话:“我一口牙都是疼过了,才自己脱落的。”牙疼,大概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历,想必只有疼过的人,才会有如此忍耐力。
装车是个技术活。先在车子前后两端绑定横梁,用以承担超出车体的载重;然后将车子倾斜放倒,绳子一头在车子上系牢,铺到地上,靠地面依托,开始装载。梳理乱草,打成“厦子”,在车子上排布整齐,相互形成勾连,使之浑然一体,再将它们捆绑固定在车子上。装好一边,几个人合力将车子抬起,倒向另一侧,用“点棍”支撑,再装另一边。捆绑固定称为“煞车子”,是装车的关键,要拉、拽、蹬、踹,手脚并用,靠全身重量和蹬力拉紧、勒实、系牢,確保将松软的草紧固在车子上,形成一体,避免在七八个小时的颠簸中“散架”。
装车时,重量分配尤为重要。后边太沉,会使大部分重量落在肩上,车子稳定,驾车时掌控平衡的难度低,可长时间行走,身体难以承受,脚步越来越抬不起、迈不动,会出现“压煞步儿”的艰难;前边太沉,则车子重心靠前,自动前倾,身体承重小,需要用力下压,可重心离驾车人越远,掌握车子平衡难度越大,方向越难以控制。因此,车子装载完成,要先行试驾,前沉、后沉、偏沉都要进行调整,不可将就。经常下洼拾草的人,经验可以让人少费周折,一蹴而就。
回家的路更长,也更加艰难。装好后的车子,比车体宽出一倍。有些重载的车子,几乎看不到驾车人,远看像一个行走的草垛。驾车的关键是平衡,自行车通过调整前轮方向,使之不至倾倒,独轮车的平衡,靠的是后点,驾车人通过适时调整位置,才能使车子平稳前行。驾轻就熟者,因势利导,平衡掌控在毫厘之间,行进犹如轻风浮云。
归途中,家并不是行程的终点。第一眼看到家的时候,太阳正压着树梢,冬日的阳光,洒向大地,一片金黄,释放出最后的温柔,夕照中的房舍,包裹着温暖余晖。倦鸟归巢,禽畜返舍,村庄一派祥和。然而,人们尚需迎着晚霞,向着黄河上游行走,赶往三公里外的一座窑厂。在那里,他们将车子推上磅秤,过磅、卸车、“倒皮”,将一天的辛苦变成一两块钱,回到家已是七八点钟。
初出茅庐的孩子,容易犯“恨载”的错误,如果装载超过车子的限度,返程将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黄河口荒原上的路,都是防洪堤或生产堤,越往荒原深处,道路越窄,路况越差,两旁多有丛生草木障碍,驾驭“过载”的车子,本就吃力,遇有磕绊,便会跌跌撞撞,东倒西歪。车子一旦失控,人车翻下堤坝,拖拽上来绝无可能,只能卸载,先设法把车子弄上来,再将柴草一一往上搬运,重新装车。坡顶上,空间局促狭小,绳子无法展开,装车的艰难可想而知。
夜色降临,荒原一片凄寂,孤独与绝望一点一点挤压过来。此时,他们早已忘记对鬼怪的恐惧,剩下的只有焦急与无助。上路回家的急切,让时间变得很慢,却只能以最大的耐心,一边流泪,一边收拾眼前的一片纷乱。超载的悲剧,迫使他们把一天收获的一部分弃之路旁。再次上路,在黑夜里摸索到家,已是深夜时分……这样的经历,仿佛一场童年的祭礼,从此,这些孩子面对困难再不会哭。一条通往黄河口荒原的路,不知是多少孩子童年的祭坛。他们仍需重复着这样的人生旅程,“两头不见太阳”的日子,要持续一个冬季。所不同的是,随着近处的草被拾光,这条路将继续向黄河入海的方向延伸。
有一年我回老家,想再去看看那片树林。近半个世纪过去,在我想象中,那树林早已枝干苍劲,古意盎然,不料却发现它已经不在了。据说,另一片林子还活着,在黄河下游入海口。我顺着“万亩槐林”路标,被导航一路指引到槐林中心停车场,看到这里荒凉已然褪尽,变成了一片景区。林中树木,大多比碗口略粗,与数十年前相比几无变化,其间杂草稀疏,开车数分钟即可穿林而过,童年时迷失其中的恐惧荡然无存。
护林人员介绍,黄河口新淤地,地表下即为盐碱层,加之地下水位高,树木经过一年茂盛期,根系扎入盐碱和地下水层,进入冬季,就会干枯,若不是每年投入资金养护,树林早已不复存在。我想,这大概就是上游那片树林消失的缘由。
往前推上数十年,这些干枯的林枝干,对在荒洼里讨生计的人来说,却是让人眼馋的一笔财富。每年入冬以后,拾草的人们,便带上锯子、铁钩、斧子等,去树林里“拾干棒”,卖往窑厂,一车干树枝相当于两三车干草价格。这在十五块钱就可过个“好”年的年代,无疑充满着诱惑。
说是“拾”,其实一半是“偷”。为防止树木遭受毁坏,每到冬季,林场会在路上设置关卡,严加防范,禁止私自砍伐。“拾干棒”一旦被抓,不仅没收工具,还会扣押车子。不过,护林人员知道,一辆车子关乎一个家庭的生计,往往会给予“宽大”处理。一段时间后,经过批评教育或找人说情,被没收物品便可索回。
一年冬天,有消息传来,树林里大量树枝枯死,林场尚未设置路卡。那是令人兴奋的一夜,大哥、三哥和村里一行数人,准备好一应工具,第二天一早就满怀希望上路了。
时近正午,却下起了雨,起初是毛毛细雨,后来雨越下越大,气温也越来越低,到了下午,树上已挂满冰凌。傍晚,又刮起大风,树在风中摇晃,树身上冰衣爆裂,发出“嘎嘎”声响。那几天父亲有事外出,母亲独自坐在炕上,为了省油,屋里也没有点灯,母亲在黑暗里等待着拾草的几个孩子。突然,母亲身体一抖,立刻挪动身体来到了炕头,摸到火柴把灯点上。也许,她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然而,光亮并没有驱散屋里凝结的恐惧。
直到晚上九点多,终于有了消息,街坊三大爷家小换哥回来了。母亲听到动静,匆匆冲出家门。路上都是泥水,母亲一双小脚,踩踏出“噗嗤噗嗤”的响声,几次差点摔倒。我悄声跟在她的身后,心里很害怕,生怕哪里做不好受到母亲呵斥。
小换哥躺在炕上,像刚刚苏醒过来,没有说话的气力。三大娘介绍,方才,她隐约听到门外有动静,再仔细听时,动静又消失了,只有门外的风声和雨声。三大爷说三大娘“耳惊”了。三大娘却不放心,下炕来到门口,听到门外传来很重的呼吸,急忙开门,小换哥扑倒进来,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三大爷是个身强力壮的人,想把小换哥抱到炕上,可一来儿子身形太过壮硕,加上棉袄棉裤都已湿透,十分沉重,根本无法抱起。老俩口勉强把他拖至炕沿下,在地上升起一堆火,脱掉他的棉衣棉裤,才把他弄进炕上的被窝。
“要不是我去看,俺小换就死在门外了。”三大娘抑制不住地呜呜哭起来。
据小换回忆,那天赶到槐林,天刚放亮。为避免被护林员发现,他们来到树林深处。有的爬树,将铁钩挂上树枝,有的在树下拉拽,分工协作,斧子、锯子各尽其用。一切都很顺利,满足载重时,还不到中午。他们将树枝截成适宜运输的长度,堆好。为防止连人带车被抓现行,他们推车到不远处隐藏起来,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一边吃干粮,等待傍晚装车子,趁夜色掩护返回。
刚吃过干粮,天上就开始下雨。起初,他们舍不得放弃到手的收获,眼见雨越下越大,年龄最长的俊山叔决定,只带上手推车和工具,投奔黄河大堤上最近的一座“坝屋子”。走出没多远,车轮因沾满红泥,转动受阻,用棍子刮掉泥巴再走;雨大,路滑,走走停停,走到“坝屋子”时,大伙已经全身湿透,个个寒冷难支。看坝屋子的老头儿,远远看到一群人来,知道是偷树枝的,怕担责任,急忙关上房门,拒绝容留。吵闹间,小换感觉体力还可支持,把车子扔在门前,独自离开。
一路上,棉衣棉裤被雨水浸透,鞋上沾满了厚厚的泥,越走越沉。不久,身体的热量在雨水中散尽,寒冷难耐,渐渐麻木得失去了知觉。他像走在梦中,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回家,回家……当他恍惚间看到家门的一刻,浑身充满暖意,却没有一丝气力,倒在门前睡着了。
夜里,雨转雪。第二天,大地洁白,世界一片静寂——下洼的人,是死是活杳无音信。
几家人商量从生产队借了两匹马,驮上衣物干糧,由叔叔带着二哥去找人。我一直想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让二哥去,那时,二哥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天冷路滑,他能担起这个重任?但二哥没有辜负母亲的重托,他和叔叔赶到堤坝上,接回了被困在看坝屋里的众人——看坝老头儿终是不忍看着几个人被冻死在风雪之中,打开房门收留了他们。
人心都是肉长的,总有温暖的悲悯啊!
责任编辑 吴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