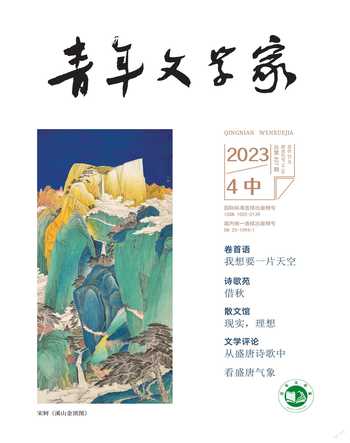于命定的局限中高歌
罗志鹏
病痛、苦难与命运,史铁生的一生都在寻找这三者的意义与答案。如果说《我与地坛》有他向往的模样,摆脱了对于“死”的追问,那么《病隙碎笔》则是他直面苦难,超越命运的赞歌。《我与地坛》里写道:“他知道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火为何而燃烧,那不是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作者早已埋下了伏笔,当时的史铁生已经看到了“命定的局限”,但在这“命定”的苦难中,他高昂着头,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对命定的命运发起挑战,是无畏的,而后也是冷静自信的。
《病隙碎笔》是史铁生笔下一部充满了生命体验的人生笔记。“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意义”,史铁生不断追问,反复追问,以生命的追问方式来不断书写,就命运、生存、生病、信仰乃至死亡做下了诸多注脚。他将自己剖离出来,进行审视,放置于时代与所处的空间中,反复审视,力图揭示生命的真相,也试图找寻生命的意义。
在我看来,生命的意义在《病隙碎笔》一点点写成的时候就已经实现。生命的意义在于反抗的力量,准确来说,是对于命定的局限的反抗,可以说这是宿命论的另一种形式。面对命定的局限,选择沉默是生命的埋没,而只有站立反抗,勇敢撞击,直面命定的局限,才是生命得以绽放的方式。人何以为人?反抗的姿态使我们成为人,从中爆发的是一种主体性的力量,这种主体性的力量使我们确证我们的存在、生命的存在,以及生命意义所在。史铁生面对命定的局限,敢于直面病痛,勇敢抵抗煎熬与近乎贯穿一生的折磨与苦难。这种生的姿态早已写就了生命的意义,这种直击命定局限的姿态使他直挺挺地站了起来,跨越病痛、跨越苦难、跨越死亡,超越了生命本身,成为自己生命的立法者,这种主体性的力量使他的生命得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永恒。
正如史铁生在文中所说:“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存在。命运并不受贿,但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在我看来,此时史铁生眼中的“上帝”,不是某个虚幻的存在,或者神话传说中所塑造的某个身份,而是希望的进行时,即始终有所信仰的状态。换句话说,是一直保持对苦难人生的乐观,一直无惧各种即将行至的磨难,满怀希望地前行,上帝自会保佑,信仰此刻就是自己,自己可以保佑自己,也就是前面说到的“成为自己生命的立法者”,生命的意义真正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与此同时,这也能回答史铁生书写《病隙碎笔》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即“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这同时也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问题会始终回旋在你的意识层,不断自我叩问,我总算找到一个答案:“自从我学会了寻找,我就已经找到。”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应该是跳出原有的框架,当你意识到活着的目的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既定的前提,活着的原因不是一开始就被给予的,相反,是被提出的。恰如文中所说的“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皈依是在路上”,没有既定的前提,也没有确定的目的,体验本身就构成了活着的原因,体验一切,即使其中包含苦难。
在史铁生的眼里,载体这件事情早已轻如鸿毛,生命的重量在于精神的永恒,在于求索的恒途。他认为“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通常猝不及防,生病是被迫的抵抗,生病始终不便夸耀。但是,凡游历总有酬报:异地他乡增长见识,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激流险阻锤炼意志,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这种体会是对病痛的一种和解,对于物质载体—肉体的一种平淡。生病,反而成了一件没有那么可怕,也可以接受的事情了。
进一步说,在《病隙碎笔》讨论完物质的意义后,他将目光聚焦于精神层面。“打个比方:一棵树上落着一群鸟儿,把树砍了,鸟儿也就没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树上的鸟儿没了,但它们在别处。”就如同人一样,肉体即使被火化,即使溃烂,即使残缺,但在此栖居的那些思想、情感和心绪不会消失。苦难在侵蚀,但人间的爱愿从未放弃,由此他坚信“他们必定还在”,这种对命运的乐观,对肉体残缺坏死的豁达,是一种对更鲜活、更明朗的灵魂与思想,情感与爱的坚定。与苦难和解是人生的重要命题,如何做到乐观与豁达,从体会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开始。“诗意地栖居”从来都不是一个目的地,是一种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精神的盈满,是一种生命恒长的体现。
信仰,一种对超越生命的“在路上”的姿态,是他超越命运的自由密匙。在《病隙碎笔》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上帝”“神”这类的词语反复出现,这些词使《病隙碎笔》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息,让人不禁发问:“史铁生先生是靠某种宗教的神秘力量以达成与命定的局限的和解吗?”现在看来,并不是。“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抵抗“命定的局限”的方法论是一种“在路上”的姿态,哪怕肉体再不堪,始终探索追寻生命的意义,挖掘生命的价值,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收获更深邃的思考,这些无尽的探索,也许没有终点,但也不必在乎终点,终点的有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路上”的一种姿态,而凡是坚持、坚定向前迈步的人,终将收获精神的永恒,这远比肉体上的生命长度更加恒长,这种相信,这种信仰,是史铁生对抗“命定的局限”的战斗姿态。因为痛苦,所以我们自由,而“自由”的定义何尝不可以来自对于生命的一种超越,正是这种超越“命定的局限”,才是一种大自由,而在这种自由的面前,苦难无非是另一种赞歌,对于生命的礼赞,对于生命意义的彰显,所以我们痛苦,由此我们自由。
“看见苦难的永恒,实在是神的垂怜—唯此才能真正斷除迷执,相信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助。这爱,不单是友善、慈悲、助人为乐,它根本是你自己的福。这爱,非居高的施舍,乃谦恭的仰望,接受苦难,从而走向精神的超越。”史铁生的一生,无时不在为生命做下注脚,无刻不在与“命定的局限”斗争,对于病痛、对于苦难、对于生命、对于命运,他怀疑、他愤怒、他颓废、他绝望,到后来,他求索,在恒途中无尽的求索,向内构建自身的精神家园,收获的是满园的盛放。此时,苦难是花开的伏笔,冬天总要为春天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