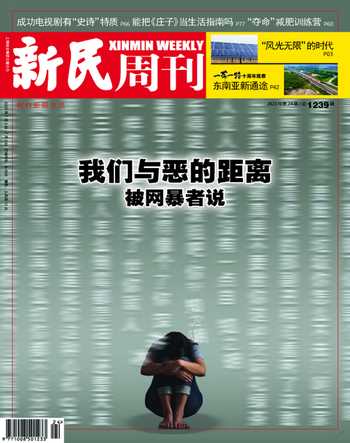为什么他们总是攻击他人?
刘朝晖

作为一种非接触性的暴力行为,网络暴力的伤害性不亚于传统的暴力行为,给被暴力对象带来巨大的身心伤害,严重的会使被暴力者不堪忍受网暴而选择以极端的方式离开人世。今年以来,已经发生多起“网暴致死”的悲剧。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不会觉得难受吗?”“难道他一点共情力都没有吗?是不是没有心?”“真的太可怕太冷漠了。”面对网络暴力中的不少极端言论,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网暴者,都是什么人?为什么数量如此庞大的个体热衷于攻击他人,却连基本的共情能力都不具备,也完全意识不到自身释放的恶意?网络环境下的社会为什么会如此冷漠,让人们的心理发生扭曲?
网暴者的群体画像
对于网暴者,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到底什么样的人才会在网上专门网暴他人?
现实生活中的施暴者,通常需要拥有一些优势,或者体格强壮或者更受欢迎或者地位更高……而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暴力的施暴者,想找到他们并不容易。在互联网上,网暴者们声势浩大,几乎在任何一个热门事件或话题下都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他们会在各种帖子下留下污言秽语,攻陷陌生人的评论区,甚至私人邮箱,他们随意曝光他人的隐私甚至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正义凛然”地质疑他人的道德品质……但当受害者试图抓住他们与之对质时,他们却躲在“马甲”背后,很难寻找到他们的踪迹和真身。
如果真能顺着网线找到他们,可能他或者她,是一个叛逆的初中生、一个阴郁的高中生、一个颓废的大学生、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打工仔……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办公室的白领,也许生活中是一个好好先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照顾妻子小孩,孝敬老人,但他会在夜深人静,对着手机屏幕给屏幕那一边的直播女子,给出“荡妇”的评价。
一项国外的研究结果显示,网络暴力的施暴者有着抑郁和低自尊的特征。换句话说,他们可能人际关系差,生活中时有挫败,不接受比自己优秀的人。他们在网上表现得越是激烈、越自信甚至自负,可能越是在掩飾现实生活中的自卑与懦弱,以此来让自己感觉好一些。
其次,他们本身可能就具有心理健康问题,人格特征异常。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网暴者常常与所谓“黑暗四分体”的人格特征正相关,包括马基雅维利主义(善于操纵他人,情感冷漠)、自恋(自我投入,渴求崇拜)、精神变态(缺乏自责感和同理心)和虐待狂(以他人的痛苦为乐)。这些人往往对他人的同理心不强,并可能将施暴行为作为增强自己权力和价值感的方式。
另外,各方面都正常甚至生活优渥的人也可能会参与网暴,“在适当的情况下,普通人也可以表现得像‘魔鬼一样”。
2017年,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网暴者并不仅限于反社会的少数群体,负面情绪和看到他人的不友善帖子都会显著增加用户网暴的概率,它们加起来还会使这个概率翻倍。
他们出发点是无聊、取乐、现实很焦虑;或者坚信自己是正义和有道德感的一方;或者享受匿名评论带来的刺激感和新鲜感。
他们还发现,有四分之一被标注为“恶意辱骂”的帖子来自于从未发布过此类内容的用户。也就是说,这些网暴者并不都是“全职”的,很多只是偶尔参与其中。他们出发点是无聊、取乐、现实很焦虑;或者坚信自己是正义和有道德感的一方;或者想尝试一种新的人格角色,享受匿名评论带来的刺激感和新鲜感。
2013年,澳大利亚记者金格·戈尔曼在受到一次网络攻击后开始调查“网络巨魔究竟是谁”。她在五年时间中与心理学家、网络暴力受害者、执法人员、学者和网暴者本人进行了交谈,完成了一本名叫《寻找巨魔》的作品。在一部分体现“黑暗四分体”人格特征的“巨魔”中,戈尔曼发现了一些共同点:他们大多是11岁到16岁的孩子,过度使用互联网,几乎没有父母的监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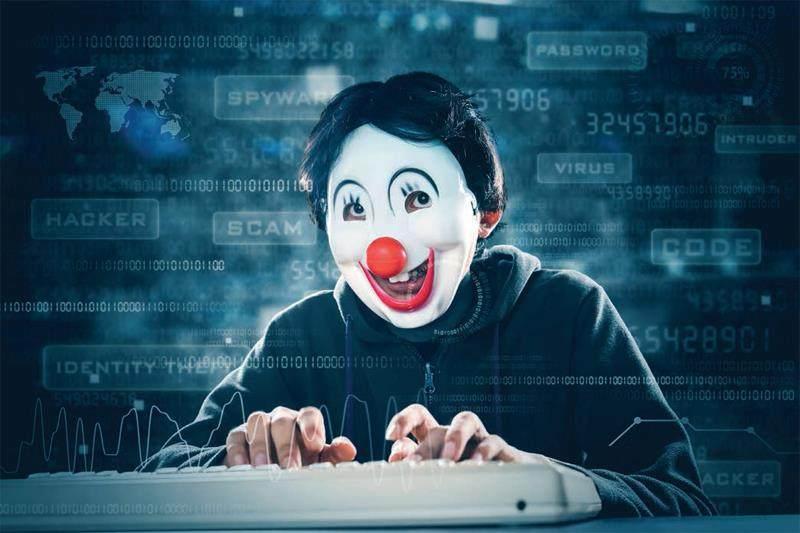
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暴的施暴者,他们躲在“马甲”背后,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
粗看起来,网暴者似乎是一个很难简单定义或者圈定范围的群体,但又并非无迹可寻,毫无特征。躲在“匿名”的面具之后的网暴者们,不全是生活不如意的“失败者”,更多的是涉世未深,经历着各不相同的人生处境的年轻人,都有着不小的“网龄”。他们是现实中的普通人,但在网络上,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极度的冷酷、漠然和固执。
网络暴力的心理动因
既然网络暴力中的施暴者,都是些普通人,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心理,让他们向受害者举起了语言攻击的武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副教授张和云向《新民周刊》记者分析了网暴者们的心理动因。
张和云认为,首先,网暴者们的心理存在着认知偏差,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网暴施暴者本身的认知偏差,有些网暴者自身认知事件存在认知偏差,喜欢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喜欢偏激的表达,个性偏执。网暴者往往相信自己以完美、准确的客观性看待世界,并引导人们与其保持一致(带节奏),认为与其意见相左的人一定是无知的、有偏见的或愚蠢的。他们从自己认为的“正确标准”去评判他人,认为他人要“一定”/“应该”/“必须”如何如何,否则就是不当的,就要对他人进行攻击。
另一个认知偏差则来自于网络本身,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世界,很多事件本身都是非全面的,所呈现的信息很多时候都是片面的,而网暴者很多时候不喜欢深入的理性的去思考,仅凭所呈现的片面信息就急于下结论,给人或事“盖棺定论”,对其认为不当的言行进行网络攻击。
其次,张和云认为,网暴者的攻击,往往是因为不合理的情绪宣泄。有一部分网络施暴者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很多挫折,自身因为各种事情不如意、不顺心,体验着由现实生活中的挫折带来的各种负面情绪情感,网络成为他们负面情绪宣泄的平台,采取了消极的、不合理的情绪情感宣泄方式,将自身的不快转化为对网络中受害者的暴力攻击。
此外,网暴者往往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越界的道德审判。在网络世界中,一部分网民可能是基于朴素的正义观,对一些社会舆情事件进行关注。诚然,有些事件正是在关注中得到了相对公正的、符合人们朴素情感的解决。但是,由于网络环境中,很多信息是片面的、不全面的,一些时候普通网民的这种朴素的正义观,又很容易被带偏,普通网民自己都可能没有意识到被带偏,但却成为了网络暴力的附和者,他们在网络中随波逐流,越界加入了一些“网络喷子”的行列。殊不知,每个独立的被带偏的附和者所进行的所谓“道德审判”,实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网络暴力,也可能对无辜的被网暴者造成巨大伤害。
网络环境对网暴的助长因素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张卓认为,人们在网络上进行留言的时候,通常具有匿名性和时间灵活性的特点,这就会导致个体在网络中的表达,更多表现为情感上的宣泄,甚至单纯地求关注,人们在网络上的表达会和现实反差较大。当网络评论演变为言语攻击和言语暴力之后,随着这一事件的持续被关注,最终言语评论会演变为群体暴力。
在张和云副教授看来,网络环境的诸多特点,可能成为助长网络暴力的因素。他同样认为,网络的匿名性助长了网络中的很多消极行为,让个体失去了对自我的监控,放松了自己言行态度的责任意识。很多人在现实环境中不敢表达,但在网络环境中却成为“键盘侠”“网络喷子”。
在很多网暴者的认知中,当一个个体成为热点,被投注于大量的流量和关注度,在这个公共场域,个体的私人性就是可以被剥夺的。
在网络暴力中,很多施暴者和附和者只是一个“虚拟头像”或“虚拟网名”,这些去个性化的网络环境,助长了施暴者做出网络暴力行为的可能性。网络的虚拟世界让施暴者失去了个人身份特性,使他们觉得不用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从而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网络暴力。
包括微博、小红书、豆瓣等在内的主流社交媒体是一个开放性极强的公共场域。在很多网暴者的认知中,当一个个体成为热点,被投注于大量的流量和关注度,在这个公共场域,个体的私人性就是可以被剥夺的。“他们太脆弱,分不清网络和现实的区别”是网络暴力施加者在事件发生后为自身开脱的常用借口。
网络中的从众心理现象也很普遍。网络暴力者往往会带节奏,渲染从众的舆论压力,而附和者往往没有较好地进行理性思考,在似乎“一边倒”的压力情境下,也选择从众,加入网络暴力的行列。且網络暴力事件中,很多人抱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态,认为自己只是表达了一种观点,那么多人都在表达同样的观点,认为随大流不会错。
张卓认为,在群体中,每个个体承担的行为后果是高度责任分散的,进而会导致个体行为极端化,环境激发出个体的言语暴力,并且社交媒体中的群体互动还会放大群体的攻击性,强化暴力倾向,会引发更极端的攻击性言语。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斯通纳早在1961年提出了群体极化现象。群体极化意味着群体成员的观点会可预见性地朝着成员们的先前倾向所指示的更极端的方向前进。“网络环境增加了群体极化现象,表现为越来越极端。网络暴力事件中,施暴群体可能会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偏激。他们会对受害者的言行举止进行挑剔,极力去找到受害者任何表态澄清或者言行举止中可能的不合适的地方,然后进行放大的、恶意的解读。”张和云说。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莫里·克罗克特则认为社交网络会怂恿人们宣泄更多的道德愤怒,他曾说:“道德愤怒的扩张显然是社交媒体商业模式的结果,而这种模式恰恰是有利于用户参与度的。”
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网络空间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跨越空间和具体生活,与更多、更远的人交流,看到他们的生活。但其实,网络空间帮助我们跨越时间、空间和具体生活的过程中,个体对他人真实性的感知也在其中被消解了。
张和云就认为,因为在网络暴力中,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并没有直接“面对面”的接触,这增加了施暴者和受害者的情感距离,施暴者包括附和者在网络暴力过程中不能直接接收到受害者的痛苦反馈,因而可能不断升级暴力攻击,造成严重后果。
此外,网络中信息的不对称也助长了网络暴力。张和云认为,很多网民实际上对某些事件的了解不够充分,所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但很多人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遐想”,对受害者的言行举止进行偏差的解读或者带有恶意的解读,进而进行网络暴力攻击行为。事实上,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完整,有些网络施暴者喜欢进行“脑补”,这符合完形心理学的理论以及自我建构理论,也即网络施暴者本身可能存在认知偏差,喜欢极端的、偏差的归因。
当然,网络暴力背后的社会心理运行机制的复杂程度,也并非前述的三言两语能解释透彻。网络暴力行为的残酷程度,下辖群体内部气氛的乖戾,使得这个话题是值得全社会每个人的重视和深思的。网络暴力,不应在我们手上继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