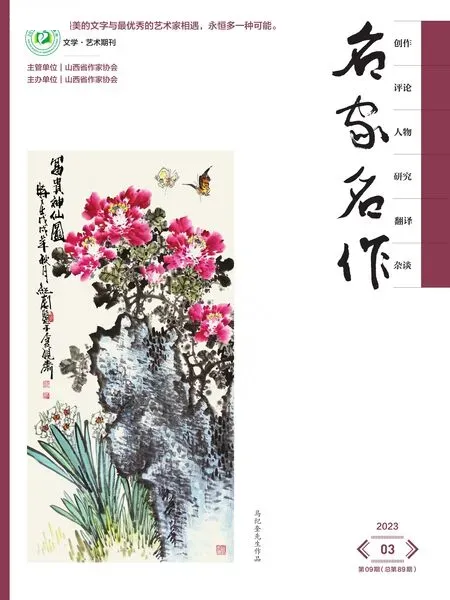论《纵横四海》暴力美学的创新与突破
陈岩松
在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背景下,香港经济发展迅速,连带着香港电影的美学形态和工业形态也有了十足的发展,成为独树一帜的“东方好莱坞”。诞生于这一时期的吴宇森式的“英雄电影”打破了传统的正规形象, 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对传统英雄的“反叛改造”,再配合独特的“暴力美学”镜头,使其成为香港英雄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作品。本文以《纵横四海》为例,浅析其独特的暴力美学镜头,并将这种风格与中国古典的侠义情怀进行对比,阐释其艺术特点及对后世黑帮电影的开创性意义。
一、暴力美学电影的诞生
(一)香港特殊时代造就的暴力美学风格
20 世纪,香港文化背景较为特殊,一方面是中英政治的繁杂交错,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较深,另一方面是受植根于国人血脉中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两方因素致使其经济实力达到了空前雄厚的地步。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其一便是民众阶层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公平的社会机制难以建立,故而民众不得不将“娱乐文化”作为精神的慰藉。一些有识之士将精力投入电影当中,并塑造出带有人文情怀与艺术色彩的人物形象,使民众得以在电影中得到精神满足,其中“暴力”“犯罪”类的电影在当时一度成为主流。
其实这种题材早在好莱坞电影时代便已形成雏形,尽管当时的“枪战”“飙车”“暴血”等电影形式还略显粗糙,但这样纯粹的暴力却极大地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在吴宇森的电影中,“他将这种暴力影像化的同时,又添加了升格、特写、慢动作等一系列带有诗意美感的包装和美化,成为一种自邵氏‘风月片’以及‘武打片’之后的新型港影形式,被称为电影中的‘暴力美学’”①李春红:《论吴宇森电影的暴力美学》,硕士学位论文,赣南大学,2005,第15-21 页。。由于人们在谈到暴力一词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浮现出血腥、罪恶等画面,所以这种电影形式在一开始也曾引发社会舆论,但吴宇森镜头下的“暴力美学”实则是一种感官刺激,只是一种外在的电影表现形式。因此,暴力美学本质上是为人提供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此类英雄电影并不提供任何社会楷模与道德模范,只是一种外在的、超现实的电影形式。
(二)传统英雄电影的成熟与新风格的突破
吴宇森的英雄题材电影自1973 年《铁汉柔情》伊始,到1986 年的《英雄本色》正式成熟,其重要角色代表便是《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一角。虽然主人公设定为黑帮人员,但其快意恩仇的洒脱却让这一人物打破了传统黑帮人员的形象,反而是将“小马哥”的义薄云天和不畏强权展现于荧幕,以精神的崇高消解了现实的恶俗,这也正式奠定了其暴力美学的电影风格。
在这之后的《碟中谍》《变脸》等一系列影片也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暴力美学镜头下不同的英雄形象。在吴宇森的导演生涯中,曾有这样一部电影同其他影片有着些许不同,便是1991 年的《纵横四海》。这部影片中加入了许多新元素,他通过升格、慢镜头、平行蒙太奇等手法所展现的枪战与复仇洋溢出一种独有的自由式浪漫,再搭配各种远、全、中、近、特镜头的转接,给观众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观影体验。因此,《纵横四海》中对个人尊严与自由的追求使其成为“暴力美学”式英雄电影中具有突破性与创新性的代表之一。
二、暴力美学与自由浪漫的融合与新突破
(一)自由与浪漫风格的高度结合
在《纵横四海》中,开场便是远景镜头接摇镜头,从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旁下摇到塞纳河。在此时的背景里,天气晴朗,白鸽四散,人物由右侧入镜,开始了全篇故事的主线。在进行了短暂的交谈之后,紧接着又是一个摇镜头“由左往右”,整个片段不过一分钟,侠盗三人组已经被完整交代出来,且整个风格洋溢出一种浪漫的、诗意化的自由感。
影片里“周张”二人在卢浮宫合作盗取画卷之时,影片采用的是暗色调,而在进入地宫之后,影片又转化为暗红色调,此时音乐逐渐变得繁重而神圣。导演利用一系列快速镜头的转接来体现盗画的紧张气氛,更加烘托出画作的“神圣”之感。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便是二人进行了空中盗取之后,却摔碎了一瓶红酒。在法国,红酒本身就是高雅、浪漫的代表,但他们却将红酒当作机关感应器,二人一边捧着酒杯,一边踏着舞蹈的步伐,最后甚至将酒杯叼在嘴上进行滑步游行。这一处理将本来惊心动魄的盗画事件变得“幽默化”,本应是紧张刺激的偷盗环节,但二人的动作却是潇洒不羁、不紧不慢,在悠闲中带着一些狂傲。这与传统的剧情有所不同,除了给观众以紧张的感觉之外,导演还用近景与中景再配合“快镜头”的转接,展现出盗取过程浑然天成的一种洒脱感。同时,吴宇森在此处使用了多机位的拍摄手法,使身体的多变性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且本段大量镜头的迅速转接,俯拍、仰拍、鸟瞰等多种角度相互衔接,再配合动作的飘逸美感与节奏流动,使欢快与忧郁两种镜头基调相互对比,达到一种特有的、自由浪漫的影片风格。
在后续剧情中,二人在卢浮宫外的对话也被后世奉为影史经典。亚占说:“我总觉得你对自己的朋友比对待自己的女人好。”而后紧接着又问他:“你有没有想过和红豆的未来与幸福?”而阿海回答道:“有时候太照顾别人的感受会失去自我的,其实你们俩也知道我的性格,我喜欢流浪。爱一个人不需要她一辈子跟着你,我爱一朵花,不一定要把它采摘下来,我喜欢风难道就叫风停下来让我闻一闻?”此时亚占却打断他说:“我和你说的是人,你却在说什么花花草草?”阿海却回答道:“结婚之后会失去自我和自由,所以我追求的是刹那的光辉。”
这短短几句台词被奉为影史经典,这些极其洒脱的话语使这两个通天大盗的形象变得有血有肉,此时的他们不再是盗贼,更像是在交谈人生的两个哲学家。以往传统的盗贼形象最终无非是横尸街头,但在这短短的几句交谈里,却体现了一种反体制的强力人格和潇洒的个人魅力,一方面他们是具有非凡能力的通天大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有着江湖侠义的、自由潇洒的“末路英雄”,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二)诗意浪漫与暴力美学的巧妙融合
在《纵横四海》这部影片的中间段落有一段枪战的戏份,导演以每秒高于24 格所拍摄的镜头,使银幕中的画面产生了特殊的视觉效果,这便是“无声”浪漫的又一体现。全段没有台词,只是通过镜头的转接以及音乐的更换,展示了一出昂扬、热血、自信以及自由潇洒的伟大赞歌。这是吴宇森对传统英雄电影的突破,也是对新风格的一种尝试。因为在他的影片中,实施暴力大多是为了实现美好,所以其影片所采用的大多是较简单的直线叙事方式,按照时间顺序来一步一步地推进剧情。但在《纵横四海》中,吴宇森将叙事视角分成不同人物,并且影片中所有的暴力场面不再是对情节的简单“陈述”,而是通过不同的暴力手段去更好地凸显出不同人物的性格以及不同人物身上所承载的精神。例如:在亚占与阿海首次盗画被发现之后,便开始了吴宇森英雄电影中经典的“枪战飙车”系列,但是在逃逸途中,阿海却选择了驾车赶往另一条路,选择了牺牲自己,主动引燃车辆。此时的升格镜头与慢镜头相互搭配使用,不仅放缓了激烈焦灼的战场节奏,同时也表现出二人不畏生死的豪迈气概。在他奋勇驱车的中景镜头里,导演用升格镜头不仅展示了阿海在这一刻高大伟岸的形象,同时也和岸边的亚占形成了对比,暗示着二者即将分道扬镳,难以同行的命运。此时的背景音乐《风继续吹》响起,再配合布景中淅淅沥沥的雨声,一种萧索的情绪弥漫在观众的心中。至此,影片开始分别从两个不同人物的视角开展,双线叙事结构下的两个人物形象则变得更加独立鲜明。
在这里,阿海和亚占已经不再是人人喊打的通天大盗,而是两个有情有义、潇洒飘逸的英雄硬汉,反而是一直处于正面形象的养父背地里却是险恶之徒。二者的强烈对比使“卑贱者反而高贵,高贵者反而卑贱”。影片结尾之处也是沿用了一贯的吴宇森式的结尾,即“快意恩仇的同时又有江湖情义”,这种处理以及通过镜头的升格来突出人物英雄气概的手法,在吴宇森的电影里屡见不鲜。
《纵横四海》中的暴力美学不同于《英雄本色》的白鸽四散、血花飞溅。这也使很多观众觉得本片的枪战不过瘾。但真正的“暴力美学”并不是一味地血腥暴力,而是一种“诗意浪漫”的武打,再配合源于中国传统的“韵律”“神韵”形成一种写意化的侠胆精神。因此,吴宇森在本部影片中所展现的“暴力美学”并不同于以往将温馨环境进行破坏而令观众产生痛感的手法,而是进行了全新的突破,他将“自由”与“洒脱”两种精神符号与中国古典侠义中所讲求的爱恨情仇进行了“意境”的巧妙融合,使其形成一种虚实相生、形神结合的新型英雄电影风格。
纵观《纵横四海》全片,如从接收者的角度来说,影片之所以能吸引观众,是因为《纵横四海》中所展现出的自由是一种等同于个人主观愿望的、随心所欲的自由,人作为自由的拥有者,其所想所感皆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因此本部影片才能令观众对其产生强烈的共鸣。而无论是镜头、音乐,还是各种场面的对接、转接,无不洋溢着一种洒脱放浪、柔情蜜意的情调。“这与西方美学中追求的理性思维有所不同,是一种‘时间化的’、动态的、追求生命意义的自由赞歌。”①万洋波:《韩国电影中的暴力美学研究——罪与美的影像风格》,湖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15 页。因吴宇森是中国香港本土人,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故而本部影片中充满了一种独特的浪漫风格,主人公虽拥有着反面身份,却英雄豪迈、侠肝义胆,是暴力形式与传统侠义的有机结合,这些隐藏在人物背后的真情实感,方为吴宇森暴力美学的精髓所在。
三、侠义情怀的融合与开创意义
(一)英雄情怀与古典侠义的结合
在《纵横四海》中,除了展现自由和浪漫之外,还展现了一种英雄文化、道德、美学的境界。在传统的武侠江湖中,江湖是紫竹林;是“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的郁郁不得志;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胸怀。传统江湖的侠义有许多种类,但纵观其相同之处,其实大多是抒发个人际遇的情感,是对封建主义、宗教伦理的否定与批判。在中国文学长河中出现的游侠形象,几乎都是正义洒脱的化身。这种“超脱散逸”的侠义是不追求任何功名利禄的,是蔑视封建礼教和世俗的,是一种完全超然物外的洒脱。这种浪迹天涯、挥洒豪情的浪漫与吴宇森所塑造的英雄情怀式的浪漫是有共通之处的。
中国古典侠义中重视“写意”“抒情”等形式,这样带来的弊端便是侠客情与义间的恩怨情仇有时表达不清,写意化、抒情化的导向容易让观众模糊对人物的概念。但吴宇森的电影则将暴力行为与侠义精神相互融合,而且影片中的英雄人物从来没有模糊不清的情感与踌躇,而是单纯地采用“以暴制暴”,这种处理直接削减了影片的暴力血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角色双面化的人性体现。这些英雄并不是暴力的崇拜者,只是会采用暴力的形式对侠义和道义进行维护。这就将以暴制暴的行为变得天然、合理化。
中国传统的侠义经历了千年文化的历史沉积,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因此非常强调道德观的判断,即所谓“正邪不两立”。但在吴宇森的“江湖”中,社会批判性很弱,甚至在他的英雄电影中几乎看不到讽刺社会人物等内容,只是单纯强调英雄应该奋起反抗一切恶俗势力,维护江湖道义。这其实从本质上弱化了观众对于暴力合理性的思考。
因此,无论是传统道义中强调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还是武侠世界中的“浪迹江湖”“云游归隐”,其文化意境皆能够在吴宇森电影中寻得踪迹。但他却通过电影向人们展示了另一种悲情的、充满恩怨与心酸的美学浪漫。再配合其镜头场面的流畅、巧妙、富有节奏感,使其“悲剧英雄”形象能够在精神上给予人们更加强烈的情感共鸣。
(二)吴式“暴力美学”的开创意义
“暴力美学”一词其实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感情色彩,讲求的是视觉冲击,故而影片中的大部分色调为“灰暗”“黑白”等凝重感较强的色调,以形成阴郁沉闷的厚重感。但在吴宇森的电影中,他将暴力变成了一种以中国美学为形式、以中国侠义为内在精神的电影哲学。他利用独特的画面构图和色彩设计,将暴力变成了一种动静结合、行云流水,却又充满张力的形式,使其最大限度地完善影像故事的同时又保持着高度的浪漫色彩,形成了独特的吴式“暴力美学”。这种“义薄云天”的反叛英雄,独特的“写意手法”与“精神内涵”对黑帮电影以后的英雄电影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张艺谋的《英雄》《金陵十三钗》,昆汀·塔伦蒂诺的《落水狗》《低俗小说》《杀死比尔》等,无不显露着吴宇森“暴力美学”的影子,而他的枪战场面和白鸽场景等更是直接影响了《黑客帝国》《惊声尖笑》等影视作品。
因此,吴宇森作为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大导演,其作品早已冲出了香港影视圈。他打破了东西方文化的壁垒,升华了人物与主题,使其电影在红色鲜血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与象征意义,在巧妙的视听语言中又暗含着情绪的起伏。这一步步的创新与发展,使其“暴力美学”以极高的艺术水准与强烈的个人风格而长存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