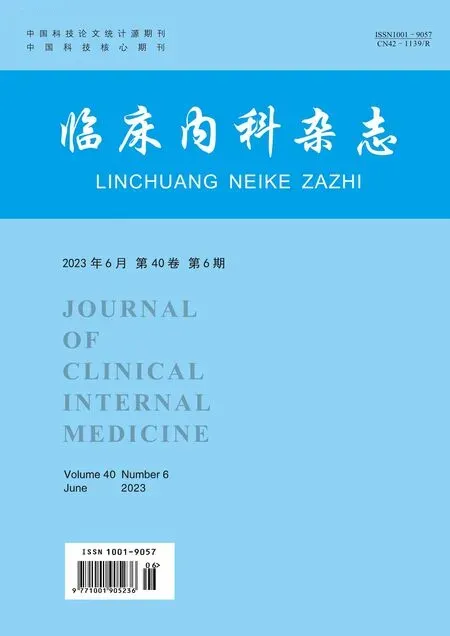糖尿病肾脏疾病的治疗进展
张玮 汪年松
糖尿病肾脏疾病(DKD)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脏损害,是慢性肾脏病(CKD)的主要原因,约40%的2型糖尿病(T2DM)患者和30%的1型糖尿病(T1DM)患者发生DKD[1-2],给患者及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预计全球糖尿病患病率将增加近50%,从5.37亿人增至7.83亿人[3],而DKD患者的数量预计将与糖尿病患病人数的上升同步增加[2]。因此,临床迫切需要优化DKD管理流程,探寻针对疾病机制的新疗法,降低疾病的残留风险,以减缓肾衰竭(KF)的进展,并减少相关的心血管事件风险(CV)。
一、DKD管理的循证实践指南
遵循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2021指南[4],所有糖尿病患者都受益于适当的血糖调控、血压控制、血脂管理、营养干预、戒烟和定期锻炼。DKD患者的亚组受益于其他干预措施,包括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抑制剂(RAASi)和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等药物。
1.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确保DKD患者可持续的非药物性获益很重要。尽管在设计和实施随机对照试验(RCT)以评估生活方式改变对临床结果的影响存在一定挑战,但多项观察性研究结果均表明,定期体育活动和均衡饮食可产生更好的临床结果。KDIGO 2021指南[4]建议未接受透析的DKD患者每日摄入蛋白质0.8 g/kg,DKD患者透析时每日摄入蛋白质1.0~1.2 g/kg;建议DKD患者每日钠摄入量<2克。体育活动被证实对减轻体重、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等有益,DKD患者每周应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体力活动。尽管DKD患者常因功能障碍而被限制活动,但鼓励患者进行有规律的、适应性的体育活动可能会产生更好的临床结果。
2.降脂:与无CKD的糖尿病患者相比,DKD患者心血管风险更高[5]。DKD患者血脂异常治疗建议与CKD人群相似。一般情况下,年龄>50岁、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1·(1.73m2)-1、血脂异常的患者均应开始进行降脂治疗,包括他汀类药物单用或他汀类药物与依折麦布合用。对于18~49岁的未透析CKD患者,开始使用降脂药物的时机应结合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如既往心血管事件史、非致死性急性心肌梗死或糖尿病[6]。在接受肾脏替代治疗的患者中,KDIGO 2021指南建议不应开始或停止使用降脂药物。
3.血压控制:DKD患者的血压控制建议与CKD患者类似[4]。高血压病的非药物治疗包括定期体育活动和限制每日钠摄入量。在药物干预方面,最近的高血压指南[7]与之前的指南相比强调了较低的目标,并扩大了RAASi对CKD患者的适应证,以延缓CKD进展。CKD患者应早期开始使用RAASi药物,并滴定至最大耐受剂量。即使在没有蛋白尿的个体中,仍建议RAASi是CKD患者高血压管理的合理选择。盐皮质激素受体(MR)拮抗剂(MRA)与 RAASi联用可有效控制高血压、显著降低尿蛋白水平。建议对CKD患者采用更严格的收缩压控制指标,如通过标准化诊室测压,收缩压应控制在120 mmHg以下。同时需注意,预期寿命较低或有不良事件(如症状性低血压)风险的患者应有个体化目标。RAASi是DKD治疗的基石之一,出现蛋白尿的患者CKD进展显著降低。DKD、高血压病和蛋白尿患者应早期启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无高血压病但有蛋白尿的DKD患者应考虑开始使用RAASi治疗。但临床中CKD患者停用RAASi很常见,并与更差的预后相关。因此,当患者暴露于轻度不良事件时,应尽量避免停用RAASi药物,特别是当存在轻度高钾血症、可逆性低血压和低血容量情况下的急性肾损伤(AKI)等可逆性原因时。
4.血糖控制:血糖控制是减少糖尿病患者大血管并发症的关键干预措施。早期强化血糖控制已被证明可减少新诊断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并发症发生[8]。然而,在进展期糖尿病患者中,强化血糖控制并没有显示出能降低大血管或微血管并发症发生率,而在CKD患者中,强化血糖控制往往导致低血糖,进而可能导致较高的死亡率。DKD患者血糖管理应重视生活方式改善和药物治疗的平衡,患者应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至高等强度的体育活动,改善营养状况的同时实现可持续的体重减轻。平衡个体因素与临床目标,可使患者受益同时实现医疗干预的价值最大化。KDIGO 2021指南建议,对于未接受肾脏替代治疗患者,DKD的糖化血红蛋白(HbA1c)治疗靶点为6.5%~8.0%,强调个体化靶目标,降糖靶目标根据患者年龄、病程、并发症等因素综合考虑。
在药物治疗方面,KDIGO 2021指南推荐使用二甲双胍联合SGLT2i治疗大多数糖尿病和CKD患者。二甲双胍历来作为治疗T2DM的一线药物,其安全性高、成本低、降糖作用良好,可减少体重增加,预防微血管并发症。二甲双胍被认为是治疗eGFR≥30 ml·min-1·(1.73m2)-1DKD患者的一线药物。
SGLT2i是一种治疗T2DM患者DKD的新模式,尤其适用于eGFR>25 ml·min-1·(1.73m2)-1的患者。DAPA-CKD、CREDENCE试验均已确定SGLT2i能减少CKD进展[9]。SGLT2i在高危糖尿病患者中可显著改善大血管和微血管的不良预后,特别是对患有CKD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10]。SGLT2i增加氯化钠输送到致密斑,抑制传入肾小球小动脉血管舒张,从而降低肾小球压力。除肾小球血流动力学作用外,SGLT2i可能通过减少三羧酸循环代谢产物,改善近端肾小管的能量平衡和线粒体功能。最后,SGLT2i可能有助于减轻肾脏中因DKD进展引起的炎症环境。在DKD的实验模型中,SGLT2i已被证明可下调近端小管细胞生长和炎症的几种标志物的表达。在使用SGLT-2i时,临床医生应尽量减少不良事件发生。SGLT-2i可能会增加患者血容量不足的风险,对于存在低血容量风险的个体,在处方前应调整利尿剂剂量;SGLT-2i可显著降低eGFR,后者反映了肾小球血流动力学的变化,一般来说其降低是可逆的,药物启动后eGFR降低幅度在30%以下者不可立即停药;危重症或禁食等酮症高风险人群则应停用SGLT-2i。
针对使用上述治疗方案仍不能达到血糖控制目标的DKD患者,KDIGO 2021指南建议使用胰高血糖素样肽(GLP)受体激动剂(GLP-RA)。GLP-1是一种肠促肠肽激素,可增加葡萄糖依赖性的胰岛素分泌,减缓胃排空,促进早期饱腹感,从而减轻体重。GLP-RA已被证明可改善T2DM患者的大血管转归。在改善肾脏预后方面,几个GLP-RA试验结果均显示这类治疗可能通过减少蛋白尿从而减缓DKD的进展[11]。目前正在进行一项评估司美格鲁肽对肾脏预后影响的Ⅲ期RCT研究,该研究将确定GLP-RA对DKD患者是否有肾脏获益。
二、DKD的治疗新进展
1.MRA:MR是在身体的许多组织和细胞(肾脏、心脏、成纤维细胞和免疫细胞)中表达的核受体,MR过度激活会导致心肾疾病的炎症和纤维化。阻断MR过度激活是DKD患者的重要治疗策略之一,MRA正是一类以MR为治疗靶点的药物。非奈利酮是新型选择性非甾体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具有非甾体结构,使其能够以独特的机制与MR结合,以抑制参与肥厚、促炎和纤维化基因表达的转录辅助因子的募集[12]。
FIDELIO、FIGARO-DKD两项RCT试验研究结果及将FIDELIO-DKD和FIGARO-DKD进行汇总分析的FIDELITY研究结果均显示,非奈利酮已被证明在降低DKD患者的心肾结局方面具有很好的作用[13]。
2.内皮素(ET)受体拮抗剂(ET-A):ET是一种血管收缩多肽,参与了DKD几个关键环节的发病机制,包括胰岛素抵抗、高血压、炎症和纤维化。在肾小球血流动力学方面,内皮素可增加肾小球压力,并与蛋白尿有关[14]。ET-A已被证明可降低蛋白尿和血压。然而,RCT研究引起了人们对ET-A液体潴留和心衰事件的关注[15]。选择性的短期ET-A药物,如阿曲生坦(Atrasentan)可能在肾脏保护作用的同时减少不良事件发生,这已在SONAR研究中进行了测试[16]。阿曲生坦虽有望成为T2DM和DKD的治疗药物,但存在因液体潴留、贫血和心力衰竭住院的风险,尚不清楚其是否利大于弊。
3.抗炎/抗纤维化药物:一组旨在通过直接抗炎或抗纤维化途径改善肾脏结局的Ⅱ期RCT研究正在进行中。SAPPHIRE试验[17]评估了一种可减少肾脏中尿酸再吸收的尿酸转运体1阻滞剂对减少CKD患者蛋白尿的作用,探索了尿酸代谢的一个独特机制,包括对肾脏中氧化还原平衡的潜在影响。
一组Ⅱb期研究正在探索直接抗炎药物在肾脏中的疗效。如MOSAIC试验,这是一项针对凋亡信号调节激酶(ASK)-1抑制剂Selonsertib的研究,旨在评估其在中晚期DKD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18],此外还有FRONTIER试验(IL-33抑制剂)和FLAIR研究(FLAP抑制剂)等。所有这些药物均针对参与CKD进展的特定炎症途径。
Janus激酶与转录信号转换器和激活因子(JAK-STAT)通路在DKD的炎症反应中有重要作用,并在肾小球和小管间质细胞中驱动多种趋化因子和其他促炎因子的表达,这一途径是由肾细胞(系膜细胞、足细胞和肾小管上皮细胞)的高血糖诱导。一项Ⅱ期对照试验结果显示,一种JAK1/2抑制剂Baricitinib可显著减少白蛋白尿和炎症生物标志物水平[19]。
4.低糖基化终末产物(AGE)饮食: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坚持健康的饮食模式与较低的糖尿病患病率之间存在关联[20]。尽管地中海饮食或热量限制和体育活动可预防或延迟T2DM风险人群的发病,但T2DM和DKD的持续流行表明,这类高要求干预措施在社区层面的成功有限。饮食和内源性AGE可增加糖毒性,小鼠饮食中过量摄入AGE会导致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和肾损伤,相反,低AGE饮食可预防这些疾病[21]。饮食中AGE是一个潜在的可改变目标,因为低AGE饮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食物制备方法,其极易融入许多饮食模式。高温和干燥条件下的烹饪方法会产生大量的AGE,特别是在动物性和高脂肪食品中,而低温和高含水量的烹饪方法会降低AGE。到目前为止,低AGE饮食已在小规模的人体研究中进行了测试,还需要在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中进行验证。
5.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肠道菌群作为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已成为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关键调节器[22]。肠道菌群产生的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s)、氧化三甲胺(TMAO)、胆囊酸(BAs)、多酚类、色氨酸衍生代谢物、支链氨基酸(BCAAs)等]在DKD发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能对宿主产生致病或有益的作用。这些代谢物及其最终产物可能在宿主的代谢网络[23]、免疫过程[24]和神经生物学过程[25]中发挥关键的作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代谢物能起到作为DKD病理生理特征的生物标志物或致病因子的作用。未来可寻找用于治疗DKD的微生物代谢产物。尽管存在很多困难,但微生物相关代谢物的产生和信号转导所涉及的代谢途径是调节疾病易感性的巨大机遇。
三、挑战和治疗前景
1.DKD管理的依从性挑战:DKD的管理在操作层面仍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在一项针对全球中晚期CKD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患者对基于KDIGO 2021指南的CKD推荐治疗依从性较低,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26]。RAASi处方从52%到81%不等,只有<50%的患者收缩压低于130 mmHg,蛋白尿测量不规律(各国为36%~43%),饮食建议不常见。在大多数国家的糖尿病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个体达到至少4个基于KDIGO 2021指南的临床护理目标,包括血压、RAASi、饮食和HbA1c。这项研究可窥见广泛实施循证推荐实践的困难,反映了患者和医务人员在教育、治疗耐受性和依从性方面的挑战。
2.中医药治疗DKD的挑战和前景:在我国,中药汤剂广泛运用于临床治疗DKD患者。中成药制剂如雷公藤多苷片、黄葵胶囊、虫草提取物等,对于减轻蛋白尿、稳定肾功能有一定的作用。但中药还需要积累循证医学证据并监测可能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26]。
四、总结
DKD是由一系列紊乱的代谢、血流动力学、炎症和纤维化过程驱动的,疾病机制的启动和进展受高血糖、高蛋白和AGE饮食、肠道微生物群改变和遗传易感性等因素影响。这些干扰引发的下游效应有助于促炎和促纤维化介质的释放及表观遗传变化。因此即使血糖达标,这些介质的持续表达也可能导致疾病进展。尽管最近已取得治疗性突破,确立SGLT2i和MRA作为新的有效DKD治疗方法,但仍存在DKD疾病进展和并发症的残留风险。其他靶点包括GLP-1R、ET-1、ASK1、JAK/STAT、包含3个炎症因子的核苷脱氧核糖核酸寡聚结构域样受体pyrin结构域的选择性抑制剂,这些靶点都在研究中,以满足降低额外风险和个性化治疗的需要。简单的饮食策略,如低AGE饮食也可降低DKD风险。综上所述,未来将有一系列新疗法和举措,为DKD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