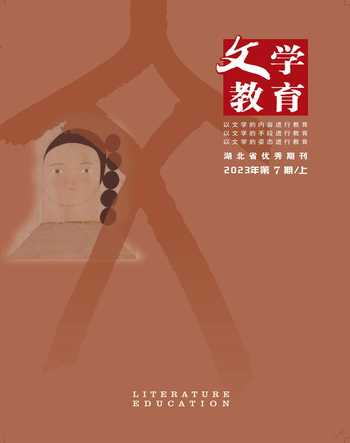鲁迅《野草》与《彷徨》的抒情交融
裴小维
内容摘要:“抒情”是解读鲁迅作品的关键之词与主要元素,凝聚了鲁迅将含蓄、隽永之艺术韵味放置于诗学、美学层面的情思结晶,不管是在《野草》亦或是在《彷徨》之中都蕴藏了鲁迅将细微但连绵不绝的心语世界构建起来的抒情世界和纯文学追求,而两部作品在意象和人物的交叉融合之中饱含鲁迅同质的情感和共同的诗性表达。本文在国内学界研究审美关照不足和鲁迅形象“欠缺”的不完整性基础之上将抒情交融置于审美诗学和小说深蕴的关联和结合之中,对鲁迅的抒情问题进行了一个诗学、美学方面的叠合,以使得鲁迅的作品更具有艺术张力和诗性品格。
关键词:鲁迅 《野草》 《彷徨》 抒情交融
“抒情”是解读鲁迅作品的关键之词与主要元素,凝聚了鲁迅将含蓄、隽永之艺术韵味放置于诗学、美学层面的情思结晶,对于再度解读鲁迅作品的多层复杂内涵与以诗学视角投射鲁迅作品的审美精神有着举足轻重、不可忽视的作用。1924-1925期间,鲁迅创作了著名作品《彷徨》小说集,几乎是同一时间,鲁迅于1924年12月1日-1927年4月26日期间也撰写了共有24篇的散文诗集《野草》。比起立足于纯文学追求目标以抒发鲁迅心境和精神状态的较强抒情性散文诗集《野草》,鲁迅的《彷徨》不同于《呐喊》而是以主体性的诗化风格将抒情寓于叙事之中,用寥寥笔墨将那个时期作者无法解决的思想矛盾、孤独、彷徨、寂寞、苦闷注入并映射在人物之中。但唯一不同的一点是在小说之中具有不为人所意识到的潜在情感和主体色彩,所以小说中所塑造的往往都是进入“抒情”内在文本结构路径的具有审美特征和诗化情感的被解构、重构、主观化的人物形象。
一.《风筝》与《伤逝》中的赎罪交融
《风筝》于1925年2月2日《语丝》周刊第12期发表,后又编入散文诗集《野草》之中。[1]12对《风筝》的抒情解读并非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篇具有浓厚乡愁情思的回忆性散文,而蕴藏在承载着创作主体心灵世界和生命体验的客观物象——风筝的背后是抒情主人公那深刻的歉疚与由衷的忏悔。当“我”在腊月寒冬的北京看到“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时“我”便在脑海中隐隐浮现出故乡早春二月时节和弟弟放风筝的儿时情景与童年回忆。而年少无知的“我”却残忍地“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同时也悄然毁灭了弟弟小心翼翼捧在手心里视若珍宝的童年和快乐。成年后的“我”因看到同质异构范式的“风筝”却也遭到了精神上的惩罚和道德上的谴责,当“我”意识到扼杀弟弟玩风筝天性的罪恶之后便试图使自己的痛苦和愧疚得到宽恕及原谅而去向弟弟忏悔。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来说,作为亚当夏娃后代的人类身上秉持着先天性和自觉性的原罪意识,而唯一的解决途径便是不断地忏悔最终得以减轻负罪感和自责感并得到解脱与释怀。身为中国人的鲁迅并不会选择去向上帝耶稣进行忏悔,而是希冀得到弟弟的原谅并能够听到弟弟说那一句:“我可是毫不怪你呵。”但事与愿违,鲁迅的弟弟却以一句极其轻描淡写和满怀毫不在乎的语气进行反问“有过这样的事吗?”另“我”如鲠在喉,耿耿于怀。被原谅、宽恕的前提是我记得、我怨恨,但全然忘却却是以断绝宽恕机会为零意义补救方式最为深刻的主体悲哀和精神虐待,[2]111它让自救的希望陷入新一轮并无限循环下去的绝望之中,被宽恕对象将永远得不到原谅与悔过。“我”因无以得到化解的溝通和交流并成为兄弟二人精神对话与情感抒发的阻隔和障碍而加深了自己的忏悔感和罪恶感,所以这部作品的抒情导向便是那自省、悔过、歉疚的情愫。
其实在小说《伤逝》之中也有这种无以复加的抒情基因和精神倾向——罪恶意识,这部小说于1926年8月出版在现实主义作家鲁迅的著名作品《彷徨》之中。鲁迅本人的情感丰厚、深沉、热烈而又复杂,而作为他的抒情小说典范之作,《伤逝》的主人公涓生将他最集中的孤独、寂寞、后悔等情愫书写在具有浓厚诗韵并贯穿全文的忏悔之中。《伤逝》可以说是鲁迅的心灵之诗,尽管这部作品以”不采诗行”的结构重新诠释与解构诗歌的精湛范式,但涓生对子君的愧疚使这部作品的抒情功能和诗性表达高于其他小说作品的审美观照与诗性品格。在短暂的热恋交往与甜蜜的爱情回忆之后,我们在涓生浓烈倾泻在子君身上如潮水般的爱意与倾慕后发现他们未能达到理想爱情中的琴瑟和鸣、灵魂共舞,接着两人由于经济基础的薄弱和爱情落入日常生活的俗套——变得食之无味后迅速地坠落爱情的破裂、虚无,由于各种现实压力的阻碍和苦于生计的束缚涓生向子君表露的冷漠态度已成为他们恋爱关系中的剪子,并在无形之中逐渐剪短了他们维持爱恋关系的亲密与承诺,涓生最终因子君的郁郁而终而对自己进行强烈的谴责和深刻的忏悔。但更深一步进行思考,涓生的忏悔实则上是为了深情而设立了一个“应该”去忏悔妻子的深情人设。诗比历史更真实,倘若深入探究古代文人悼亡诗中的男权话语建构,便会惊觉这些表面深情悼念和追忆已逝妻子的诗人男性实际上何尝不是借用一个已丧失发声话语权的女性指称对象以宣泄自己的不安与道德上的内疚,并为了弥补精神上的不安去标榜所谓的深情与道德。而涓生面对子君的死毫无任何情感上的罪过,仅仅只是通过感伤文字直接而简单的诗情特征和美学意境以达到内心情志的终极平衡。由于内心深处一直萦绕不散那错综复杂的纠结负罪感,涓生秉持着畏惧罪恶的心态对子君进行无限次的忏悔,到文章最后这段为自己罪过买单的罪恶感达到了全文的高潮和顶峰,“我愿意真的有所谓鬼魂,真有所为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3]160至此,涓生的愧疚虽是短暂而脆弱的,但也是真实而痛苦的。《伤逝》以抒情诗的传统技巧和抒情话语对涓生心灵深处的负罪感表达到了极致,这种郁结在心中的愁丝浸透着涓生忏悔的隐秘情怀,[4]142-143可谓是“抒情的小说”。
正是这种所谓深陷泥沼的赎罪之感构成了《风筝》和《伤逝》抒情结构之中的主导性力量,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赎罪,使得摄人魂魄的情感对比深深地震撼和强化了鲁迅作品的表情达意功能,塑造和彰显了鲁迅作品抒情品格的发生意义。
二.《颓败线的颤动》与《祝福》的冷漠交融
鲁迅在《野草》之中创造了一类打破读者既有固化思维和超现实抒情感知的传统意象——颤动的“颓败线”,这部作品是鲁迅裹挟着诗化的语言和使用跨文体的抒情方式对“老妇人”形象背后蕴藏的深层内蕴的审美价值体认与塑造。在这里,鲁迅用破裂之美的语言和颓靡绮丽的色彩风格塑造了一个极具视觉震撼力的、痛苦迷茫、躯体颤抖的垂败岁衰的“老妇人”。[5]55进入鲁迅的“梦文本”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梦不同寻常以做梦者主体境遇和遭况为主要叙述对象,而是以梦境之中的垂老女人际遇为主,这便更循着曲折含蓄的抒情轨道将“我”的情感潮水与站在旷野中央对命运不公进行诘问的女人情绪意向水乳交融,这种变形折射的抒情手法则更具象征意义和诗性韵味。这位羸弱瘦小的母亲无言但有力的一瞥是一种精神上的战栗和窒息,具有惊天动地的巨大情感落差:哑忍与抗拒,凄苦与慰藉,凌辱与贞洁,绝望与希冀等诸多相似又对立的情感河流融合又交汇,淹没并杀死了一切,又使新生事物发芽并盛放。但“我”很快在梦中“呻吟着醒来”,往昔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母女两人关系本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和重构,成人后的女儿一家以怨报德、将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伦理道德问题“饮过我的血的人”堂而皇之地暴露在外,并用连珠炮似的辱骂和异口同声的讨伐使老妇人最后一道精神防线和借以生存的“精神意志”彻底崩塌和摧毁。其中诗歌中玩芦叶的小孙子对其大喊一声:“杀!”与鲁迅先生在《彷徨》中的《孤独者》一篇相互对应,“我”与魏连殳讨论有关小孩子的善恶后也出现了相似情节:魏连殳在路上碰见一个不大能走路的孩子扔着芦叶说:“杀!”[3]111于是认同了“我”的观点。可见这一情节或许曾真的出现在鲁迅先生的生活中,让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波动与对所谓“性本善”的深深怀疑。老妇人在无言的同时已被自己用血哺育的儿女剥夺了生存下去的意义,残躯的“颤动”裹挟着繁复庞杂的抒情之悲油然而生。若从许广平《两地书》中鲁迅的信来深入理解和透彻剖析,读者便触及到了此篇散文的梦境深层涵义并不是单写劳动妇女的悲剧命运,而是更深入地、复杂地渗透鲁迅先生对于人性本体所秉持的忘恩负义、寡恩薄义、人情冷漠等丑恶行径的愤懑和失望。[7]23-24
鲁迅通过梦境与抒情在他的这篇作品中创造了“老妇人”的形象以及其被他人冷漠处之、鄙夷待之的可悲处境,与《彷徨》中的著名小说《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相互对应,《祝福》不乏“以散文之形”叙事的的诗学方式,但其更偏重的则是创造一个冷漠与讽刺互映,精神绞杀和世态炎凉凝聚起来的复杂情感世界,每每一团思想、一堆情感的焊接、组合和交融都构筑了《祝福》这篇小说情感价值和思想蕴涵的抒情大厦。“看客”是鲁迅用愤慨的笔墨塑造的经典艺术形象,他们的心理是残酷地鉴赏、无聊地起哄、敌视地嘲笑与幸灾乐祸。[8]122在鲁镇,受到落后思想荼害和封建礼制压迫的麻木人群通过消费祥林嫂的不幸和痛苦来满足本体的需求欲和以幸灾乐祸的扭曲心理来使他人的唏嘘经历成为枯燥家庭和无趣生活的“调味剂”。这群保持着看客心态的“旁观者形象”是鲁迅作品中经常出现并不惜笔墨重点关注和描写的一类人群,创造的意图往往是为了揭露国民性质的劣根性,以愚昧麻木的冷漠形象唤醒嗜血如命的中国民众。鲁四老爷便是一位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疯狂榨取祥林嫂质优价廉的劳动价值的同时对她的身世命运毫无怜悯之心,甚至在祥林嫂两次丧夫后将麻木冷漠和自私残忍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嫌弃和厌恶在用“谬种”总结祥林嫂的亡故后彻底蜕变成逼死祥林嫂的“施暴者和刽子手”。还有和她同一个社会低级阶层和同处于旧中国劳苦妇女地位的柳妈,虽和祥林嫂一样饱受欺凌和奴役,但却以一位高高在上的优越者形象俯视和鄙夷经受命运摧残的祥林嫂,甚至步步紧逼祥林嫂承认他们认为不守妇道、有伤风化的有罪标签,[9]82但这并未停止对祥林嫂的精神摧残,柳妈告诉祥林嫂女人不洁的后果便是死后到阴司会被两个男人劈成两半,这便通过对肉身惩戒的恐吓将福柯规训的“监禁”画卷展现了出来。一位印度演员阿米尔汗曾在节目中说:“女人的贞洁是由我的心灵决定,而不是由我的阴道决定。”封建礼教毒害下的男性和女性都将女性主观动机的豁免权剥夺,她们的地位和身份始终是被卑鄙险恶的“吃人者”居高临下地进行审判,在确认结果和证实事实之前就被代入了怀疑和否认的前置审视,倘若女性想要平等的公道就只能滚钉板喊冤。她们不停被套上无形但十分沉重的道德枷锁和性别束缚,还要被迫将自己的伤口被他人当作宣泄表演欲的出口,解释一个本就无需多言去解释的“为什么”。所以女性主义批评便很好解释了受到男性视角和男性束缚规训而成的女性特质,这一特质在同性别的扭曲和毒害下演绎到了泯灭人性的巅峰和极致,封建父权社会不仅是吃男人也吃女人的社会,也是男人吃女人的社会,更是女人帮着男人吃女人的社会。而鲁镇上其他人也都是“旁观者”群体的代表,他们将祥林嫂的悲惨经历反复“咀嚼”和“鉴赏”并且当作茶余饭后和凸显自己幸福的谈资,非但没有共情也没有小心翼翼怕触及到祥林嫂的痛处,而是在“坐稳了奴隶”的身份之后站在以同类悲剧为乐趣的至高点上吃更为弱小群体的血肉,最终认为榨取不到“快乐”并选择“满足的去了”。人总归是有血肉、有情感的,只不过在黑暗封建制度的“规训”中逐渐被消解、被割裂,在愚昧的冷漠拧结后扭曲成面目全非的人性。集体的冷漠力量是无比巨大的,尤其是这种在绵长黑暗制度与源远封建礼教环境下滋养并生发出的集体无意识——冷漠之情,更是在采撷旁观者的“罪恶之花”后具有毁灭性的力量。
《风筝》里的“我”对弟弟的忏悔之意与《伤逝》之中的涓生对子君的赎罪意识紧密交融,鲁迅在心灵深处对自我精神进行了一场毫不留情的解剖手术,使得小说和诗歌的诗情特征和浓烈的诉诸情绪翻滚倾泻进读者们的心田。[4]142《颓败线的颤动》将老妇人的“无言呐喊”与《祝福》中的祥林嫂的失语特征结合,她们都是在冷漠麻木人群的鄙夷下被逐渐排斥到社会边缘的异类群体,都在强烈浓郁悲情下将希望与绝望进行了融合和重叠。不管是在《野草》亦或是在《彷徨》之中都蕴藏了鲁迅将细微但连绵不绝的心语世界构建起来的抒情世界和纯文学追求,笔者通过鲁迅缠如毒蛇,虬如老松的语言力量将被边缘化的抒情文学置于作品政治性和思想性的有机体之上对抒情问题交融的丰赡内容进行全面的开垦和深究。而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中国现代散文诗之师”的鲁迅,更是在审美意识与理性认知之间以高度的精神诗意性和深刻的思想复杂性偏向于对作品抒情功能的书写和艺术情景的重视。本文在研究审美关照不足和鲁迅形象“欠缺”的不完整性基础之上将抒情交融置于审美诗学和小说深蕴的关联和结合之中,[10]81对鲁迅的抒情问题进行了一个诗学、美学方面的叠合,以使得鲁迅的作品更具有艺术张力和诗性品格。
参考文献
[1]原诗萌.1923—1927:《彷徨》、《野草》中“自戕”意识探索[D].吉林大学,2006.
[2]张崇玲.真诚的忏悔艰难的交流——鲁迅《风筝》解读[J].语文学刊,2007(02):109-111.
[3]鲁迅.《彷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
[4]杜秀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源头——论鲁迅的抒情小说[J].社会科学辑刊,1989(01):140-145.
[5]黄飞.论中国现代抒情散文的诗意追求[D].福建师范大学,2004.
[6]赵凯.《野草》的梦幻与悲怆[J].安徽大学学报,1996(03):48-49.
[7]从月.《野草》的文体选择与抒情策略[D].湖南师范大學,2004.
[8]席昳旻,许晓瑜.祥林嫂“失语”原因探析——从重复叙事谈起[J].汉字文化,2022(11):121-123.DOI: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2.11.034.
[9]乔保玲.无尽的同情,无情的鞭笞——鲁迅《祝福》中祥林嫂悲剧命运探析[J].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2021(09):81-82.DOI:10.13525/j.cnki.bclt.2021
09029.
[10]席建彬.“抒情传统”中的鲁迅研究——关于“文学鲁迅”问题的思考[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06):81-87.
(作者单位:江苏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