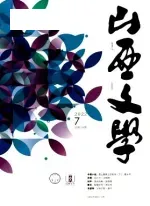一晃经年
刘 婷
村落
村子在县城西北,傍着汾河,西行的主干道从村子的心脏上呼啸而过,为它输送新的血液和养料,如果再加上二十一世纪中现代文明哗然的蒸腾,这里便如同烤箱中的面包一样,迅速地迭变,膨胀。
在汾河还被奉为神明的历史中,村庄是谦卑的、安谧的。农人的耕耘、制香人的作坊,全赖河水的恩赐,人们不惜耗费工力,在土地上挖出一条豁口,让河水能更深入地滋润这片土地的肌体。现代科技到来的前夜,人们尚且泛舟河上,带着一壶老醋,划向十里之外的村庄,去探望黄土墙下抽着旱烟的老舅。村中古庙中拆卸下的梁木,纷纷投入这南行的河流,向着市中的学府,装点七八十年代一方学子的象牙塔。
现代文明的横行注定需要先驯服那条邻着的河,一点一点与它缠斗,悄悄地侵占它的躯干,让它虚弱,由它枯槁,然后囚禁它,圈养它,让这“洪水猛兽”成为安澜平静的萌宠,穿着人们精心设计的草皮与花树,点缀着彩色的荧光,孱弱如美人。然后彻底忘记它是共工的后裔,曾经冲天奔地,肆虐九州,让大禹为之头痛,汉武为之畅醉。
孱弱相对的是村庄的雄壮和现代文明的强悍。这是一个生产力裂变的时代,人们不必再死守着土地,向老天讨要一年的米粮。工业入驻将会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人们簇拥着厂房,朝八晚六地生活,流水线上的香、机床上的零件、温室之中的菌菇或者厂房之中的香醋,都会通过公路运输出去,最终走向市场,换取村人们的生计。生计之余,人们开始打扮着村庄,小区代替平房,公路代替土路,人们种起了行道树,立起了路灯,此时村庄已经褪去了蓬头垢面,精心妆成了城市。
领略了大部分村落,太多的整齐划一,总让我想起在水泥地之下覆盖的莽原。但现代文明铺天盖地,铺陈出幅员辽阔的同质的土壤,迅速被人们捏塑着,成为示范、样本,直至城市成为森林。
村中的人向我描绘了村中制香的历史,从陕西迁来的一户人家,在寺庙成群的村子中落户,从此家家户户以制香为生计,洪洞一带的香火灯烛,大多来源于此。
香火延伸的是土地上的信仰,在我去不了的历史中,我曾多少次想象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景,这一刻,仿佛就在这土层之下。一望无垠的寺庙楼阁,连着汾河水岸,鹳鸟高旋。人们从岸边挑了水,在凉棚下和着木屑,抽成长条,再剪裁成细香。翌日,妇人将晾干的香取下,捆成把,由丈夫挑着担子,赶在第一缕阳光缀上燕翼之时,在寺庙前叫卖。
“卖香嘞——供奉神佛菩萨的高香——”
与吆喝声一同在时空中氤氲的是烟雾的缭绕,如果有能够洞察古今的延时摄像,那么这烟气必然是慢慢地弥散,那些曾经的庙宇:水神庙、老爷庙、奶奶庙、三官庙、土地庙、玉皇庙、圣王庙、原君庙,从香火鼎盛到无人问津,再到最后,镜头前只留下凋落的庙宇,慢慢荒圮,成为废墟。
村中仅剩下两家世代制香的作坊,也双双摒弃了传统的手工制香,超越于历史上一村垄断洪洞香业的盛况,今时只需一家便能应对市场需求,多余的产能远销他乡。村中的人,走进了学校工厂,也有外出远行的人。在工作时间,街道空落落的,安稳,雅致。
村中尚有一二与历史较劲的人,他们在村落之中,修葺了寺庙,在门口浅浅看了一眼,这里供奉了佛道儒三教众神,似乎有心将那些被人所遗忘的神祇一处安放,为村庄修补一段远古的记忆。也有缝合文字的人,历经三年,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结成一本村志。
觥筹交错间,修志人隐约地提了一句,要让村志成为子孙后代铭记历史的工具书。便仔细问了村中的家族情况是否有记载,修史人说村中几大家族、零星散姓,应有尽有,想到修志人东家跑西家问的口舌功夫,油然地生出佩服和敬仰。
发展并不一定需要遗忘所有。又或许,社会的温度并不在于文明发酵的程度,不管是传统或者现代,一个村庄的温度最终还是人心的黏合。在香厂,我看见张贴着一张招聘50 岁到60 岁老年人的启事。在中学,办学人斥巨资为学生打造了省内一流的塑胶跑道,在村委会中,有一份记载翔实的留守儿童档案。在寺庙戏台下,簇拥八仙桌老人在曦阳下做着活计……在文明迭变所弥生的缝隙之中,是人心愈合着文明的伤口。
啊!在现代村落的肌体之中,涌动的,终究是人!
出离
从热闹中出离,模糊的喧闹与寥落的心迹生出了一种唐人的意趣——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村中的路弯弯曲曲向天空延展,尽头是砖红色的门楼,一边临着山崖,一边依着庙宇。灯光明明暗暗,又多情悱恻,如同班婕妤孤身在宫闱中挑动的红烛。
灵魂相对时,我想此时我与村庄都有些尴尬。她拒绝着我一切的触碰,街道上闲散溜达的鸡鸭惧怕我的热切,蹴跃过院外的篱笆墙。猪圈中的母猪惧怕我的探究,用身躯掩住崽子的视线。瘫在麦粒上的野猫不肯让我抚摸,蹿进了文化栏旁的车轮下。路旁散发清香的幽兰,埋首灌木丛,不肯接纳我的仰慕和笑靥。
可谁能阻挡醉酒之人的告白呢?我对着她的背影,拉扯了一顿陈年的闲话。我说很多年前,我的母亲已经帮我拒绝了泥土,他们将我裹在城市的玻璃房中,透过电视,我学着去用流行的音乐和彩色的画笔去歌颂城市和工业。他们说土地是粗鄙的,我们要无限地走出去,让外埠的阳光为自己换个筋骨,然后驱使着摆臂机械,高高在上地划破土壤。
我说自己现在是个“光鲜亮丽”的打工者,用着三十岁的精力和颜色来讨好俗世盛赞的功名和安适。把自己活成一把电钻,听从一些所谓“流行”的指挥,不顾一切用力,永不停歇做功,跳跃着触碰那些俗世的功利奖赏,但所得很少。
我说我被城市和文明钳制着,心里还暗藏一片原野,她春时澹冶如笑,夏日苍翠如滴,秋妆明净,冬睡惨淡,娇羞与嗔怒时有薄荷味的柔风。它曾醉倒在我的画卷前,披一身落花,睡梦中说要赠予我四时明媚,像春泉,夏山,秋叶和冬云。
村庄升起了凉风,她柔柔地落在我的肩上。
某一刻,我想我被诱惑和劝解。她说不必仿照文明的规整,且去追随自由肆意的灵魂。院子里可以疯跑着蔬菜和爬蔓,道路上仰卧着车辙和麦粒,小卖部也可以是邮局和茶水铺,屠夫的别院中滚着热辣的羊汤。她说皮囊污浊,定义沉重,地图无效,不必把自己摆在那一种框架中,耕地的是农民也可以是教师;敲大锣的可以是隔壁的大婶也可以是从城市回来的露丝。不必努力去钻研,浪费人生在某一种不实用的方向上。只需坦诚地照顾好自己的吃喝拉撒,然后开怀地笑。
我想我应该犹疑和确认。风混杂了麦田、羊粪、藤蔓和炊烟,我埋首在村庄的血管中,放纵,恣意,啃食,口器未深入肌理,啮咬不到肌肉,热切且不得方向,如同探入的针头、吸血的蜱虫、拖着脐带的巨婴、入侵而来的异生物。我充满了窥探的欲望,想敲破高墙深挖根基探明它的来龙去脉,汲取她魂中的真谛,真切我不明的渴慕。
疯狂,无礼,又或许有些放纵。她只是转身,将灯火点亮,让我看清归途。
路已经走到尽头,那复式的小院比远处的寺庙更显暖融。灯光刺向我的眼,用俗世的“亲厚”刺向我心生的疏离。她温柔地擦拭我面额上的汗水,原谅我因酒意催生的唐突与疯狂。
推杯换盏的声音又起来,职场中的口蜜腹剑又混迹于人声。进入门的一刹那,我又在灯火的映照下成为“体面人”。我内心的那个自己某一刻浮出水面,冷若冰霜地注视着自己,仿佛丝毫没有被酒意融化过。我眼睛恢复清亮,像君子一般衣冠楚楚地辞行,体面优雅。不过多久,我们的车应该会走出这片高垣,那么风和灵魂,又成为被我弃若敝屣的旧书本,一页也不愿意再翻起。
抛下村庄时,我听见风在轻嗤地笑!
饼
下班的时候,转过街角闻到了饼的味道。
街道的起点、末尾、中心,小区、学校、工厂的附近,有人群往来的地方,总会有一个饼铺。那些年,家住在赵城,火车站到磨头的十字路口处就有一家饼铺,铺里售卖的是炉火现烤的圆饼、三角饼和半圆饼。小时候,村中人称饼子为“宣子”,每每爸爸拿出几毛钱吩咐我到街口买“宣子”,都能看见我妈附送的白眼,“别学你爸的口音,难听死了。”
物资单薄的年代,饼中的馅料也仅有白糖、红糖,有些地方也有红豆馅饼,但豆沙着实是我饮食的雷区,所以家中可以看见的似乎多是三角形状的咸饼和圆形的糖饼。后来初一来到洪洞上学,理所当然地在某家买了三角饼,咬开一看,红糖甜死个人。才知道所谓形状,跟饼的甜咸没有绝对关系。
当王女士从洪洞某个小破初中把上课吃零食的我拎回赵城亲自管教时,我的常住地也终于从城边界走向了城中央。考虑到住校,王女士给予了我一定的经济自由。我便突然觉察到,世间的饭菜不只有王女士所做的西红柿鸡蛋菜和酸菜擀面,就连平素所吃饼子,也可以是丰富的:夹一些鸡蛋和香肠,切碎香葱和辣椒,再淋一口香浓的肉汤。一口咬下去,葱冲料厚。囫囵吞下去,即便是在寒风刺骨中,似乎也有了不惧冷意的屏障。当然,吃完后还必须及时穿行二十分钟的路途赶回学校。即便如此,为了这一口滋味,辛苦也是值得的。
高中的饼铺在学校之中,这一段时光乏味可陈。在煎熬的岁月中,发现不了一家可以慰藉口舌的饼铺是难过的。故而在咽下十几个蒜薹肉饼之后,馋嘴的本能便开始做起了自救的营生。你看,单吃饼对于口舌来说一定是乏味的,若一定要增长滋味。卤蛋天生寡味,煎蛋又干巴巴的,香肠好吃但量少不能尽兴。只有那红扑扑香津津的辣条,天生与饼相合。咸辣的滋味弥补了寡淡,朴实的面饼也中和辣条的香冲。高考前那些争分夺秒的日子里,披着星戴着月,在人来人往的操场之中,用一个喷香的饼,填饱饥肠。再迎着北风,匆匆地走进教室,将许多书卷,装进脑中。那时候肚子饱了,头脑撑了,便有力气,让自己走远。
忻州的饼是一种乡味的嫁接。在忻州师范的那些日子,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领略到晋南的卤味镶嵌在厚实面饼中的绝妙滋味。俗话说,一个大学养育一方经济,因此门口的街上常年总有一些小商小贩就地经营,食物样式多,花样新,仅饼就有四种:油炸过的白吉饼,夹上铁板上用辣椒和洋葱煎过的里脊肉。稍微放一下散过热气,大口咬下去,饼酥软,肉香嫩,堪称忻府区汉堡王。王女士念念不忘的是一种春饼,饼皮类似于洪洞的春卷,里面加上土豆丝胡萝卜丝豆芽之类的蔬菜,清清爽爽地,让人唇齿留香。王女士在忻州待的一天一夜中,连吃了三个春饼,多少年后,向人提起,也会盛赞其中滋味。鸡蛋灌饼是同学最为热捧的,每每过去,都有一行长队。我光顾较多的是角落中那一家运城夹肉饼,炉中烤的那种。每每过去,总能看见那老妇人,用力地揉面,然后将案板上那做好的面饼放在火炉中,再拉开一个抽屉,将一排烤好的饼,倒出来。
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总会寻找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时间变幻出春夏秋冬,岁月演变出风雪雷电,一方土地的河流和庄稼总会在炊烟袅袅中幻化出一种属于地域的味道。味道也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味觉的东西,它与你的眼耳喉鼻息息相关。在晋北的街道上,你拗着一口普通话,买饭的大爷用着耿良的嗓音与你应和,递到手中的饭,似乎都沾染上了晋北的倔强,硬得打牙,干得如同皲裂的土壤。
那些年心中叹息过的是,出了临汾再也找不到地道的牛肉丸子面,出了临汾再也吃不到咸香麻辣的大盘鸡。那些年腹诽最多的是忻州的辣椒,在一个晋南人看来,便如同闹着玩似的,用勺子舀上几大勺,仅能增个香味,想要驱散严寒,吃得汗流浃背,口角冒汗那是万万不能的。其次便是大盘鸡,吃了几回大盘鸡,那酱甜口,让人心中发腻。心中不住地暗想,或许多放些辣椒,便隐隐约约咂摸到了家乡的味道。但是味道却在摇摆中总越过那个最佳阈值。许多手法上分明应该,但你知道,永远到不了。
所以,我时常光顾的便是那家运城夹肉饼店。老板是运城人,说话隐隐带些运城的软嗲,与晋北的大汉吵架般的嗓音比起来,着实软和许多。卤肉是用砂锅煨的,掀开盖子,看见的是黑赤色的酱汁,冒着气泡,泛着油光。店家会根据你的需求给你选肉,有单爱肥肉的,也有单爱瘦肉的。但店家总会贴心建议你选一块肥瘦相间的,在中间带有凹槽的案板上切碎,和上青椒、香菜碎,再浇上肉汁。吃下去精肉会带出肉香,而肥肉则会化成汁水,嵌入烧饼的肌肤,在咀嚼中添上一份乡味,让胃肠在冽风寒岁中得以安实,也让天地之间的羁旅中有一丝温柔的暖风,牵牵绕绕,念念不忘。
上班之后,饼便如行军的干粮一般。打工人熬夜或者贪睡,路途中顺手买到的烧饼就是一日的踏实。饼铺临着街道,做饼人对着大街,娴熟的手艺下,还能与问询的顾客一搭一和。“来了,要什么饼,夹不夹东西?”只见那人牵着孩子,一脸嫌弃地说,“倒霉孩子贪玩不做作业,今天得迟了,夹个鸡蛋让他补充点营养。”孩子则眼巴巴地望着卤水之中的香肠,试图做些反抗,“我要夹香肠和辣椒。”大人便呵斥:“夹什么辣椒,香肠,都是垃圾食品,那个豆腐串给他夹上一份,让你不早起,明天再这么晚起,就没饭了。”孩子还敢继续顶嘴:“哼,没有饭,我就去学校买得吃!”说着,饼铺的师傅已经将做好的饼递过来,顺口问上一句:“要不要豆浆,光吃饼干,豆浆也有营养。”家长欣然同意,顺手扫码便结了早饭钱。
上班人的基本操作是将小区和单位沿道之间的小吃铺子牢牢记下,这家的饼是油炸的,可以夹上炸的烧烤和肉,第二家饼店会有更好吃的卤肉,第三家是鸡蛋灌饼,第四家好停车。上班人的早饭总是在味蕾和盘算中计较,然后福至心灵在某一处停下车,选购上一份美味加料的早餐。当然,不止是早晨,许多个开会的夜晚,带着疲惫和饥饿,在某一处温和的灯光下接收到补给,那月亮会更加柔美,梦会更加香甜。
疫情期间,街道门市惨惨淡淡的,那一些市井之间的小吃店干脆关门大吉。早早出门,走在大街上,街上少了车水马龙,少了打开的门窗,少了窗子中的灯火,也少了灯火下忙忙碌碌地做饼师傅。人世间的烟火,在于流动,在于吆喝,在于你走在某一处的所见,所问,所听,在于那空气中流窜的炊烟和饼香。
人世间有多少种饼呢,历史长河之中,在长安的大街之上、在金陵的河流之畔、在汴梁的酒馆之中、在北京的梨园之邻,出现过松子饼、雪花饼、芋头饼,出现过黄精饼、卷煎饼、麻油饼,过水的是汤饼,笼蒸的是炊饼,油煎的叫煎饼,炉熟的是胡饼。几千年过去了,每个时代自有挚爱的菜肴,但时间愈久,我们仍然欣然接受的,寥寥无几。唯独饼,贵如天子也可在满堂珍馐之间捡拾一方烧饼,贱如丐子也能在嘈杂的市井之中咀嚼几口面饼。健康人吃其充饥,病乏之人食之温补。《寿世保元》中记载过消食饼和千金肥儿饼,用莲肉去皮,山药炒,白茯苓去皮,芡实去壳,神曲炒,麦苗炒,扁豆炒,然后用山楂去子,将这些等分为末,每四两加白面一斤,用水和,烙焦饼使用可以消食止泻止吐,定肚痛,益元气,健脾胃。即便是小儿无病,日常使用三五块,也能防患于未然。
真实、平凡、纯粹的东西,因为朴素,便可以丰富丰满。走在街上,此时山河平和邈远。数易风霜,天地依旧平常。时间横轴之上,固然有玉盘珍馐伴随着顶端英豪睥睨众生、惊艳天地,但千万黎民前行的行囊中,总会有一张饼可以填饱饥肠。
圪栏
洪洞一带将石头饼叫“圪栏”(音译)。这是一种采用石烹技术制成的面饼。每逢七月十五,十字路口,或者小巷巷口,那些满头银发的阿姨们便会用塑料袋装上几袋,坐上平板车,带着一些自家种的菜蔬一起叫卖。我微微减速,离个六七米,便有阿姨吆喝“闺女,刚搭好的‘圪栏’,买回去献‘爷爷’”。“爷爷”在我们这里是神明祖先的意思,土话音类似“压”,但“a”的音要稍微长一点。
记忆中,我是不爱吃这种饼的。丑陋——土质的“圪栏”坑坑洼洼,类似于月球表面的形态,火候掌握不好容易,黑一块黄一块,像门外头布满斑点状的流浪狗。寡淡——小时候也只有两种口味可选。椒盐或者甜的,尽管是口味可选,但你依然得说服自己咬下去的是一种硬点的面饼,不是土饼。但小时候又何必委屈自己呢?奢侈一点有旺旺雪饼,朴素一点大可捏碎方便面,再撒上麻辣鲜香的调味包。那能磕掉牙的饼,它只配在土地爷的香案上,放到除夕。
但“圪栏”制作时却是顶好玩的事情。这种饼还果真是在石头上给烹制出来的!石头要选涧河河滩上的小圆卵石——这件事通常是孩子们的事,一群人提着编织篮,一个下午,便能摸出足够的石子。等到了家,姥姥便从中筛出品相较好的,清洗完用热水煮过,便摆在院中晒几天太阳。
和面是用鸡蛋和水,一大家子六户人,姥姥总要和足够的面,我们从面上掐出小块在一旁捏面人。三姨总会对我们的行径凶上一脸,姥姥便摆出一脸慈祥出言喝止,“由他们去吧,孩子就是要玩!”老人家跟锅碗瓢盆打了一辈子招呼,烹制的事情也不愿借手旁人。姨姨们在旁边做一些擀面的活儿,姥姥已经熟练地控制好火候,将石头铺到鏊子上。
能够想起来的场景也只有这些,因为小孩子是远庖厨的。等玩回来,便有做好的石头饼可吃。加糖的称为“甜饽饽”,面饼薄者称“圪栏”。老人家手酸得很,但依然麻利地装好塑料袋,分给她的子女,并顺便撵走这一大群“不肖子孙”。我妈提着塑料袋,我尾随其后,麻溜地回了赵城。
和姥姥家的习俗不一样。爷爷家信教,因此我家的“圪栏”待遇也只是在储物箱之中,谁爱吃捻上一口。但我家人都一致性地健忘,久而久之,逢年底打扫时,便能从储物箱中原封不动地收拾出一袋。如此便收拾了几年。终于有一年,我家再收拾不出来“圪栏”。那一年,姥姥过世了。
我妈对于烹制饼类一向属于间歇性激情爱好者,以至于家中的电饼铛、鏊子、薄饼机在一段时间中会充斥于厨房。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制饼的机器便全部落了尘灰。我爸便装了塑料袋,收拾到储物间。每每过年打扫,我会在相同的位置为它们换上塑料袋,不由得想起曾经那些被处理的“圪栏”。不知珍贵的年岁中,它是地上草,是炉边灰,平凡得让你有足够理由漠视。可当你成年后,郑重其事地打算好好品尝其中滋味,它却只能属于回忆。
我再一次端端正正地注视“圪栏”,它已经换了个名字,明明白白地写在我各类工作文案上。工作需要,我要细致了解、妥善思虑,为“圪栏”——那中元节祭祖大典上的主角撰写画外解说。这一次,它被世俗人尊称为石头饼,是中元节纪念祖先的地方特色供品,需要在本地手艺最为精湛的老字号中专门订购,尺寸要不大不小,有薄有厚,顶端的几个要求绘彩,甚至连订购的数量都富含寓意说法。这一切的流程,我要牢记于心,并要写出精湛深情的文字,展现这一方薄饼所凝聚的特色文化。
你看,人生中这种“来年让你高攀不起”的戏码比比皆是。当年对它弃若敝屣,如今它倒摇身一变成为大爷,我便只能演起了这奴仆的戏码,苦笑着盘算这番“孽缘”,心中问候并查询起了它的祖宗十八代。
查起来便明白了,大爷还真是大爷。至少人家属于存世的活化石,见证并贴心陪伴人类从猿人到现代人的艰难历史。资料显示,大爷诞生于人类开始使用火之后,人类乍一步入熟食时代,大爷便从石烹中产生。据说发明者还是尧帝。
严肃的腔调中,故事是这样讲述的。相传有一年新麦丰收,大雨使得粮仓坍塌,麦粒被压成粉状。雨后初晴,人们舍不得将潮湿的麦粉扔掉,便把这些麦粉铺于石板上晾晒,却在火热的太阳下闻到了奇异的香味。于是尧帝便教人们用石盘、石棒将黍麦打碎,以燔黍之法烙制面饼。流传至今,晋南一带便常在麦收之后烤制石头饼。
考证缘由自然能为历史插上想象的翅膀,但把所有功绩归功于尧帝也不是历史学应有的视角和思维。可以推测在黄河流域这片土地上,曾经有那么一群先民,在荒野和莽原弥漫的黑暗年代,最先撕裂出一线智慧和生机。他们在烈日炎炎的酷暑之中,反复向自然求证这香气的来源,从追寻到懵懂再到灵感迸发,一种食物诞生了。它为部落所热爱,所痴迷,人们带着它从石洞走进了草屋,再走进千家万户。在汉武帝横舟河汾之时,尝到了它朴实的滋味,被列为贡品。在唐代,人们给它一个文雅的名字“石鏊馍”。流传至明,至清,它依然是乡人口中磨牙的零食、远行的干粮,去过战火纷飞的前线,支援过人民子弟兵,到了今天,它被现代人排挤在生活之外,但在祖先案前,它还是后人的告慰,是丰收,是丰庆,是团圆,也是赤子的思慕。
工作原因,我时常去想供品的意义。一张小小的供桌,林林总总地摆满的东西。今人如此,古人亦如此。如果说最先开始祭祀的那一批人,是在用最为珍视的物品,换取对于死亡、对于未知、对于生活环境中的风火雷电以及莫大恐惧的撒赖和贿赂,以企图向祖先或者神明,讨要飞沙走石中的一丝安澜。那么,再之后呢?当人们开始对生老病死无动于衷,了然了自然和神明的客观可欺,再也无需事神致福保佑平安。馨香陈俎,意义何在?
转眼快到中元节。我蜷缩在我妈的后脚跟处抱怨工作的繁琐。我妈哦一声,从我的抱怨中刨出了“快到中元节”这个话头。她开始兴致勃勃,设想着自己去做一次“圪栏”。我条件反射式挤对,“你们三姊妹,除了我大姨能做成,你和我三姨估计都不行,小时候没被生活锤炼过。您还是买些凑合一下就算了吧。”
“那可不行,我这回要做好送你舅舅家,中元节时,让他们献上一点,让你姥姥给检验一下。”我顺口怼回去:“您当这是汇报工作,还检验,以前也没见你多勤劳。”我妈顺头给我一记白眼,“这不是给你打样吗?省得你以后什么都不知道。”
玩笑归玩笑,但听语气是下了决心的,我也没有再说什么。与我妈一样,在千万中国人们的心中,如果还存在对生命的慎重、对天地的感谢、对逝去的留恋,便一定要会慎重地对待那一桌香烟缭绕的桌案。暑热天气要选取解暑瓜果,饭菜筹备要挑拣故人所爱,心里默祷了千万句思念的话语,最后一炷清香,愿思和想均能到达彼岸。
那么端坐神位的人呢?是慈爱庄严的样子吗?透过香烟和雾缭,可吃到了降暑的瓜果,可看到了儿孙们的近颜。是否知道了家中不错,那谁病过一场,但恢复得还行。这做“圪栏”手艺是否得您真传,是否接收到了思念和诉说?
于是,在时光流逝中,在千千万万中国人划定了年岁的关口,阖家人跪拜在家中那一方小小的神案上,摇曳的烛火照亮了旧年经营生活的成绩单,便如幼年时拿回家的考卷一样。此一刻,顶梁柱亦是垂髫小儿,忐忑地等待着祖先的审视和检查。这样的场景,如果在浩如烟海的人类文明历史中搜索,结果一定是卷帙浩繁,如果有兴趣再一一对比,它会出现在每一代人,每一个年岁,每一个祭祀的节日。
所以,这“圪栏”便是答卷。它在岁月的烹炼中失去了弹性和柔软,将润白的品性打磨得坑坑洼洼,但也就凑凑合合走过了人生的大半段路。面饼硬韧如铁,能抵御际遇的厮磨。滋味吗?如今手艺人已经往里头加各种馅料,有红糖,还有花生,倒比以前的滋味要好吃很多。
年岁渐增,渐渐咀嚼出一些成规的滋味。眼下再筹备中元节,文案中的“圪栏”便也深沉了许多。那些源自于人类本能意识中的敬和爱,或者粗鄙直接的撒赖念想,都伴着时间的行进与栖止颠簸沉浮,而时间也终于不再抽象,隐隐透露出期许和希望,便如一晃经年,这“圪栏”些微的油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