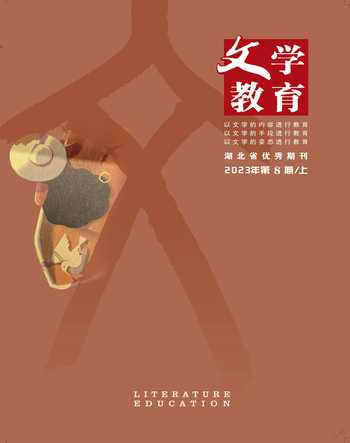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影响下余华长篇小说的中国意识
马迎春
内容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创作,但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活力与民族精神的缺失。许多作家认识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局限,开始摒弃西方后现代主义注重解构与非理性的创作,转而将创作基点聚焦于中国,余华作为转型的代表作家受到关注。论者将余华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作的六部长篇小说与之前的作品对照可以发现,余华在转型后更加有意识地展现中国面貌,书写“中国意识”,更新“中国形象”,以求在世界性中彰显民族特性。余华不仅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体化,展现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回归,还深入中国民间社会,探寻真实的中国民间生活,挖掘中国民间底层人民坚韧、乐观的民族性格。同时,余华也开始吸收家乡的地域文化资源,在标准的汉语中融入海盐方言和越剧腔调。
关键词:余华 “中国意识” 长篇小说
“中国意识”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风貌、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集中表达,本文谈论的“中国意识”是文化審美意义上的“中国意识”。“中国意识”在中国文学创作中有迹可循。新中国成立前,《阿Q正传》、“激情三部曲”、《子夜》、《四世同堂》等都包含着作家对中国社会的思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家的创作转向“工农兵方向”,构建了一个有别于西方“公民”社会的“人民”社会。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盛行。西方后现代主义以其在内容上消解文本意义,在叙述上表现解构、颠覆与非理性,在结构上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影响各国的文学创作。当时中国正值文化转型时期,且20世纪80年代的趋势就是“全球化”“一体化”,西方后现代主义也就顺势进入中国,直接促进了先锋文学的诞生。由于许多作家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过度模仿与跟随,“中国意识”被剔除在文学创作之外,只关注内容的解构和形式的实验。之后,虽然西方后现代主义仍在盛行,但中国的先锋文学并没有持续很久,中国的学者与作家认识到跟随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失却了文学的活力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叙事内容与叙事形式的重复也引起了审美疲劳。许多作家开始将创作基点聚焦于中国,创作出了一批有民族特性的作品。
余华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早期创作了许多内容上展现非理性、解构与颠覆,语言上使用陌生化手法冷漠叙事的文学作品,如《十八岁出门远行》(1987)、《现实一种》(1988)、《世事如烟》(1988)。正因为余华对西方后现代主义了解深刻,他认识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局限性,开始将书写对象和写作资源指向中国。余华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创作了一批展现中国风貌的长篇小说,包括《在细雨中呼喊》(1990)、《活着》(1992)、《许三观卖血记》(1995)、《兄弟》(2005至2006)、《第七天》(2013)、《文城》(2021)。余华的长篇小说中浸润着余华对中国人民的人性关怀、对乐观与坚韧的生活态度的赞扬和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深刻认识,叙述风格也由冷漠、荒诞转向温情、乐观。余华在《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2008)中也说“我相信文学也是一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了解自己民族传统中特别的性格,然后在自己的写作中伸张这样的特别性格”,这里“民族”的指向对象就是中国。
由此,论者认为余华是在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且认识到其局限之后,有意识地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自己笔下的中国,探寻其中包含的“民族性格”与“中国意识”,寻求民族性建设以求在世界彰显独特的“中国意识”,更新“中国形象”。本文以余华创作的六部长篇小说为研究文本,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回归、中国民间社会的温情思索和中国地域文化资源的吸收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回归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文化转向》(1998)中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有关经济、消费的,历史感已经消失殆尽。历史与现实不再是叙述的重点也并不具备内涵指向,只是功能性的符号。《十八岁出门远行》叙述了一个刚成年的男孩独自出门远行的故事。在这一路上,主人公受到的攻击可以是发生在任何时间段的,时间也就失去了意义。余华早期创作中的历史与现实是缺席的、符号化的,或者说是无时间性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中,中国历史与现实开始回归。正如洪治纲所主张的,余华也“试图在重建一种具有中国经验的、比自己以前小说更具历史丰富性的‘大叙事”。[1]这时,余华笔下的历史与现实是能够影响人物和情节的存在。
(一)中国历史的回归
《活着》以福贵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历史变迁,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历史与人物命运的交织与同叙。余华书写的是个人记忆中的历史,也是被历史影响下的个人命运,历史成为余华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情节结点。《活着》叙述了福贵的一生,历史与福贵的命运息息相关。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福贵败光了家产、田地,福贵认清事实决定重新做人开始租地种田,开启了他的农民生涯。之后,历史的偶然使福贵跟随军队过了两年,福贵的命运被改变了,也正是因为战争福贵明白了生命的可贵。再后,福贵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饥荒等历史事件,在这其中历史和偶然一次又一次改变着福贵的命运,也加强了福贵对生命的坚守。福贵就如历史长河上的浮萍无法控制地被带往别处,在漂浮中不仅见证了中国的历史,也坚定了福贵活着的信念,福贵的命运与历史同构。
不仅福贵的命运与中国历史联系密切,许三观的命运与中国历史也有着关联,陈思和指出“许三观一生多次卖血,有几次与重大的历史时间有关,如三年自然灾害和上山下乡运动”。[2]在大饥荒时,许三观因为家里粮食短缺而卖血。二乐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许三观为了招待二乐所在的生产队队长又一次卖血。从这两次卖血中可以看出,许三观是受到历史影响的被动卖血。历史不仅影响着许三观的命运,也影响着卖血情节的构造。
《文城》中小美的生命历程也与历史交织在一起,“小美入土为安,她生前经历了清朝灭亡,民国初立,死后避开了军阀混战,匪祸泛滥”。《文城》不仅勾勒了清末民初的历史,也补全了余华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书写。
自余华创作长篇小说始,余华以小人物的命运为表征,叙述人物背后中国历史的变迁。余华笔下的历史开始具体化,历史开始与人物的命运和情节的构造相勾连,历史也成为余华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现实的回归
新世纪以来,余华愈来愈关注中国当下的现实面貌,《兄弟》和《第七天》就是典型代表。
余华在《兄弟》的后记中表明《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兄弟》是余华对现实发起了“正面强攻”。《兄弟》以两个人物四十多年的经历叙写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的“中国记忆”,也书写了余华对改革开放后中国道路的思索以及经济繁荣背后的忧思,有着现实警惕性。李光头去福利厂当工人搭上了改革的热潮,成为刘镇最富有的人,也带领刘镇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刘镇可以说是中国的缩影,由李光头、宋钢带来的刘镇的变化也是中国现实的变迁。《第七天》是对《兄弟》的接续,以亡灵的见闻叙述中国的现实。余华将许多新闻事件引入創作,许多学者也将《第七天》看作是“非虚构”作品,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第七天》的现实指向性。
余华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通过书写中国历史对中国底层人民的命运进行思索,在新世纪主要对现实“正面强攻”。由此,论者认为余华早期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其创作的历史与现实是符号性的,中国历史与现实是失却的。之后,余华开始有意识地书写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探索“中国意识”,从中展现对中国本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思索。
二.中国民间社会的温情思索
陈思和主张“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只有融入民间才有力量。余华“从八十年代的‘极端先锋写作,转向了新的叙事空间——民间的立场,知识分子把自身隐蔽到民众中间”开始讲述老百姓的故事。[3]余华找到了“民间化”的道路,余华虽然深知民间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但民间也是至真至情的地方。余华抛弃早期创作中人物书写的符号化、小人物的“非理性”体验和叙述风格的冷漠,转而书写中国民间的日常生活,挖掘中国民间底层人民乐观、坚韧的民族性格,对中国民间底层人民寄予温情的思索。这不仅更新了中国民间形象,还进一步构建了具有民间性的“中国意识”。
(一)中国民间的日常生活
余华与老百姓共同经历民间生活,着重描摹老百姓的生活细节。就像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2015)中说“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余华从《活着》到《许三观买血记》再到《兄弟》描摹了一幅幅老百姓平凡的日常民间图景。
《活着》细致地描写了福贵的农耕生活,福贵在家道中落后深刻思索蜕变为农民,每日劳作、种田。田地不仅是生活的希望,也是生命的象征。福贵对田地有着深沉的热爱,小时候,福贵的娘告诉他泥巴能治百病,福贵的爹跟福贵诉说着田地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时,最开心的就是家里获得了五亩地,这代表生活的安康。《活着》中还有着民间歌谣的传唱,如福贵会唱“皇帝叫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等民谣。因此,陈思和、逸菁在《逼近世纪末的回顾和思考——90年代中国小说的变化》(1995)中认为《活着》是中国民间性与民族性的代表,“这个故事的叙事含有强烈的民间色彩”。
《许三观卖血记》细致地书写许三观因为生存和家庭十二次卖血的经历。《兄弟》则细致地描写了宋凡平和李兰相爱的细节,宋凡平和李兰这一二婚家庭组建的过程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宋凡平细细呵护李兰、幽默地陪孩子玩耍;李兰和宋凡平耐心教导宋钢和李光头;宋钢和李光头又吵闹又温馨的童年生活。此外,文中还写了刘作家童铁匠、苏妈、余拔牙等居住在刘镇的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余华不仅书写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细节,还有着中国民间道德伦理的叙述。如《兄弟》中对“你会有善报的”这句话重复了7次,始终萦绕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民间伦理观念。
余华笔下的福贵、许三观、宋凡平等老百姓都身处于中国民间的底层,他们日常生活的描写不仅展现了中国民间底层人民真实的生活状态,还是民间社会经验、民间伦理的结合。论者认为,余华正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书写中国民间底层人民的衣食住行、爱恨情仇。民间的一切在余华的手中鲜活起来,余华也在其中试图寻找独属于中国民间的智慧,探索“中国意识”的民间性。
(二)中国民间底层人物的温情思索
在王安忆、余华对谈暨余华作品研讨会(2023)上,王安忆指出:“过去的‘人以符号的方式存在,现在的‘人以‘人的形象出现。”余华于90年代发现了“别人”的存在,开始注重“别人”的声音,他笔下的“人”更鲜活了。余华笔下的“人”都是中国民间底层人物,有着乐观、坚韧的民族性格。正如洪治纲在《悲悯的力量——论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及其精神走向》(2004)中所言,余华“回到现实的底层,回到生命的存在,回到悲悯的情怀”,对世间抱有着善意的怜悯。
虽然福贵一家与许三观一家的生活多是无奈的与悲苦的,但他们仍能乐观面对命运的拨弄,坦然坚守自己的真情。福贵早年纨绔不顾家庭且输掉了家产,他的母亲说出“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的乐观之语。妻子家珍在被父亲接走后仍带着儿子回到富贵身边不离不弃、共渡难关。凤霞的丈夫二喜不管每天干完活多累,都要走十多里路到乡下看儿子苦根。许三观即使知道一乐不是自己的孩子,仍然真情相待。
《兄弟》则更侧重书写人性的美好。宋凡平是人性美的代表,他身上仿佛集中着世间所有优秀的品质,他正直善良、同情弱小。宋凡平面对妻子时,处处体贴照顾,两人虽然相处时间不久,但仍能不离不弃、忠贞不渝。宋凡平永远是李兰心中最爱慕和最骄傲的丈夫。宋凡平面对孩子时,细心爱护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宋凡平独自承担着悲痛给孩子带去的永远是笑脸、乐观与坚韧,尽管他的胳膊被打的脱臼仍然没有抱怨,而是幽默地对孩子说“它累了”,热情地教孩子如何让胳膊“休息”。宋凡平以其乐观、坚韧、微笑以及人性中闪光的温情与命运抗争,成为了伟大的丈夫、伟大的父亲,始终“有尊严的活着”。
当然,《兄弟》中最值得思考的还是宋钢与李光头这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两兄弟至真的手足情。在童年时,两人的家庭是乐观的、温暖的,他们一起品尝绿豆汤、一起吃糖、一起玩耍,两人也慢慢懂得了爱。长大之后,李光头发工资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宋钢买那副最贵的眼镜,宋钢始终记得他在母亲临终时说的话“妈妈,你放心,我会一辈子照顾李光头的。只剩下最后一碗饭了,我会让给李光头吃;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了,我会让给李光头穿”,并以之为行为准则。两人一直乐观、坚韧的生活,尽管两人经历了断交,但两人心里放不下的始终是对方。
在以上这些血肉丰满的中国民间底层人物形象中,余华秉持着悲悯的情怀,用孕于中国民间底层人物乐观、坚韧的民族性格,探索“中国意识”的温情特性。
三.中国地域文化资源的吸收
余华早期的创作有选择性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如《古典爱情》中对才子佳人形象的借鉴、《鲜血梅花》中对江湖复仇情节的书写、《河边的错误》中对侠义公案小说的模仿,但其中叙述多是无地区性的。论者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余华也从中国地域文化资源中汲取创作灵感,探寻他故乡中特有的“中国意识”。
(一)海盐方言的吸收
余华出生于浙江杭州,三岁时随父举家搬迁至浙江海盐。余华曾在《我能否相信自己》(1998)中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这里的家就是海盐。余华曾写到“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4]可见,海盐作为余华的故乡,对余华的创作影响颇深。
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的意大利文版自序中指出“我就是在方言里成长起来的”。《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中就有着海盐方言的留存。《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中近二十次使用“眼泪汪汪”这一海盐方言,叙述许三观、许玉兰、李兰、李光头、林红等人回忆的悲伤或感动的喜悦。“搁”、“淘”等海盐方言也展现了中国民间底层人民真实的生活细节。此外,“熟了”(过世)等方言俗语也经常运用。但余华曾针对方言的使用做出思索“十五年的写作,使我灭绝了几乎所有来自故乡的错别字,我学会了如何寻找有力的词汇……我学会了在标准的汉语里如何左右逢源”。[5]
因此论者认为,余华虽然竭力避免着“故乡的错别字”转而在“标准的汉语”中左右逢源,但他始终无法摆脱海盐方言对其创作的影响,其语言是具有民族特性的。
(二)嵊县越剧的吸收
余华于海盐县文化馆中接触到了越剧,越剧(中国第二大剧种)发源于浙江嵊县,影响了余华的创作。余华意识到越剧唱词和台词是相似的,在《我只知道人是什么》(2018)中说“台词是往唱词那边靠的,唱词是往台词那边靠的”,于是余华开始将越剧唱词与叙述语言结合,让说话呈现出“节奏和旋律”。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对话有着明显的越剧腔调。如许玉兰问许三观,在她生产时许三观是不是在外面哈哈大笑。许三观说:“我没有哈哈大笑……我只是嘿嘿的笑,没有笑出声音”。许玉兰回道:“所以你让三个儿子叫一乐,二乐,三乐,我在产房里疼了一次,两次,三次;你在外面樂了一次,两次,三次,是不是?”许三观与许玉兰的对话宛如越剧唱词中的一唱三叹,叙述节奏轻快,有着明显的韵律节奏。余华在一次访谈中也指出“那个许玉兰,她每次坐在门槛上哭的时候,那全是唱腔的,我全部用的那种唱腔”,这里的唱腔就是越剧唱腔。[6]
由此,论者认为余华的长篇创作中有意识地吸收海盐方言和越剧资源,在标准的汉语中融入浙江的气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寻求“中国意识”的地域性。
综上,论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许多作家跟随并模仿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创作,中国先锋文学的诞生就是“他塑”的结果,注重解构、非理性与语言实验,“中国意识”被剔除在文学创作之外,失却了中国的民族特性。余华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积极地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自己笔下的“中国意识”,展现中国面貌,更新“中国形象”,在世界性中凸显民族特性。当下文坛也亟需创作具有“中国意识”的内容,构建具有中国民族特性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话语”,增强文化自信力,有意识地在世界文学中“自塑”。
参考文献
[1]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第3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3]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第3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4]余华.兄弟(第3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6]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7]余华,杨绍斌.“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J].当代作家评论,1999(01):4-13.
[8]洪治纲,余华.回到现实,回到存在——关于长篇小说《兄弟》的对话[J].南方文坛,2006(03):30-35.
注 释
[1]洪治纲:《在裂变中裂变——论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第96-104页。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23页。
[3]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0年,第68-70页。
[4]余华:《余华自传》,见《余华作品集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81页。
[5]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5页。
[6]余华、陈韧:《余华访谈录》,《牡丹》,1996年第8期。
基金项目:2022年度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中国意识”——以余华的〈兄弟〉和黄碧云的〈烈女图〉为例》(项目编号:2022SKY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