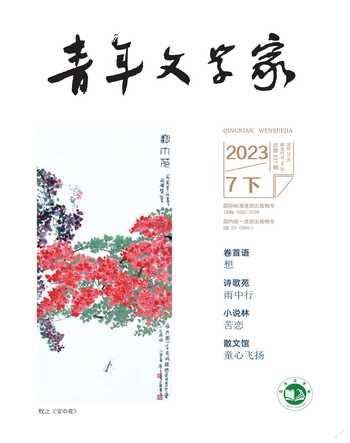童心飞扬
王琳


我对童年的记忆是由一段斑驳的城墙和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开始的。
古老的城墙砖成了最里一排平房的山墙。那时,人们没有文物古迹的概念,用现在人的眼光看来,依城墙而建的房子,既没有延伸城墙的岁月,又无法得到稳固的庇护(因为城墙上的碎石会随时滚下来)。民宅中善用粗略的灰瓦,看上去像是将城墙从腰部斩断,使人分不清它是一段建在房顶上的城墙,还是一排盖着城墙顶的民房。在外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结构,只有和我一样处于童年的孩子才能理解其中的美妙,因为每家每户的室内都有入口可以进入到城墙里—与墙体一样悠久的防空洞。虽然房屋是一间间隔开,但防空洞是由一条狭长的廊道连接在一起的,自始至终我们不知道这条廊道有多长。因为房子的主人们无法容忍外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到自己的家里,所以在短暂的闲趣后,大家都把自己屋内的洞口给封死了。
虽然是一排排的平房,一直延伸到马路上时已经很难分辨出这是由多少排房子组成的住宅区了。那个时代房子都是公家的,这个单位在这儿盖一片,那个单位在那儿盖几间,不同的公家为了让自己的房子相对独立,即便盖得再长,也要在这一排的对面再盖上一排,脸对脸地环抱成一个长长的院子。两排房子中间狭长的过道就成了我们儿时嬉闹的舞台。
院子里最好的位置是处于两端的家庭,把过道一封,装上一扇大门,又形成一个自己的小院。夏天消暑纳凉,冬天储物囤菜,怡然自得,不碍他人,硬要找出它们的缺点的话,就是离院子的出口较远(狭长的院子出入口都在中间部位),在那个生活设施尚不便利的年代,意味着要负重走更多的路。
我还有遥远的以幼小的身躯负重前行的记忆,但记忆穿越悠远的时间来到我眼前,已经无法还原彼时的身影。当时只有六七岁的我,显然无法完成过重的体力劳动;于我来说,却是儿时劳动的快乐。不到十岁孩子的乐趣很简单,它们由成群结队和别出心裁组成。提水和倒垃圾是我们能消遣的体力活儿。一个院子六七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如果看到别人拎着桶打自家门口过,其他的男孩子或女孩子必定踊跃争先,向自己父母申请个同样的活儿,迫不及待地抓起桶跑出去。水桶沉,我们只有提半桶的力气;垃圾桶轻就无所谓了,但垃圾桶的路远反而更消耗体力。这时候,劳动的技巧在我们用臂膀的单薄对抗物体的沉重时发挥了作用,通过双手交替和身体摆动,让桶围绕着身体不断转圈,悠起来,让我们既从重量上感到了轻松,又可以充分利用惯性加快前进的速度。随着技巧的日渐纯熟,重量和距离就不再是我们的难题了。
成群结队的劳动,是为结伴而行的比拼和短暂脱离监管的放飞,偶然遇到路上的嬉戏,还可以横插一脚,热切地投入到别的孩子搭建的游戏中去。如果把自己的新玩具带出来展示一下就更加完美了,会受到其他孩子友善的欢迎。
在我十岁之前,每家每户用水都要到院子里的公共水管去提。那个年代,技术落后,工业品匮乏,没有如今轻便的塑料桶,提水用的水桶都是铁皮箍的,仅空桶就很有分量。每到傍晚用水高峰时,在水管前等待的人们是一道密集的风景,这让我怀疑,不到十岁的孩子承担这一任务的不切实际。回忆带来的模糊印象也许只是不同时期类似场景的重疊,而实际上,当时那个流着清鼻涕看着大人们走来走去,皱皱巴巴站在旁边的才是我,借助倒垃圾行玩乐之实的才是真实的我们。
后来,家家铺设了上下水管道,再也不用为冬天结冰的管道、通红的手指和冰冷的水桶而发愁了。大人们在释放了因进嘴带来的负担后,毫不吝啬地将出嘴污秽物的处置权交到了我们手上—每家半大的孩子完成倒垃圾的使命。三十年后,这些琐碎劳动已被吸尘器、洗碗机和抽水马桶等便利的家用设施所代替,现在的孩子也就失去了通过劳动直达快乐的体验。
比起楼房的独门独户,互不干扰,平房的生活显得杂乱无章。每个人吃喝拉撒睡的个人事项,都有可能与别人的交织在一起。出了屋门,邻居们都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做饭、洗衣服、修修补补、谈天说地……有时,过路可能要等待别人为你腾开地方;有时,你在屋外摆放杂物还要跟邻居商量放置的位置;有时,你想一个人想静一静,还要妥善回应别人的友好;你既要走到别人的生活跟前,又要允许别人审视你的一举一动。你得病,他吵架,今天这家吃的什么鱼,明天那家喝的什么酒,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家家没有秘密。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他,后天他还你。如果有了矛盾,抬头不见低头见,同样让分歧无所遁形。邻里之间只能就可能产生矛盾的预期问题进行规避,但在个人利益面前,也不能期待人人争做活雷锋,有可能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当事双方往往还时不时拿陈年往事来翻一翻、晒一晒。
大人之间的矛盾往往不影响孩子们的你来我往。大杂院比设施优厚的楼房对孩子们的吸引力更大,劳动的辛苦在孩子心里不值一提,同龄玩伴才更为重要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团团伙伙,孩子之间的团伙总是以院子为中心向外延伸,一个院里的孩子总要自然地走在一起,并就近与院外常一起玩儿的孩子形成松散的团体,这种联系的最大用处是用来抵御来自未知的侵扰。
我至今还有被一个成年人追到厕所里逼问同伙家住哪儿的记忆。我自作聪明地在大家一哄而散后,逃到了附近的一个公厕里,蹲在那儿假装使劲儿。当那个被我们打了的孩子的爸爸追到厕所里时,看见我孤零零地蹲在那里,我心想,完蛋了!我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最为机敏地躲在了一个避风港里,那孩子他爸一定在外面像老鹰捉小鸡一样逮我那些四散奔逃的同伴,这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却毫不犹豫地出现在了我面前,我都能感觉到他是径直冲着我来的。他大声地呵斥我:“那个小黑崽子是哪家的,住哪儿?”我还未挣扎就在他的气势前彻底败下阵来,支支吾吾,语无伦次,只记得“在后边住,还得往里走”几句不完整的话从我嘴里不由自主地滑了出来,换取了短暂的安宁。
就像我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躲藏能力一样,这次我又低估了自己的愚蠢。在那个孩子的爹走后,我以为一劳永逸地远离了危机,并在厕所里磨磨叽叽地平复心情时,那个男人又折了回来:“小崽子,快起来,带我找他家去!”吓得我哇哇大哭起来。现在想来,我的愚蠢在于,连那个当爹的都无法确定,我是否认识那个小黑崽子时,就已经缴械投降了。
这是我记忆中的唯一一次“出头儿”,我纠集了我们全院的男孩儿,为一个院外的低年级孩子向曾经侮辱了他的别的孩子施加报复。最后,我们在那个凶巴巴的爹面前百口莫辩时,那个被欺负的孩子却向我们大门紧闭。
记忆中寒暑假大都是在乡下度过,因为父母要上班,一周工作五天半,院子里的孩子也会被父母送回农村老家住上些日子,没有了我们这帮孩子,大人也能享受几天安静日子。父母常常把我放在乡下几个星期,其间也不来看我,让我在田间地头变成了无拘无束的野孩子。因为乡下的孩子被大人撒出去是有活儿要干的,拔草、扒地瓜、割猪食……我是难得没有任务的自由身,但对于乡下的玩法不得要领,常常通过旁观某一场景泥足深陷,忽略了通过参与来解决自己的少见多怪。
在城里上学时,孩子们穿凉鞋是要穿袜子的,那时我对裸露在外的皮肤既排斥又痴迷。尤其是女孩子光着脚穿凉鞋,在学校里是见不到的,偶然在校外看到一个成年女性光着脚穿鞋,就会带走我好奇的目光,久久无法自拔。可笑的是,轮到自己时,只要出门,就要把脚裹得严严实实。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穿拖鞋、穿凉鞋,没人穿袜子;男人和女人们或扛着锄头,或挎着篮子,脚上裹着厚厚的泥巴,和鞋上的泥巴混在一起,远看像穿块石头。我依然固执地耻于将脚裸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其他孩子无拘无束地在田地里行走的时候,我只有在后面一跳一跳地、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泥巴。
一场雨水让我明白,我的整洁独木难支。那时的农村是见不到硬路的,一场雨后,所有的土路变成了泥路,一脚踩下去,泥巴盖住脚面,因为穿了袜子,泥粘在脚上,甩也甩不掉,有一种癞蛤蟆爬到脚面上的感觉,犹豫着下一脚如何踩出去。孩子是禁不住同龄人说三道四的,只有在别人的怂恿下,我才能抵抗住内心的煎熬,一步一步踏泥而行,之后已顾不得脚上沉重得像一块石头,只求奔到水里将脚洗干净。
对于乡下孩子来说,任何的水状物都能够与脚和谐共处,即便是路上的水坑。在他们的认识里,脚与泥土为伴,不应一尘不染,只需走时没有沉重的负担就行,我可不行。所以,让我念念不忘的是在灌溉渠充满水时,在渠里淌水的场景。农村的田地里都有由石板砌成,把不同的地块隔开,利于集中灌溉的水渠。一般深及孩子的小腿,开闸放水时水渠里充满干净的清水,地的主人们通过长把儿的水勺将水舀到自己的田里给农作物浇水。开闸放水时孩子们都集中到闸口,看着碗口粗的水管内白花花的清水喷薄而出。
起初,在这段回忆里并没有找到自己能够置身其中的情绪。因为那时的我时时刻刻保持妆容严整,甚至要把衬衫的扣子系到领口,即便和农村的孩子们玩儿也一样。严谨的穿着,被袜子包裹严严实实的脚,让我很难像其他孩子那样在土地上摸爬滚打。所以,一方面羡慕着别人的无拘无束,另一方面又被自己在城市里的行为习惯捆得结结实实。
听老人说,我总是在不远不近的距离下,看着同龄人肆无忌惮地玩耍,只有他们中规中矩时,才和他们玩儿起他们并不擅长而自己应付自如的游戏。第一次看到孩子们赤裸着腿脚下到水渠里时,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完全是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场景,但是短暂的惊讶转瞬即逝,换来的是长久的痴迷。
我喜欢站在水渠中看着汹涌的水流将我的脚快速地冲刷干净,不但脚面干净了,还把鞋底、鞋面,以及边边角角和坑坑眼眼的泥沙全部带走,即便在视觉和触觉上认为干净了,但还要在水渠里反复地走动,直到水中呈现出一尘不染的肌肤。这时,我心中因满脚污泥而背负的包袱已烟消雾散,感受无忧无虑的舒爽。当久久的沉浸换来心满意足时,又不得不面对冷峻的现实,我还要继续面对泥土的挑战,虽然心情有些沮丧,但此时已经接纳了肌肤与泥土的和谐相处,回到家总要把脚冲干净的。
那时的家庭还没有影像记录设备,回顾曾经的岁月一是靠相片,二是靠讲述。我从没有想到记忆还没有来到我身体里时的经历,后来会成为我津津乐道的资本。
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人依然沿袭着守家在地的生存模式。计划经济下的就业与人民生活紧紧地与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人离开自己的户籍生存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可以通过上学、异地工作、旅居实现的跨省市生活,在以国有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是很难想象的,即便是行走于两地之间也是一份极特殊的经历。
妈妈会把家庭成员的所有照片工工整整地固定在相册里,照片是黑白两色,相纸很厚,颗粒感很强,灯光下有制成时特有的纹路。虽是黑白照片,但画面很清晰,层次也很鲜明。相册的翻页是黑色硬纸板,纸板很厚,对照片起到了足够的支撑和保护,正反面有固定照片的卡缝,每页之间还有一张白色胶纸作为保护,照片就隐藏在这胶纸与卡缝的包裹之中。照相机已经进入家庭,但鲜有人买,需要时都是相互借;胶卷也是自己冲印,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手艺,就像现在会自己修电脑一样。
妈妈总是给我详细讲述每张相片的时间、内容和背景,当然,是那些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光;于是,我很早就知道了我跟她一起去甘肃的经历,她会着重描述她认为有意思的情节。
而我乐于回味婴幼儿时期那个长得跟年画上的大头娃娃一样的自己。其中一张妈妈陪我玩球的照片让我印象深刻。据说在荒凉的马莲山上,除了风,看到最多的就是石头,如果有幸,能看到的奇观是风吹石头跑。照片里的我,明显刚会站立,扶着椅子试图伸手够妈妈手中的皮球,妈妈蹲在那里,我们俩人都是一身白色,映衬在照片背景的一片白色里,此外不再有任何景物。还是通过爸爸后来的描述,我弄清了当时自己与外界的关系。马莲山上坐落着西北最大的散射站,这是当年部队高科技的代表。爸爸是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他和战友轮流驻扎在杳无人烟的荒山上。当时的照片拍摄自散射站的驻扎點,那里与营部有一段距离,是一个四周空旷,光秃秃的山头,白色的土,白色的石头,是它的地貌特征。不到一岁的我,由妈妈背着到了爸爸的驻勤点。听说,正因为见到了那个月份的我,爸爸决定跟部队请探亲假,回家来照看我。这件事最终换回了爸爸一年的假期。
在爸爸复员之前,我有三次随妈妈去部队探亲的经历。据他们二人的回忆,每一次都有值得回味一生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而我能绞尽脑汁回忆出来的只有五岁那次—最后陪爸爸办好了复员手续,一起坐火车返回的镜头。连这个仅存的景象,我依然是复述着别人口中的情节,因为实在找不到当时那还尚不属于我的感受,只是有一种情绪跨越经久不衰的岁月找到了我。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才能体会到后代在每个人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所表现出的真实分量,这是每个人穷极一生的负载。
现在,我们对孩子的关怀凝结为“陪伴”二字:从幼年开始,各种早教班、亲子班,给孩子和父母提供了密不可分的生活契机;就连孩子娱乐场所的入场券,都不再把孩子和大人的票分开卖,而是一大一小的套票。
我的孩子就读的小学距离我家很近。从家出门,连坐电梯的时间算在内,走路只要五分钟。中间经过的是一条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的街道,在街道上行走,开车人是唯一的弱势群体。每天的上下学时间,这条街就是孩子和家长的演练场,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家长们都要完成目视孩子从学校出来的过程,而后是家长还没逮到孩子,孩子已经到家了。
我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没有独自一人上下学的经历;即便他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密室逃脱经验,但大人们反而愈加怕他在家人的密室里逃脱成功,总愿给他带上一把注目的“长命锁”;即便需要孩子独自在家时,也希望快去快回。这让我想起,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或者是更小的年纪,大人们是怎么对付我们的。
我只是偶尔有过父母送我上学的印象,日后经过证实是在一年级上半学期的事,后来就是跟院里的小伙伴们结伴而行了。可能是那时养孩子没有上一代人的帮助,做父母的又要准时上下班;不像现在,家长的父母退休后可以承担起操练新一代的任务。
孩子们结伴而行,就不存在通过逃脱得来的满足感。出了校门老师是不管的,你几点回家,路上干什么,去了哪儿,是家长的管辖范围。有些孩子放了学老老实实往家走,中间不开小差,也不受玩伴诱惑;有些孩子在回家途中,三一群五一伙儿地扎在某个角落里拍洋画、砸方宝;也有的孩子出了校门就进了游戏厅的屋门。只要你对放学后到父母下班前的这段时间善加利用,你就可以满足那个年代你童年的所有快乐。
但是,父母永远是变量的砝码,是增是减全看他们认为要把你这颗螺丝拧紧还是放松。这时,在天平的另一端放置着考试的成绩、老师的表扬、家务的劳动、现实的表现等等,至于拿走哪些,放下哪些,孩子是没有发言权的。你可能觉得今天拿回一张成绩不错的试卷,大人却说你怎么把衣服弄得这么脏,揪出了你放学后的劣迹斑斑;你也可能在放学后利用手中攒的零花钱买一个心仪的玩意儿,结果到手后东躲西藏,就怕父母看见,怕什么来什么。所以,放学后是孩子们与时间的较量,具体说是与家长时间的较量。那些出校门就急急忙忙奔家走的一定是家里大人在家或下班早,而又没有可以交差的好消息给家长,只能乖乖争取个好态度。那些不着急不着慌,边走边玩的,肯定是知道家长不会太早下班,或掐准了家长到家的时间,或有本领不被责怪,游刃有余的。只有那些确信家长不会过多过问或爱管不管的,才会大胆地跑去游戏厅结结实实爽一把。
为此,每个孩子都练就了一手探听父母第二天干什么,啥时下班,几点到家的功夫。为了不让父母疑心,他们先从父母谈话的只言片语找门道,听他们讲讲今天,再讲讲明天,今天没完事的是不是要明天继续,明天还有啥特殊安排,是不是在外奔波,去得远近,再不经意间问上一句“那明晚咱们吃什么”。如果他们说“回来做”,那就代表不会太晚;如果让你自己饿了热剩饭吃,就可能不会太早。但后来我发现,完全相信他们的话,你就错了,因为每个孩子都体验过,到家前发现大人已经回家时那心里的一“咯噔”—尤其是满心欢喜的趁着放学后自以为充裕的时间玩得大汗淋漓时,尤其是在你头一天已经自以为窃得大人即将晚回家的机密情报后,尤其是在你已经忘记了应该几点到家,让大人失去耐心后,大人们会用那上帝一般的臂膀拿起你无法抵御的重量放在你另一侧的天平上:“以后再这么晚,回来别吃饭!”
现在孩子与大人的博弈是在视线以内完成的,比如看似在学习,实则是在上网;你让他完成某某事情,他给你偷工减料,稍不注意很难发现。我们那时与大人的博弈往往发生在视线之外。
比如,为了让孩子按时完成假期作业,父母上班时把孩子反锁在家里。被锁在家里是很多上小学孩子的共同体验,不同的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家住的是平房,是大杂院,每间房都由木条框的玻璃门窗将室内和室外“友好”地隔离开来。不管是方形的院子,还是长形的院子,在天气晴朗时,院子的明朗使房间在玻璃门窗的保护下,凸显室内的隐秘和幽暗,很好地为每一户人家保留了独立而秘密的生活角落。那些从父母角度是出于好心,但在别人看来定是惩罚的孩子就常常被锁在这角落里。
在我那狭长的院子里,最不缺的就是年龄相仿的伙伴,任何孩子只要若无其事地在院子里晃荡上一圈,其他在家的孩子就像看见信号弹,能出来的皆施个“遁身术”,到院门口集结;家里有大人的出不来就不多指望;被家长反锁在屋里的,这时一定要离开幽暗的角落,来到玻璃前,再有失望的表情或是无奈的言语,都无须向伙伴们倾诉,因为大家了然于心。
四年级开始,我就不会再被这窗和这门阻挡住因锁在屋内而无处释放的活力了。这么做的自信,来自我的身高已经使我可以稳妥地爬上窗台,我的腿长可以使我跨越打开的窗框而不会卡在中途不知所措。要知道,这一套动作不是到了一定岁数就无师自通一气呵成的,这是在多年的望而却步和半途而废下被成长来了醍醐灌顶的那么一下,接下来的一切,就豁然开朗。
当然,最初的试探还是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我在外面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绝想不到从窗户原路返回时遇到的困难,当我站在院里面对高高的窗户和窗台时,“这是我们家吗,我不可能变小了啊?”慌张感不禁油然而生,仿佛退回到之前的望而却步和半途而废,不同的是,我现在多了掩盖自己出格行为的胆量。安全回到屋里,让悬着的心得到了缓解。抹去额头的汗珠,再次站到窗户前时,回过神,原来室内的地面要高出院子一大截儿。当我再次回想到这一幕时才领悟,每个孩子的成长路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挑战,只是因为你是孩子才无所畏惧,也因为你是孩子,才不会让它弄得伤痕累累—苦难在孩子面前永远是不堪一击的。
翻窗户这件事大人们很快就有所察觉,但让当时的我不解的是,父母并没有向我提出过这方面的意见,也未进行过带有是非对错的试探。很快院里的孩子们都能以这种方式出入自由了。正当我们以为可以大显拳脚时,大人们也就不再用这种方式约束我们了。
有人说,童年是自己的感受,不是他人的看法。直到一天,我独自坐在餐厅里,文中那些被我描述的场景,再次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动着浮出水面,它们并没有带给我扑面而来的压迫,而是像一幅悠远的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每一个完整的画面都是由我心中那一张张稚嫩的面孔,一双双清澈的眼睛拼凑而成。餐厅内,巨大的玻璃窗帮我隔绝了近在眼前的喧闹和来来往往的人群,使我奢侈地享受著独自的安宁—突然,一袭白裙在窗外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划过:她明艳的身影,显得修长而挺拔,洁白的长裙飘逸在轻盈的步伐节奏中,乌黑秀美的长发在午后的阳光下耀眼夺目。虽然不是迎面而来,但她的侧身在正式进入我的视线之前就已被我眼角的余光所捕捉,一股熟悉而亲切的暖流在我心头翻滚涌出。
我离开座位,急切地追随着这个身影,直到推开餐厅明亮的大门。夏日的阳光顿时洒满我的全身,在额头盘踞的光亮让我一时间无法睁开眼睛。片刻,在手掌的遮挡下,我挣扎着睁开双眼,环顾四周,却不见了那白色裙摆的灵动,三三两两的行人与我擦肩而过,阳光已不是威胁,我试图在努力寻找,但怎么也摆脱不开怅然若失的干扰。直到那温柔清秀的面容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她明亮清澈的眼睛越来越清晰。我感受到热烈的喜悦。在这双眼睛的背后,越来越多清澈的眼睛从幽暗的深处迎面而来,他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是那样稚嫩,又是那样熟悉,使我久久地沉浸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