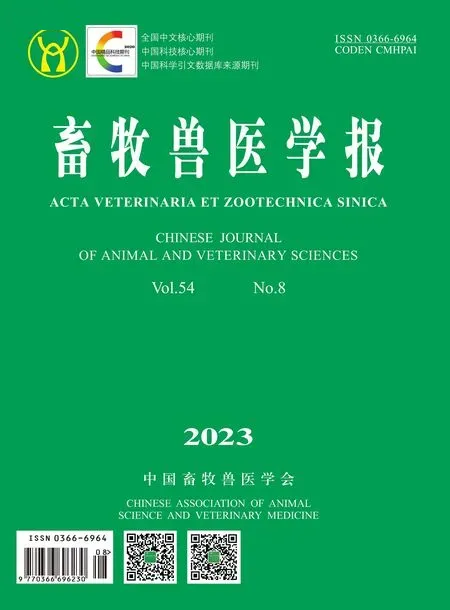鸡性别决定及分化关键调控基因DMRT1研究进展
郑 钢,连 玲
(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遗传资源与分子育种实验室,北京 100193)
根据FAO(https:∥www.fao.org/faostat/zh/#data/QCL)统计数据,1961—2021年间,全球鸡蛋产量从1 438万吨猛增至近8 639万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鸡蛋生产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1/3左右。在规模化蛋鸡养殖产业中,雏鸡出生1日龄便对其进行性别鉴定,母雏全留,公雏被淘汰。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全球有将近60~70亿只公雏被扑杀[1],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还面临严重的伦理问题。雏鸡的性别鉴定方法主要有翻肛法、羽色法和羽速法[2],这些方法都是通过对1日龄雏鸡进行人工性别鉴定,为了节省孵化成本,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探索性别早期鉴定的方法,比如以DNA检测为主的分子生物学方法、依据种蛋蛋形指数的蛋壳形态检测方法、以拉曼光谱和高光谱为主的光谱检测方法、提取尿囊液进行激素检测等,见表1[3]。但这些方法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如需要打开蛋壳等操作,存在影响胚胎发育的风险,同时上述方法也有检测准确率低、判定时间较晚等问题,此外分子生物学检测和光谱检测在应用上还存在操作复杂或检测成本高等问题,基于挥发物组成差异进行检测目前仅针对于京粉一号品种,且对试验环境和设备精度要求很高。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通过生物学手段人为控制或者逆转性别已成为可能。从性腺发育、分化以及性别决定基因入手挖掘性别控制的遗传基础已成为研究热点,其在科学研究以及产业应用上均具有重要价值。

表1 鸡种蛋胚胎性别检测方法比较[3]
哺乳动物性染色体组成为X/Y,雌性表现为同配(XX),雄性表现为异配(XY)。在奶牛上,通过流式细胞术分离携带X或Y的精子,能有效实现对后代性别的控制,但还存在受孕率低及高成本问题[4];而鸡和其他鸟类动物与此相反,雄性表现为同配(ZZ)而雌性表现为异配(ZW),由于染色体组成的差异,无法在鸡上采取同样的精子分离方法进行有效的性别控制。早在1991年,研究人员就鉴定了哺乳动物中的Y染色体连锁的睾丸决定基因SRY(sex determining region Y)[5],但目前为止,在包括鸡等鸟类动物中未能找到与SRY等效的性别决定基因,这提示鸟类动物存在不同的性别决定方式。
鸟类动物的性别决定过程受到性染色体(ZZ/ZW)调控,这些性染色体中的一条或两条携带的基因在鸡胚发育早期能控制性别分化,在雄性个体中左右性腺都发育形成睾丸,而在雌性个体中,性腺发育左右不对称:左侧性腺产生功能性卵巢,而右侧性腺退化。鸡等鸟类动物的性别决定机制目前主要有两种假说[6]:一是Z染色体剂量效应假说:只有一条Z染色体的个体发育为雌性,有两条Z染色体的个体发育为雄性,该假说认为Z染色体剂量依赖机制是鸡性别决定的基础。其中Z连锁DMRT1(doublesex and mab-3 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1)基因的剂量效应是Z染色体剂量效应假说中最典型的证据,DMRT1在胚胎性腺发育中起关键作用,是调节睾丸发育形成的关键基因。二是W染色体显性效应假说:即W染色体上存在有显性的雌性发育相关基因能直接调控雌性性别决定过程,相关研究工作[7-9]发现一些W染色体连锁基因可能直接参与控制雌性的性别决定过程和表型的发生过程。Shaw等[10]和Lin等[11]发现,具有3A:ZZW(A:常染色体Autosome)基因型的三倍体鸡表现为两性中间体,这些鸡有一个右侧睾丸和短暂出现的左侧卵巢(卵巢随年龄增长而逐渐退化),在发育成熟后表现为雄性外型。这表明,W染色体带有雌性性别决定相关基因,因为尽管存在两条Z染色体,仍可能形成一些卵巢组织,该发现也侧面佐证了Z染色体剂量对性别决定的重要影响。除上述两个假说外,激素调控以及细胞自主性识别(cell autonomous sex identity,CASI)假说也被广泛提及,激素调控性别假说认为由性腺分化而产生的性激素在性别分化中起调控作用,通过阻断或外源添加雌激素,能分别使雌鸡或雄鸡出现异性的性别特征,激素调控理论更多的是强调在性腺分化的基础上,性腺分泌的激素参与到性别分化进程。细胞自主性识别假说认为鸡等鸟类体细胞具有固有的性别识别方式,其性别分化本质上是细胞自主的[12],该假说认为雄性和雌性的差异主要不是由于激素作用的结果[13],且激素水平的改变不影响鸡等鸟类动物的体细胞自主性识别过程,这一点区别于人等哺乳动物激素水平对个体发育形态的影响,说明在鸡等鸟类动物中不以激素调节性别表型,提示这种特殊的调控机制背后涉及到复杂的基因调控。
本文综述鸡性别决定及分化关键调控基因DMRT1的研究进展,从多个角度剖析DMRT1在鸡胚性别决定及分化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影响DMRT1表达的潜在因素,为深入研究DMRT1在鸡等鸟类动物性腺分化中的作用以及为研究鸡性别调控相关理论提供参考。
1 鸡胚性别决定及分化进程
性别决定是指有性繁殖生物中,产生性别分化,并形成种群内雌雄个体差异的基础,性别分化指受精卵在性别决定的基础上,进行雌性或雄性性状的发育过程。脊椎动物的性别决定分为遗传型性别决定(genetic sex determination,GSD)和环境型性别决定(environment dependent sex determination,ESD)[14]。哺乳动物和鸟类的雌雄两性个体具有明确的性染色体差异,其性别决定过程受性染色体的遗传调控[15]。性腺是由生殖细胞和体细胞两类细胞组成的,原始生殖细胞 (PGC)来源于胚胎发育早期的中胚层,然后经过定向迁移到达生殖嵴(genital ridge),与性腺体细胞共同发育为性腺。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脊椎动物不同,鸡胚胎支持细胞(sertoli cells)并非来自腔上皮,它们来自DMRT1(+)/PAX2(+)/WNT4 (+)/OSR1(+)间充质细胞群,在生殖细胞迁移到性腺的早期,这些细胞定植于未分化的生殖嵴[16]。另外,雌雄鸡胚早期都有两套原始生殖管道:一对沃尔夫氏管(Wolffian duct,又称中肾管)和一对缪勒管(Mullerian duct,又称中肾旁管)。在雄性个体中,沃尔夫氏管发育形成雄性生殖管道,而缪勒管退化;而在雌性个体中,沃尔夫氏管退化,缪勒管则形成雌性生殖管道。
鸡最早期性别决定发生在鸡胚受精卵形成时,由差异化的染色体组成(ZZ/ZW)决定。鸡胚性腺发育历程简化如图1所示[17]。鸡的胚原基(原始性腺)在胚胎发育E3.5 d开始形成并发育成原始生殖嵴,有报道指出早在E2.0 d时[18],侧板中胚层(LPM)腹内侧的细胞就被确定为性腺祖细胞(GPC),GPC在E2.0 d-E3.0 d 时受Hedgehog信号激活进而分化形成性腺细胞并形成生殖嵴,E3.0 d时腹内侧出现明显的增厚,这是鸡性腺发生的第一个迹象;在E3.5 d-E4.5 d时,还无法在形态上区分性腺的雌雄差异,在E5.5 d时,性腺在形态上表现是外部上皮细胞层和密集的下层髓质中的细胞索,到E5.5 d-E6.5 d开始出现形态上的差异,逐渐分化形成雌/雄性腺。在雄性胚胎中,性腺皮质开始退化,生殖细胞与髓质相互作用形成生精小管索结构。而在雌性胚胎中,左侧性腺体细胞和生殖细胞在皮质内增殖,皮质层显著增厚,右侧性腺则开始退化;在E6.5 d-E21.0 d期间,两性性腺出现显著形态学差异:雄性睾丸对称且大小相似,两侧性腺组织中的皮质层进一步变薄,髓质形成管腔结构,生殖细胞与周围的支持细胞组成生精小管索。而雌性卵巢组织不对称,左侧性腺皮质层逐渐增厚且结构致密,髓质结构疏松,卵母细胞开始进行减数分裂,尽管右性腺也能类似于左性腺发生髓质空泡化,但它无法形成增厚的富含生殖细胞的皮质,右侧性腺逐渐发生萎缩。相关生殖管道的发育在鸡两性间也存在差别,雄性缪勒管在孵化E8.0 d停止发育,并在E12.0 d消退;而雌性左侧缪勒管发育形成输卵管,右侧导管在E12.0 d后经历相对缓慢的退化后在孵化时完全消失[19]。
2 鸡胚性别决定或者性别分化过程中涉及的重要基因
鸡胚早期性别决定和性别分化过程中涉及很多相关基因的参与。目前研究较多的基因主要有DMRT1、SF1(orphan nuclear receptor steroidogenic factor-1)、LHX9(LIM homeobox protein)、DAX1(NR0B1,nuclear receptor subfamily 0 group B member 1)、SPIN1/SPIN1 L(spindling 1/spindling 1 like)、SOX9(sry-box transcription factor 9)、HEMGN(Z-linked male factor,hemogen)、AMH(anti-Mullerian hormone)、WT1(Wilms tumor 1)、CYP19A1(cytochrome P450 family 19 subfamily A member 1)、FOXL2(forkhead box L2)、ESR1(estrogen receptor 1)、HINTW(histidine triad nucleotide binding protein W)、UBE2I(ubiquitin conjugating enzyme E2 I)、WNT4(Wnt family member 4)等。其中DMRT1、AMH、SOX9、HEMGN等在雄性发育中起关键调节作用,而CYP19A1和FOXL2等在雌性发育中起关键的调节作用。上述基因中,DMRT1被广泛认为是调控公鸡睾丸形成的核心基因,DMRT1基因的剂量直接影响鸡性别决定进程。
3 DMRT1简介及胚胎期原位表达
DMRT1最早在无脊椎动物中被发现,是一种古老的性别决定基因,是少数几个在鱼类、龟类、鳄鱼、两栖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的代表性物种中被绘制的性别相关基因之一[20],DMRT1在许多进化物种中均表现出性别二态性(指同一物种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别)表达,是脊椎动物性别决定通路中的保守成分[21-22]。鸡DMRT1基因位于Z染色体26.45~26.50 Mb之间,其编码的mRNA长度为1 244 bp,由6个外显子组成,经典蛋白产物长度是365 aa(Uniprot)。DMRT1蛋白位于核内,是DM结构域(DM domain)家族转录因子之一,DM结构域在进化中高度保守,DM结构域基因是最早在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门类中显示出性别二态性表达的基因[21]。
DMRT1的表达具有很强的组织特异性,主要在性腺及相关组织中表达。Omotehara等[23]于2014年研究了鸡胚胎发育过程中DMRT1蛋白在雄性和雌性鸡胚的泌尿生殖系统(包括缪勒管)的表达模式(图2)。发现在性别决定的推测期(E4.5 d)之前,雄性未分化性腺的性腺体细胞与雌性相比表现出更强的DMRT1的表达,在鸡胚性别决定之后的E6.5 d,雄性鸡胚形成睾丸索的支持细胞表达DMRT1,同时发现在性别开始分化的E4.5 d后,雄性和雌性的生殖细胞同样能表达DMRT1,但在雄性鸡胚的表达是连续的,而在雌性鸡胚发育过程中,在左侧卵巢皮质生殖细胞中的表达不连续-从左侧卵巢皮层中央部分的生殖细胞向两侧边缘逐渐消失。同时DMRT1也在E4.5 d-E7.5 d的输卵管嵴(缪勒管的前体)中被检测到,在雌/雄鸡胚缪勒管的间充质和最外层的腔上皮都能检测到DMRT1的表达,DMRT1在雄性缪勒管退化前表达高,在E8.0 d,雄性缪勒管消退,DMRT1表达仅限于间充质区域,而雌性表达模式没有变化。尽管该研究对DMRT1基因原位表达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该研究仅主要集中在E4.5 d-E15 d,相关研究发现早在E3.5 d的鸡胚生殖嵴中就已经有DMRT1的表达[24],有关覆盖胚胎性腺发育全阶段DMRT1的时空表达图谱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线宽表示与异性相比的相对表达水平。阴影线表示性别决定的推定期
值得一提的是Ayers等[25]在2015年报道了DMRT1不仅在早期形成的鸡胚缪勒氏管嵴中表达,还在导管形态发生期间经历从上皮细胞转变到在间充质细胞中表达,同时发现在鸡胚中敲低DMRT1会导致间充质层大大减少,阻断导管管腔上皮的尾部延伸,因此提出DMRT1是缪勒管发育的早期必需步骤。然而Ioannidis等[26]在2019年研究DMRT1基因敲除后的鸡胚(Z-W)发育时,发现其能形成正常左侧缪勒管,该结果对DMRT1在缪勒管发育早期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值得注意的是Omotehara等[27]在2017年研究发现,部分表达DMRT1的皮质细胞仅在左侧睾丸发育开始后对左侧睾丸髓质中的支持细胞有贡献,结果表明DMRT1在睾丸中的表达存在不对称性。
4 雄性鸡睾丸形成依赖于DMRT1基因剂量
早在1999年,Raymond[28]就发现DMRT1在鸡性别分化之前的生殖嵴和沃尔夫氏管中表达,且在ZZ型胚胎中的表达水平高于ZW胚胎;Shan等[24]在2000年的研究中发现,DMRT1在E3.5 d的雄性生殖嵴中的表达高于雌性;Nanda等[29]在2000年基于染色体同源性研究中发现,DMRT1基因与人类上的直系同源物和人类XY性别逆转相关,提出DMRT1是脊椎动物性别决定最早期的剂量敏感基因。Oréal等[30]在2002年通过对性腺分化前后相关基因表达趋势的分析,发现在E5.0 d时DMRT1在整个性腺中表达,但由于原位杂交技术的局限性,未在此阶段揭示该基因表达是否存在明确的性别二态性,但在E6.0 d的鸡胚中,雄性比雌性显著高表达。随后,E7.0 d的雄性性腺中出现AMH和DMRT1的高表达(DMRT1在雄性性腺中比雌性性腺表达高两倍以上)以及SOX9的开始表达,且同时伴随着睾丸索的形成;除上述基因外,其他基因不呈现显著的性别二态性。另外,Yamamoto等[31]在2003年发现DMRT1表现出雄性特异性表达模式,提出DMRT1、SOX9和AMH在E5.5 d-E8.5 d时与睾丸形成有关。
Smith等[32]2003年在使用芳香酶抑制剂FAD(fadrozole)诱导的雌性反转为雄性的鸡胚中分析DMRT1的表达,发现性反转胚胎DMRT1表达水平升高,该现象与具有两个Z染色体拷贝的正常雄性个体相似,基于此结果,他认为睾丸发育中确实涉及DMRT1基因上调,但两个拷贝DMRT1并非是必须的;此外郑江霞和杨宁[33]在2007年,利用经芳香化酶抑制剂处理产生的性反转鸡胚进行试验,也发现DMRT1的上调表达与睾丸形成有关。2009年,Smith等[34]给出了有关DMRT1表达与鸡性别决定有关的最直接证据,他们使用RNA干扰技术(RNAi)敲低早期鸡胚中的DMRT1基因,发现试验组的雄性表现出部分性别逆转,导致遗传雄性(ZZ)胚胎出现性腺的雌性化,包括左性腺显示雌性样组织、睾丸索紊乱、睾丸标志物SOX9下降。该研究还发现,在性腺雌性化的ZZ鸡胚中,卵巢标志物芳香酶被异位激活,而且相比较于左侧性腺,右侧性腺DMRT1和异位芳香酶活化的变化更大,表明左右性腺对DMRT1的敏感性不同。
随后Lambeth 等[35]在2013年使用逆转录病毒载体RCASBP在鸡胚中异位表达芳香酶基因CYP19A1,发现雄性鸡胚胎中过表达CYP19A1诱导了雄性性腺向雌性的反转,此外还发现雄性性腺发育的关键基因DMRT1、SOX9和AMH的表达受到抑制,性反转雄性个体的生殖细胞分布和雌性相似。同年,Fang等[36]的研究指出在性别决定和性腺分化期间,由外源雌激素诱导雄性到雌性的性反转胚胎中,在E3.0 d-E5.0 d期间DMRT1表达活性较低。随后2014年Lambeth[37]的研究还发现,DMRT1在雄性胚胎性腺中表达上调是出现在HEMGN、SOX9和AMH表达之前的,这表明DMRT1在胚胎雄性性别决定中处于更靠前的位置,另外过表达DMRT1会诱导雄性发育相关基因的表达并拮抗胚胎性腺中的雌性相关途径,而在雌性性腺中异位表达DMRT1能诱导局部AMH、SOX9、HEMGN等雄性相关基因的表达。
2017年Hirst 等[38]在鸡胚发育E3.0 d时外源注射FAD至胚胎中,最终诱导了雏鸡雌性到雄性的性反转,在反转个体性腺中发现芳香酶活性显著丧失并伴随着性腺出现雄性化特征,但W染色体连锁的HINTW、FAF和FET1基因的表达水平在雌性鸡性反转前后没有差异,据此,提出是Z连锁的DMRT1而不是W性染色体调控鸟类的性别分化过程。
DMRT1剂量对鸡性别分化影响的最直接的证据是Ioannidis 等[26]在2021年的报道,基于CRISPR-Cas9的单等位基因靶向方法产生具有DMRT1基因靶向突变的鸡,发现由此产生的具有DMRT1单一功能拷贝的染色体雄性(Z+Z-)鸡发育形成卵巢,直接证明鸡性别决定机制基于DMRT1剂量,结果说明了在雄性个体中,DMRT1剂量(两个拷贝)对睾丸形成命运的决定作用,有趣的是突变鸡(Z+Z-)的外形、生长速度和肌肉发育等和野生型的公鸡更为相似,该结果也支持了鸟类动物的CASI假说。同年Lee 等[39]也做了相似的工作,采用CRISPR-Cas9破坏DMRT1起始密码子,发现在雄性鸡胚发育的早期阶段,DMRT1的破坏诱导性腺雌性化,在激素合成紊乱的情况下,雌性的功能性生殖能力无法实现。
5 DMRT1作用途径
有关DMRT1在性别决定和分化中如何发挥作用尚未有完善的试验性结果,但大多数研究推测认为DMRT1主要是与FOXL2拮抗抑制雌激素通路从而调节性腺分化的进程。Snchez和Chaouiya[40]2018年依靠已发表的试验数据组装了一个基因网络,形成了一个整合Z染色体剂量效应和W染色体显性效应的假设逻辑模型 (图3)。该模型表明,鸡性腺的命运是由DMRT1和FOXL2之间存在相互抑制的关系引起的,其中DMRT1产物的初始量决定了性腺的发育。Hirst等[41]在2018年的研究中指出,性腺中表达的DMRT1可以激活睾丸发育中的SOX9、AMH和HEMGN基因,同时发现DMRT1还抑制卵巢通路基因,如FOXL2和CYP19A1,但雌性性腺中较低水平的DMRT1表达与卵巢通路的激活是可以同时发生的。Major等[42]在2019年的报道中指出,雄性鸡胚性腺中FOXL2的错误表达会抑制睾丸发育途径,消除雄性发育相关基因DMRT1、SOX9和AMH的局部表达的同时会抑制支持细胞发育,也验证了FOXL2与DMRT1潜在的拮抗关系。

Z1和Z2表示任意一条Z染色体,而W表示W染色体;粗、细实线箭头分别表示促进和抑制作用,虚线箭头表示间接或潜在的作用
Ioannidis等[26]在2021年较为系统的阐述了DMRT1和FOXL2雌激素相关通路在调控性腺分化中的相互作用(图4)。该研究指出,在DMRT1表达正常的Z+Z+(两个拷贝)鸡胚胎中,DMRT1抑制FOXL2的表达,进而引起芳香化酶的表达减少和雌激素合成减少,在Z+W 胚胎中,DMRT1的量不足以抑制FOXL2的表达,从而导致雌激素E2对睾丸发育通路的抑制。另有研究发现,在DMRT1基因突变的Z-W胚胎中,虽然发育形成了卵巢结构,但与Z+W相比,性腺在形态上更小且皮质层薄,不能正常进行减数分裂,这表明DMRT1的存在对于雌性性腺正常发育也是必须的;在E2合成受阻的Z+W和Z+Z-鸡胚胎中,雄性相关发育通路未被抑制,发育形成了睾丸结构,同时在对照组野生型ZW胚胎的雌激素合成阻断试验中,性腺发育形成睾丸,但在E2合成受阻的Z-W鸡胚胎中性腺髓质类似于卵巢,结果充分表明了DMRT1的剂量效应对雌性发育的影响依赖于雌激素,DMRT1在雌性个体形成卵巢的发育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x和1x表示2个拷贝和1个拷贝;虚箭头和实箭头分别表示雄性和雌性的作用,线宽表示作用的强弱
目前相关研究发现,DMRT1直接或间接激活雄性相关因子HEMGN、SOX9和AMH的表达[43],但其在禽睾丸发育过程中的直接转录靶标目前尚不清楚。DMRT1促进雄性胚胎中的睾丸发育而抑制雌性胚胎中的卵巢发育,DMRT1很可能在鸡胚性腺中既能充当转录激活因子又能充当转录抑制因子,但这些还缺乏试验性数据支持。DMRT1基因在其他物种上的研究也值得借鉴,如在幼年小鼠睾丸中,采用染色质免疫共沉淀结合高通量测序技术(CHIP-seq)和RNA表达分析测定DMRT1全基因组靶标,发现DMRT1蛋白大约能结合到1 400个近端启动子区域,这里还包括DMRT1本身[44]。Lindeman等[45]在小鼠体内和体外细胞培养中发现,SOX9和DMRT1在颗粒细胞重编程成支持细胞中协同发挥作用,提出DMRT1可作为先驱因子开放染色质从而引起SOX9的结合。另外,Gao等[46]于2005年在斑马鱼上的研究发现,SOX5结合DMRT1启动子并抑制其表达,指出DMRT1和SOX5之间的拮抗关系,同时也表明DMRT1在早期胚胎发生中存在潜在的转录调控机制;Lei等[47]在2009年对大鼠的研究发现,FOXL2通过3.2 kb/2.8 kb调控区抑制DMRT1启动子,为颗粒细胞中的DMRT1转录沉默提供了潜在原因;Tang等[48]和Wei等[49]在2019年发现,DMRT1通过直接结合SOX30和SOX9B启动子内的特异性CRE正调控罗非鱼SOX30和SOX9B的转录。上述物种上的研究为解析DMRT1在鸡等鸟类动物上复杂的分子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6 DMRT1的潜在调控机制研究
6.1 miRNAs的调控
miRNAs是机体内调控基因转录后表达的重要途径,miRNAs通过靶向目的基因mRNAs的3′UTR区域沉默mRNAs表达或者降解mRNAs,以达到对基因表达的抑制作用。相关研究有证据支持miRNAs在鸡胚胎性腺发育中发挥作用,而关于miRNAs和DMRT1的研究提示miRNAs可作为DMRT1潜在的调控靶点。Bannister[50]使用雌激素诱导鸡胚雄性性腺到雌性的反转后,MIR202*的表达降低到正常雌性鸡胚的表达水平,而用芳香酶抑制剂诱导雌性到雄性的性反转后,MIR202*表达增加,研究还发现MIR202*表达降低与睾丸相关基因DMRT1表达减少相关,而MIR202*表达增加与FOXL2和芳香酶的下调以及DMRT1和SOX9的上调相关。结果证实,MIR202*的上调与胚胎鸡性腺的睾丸分化方向一致。此外,Cutting等[51]2012年通过对性腺中miRNAs的表达分析发现一些miRNAs在性腺中表达的二态性,也提出了miRNAs能潜在调节DMRT1的表达。
Warnefors 等[52]在2017年对雌/雄鸡不同组织miRNAs进行测序,研究结果发现了很多具有明显性别偏向性表达的miRNAs,其中miR-2954-3p编码基因位于Z染色体上,表现出雄性偏向性表达,且显示出对鸡Z染色体上剂量敏感基因的保守偏好。同时依据他们的测序结果,笔者发现gga-miR-30e-3p、gga-miR-2954-3p、gga-miR-202-3p、ggamiR-153-5p、gga-miR-6562_M2-3p、gga-miR-6562_M1-3p、gga-miR-138-2-3p和DMRT1也存在靶向关系,同时在性腺中也具有显著的性别偏向表达,可作为后续DMRT1基因研究的潜在靶点。此外,Prastowo和Ratriyanto[53]使用3个在线数据库(即miRDB、TargetScan和microT-CDS)挖掘靶向鸡DMRT1的miRNAs,共得到78个靶向DMRT1 的3′UTR的miRNAs,在最少两个数据库中发现了8个miRNAs。这些研究结果提示,miRNAs在DMRT1的表达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深入的机制解析还有待开展。
miRNAs作为药物治疗已经有广泛的应用,筛选潜在作用于DMRT1基因的miRNAs可能是实现性别调控的重要手段。
6.2 鸡雄性高甲基化区域(cMHM)调控
由于在鸡上没有直接证据表明Z染色体随机失活现象的存在,但鸡Z连锁基因在雌雄个体间的平均表达差异是1∶1.4~1.8[41]而不是1∶2,这说明有相关机制起到了一定的剂量补偿作用,其中雄性Z染色体上的MHM以及其附近区域的转录活性较低,对邻近一些基因表达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MHM也被认为是剂量补偿效应的一个解释。MHM 最早由Teranishi等[54]在鸡Z染色体的短臂上发现,位于鸡Z染色体的27.140~27.398 Mb区域内,其包含有200多个长度为2.2 kb的串联重复序列,在雄性体内高甲基化且没有转录活性,但MHM在雌性个体中低甲基化并能转录形成长链非编码RNA(lncRNA)[54-55]覆盖Z染色体。另外Teranishi等[54]还发现,在ZZZ三倍体细胞中,所有3个Z染色体的MHM区域都是高甲基化和无活性的,而在ZZW三倍体中,MHM区域是低甲基化并且两个Z染色体都能转录,这些结果提示W染色体或许存在某些特殊的调节方式调控MHM区域的表达。
Yang等[56]在2010年为了分析MHM对性别依赖基因表达的调控作用,构建含有鸡MHM的外源质粒并注射到13周龄公鸡的左侧睾丸中,结果发现用外源性pEGFP-N1-cMHM质粒处理的公鸡睾丸中DMRT1表达下调。Roeszler等[55]在2012年的研究中发现,在胚胎阶段雄性个体中的MHM的错误表达会导致DMRT1的表达受损;另外Caetano等[57]发现,在同一发育阶段,雌性中的MHM上调而DMRT1下调,从而提出MHM可能在卵巢发育中起作用,这些结果充分表明MHM ncRNA对DMRT1存在潜在调节作用。
Sun 等[58]在2019年对鸡Z染色体研究发现了两个雄性高甲基化位点MHM1(之前报道的MHM)和MHM2,MHM1、MHM2分别位于染色体27.140~27.398 Mb和73.160~73.173 Mb区域。在鸡的整个发育阶段,与大多数体细胞中的Z染色体其余部分相比,位于MHM1或MHM2附近(25~32 Mb,72.5~73.5 Mb)基因的表达(指雄性∶雌性的相对表达量)会降低,笔者发现DMRT1基因刚好位于Z染色体26.45~26.50 Mb之间,其表达可能受到MHM1的影响,但Sun等[58]未在性腺组织上采样进行比较,因此,在性腺组织中DMRT1转录活性是否也会受到MHM1影响还有待探索。
Shioda等[59]也报道了与之类似的表观遗传修饰对性腺分化的影响,其将遗传雄性(ZZ)鸡胚用外源性雌激素刺激处理后发现,在孵化时性腺暂时出现雌性化,性腺雌性化的ZZ个体在1年内被雄性化回退形成睾丸。该研究指出,性腺雌性化的ZZ个体中,可能其体细胞群和生殖细胞群都保持着遗传性别的转录组和表观遗传记忆。这种表观遗传记忆是否与DMRT1基因功能有关也还需进一步研究。
7 结论与展望
从对鸡DMRT1基因的研究进展来看,DMRT1基因剂量直接影响鸡的性别决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认为的DMRT1基因在性别决定中发挥作用的途径主要是抑制雌激素通路,而有关DMRT1的上游调控机制目前还没有系统完整的研究。因此,完善DMRT1基因在鸡等鸟类动物中所参与到的生物学通路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有两篇重要的报道:一是Ayers等[60]在2013年通过分析鸡胚性分化之前的E12 h胚盘和E4.5 d胚胎性腺中基因表达谱,发现这两个阶段的组织中,很多已知的性别相关基因和一些常染色体上基因已经出现了强烈的性二态基因表达,因此提出在表型可见的鸡胚性别分化之前分子水平已开启了性别分化;二是Ichikawa等[61]在2022年的报道中提出性别决定在雌性中似乎比在雄性中更早发生。上述研究结果让研究者们对细胞命运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而且后者的观点与现有的有关DMRT1抑制雌激素相关通路发挥作用的方式十分吻合,同时也暗示着在鸡等鸟类生物中,雌性发育的优先级更高。
DMRT1所处的复杂调控状态提示我们思考剂量表达的重要性以及机体为何要采取如此复杂的程序调控基因表达,如何实现如此精准的调控?雌性鸡为何会发生一侧性腺的退化?这注定不会是随机事件,因为总是右侧性腺退化,机体又是如何精准的控制不会发生错误的性腺退化?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进行补充。
在生产中,对鸡胚进行早期性别鉴定,甚至于能够实现只产雌性胚胎或者雄性胚胎,将节省大量的时间和人工成本,这无疑是家禽业发展的历史性革命,因此以DMRT1基因作为切入点,系统深入地研究鸡性别决定机制、描绘完整的性别分化图谱以及各环节基因间的调控关系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生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