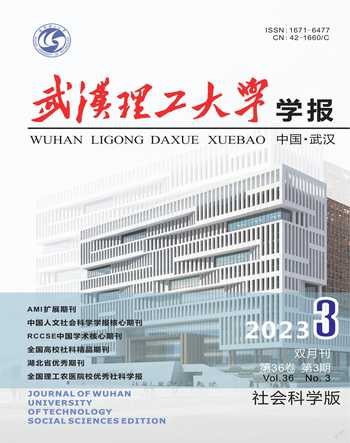崇高美学:从利奥塔到朗西埃
郭玉生 王蕙心
摘 要: 利奥塔认为崇高美学与意识不可把握、不可表达的悖谬性时间——“此刻”密不可分。以此为前提,利奥塔所理解的崇高不再附属于自然存在的对象,也不再涉及表现任何具体内容,而是感受“此刻”“发生”“事件”。在感受“此刻”“发生”“事件”的基础上,人对于绝对差异敏感的感觉力得以产生。利奥塔将康德对于崇高美学所提出的否定性的“无形式”发展为“不可再现物”。朗西埃把利奥塔的崇高美学视为法国当代思想“伦理转向”的典型例证。他认为利奥塔的崇高美学仅仅强化了既有感觉分配秩序,没有真正激活绝对差异,从而开拓新的感知方式。在朗西埃看来,利奥塔的“不可再现物”接近黑格尔的无限理念,其崇高美学体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利奥塔阐述“差异”旨在强调作为“事件”呈现出来的关于“不可再现物”的感性异质性,朗西埃提出“歧见”目的是为了推动可感性重新分配的美学革命。
关键词: 崇高美学; 利奥塔; 朗西埃
中图分类号: B83-0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3.03.013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立足于后现代思想,拆解现代性,反对元叙事,以“不可再现物”为核心建构崇高美学,强调对于绝对差异敏感的感觉力,确立了后现代美学与艺术原则。朗西埃作为比利奥塔晚一辈的法国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基于对法国当代思想“伦理转向”的理解,批判性反思了利奥塔的崇高美学,提出以“歧见”为基础解决法国当代思想“伦理转向”中出现的问题,进而发挥审美的政治潜力和批判功能。
一、 “此刻”与“事件”
在崇高美学的发展过程中,18世纪的美学家博克把崇高的情感理解为痛苦与快乐交织的矛盾情感。博克认为崇高的情感涉及的是对于虚无的恐惧,而对于虚无的恐惧又与丧失密切联系,例如光的丧失产生对于黑暗的恐惧;亲友的丧失产生对于孤独的恐惧;言语的丧失产生对于沉寂的恐惧;客体的丧失产生对于虚空的恐惧,生命的丧失产生对于死亡的恐惧。虚无的胁迫使人产生痛苦的感受。不过,在艺术中,人与恐惧之间保持着审美距离,恐惧具有悬置的、张而未发的特征,人由此获得了舒解恐惧的愉快。利奥塔的崇高美学赓续了博克的观点,否定了康德崇高美学所体现的主体理性和伦理指向。
利奥塔认为,唤起崇高的情感的“绝对”,并非康德所说的自然事物的数量或力量的绝对大,而是不断消逝、不可重复的“此刻”。“此刻”是一种永远在到来,而却从不作为“实体”而存在之物,与过去和未来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无中心、无秩序、无定向。人无法在意识中把握“此刻”,它在意识中只能以提问的方式存在:到来了吗?进而提问:到来的是什么?这种对于“此刻”的提问源自对虚无的焦虑,其所指向的并不是未来,而是现在:“但问号是‘现在,是此刻,就像什么也未到来的感觉那样:现在是虚无。”[1]103不过,类似于悬念和未知可以让人获得乐趣,这种对于“现在”的焦虑又能够让人感到愉悦,从而成为了矛盾的情感。利奥塔在这种焦虑与愉悦交织的矛盾情感基础上阐释了崇高美学。
利奥塔以先锋派艺术代表人物巴内特·纽曼为例分析了“此刻”与崇高的密切关系。他认为纽曼的绘画作品揭示了“崇高就是此刻”:“如果说有‘主题,那么它就是‘现时。它现在到达这里。‘在(quid)随后到来。开端是有……(quod);世界是其有。”[1]91“在”是一种确定的、可以被意识理解的存在状态,“有”则是一种不可思维、只可感觉的不确定性能量状态,它就是“此刻”。纽曼的绘画作品就是要展现“此刻”的充满偶然性、不可预测性能量状态,以此揭示总是存在着既不能被意识把握又总是在记忆中存在、既不能被复原又不能被放弃的东西,“纽曼的创造不是某个人的行为,它是到达未确定性中者(这)”[1]91。虚无由此产生,而崇高以对于虚无的恐惧为基础产生愉快,所以利奥塔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人们感到可能什么都再不会到来。所谓崇高,是指在这种虚无的胁迫中,仍然有某事物会到来,发生,宣示并非一切皆尽。一个简单的‘这字,最细微的际遇,就是这个‘地点。”[1]94按照利奥塔的论述,纽曼的绘画作品不传达任何思想意义,仅仅见证艺术作为独一无二性“事件”的发生,提供关于“此刻”的感受,即崇高。崇高的内涵在于“此刻”“发生”不可重复的“事件”,而对虚无的恐惧来自于“事件”将可能“不发生”的威胁,因此,崇高成为了人有效抵御虚无的屏障。这意味着,利奥塔所理解的崇高不再附属于自然存在的对象,也不再涉及表现任何具体内容,而是感受“此刻”“发生”“事件”。在感受“此刻”“发生”“事件”的基础上,人对于绝对差异敏感的感觉力得以产生。
康德主张,崇高的情感雖然源于有限的想象力把握超越时空、不可表象的“绝对”的失败,但随着理性理念被引入,想象力的有限性被克服,主体理性超越无限的能力就显示出来了。自然事物并不是因为数量或力量巨大,使人感到恐惧,然后被看作崇高的,而是人相信自己凭借理性战胜自然界中的恐惧力量,因此产生了无限自由感和道德尊严感。基于此,崇高成为了人从审美情感领域过渡到伦理道德领域的桥梁。利奥塔接受了康德所提出的崇高具有否定性呈现和无限超越性特征的思想,但不同意康德推崇主体理性的超越性、无限性或统一性,进而将崇高的情感道德化,他认为崇高的情感恰恰来自于理性面对“此刻”“发生”“事件”,呈现出了自身的有限性。“此刻”“发生”“事件”具有不确定性、无限可能性和开放性,理性不能将其概念化、符号化、形式化。纽曼的绘画作品所激发的崇高的情感就是最好的例证。当观众在一个狭长的空间里近距离感受纽曼的绘画作品所展现的一整块蓝色、红色涂料甚至是白色或黑色的虚空时,思想意识一片空白,体验到的只有颜色和材料带给感官的震惊。与此同时,观众又会感到茫然、晕眩、焦虑,他们无法依赖已有知识、理论和观念感受作品,之前的审美经验和趣味完全无效了。观众从作品中获得的,既不是对再现客体的辨认,也不是对外观形式的把玩,更不是伦理道德的教化,而是对于“此刻”“发生”“事件”的感受。因为“事件”不能被理性赋予确切意义,所以对于“此刻”“发生”“事件”的感受也就不能转化为审美快感和道德敬重。崇高的情感不是像康德所认为的只是由于数量或力量巨大的自然事物的激发偶尔产生,而是普遍渗透于社会生活细微之处,抵抗庸俗的日常,体现多元、差异与歧义,为人们在否定元叙事、元语言的后现代状况中思考、判断和实践提供依据与准则。
二、 “形式”与“物”
利奥塔强调,“此刻”“发生”“事件”不仅不能被理性、精神所把握,而且不能在艺术作品中再现出来。因为再现就意味着将“此刻”“发生”“事件”相对化、关系化,就是要将其放置在特定的语境和条件中。由此对“不可再现物”的强调成为了利奥塔崇高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利奥塔认为,康德对于美的分析强调形式综合了多种多样的不稳定的质料,这既使审美趣味具有了超功利性,又使审美判断具有了普遍性,体现了古典美学的和谐观念。美(优美)就体现了这种主体追求时空中形式的和谐观念。康德对于艺术的分析则提出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质料推动着艺术创造,同时,质料最终需要获得形式。质料与形式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是按照合目的性原则运作的,表现了康德美学思想中对于质料本身所具有力量的漠视和压制。不过,康德对于崇高的理解则走向了推崇无形式。他以犹太教禁止制造偶像为例,认为“这是最崇高的,因为它禁止了任何对绝对的表现”[2]。康德主张通过“否定的表象方式”来反证“绝对”这一理念的存在,从而激发崇高的情感。基于此,艺术家可以按照否定性“无形式”的方式暗示“绝对”,表现崇高,将人从审美情感引向善的追求。因此康德认为,“不必担忧崇高的情感会由于在感性的东西上完全是否定性的这样一类抽象的表现方式而丧失掉;因为想象力虽然超出感性之外找不到它可以依凭的任何东西,它却恰好也正是通过对它的界限的这种取消而发现自己是无限制的;所以那种抽象就是无限东西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虽然正因此而永远只能是一种否定的表现,但它毕竟扩展了心灵”[3]。
利奥塔在康德崇高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形式的破碎与无序,认为美(优美)和崇高之间出现了断裂,崇高抛弃了美(优美)所追求的时空中形式以及审美共通感。西方传统思想观念强调可感的物質统摄于形式,因此进入意识被表象的可感的物质并非无限杂多,而是已经渗透了“形式”的“被给予者”。为了区分于传统思想观念,利奥塔强调质料是非物质的或者说无形式的,这意味着,质料摆脱了对于形式的需求。在利奥塔这里,物质可被感知或可被认识,与精神相对并能够被精神把握。但是精神不能把握无形式的非物质,就像意识同样不能把握“此刻”,原因在于无形式的非物质体现了一种绝对差异。利奥塔以音调和色调作为例证,指出即便物理参数完全一致的音符或色彩,基于音调和色调所体现的绝对差异,在和谐的同一中也出现了千差万别,以致分类的确定性完全不能实现。就艺术领域而言,崇高不再呈现为康德所主张的想象力失败,而是形式与质料之间的紧张关系。形式不能转化和统摄质料,质料占据了绝对的优先地位。因此利奥塔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崇高之后的艺术悖论是,艺术转向了一种不转向精神的物,无论精神喜欢物还是讨厌物,都对精神绝无所求。在崇高之后,人们处于意愿之后。我对材料这个名词的理解是物。物不等待人们给它定命,它什么也不等待,它不求助于精神。……它是一种不能呈现于精神的呈现,它总在摆脱精神的控制,它不向对话和辩证法开放。”[1]156显而易见,利奥塔所说的“物”,不是指与意识相对并能够被意识所理解的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是指质料在音调、色调、纹理、芳香等不同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绝对差异,属于非物质的能量。对于质料所呈现绝对差异的感受能力是抵抗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总体化控制所形成非感性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利奥塔看来,质料作为无形式的非物质具有不可化约的差异,因此与“不可再现物”有着天生的亲缘性。利奥塔如此描述了“不可再现物”:“会有一种受到‘呈现折磨的精神状态,一种没有知性的精神状态,具有这种精神状态为的不是使材料成为可见的,可构想的,可给予的,可掌握的,而是为了有某物。我将之称为材料为的是指明这‘有。因为这种没有积极精神在场的呈现永远只是某种感觉状况、某种感觉中枢(sensoria)、某种感受力中的音色、音调和色调……”[1]155“不可再现物”作为一种源初的发生事件,不会频繁发生,因为理性、精神、意识等主体能力作为再现的源泉,会使关于“物”的当下体验成为虚无,所以这种事件的发生必须以理性、精神、意识等主体能力的中断为条件,突如其来。进而言之,利奥塔对于“不可再现物”所关注的是作为“事件”呈现出来的,关于“物”的“此刻”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感觉体验,这种感觉体验常常表现为“震惊”。“不可再现物”见证了主体理性的暴力,不可化约的差异,永不停止的抵抗等。
可以说,利奥塔通过崇高美学建构与后现代文化相适应的感性学,反对总体性,重写现代性。他所提出的“不可再现物”的观点凸显感觉,否定精神,消解主体,强调了崇高所寓示的矛盾、分裂或差异的张力内涵,深刻阐释了先锋派艺术,极大地拓宽了崇高美学的理论视域。
三、 “感性”与“再现”
朗西埃认为法国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出现了“伦理转向”,其特点在于消解了“现实与法则、是与应当”之间的差异,对于资本主义整体共识失去了整体性批判和反抗的能力。利奥塔被朗西埃视为法国当代思想“伦理转向”的代表人物。基于此,朗西埃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出发批判了利奥塔的崇高美学。他认为人的身体所呈现的各种样态,例如性别、族裔、信仰、语言、劳动能力等,并不会被共同体全部接受和容纳,其中有一些身体样态可能会被共同体根据价值排序排斥、压抑而沦为不可见的“无分者之分”。基于此,朗西埃提出了“治安”(police)这个概念,“治安”决定感觉秩序如何配置,由此体现共同体的价值排序,伦理则是治安的典型。伦理将共同体价值排序内化到人的感受体验、思想意识、实践行为的各个环节,比国家机器、社会制度、法律法规、意识形态等更隐蔽地塑造着主体的思维和性情。作为个体的人很少自觉反思伦理,即使偶尔反思,所运用的判断标准和表述方式也已经被伦理法则预先规范。伦理在共同体内部形成了共识,在共同体外部形成了异议,同时伦理对于共同体内部和外部各自场域的区分处于停顿状态,形成了伦理无区分的隔绝空间。
“政治”是与“治安”对立的概念,“治安”在共识的基础上配置感觉秩序,确定了可感性的范围,而“政治”把平等作为预设,反对共识的主导,否定现有的治安所配置的感觉秩序,以此“使本来没有位置、不可见的成为可见的;使原本被视为噪音的,成为能够被理解的论述”[4]。朗西埃所说的“政治”不是基于既定感觉秩序之内的利益或价值冲突产生诉求与期待,而是指向彻底更改感觉秩序。举例来说,工人要求与资本家均贫富,女性期待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工作机会,这都不符合朗西埃所提出的“政治”含义。原因在于前述要求与期待体现的是已经存在于治安所配置感觉秩序中的“有”,而不是“无分者之分”的“空”。与此相反,工人受雇装修资本家豪宅,在劳动之余把豪宅当作自己的家,观赏豪宅以及窗外美景;女性在家务活动的间隙,艾玛式陶醉于日常生活的某个瞬间或情境,此时未被治安组织和分配的感知经验突然出现,朗西埃所谓的“政治”才真正产生了。在此基础上,朗西埃阐述了政治与艺术的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特定时空中个别身体的在场形式。”[5]26政治与艺术都能够扰乱治安所配置的感知秩序并开拓新的感知方式,具有同质性。不过政治与艺术并不要求取消治安对于感觉秩序的配置,而是使治安对感觉秩序的配置产生紊乱,进而使之前未被命名、不被计数的不可见者前台化,使产生冲突的不同感知方式显现出来。基于此,朗西埃强调,利奥塔所提出的“绝对差异”、“不可再现物”恰恰体现了伦理无区分状态,使艺术与日常生活经验隔绝,导致艺术不能打破感性分配的等级秩序并开拓新的感知方式,从而丧失了应有的解放功能。
在朗西埃看来,利奥塔所提出的质料作为无形式的非物质具有绝对差异,其根据在于事件的普遍性。换言之,“不可再现物”虽然预设了某种无法抵达的理想之境,看起来似乎独立,实际上完全依附于事件。对于事件的发生过程,主体所体验到的是被动性的感受,原因在于主体并不能够控制事件的发生。朗西埃认为利奥塔与康德对崇高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康德主张,主体以崇高为中介沟通了美和善,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不仅超越了普遍绝对,而且在道德律中寻求到了超越普遍绝对的依据,由此崇高的情感表现了主体为自身立法的自由感。所以康德的崇高美学具有推崇主体性的特点。与此相反,利奥塔的崇高美学消解了主体性。在利奥塔这里,崇高呈现“不可再现物”,目的在于以感觉的方式而非精神的方式与绝对差异相遇。利奥塔所言的感性具有源始的纯粹接受性特征,对于“事件”的绝对异质性与独一无二性极为敏感,同时又不会压制“事件”的绝对异质性与独一无二性。朗西埃强调,利奥塔的崇高美学所指向的是一种“认为我们的精神亏欠了他者律法的无穷债务的症候。这种他者的律法可能是上帝,也可能是无意识之事实性力量的诫命。这就是不容置疑性最终所意涵的。这意味着一种极端的不对称的经验”[6]。朗西埃认为在利奥塔的崇高美学中,与“不可再现物”相关的艺术经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因此割断了艺术激进性与政治激进性之间的同盟关系,强化了某种感觉分配秩序,未能真正激活绝对差异从而使既有可感性重新分配,最终产生的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伦理共同体。
朗西埃不仅从政治维度尖锐批判了利奥塔崇高美学,还从美学维度深入反思了利奥塔崇高美学。他认为康德旨在把崇高美学的有效性延伸到主体的感性与伦理生成,利奥塔则把崇高美学的有效性限制在艺术之内。崇高艺术被利奥塔视为消极的表现,其呈示的是一种绝对差异即“不可再现物”的踪迹。崇高艺术通过否定性的方式呈现“此刻”“发生”“事件”。这种“发生”往往在意识把握它之前发生,所以崇高艺术不是呈现“此刻”“发生”“事件”的形象,而是“记录感性的冲击并且证明原始的差距”[7]171。利奥塔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视为西方哲学总体化倾向的典型代表,辩证法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排除差异的理性程序。因此,朗西埃指出,利奥塔的崇高理论的哲学主旨就在于否定辩证法的综合化运作。
不过,朗西埃并不认可利奥塔的崇高美学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否定。在他看来,利奥塔的崇高美学反而体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推论出一个抵抗任何辩证同化的原始的不可想物。不过这个不可想物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整体的理性化的原则。”[7]174黑格尔把崇高视为象征型艺术的本质,其特点是无限理念越出了有限事物的形象,理念与感性表现之间存在不和谐关系。在朗西埃看来,利奥塔的“不可再现物”接近黑格尔的无限理念。既然利奥塔把崇高艺术视为一种消极表现,那么他所阐发的仍然是一种再现艺术,“不可再现物”对于艺术再现體制而言是结构性的而非超越性的,因此巩固了艺术再现体制的合法性,所以利奥塔与黑格尔在此有着共同之处:“如果存在不可再现物,那也只有在这个体制中才能给它定位。在我们的体制中,在艺术的美学体制中,这种概念没有可确定的内容,充其量有一个与再现体制存在差距的纯粹概念。它表达了一种直指与意指之间稳定关系的缺席。但是这种失调朝着不是更少而是更多再现的方向发展:更多的构建对等的可能性,让不在场变成在场的可能性,让意义与非意义之间关系的特殊调节和表现与退缩之间关系的特殊调节相吻合的可能性。”[7]177
四、 “差异”与“歧见”
朗西埃在批判利奥塔崇高美学的过程中否定了其所提出的“不可再现物”。但是,否定“不可再现物”并非取消“不可再现物”,而是把不可再现的问题转化为调整再现焦距的问题。在利奥塔这里,艺术是无确定性、偶然性、不可规范性的创造,以否定性方式呈现绝对差异,他否定以理性、精神、意识等主体能力为基础形成的再现机制,认为再现机制与形式对质料的统治密切联系。基于此,“调整再现距离的问题转换成再现不可能性的问题。于是禁忌便逐渐滑进这个不可能性中,同时又自我否定,赋予自己物体的特性,作为简单的后果”[7]148。
对于利奥塔而言,艺术以否定性方式感性呈现“不可再现物”,也就是呈现“可见中的不可见”,由此利奥塔就面临着可见性问题。他通过比较分析摄影和先锋派绘画解决可见性问题。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摄影在世界的图像化再现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绘画面临着难以为继的严峻问题。这迫使先锋派艺术家重新理解绘画的含义。画家为了确定绘画的价值,就致力于描绘摄影无法再现的形象,“需要呈现出某种按照‘合法建构不能呈现的东西。他们着手动摇所谓的视觉‘已知条件,为的是使人们看到,视界藏匿着因而必然有某种看不见的,仅仅用眼睛(国王)所不能发现而要用心灵(流浪汉)才能揭示的东西”[1]138。因此,先锋派绘画所追求的是呈现“可见中的不可见”。“不可再现物”虽然不能被再现,但能够被暗示出来:“现时代的精神无疑已不是取悦于人,艺术的任务仍然是内在崇高,仍然是暗示一种毫无感化人之处的不可再现物,但这种不可再现物被录入了‘现实之转化的无限性中。”[1]141
可以認为,所谓“不可再现物”虽然从理性、意识或思维形式中逃逸了,但“不可再现物”在拒斥再现的同时又期待着呈现自身。先锋派绘画对于呈现“不可再现物”的方式就是认同抽象(abstract)而否定具象(figurative)。不过,抽象和具象尽管有着显著差异,但都是以可见的形象为基础呈现新的可见性。这样一来,先锋派绘画的特质实际上在于呈现“不可见中的可见”。利奥塔非常重视与“不可见”相对应的主体意识综合无法完全构造和恢复的向度,“有一种艺术思想,它不是无交流的思想,而是无概念交流的思想”[1]121。利奥塔的崇高美学强调激活绝对差异,推崇感性异质性,中断乃至悬置主体性。而“可见性”总是被主体意识所规范,被视觉模式所同化,压制着绝对差异的呈现。
不同于利奥塔推崇“不可见”,朗西埃更为重视“可见性”。他认为精神与感性之间的矛盾不是必然导向“不可再现物”,而是“意味着再现世界的出口,即定义不可再现物标准的世界的出口”[7]161。在朗西埃这里,“出口”就是释放被精神压抑的感性异质性,即“歧见”(dissensus)。“歧见”源于康德所提出的审美共通感,经由席勒的阐述,发展为包含差异的歧见共同体。由“歧见”形成的审美共同感既非认识对象也非意志对象;既不遵循由范畴决定的知性法则,也不服从由欲求支配的感性法则。席勒提出的审美经验中的和谐感受并不是产生于利奥塔所谓形式和质料统一,而是产生于知性与想象力之间的自由和谐关系,这种自由和谐关系蕴含着特殊的感知经验,并且在传统的等级支配的感性领域引入了新的平等的经验领域,最终产生了审美共同体的新形式,即歧见共同体:“美学的自由游戏,或者说中立化过程,确定了一个尚未到来的普遍和平等的感性新形式”[5]98。歧见共同体提供了取消身份等级,每个人都可以进入的空间,属于集体解放的审美共同体。
通过分析“歧见”的美学源流,朗西埃得出了如下结论:美(优美)并没有像利奥塔所宣称的走向终结,美(优美)与崇高能够在“歧见”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歧见,这个位于思想和感知之上的断裂已经处于美学的统一和安宁中了”[5]98。朗西埃具体论述了“歧见”的内涵:“不能被描述为部分的增补。它是感性与感性之间的另一种关系,既揭示又中立化感性之中心区分的增补。我将之称为歧见,歧见不是纷争,它是感性与感性之惯常关系的微扰”[8]。“歧见”既不是“同”,也不是“异”,而是“非”,即可感知的事物本身内部存在的裂缝,主要体现为平等的感知世界和不平等的感知世界之间的冲突。“歧见”作为审美区分使治安所配置的感觉秩序产生裂缝,打破了伦理区隔,否定了“治安”在“共识”与“异议”之间制造的对立,不可见的“无分者之分”得以呈现,朗西埃所谓的“政治”在此产生。这样一来,“歧见”成为了主体反抗既有感觉秩序的政治行动。利奥塔提出“差异”旨在强调作为“事件”呈现出来的关于“不可再现物”的感性异质性,朗西埃倡导“歧见”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可感性重新分配的美学革命,提供法国思想“伦理转向”带来的“现实与法则、是与应当”无区分问题的解决方案,激发人的实践热情,从而发挥审美的政治解放功能。不过,朗西埃的崇高美学期望通过以“歧见”为基础的美学革命,重新分配可感性,实现政治平等,在社会实践中缺乏可行性,结果可能只是幻象。
[参考文献]
[1]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M].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3.
[2]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M].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37.
[3]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4-115.
[4] Jacques Rancère.Disagreement:Politics and Philosophy[M].Trans.Julie Ros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29-30.
[5] Jacques Rancière.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M].Trans.Steven Corcora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9:26.
[6] 朗西埃.美学异托邦[M]//汪民安,郭晓彦.生产(第8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208.
[7] 朗西埃.图像的命运[M].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 Jacques Rancière.The Aesthetic Dimension:Aesthetics, Politics,Knowledge[J].Critical Inquiry,2009,36(1):1-19.
(责任编辑 文 格)
Sublime Aesthetics: From Lyotard to Rancière
GUO Yu-sheng, WANG Hui-xin
(School of Literature,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Heilongjiang,China)
Abstract:Lyotard believes that sublime aesthetics and consciousness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inexplicable and inexpressible paradox of time——the “present moment”.Based on this premise,the sublimity understood by Lyotard is no longer attached to the objects of natural existence,nor does it involve the expression of any specific content,but rather the perception of the “moment”,“occurrence”,and “event”.On the basis of feeling the “present moment”,“occurrence”,and “event”,a persons sensitivity to absolute differences can be generated.Leotard developed Kants negative “formless” view of sublime aesthetics into an “irreproducible object”.Rancière regards Liottas sublime aesthetics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ethical turn” in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He believes that Leotards sublime aesthetics only strengthen the existing order of sensory distribution,without truly activating absolute differences,thus opening up new ways of perception.In Rancières view,Leotards “irreproducible object” is close to Hegels infinite concept,and his noble aesthetics reflect Hegels dialectics.Leotards exposition of “differences”aims to emphasize the perceptual heterogeneity of “non reproducible objects” presented as “events”,while Lancier proposed that the purpose of “differences” is to promote an aesthetic revolution in the redistribution of perceptibility.
Key words:sublime aesthetics; Lyotard; Ranciè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