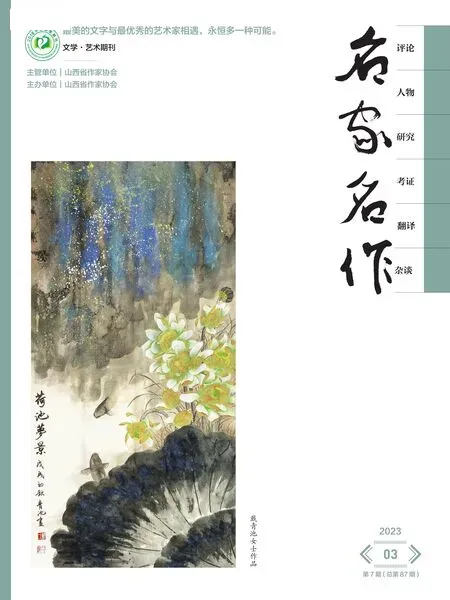城与乡的摆渡人
——王安忆的创作梳理及其城乡构建比较
周琪儿
从空间上来讲,王安忆将创作分为城市与乡村。城市并不是先进文化的代名词,而乡村也并不是腐朽落后的。王安忆在作品创作中加入了自己的审美与考量,并将城乡的差异落实到了具体的人物塑造与细节描写之中。王安忆在安徽插队有过一段不长的知青生活,正是这一插队记忆为她日后的创作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我们不得不关注作为“上海作家”的王安忆的另一种身份——知青作家。这一身份让王安忆具有了独特的乡土观察的出发点和写作视角。纵观王安忆近30 多年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生活”与“上海生活”经常交叉、交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于是,我们不仅要考察如《小鲍庄》《大刘庄》《姊妹们》《隐居的年代》等以乡土为主体的作品,而且要考察王安忆在不同的时代际遇中如何处理城乡关系,其中包括在大的时代节点上王安忆对城乡社会的体验和感悟。
一、归去来兮——创作脉络梳理
当我们梳理王安忆的小说时,发现其创作大致路线为:农村—城市—反观农村。
20 世纪80 年代“上山下乡”,体验农村生活,在当时一众寻根热潮中批判农村不变的、落后的文化。
20 世纪90 年代回到上海,思索城市精神及文化底蕴,也就是《长恨歌》的创作阶段。
20 世纪90 年代末到21 世纪初,思想成熟,反观农村,退居于“我们的村庄与我们的城市之间”。
王安忆在创作中心上实现了“归去来”。在20 世纪80 年代“上山下乡”时,她的创作主要是基于农村插队生活的经验,而20 世纪90 年代末到21 世纪初期的乡土作品是从城市写作中回归而来的,此时她对城市与农村有了深刻的领会和把控,在谈农村时则呈现出了另一种全新的视域——“我们的村庄与我们的城市之间”。王安忆前期的乡土作品是基于现实的虚构,后期的乡土作品则是从大量的虚构中回到了现实之中,由绚烂归于平淡,从最普通的生活中寻找情景和形式以探究它们的审美本质,带有重新发现与重新审视的意味。这种“归去来”的写作脉络与时代浪潮紧紧相连,20 世纪80 年代的文学亟须转型,而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的知青发现了乡间无路可走,便又返回了城市,而后农村中的新生一代也不断地寻求走出农村,因而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再到城市的人口迁徙大趋势,这一趋势也反映在了作家们的文学创作之中。王安忆便是其中的一位。
(一)20 世纪80 年代的群像叙事与城乡墙基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王安忆的乡土文学作品有《小鲍庄》《大刘庄》《流水三十章》等,此时,王安忆被划入了当时的寻根派作家群。其实,王安忆就其创作本身而言并不完全聚焦于“寻根”“农村”这类,她涉猎的范围比寻根派更广。如果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的话,其实是上山下乡与改革开放在文学上的反映。“上山下乡”是近代中国规模空前的文化移置和改造运动,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同时“山”“乡”也被知识分子融入小说的建构之中。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学从20 世纪70 年代末的呼唤改革转向了20 世纪80年代的面向世界,呈现出多向度探寻特征,继而引发了“寻根文学”这一文学思潮,带有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与主题话语模式,带着特有的地方性经验。王安忆在寻根主题上并没有将目光聚焦于特定的女性形象,而是塑造了一个农村群像。
《小鲍庄》中有这么劝丧孙的鲍五爷的:“现在是社会主义,新社会了。就算倒退一百年来说,咱庄上,你老见过哪个老的,没人养饿死冻死的!”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揭露点。“社会主义新社会”和“倒退一百年”之间用了“就算”一词连接,也就是说,一百年前与现在也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在没有实现共产主义、推崇无私奉献精神的情况下,村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价值观念已经代代维系了下来,农村有其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一套价值、宗法体系。再如《隐居的时代》中作者写道:“这样的以家族为组织单位的乡村就是一座坚实的堡垒。”亦是谈的这种制度坚不可摧。《小鲍庄》写的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时间线是与当下时间所吻合的。它强调了“仁义”,同时农村人也不断地对城市进行主观想象,比如“城里疯人院”;当谈及童养媳时写道:“小鲍庄的童养媳是最好做的了,方圆几百里都知晓,这庄的人最仁义 ,可惜太穷了。”有一种正话反说的意思。在第十节作者则提到了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的斗争状况,将处于虚构时空的农村与历史时间联通了起来,同时也通过对比表现了农村的闭塞滞后与城乡墙基的牢不可破。在这种以村庄为规模的叙事中,王安忆的视角是广阔而深沉的,她借助新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与地域文化掩体显示出独立的文化觉醒。
(二)20 世纪90 年代的知青文学与乡土女性
20 世纪90 年代初,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城乡之变与社会转型,文学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收获期,同时也受到了市场浪潮的冲击。在这样的浪潮之中,王安忆在知青文学的延长线上更倾向于女性成长小说,同时在寻根文学的延长线上向20 世纪90 年代展开。
构成王安忆20 世纪90 年代小说创作主流的是《姊妹们》《蚌埠》《喜宴》《开会》《青年突击队》《花园的小红》《王汉芳》等一批乡村小说,多为短篇,风格写实,创作灵感来自王安忆“感性的经验”,即知青插队的生活体验。王安忆认为:“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了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王安忆通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纯粹的农村生活在她笔下的反照,而是通过作者有意的审美加工,使作品拥有了另一番世俗的人间情怀。王安忆为了维护农村生活未经雕琢的、质朴本真的特性,特意压低了叙述声调,拉开了叙述距离,而在冷静客观的叙述中又蕴含着叙述者的温情与怀想。《喜宴》中的知识青年、《开会》中的孙侠子、《青年突击队》中的小勉子也接续了20 世纪80 年代《大刘庄》《小鲍庄》和《姊妹们》的时空架构,作者仿佛写成了不同形态的连载短篇小说,相互衔接呼应。
知青作家的心理结构具有半制度化半知识分子化的特点,他们一面立足于对农村的崇敬,另一面却站在城市知识分子的美学立场上。王安忆的插队生活让她拥有了地方性经验,她同时又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这一经验进行了文学建构,将具体的情节安置在知青时代,主题也与知青文学的恋爱、劳动、思想相关,而实际的叙述却更致力于获得一种失去时空特征的恒定感,因而使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具有了自身以及20 世纪90 年代的审美特征。
(三)21 世纪初的移民文学与城乡流动
21 世纪初,王安忆出版了《富萍》《剃度》《上种红菱下种藕》《遍地枭雄》等乡土小说,其主人公通常流动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这一阶段,作者不再强调城市与乡村的地域性和时代性,而是重点落在了城市与农村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这种特征在《遍地枭雄》这一作品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在经历了市民社会中年代以来朴素的劳动与审美观念的失落以后,王安忆在移民文学中重新发现并解构了城市中的“劳动与美”的历史。
《富萍》是城市里的农村,而《上种红菱下种藕》则是正在城市化的农村。因此,《上种红菱下种藕》的主人公秧宝宝是成长着的,而农村也是成长着的。秧宝宝年仅9 岁,女孩成长岁月中的琐琐碎碎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身处江南古镇转型期细腻敏感的少女形象。小说的结尾,她即将走入绍兴、走入城市。从农村到乡镇,再到小城绍兴,还有隐含的更大城市,都指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父亲夏介民的生意做得越大,秧宝宝也会走得更远,与农村的距离也越来越大。她不自觉地被父母的愿望拖着走,而她本人也在父母的愿望中成长,正如正在城市化的农村一样,也会与原本的模样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而《富萍》则更像是秧宝宝的接续,她依旧从农村走向城市。《富萍》写的是一个名叫富萍的扬州乡下女孩,因在乡下与男青年李天华的婚约关系而到上海看望李天华在上海帮佣的奶奶。尽管历经艰辛,在上海的生活使富萍渐渐了解了上海,最重要的是在这座城市里她感受到了虽然作为女性,但只要辛勤劳动,“在哪里活不下去?”最终富萍选择留在了上海,嫁给一个自尊、乐观 、肯干的残疾青年。通过对21 世纪初王安忆乡土女性文学作品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该阶段女性主义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加成熟,女性形象也更为复杂,不再是单一的农村妇女或者女知青,而是城里的异乡人和乡里的异城人,在接续了20 世纪90 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的基础上,开始关注女性的自我认知、自我发展和如何成长的问题。
其实,王安忆的城乡小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她不仅会在城镇叙事中掺杂乡土元素,也会在乡土作品中插入城市。我们可以这样看,农村的对面是城市,城市的对面是农村,两者是相呼应的,王安忆在写城市的时候也是对农村的投射,而在写农村的时候也一样会对照城市,所以在她的笔下,城市与农村绝非二元对立体,而是在思考两种文化交织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我们可以用一种共通的视角来观之,城与乡在其创作中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王安忆期待在城市中发现乡村,期待在文本中创造出“劳动与美”的理想形态。
二、常与变——女性主义叙写
从人物塑造来看,王安忆的都市小说基本上都由女性来充当主角,因为她要通过城市与女性之间的密切关系来展现城市的精神与生活图式,而这一关系是相对于男性城市更加稳定且绵远的,类似于“点滴到天明”的细腻温暾的感触。王安忆的小说始终贯穿着一个永恒的主题,即对女性的人生经验与个人的独立意识的书写,而在这个主题的下面又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转变。
从乡土女性的人物形象出发,自20 世纪80 年代的《小鲍庄》到20 世纪90 年代的《王汉芳》以及后来的《富萍》,她对女性的心灵世界的理解,不仅是对物质的拷问,更是对心灵的反省,使我们看到了一部埋藏在历史尘埃中的女性的心灵史与奋斗史。王安忆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意识的不自觉中,表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发展历程。其创作主题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循序渐进的特点,即女性的自我觉醒、自我发展、自我重构。这三个阶段与乡土创作的阶段呈现出一种动态映照的关系。乡土女性的自我觉醒较为突出的是《小鲍庄》中的小翠子这一童养媳形象,她以“我才十六岁” 进行着宣告与反抗,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爱情。创作重心落在女性的自我发展上的应该是《王汉芳》一类的知青文学,王安忆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知青女性寻求发展,而是农村妇女寻求发展。她从日常生活出发,把女性放置在持久的农村日常生活中,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审美能力与实践能力,同时女性自身的魅力又美化了日常生活。到了20 世纪末,随着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衰落与女性主义研究的转向,书写乡土世界成为女作家重新打开广阔的外在世界并寻求女性主体解放与新生的重要途径,此时王安忆以富萍的形象以及其内在的劳动美实现了重构,走向了生命的舒展以及两性和谐。
在王安忆笔下,城市的变化就象征着女性的变化,女性的命运也暗示着城市的改变,对于女性的叙述与描写在王安忆的城市小说中呈现出一种纵向聚合的能指世界,女性也成为纷繁的城市意象中的一种。而王安忆的整体乡土小说并没有完全地凝聚于女性,她不同时期的创作重心都有所偏移。她虽然写的乡村在地理范畴上并不大,但是所塑造的农村人际关系却是复杂宏大的。在乡土小说中,王安忆也更多地触及了城乡关系之间的问题,例如《姊妹们》中关于走出去的言论:“事实上,她们大多只能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但这种宿命并不能消除她们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她们特别热心她们也许永远不能企及的地方。”当然,这种宏观又局限的视角到了21 世纪初跟随着王安忆创作经验的积累也发生了流变,比如《上种红菱下种藕》和《富萍》的叙事重新聚焦在了女主人公的形象上,而聚焦的问题也跟随时代产生了新的变化,她开始探讨女性如何从农村走向城市,又为何从城市走回农村等一系列问题,较之于前期庞大的宗法村落叙事体系,王安忆将笔触落在了女性身上,笔下的农村也发生了新变,它不再像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凝固,而是受到城市、工业文明的影响开始发生转型,揭露的是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关系,并且农村的转型与蜕变表现出一种苍凉之感。
当讨论王安忆的乡土文学作品时,我们不仅要进行城乡的对照、阶段的对照,还可以从中挖掘女性主义的发展与成熟,以及在不同阶段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女性与农村之间的紧密联系。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女性笔下的乡土”与“乡土中的女性”在互动的目光之中构成了对于改革开放后乡土世界的女性言说,并形成了独特的乡土性别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