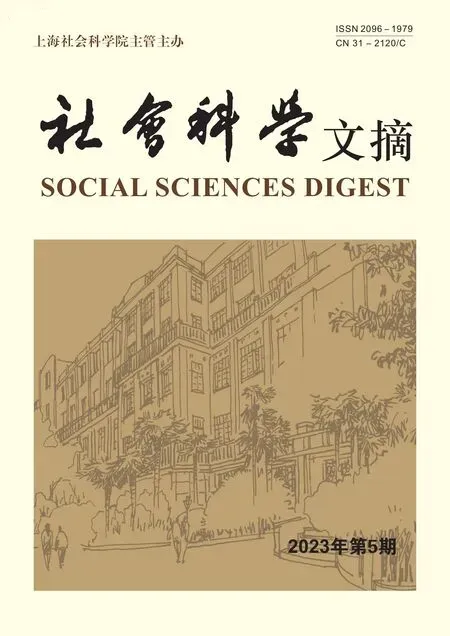文化视野、对抗式批评与宗法共同体
——重审《白鹿原》阐释史上的几个命题
文/沈杏培
《白鹿原》无疑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现象级文本。这个文本自身的经典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吸引着人们久盛不衰的阐释热情。从文化角度“拯救”民族历史,以浓郁的地方村落经验为中国西部大地作传,用儒家文化为小说赋魅,这是陈忠实在这部经典中确立的写作法度。在大的文学形制和文学基本品质方面,《白鹿原》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宗法制文化在现代社会大潮下的崩溃与挣扎,勾勒了具有存史意义的典型文化人格景观,在文化表达和文学叙事上取得了惊世骇俗的效果。当然,陈忠实和他的“垫棺作枕”之作在收获实至名归的褒赞和盛名之时,争议、批评和商榷之声也从未停止。本文重新聚焦《白鹿原》的儒家文化视角、对抗式批评、复线历史和宗法共同体等问题,并对这些命题的逻辑、特点、优劣等问题进行辨析。
儒家文化视角的生成逻辑及其叙事羁绊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之初到《白鹿原》的构思和创作之间,陈忠实几次经历创作的危机、困境以及自觉的调适。《白鹿原》的诞生可以视为陈忠实在文学观念和写作手法上对旧有写作陈规的一次超越,是作家写作生涯上的自我升级和“危机克服时刻”。从忠于现实表现到启用文化视角,从注重塑造人物性格到注重开掘人物的文化心理,这是陈忠实80年代文学发生的巨变。正是这次变化,才有了后来的《白鹿原》。对于陈忠实来说,引入“文化心理结构”,首先在于帮助他在塑造人物方面确立了新方法和新的叙事角度。可以说,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既是《白鹿原》的叙事内容,也是塑造人物的核心方法,儒家文化在这部作品中具有毋庸置疑的主体性地位。
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中具象化为白鹿村的“乡约”规定。这种“乡约”精神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心理结构,构成了《白鹿原》的基础质地,人物气质、性格类型、行为动机都受此制约,并形成了白鹿村的主宰式人格、顺应式人格、堕落式人格、反叛者人格。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象征着白鹿村最高智慧的半人半神的朱先生无疑是主宰式文化人格的体现;白孝武、白孝义、鹿三和白鹿原上众多贤妻良母式女性属于顺应式人格;而鹿子霖、白孝文无疑代表了这种文化的反面,是一种丧失了仁义传统和乡约精神的堕落人格;白灵、鹿兆鹏、鹿兆海、黑娃这些原上的年轻一代,以不羁的个性和决绝的抗争成为儒家文化的反叛者,是这种文化内部生长出的异质性力量,有力地冲击或解构了这种文化的现代合法性。白嘉轩和鹿三之间平等友善的主仆关系,以及鹿三怒杀田小娥,其背后体现的依然是儒家文化逻辑。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陈忠实试图让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统摄性的力量主宰《白鹿原》的叙事进程和人物性格内在逻辑,然而,客观上这种叙事意图和雄心在写作实践中并未能实现,相反留下了诸多叙事裂隙和逻辑谬误。白鹿村的“耕读传家”和“仁义至上”的教谕固然能够处理白鹿村内部世界的问题与危机,《乡约》所代表的宗法文化能够通过惩恶扬善和有效运行维持这个世界内部的秩序。但是,当白鹿原的叙事溢出原上这个小世界,叙事则显得散漫。这典型地表现为小说前半部分灵动饱满,后半部分叙述各种历史大事件时则显得仓促生硬,这种前强后弱、前盛后衰的叙事局面根源还是在于儒家文化不能主宰小说的始终,而在文本上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缺憾。即使如白鹿原上的圣人朱先生,作为《白鹿原》里被极度神化的智者,面对大时代,他对于国共两党“大同小异”“为啥合不到一块”的这种认知,充满了显见的偏见和短视。这是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历史处境,二者之间是脱节的,儒家文化视野无法解释现代历史运行的规律,儒家文化自身也并未很好地融入现代社会之中。也就是说,《白鹿原》所书写的“白鹿原秘史”和“民族宏大历史”两大叙事主体之间实际上是脱节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不能成为勾连这二者的有效黏合剂,从而使得小说在整体上留下了叙事失衡的缺憾。
由于这种既定的文化心理视角,《白鹿原》在人物塑造上实际上也戴上了有形或无形的枷锁,造成了人物形象的程式化,甚至由于既定的文化人格的设定,造成了人物行为逻辑的紊乱或缺失。陈忠实自己说,他对白嘉轩进行了“删减”,删减实际上就是对白嘉轩人格的提纯,对于可能会溢出这个理想道德和人格的其他维度进行删削。可以说,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等人都是单一向度的人格类型,成为某种固定的文化隐喻与人格修辞。
此外,由于过于强调儒家文化对人的内在规约和主宰作用,因而《白鹿原》中的人物常常必须脱离自身的性格逻辑和行动逻辑,而强行听从于儒家文化的调遣。黑娃从投身革命到落草为寇,再到回归祠堂,构成了一个能够自洽的叙述逻辑,凸显了儒家文化对个体的规训。但客观上,这种逻辑选取并没有构成一种普遍性的现象,这是白嘉轩的一种文化幻想和现实幻觉。黑娃回归祠堂的叙事凸显了文化逻辑和文化的力量,但也限制了人物性格发展和行为选择的多样性,损伤了艺术自身的逻辑生成。
《白鹿原》阐释史中的“噪音”与“对抗”
《白鹿原》的经典化过程,一直伴随着各种批评、质疑的声音。回顾、省思、辨析这些经典化历程中的“噪音”,有助于我们在更为多维的阐释视野里理解这部文学经典。客观而理性地审视人们提出的《白鹿原》的所谓瑕疵或局限,实际上是在一种对抗性和对话性的关系中拓殖这部经典的其他意义和空间,也是在作品既有维度和品质上挖掘其他可能性的应有之举。
《白鹿原》在90年代初发表,引发好评并获得“史诗”“杰作”赞誉时,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分析视角。这些批评聚焦的并非这部经典的细枝末节,而是涉及作品的史诗主旨与文本叙事的融合、整体篇章结构的均衡、思想表达与艺术生动的共生等重要问题。同时,不少研究者看到了《白鹿原》对待传统文化的矛盾和悖论性态度。而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白鹿原》的批评不断涌现出新的观点,丰富了对于这部经典的阐释。这些解读,带着阐释者鲜明的批评意识,犀利指出《白鹿原》文本和作家思想认知上可能存在的局限、困境和矛盾,打开了作家和文本未能到达的高度和深度、精彩和深刻,措辞虽严,其情也真,为我们理解这部经典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价值基点。
整体来看,围绕《白鹿原》形成的商榷、质疑和否定构成了《白鹿原》阐释史和接受史的重要内容,也是这部名作经典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维度。《白鹿原》的批评史,本身已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关于这部经典的“副文本”。在众多批评中,不免感性、苛刻、偏见之论和故作惊人之语,也有不少犀利、深刻而理性的观点,与《白鹿原》构成了对话关系。在《白鹿原》的阐释史中,关于该作的“修改”和“获奖”是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陈忠实在访谈文章中,曾详细叙述了关于修改和获奖的原委。实际的情况是,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已经确定把奖颁给《白鹿原》,评委会觉得小说中有两个细节值得商榷,征询陈忠实愿不愿意做些修改。这两个细节即是朱先生说的两句话,即“白鹿原这下成了鏊子了”和“国共无差别论”,陈忠实当时就表示接受修改意见,并对两处做了近3000字的删改。这两处修改对文本的整体思想与人物的完整性并未形成大的影响,在专业编辑看来实际上属于“并非伤筋动骨的修改”。因而,指摘陈忠实放弃作家独立性迎合评奖要求,给作家扣上“可怜的功利主义”的帽子,实际上显得苛刻而偏颇。
《白鹿原》发表至参评1997年的茅盾文学奖前后,被非议较多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朱先生“翻鏊子”的一通言论,让作品的“历史倾向性”和“政治倾向”受到质疑,也一度让该作参评各种文学奖项蒙上了阴影。陈忠实本人并不认同这种指摘,把这种意见视为“误读”,他认为“鏊子说”符合朱先生的文化心理结构。客观来看,根据小说人物所说的言论而给作家扣上某些“帽子”,这是庸俗而低劣的解读方式。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一方面,历时性呈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思潮更迭和典型事件,在大历史视野中呈现人的生存处境与各式文化人格;另一方面,通过一些生动精微的历史场景、人物言行呈现了历史的偶然性、非线性与非主流的一面。
可以说,陈忠实以一种严谨客观的历史精神,深入中国复杂的现代史和革命史内部,呈现出历史深处的多重景观,这些叙事超出了狭隘的阶级或政治立场,突破了单一的进化论史观,体现了小说试图为遮蔽的历史张目的叙事意图——这是《白鹿原》体现的小说精神和历史意识,值得肯定。当然,毋庸讳言的是,学界关于陈忠实及其《白鹿原》的批评意见中,有不少真知灼见,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客观正视并理性探讨它们是《白鹿原》经典化和历史化的必然要求。
文化乌托邦、复线历史与宗法共同体
《白鹿原》是关于乡土中国前现代文明的一曲挽歌,白鹿村凝聚了传统宗法制文化的核心要义,并在近现代波诡云谲的历史浪潮中承载着时代剧变带来的革命性冲击和现代性转型。陈忠实通过《白鹿原》对儒家文化及其宗法制规约进行了一种考古式深描,试图发掘这种文化在现代社会延续和再生的可能性,显然这种复古和寻根之路带来的是一种悲剧性结局。白鹿村的祠堂并没有能够规约白鹿村的所有子民并继而收编所有孝子贤孙并让他们臣服。白嘉轩的仁义道统,并没能在后代身上得到绵延和继承,相反,子辈毫不留情地对白嘉轩的文化古训和精神遗产进行了挥戈一击。
《白鹿原》构思与写作于“寻根文学”方兴未艾之际,创造与“寻根文学”相异的反思路径是陈忠实的自觉诉求。区别于在古旧历史时空中寻根的写作路径,陈忠实借助于白鹿原在现代社会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呈现现代史视野里的文化寻根之旅。实际上,《白鹿原》的这趟寻根之旅在结局上,和韩少功、王安忆、李杭育的寻根叙事几乎殊途同归,所谓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一个高亢、乌托邦的开头,续上一个悲怆而挽歌式的结尾。可以说,《白鹿原》充满了寻根的幻灭,陈忠实念兹在兹的关中学派以及白嘉轩、朱先生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在近现代的历史变革时期面临着深刻的断裂、转型与重生。
《白鹿原》除了描绘村落小历史和文化乌托邦,也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大历史。以白鹿原为圆心的“小村落”和宗法“小共同体”,与以近现代史作为主脉的“大历史”和“大事件”是《白鹿原》叙事的两极。《白鹿原》关于现代中国的讲述采用了复线历史结构,在白鹿原的地方村落史演进中穿插了大时代的历史脉络。在这种多声部的复线叙述中,陈忠实放弃了传统因果式和进化论的历史观念,细腻勾勒了历史现场中那些精彩生动的场景,真实敞开了大历史中那些惶惑的时刻,大胆定格了历史现场中那些循环甚至退步的趋向,释放了被进化论史观、革命史观所摒弃的那些历史场景和意义系统,有效打捞出了那些散失的、被压抑的历史。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复线历史在历史事件上的拥堵造成了小说叙事的“事件大于人物”局面,造成了事件铺排与人物塑造、情节推进与性格逻辑之间的断裂。
值得注意的是,《白鹿原》所创造/再现的“关中宗法共同体”,成为当代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景观,作为一种地方经验的陕西村落文化和关中宗法秩序,经由小说《白鹿原》的勾勒和传播,得到了当代延展和艺术创造。从这个角度看,随着《白鹿原》的经典化,白鹿原作为一个重要文学地理标识越来越成为当代人观察、理解关中村落文化及其宗法秩序的一扇文学窗口,这是陈忠实及其文学经典的功绩。白鹿村这个共同体,当个体顺从共同体的秩序和教条时,个体能够得到“保护”,但大多时候,共同体与个体之间是对立、紧张的。共同体扼杀个体的诉求,干预并剥夺个体的情感与婚姻选择,惩戒个体超出“乡约族规”的离经叛道之举,取消个体的反抗意志。正因为这种村落共同体借助于奴役、惩戒机制控制并束缚着个体,并将之常态化、秩序化,从而造成白鹿村个体思想和行为选择上的“不自由”。可以说,《白鹿原》的“宗法共同体”塑造的是静默化、顺从型和被缚型的文化人格。
在陈忠实的写作谱系里,农民一直是很重要的写作内容。经历过80年代中期的写作裂变,在卡彭铁尔进入海地、寻根文学和文化心理结构“三条因素”的刺激之下,80年代中期之前的乡土写实型叙事遭到了陈忠实的扬弃,他的“农民世界”的叙事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种统摄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蓝袍先生》《四妹子》《白鹿原》这些作品塑造农民的基本方法,这种叙事使陈忠实笔下的农民摆脱了早期农民形象身上那种显见的阶级性和时代性。纯粹的农民从《白鹿原》中整体撤退了,由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农民构造“农民世界”不再是陈忠实的兴奋点,共享宗法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农民成为新的叙事法则。实际上,不仅是农民,白鹿村作为宗法共同体的首领、执行者,甚至其他阶层,都受这种文化力量的主宰和共同体秩序的阉割,白鹿原中的个体大多属于依附性或残缺性人格。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如何处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如何让个体从一种被束缚、被依附,走向一种现代人格,成为现代化的一种内在诉求。正是在这个层面,《白鹿原》提供了关于乡土中国未经现代化的前现代社会形态和人格图景,乡土中国如何走出白鹿村这样的“宗法共同体”,并警惕白嘉轩这样的文化幽灵在当代借尸还魂,成为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