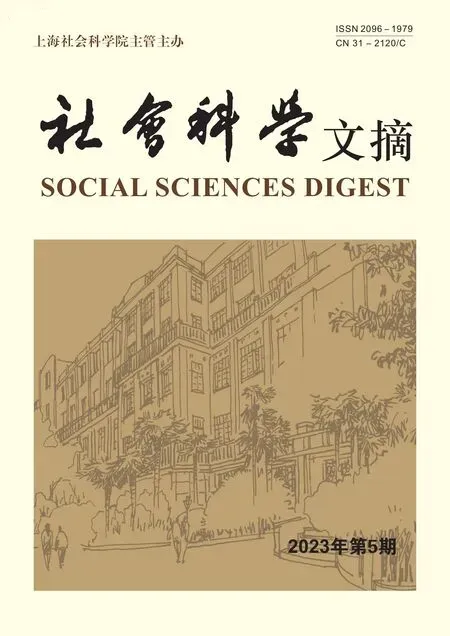流散文学溯源及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范式
文/徐彬
流散文学的创作传统可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著名作家索福克勒斯、西塞罗、荷马、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散文、诗歌和戏剧创作。尽管他们并未使用“流散”而使用了“流放”一词,但根据流散问题研究专家哈齐格·托劳廉等人的定义,可以发现“流放”属于“流散”的范畴。以伊壁鸠鲁和第欧根尼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均对古希腊流散/流放现象做过哲学和文学阐释。
“流散文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方式。狭义上讲的“流散文学”指具有流散经历的作家创作的、与其流散经历密切相关的文学作品,如俄裔流散作家阿列克赛·阿恰伊尔广为人知的诗歌《在各个移居国里》、英国流散作家多丽丝·莱辛的小说《野草在歌唱》、加勒比流散作家乔治·拉明的自传和批评文集《流放的快乐》等。广义上讲的“流散文学”对应的是以流散为叙事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蕴含“作家本人对流散思想与价值观的阐发”,作家本人并不一定具有流散经历。广义层面上的流散文学可将《圣经》、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英国史诗《贝奥武夫》、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等大量文学作品纳入其中。
“流散文学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已是显性表达。流散文学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一词既有对族群、种族、民族国家等的狭义指涉,又有对“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跨种族、跨文化、跨国界的全世界人民的广义指代。以此为依据,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为有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两种类型。尽管流散文学中所描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多属于有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畴,却也隐含着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流散文学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是由流散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统一(尽管有时这种团结统一只是殖民政治文化宣传的产物)和超越文化、种族、民族国家边界的交流与合作。流散文学作品中在经历创伤和灾难后的流散者身上更为明显地展现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类的“生本能”,表现为流散者个体和集体的“失而复得”的快乐和扩张欲的满足,这也可被理解为流散文学中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家园的“失而复得”和作为故乡或故国替代物的异托邦投射是理解流散文学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关键之所在。殷企平教授曾写道:“大凡优秀的文学家和批评家,都有一种‘共同体冲动’,即憧憬未来的美好社会,一种超越亲缘和地域的、有机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流散文学作家也不例外,蕴含于流散文学作品中的“共同体冲动”表现为作家本人对不同类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与构建。
尽管因不同国家地区的人的价值观不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尚无法达成,但并不能否定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与生俱来的追求。流散文学中所描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失乐园与复乐园叙事模式下神命“建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二是殖民文化生产构建的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三是以修复创伤和解除灾难为旨归构建的跨界命运共同体。上述流散文学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式之间有时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重合。简言之,流散文学不仅仅是讲述流散者由于某种原因离开家园,移居或暂居异国他乡的文学,更是在阐释人类流散如何影响全球政治文化格局与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基础上想象和构建特定类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
“神命”与流散建国者命运共同体
以《圣经》和《埃涅阿斯纪》为代表的早期西方经典流散文学作品展现出“神命”与人类流散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人因违背神的意志而被迫流散,人只有在神的指引下才能到达被称为应许之地的流散目的地。《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遭到神(耶和华)的放逐而被迫离开伊甸园的故事和耶稣将带领人类回归乐园的宣称构成西方经典流散文学作品中“失乐园”与“复乐园”的叙事原型。
西方经典流散文学作品将人类流散的历史事实进行艺术加工,将其描写为“神命”的结果。“神命”为流散者提供了心理安慰和重建家园的信心,如罗伯特·加兰所写:对古希腊人来说流散并无贬义而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古希腊人之所以敢于流散得益于文化和宗教传统赋予他们的心理力量,“移民、放逐者和逃亡者等始终相信他们世代坚守的神会保护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到达定居地”。西方经典流散文学作品中的“神命”揭示了人类流散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内含对道德禁忌与民族国家(城邦是其早期表现形式)构想的抒发和与之相对应的文化模式的散播。神命“建国”流散文化模式的精神信仰甚至超过流散建国或“复国”的实际行动本身的重要性。
“巴别塔”神话中有关上帝对人类流散惩罚的描写并非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否定,而是出于维护上帝的权威和惩戒人类物欲的目的。《圣经》中犹太人的应许之地“迦南”可被视为“巴别塔”之后人类流散过程中重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望的文学表达,内含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构”到“人类流散行动/事件”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构”的逻辑关系。
在17和18世纪民族国家概念尚未形成之前,部族和城邦的文化与伦理道德是西方流散文学创作的主旨思想。古希腊、古罗马流散文学中对英雄主义行为和悲剧英雄故事的描写皆围绕部族和城邦共同体的建立和巩固等主题展开。英雄主人公超越了主体欲望(如权力欲、控制欲、享乐欲和情欲等)的限制,确立并维护了以部族和城邦共同体为核心的政治伦理秩序。
虽然流散文学中“神命”建国的流散文化模式自古至今普遍存在,并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文本参照,如美国独立和以色列建国,但并非颠破不灭的真理。美国犹太流亡作家艾萨克·辛格在短篇小说《从美国回来的儿子》中描写了犹太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地方兼全球的双重属性。《圣经》中犹太人前往耶和华指定的应许之地的流散“复国”文化模式被替换成犹太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主义伦理道德模式,其核心思想是信仰所至,四海为家。由此可见,辛格并没打算将《圣经》中犹太人在神的指引下和在“摩西十诫”的规约下前往应许之地建立家园的故事视为可被实践的寓言,转而将其改写为犹太流散者建立精神家园的神话,“摩西十诫”和“应许之地”是贯穿其中的道德指针。
殖民文化生产与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
截至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系统阐释流散文学创作与帝国殖民扩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英国为例,不难发现文艺复兴时期涉及流散主题的英国文学创作已开始致力于描绘大英帝国的未来图景。英国流散文学中一个又一个高大、鲜活的英雄形象激发和指引着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流散至大英帝国殖民地,为殖民地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是殖民文化生产中虚构的共同体,是英国政客和文人,其中不乏桂冠诗人(如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鲁德亚德·吉卜林),共同建造的殖民主义“巴别塔”。完美的绅士、浪漫的爱情、大力神和尤利西斯的海外征服、白手起家的中产阶级神话、高尚的戍边将士和帝国淑女,是英国作家笔下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组成成员和要素。上述帝国流散者的光辉形象被潜移默化地编织到英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使其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中可以学习、借鉴和模仿的榜样。
英国文学文化圈构建和美化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远超三个世纪。虽历史悠久,但这一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组成范式几乎从未改变。首先,进行流散文学主题创作的英国作家数量众多,虽然彼此之间并无密切的个人交往,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却将他们跨时空地联系在一起,并使其创作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其间没有前驱作家对后继作家影响的焦虑,只有彼此之间连绵不断地薪火相承。其次,此类作家将帝国意志拟人化,作品中的流散主人公是帝国意志的载体;由此产生一系列高大、美好和神圣化了的大英帝国流散者形象,这些形象历时性和共时性地聚合在一起勾画出一幅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精神内核的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谱系图。流散者对帝国事业的贡献、个人财富的获得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是内含于该谱系图中的核心思想。
上述被美化了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并非铁板一块。约瑟夫·康拉德的流散文学创作祛魅和解构了前驱作家合力美化了的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揭穿了英国人向殖民地移民前途命运一片大好的美丽谎言。
创伤、灾难与跨界命运共同体
流散文学中具有不同种族、文化和国籍身份的流散者,流散者与非流散者对同一创伤、灾难的相同或相似认识与经历使其产生情感与道德上的共鸣。他们彼此之间休戚与共构成跨种族、跨文化和超越国家政治地理疆界的命运共同体,简称跨界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成员的种族、文化与国籍身份差异变得不再重要,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和向善而生是这一跨界命运共同体的组织原则。流散作家坚守源出地(故乡或故国)的文学文化传统,身在天涯心系故土,经历政治危机和遭受流散创伤却仍致力于构建带有鲜明民族文化倾向的跨界命运共同体。
超越国家政治地理和种族文化边界的跨界命运共同体叙事在具有一定规模的族裔流散文学(如俄裔/国流散文学和华人流散文学)中有所体现。首先,将族裔流散者凝聚在一起的外因是族裔流散者遭遇的创伤性经验或灾难性事件,内因是族裔流散者的民族/种族文化归属。其次,族裔流散文学中的跨界命运共同体有两个跨界指向:(一)流散者在与本土居民和合共生的基础上,实现对源出国文化和所到国文化的双向融合;(二)流散者将自身和所在国利益与故国/乡的民族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现当代俄裔/国流散文学中的跨界命运共同体主要表现为跨界指向中的第一个,其跨界命运共同体叙事可被归纳为三种类型。(一)十月革命之前的“屠格涅夫式”流散创作模式,该模式是十月革命后为数众多的俄裔/国流散作家所遵循的创作典范。战争经历和被迫流散的悲惨经验和精神创伤并未减弱作家本人的思乡之情,与之相反,乡愁与怀旧却激发出作家本人文学创作中对“俄国性”和俄罗斯精神的赞扬。他们为“回国”而进行流散文学创作即是“回国”的旅程。(二)流放的快感与神圣使命相结合的“伊万诺夫”模式。部分俄裔/国流散作家对新政权充满敌意,认为被流放意味着个人自由。然而,在享受流放的快感的同时他们并未放弃作为俄裔/国流散作家的使命,如从宗教视角出发,伊万诺夫重新定义了“流亡者”的概念,认为流亡者的迁移肩负将东西方基督教的分支统一在一起的神圣使命。(三)俄国文学的译介与跨语言、跨文化创作是十月革命后俄裔/国流散文学的第三种模式。解构欧洲现代性、促进欧洲与俄国哲学思想的融合和构建俄裔流散艺术家的共同体是这一模式的核心所在。
20世纪东南亚华人流散文学中的跨界命运共同体主要表现为跨界指向中的第二个。东南亚华人流散文学创作凸显了中华文化在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凝聚作用。以20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和东南亚反华排华运动等灾难性历史事件为背景,东南亚华人流散文学创作涉及文化改良、抗日救亡、多元文化和“精神原乡”等主题,展现出中华文明超越时空、跨越国度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对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类共同价值作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东南亚华人流散文学中所描写的跨界命运共同体主要有两种,分别是新文化运动与抗日救亡命运共同体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命运共同体。新文化运动与抗日救亡是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人流散文学的主题。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初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蔡元培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传播至东南亚,成为流散东南亚的华人作家创作的主题。在小说、诗歌和散文等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东南亚华人作家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上凸显出“中国中心性”(China centeredness)。身在东南亚,心系祖国是该时期东南亚华人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
结语
人类流散是亘古不变的事实,当今世界以移民、难民和跨地区、跨国劳动力流动为表征的人类流散仍在继续。种族文化基因和传统习俗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散播与人类流散相伴而生。流散文学忠实地记录了与人类流散相伴而生的政治文化与伦理道德观的散播、冲突与融合。流散文学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基本范式相对全面地反映出人类流散过程中普世的政治文化与伦理道德追求。三个基本范式既是显性的过去时存在,又为勾划未来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依据。在满足个人和共同体欲求的同时,流散行动/事件形塑了不同类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至今日,人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依旧清晰可辨,人类利益之争、武装冲突和种族歧视仍在继续。流散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旨在追根溯源揭示因人类流散而产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初样态及其演变范式,打破人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的思维模式,阐释流散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作用,以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贡献学术智慧。